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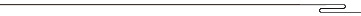
立宪派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支中间派的力量,海外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居住国内的代表人物有张謇、汤寿潜、汤化龙、孙洪伊等。这些中间派在政治大变动中所持的态度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有着明显的两重性,各人的情况和各个时期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用简单的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来作出评断。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先后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刊物,其中影响更大的是前两种。康、梁两人的思想又有差别。后来,梁启超的影响大大超过康有为。
《清议报》创刊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办了一年。他们的政治主张集中到一点,就是“尊皇”。梁启超在《尊皇论》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他把光绪皇帝描写成千古以来未有的圣主,中国的安危存亡都寄托在他一人身上:“今日之变,为数千年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
 这自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幻想,会对人们起着误导作用。从这点出发,他们把慈禧太后准备废立这件事看作时局的关键,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字来论述这个问题,同时猛烈地反对革命,抵制革命。
这自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幻想,会对人们起着误导作用。从这点出发,他们把慈禧太后准备废立这件事看作时局的关键,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字来论述这个问题,同时猛烈地反对革命,抵制革命。
但他们的言论也有着积极的内容:第一,更深刻地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局势。他们这时避居海外,接触到大量西书西报,对世界全局的形势有了比在国内时更清楚的了解,所以,他们对“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和“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这两方面的认识和宣传,显然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第二,进一步宣传了“民权”思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提出了“国民”这个概念。梁启超写道:“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因此,爱国首先要从兴民权开始。他们还把“国民”同“奴隶”鲜明地对立起来,作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宣传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处处以“国民”自许,反对形形色色的“奴隶”道德。第三,鼓吹破除传统思想的束缚,鼓舞人们前进的信念。梁启超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文章,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因此,爱国首先要从兴民权开始。他们还把“国民”同“奴隶”鲜明地对立起来,作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宣传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处处以“国民”自许,反对形形色色的“奴隶”道德。第三,鼓吹破除传统思想的束缚,鼓舞人们前进的信念。梁启超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文章,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新民丛报》的影响大大超过《清议报》。其中,占着显著地位、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这篇文章,从《新民丛报》第一号起,长篇连载,是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字。文章在《叙论》中就提出一个问题:地球万国,有的兴,有的亡,有的强,有的弱,是什么原因?他回答:一切由国民自己文明程度的高低所决定。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在接下去的“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写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什么是“新民”?文章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
 他接着列举中国国民所当自新的纲目,包括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等等。
他接着列举中国国民所当自新的纲目,包括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等等。
怎样评价《新民说》这篇在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呢?它也是有两重性的。这篇文章着重论证:中国所以衰败,主要不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屈服,而是由于国民自身的“衰弱、堕落”。因此,中国人要使国家富强,就不应该去责备清政府,倒是应该责备自己,不应当起来革清政府的命,倒是应该革自己的命。“责望于贤君相者深,则自责望者必浅,而此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
 在当时国家命运处于千钧一发、革命思潮高涨的严峻时刻,这种主张不只是缓不济急,而且本末倒置。但另一方面,它比较系统地宣传爱国思想、社会公德、个人权利思想、个人责任心、积极进取等西方近代道德观念,批判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又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当时国内还有不少比较闭塞落后的地区,《新民丛报》比革命书刊容易进入这些地区,使一些原来受封建思想禁锢较严的知识分子得以接触一些新的知识,打开了眼界。《新民说》在这方面所起的启蒙作用,应该给以足够的肯定。
在当时国家命运处于千钧一发、革命思潮高涨的严峻时刻,这种主张不只是缓不济急,而且本末倒置。但另一方面,它比较系统地宣传爱国思想、社会公德、个人权利思想、个人责任心、积极进取等西方近代道德观念,批判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又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当时国内还有不少比较闭塞落后的地区,《新民丛报》比革命书刊容易进入这些地区,使一些原来受封建思想禁锢较严的知识分子得以接触一些新的知识,打开了眼界。《新民说》在这方面所起的启蒙作用,应该给以足够的肯定。
《新民丛报》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其中包括梁启超所写的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康德、意大利建国三杰等人的学说和传记,《泰西学术思想变化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欧洲地理大势论》等论文。他还努力用这些西方近代学说来分析解释中国的历史,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化之大势》《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国地理大势论》等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最早可能就是出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倡新小说、新史学。他所写的长篇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大体上是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这些,也都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但总起来看,当革命运动高涨后,《新民丛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对革命,受到《民报》等的猛烈批驳,这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批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排除这些激烈反对革命的言论,就不可能有短短几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也不可能结束在中国统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那正是当时中国社会进步最迫切需要的前提。在这个关系近代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上,梁启超的主张是错误的。
再来看国内的立宪派。他们最重要的活动是发动了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当清政府在一九〇六年九月宣布预备立宪、九年后召开国会后,国内的立宪派十分兴奋,在当年十二月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推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第二年,开始推动请愿早开国会活动,但在清政府弹压下又暂时低沉下去。
一九〇八年的八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离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前两个多月,清政府公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制定“宪法”的准备。接着,宣布将在第九年再颁布钦定宪法,实行宪政(有些人把二〇〇八年称为中国宪政百周年,实在是没有认真查历史而闹的笑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读那个《钦定宪法大纲》就清楚了。它的第一条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它规定: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握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不得干预”。
 《民报》上说得很痛快:“其所以悬预备立宪之招牌者,不过欲假此名义,增爱新觉罗氏万世一系、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君权至尊无限之三大条于钦定宪法上,以巩固其万年无道之基而已。”
《民报》上说得很痛快:“其所以悬预备立宪之招牌者,不过欲假此名义,增爱新觉罗氏万世一系、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君权至尊无限之三大条于钦定宪法上,以巩固其万年无道之基而已。”
 名实之不相符,有如是者。它在中国历史上只留下一个笑柄,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名实之不相符,有如是者。它在中国历史上只留下一个笑柄,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一九〇九年,各省咨议局成立,在十月十四日开幕。议员中得有功名、曾任清朝官职的士绅最多,从事教育与商业者次之,新式学堂毕业生又次之。立宪派人士虽不占多数,但由于他们具有法政方面的新知识,活动能量大,最为活跃,在咨议局中起着左右局面的作用。不少立宪派重要人士如张謇等担任了议长或副议长,便于他们以咨议局为合法基地,开展立宪派的政治活动。
清政府设立咨议局时,只是想用它来装点门面,它所通过的决议必须经过本省督抚的“裁夺”,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但议员们有了这样一个舆论阵地,便可以用来抨击地方弊政,提出一些发展工农业生产、兴办教育等主张,同地方官吏之间发生不少争执,对打破专制局面、活跃民主空气多少起了作用。
正是在各省咨议局成立后不久,立宪派在国内先后掀起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第一次是由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带头发动的。他发起成立咨议局联合会,并邀请各省咨议局派代表齐集上海,共同商讨促清政府速开国会的事情。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六省代表五十多人到达上海,推定进京的请愿代表团。临行时,张謇设宴送行,并致辞说:
我中国神明之胄,而士大夫习于礼教之风,但深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

请愿代表由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领衔到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在一年内召开国会。但清政府以“预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借口,加以拒绝。
第二次是一九一〇年六月间举行的,入京请愿代表一百五十多人,除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商会、教育会、华侨等代表,号称代表三十万人,上书言辞也比上次更为激烈。但清政府比上次更不客气,申斥代表“谓议院一开,即是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宣布:“定以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并且警告说:“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这无异给请愿立宪的人兜头一盆冷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文章评论说:“国民即好虚名,亦何争此区区数年之岁月?而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
 最后那句很重的话,结果真被他说中了。
最后那句很重的话,结果真被他说中了。
第三次请愿在十月上旬。这时,在立宪派人士看来局势已更危急:在外,日本强行并吞朝鲜,列强纷纷“协以谋我”;在内,民变蜂起,革命风声日紧。他们在上书时写道:“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瓜分之祸,昔犹空言,今将实现”,“伏莽满山,举国儳然,不可终日”。“今则火既然矣,且将燎原矣。举国臣民,顾影汲汲,朝不保夕,非赖皇上威德,亦复何所怙恃。此所以不敢避斧钺之诛,沥心泣血而思上诉者也。”
 这些话把他们那种对国家命运坐卧不宁、焦虑异常的心情,那种仍依恋着“皇上威德”的孤臣孽子之心,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
这些话把他们那种对国家命运坐卧不宁、焦虑异常的心情,那种仍依恋着“皇上威德”的孤臣孽子之心,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请愿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激烈程度上都大大超过前两次。在各地,广泛开展要求速开国会的群众性签名活动。许多省的咨议局议长都前往北京,并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会长,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副会长,孙洪伊为执行长。请愿活动得到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十月七日,代表们向摄政王府呈递请愿书时,前来送行的东北学生中有两人割肉写下血书。尽管请愿的情绪如此激昂,遇到的却依然是冷冰冰的对待。
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对这次请愿活动毕竟不能太小视。十一月三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他们觉得如果再不提前召开国会,将使自己更加孤立,但又深恐答应得太爽快,会造成大权旁落的印象,仿佛朝廷已不能做主了。因此,一定要表示出“此次缩短年限,虽由于臣民之公请,仍出自朝廷之独断”。
 第二天,清廷颁发上谕:“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引者注:即一九一三年)实行开设议院。”接着,就强硬地声称:“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断不使于宪政前途稍有窒碍。”
第二天,清廷颁发上谕:“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引者注:即一九一三年)实行开设议院。”接着,就强硬地声称:“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断不使于宪政前途稍有窒碍。”

第三次请愿仍没有达到即开国会的目的,但软弱的立宪派人士大多感到已无能为力,没有再发动第四次请愿活动。而有些地区(如东北和直隶)的立宪派人仍不罢休。这下清政府就不客气了,在十二月下旬将来京请愿的东北代表强行押送回籍,将倡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要求的直隶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此,立宪派抱着满腔期望来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不得不黯然收场。
请愿早开国会运动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把君主立宪宣扬成为当时救国的唯一良策。仿佛只要国会一开,奇迹就会出现在眼前。他们一再告诫,不许有任何越轨的举动,并且明确地把抵制革命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清政府连这样温和的运动也不能容忍,最后采取了高压政策。事实证明:期待这个政府的恩赐,指望靠什么“清末新政”就能实行根本性的改革,其实无异梦呓。清政府实在做得太绝了,使很多原来维护它的人士也感到寒心。武昌起义后,不少立宪派人士也卷到革命行列中来,不能不说同这种事实的教训有关。许多反动势力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往往出现众叛亲离的大崩盘现象,这也是一个例子。它对辛亥革命无疑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