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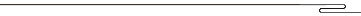
中国要奋起,单靠一股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和勇气远远不够。从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单靠中国社会内部旧有的那些社会力量已经不能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时代已经变了,需要有新的社会力量来担当这个角色,尽管新的社会力量当时还很微弱,还不足以担当起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任务,但终究把中国历史很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种新的社会力量的产生和成长,是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的嬗变而来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是民族工商业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一个是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形成。由此,新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相应地产生出来。
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走的不是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它的主体,不是从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某种程度上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产物。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和自然经济结构的开始崩坏,由于人们逐渐看到新式工业有利可图,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一些原来的买办、商人、官僚、地主开始向新式工业投资。这时,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办的工矿企业还很少,本来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那时社会条件还不很成熟,兴办新式工业又处在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下,它的发展依然很慢。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才接连掀起三次高潮,使局面发生很大变化。
为什么这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受到民族危机激化的刺激。《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制造,引起很大震动。许多人感到发展民族工业已刻不容缓,如果等到外国的企业在中国到处发展后再做,那就晚了。第二,更重要的直接原因是看到这样做可以获得优厚的利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的倾销,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农民的破产,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和劳动力方面的重要条件。如杨宗濂等一八九六年在江苏无锡开办业勤纱厂,虽然日夜开工,仍无法完全满足常州、苏州两府市场的需要,年股息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庚子战后也因为看到吃、穿两种货物在市场上销售状况最好,才投资兴办规模巨大的茂新面粉厂。如果无利可图,任何力量也无法使他们把资金转移到近代工业中来。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这五年间设立的商办厂矿的数字和资本总额,比以往二十多年的总和要大得多。规模大的,如山东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创办资金为一百万元,江苏南通由状元张謇等开设的大生纱厂创办资金也达到七十万元。更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战前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总额中,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一直居于主要地位,而战后五年间商办厂矿的资本额已超过前者而取得主要地位。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第二次高潮是在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一九〇三年以后。它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超过了第一次高潮。商办工厂投资的范围,从原有的缫丝、棉纺织、面粉等几个主要行业,进一步扩大到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妆品等行业,几乎涉及民众日常消费品的方方面面。还出现了一批投资几个行业或拥有较雄厚资金的企业集团,如张謇的大生集团,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经营面粉业、纺织业的茂新集团(以后演变成申新集团)等。
第三次高潮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一年。七年内的投资总额同以往三十多年的总和相等,其中的高峰是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八年。投资的对象,面向国内市场的棉纱、造纸、面粉等行业遥遥领先。发展最迅速、力量最集中的地区是上海、武汉和广州,城市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并且逐步成为国内革命活动和请愿立宪活动的中心。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重点是铁路修筑权,又由于铁路投资能获得优厚的利润,于是,在国内掀起一股筹设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自修铁路的热潮。到一九一一年,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广东粤路公司、浙江铁路公司三家的实收股额已达四千零八十三万元,超过纺织工业四十年投资总额。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辛亥革命前夜保路运动会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为什么四川保路运动能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那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虽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方向,并且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的压迫,有着一定的爱国和民主思想。反映他们利益的《中外日报》在一九〇七年曾写道:“前数年,论时务谋政策者,不曰转弱为强,即曰易危为安,今则无暇为此门面语,直当曰:救死而已矣,救亡而已矣。”
 这段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可是,他们也有严重的弱点:中国民族工业在全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毕竟很小。它的上层大多从地主转化而来,往往同时还保有不少田产,同官府也有相当关系,因而有着浓重的封建性,基本上采取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态度,害怕革命的发展。一般中小工商业者由于力量微弱,常有身家性命和财产保障等重重顾虑,长时间内不敢采用激烈的手段来争取在中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这和法国大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显然不同。于是,领导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本来应由他们承担的历史责任,却更多地由刚刚形成的受过近代教育、能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群挑起来了。
这段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可是,他们也有严重的弱点:中国民族工业在全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毕竟很小。它的上层大多从地主转化而来,往往同时还保有不少田产,同官府也有相当关系,因而有着浓重的封建性,基本上采取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态度,害怕革命的发展。一般中小工商业者由于力量微弱,常有身家性命和财产保障等重重顾虑,长时间内不敢采用激烈的手段来争取在中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这和法国大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显然不同。于是,领导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本来应由他们承担的历史责任,却更多地由刚刚形成的受过近代教育、能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群挑起来了。
随着外国和本国企业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形成了。他们遭受压迫的严重和残酷是少见的:每天劳动时间一般在十二小时以上,劳动强度大,人身安全根本没有保障,工资收入极为低微,而且常受失业的威胁。他们进行过不少反抗,但总的说来,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生活很不安定,只是被人贱视的“苦力”,在参加革命和其他活动时只是作为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很晚。甲午战争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仍是那种旧式的封建士大夫。他们日夜孜孜攻读的还是古老的“圣贤之书”,以为这才是“大道”所在,也是他们在社会上赖以晋升的唯一途径。对绝大多数士大夫来说,除这些东西以外,确实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可以称作学问。梁启超回忆他早年的情景说:“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
 谭嗣同承认,他三十以前所学的都是“旧学”,三十以后所学的是“新学”他那个“三十”之年,就是甲午战争那一年。再如章太炎,甲午战前还是埋头在杭州诂经精舍的故纸堆里,并没有过问多少时事。此后思想激进如谭嗣同、章太炎那样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
谭嗣同承认,他三十以前所学的都是“旧学”,三十以后所学的是“新学”他那个“三十”之年,就是甲午战争那一年。再如章太炎,甲午战前还是埋头在杭州诂经精舍的故纸堆里,并没有过问多少时事。此后思想激进如谭嗣同、章太炎那样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
尽管那时也有很少数人已在提倡研究商务、工矿、铁路、海军等问题。但一般士大夫即便表示赞同,仍不把它看作自己的事情,不屑认真去学这些东西,说这“有同文馆、水师学堂诸生徒在”。
 而那些“生徒”是被一般读书人看不起的。福州船政学堂出身、后又留学英国的严复,因为不是从科举的“正途”出身,就长期遭受歧视,以致他有“当年误习旁行书(引者注:指英文),举世相视如髦蛮”之叹。
而那些“生徒”是被一般读书人看不起的。福州船政学堂出身、后又留学英国的严复,因为不是从科举的“正途”出身,就长期遭受歧视,以致他有“当年误习旁行书(引者注:指英文),举世相视如髦蛮”之叹。

在十九世纪末叶,可以说,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力量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二十世纪初,这种状况有了改变。发生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一是大批年轻的读书人出国留学;二是在国内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三是西方近代文化通过各种书刊的出版在社会上得到较广泛的传播。这个变化过程的特点是:先有大批年轻人出国留学,而后又有力地带动了后面这两个变化。
出国留学者在一九〇〇年以前为数很少,归国后一般也不得其用。二十世纪初年却陡然增加。以当时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日本来说,一八九六年才开始有,一九〇〇年以前还不到一百人,一九〇三年初已有九百人,到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更激增到八千多人(有的记载说有两万人,可能是高估了)。留欧美的学生还比较少,但比过去也有增加。
留学生人数激增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严重的民族危机使许多人产生一种认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游学外洋”,特别是近邻日本,便成为学外国的终南捷径。一九〇三年留日的吴玉章有一首诗:“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
 很可以看出很多人出国时的心情。第二,清政府废科举,奖励游学,以功名为诱,也推动不少人出洋游学。他们认为:“向之极可慕恋之科举的虚荣者,今已为蕉梦矣。而出洋学成,量与出身,已见明谕。宦达之路、利禄之路、学问之路、名誉之路,胥于是乎在。”
很可以看出很多人出国时的心情。第二,清政府废科举,奖励游学,以功名为诱,也推动不少人出洋游学。他们认为:“向之极可慕恋之科举的虚荣者,今已为蕉梦矣。而出洋学成,量与出身,已见明谕。宦达之路、利禄之路、学问之路、名誉之路,胥于是乎在。”
 派遣或奖励留学是清末“新政”的一项内容,可是在出洋留学后,不少人的思想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转向反对清政府,这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
派遣或奖励留学是清末“新政”的一项内容,可是在出洋留学后,不少人的思想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转向反对清政府,这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
国内废科举后兴办学堂,也是一件大事。一九〇九年,全国中学堂已有四百六十所,中学生四万四百六十八人;小学堂五万一千六百七十八所,小学生一百五十二万二千七百四十六人。
 这些学堂的教育内容,其实并不全是新式的,读经等课程仍占着很大比重,教师大多还是旧式的士大夫,许多人把入学看得同过去的科举应试差不多;但它和过去终究有了许多不同,学堂里开设了中外历史、地理、格致(物理)、算术、外国语等课程,高等文法学堂更开设了介绍西方社会学说的课程。留日学生中,数量最多的是师范速成生,回国后就在这些学堂中任教,带来不少新的思想和习尚。学堂中的风气同过去的书院很不相同,从这里也培养出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
这些学堂的教育内容,其实并不全是新式的,读经等课程仍占着很大比重,教师大多还是旧式的士大夫,许多人把入学看得同过去的科举应试差不多;但它和过去终究有了许多不同,学堂里开设了中外历史、地理、格致(物理)、算术、外国语等课程,高等文法学堂更开设了介绍西方社会学说的课程。留日学生中,数量最多的是师范速成生,回国后就在这些学堂中任教,带来不少新的思想和习尚。学堂中的风气同过去的书院很不相同,从这里也培养出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
此外,介绍欧洲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的著作、教科书、小说等这时陆续翻译出版。在一九〇〇年以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及外国历史著作译成中文的只有六十多种,小说只有三种。读的人很少。到一九〇四年,前者增加到二百五十多种,后者也增加到二十多种。它们大多是由留日学生从日译本转译的,但也有直接从欧洲翻译过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严复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间陆续翻译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前三册、约翰·穆勒的《名学》上半部。这些外国著作与教科书的翻译、出版和流传,产生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不逊于学校教育,也在国内逐渐培育出一批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一批“新派”的人。一九〇二年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忆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他们和旧式士大夫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他们和旧式士大夫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有了比较多的世界知识,知道如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有更深切的体会,爱国思想更加强烈。李达回忆自己一九〇五年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时的情景说:
十五岁的时候,我考入一所享受公费待遇的中学,并开始接触一些新的知识,逐渐知道一些国家大事。如从看地图中,知道过去常常谈论的“洋鬼子”国家就是英、美、德、法、意、日、俄、奥等国,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清廷的媚外……开始有了一点爱国观念,知道爱国了。

第二,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些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理想、新的衡量是非的尺度。当时,中国人民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民族独立和民主。在他们看来,美国的独立和法国的革命仿佛最出色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于是,法国和美国便代替戊戌变法时的俄国和日本,成为不少人心目中追求的榜样。十八岁的邹容在脍炙人口的《革命军》中写道: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上。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他们的爱国热情是真诚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令人感动,但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似乎只要把他们如醉如痴地从外国书本上读到的那些新观念、新方案照搬过来,中国土地上的百病都会霍然而愈,令人困扰的种种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这是缺乏实际社会经验的知识分子的幻想。但在当时,这种信念以及华盛顿、拿破仑等的榜样,确实有力地激励着他们中许多人,愿意为实现这些新的理想而奋斗。
第三,他们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对前途满怀着信心,总觉得自己比一般民众懂得更多,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许多人的家庭正在破产没落,自己也遭受着失业和找不到出路的威胁。这些人大多有些个人抱负。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慨和不满,容易引起他们反抗的情绪。许多人在形势发展和革命宣传的推动下,容易积极投身到革命行动中去。
如果没有二十世纪初十来年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的这种大变动,辛亥革命是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