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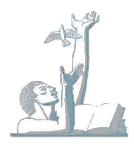
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值得过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余的,如世界是否是三维的,精神是否有九个或十二个等级,都在其次。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事。但首先必须回答。假使果然如尼采所愿,一个哲学家为了受人尊敬应该以身作则,
 那么,人们就理解了这一回答的重要性,因为它后面就是决定性的行动了。这是心灵容易感觉到的明显的事情,但是还应加以深化,使之在人们的思想里清晰起来。
那么,人们就理解了这一回答的重要性,因为它后面就是决定性的行动了。这是心灵容易感觉到的明显的事情,但是还应加以深化,使之在人们的思想里清晰起来。
假如有人问,根据什么判断某个问题比另一个问题更为紧迫,我的回答是,根据它所采取的行动。我从未见过一个人为了本体论的理由而死。伽利略掌握了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当这个真理使他有生命之虞的时候,他就最轻松不过地放弃了它。在某种意义上,他做对了。这个真理能值几文,连火刑使用的柴堆都不如。地球和太阳谁围绕着谁转,从根本上说是无关紧要的。说到底,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相反,我看见许多人死了,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生不值得过下去。我也看到另外一些人为了那些本应使他活下去的思想或幻想而反常地自杀了(人们称之为生的理由同时也是绝好的死的理由)。我由此断定,人生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呢?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我指的是驱人去死的问题或者十倍地增强生之激情的问题,大概只有两种思想的方式,一种是拉帕利斯
 的,一种是堂吉诃德的。唯有事实和抒情之间的平衡才能使我们同时得到感动和明晰。在一个既平常又哀婉动人的主题中,可以想象,深奥的、古典的论证应该让位于一种同时出自常理和同情的更为谦逊的精神姿态。
的,一种是堂吉诃德的。唯有事实和抒情之间的平衡才能使我们同时得到感动和明晰。在一个既平常又哀婉动人的主题中,可以想象,深奥的、古典的论证应该让位于一种同时出自常理和同情的更为谦逊的精神姿态。
人们从来只是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处理。这里正相反,问题首先在于个人的思想和自杀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行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的沉寂中酝酿着的。当事人并不知道。一天晚上,他开枪了,或者投水了。一个房屋管理人自杀了,一天有人对我说,他失去女儿已有五年,从那以后他变得厉害,此事“毁了他”。再没有比这更确切的词了。开始想,就是开始被毁。对如此开始的阶段,社会是没有多大干系的。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应该到那儿去寻找它。这是一次死亡游戏,从清醒地面对生存发展到逃避光明,都应该跟随它,理解它。
一起自杀有多种原因,一般说来,最明显的原因并不是最起作用的原因。人很少(但不排除假设)经过考虑而自杀。触发危机的东西几乎总是无法核实的。报纸常说“隐忧”或“不治之症”。这些解释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应该知道自杀者的朋友那天跟他说话时的口气是否无动于衷。此君正是罪人。因为这足以加速还处于悬而未决状态的一切怨恨和厌倦
 而走上绝路。
而走上绝路。
但是,如果说确定准确的时间、确定精神把赌注押在死亡上的细微动作是困难的话,那么,看到行动本身所意味着的后果就不那么难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如同在情节剧中一样,自杀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所超越或者他并不理解生活。让我们不要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常用的词上来吧。那只是招认“不值得活下去了”。当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人们不断地做出存在所要求的举动,这是为了许多原因,其中第一条就是习惯。自愿的死亡意味着承认,甚至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可笑性,承认活着没有任何深刻的理由,承认每日的骚动之无理性和痛苦之无益。
究竟是什么难以估量的情感使精神失去了其生存所必需的睡眠呢?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所有健康的人都想过他们的自杀,无须更多的解释,人们便可承认,在这种感情和对虚无的向往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
本文的主题正是荒诞和自杀之间的这种关系,自杀作为荒诞的一种解决的确切手段。原则上可以确定,对一个遵守常规的人来说,他信以为真的东西应该支配他的行动。因而相信生存荒诞的人就应该以此来左右他的行为了。明确地、不动虚假的悲怆感情地自问这一现实问题的结果是否要求人们尽快摆脱一种不可理解的状况,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好奇心。当然,我这里说的是那些打算和自己取得一致的人。
这个问题用明确的语言提出来,可以显得既简单而又难以解决。但是,简单的问题带来同样简单的回答,明显导致明显,这样的假设却是错误的。首先并且把问题的措辞颠倒一下,如同人自杀或不自杀,似乎只有两种哲学的解决办法,一种是“是”,一种是“否”。那就太妙了。但是还应考虑到那个总提问、却没有结论的人。这里我只略带点讥讽味道,因为他们是大多数。我也看见有些人嘴上说“否”,行动起来却好像心里想的是“是”一样。事实上,如果我接受尼采的标准,
 他们这样想也好,那样想也好,想的的确是“是”。相反,自杀者却常常是确信生活意义的人。这种矛盾是经常的。甚至可以说,矛盾从来也没有像在相反的逻辑看来如此令人向往的时候那样尖锐。比较哲学的理论和宣扬这些理论者的行为,这是老一套了。但是必须指出,在所有拒绝给予人生一种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属于文学的基里洛夫、
他们这样想也好,那样想也好,想的的确是“是”。相反,自杀者却常常是确信生活意义的人。这种矛盾是经常的。甚至可以说,矛盾从来也没有像在相反的逻辑看来如此令人向往的时候那样尖锐。比较哲学的理论和宣扬这些理论者的行为,这是老一套了。但是必须指出,在所有拒绝给予人生一种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属于文学的基里洛夫、
 出自传说
出自传说
 的波勒格里诺、
的波勒格里诺、
 处于假说范围之中的儒勒·勒基埃
处于假说范围之中的儒勒·勒基埃
 之外,没有人同意他的逻辑直至否定人生。人们常常为了取笑而提到叔本华在丰盛的餐桌前赞颂自杀。此举毫无可笑之处。这种不把悲剧当回事的方式不那么严肃,但是它最终对当事人做出了判断。
之外,没有人同意他的逻辑直至否定人生。人们常常为了取笑而提到叔本华在丰盛的餐桌前赞颂自杀。此举毫无可笑之处。这种不把悲剧当回事的方式不那么严肃,但是它最终对当事人做出了判断。
面对这些矛盾和难解之处,难道应该认为在人对生活可能具有的看法和他为离弃生活所做出的举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吗?在这方面我们不要有任何夸张。在一个人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苦难都更强大的东西。肉体的判断并不亚于精神的判断,而肉体在毁灭面前是要后退的。我们先得到活着的习惯,然后才获得思想的习惯。在我们朝着死亡的一日快似一日的奔跑中,肉体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总之,这个矛盾的本质存在于我称之为躲闪的东西之中,因为这种躲闪既比帕斯卡所说的移开少点什么,又比他所说的移开多点什么。致命的躲闪形成本文的第三个主题,即希望。对另一种“值得生存”的生活的希望,或对那些活着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以致超越生活并使之理想化的人的弄虚作假,它们都给予了生活一种意义,并且也背叛了生活。
这样,什么都把问题弄得复杂了。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在玩弄辞藻,装作相信拒绝赋予人生一种意义势必导致宣布人生不值得过,而且这也并非徒劳。事实上,这两种判断之间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尺度。只是应该不要被上述的混乱、不一致和不合逻辑引入歧途。必须排除一切,直奔真正的问题。人自杀,因为人生不值得过,这无疑是一个真理,不过这真理是贫乏的,因为它是一种自明之理。然而,这种加于存在的凌辱,这种存在被投入其中的失望,是否来自存在的毫无意义呢?它的荒诞一定要求人们通过希望或者自杀来逃避它吗?这是在排除其余的一切的同时需要揭示、探究和阐明的。荒诞是否要求死亡,应该在一切思想方法和一切无私精神的作用之外,给予这个问题以优先权。差异、矛盾、“客观的”精神总是善于引入各种问题之中的心理,在这种探索和这种激情中都没有位置。其中只需要一种没有理由的思想,即逻辑。这并不容易。合乎逻辑是轻而易举的。但把逻辑贯彻到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死于自己之手的人就是这样沿着他们感情的斜坡一直滚到底的。关于自杀的思考使我有机会提出我感兴趣的唯一问题:有一个一直到死亡的逻辑吗?只是在不带混乱的激情而单凭明显的事实的引导来继续我在这里指明其根源的推理的时候,我才能够知道。这就是我所谓的荒诞的推理。许多人已经开始了。我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坚持。
当卡尔·雅斯贝尔斯
 揭示了使世界成为统一体之不可能时,喊道:“这种限制把我引向自我,在那里,我不再躲在一种我只会表现的客观的观点之后,在那里,自我和他人的存在都不再能成为我的对象了。”
揭示了使世界成为统一体之不可能时,喊道:“这种限制把我引向自我,在那里,我不再躲在一种我只会表现的客观的观点之后,在那里,自我和他人的存在都不再能成为我的对象了。”
 他在许多人之后又让人想起思想已达其边缘的那些荒凉干涸的地方。在许多人之后,大概是这样吧,但有多少急于摆脱困境的人!许多人,而且还是最卑微的人中的许多人都到达过这个思想摇摆的最后的拐弯处。他们于是放弃了他们曾经最为珍贵的生命。另一些人,他们是精神的王子,他们也放弃,但他们进行的却是他们的思想在其最纯粹的反抗中的自杀。相反,真正的努力在于尽可能地坚持,在于仔细考察这遥远国度的怪异的草木。持久性和洞察力是这场荒诞、希望和死亡相互辩驳的不合人情的游戏中享有特权的观众。这个舞蹈既是基本的,又是细腻的,精神可以先分析其形象,然后再阐明之,并且再次亲身体验之。
他在许多人之后又让人想起思想已达其边缘的那些荒凉干涸的地方。在许多人之后,大概是这样吧,但有多少急于摆脱困境的人!许多人,而且还是最卑微的人中的许多人都到达过这个思想摇摆的最后的拐弯处。他们于是放弃了他们曾经最为珍贵的生命。另一些人,他们是精神的王子,他们也放弃,但他们进行的却是他们的思想在其最纯粹的反抗中的自杀。相反,真正的努力在于尽可能地坚持,在于仔细考察这遥远国度的怪异的草木。持久性和洞察力是这场荒诞、希望和死亡相互辩驳的不合人情的游戏中享有特权的观众。这个舞蹈既是基本的,又是细腻的,精神可以先分析其形象,然后再阐明之,并且再次亲身体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