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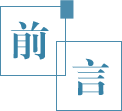
那是2012年的事了。当时我正在撰写一部题为《日本风俗女子》(新潮新书出版)的拙著,日常闲聊中,我和我的责任编辑讲了一些过去的经历,比如采访成人影片女优和风俗小姐,和在看护现场的一些见闻等。当时,这位责任编辑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么看来,原来中村先生一直都在挖掘贫困问题啊。
当时的对话,是我头一次在自己亲历的事情里听到“贫困问题”这个词。
那个时候,虽然我对采访对象的状况、言语、日常接触人群的异常抱有问题意识,却从未想过这会是贫困问题。
用身体去换取金钱的,主要是一些生活在以东京为主的大都市的贫困女性。现在是少子高龄化社会,所以女性从事风俗业和卖身的年龄是没有上限的。
决定承担风险出卖自己身体的女性,基本上都是以提高收入、解决负债偿还等经济问题为大前提的。
然而,因为钱赚得太容易,她们对经济的感觉会失衡,会在名牌或男公关身上大笔消费或者招致一些图谋不轨的男人,从而又陷入其他问题。
她们的故事虽然不是平稳而幸福的,但也充满了传奇的痛快感。
各有难处的女性最终堕入赤身裸体的特殊产业,因为,一旦下定决心堕入这个世界,它不仅能使你脱离贫困,可能还能让你超越中产阶层进入富裕阶层。
简单总结一下我的履历:1990年代中期,我成为自由撰稿人,自那之后的20多年,我一直在对成人影片女优和风俗业进行采访。
大学的时候,我很憧憬当时最受人追捧的职业——杂志撰稿人。而我开始涉足男性成人杂志的相关工作,是因为比起时尚杂志、爱好专题杂志和周刊,它的门槛是最低的。
涉嫌违法的工作,基本不会登载在招聘杂志上。20多年前我读大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同级校友在居酒屋里喝酒,突然有一个穿着打扮十分可疑的人走到我们的座位旁,和我们搭话。
“你们想不想打点零工?姑且,算是媒体的工作吧。”
只有我一个人举起了手。
几天后的一天上午10点,我被叫到了中野站南口。那天和我们搭话的,是个参与过成人影片制作、自己刚开始创办杂志的社长。从车站步行几分钟就是他的家,也是杂志社的办公室,虽然杂志社是在看上去租金不菲的住宅楼里,但一打开玄关门,我就看到了一个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垃圾场。
打开门的一瞬间,就能看见从玄关通往客厅的走廊上堆出好几处1米多高的垃圾山,我们只能踩在各种垃圾上,朝最里面的客厅走,我的四周还飘散着异味。社长习以为常地在垃圾堆间穿行。差不多25平方米的客厅里,有一块没有垃圾、勉强能让人坐下的平地,那就是办公的地方。
我只听说是媒体的工作,结果让我做的事是编写一些文字填充男性成人杂志的版面。我在几乎没有文章撰写经验的情况下,开始了写作。社长说:“成人杂志的文章根本就没人看,所以只需要用日语把版面填满就行,只要内容够色情,你爱写什么写什么。”就这样,类似一般企业OJT
 的过程,仅5秒钟就结束了。
的过程,仅5秒钟就结束了。
我本来对女性和成人杂志都没什么兴趣,也没什么才能。但我把自己随便用文字处理软件敲出来的文章丢给编辑之后,只过了两周左右,就被印成杂志,摆在书店里卖了。甚至有时候还能署上名字,实在是很有意思。于是,由于我干劲儿太足,工作也逐渐多了起来。
为了在风俗资讯杂志和男性成人杂志风俗资讯栏目中刊载的内容而到处寻访风俗店,是每一个男性成人杂志新人写手和编辑的必经之路。在“风营法”
 修订之前的90年代,东京简直到处都是风俗店。尤其是在山手线各站徒步1分钟范围内,几乎每一栋楼里都能闻到一股风俗店特有的消毒液的味道。
修订之前的90年代,东京简直到处都是风俗店。尤其是在山手线各站徒步1分钟范围内,几乎每一栋楼里都能闻到一股风俗店特有的消毒液的味道。
我工作的内容就是电话联系风俗店约好相关事宜,过去给风俗小姐拍照,进行10分钟左右的简单采访,然后离开。像这样,一天能跑好几家。采访风俗小姐时一般就问“敏感带在哪里?”“喜欢什么类型的男性?”之类无关痛痒的问题。风俗小姐不希望男性客人对自己的身体有过多不必要的接触,于是会说“敏感带在背上还有手臂上”。
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几乎都没去上课,也没找工作,毕业后就直接成了自由撰稿人。当时的杂志非常多,工作接踵而至。风俗小姐名鉴,成人影片以及无码影片的评论,胡编乱造的性爱告白,风俗店和可疑地点的潜入采访,成人影片拍摄现场的采访,等等,这些工作我做了个遍,只是当时合作过的杂志,几乎全都停刊了。后来很多出版社也都倒闭了。
男性成人杂志彻底消失了,我的工作几乎都没了,唯一持续到后来的,只有在商业杂志以及网络媒体上刊登的成人影片女优、风俗小姐的长篇访谈。和她们见面,听她们讲述,然后写成稿件,周而复始。到今天为止采访过的女性人数我没有精确计算过,也不是每个人都记得,但不管怎么说,也有1300人以上了。
说实话,采访出卖身体的女性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除了采访技巧之外,和她们的距离感、彼此的立场、自己想要通过她们表达些什么,都很难有确切的答案。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都在试错。
“她们并不是性玩具,而是人”——这是年轻气盛时的我曾经有过的一种单方面的、类似人权意识的感觉。记忆中,我也曾经因个人的价值观而同情过她们。
做成人影片女优也好,做风俗小姐也好,都是将女性自身作为商品,提供性爱影像或性服务的一种商业行为。不管是市场原理还是商品本身,只有适应男性的需求和喜好才是正义,让她们重视自己、否定自己是适应男性需求和喜好的物品,就成了罪恶。
于是,懂得珍惜自己的女性在产业里成了恶人,而与她们的烦恼和痛苦产生共鸣,并将之公之于世的行为也成了恶行,有时还会招致攻击。甚至我单方面同情的女优有时也会因此恼怒于我。
因为她们一旦开始重视自己,不再只把自己当成性玩具,收入就会减少,导致生活无以为继。就算她们本意并非如此,但成为性玩具就能获得足够的经济能力,其中的多数人也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保持精神上的稳定。
然而现实是,赤身裸体的世界是能直接反映日本社会男性优势地位的产业,而身陷其中的大多数女性都因无法维持身心的平衡而非常痛苦。
成人影片业界会在网络上或繁华街道的路边发掘一些有吸金潜力的女性,让她们同意成为脱衣服赚钱的商品,在成人影片拍摄现场拍摄出男性猥琐欲望的最大公约数,然后将这些影像根据法律要求修剪后,再投放到市场上去。成人影片产业就是这样的一种产业。
他们彻底遵从市场原理,让女性承担所有风险,毫不留情,用完就丢,因此成人影片女优后来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大多都是黯淡的。
长期在成人影片业界内部采访让我发现,成人影片业界的实态,其实充斥着违法乱纪,根本没有人权可言。然而,作为当时的业界相关人士,我能做的也只有尽量在不触及高危线的前提下,将事实的一部分写出来,然后传达出去。
如果我以我的立场揭露他们的违法行为,提倡他们毫不关心的女性人权,逼迫他们改善对女性不利的从业环境,即使不被杀死,也得被弄成重伤住院。那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我只能在被他们彻底厌恶、驱赶出业界之前,适可而止。
最终,我找到的答案: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入采访,彻底充当一个旁观者,不培养超越采访的人际关系,在自己不会受到攻击的安全线之内最大限度地采写和传递真实。我不是援助者,而是一个令她们正在面对的现实可视化的采访者。这种意识,我一直贯彻至今。
此外,在采访现场,除去获取信息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提问,我几乎不会主动开口说话,只倾听她们的讲述。不管她们的回答是什么,我都不予以否定。这些女性,不知为何,大多更愿意对不否定她们的对象倾诉。
2000年以后,日本经济开始下滑,各种各样的公共事业兴起,社会福利和非营利组织开始受人瞩目。现在,希望能为别人提供帮助的援助者和他们想要帮助的人何其之多。
和采访一样,援助赤身裸体的女性也非常困难。援助者虽然想要为深陷苦难中的她们提供帮助,但大多数情况是援助者与她们所处的阶层截然不同。一心想要帮助她们,结果却是援助者站在了居高临下的位置上,一边对卖身持否定态度,一边向她们伸出援手。
同时阶层的差异造就了成长环境和文化的差异,两者之间共通的认识极少,彼此缺乏理解,所谓的援助也难免变成了一种单方面的行为。
我虽然也无法全部理解,但身处的阶层与她们是相似的。我想在此表明,我的采访,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援助者的评估和调查,以及如窥视一般的实地调研是不同的。
从她们口中讲出的,是父母无休止的虐待、精神疾病、负债、自残、被人口贩卖等各种各样的残酷经历。而这些经历,我已经专注倾听了将近20年。
在被那位编辑提醒之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做的、对赤身裸体的女性的这些采访,从结果上看,竟成了对“贫困”这一社会问题的一种实地调研。
***
对赤身裸体的女性所作的采访,一直都是围绕东京这个舞台进行的。
虽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项实地调研,但我在2006年到2007年间,渐渐产生了“日本社会是不是出问题了”这种模糊的不安感。
不仅要赤身裸体,自己的性爱影像还要被公开贩卖,虽然背负如此高的风险,但成人影片女优中间出现了“演出费太低,根本就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阶层。
演出费和拍片的数量因竞争的出现而减少,在东京高额房租的压迫下,她们的生活开始变得困窘,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如今已经发展到收入能够维持自己生活的仅为上游的一小部分人。
从2005年左右开始,援助交际和卖身的市价也开始大规模持续下跌。想要出卖身体的女性急剧增加,结果造成了价格的急剧下降。
人们害怕贫穷,害怕没钱,于是,因蓄意坑害他人而引起的争端和犯罪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市场行情急转直下的赤身裸体的世界里,相关人员恐吓其他相关人员的事件频频发生,我实在对此感到厌烦,于是开始经营起了因存在巨大需求而备受瞩目的看护机构。
我原本以为逃到看护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事业里,就可以逃离那些丑陋的争端,没承想,看护的世界却是我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困窘之人的巢窟。
持有“介护福祉士”国家认证资格的专门人士,即使是在行政的监督之下,也只能在每月到手仅14万到16万日元的低回报条件下劳动。“被服务者的感谢就是我们的报酬。我们要对高龄者抱有感恩之心。我们大家应该对能从事如此美好的事业而深感荣幸。”像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口号,居然被当作理所当然的正确理论。
我起初无法理解,为何持有国家认证资格的专业人士提供政府规定的服务,反而要感谢被服务者。但很快我就明白了,这是为了用言语上的洗脑来遮掩相关业务由官办转为民办之后产生的贫富差距和雇用金的下滑。
顺带一提,现场看护工作人员实际的平均年薪不到300万日元,而地方公务员的年薪要多出其一倍有余。将公务剥离出来让民间自营,人力成本就可以压缩一半以上。
大多数看护工作人员都对专门学校和证书培训学校反复强调的“感谢即报酬”的理念深信不疑,过的却是一个月只能去一次家庭餐厅、唯一的乐趣是玩一日元弹子机的生活。
此外,把结婚组建家庭当作一种奢望的思想也十分普遍,虽然不会说出口,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将来,只想着让眼前的高龄老人过得更幸福一点。在极端优待高龄老人的趋势下,黑色劳动悄然蔓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贫困的巢窟。面对看护界的这种彻底轻视年轻世代的体制,我愕然了。
先是置身于与社会隔绝的成人影片和风俗业这类闭塞的灰色营生之中,不断地进行采访;抽身之后又忙于眼前的看护事业,对“派遣解雇”和“跨年派遣村”这类现象冷眼旁观的我终于发现,“日本社会是真的出问题了”。
虐待、精神疾病、负债、自残、人口买卖等残酷的故事,在成人影片女优们的口中竟成了常事。另一方面,看护现场也是一边讴歌感恩之心,一边泛滥着权力欺压、性骚扰、虐待和黑色劳动。将这些不断涌现的不和谐的点之间连成线的,是从小泉纯一郎政权开始正式展开的新自由主义路线。
原本没有被市场化的领域因为管制的放缓和法律的修正而市场化,于是催生了竞争。历来由公务员担任的看护工作最先被当作市场化的对象。为了不让支撑看护现场的职员们意识到自己的贫困,各种各样的洗脑和宣传开始了。我参与的机构就生产出了大量无论现实多么黑暗、永远乐观向上、拿着低工资拼命劳动的员工。
由于可以随时解约,对企业来说更便于管理的雇用很快流行起来,就连自治体也开始积极聘用非正式员工,在如今的女性受雇者中,非正式员工已占据了4成左右。
对于经营者和企业的正式员工来说,富裕的人致富更容易了;而对非正式员工,正常的工作却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于是,贫富差距就此拉开。
日本社会针对贫困的当事人有一种很强的责任自负的认识。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女性身上,究竟发生着什么呢?
***
开始设身处地地思考女性的贫困问题之后,我接到了一个以前认识的女性的电话。之后,她成了和我一起进行采访的编辑。
“啊,好久不见,自从高中毕业以后,有25年没见了吧?我明天要换新的工作了。你知道东洋经济在线吗?”
她和我同龄,是在高中时代认识的。我记得她当时毕业于东京著名的初高中一体的女校,考进了庆应义塾大学,后来进了一家大型演艺事务所工作。
“咱们来开一个连载吧。女性的贫困,现在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吗?”
在杂志接连停刊、出版社接连倒闭的大趋势下,年过40了要想换工作,必须能够马上适应工作岗位才行。而她在构思要提交给总编辑的选题时,忽然想到可以深度挖掘贫困女性的现实,于是查到了我的手机号码,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像你这样从全是富人阶层的大小姐学校毕业,又考进了庆应义塾,后来又混迹丰富多彩的演艺世界的上流阶层人士,要想插手贫困世界的问题可不大现实。”
我告诫她,阶层的差异会在采访现场造成沟通的障碍,彼此不能理解对方的语言,会令采访过程举步维艰。
“啊?你在说什么呢?我可是身处底层中的底层啊,简直无可救药了。庆应中途就退学了,都这个岁数了也从没当过一回正式员工,老公每天都骂我是笨蛋、废物,工资太低存不下来钱,都要走投无路了。还上流阶层,你别开玩笑了。”
她真的很快就让这个选题通过了,东洋经济在线从2016年4月起,开始了《在贫困中呻吟的女性》的连载。这个连载也是本书的起源。
起初我从寻找自己周围的贫困女性开始,后来以居住在东京的女性为中心,与她一起不断地进行关于贫困问题的采访。没想到,她十分顺利地融入了贫困女性群体,丝毫不着痕迹,简直令人惊诧。她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中对贫困女性的痛苦境遇表示出理解和共鸣,使对方没有对彼此阶层的差异感到怀疑。不管对方说了什么,我几乎从没见她表示过否定。她不只是随口说说,而是真的亲身体会过底层的生活。对此我深感佩服。
在这一系列连载中,为了探究女性,特别是单身女性与单身母亲的贫困问题,我们刻意没有做总述,而是将焦点放在了介绍“个人经历”之上。同时,我们随时接收正因贫困问题而深感苦恼的读者的采访申请,并从中筛选采访的对象。
贫困,是在出身和成长经历、家庭环境、健康状态、就业、政策、制度、个人和配偶的性格及人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的。每个人面对的现实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能在详细分析每一个生活案例之后,从中提炼出真相,才能找到。我认为,哪怕多讲述一个贫困的故事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开始了我的采访。
而这本书,就是这3年间的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