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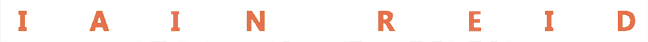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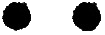
是两盏车头灯——我一睁眼,就看见了灯光。透着诡异,因为灯光赫然发绿,绝非附近一带常见的白色车头灯。透过窗户,我遥遥望见乡间小道尽头的绿色车灯。刚才,我一定是打了个盹:毕竟刚吃完晚餐,再加上傍晚热浪袭来,不知不觉睡过去了吧。我眨眨眼睛,想看清楚些。
没有任何征兆,也毫无道理。从这个位置,我听不见汽车的响动,却一睁眼就发现了绿色车灯,仿佛绿光突然凭空冒了出来,只为把我从恍惚中照醒。这两盏灯比大多数车头灯都亮,从小路尽头的两棵枯树间发出夺目的光。说不清现在到底几点钟,但暮色已至,天时已晚,早已过了客人登门的时间——倒也不是说,我家会有数不清的来客。
我家根本不会有人登门,一个也没有,谁会到这么偏的地方来拜访我们?
我站起身,伸个懒腰:后腰好僵。我拿起手边已经启盖的啤酒,从椅子旁边迈出几步,来到窗前。跟平时一样,因为正值黄昏,我没有系衬衣扣子:只要热浪袭来,干什么都要费不少劲,干什么都省不了力气。等着瞧吧,瞧瞧那辆汽车是否会跟我料想中一样停下,掉头再开回公路,然后一路往前,把我们孤零零地抛下——本该如此嘛。
但事实并非如此。那辆车停在了原地,绿色车灯直指我家所在的方向。不知道是出于犹豫、不情不愿还是左右为难,总之拖了好一会儿以后,汽车又开始向我家驶来。
有谁跟你约好要来我们家吗? 我扯开嗓子,对小塔喊道。
“没有啊。”她在楼上高声回答。
还用说吗,当然不会有,我干吗还要多嘴问上一句呢。怎么会有人在入夜时分来我家,绝无可能。我灌下了一大口啤酒。酒是温的。我遥望着那辆车一路驶到了我家,停在我的卡车旁边。
唔,你还是下来一趟的好,有人来我们家了。 我又高声对小塔说。


我听见小塔下了楼梯,走进房间。我转过身——小塔一定是刚刚冲过澡。她穿着黑色背心加短裤,一头湿漉漉的秀发,看上去美丽动人。她真美;恐怕再不会有比此刻更本色、更美艳的小塔了吧。
哈喽。 我对小塔说。
“嘿。”她答道。
有那么片刻,我们两人都一声不吭,直到小塔打破了沉默。“我都不知道你在……不知道你在家里。我的意思是,我还以为你在外面的鸡舍。”她说。
小塔抬起手,摆弄秀发,先慢吞吞地用食指绕上一绺,再把它拉直——显然,小塔的“强迫症”犯了。但凡心潮澎湃或者竭力想要集中心神的时候,她就会犯这个毛病。
有人来我们家啦。 我重复了一遍。
小塔却呆立原地,直勾勾盯着我,连眨也没有眨一下眼睛。她的姿势很僵,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怎么啦? 我问道, 出了什么事?你没事吧?
“没事,没什么事。”小塔说,“我们家居然有客人上门,吓我一跳。”
她迟疑着,向我走近几步,在距我半米远处站住了,足以让我闻到她的护手霜香味:是椰子味,再加上某种别的味道。可能是薄荷,颇为特别,我就叫它“小塔味”好了。
“你认识开那种黑色汽车的人吗?”小塔问。
不认识。 我答道, 看上去像是公务用车,政府之类,对吧?
“有可能。”小塔说。
汽车的车窗贴了膜,我无法望见车内。
“不管来的是什么人,他必有所求。毕竟,人家大老远地来了这个鬼地方。”小塔补了一句。
车门终于开了,却没有人钻出汽车,至少目前没有。小塔和我只管等着。感觉像是过了足足五分钟——我们站着,遥望着,只等瞧瞧车里钻出的究竟是何方神圣。不过,也有可能,我们只等了二十秒。
随后,我望见了一条腿——有人踏出了汽车。是一名男子,有着一头长长的金发,身穿深色西服配衬衣,敞着领口,没有系领带,随身带着一只黑色公文包。来人关上了车门,理了理外套,迈步走向我家的前廊。我的耳边,传来陌生男子踏上旧木板的声音。其实,来访的男子无须敲门:因为小塔和我正紧盯着对方,而他可以透过窗户望见我们。我们心知他已经到了门口,但小塔和我却原地不动,观察着来人。于是,敲门声终于响了起来。
你去开下门吧。 我一边对小塔说,一边系上衬衫的纽扣。
小塔没有吱声,转身出了客厅,向前门走去。她突然迟疑了片刻,回头望望我,转身吸口气,打开了我家的大门。
“哈喽。”小塔打了声招呼。
“嗨。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打扰两位。”西服男子开了口,“希望两位不要介意。您是亨丽埃塔,对吧?”
小塔点点头,垂下眼睛,望着自己的脚。
“我叫特伦斯,希望能跟两位聊一聊。如果不介意,那就进屋一聊吧。您丈夫在家吗?”西服男子说。
自从小塔打开我家大门,西服男子的脸上就挂着夸张的笑容,始终没有变过。
请问您有何贵干? 我一边问,一边走出客厅,进了门厅。我就站在小塔的身后,一只手搭上她的肩头。冷不丁被我伸手一碰,她打了个哆嗦。
来客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我比他高,比他魁梧,还比他大好几岁。我们四目相接,对方紧盯着我望了好一会儿——久得似乎不太寻常。来客的眼中增添了一丝笑意,仿佛见到的景象让他很满意。
“您是朱尼尔,对吧?”他问。
不好意思,请问我们认识你吗?
“您看上去气色不赖。”
你在瞎扯什么?
“真是激动人心。”来客向小塔望去,她却避开了他的眼神,“前来您家的一路上,我心里一直很忐忑,再说了,您家离市区确实也不近。很高兴终于见到您,我是特意来访的。”陌生男子说道,“只为了来跟两位聊聊,仅此而已。我觉得,两位会乐意听听我要说的话。”
请问您究竟有何贵干? 我又重复一遍。
此人突然上门,有点不太寻常。很明显,小塔很不自在。我也很不自在,因为小塔很不自在。至于来访的客人,他还是把话说清楚一点的好。
“我是代表‘奥特摩’来访的。两位听说过我们吗?”陌生男子问。
奥特摩, 我重复了一遍, 是那个组织吗,致力于……
“能否让我进屋再聊呢?”
我把房门敞开了些,跟小塔一起退到一旁。就算来者不善,我也已经观察了好一阵,因此心里有数:至少对我来说,特伦斯不足为虑。这小子没什么能耐,长了一副白领身材,细皮嫩肉的样子。是个耍笔杆子的家伙,跟我不属于一类人,毕竟,我可是一直干体力活的。一进我家前厅,特伦斯就放眼四处张望。
“好地方,”他开口说道,“宽敞、质朴,具有乡村风,很招人爱的乡村风,真不赖。”
“你不想找个地方坐下吗?”小塔一边说,一边领着我们到了客厅。
“多谢。”特伦斯回答道。
小塔开了一盏灯,坐到她的摇椅上。我坐到常坐的躺椅上。特伦斯在我们前方那张沙发的正中间坐下,把公文包放上咖啡桌。他坐下的时候,裤腿抬了起来:他穿的是一双白袜子。
你车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问道。
“只有我。”特伦斯说,“我的工作就是造访各位,不过,到您家花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久一些,确实是很长一段路,所以我到得有点晚。再次向两位致歉,不过,很荣幸能来到这里,见到两位。”
“没错,确实已经很晚了。”小塔说,“幸好我们还没睡。”
陌生人是如此冷静,如此放松,仿佛他早已经来过我家,在我家的沙发上安坐过数百次。他这副过于气定神闲的派头,反而让我生厌。我本打算观察小塔的眼神,她却直勾勾地瞪着前方,头也不肯扭一下。还是先应付特伦斯好了。
请问您究竟有何贵干? 我问道。
“唔,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吧。正如我刚才所说,我是代表‘奥特摩’来访的。我们‘奥特摩’创立于六十多年前,起步于无人驾驶汽车领域,拥有世界上最高效、最安全的自动驾驶汽车。多年来,‘奥特摩’的宗旨几经变化,如今已十分明确。我们从汽车行业拓展到了航空航天、勘探和开发领域,正向下一阶段的转变努力。”
下一阶段的转变。 我把他的话重复一遍, 举个例子,比如太空?是政府派你来我家的吗?你坐的可是政府用车。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如果稍微关注一下新闻,你就会知道:‘奥特摩’是个公私联营的组织。我们在政府内设有分支,因此会有政府用车,但又植根于私营企业,我可以给你播放一则关于我们‘奥特摩’的简介视频。”特伦斯说。
他从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一台电脑,用双手举高,面对着我和小塔。我瞥了一眼小塔,她点点头,示意我看个究竟。视频开始播放了,看上去属于典型的官方宣传片,过于热情,过于卖力。我又朝小塔偷偷抛去一瞥,她似乎兴致索然,正用食指绞着一绺头发。
电脑屏幕上的图像一帧接一帧,换得飞快,快得让人认不清细节,摸不透意图:画面中的众人笑意盈盈,致力于集体活动,一起欢笑,一起进餐,每个人都很开心。其中有几幅蓝天的画面、火箭发射的画面,以及一排排兵营式金属床。
视频播完了,特伦斯又把电脑收进公文包。“唔,”他开口说道,“如你所见,我们‘奥特摩’在这个项目上已经花了很长时间,远远长过大多数人的预期。目前项目尚需努力,但进展颇佳,技术相当先进,令人惊艳。最近我们又收到了一笔巨额资金。总之,此事千真万确。我知道,媒体上有一些相关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曝光的内容只是冰山一角,这个项目实属厚积薄发。”
我竭力梳理他的逻辑,可惜还是没有听懂。
不好意思,先问一声,刚才你提到“此事千真万确”,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夫妻俩对新闻不怎么关注,对不对? 我一边说,一边向小塔望去。
“对,”小塔答道,“不是很在意。”
我只等小塔接过话头,要么追问一个问题,要么再补上几句,总之说什么都好,但她并没有接话。
“我指的是首批‘安置’之旅,也就是‘安置计划’。”特伦斯说。
你在胡扯些什么啊?
“‘安置计划’,第一批临时移居。”特伦斯说。
“移居”。比如,从地球移居太空? 我问。
“说得对。”特伦斯答道。
我还以为“移居太空”只是个设想呢,嘴上说说而已。 我说, 这就是你来我家的原因?
“‘移居太空’再真实不过了。对,没错,这就是我的来意。”特伦斯回答。
小塔长吁了一口气——不如说是呻吟了一声,几不可闻,说不清是心烦还是忐忑。
“抱歉,”陌生男子说,“不知道两位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开车过来一趟,我快渴死了。”
小塔站起身,朝我所在的方向扭过头,却没有与我对视。“你也想喝点什么吗?”她问。
我摇摇头。我的啤酒还没有喝完呢,是我在特伦斯来访之前喝的那瓶,在今夜陡生风波之前。我从桌上拿起啤酒瓶,喝了一大口温热的啤酒。
“唔,只剩你跟我了。这栋是你的私宅吧,真不赖。这宅子有多少年的历史?”小塔动身去了厨房,特伦斯开口问道。
老宅,大约几百年。 我答道。
“太棒了!真让我羡慕。你在这里住得开心吗?你喜欢这里吗,朱尼尔?你感觉生活舒适吗?过着只有你们夫妻两人的日子?”特伦斯问。
他的弦外之音是什么?我有点好奇。
我们的眼界也就这样了,小塔和我。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一起过得很开心。 我答道。
特伦斯歪了歪头,再次露出了笑容。
“唔,真是绝妙的地方,绝妙的经历。瞧瞧这些墙,一定承载了多年的历史。住着这么宽敞、幽静的大宅,感觉一定很称心。在这种地方,简直可以为所欲为,反正不会被别人听见,也不会被看见,根本不会有人打扰。你家附近一带,还有别的农场吗?”特伦斯问。
现在没什么农场了。以前有一些,现在基本上全是农田,种了些油菜。
“没错,开车过来的路上,我看见农田了,我还不知道油菜能长那么高呢。”特伦斯说。
以前,这些土地还属于农场主的时候,油菜可长不了这么高。现在,大部分土地属于大公司或政府,公司就在田里种上了新品种。杂交品种吧,比原来的油菜高得多,颜色更黄,而且几乎不需要水。这些油菜熬得过久旱,长得也快,依我看,似乎很不自然,不过它就这样。
特伦斯俯身向我凑过来。
“真有意思。那你是否有过感觉……烦躁的时候?毕竟,你们两位孤零零离群索居嘛。”
小塔端着一杯水回了客厅,递给特伦斯,又把摇椅挪得离我更近些,坐了下来。
刚从我家井里打出来的水,你在城里可喝不到。 我对特伦斯说。
特伦斯向小塔道了谢,举杯一口气喝了好久好久,“咕咚咕咚”灌下了四分之三杯。一串水珠从他的嘴角流下,沿着下巴滴下来。他心满意足地叹口气,又把杯子放回桌上。
“好喝。”他说,“言归正题吧,如我所说,该项目正在计划之中。我是公关部的联络员,你们的档案被分到了我手里,我将与两位紧密合作。”
与我们“紧密合作”? 我问道, 你们竟然有我们的档案?你们为什么会有我们的档案?
“本来没有,但最近……唔,情况有变。”特伦斯回答。
我感觉嘴里发干。我咽了口唾沫,可惜没有用。
我们可没有报过名,也没有同意过建档。 我一边说,一边呷着啤酒。
对方再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依我猜,跟城里其他人一样,他那口白生生的牙齿也都是些种植牙。“确实没有。不过,我们‘奥特摩’举行了首次‘抽彩’,朱尼尔。”
首次什么? 我问道。
“首次‘抽彩’挑选幸运儿。”特伦斯说。
“你们‘奥特摩’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小塔一边说,一边摇头。
“抽彩”挑选幸运儿?你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问道。
“我不太清楚,像二位这样的普通公众已经得知了多少消息;我也不太清楚,你们已经根据读到或看到的消息悟出了多少内情。依我猜,在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你们应该所知不多。但总之一句话:你被挑中了。这也正是我的来意。”特伦斯说。
尽管特伦斯没有张嘴,我却依然可以看出,他刚刚伸舌头扫过了一排上牙。
我向小塔望去,她却再度直视着前方。小塔干吗不肯跟我对视?她一定有什么心事。躲开我的眼神,并不是小塔的作风——我不喜欢她躲着我。
“我们得认真听一听,朱尼尔。”小塔开口说话了,语调却有点诡异,“我们得好好体会一下人家在说些什么。”
特伦斯的眼神从我的身上挪开,落到小塔身上,又落回我身上。他听出小塔的语气有多恼火了吗?他听得懂吗?不过,他并不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夫妻在没有外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抱歉,我有点失礼。”特伦斯说着,起身脱下了外套,“刚才那杯水很解渴。可是,天气还是有点热,我住的地方到处都有空调,希望两位不介意我脱掉外套。你确定不要喝杯水吗,亨丽埃塔?”
“不用了。”小塔答道。
亨丽埃塔——特伦斯叫的是小塔的全名。特伦斯的衬衣已经被汗濡湿,一块块毫无规律的汗渍看上去活像地图上的一个个小岛。他叠好外套,放在身边的沙发上。
发问时间到了:对方正在给我发问的机会,从他的肢体语言就可以看出来。
刚才你说,我被挑中了。 我说。
“对。”对方回答,“是的。”
挑中去做什么? 我问道。
“‘安置计划’。很显然,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属于起步阶段。我必须强调的是,目前,你只是进了初选名单,因此暂时无须太过激动。不过,话说回来,又有什么办法呢?怎么可能不激动嘛,连我都为你感到激动。说起这份工作,这正是我最爱的环节:给大家带去喜讯。现在还不能保证你最终能顺利入选,希望你理解。事实上,最终入选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进入初选已经很了不起了,意义十分重大。”特伦斯说。
他向小塔望去。小塔面无表情。
“你绝不会相信,过去几年我们究竟见识了多少志愿应征者,数千人眼巴巴地盼着被本项目选中。此时此刻,不少人为了收到入选的喜讯,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因此……”
我没有听懂。 我说。
“是吗?”特伦斯放声大笑,摇了摇头,又镇定下来,“朱尼尔,恭喜!你进了初选名单!‘安置计划’的初选名单。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你最终被选中的话,你将可以参观‘奥特摩’开发的安置点,甚至有可能成为第一拨移居安置人员中的一分子。你也许可以‘一步登天’。”
特伦斯伸手向天花板一指,但他显然指的是天花板之外,屋顶之外,指向茫茫的太空。他又伸手抹了把前额,只等我们领会他带来的大好消息,然后接着说下去。
“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目前还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已经启动了首次‘抽彩’挑人的程序,因为这种……征召幸运儿的形式……需要慢慢来。”
我又喝了一口啤酒。看来,得再来一瓶了。
征召幸运儿? 我问。
“我知道,这是个大好消息,需要好好消化。”特伦斯说,“但请记住一点,这一点我每次都提,我也真心相信:万事都在变化,变化是生活中唯一确定不变的事。人类在前进,我们别无选择。人类在进化,在行动,在发展壮大。一度看似牵强、极端的事物,眨眼间就会变得寻常,甚至过时,人类再向下一个热点、下一个前沿进发。我们头顶的那片天,其实并不是另一个世界,只是远方而已。自从人类诞生,大部分时间里,它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但它一直在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近,人类在拉近与太空的距离。你懂了吗?”
他的眼中满是自信与兴奋之色。不过,在他看来,我的眼睛又是什么样子?我并不感到兴奋;我本该感到兴奋才对,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我望了望小塔,她觉察到了我的眼神,转过身,露出一抹乖巧的微笑——小塔总算露出了笑容。一抹微笑,顿时让我们两人心连心:小塔跟我站在同一个阵营,她又恢复正常了。
太扯了吧。 我说着,向小塔的胳膊伸出手。 太空,是另外一个世界。可我们眼前明明就有一段人生,一个世界,一个二人世界。
我忽然起了戒备心,只想保护眼下的人生,这种我所熟知、我所懂得的人生。
你突然踏进我家的大门,还堂而皇之地宣布我可能要离家出发?根本不管我怎么想?依你看,我和小塔在这里过了这么久,为什么非得离开这里?这种破事我可不想掺和,太离谱了。 我对特伦斯说。
特伦斯又咧嘴一笑,慢吞吞地前倾身子,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听着,”他说,“我登门造访,是前来预警。”他住了嘴,调整了一下坐姿,“不,抱歉,恕我措辞不当。说是‘预警’,听上去很不顺耳,再说,事实也并非如此。被项目选中,是件大好事,属于梦想成真。我不得不说,你确实不是自愿加入,不完全是吧。不过,你曾经谈起过‘太空’,我们‘奥特摩’的算法对此有所识别。”
听到这句,小塔似乎气炸了。“也就是说,你们‘奥特摩’一直在监听我们?”她突然问道,“你们监听我们多久啦?”小塔的语气,透着一种陌生的风格,让我感觉……我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我不喜欢。
特伦斯伸出双手,看似在表达歉意。“拜托。”他说,“都怪我没有说清楚,没有把事情说透。其实,跟什么监视、监听无关,是因为你们电脑里的麦克风一直开着——知道吧。就是数据收集,我们使用的程序会对信息进行梳理分类,识别出关键词。”
“我敢说,现在你们盯他盯得更紧了吧,对不对?”小塔说。
“对,确实如此。”特伦斯回答。
小塔板着一张脸,显得镇定自若,却又不露声色。
“关键词”?能麻烦你解释一下吗? 我问道, 所谓“抽彩”挑选幸运儿,会采用什么样的“关键词”?顺便说一声,对这场“抽彩”挑人,我自己居然毫不知情?
我一心期盼这也正是小塔想问的问题。
“秉承我们‘奥特摩’的目标,关键词包括任何关于旅行、太空、行星或月球的言论。毋庸置疑,我们会识别相关字词,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信息。”特伦斯停下顿了顿,似乎在权衡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我们的‘抽彩’挑人系统很复杂,无法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只能拜托你相信我们。毕竟,‘安置计划’的立足之本,就是信任。”
小塔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她是那么泰然,那么安静。她为什么一声不吭?为什么不多问几个问题?为什么让我处理这一切?
你能跟我们说得再详细一点吗?安置点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问道。
“几年前,计划刚开始的时候,人类在太空的居住地似乎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比如月球、火星。‘奥特摩’甚至曾经考虑过殖民一颗刚发现的行星,那颗行星围绕着临近太阳系的一颗恒星运行。但到最后,我们决定打造我们自己的‘星球’,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的空间站。”
对我这种人来说,对方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比如“临近太阳系”之类,都十分难以理解,但我必须试一试。
为什么? 我问特伦斯。 既然我们在地球上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要建什么空间站?既然太空里已经存在很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为什么还要另外兴建什么空间站?
特伦斯挠了挠头。“诸多原因吧。例如,假如你想去上述星球中的某一个兜一圈,即使你以光速赶去——当然,你是无法做到以光速前往的——也要花上大约七十八年的时间,才能往返一趟。因此,那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而我们选择去翻越其他难关。我们希望第一阶段,也就是安置点阶段,成为一个测试期,一次调研。有人会被送入太空生活,而我们进行观察、测试、分析,再送人回家。打造我们自己的星球,跟这一模式最为契合。太空里本来就有人类的空间站,早就有了。我们‘奥特摩’的首个空间站,是几年前送入太空的,自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进行扩建。安置点发展壮大的速度十分快,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空间站。就在此刻,它正绕着地球转动,虽然尚未完全建成,但它已经在太空之中了。”
人类真是不能自拔啊,非要扩张、拓展、征服不可。 我暗自心想。
你说的这一切,政府都知情吗? 我问。
“我们就是政府。”特伦斯说,“我们与政府息息相关,这是我们共同的研究。”
我还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呢。 我说, 小塔也没有。她肯定不乐意,她连远门也没有出过,移居太空会吓到她。
“唔。”特伦斯答道,“刚才我应该把话说清楚的,确实是我的错。入选者指的是你,朱尼尔,只有你一个人。”
我恍然大悟。我听懂他的言外之意了。
难道小塔没有跟我一起在初选名单上吗?我们不都属于“抽彩”挑中的幸运儿吗? 我问。
“不,恐怕不是。入选的只有你,朱尼尔。”特伦斯回答。
小塔毫无反应。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没有吭一声,甚至没有叹气,只是默默安坐一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小塔却在帮倒忙。
接下来要怎么样? 我问特伦斯。
“短期之内,不会有什么大事。初选名单长得很,流程也长得很,把它当作一场马拉松吧。按照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办到,‘奥特摩’定会派人将消息亲自通知入选者,这是开始双方合作的最佳方式。如果你没有进入决选名单,这就将是我们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访,但也有可能,我们会有深度往来。”特伦斯回答。
初选名单上有多少人? 我问。
“朱尼尔,我相信你能理解:很遗憾,除了初选名单上有你的名字,我不能再透露任何细节,其他事项都属于机密。我只能说,在未来几年之内,事情恐怕定不下来。”
“未来几年之内”——听到这句话,我暗自松了一口气。其实吧,可能性很渺茫,很遥远,跟那个正绕地球运行的空间站差不了多少。也许小塔从一开始就看透了这件事;也许,这也正是小塔如此镇定、如此安静的原因。
某种意义上,特伦斯与我的对话就此画上了句号。事实上,特伦斯还在滔滔不绝地说,在高谈阔论,又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解释“奥特摩”的各种目标,但他并没有提到任何与我相关的事情。每当我插嘴问个问题,评论几句,他就搬出一副官方腔调。他嘴里说出的许多言论,都像早已事先编排过。不知道他干这行多久了——不会太久吧,特伦斯还显得太照本宣科,太做作。很明显,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之情,这一点毋庸置疑。他跟小塔和我提起“奥特摩”开发的某种产品,某种名叫“生命啫喱”的外用药膏,可以帮助人体适应缺乏空气的环境。 某种“啫喱”, 我暗自想道, 一种用来帮你适应某种事物的啫喱。 也太诡异、太抽象了吧,以至于让我无法想象。
特伦斯去了洗手间,客厅终于只剩下我和小塔了。刚开始,我们两人都没有说话,茫然而沉默地坐着。终于,小塔向我望了过来。
我直视着她的双眼:此刻,小塔的眼里有我,小塔的注意力在我身上,我立刻感觉好受了不少。
“你怎么看?”小塔问。
我说不清楚,还在努力消化。 我边说边摇头, 我知道,我本来应该感觉很开心,很激动,谁让这是个大多数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呢,可是……
“你感觉不开心吗?感觉很害怕、很傻眼?”小塔问。
不,不,不。 我说, 我没事。
“那就好。”小塔说,“确实很难消化,见鬼的‘生命啫喱’。”
是啊,见鬼的“生命啫喱”。 我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
正在这时,特伦斯回到了客厅,小塔和我没有办法再单独细聊下去。特伦斯又接起了话头,接得几乎天衣无缝。然而,他依然没有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却满嘴扯些不着边的空话,谈起初选名单的复杂算法细节,给我们播了一段阐释“推力矢量”的视频,又给我们播了另一段视频,讲的是“奥特摩”新造的火箭,它排出的废气是透明的。
小塔一直坐在我的身旁,听着特伦斯的言论。大约半小时后,她起身离开了。特伦斯又对我夸夸其谈了片刻,到了最后,他似乎再也找不出什么话讲。我心知自己还有一肚子问题和担忧,想开口问他,可惜,整件事来得实在突然,又让人不堪重负,害我根本想不起自己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耐性和好奇心都已经被磨得一干二净。随后,我送特伦斯到汽车旁边,望着他并和他握了握手。就在这时,我今晚第一次产生了奇怪的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
特伦斯把公文包放进车里,没有关车门,却转身给了我一个拥抱,冷不丁吓了我一跳。他松开我,后退一步,伸手攥住我的肩头。
“恭喜,”他说,“很开心在这里见到你。”
我认识你吗? 我问。
他那口白牙,他那副笑容。“今天只是个开始,算是第一天吧。但我有种预感,我们不久就会再见面。”说完,特伦斯钻进车里,“祝你好运。”
车门“砰”一声关上了。我遥望着汽车驶下小路,又驶上公路。屋外已经漆黑一片,可以听到蟋蟀和各种生物在油菜丛中发出的声响。我环顾四周:眼前便是我的家乡,是我所熟知的世界,是我所知的一切。我一直以为,我永远都不会踏出这个世界。
我抬头仰望天空:空中繁星点点,一如平日。我一生都在仰望同一片夜空,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片天,万千繁星、卫星、月亮。我知道,月亮与我们相隔万里之遥,但今天晚上,它显得有点异样。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思考过关于月亮的问题,如果我身在此地,用肉眼就能望见眼前这一幕,望见漫天繁星,望见一轮明月,那它们又能远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