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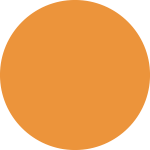
据《隋书·经籍志》,我国唐以前的诗歌总集,计有《诗经》《楚辞》《古诗集》《六代诗集钞》《今诗英》《古今诗苑英华》《众诗英华》《玉台新咏》《文林馆诗府》《古乐府》等多部。但除《诗经》《楚辞》《玉台新咏》外,其余皆已亡佚。南北朝时期是诗歌史上总集编纂的一个鼎盛时期,前述总集除《诗经》《楚辞》外,都编撰于南北朝时期,而其时编纂的众多总集皆已亡佚,仅得一部《玉台新咏》流传至今,可以说是硕果仅存。
《隋书·经籍志》云:“《玉台新咏》十卷,徐陵撰。”新旧《唐书》等史籍、《郡斋读书志》《千顷堂书目》等公私书目著录与此相同;在留存至今的《玉台新咏》诸本中,被梁启超推为“人间最善本”的明代赵均小宛堂覆宋本,也在书前明标“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字孝穆撰”;可见,《玉台新咏》的编者为徐陵,在学界已为共识。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其父徐摛,初为晋安王萧纲侍读,中大通三年(531)萧纲被立为太子后,转家令,兼掌管记。出为新安太守,回建康(今江苏南京)后授中庶子,迁太子左卫率,深得萧纲宠信。萧纲即位为简文帝,在侯景乱中被幽禁,感气疾而卒。徐陵为徐摛长子,早年随父在萧纲幕中任职,参宁蛮府军事。萧纲被立为太子后,任东宫学士,不久迁尚书度支郎。出为上虞令,时御史中丞刘孝仪与徐陵有隙,风闻徐陵在县赃污,劾之,被免。久之起用,迁通直散骑侍郎、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军。太清二年(548),出使东魏,值侯景乱起,滞留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北齐代东魏,梁湘东王萧绎称制于江陵,为元帝,复通使于北齐,徐陵屡求南归,不得。梁承圣三年(554),西魏攻克江陵,杀元帝,北齐送梁贞阳侯萧渊明南返为梁帝,徐陵才得随萧渊明返回建康(今江苏南京),任尚书吏部郎。绍泰二年(556),又出使北齐,返回后任给事黄门侍郎、秘书监。太平二年(557),陈霸先代梁自立,是为陈武帝。徐陵仕陈,历任太府卿、五兵尚书、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吏部尚书、领大著作、尚书左仆射、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等职,于至德元年(583)卒。其传在《陈书》卷二十六、《南史》卷六十二。
据《梁书》卷三十《徐摛传》,徐摛“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梁武帝萧衍曾以《五经》大义、历代史及百家杂说、释教相询,徐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萧衍“甚加叹异”。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徐陵因此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陈书》本传载,徐陵“八岁,能属文。十二,通《庄》《老》义。既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在东宫,诗文与庾信齐名,世号“徐庾体”,“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入陈,“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为一代文宗”。“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陈书》本传)。可见,在梁、陈两代,徐陵都是文坛的领袖人物,其诗文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
用现代的眼光看来,诗之作为诗,它必须具有两大美质:从内容来说,它必须是抒情的,能够以情感人;从形式来说,它能给人以美感,特别是,由于诗的语言是诗的物质外壳,是直接诉诸观者的视觉和听者的听觉的,它就更应当是美的。对于诗歌的这个特点,古今人的认识其实是相通的,只不过人们最初的认识是并不明确、自觉的,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是并不明确、自觉的。从并不明确、自觉到比较明确、自觉,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其中的“诗言志”,被朱自清认为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诗言志”中的“志”,古人曾有不同的理解。一是把“志”理解为“意”,如汉人许慎《说文解字》:“志,意也。”一是把“志”理解为“情”,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产之言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杜预注:“为礼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过节。”显然,这里所说的“六志”,指的就是“六情”。应当说,“意”与“情”在思维活动及创作实践中是不太可能截然加以分割的;但另一方面,两者确又存在着区别,特别是在将“志”理解为“思想”的时候。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由于对“志”的理解不同,从不同的立场、角度乃至需要出发,对诗歌的特点也就有了不同的认识,同时对诗歌创作也就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先秦时期,由于儒家看重政治教化,往往将“志”理解为志意、思想,而对诗歌抒发情感、以情动人的特点缺乏认识。到了汉代,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志意、思想更被强调到极端的地步。儒家诗论的纲领《诗大序》虽有“吟咏情性”之说,但又同时给它附加了三个条件:一是要“美盛德之形容”,即要赞美统治阶级的“盛德”。二是要“吟咏情性,以风其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发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功用和伦理道德功用。三是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即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限制情性。这样一来,诗歌的功能在实际上就只剩下社会功能,社会功能也只剩下“美”“刺”两端,而其审美功能、抒情的特点及其应当具有的语言美,就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乃至否定了。
东汉末年,由于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统一的中央政权解体,儒家思想逐渐失去维系人心的力量而走向衰颓,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活跃的局面,诗歌的特点也开始有意识地被重新审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诗赋欲丽”的命题,所谓“丽”,指文辞的华丽,曹丕说“诗赋欲丽”,表明他对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诗歌的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东汉以后,人们对诗歌的特征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陆机在其《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所谓“诗缘情”,即谓诗歌乃因情而作,第一次明确地强调了“情”对于诗歌的重要性;所谓“绮靡”,《文选》李善注为“精妙之言”,即语言要精美,要有文采。从《文赋》“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等论述看,陆机所说的“绮靡”,是包括了文辞的色泽、声律、骈偶、用典等诸多方面的,对诗歌语言美的认识,可以说已经相当全面了。
到了南朝,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走向开放,对情性的追求也更加大胆,在这方面梁简文帝萧纲与梁元帝萧绎的看法可能是最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了。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明确地提出了为人与为文不必一致的二元化主张。所谓“立身先须谨重”,即要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讲究做人的规矩,不得放荡;而为文则不一样,不仅不必“谨重”,而且还须“放荡”。这里所说的“放荡”,乃与“谨重”相对而言,是通脱随便、不受拘束的意思。萧纲的弟弟萧绎也发表了与萧纲相似的见解,他在《金楼子·立言》中,将作为抒发性灵的“文”与作为实用文体的“笔”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且认为:“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不难看出,萧绎所理解的“文”的特征,包括情感、词采、声韵三个方面,这个“文”已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文学大致相当,代表了当时对于抒情文学,特别是诗歌审美特征认识的最高水平。
在萧纲、萧绎等人的带动、影响和推动下,一种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诗歌特征的新认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诗体即宫体应运而生。
“宫体”之名,最早见于《梁书》卷四《简文帝纪》:“(简文帝)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又《南史》卷八《梁本纪论》:“简文文明之姿,禀乎天授。……宫体所传,且变朝野。”
又《梁书》卷三十《徐摛传》:“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又《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仿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
又杜確《岑嘉州诗序》:“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辞,名曰‘宫体’,自后沿袭,务为妖艳。”
不难看出,“宫体”的所谓“宫”,指太子所居的东宫(也称“春坊”),所谓“宫体”,即在宫中流行的诗体。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宫体的特色主要是:内容多表现女子的生活和情思,“思极闺闱之内”,甚至有“止乎衽席之间”者;形式上追求声律,讲求对偶,雕琢辞藻,驰逐新巧,崇尚丽靡,形成了一种绮艳柔媚的风格。宫体不仅与汉魏时期的古体诗迥异其面,就是与南朝宋以来的元嘉体、永明体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确实是“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的产物。
宫体因东宫而得名,但其形成却在萧纲入主东宫之前,其真正的开创者是徐摛和庾肩吾。徐摛和庾肩吾都是长期追随萧纲的人物。徐摛是在天监八年(509)萧纲以晋安王、云麾将军身份出戍石头城时为萧纲侍读的,其时萧纲还是一个只有六岁的孩子,萧纲自称“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可以认为这“诗癖”是在徐摛耳提面命的教诲和影响下形成的,其审美取向必然与“属文好为新变”的徐摛趋同。庾肩吾是著名诗人庾信之父,在当时最为讲究声律的调谐和字句的琢炼。他进入萧纲王府的时间,应与徐摛相去不远,在长期的伴随中对萧纲自也会产生不小影响。除徐摛、庾肩吾外,在萧纲身边还聚集了大批文人,如任雍州刺史时,徐摛、庾肩吾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等八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刘遵、陆罩、刘孝仪、王台卿等人也曾先后被萧纲所赏接。萧纲入主东宫后,所倚重的大抵还是他在藩镇时追随在他身边的以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大家相互影响和唱和,从而使宫体得以最后确立。
萧纲对于宫体的追求,还得到了乃父梁武帝萧衍的认可,得到了他的弟弟萧纶、萧纪等的支持。南朝的帝王大都喜欢网罗文学之士,尤以梁武帝父子最为突出。而当时的文学之士由于入仕缺乏稳定的制度上的保证,也往往乐于依附皇帝及诸王,因此梁武帝父子的好尚,对他们自然会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于是宫体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了“递相仿习”、风靡朝野的局面。
就在宫体诗创作的鼎盛时期,徐陵奉萧纲之命编撰了一部诗歌总集,即《玉台新咏》。《文选》陆机《塘上行》:“发藻玉台下,垂影沧浪泉。”刘良注:“玉台,以玉饰台。”又《文选》张衡《西京赋》有“西有玉台,联以昆德”之句,薛综注指“玉台”为“台名”。这里借指东宫。全书共十卷。所收诗作数量,由于有的将一首分作数章的诗算作一首,而有的却算作数首,因此造成统计数字不一,如赵均《玉台新咏跋》云:“凡为十卷,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几二百。”吴兆宜《序》则云:“孝穆所选诗凡八百七十章……宋刻不收者一百七十有九。”现依通行标准计算,则宋刻本加上郑玄抚等明刻本所增,共收自汉迄梁的诗840首(张衡《四愁诗》、傅玄及张载的《拟四愁诗》均算作四首),其中有署名的作者134人,诗793首,无名氏作者的诗47首,宋刻本未收的诗179首。
关于《玉台新咏》编纂的时间,赵均《跋》云:“此本则简文尚称皇太子,元帝亦称湘东王,可以明证。惟武帝之署梁朝,孝穆之列陈衔,并独不称名,此一经其子姓书,一为后人更定无疑也。”即认为书编成于萧纲尚为太子时,其时徐陵为东宫学士。此说大体得到学界的认同。《玉台新咏》十卷,前六卷所收为已故诗人的作品,大体按诗人卒年先后为排列顺序;卷七、卷八所收则为尚在世诗人的作品,其中卷七为梁武帝父子的作品,以父子兄弟为序,卷八为梁朝群臣的作品,大抵以其官职为序。曹道衡、沈玉成认为:“卷五、六所收已为入梁的作家。如果不是已做古人,绝无排列在梁武帝父子之前的理由。从卷六中最晚卒的作家何思澄大约卒于中大通五、六年,卷八中最早卒的作家刘遵卒于大同元年,由此可以断定《玉台新咏》的成书当在中大通六年前后。”(《南北朝文学史》)其时萧纲不过三十一、二岁,入主东宫才约四年。
关于《玉台新咏》的内容,徐陵自序云:“撰录艳歌,凡为十卷。”即说明所收录的皆为“艳歌”。又据前引《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所收皆为“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之作。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则云:“《玉台》但辑闺房一体。”此三说皆有道理,而从所收作品的实际看,胡应麟所说更具代表性,即所收皆为表现女性闺房及男女之情的作品。
关于编纂《玉台新咏》的目的,据徐陵自序,是为了供后宫喜欢“新诗”的妃嫔宫女们读书作文、排遣寂寞之用。由于“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颇不方便“披览”,因而才决定编撰此书。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公直》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刘肃所说不知所据为何。如前所说,此书若编于中大通六年(534)前后,则其时萧纲尚不能被称作“晚年”。萧纲为因写作宫体而后悔,“追之不及”而欲“改作”之,尚找不出相关资料支持这种说法。至于“以大其体”,不知所指为何。《玉台新咏》前六卷选录了不少自汉以来诗风大体古朴,而与“艳诗”渊源有关的作品,其目的也许在表明宫体其来有自,以标榜其正当性,并借以壮大声势,不知这是否即“以大其体”的含义?总之,其编纂目的还是以徐陵自序所说较为切实、可信。甚至不妨认为,编纂《玉台新咏》的目的,是要对宫体创作的时风和宫体创作的实绩作一总结、展示和肯定,同时发挥其示范和引领的作用,不然,对宫体后来进一步的发展和泛滥就难以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由于宫体诗多为“艳诗”,多为“思极闺闱之内”“止乎衽席之间”之作,风格又“伤于轻艳”,因此历来颇遭非议。《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所评虽为“大同之后”的作品,但毋庸置疑是就宫体的整体而言,这里将其斥为“亡国之音”,可以说是十分严厉的批评。作为收录宫体的《玉台新咏》,自也不免受到牵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受到轻慢乃至非议。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站在正统儒家思想的立场,特别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来看待宫体及《玉台新咏》,其可非议的地方自会不少。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审美观及审美标准。在今天看来,宫体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玉台新咏》更有其不可轻忽的价值。以下几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一)《玉台新咏》是我国诗歌史上女性题材诗歌的第一次大汇集、大展览,这不仅在当时是空前的,后世的同类集子也罕有能与之匹敌者。从内容看,其可注意和肯定者有三:一是从多方面、多角度表现了古代妇女的生活,真切、细腻地表现了她们的思想和情感,展示了她们孤独的守望、难耐的寂寞、无尽的悲凄和深沉的哀怨,对她们的种种不幸给予了关注和同情。二是大胆地表现、赞美了女性之美,包括她们的天生丽质之美、一颦一笑之美、歌容舞态之美及妆容服饰之美等。女性美本来就是世间一种客观存在且不可或缺的美,它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人们表现、欣赏的对象,《玉台新咏》中的作品大胆地涉足这一领域,以强有力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审美类型,这无疑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三是大胆地表现了对于女性的欣赏和爱慕。自西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说教以来,人们的思想常被名教礼法思想所束缚,即使是正常的欲念也常要深自压抑,对男女之情极为正常的表现也常被视作禁区,《玉台新咏》对此予以突破,具有反封建的正面意义。
(二)《玉台新咏》卷一至卷四所收为自汉至南朝齐的作品,卷九所收为以七言为主的杂体诗,其中有不少内容雅正、诗风古朴的作品,比如来自民间的《汉桓帝时童谣歌》《日出东南隅行》(又作《陌上桑》)、《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及阮籍《咏怀》、左思《娇女诗》、鲍照《玩月城西门》等。在卷五、卷六所收梁诗中,也有不少诗风与此类似,比如江淹《古体四首》、吴均《与柳恽相赠答六首》等。把这些诗划入“艳诗”的范畴显然不妥。它们之所以被选入《玉台新咏》,只是因为它们也描写了女性,也表现了男女之情,如胡应麟所云:“《玉台》所集,于汉、魏、六朝无所诠择,凡言情则录之。”(《诗薮》外编卷二)就数量而言,这一类诗在《玉台新咏》中要占到多数;换言之,《玉台新咏》中的多数作品不能被视作艳诗。这些不能被视作艳诗的作品,与《诗经》中的相关作品在精神、风格上是一脉相传的,故陈玉父《跋》云:“若其他变风化雅,谓‘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之类,以此集揆之,语意未大异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云:此书“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实事求是的。
(三)那么,地道的宫体诗是否就可一概以“淫艳”视之、斥之呢?其实也不能。萧纲是宫体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玉台新咏》共收其诗109首(其中卷七70首,卷九14首,卷十25首),是所有诗人中收诗最多的一位。但综观其诗作,虽总的说来题材较琐屑,文辞较绮艳,格调不够高,但真正读来让人觉得不堪的作品却几乎没有。兹以历来最遭诟病的《咏内人昼眠》(此诗为宋刻本未收作品)为例。该诗历来被视作宫体诗中之最“艳”者,以“轻薄”视之者有之,以“色情”“肉欲”视之者亦有之。诗篇其实是描写一个青年女性的睡态美,她的丈夫站在一旁,欣赏她的睡态和美貌,有感而作了此诗。对女性睡眠时体态、情景的描写十分细腻,特别是“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四句,“纤曲尽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二),尤为突出。过于迫近、直接、具体地描写女性的睡姿,缺少含蓄和寄托。不过,以“色情”“肉欲”视之,也有判罚过当之嫌。尤可注意的是,萧纲的一些诗还具有积极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倾向。如《从顿暂还城》虽有“舞观”“歌台”这些宫体中常见的语句,但也颇有些在边塞诗中常见的雄浑气象和豪迈精神。“持此横行去,谁念守空床”,一反它诗绮靡哀婉的情调,有南北音合流之象。《和人以妾换马》咏人以爱妾换马,实代女子表达了内心的哀怨、痛苦和愤激,能看出诗人内心有同情女性、理解女性的一面。类似的作品,在宫体诗中并不鲜见。
(四)南朝时期,“追新求变”在诗坛是一种显得十分突出的风气,萧纲、萧绎、庾肩吾、徐摛等人无不把“新变”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徐陵“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对“新变”也有一股刻意追求的劲头。《玉台新咏》书名题作“新咏”,其自序言及音乐曰“新曲”“新声”,言及诗歌曰“新制”“新诗”,其属意于“新”,十分显然。宫体诗人刻意追新,由此带来诗坛日新月异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就是:诗人们不再接受任何名教礼法思想框框套套的束缚,大胆地表现女性和闺情,抒写自己的真性情;更广泛地将永明声律理论运用于创作实践,将其向精细化的方向推进;更加追求辞藻之美;更多地运用七言歌行和五言古绝这两种新的体式进行创作。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实现了文学观念的自觉,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从此有了一个清晰的划分,诗歌由功利转向非功利,从而涌现出大批真实地表现个人的喜怒哀乐、辞藻华美、声韵谐协、对偶精整、以审美价值为依归的作品,古代诗歌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玉台新咏》实为当时诗坛新变潮流的产物,反映了当时诗歌发展的新趋向、新成果。
(五)与此同时,《玉台新咏》显示诗人们对诗歌表现技巧的刻意追求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所收作品不少十分讲究描写的精致工细、表现的新奇工巧。如萧纲的《春日》描绘春日美景,可谓刻绘如画。“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二句,将春日具有特征性的景物之美表现到极致,同时融情入景,将诗人对春日景物发自内心的喜爱之情表现到极致,可拈为“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之例。“落花随燕入,游丝带蝶惊”二句,既出神入化,又自然天成,故王夫之评云:“得之空灵,出之自然。”(《古诗评选》卷六)注意在艺术表现和艺术技巧上下功夫,这对促进诗歌艺术特别是诗歌表现技巧的发展和进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此外,不少作品题材虽显得琐细,但却体现了诗人们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和诗美的能力,这对促进诗歌题材的生活化、世俗化,对拓展诗歌的表现功能和表现领域也会发挥积极作用。
(六)除《玉台新咏》外,在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文学总集流传至今的尚有萧纲之兄萧统负责编撰的《文选》,亦称《昭明文选》。《文选》问世后,由于其内容丰富,风格文质兼具,因此长期以来受到人们重视,成为人们学习汉魏六朝文学的主要读物,研究《文选》的也代不乏人,以致《文选》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所谓“选学”。而《玉台新咏》“则在若隐若显间,其不亡者幸也”(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序》),其命运与之相去甚远。但实际上,两书各有所长,可以互补。仅略举数端。其一,《文选》共收作品700多篇,但却是诗歌、辞赋和各体文章兼收并蓄,因此所收诗作数量远不如《玉台新咏》。据统计,两书同收的作品仅69篇,因此《玉台新咏》更多地收录了汉以来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赖《玉台新咏》才得以留存至今。如著名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又如“曹植《弃妇篇》、庾信《七夕诗》,今本集皆失载,据此可补阙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有鲍令晖、许瑶等本来就无集传世的诗人,如果没有《玉台新咏》,他们的作品极有可能会完全湮没无闻。又,《文选》不收生人的作品,而《玉台新咏》不拒生人作品,因此保存了大量梁代(特别是梁中期)作品,从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优势。其二,由于《文选》以“雅正”为收录标准,因此许多被编者认为“俗艳”的作品(包括乐府民歌及文人的拟作乐府)被排除在外,而《玉台新咏》却予大量收录,这才使我们获得了将这两个方面的作品结合起来,一睹当时诗歌创作全貌的机会。其三,与《文选》相比,《玉台新咏》更注重对产生于南齐永明年间及其以后的新体诗的收录,特别是收录了大量短诗,其中五言四句的小诗还专门辑成了一卷,共185首,而《文选》收录短诗很少,五言四句的小诗一首也没有收录。其四,由于《玉台新咏》所收诗作较多,因此可较充分地发挥其补阙佚、资考证的功用。如“冯惟讷《诗纪》载苏伯玉妻《盘中诗》作汉人,据此知为晋代。梅鼎祚《诗乘》载苏武妻《答外诗》,据此知为魏文帝作”(同前)。还有大量作品虽也为其他总集及诗人别集所收录,但文字常有不一致处,《玉台新咏》可在考订异同、辨析真伪方面发挥作用。
(七)《玉台新咏》在编纂体例方面也有其特色。其前八卷为自汉至梁的五言诗,第九卷为七言歌行,第十卷为五言四句的小诗,其中前六卷及卷九、十两卷均大体依作者卒年及时代先后排列,于此可睹历代诗歌的发展轨迹及其盛衰之变,特别是如梁启超所云:“欲观六代哀艳之作及其渊源所自,必于是焉。”梁启超因此对《玉台新咏》大为肯定,说:“故吾于此二选(按指《文选》及《玉台新咏》),宁右孝穆而左昭明,右其善志流别而已。”(《玉台新咏跋》)各体诗歌分卷收录,对了解各体诗歌的发展轨迹自也大有好处。此外,《玉台新咏》一改《文选》不收生人作品的成例,大收生人作品,其中萧纲作品竟多达109首,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详今略古乃至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具有开创的意义。
总之,无论宫体还是《玉台新咏》,都有其不可轻忽的价值。当然,两者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就《玉台新咏》而言,虽然“但辑闺房一体”无可非议,但同一题材、同一风格的作品读多了就难免不给人以“千人一面”之感,何况其中确有取材较为琐细、内容缺少含蕴、格调不够高、风格过于轻靡的作品,因此对作品的取舍并非无可指摘。在编排、诗题、作者归属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编排方面,卷九将《越人歌》置于《东飞伯劳歌》和《河中之水歌》之后,明显的是自乱其例。自明本增益作品之后,同一诗人的作品,甚至同题之作常被分列两处,如卷五同为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作品,其中四首列于前,一首列于后,不免给人以凌乱之感。诸如此类。
《玉台新咏》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所幸刘跃进教授的《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和傅刚教授的《〈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18年版)对此作了颇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极大方便。
大概由于不被重视,《玉台新咏》唐及唐前没有写本存世,明前没有刻本存世。现能见到的最早的传世版本是敦煌唐写本残卷,收于《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据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该本“起张华《情诗》第五篇,讫《王明君辞》,存五十一行。前后尚有残字七行”。宋已有刻本,但未能留存至今,但能见到明翻刻本,宋刻本陈玉父《玉台新咏后叙》即见于明五云溪馆铜活字本、万历张嗣修巾箱本(此本或已失传,现在能见到的为康熙四十六年刻本)和崇祯寒山赵均小宛堂覆宋本,显示这三种本子的底本当都为陈玉父宋刻本。
明清两代,《玉台新咏》版本频出,除上面已提到的三种外,尚有嘉靖间徐学谟刻本、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嘉靖二十二年张世美刻本、万历七年茅元祯刻本、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汲古阁本、崇祯二年冯班钞本、明陈垣芳刻本、清钞本、清初钞本、康熙四十六年孟璟据明万历张嗣修钞校本刻本、康熙五十三年冯鳌刻本、乾隆二十六年保元堂本、乾隆三十九年纪昀校正本、乾隆三十九年吴兆宜注程琰删补本、嘉庆十六年翁心存影钞冯知十影宋钞本、梁章钜《玉台新咏定本》、清芬堂丛书本、光绪五年宏达堂本、光绪十二年抱芳阁本等。进入民国后,尚有民国十一年徐乃昌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本等。
在以上所列诸本中,以赵均小宛堂覆宋本最受学者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本为赵宧光家所传宋刻,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重刻跋,最为完善。”梁启超《玉台新咏跋》:“赵氏小宛堂本据宋刻审校,汰其羼续,积余重刻,更并雠诸本,附以札记,盖人间最善本矣。”张尔田《玉台新咏跋》:“今宋本已罕见,无以核其异同,则赵刻要为天壤祖本矣。”傅刚云:“我自己通过对《玉台新咏》版本的调查,认为赵氏覆宋本是最合于徐陵原貌的版本。”傅刚经认真研究,认为赵氏覆宋本有初刻初印本、初刻修板印本和补板修字印本(此本为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所据本子)三种本子,以“第二次印本堪称最为精善”。
据刘跃进研究,明清版本“大体上不出陈玉父刻本和郑玄抚刻本这两个版本系统”。赵均小宛堂覆宋本、五云溪馆本、张嗣修巾箱本属于陈玉父刻本系统,茅元祯刻本、张世美刻本、汲古阁刻本则属于郑玄抚刻本系统。还有属于某些刻本的子系统,如康熙刻本、抱芳阁本、清芬堂本属于张嗣修巾箱本这个子系统,沈逢春刻本、陈垣芳刻本属于茅元祯刻本这个子系统等。
傅刚则认为:“《玉台新咏》版本存有两个系统:一是宋陈玉父系统,包括赵均覆宋本、孟璟刻本、五云溪馆铜活字本,一是明通行本系统,包括徐学谟本、郑玄抚本、张世美本、茅元祯本、沈逢春本等,这两个系统最大的区别是梁武帝父子作品排卷以及萧纲、萧绎的署名问题。”
《玉台新咏》明清时期版本不少,但注本只有吴兆宜一家。傅刚认为:“吴兆宜最初用通行本作底本注释,后来应该是发现了赵氏覆宋本,当时的学术界都认为赵氏覆宋本最合徐陵原貌,因此吴兆宜便将底本改为赵氏覆宋本。”吴兆宜注引证颇为赅博,并将明人所增益的作品退归每卷之末,注明“已下诸诗,宋刻不收”。由于吴兆宜注时有繁而失当之处及其他舛误,程琰又特予删补,将“讹者悉正,且删繁补阙,参以评点,洵为善本”(阮学濬《玉台新咏跋》),竣稿后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行。无论是吴兆宜的注本还是程琰的删补本,前人都颇表肯定,如民国时期黄芸楣曾云:“《新咏》之有吴兆宜注,殆犹《文选》之有李注乎!程琰删补,只字单辞,必求依据,雠勘之功,亦不可灭云。”(《玉台新咏叙》)
由于“《玉台新咏》自明代以来刊本不一,非惟字句异同,即所载诸诗亦复参差不一”,于是纪容舒“详为校正,各加按语于简端,以补其所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遂有了《玉台新咏考异》十卷。该书参校诸书,确实校正了诸本不少错误。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云《考异》实为纪昀所撰,因某种原因而“归之于父也”。刘跃进经过考证,认为此说可信。
1985年6月,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了穆克宏点校本《玉台新咏笺注》。该书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行的程琰删补本为底本,并以赵均覆宋本、五云溪馆本、纪容舒《考异》和《太平御览》等类书参校,有参考价值的异文皆出校记,能够断定讹误的在校记中予以说明,但不径改原文。书后除附有原书十二篇序跋外,又辑补了二十八篇序跋,颇便于研究者参考。
傅刚的《〈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分为上、下两编。下编《〈玉台新咏〉校笺》(不出作品全文,宋刻不收者不校笺)是近年来《玉台新咏》整理、校笺的最重要成果。该《校笺》以赵氏覆宋陈玉父本做底本,以清人笺校考释为考察对象,以清人所参考利用的明代版本为主要的参校本,并以清代以前各总集、类书、别集等参考、参校。这项工作耗时十余年,作者“爬梳剔抉,参互考寻”(《宋史·律历志》),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比如,由于《文选》与《玉台新咏》关系最近,二书所选作品相同者最多,因此作者所采用的《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各种版本竟多达十余种,除刻本外还兼及写钞本,如日本藏九条家本等。作者向来重视版本研究,通过版本研究发现了许多问题,写成系列论文发表,从而大大推进、深化了对于《玉台新咏》的研究。
(一)本书译注原文所依从的本子,为穆克宏点校本《玉台新咏笺注》,各本《玉台新咏》所存在的异文,则参照、利用傅刚《校笺》所取得的成果。由于傅刚《校笺》不校宋刻不收者,所以本书仍在穆克宏《笺注》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必要的校勘工作,引为校本的是宋以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总集和类书,主要有以下几种:
1.《文选》,(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重刊宋尤袤本。
2.《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日本足利学校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
3.《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排印汪绍楹校订宋绍兴刻本。
4.《初学记》,(唐)徐坚等撰,中华书局1962年版。
5.《太平御览》,(宋)李昉等撰,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文苑英华》,(宋)李昉等编,中华书局1966影印宋、明刊本(其中宋刊140卷,明刊860卷)。
7.《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有参考价值的异文,都在注文中标出。能够断定讹误或明显不妥的,为与译文保持一致,径改原文,并在注文中加以说明。所发现的异文同时见于他本《玉台新咏》者,为避烦琐,不再标列。但未曾发现的异文在他本中出现,则以引用傅刚《校笺》相关文字的方式予以标列。傅刚《校笺》引用纪容舒《考异》文字如有所取,也用此种方式处理。傅刚《校笺》所用参校诸本的简称为:明五云溪馆活字本简称五云溪馆本,明徐学谟本简称徐本,明郑玄抚本简称郑本,明张世美本简称张本,明茅元祯本简称茅本,明沈逢春本简称沈本,赵氏覆宋本简称赵本,明冯舒冯班校、清冯鳌刻本简称冯鳌本,明陈垣芳刻本简称陈本,清康熙四十六年孟璟据明万历张嗣修钞校本刻本简称孟本。由于《文选》《艺文类聚》等总集、类书存在不同版本,在傅刚《校笺》中出现的他本异文酌情予以标列。除原文外,诗题也有存在异文的情况,均在“题解”中加以说明,有的应以异文为是,但诗题仍保留原貌,不径改。
(二)全书除前言外,以作品为单位,分为“作者简介”“题解”“原文”“注释”“译文”五个部分,具体情况如下:
“作者简介”对作者的基本情况包括生卒年、所处朝代、主要经历、文学成就、创作特色等予以介绍,作品收录不只一篇者,其情况只在首次出现的作品“作者简介”中介绍,后以参见从略。
“题解”对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思想艺术特色,特别是在艺术上的特色予以分析说明。如有前人的适切评论,随文加以征引。力求突出重点、特点和难点,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言不烦,点到为止。书中有不少组诗,有的同为一题(如卷八王筠《春月二首》《秋夜二首》),或所咏为同一题材甚至同一件事(如卷九《汉成帝时童谣歌二首》),一般只写一个题解。有的是将若干首诗临时集为一组,既有一个总的题目,同时组内各诗又往往自有题目者(如卷一《古乐府诗六首》),一般每首诗都有题解。
“注释”主要注释较难理解的字、词(包括成语、双关语等)。因有译文,因此一般不再做句意的串讲,文字力求准确简明。前人旧注有价值者,酌予引录,尤其是对词义的训释,为保持原始面貌,避免走样,有前人训释者尽量予以引录,一词多义者则以己意断之而有所弃取。难认字加注拼音。
“译文”以白话诗的形式出现,以信、达、雅作为追求的目标,对“信”尤为看重。所谓“信”,就是忠实于诗的原意,目的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诗。译文一般只将字面的意思译出,用隐喻、象征、借景抒情等手法表达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原则上留给读者自己去揣摩、想象和构建,一般在字面意思之外也尽量不再额外增添修饰性的词语。译文除力求准确、流畅外,还力求表现出原诗的风格,传达出原诗的神韵。
(三)原书前有目录,但较简略,如卷一有《古诗八首》,但不出八首古诗的标题。为方便读者查阅,本书将每首诗的标题均一一列出,并将原书目录与书中正文标题不一致的地方加以统一(如原书卷八目录有《刘孝绰杂诗五首》,而书中正文前却只“刘孝绰”三字,本书在“刘孝绰”三字后补上了“杂诗五首”四字)。
(四)由于本套丛书定位为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本的全本注译图书,因此本书努力将“准确”“谨严”作为追求的目标。凡引文必与原文核对,并标明出处,以方便读者查核。由于诗歌意旨多采用委婉、含蓄、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的手法加以表现,特别是作品的形象、意象、意境中往往有着极为丰富但又令人难以捉摸、确定的蕴涵,因此给人们的解读留下了非常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但是,其解读实际上也有个准确不准确、到位不到位的问题,其判断的标准就是:读者所理解的东西是不是符合文本总体的指向性,是不是在文本所提供的客观材料和信息(主要是其语言文字及运用语言文字所构建的形象、意象、意境等)所规定的方向和范围之内。因此,本书对作品的解读注重从文本实际出发,绝不信马由缰、天马行空,绝不穿凿附会,力避对作品的曲解和误解。
本书的写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初稿完成约三分之二时,因故停了下来,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停就停了二十多年。当时尚未使用电脑,全靠手写,我写出初稿后,由内人王笏用专用的稿纸誊正,其字迹端丽,读来令人赏心悦目。今天旧稿仍在,而斯人已逝。这次对旧稿重加整理,见字如面,岂能不悲从中来、感慨系之!
近年因拙著《嵇康集校笺》在中华书局出版,因此与书局相关编室及编辑有较多联系。去年元月,因书局要再版由张启成、徐达二位教授主编,我亦为作者之一的《文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台湾台北古籍出版社1996年繁体字版),我又得以结识书局基础图书出版中心编辑熊瑞敏先生。我向熊先生提出我有这样一部书稿,能否纳入《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出版,他当时没有做出明确表态,但显然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两月后,熊先生来电,说让我提供一份样稿。样稿很快获得通过,并很快得到将书稿立项的允诺,于是我立即转入紧张的工作状态,对旧稿进行修订和补充,并完成尚未完成的部分。经过近一年半焚膏继晷、矻矻不已的努力,书稿终得告竣,这自然让人感到十分释然、欣然。
在修订、补充和完成书稿的过程中,与熊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不断从他那儿得到支持、鼓励,和非常专业的指导意见。基础图书出版中心主任王军先生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本书译注原文所依从的本子为福建师范大学穆克宏教授点校的《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各本《玉台新咏》所存在的异文,则参照、利用了北京大学傅刚教授《〈玉台新咏〉校笺》(中华书局2018年版)的成果。谨此一并致谢!
无论题解、注释还是译文,或都存在疏漏乃至谬误之处,敬祈读者、方家不吝教正。
张亚新
2020年8月于北京玉渊潭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