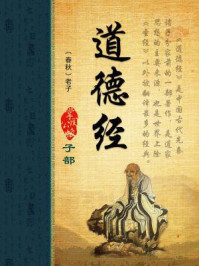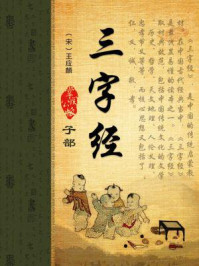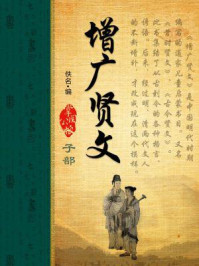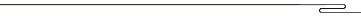
山水诗由谢灵运确立,这是公认的事实。因而欲明山水诗的起源,前提就是对谢诗之传承、体势、演进轨迹的切实把握。但通行文学史的叙述似把二者关系倒了过来:先由刘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二语得出山水诗源于玄言诗的观念,从而认定谢诗先天地有“玄言尾巴”,每有象意分离,有句无篇之病;再反过来以所谓“玄言尾巴”证明山水源于玄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循环论证。王世贞云:“余始读谢灵运诗,初甚不能入;既入而渐爱之,以至于不能释手。”
 于是对难入而多争议的谢诗作“入里”的再研究,就是对山水诗起源再探讨的必循之途。
于是对难入而多争议的谢诗作“入里”的再研究,就是对山水诗起源再探讨的必循之途。
笔者无意否认玄风对谢诗的影响,且充分肯定玄风曾启迪了魏晋后人对自然的崇尚,然而这与山水诗起源于玄言诗说不侔。文艺之受影响于哲学,并非总是直接的反映,否则一切作品都成了思想的图解。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要求研究者注意“思想在实际上是怎样进入文学的”,并认为思想只有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时,于文学方有意义。此论对本题的研究颇有启发。
哲学之影响于文学,必须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其中最主要的是,哲学首先要转化为一定的、人各有异的生活观念或情趣,积淀于作者的心态中,再通过创作,进入各各有别的文体内。因此,同一思想对不同人、不同文体的影响势必不同;否则百歌千咏,各种文体又将归为一律。这一点对研究特重体势的中国古典诗歌尤为重要。体势即“因情立体,即体成势”
 ,说的是文各有体,作者情致不同,应选取不同的文体,既循文体之格局,又变化而达其意,才能产生自然的文势。所以说“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
,说的是文各有体,作者情致不同,应选取不同的文体,既循文体之格局,又变化而达其意,才能产生自然的文势。所以说“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
 。因此要切实研究山水诗之起源,必须抓住两个要点:其情主何,其体孰承。
。因此要切实研究山水诗之起源,必须抓住两个要点:其情主何,其体孰承。
山水诗起源于玄言诗之说,在这两点上都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玄言诗是现代人诗史研究中出现的极笼统含糊的概念。玄风被及一代,当然会影响众多的诗人、诗体。如果把一切带有玄言成分的诗都划入玄言诗——姑且假设这一界定成立——则所谓谢客山水诗渊源于玄言诗,就是一个空泛而毫无实际意义的命题,因它既根本回答不了山水诗主要由当时哪一体诗蜕出的问题,更无助于深究其自身的体势。因此,必须仔细考察玄风进入诗歌不同的实际情况。魏晋以降,诗歌受玄风影响,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玄风通过玄学家
 主理的个性进入当时各体诗中,以谈玄的方式作诗;这是玄风在诗歌中的“自惩”。其失有二。一是诗各有体,谈玄在各体诗中的滥用,必然“离体立势”,“使体束于势,势虽若奇,而体因之弊”;
主理的个性进入当时各体诗中,以谈玄的方式作诗;这是玄风在诗歌中的“自惩”。其失有二。一是诗各有体,谈玄在各体诗中的滥用,必然“离体立势”,“使体束于势,势虽若奇,而体因之弊”;
 二是玄风本来启迪了人与自然的接近,但由于一味“崇盛亡机之谈”,而“嗤笑徇务之志”,反使诗作脱离生活的自然,遂使间或出现的片断山水也“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
二是玄风本来启迪了人与自然的接近,但由于一味“崇盛亡机之谈”,而“嗤笑徇务之志”,反使诗作脱离生活的自然,遂使间或出现的片断山水也“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
 成为理念的附庸,因而将哲理诗连同山水描写也带入了死胡同。今存许询、孙绰等人绝大部分诗作,“皆平典似道德论”,虽间有山水,也“淡乎寡味”,其因盖出于此。然而思想材料的作用往往大于材料本身。玄风在“自惩”的同时,又在另一种情况下得以“自赎”。其最突出的功绩是玄学思辨通过诗人主情主美的个性,进入诗作,从而促使事物景物观察的深化,促进各体诗在六朝向富于理趣的方向发展。
成为理念的附庸,因而将哲理诗连同山水描写也带入了死胡同。今存许询、孙绰等人绝大部分诗作,“皆平典似道德论”,虽间有山水,也“淡乎寡味”,其因盖出于此。然而思想材料的作用往往大于材料本身。玄风在“自惩”的同时,又在另一种情况下得以“自赎”。其最突出的功绩是玄学思辨通过诗人主情主美的个性,进入诗作,从而促使事物景物观察的深化,促进各体诗在六朝向富于理趣的方向发展。
要之,玄风使六朝各体诗表现出两种走向:其一是因玄风直接的粗暴的介入,各体中都有许多篇什抽象谈玄,因而乖离、破坏了其原有体势,连本以说理为主的哲理诗,也被扭曲为玄言化的哲理诗,亦即玄言诗。玄言诗不是另起炉灶的新诗体,而是鸠占鹊巢地附着于传统各体(如赠答、咏怀等)上的赘疣。故此六朝的诗体分类根本无玄言一目。另一走向是各体诗中仍有许多诗作保持着其原有的体势,玄风只是对它们产生若干影响,却往往能有机地成为其肌理中的一分子,使理语化为理趣。它们不是玄风的必然产物,而是传统体格在六朝的循体而能变。这类诗作当然不能划入玄言诗范畴,否则必将导致阮籍《咏怀》诗后(特别是东晋)只有玄言诗,连谢朓乃至唐代王孟的诗都是玄言诗的论断,似乎玄言诗中断了传统诗体发展达二百年。这是与史实不符的。因此研究山水诗渊源又必须明辨两点:首先是它发生于何种传统诗体,其次是发生于这种诗体中的何种走向。为此须先对东晋玄言诗发生前各体诗中的山水成分作切实的分析。
玄言诗发生前各体诗中都已有山水成分,其中宴游、行旅(兼及行旅性的赠别杂诗)两类以行游为特征的诗更已达到了较高水准。宴游写景建安时就较发达,如曹植《公宴》: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摇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这类宴游诗,其实已执历来被认为是山水先驱的晋宋间人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和谢混《游西池诗》之先鞭。殷诗为从桓玄游九井所作。谢诗《文选》注引《宋书》云:“西池,丹阳西池,混思与友朋相与为乐也。”《新唐书·艺文志》更有颜延之《西园宴游诗集》,此诗当在其中,可知均为宴游,而宴游亦为可独立的诗体。试看谢诗:
悟彼蟋蟀唱,信此劳者歌。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无为牵所思,南荣诫其多。
其与曹植诗都先述事因,中段写景,结以抒情。二者传承,无庸置疑。
较宴游诗写景更出色的是行旅诗,由建安而至晋代潘、陆诸家愈益精细,试看潘岳《河阳县作诗二首》其一:
微身轻蝉翼,弱冠忝嘉招……长啸归东山,拥耒耨时苗。幽谷茂纤葛,峻岩敷荣条。落英陨林趾,飞茎秀陵乔,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徒恨良时泰,小人道遂消,譬如野田蓬,斡流随风飘。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登城眷南顾,凯风扬微绡。洪流何浩荡,修芒郁岧峣。谁谓晋京远,室迩身实辽。谁谓邑宰轻,令名患不劭……福谦在纯约,害盈犹矜骄。虽无君人德,视民庶不恌。
此诗在潘岳行旅诗中是写景成分较少而议论成分较多的一首,但其格局深可注意:首述事因,结以抒情二点一同于前引二诗;而中间部分则写景叙事交叉,所写景物分为二层。这种格局在晋诗中极少见,但它正是谢灵运山水诗的最典型的体式。
宴游、行旅诗中写景成分的发展决非偶然。诗人游行于园林山水之中,取为诗资以表情达意的媒介当然是自然,且因身临其境,感受真切,从中发展出山水来,顺理成章。今以谢客创作历程概略证之。
今存谢诗,除乐府(很少写景)外,大多可确定大体作时。永初三年(422)前存诗唯《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及《三月三日侍宴西池》二首宴游诗稍涉景物;然而自永嘉之贬后山水成分多了起来。首可注意者是赴任途中的行旅诗:《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邻里相送至方山》《初往新安桐庐口》《富春渚》《七里濑》《过始宁墅》等。一些公认的山水名句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定山缅云雾,赤亭无淹薄;溯流触惊急,临圻阻参错”(《富春渚》);“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七里濑》)等已出现。此后谢客写了大量模写山水之作,一为游览,一为行旅,交相影响,日益精进,如景平元年初去永嘉之“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初去郡》);元嘉七年自京往临川之“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都是谢客代表作。永嘉之贬是谢客仕途中的转折点,却又是诗歌创作新境界出现的转捩处。谢客作为中国山水诗鼻祖的地位,显然是由其宴游诗,特别是行旅游览诗奠定的。这一初步结论可由《文选》验之。
《文选》大抵依题材分诗为22类,独无玄言与山水二类。有关山水之作包括谢客山水诗主要收入“游览”与“行旅”两类,
 其他如“公宴”“赠答”“杂诗”“祖饯”等类中某些篇章也有较多的山水描写,而不少或可视为以上二类之附类(公宴、祖饯);或其中山水之作大体与行旅或游览相关(赠答、杂诗)。所以要理清今人所说“山水诗”的来由,主要应考察“游览”“行旅”二类。
其他如“公宴”“赠答”“杂诗”“祖饯”等类中某些篇章也有较多的山水描写,而不少或可视为以上二类之附类(公宴、祖饯);或其中山水之作大体与行旅或游览相关(赠答、杂诗)。所以要理清今人所说“山水诗”的来由,主要应考察“游览”“行旅”二类。
先可注意者,为“游览”诗中宴游与独游之杂陈。此类首列曹丕《游芙蓉池》诗,曹植有同题和作,无疑为宴游诗。以下即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及谢混《游西池诗》二宴游诗。他如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等性质均同。而于谢客山水名篇者首列宴游诗《从游京口北固应诏》,更列《晚出西射堂》《登池上楼》《游赤石进帆海》等独游名篇。整个“游览”类中宴游诗占4/10,且前期之作均为宴游,可见群体而游的宴游诗实乃独游诗之一种先导,独游诗至谢客才发展成熟,故在南朝人心目中并无本质区别,而今天正可从中看出山水诗与宴游诗的血缘关系。
其次是游览诗与行旅诗的交叉。《文选》行旅类中如潘岳《迎大驾》、陆机《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其实是宴游诗。而如谢灵运《登江中孤屿》《入彭蠡湖口》《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或为独游作,或为行旅中游览之篇。尤其是《登江中孤屿》,本与“游览”类之《游赤石进帆海》是一次游程中的两首诗。这说明行旅与游览二类其实很难区分。行旅应为独游的又一先导。因为行旅途中本不妨于一地作游览。而较长的游程本身就有行旅性质。谢客更每于谪放的行旅中借登临山水一泻块垒,又独创为百里之上以山水为目的的远游,于是在他身上就明显地体现了山水诗逐步形成的轨迹。他在早年的宴游诗中初步锻炼了写景才能,在永嘉之贬的行旅诗中提高了山水成分与质量,然后在永嘉后的行旅式的远游中将山水诗发展成熟,也反过来使他的行旅诗同样具备游览山水的性质。此后在归隐始宁,征召赴京,二度归隐,外放临川时,行旅与游览更成为难以分割的模写山水的两种基本形式。至此谢客山水诗由宴游,特别是行旅诗中蜕出当无可疑。
那么谢客又继承了原有以行旅为主的诗体中何种走向呢?这要从建安诗内涵的重大突破谈起。从建安起,诗歌中情与事的关系起了重大变化。从《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都是即具体之事而发具体之情。即使抒情性极强的《古诗十九首》也多如此,如《青青河畔草》为思妇感春,《驱车上东门》为哀叹无常等等。唯楚辞时或突破这种框架,如《涉江》,所抒之情,非涉江事件可牢笼,而包容了屈原深广的爱国之思,但这种感情仍与去国流放相关,情对事的超越还不充分。虽如此,楚辞之体近五百年中也基本未获发展。“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诗人开创了诗歌个性化的时代,其大量篇章中情对于事已有了明显升华,诗情不仅仅是即事生情的具体之情,而多借事(物)引发,抒写积郁的情思乃至理念,充分展示一己个性,亦即作者潜在的意识,特定的心态,独异的气质。建安后出现的大量咏物、咏史、咏怀诗及所谓“不拘流例,遇物即言”
 的杂诗,就是与这种创作方法相应的新诗体。如曹植《杂诗六首》之五:“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诗中之事是由洛阳东归雍丘封藩,但于行程却无多笔墨,所抒之情更非旅途观感;而将现实的远游与理想中的平吴远游糅合在一起,在矛盾痛苦中写出骨肉相煎之憾,壮志难酬之悲,情已完全超越了事件本身的含义。
的杂诗,就是与这种创作方法相应的新诗体。如曹植《杂诗六首》之五:“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诗中之事是由洛阳东归雍丘封藩,但于行程却无多笔墨,所抒之情更非旅途观感;而将现实的远游与理想中的平吴远游糅合在一起,在矛盾痛苦中写出骨肉相煎之憾,壮志难酬之悲,情已完全超越了事件本身的含义。
这种创作方法也影响到其他如赠别、行旅、宴游之作中,如前举子建《公宴》诗,清秋澄明的夜空之下,“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的景象,潜在地表现了邺下文人开阔的心态,高昂的意气。而公宴本身已并非所要歌咏的了。对照《小雅·宾之初筵》之极写宴饮之状,区别显而易见。《文心雕龙·明诗》云:建安诗人“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正说出风月宴游之事,只是诗人任气使才(才性)的触媒而已。
情对事的升华,是建安诗人对诗史最重大的贡献,它既说明个性的自觉,使诗境由质实向疏朗高迈发展;也必要求创作技巧的更新。因在这种情况下,抒情已不再能凭事件为线索,诗人必须以个性诗化外物,使不必相关的情事融成整体,这就须对事物作更深细的观察,提炼出与个性合若符契的成分;要求以更大的组织才能去谋篇布局,将散珠片玉糅合为一。可以说建安诗史的一切进境,都是以情对事的超越升华为出发点的。这样,建安后的宴游、行旅诗,实质上多已成为以景物描写为媒介的咏怀诗,特别是行旅性诗因最得江山之助,故自曹丕《于玄武陂作》、曹植《赠白马王彪》后,西晋潘陆张昆仲等,虽间融玄语而体势一贯,踵事增华,刻画亦精(如前引潘诗);但晋室南渡后,因玄风更炽而分化渐明。一类如桓玄《登荆山》:“理不孤湛,影比有津。曾是名岳,明秀超邻。器栖荒外,命契响神,我之怀矣,巾驾飞轮”;庾阐《衡山诗》:“北眺衡山首,南睨五岭末,寂坐挹虚恬,运目情四豁。翔虬凌九霄,陆鳞困濡沫。未体江湖悠,安识南溟阔”,均将孙绰答许询式的哲理诗体强纳入游览体,全乖体势,故其山水描写被窒息为“翔虬”“陆鳞”句那样肤廓非现实的寡淡东西。较之潘陆等明显倒退,也使情对事的超越走向其反面,变成附赘性的玄言诗。
这里还应补充分析常与玄言连言的郭璞《游仙》。郭诗气体才丽逸荡,较之平典的玄言诗显然富于情致个性。然观其景物却多为以绿萝、清波、丹霞、云梯类词组成的笼统意象。故读郭诗,一篇甚佳,而全组并看,顿觉雷同。这是因为“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
 ,其体势本就是主理超世而象征性的。郭璞之功在“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
,其体势本就是主理超世而象征性的。郭璞之功在“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
 ,以其卓拔之性情及出色的诗才将源于楚骚、成乎何劭的传统游仙诗推向新境。但终为游仙“志狭中区”的象征性体势所囿,故其山水性质必然笼统。试问,有谁能真切地观察摹写仙境呢?《文选》单列游仙一类,绝不与行旅、游览类相互交叉,正可见其体势与入世主情,深于体察的行游、游览不同。应当说郭璞对谢客有所影响,这主要在于风调之才丽逸荡上,而非山水意象构成的取径上。今存谢诗无纯然游仙之篇,却每于行旅游览中参以游仙笔调;《文选》亦绝不将此类谢诗收入“游仙”,正可见其主次。因此,郭璞《游仙》可说是对山水诗形成起了辅助作用,只是并非辅助于赘生的玄言诗,而是辅助于传统的宴游行旅诗体。
,以其卓拔之性情及出色的诗才将源于楚骚、成乎何劭的传统游仙诗推向新境。但终为游仙“志狭中区”的象征性体势所囿,故其山水性质必然笼统。试问,有谁能真切地观察摹写仙境呢?《文选》单列游仙一类,绝不与行旅、游览类相互交叉,正可见其体势与入世主情,深于体察的行游、游览不同。应当说郭璞对谢客有所影响,这主要在于风调之才丽逸荡上,而非山水意象构成的取径上。今存谢诗无纯然游仙之篇,却每于行旅游览中参以游仙笔调;《文选》亦绝不将此类谢诗收入“游仙”,正可见其主次。因此,郭璞《游仙》可说是对山水诗形成起了辅助作用,只是并非辅助于赘生的玄言诗,而是辅助于传统的宴游行旅诗体。
玄言、游仙外,南渡后承传统宴游、行旅体势的作品依然存在。如李颙《涉湖》:“旋经义兴境,顿棹石兰渚,震泽为何在,今唯太湖浦。圆径萦五百,盻目渺无睹,高天淼若岸,长津杂如缕。窈窕寻湾漪,迢递望峦屿,惊飙扬飞湍,浮霄薄悬岨。轻禽翔云汉,游鳞憩中浒。黯蔼天时阴,峣岧舟航舞。凭河安可殉,静观戒征旅。”又如兰亭游宴诗中部分佳作,如孙统诗:“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因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二诗均顺建安以来借景物写情明志的传统体势,且景物成分增多,观察描写加细,唯情致略微有别。后诗更多庄玄情趣,笔法也较疏朗,因此与玄言诗的区别更为微妙。关于这一点,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指出:“庾阐诸人”的诗是“玄学的概念性的诗。凡属概念性的诗,必是抽象的、恶劣的诗”,是“浅薄的”,“仅有思辨而未能落实于人生之上的”。又认为陶谢诗才将老庄思想“反映在文学作品上”,是“为了满足美的要求”,尤其陶诗更将庄子思想化为恬适自然的生活情趣云云。这个区划很重要,可借以观察桓、庾二诗与李、孙二诗在写作思维上的本质区别。但徐说似尚有可商榷之处。首先,这种区别并非尽是由庾阐等人到陶谢,依时间先后从概念性到文学性。庾、桓与李颙、孙统本属同一时代。可见前析玄风实际进入诗歌,分化为抽象的、反文学的与有机的、文学的两种相反形态,在南渡后并非先后而是同时并存的。其次,写作方法对文学的这种向与背,必然落实到诗歌体势的离与合。只有明辨体势传承,方能理清发展序列。对传统的行旅、游览诗来说,桓、庾二诗既背体离势,阻遏了山水成分的进展,因而作为“卓越的艺术作品”的谢客山水诗,必不能产生于庾、桓那种玄言诗的贫瘠土壤上;而理当上承曹陆潘张乃至李颙、孙统、谢混一系,并兼参郭璞游仙之逸荡才丽气调。这是大的走向上的区划。
刘熙载云:“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
 陶谢与孙绰等所循大走向相反,故品格迥异;陶谢之大走向同,均使理语融于景入乎情顺乎体,故能化理语为理趣。而又各有胜境,则因虽能循体而变,但内含情致有异,亦引起创作手法之别,诗歌境界之异。陶且不论,今更从谢客诗体势以及演进过程的具体分析来进一步确证上文关于山水诗起源的辨析。
陶谢与孙绰等所循大走向相反,故品格迥异;陶谢之大走向同,均使理语融于景入乎情顺乎体,故能化理语为理趣。而又各有胜境,则因虽能循体而变,但内含情致有异,亦引起创作手法之别,诗歌境界之异。陶且不论,今更从谢客诗体势以及演进过程的具体分析来进一步确证上文关于山水诗起源的辨析。
不妨先来分析一下一些常见的最早评论:
颜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

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

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富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现将上述各条有关要点分列如下:(1)指出谢诗源于曹植,即以建安体为骨格;(2)指出谢诗兼取张协,能“巧构形似之言”
 ;(3)指出谢诗“兴多才高”“兴会标举”,这与论建安诗人之任气使才有所不同;(4)认为谢诗之美是一种自然美;(5)认为谢诗有“逸荡”之气;(6)认为谢诗时有繁芜或体格放荡,不辨有首尾之病。六点中一至三尤为重要,指出了谢诗的渊源与创作方法上的重要特征,试论之。
;(3)指出谢诗“兴多才高”“兴会标举”,这与论建安诗人之任气使才有所不同;(4)认为谢诗之美是一种自然美;(5)认为谢诗有“逸荡”之气;(6)认为谢诗时有繁芜或体格放荡,不辨有首尾之病。六点中一至三尤为重要,指出了谢诗的渊源与创作方法上的重要特征,试论之。
谢诗既承曹植之“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故其山水当为抒发意气的媒介。但另一方面,谢诗又将宴游、行旅中的山水成分,发展成游览性的山水诗,这必然使他取熔“巧构形似之言”的张协等的太康诗风,而更注重对山水形相的精细刻画。如果说建安以来的宴游、行旅之作,是以情意为明显主线来驱遣片断之景物的单线结构;那么到谢灵运的山水诗,则经由景物成分的逐渐增加,而逐渐发展成以游程中所见景物为明线,而以情志所生的感情为时隐时现于景物之下的暗线的双线结构。其格局较前人远为复杂。这一点,唐代一些大诗人其实已有所觉察。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久为谢客寻幽惯,细学周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白居易《读谢灵运诗》:“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二人皆拈出了谢诗在重重掩掩的山水草木中潜伏着的以幽愤为主要特征的感情线。细咏之,能于其中领略到与常作不同的逸韵与奇趣。
,故其山水当为抒发意气的媒介。但另一方面,谢诗又将宴游、行旅中的山水成分,发展成游览性的山水诗,这必然使他取熔“巧构形似之言”的张协等的太康诗风,而更注重对山水形相的精细刻画。如果说建安以来的宴游、行旅之作,是以情意为明显主线来驱遣片断之景物的单线结构;那么到谢灵运的山水诗,则经由景物成分的逐渐增加,而逐渐发展成以游程中所见景物为明线,而以情志所生的感情为时隐时现于景物之下的暗线的双线结构。其格局较前人远为复杂。这一点,唐代一些大诗人其实已有所觉察。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久为谢客寻幽惯,细学周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白居易《读谢灵运诗》:“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二人皆拈出了谢诗在重重掩掩的山水草木中潜伏着的以幽愤为主要特征的感情线。细咏之,能于其中领略到与常作不同的逸韵与奇趣。
景物的明线(山水)与情志的暗线(咏怀)如何统一起来呢?这就要靠“兴会”,亦即情景泊然相会而勃然以兴的创作冲动。因“兴会标举”,故“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万物奔凑于笔底,而借“才高”来一一活现之,这就形成了谢诗“逸荡”的气势,也带来了某些篇章“繁芜”的毛病。此体固非习惯于宫体轻浅的齐高帝所能领略,故有所谓“作体不辨有首尾”之讥。
对今人来说,最难理解的恰恰是鲍照及汤惠休评谢诗“如初日芙蓉,自然可爱”二语。但若明确了谢诗的体势特征,再参以南朝人的自然观,就十分了然了。
玄学兴起,使两晋后人的自然观,较之先秦两汉儒道两家的素朴自然观,有了重大进展。这一问题颇为复杂,笔者另有专文详论,这里仅挈其要点如次:
玄学自然观,首先变老庄崇本黜末观念而为崇本举末,这就为打破大音希声的传统观念,重视万事万物的具体规律,提供了哲学基础。反映于美学,玄学自然观继承了先秦儒道以和谐为美的思想,却从原来片面强调整体的和而小视局部的谐,转而形成执一驭众,由局部之谐返于整体之和的思想。在这里郭象有关任物之性以使之而不过当的观念尤其重要。在庄子看来,对外物的一切人为干预,都会损害物的自然本性,譬如穿牛络马等等,均为反道之举。但郭象却认为,牛马之本性就是以能载善跑而可供役使,一味放之于野,非但不是全其本性,相反却是埋没了自然之材,因此穿牛络马使之拉车驱驰,才是任物之性。唯其不能过当;能跑八百里的马,不要让它跑八百零一里也就是了。
 魏晋后大量研讨艺术风格、方法的音乐、绘画、书法、文学“工拙之数”
魏晋后大量研讨艺术风格、方法的音乐、绘画、书法、文学“工拙之数”
 的论著正是产生于这种自然观念之下。如刘勰《文心雕龙》以“自然”为纲,但全书谈的则是各文体的演变史及各种文学手段。在刘勰看来,只要深明这些艺术手段的工拙之数,精微之理,得其中而不侈,就能达到自然之美。应当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然美。以上是玄学自然观影响创作方法在客体方面的主要体现。
的论著正是产生于这种自然观念之下。如刘勰《文心雕龙》以“自然”为纲,但全书谈的则是各文体的演变史及各种文学手段。在刘勰看来,只要深明这些艺术手段的工拙之数,精微之理,得其中而不侈,就能达到自然之美。应当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然美。以上是玄学自然观影响创作方法在客体方面的主要体现。
再就创作主体看,玄学才性观的更新影响尤著。老庄眼中的自然人是原始状态的,因此,七窍凿而混沌死。汉末三国,才性讨论兴起,而均以才性同一不二,
 无形中否定了积学富才与自然本性统一的可能。晋代以降,很多迹象说明才性观念有了进展。葛洪《抱朴子·勖学》说:“虽云色白,匪染弗丽;虽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丹青不治,则纯钩之劲不就。火则不钻不生,不扇不炽;水则不决不流,不积不深。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意谓人的自然本质只有通过刻苦学习,反复磨练,方能焕发出内在的美来。这与庄子的说法大异。此种才性观影响了六朝文论,而集大成者则是《文心雕龙》。《体性》云:“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人的才、气、学、习四者,均因天资的差别及外界的陶染而异,却一并凝聚到各自的情性中来,又为“情性所炼”而融和为人人各异的才性。这样“情动而言形”,“因内而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方有文坛的云谲波诡。可见刘勰的情性观明显地具有重视陶染与才学的特色。在他看来,凡合才、学、性为一体的人,都是“自然之恒资”
无形中否定了积学富才与自然本性统一的可能。晋代以降,很多迹象说明才性观念有了进展。葛洪《抱朴子·勖学》说:“虽云色白,匪染弗丽;虽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丹青不治,则纯钩之劲不就。火则不钻不生,不扇不炽;水则不决不流,不积不深。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意谓人的自然本质只有通过刻苦学习,反复磨练,方能焕发出内在的美来。这与庄子的说法大异。此种才性观影响了六朝文论,而集大成者则是《文心雕龙》。《体性》云:“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人的才、气、学、习四者,均因天资的差别及外界的陶染而异,却一并凝聚到各自的情性中来,又为“情性所炼”而融和为人人各异的才性。这样“情动而言形”,“因内而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方有文坛的云谲波诡。可见刘勰的情性观明显地具有重视陶染与才学的特色。在他看来,凡合才、学、性为一体的人,都是“自然之恒资”
 。可见六朝人心目中的自然人也同样是更高层次的自然人。
。可见六朝人心目中的自然人也同样是更高层次的自然人。
主体和客体合而观之,六朝时新的自然美观就是:合才学与情性而为一的自然人,精研各艺术部类手段精微的自然之理、工拙之数,而后以情性为本,执一驭众,任物之性以使之而不过当,从而由谐求和,达到高层次的自然美。玄学自然美的本质精神对文艺的启迪意义,即在于此。
刘勰虽晚于谢客数十年,但其《文心雕龙》一书却是晋宋以来各种思想成果的结晶。而一部《世说新语》,以自然为尚,记言叙事无不英华焕发,往往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正说明这种观念在晋宋时已化为士人的生活情趣。谢客在此之前,已得风气之先。他在《辨宗论》中发挥竺道生的顿悟见性说为“积学顿悟”说,使积学与明性相统一,堪称才性学合一思想的先声。他崇尚建安诗人,作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从他对前代诗人“罗缕岂阙辞,窈窕究天人”“众宾悉精妙,清辞洒兰藻”的向往中,又可见他以建安风力与罗缕之辞,即美文清音相统一的观念。至此,鲍照“谢颜高下”之论的含义就不难理解了。
谢诗既以幽愤为骨格,以情与景契的兴会为发端,将其饱学多才的个性融注到山水之中,“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当然被认为“如初日芙蓉”之清丽而“自然可爱”,即使间有繁芜之病也无损其“青松”“白玉”之自然品格。至于颜诗之“铺绣列锦”,显为缺少谢诗之内在真气、用文过当所致,所以“雕缋满眼”,只能等而下之。
要之,谢客继承了建安诗任气使才的传统,以幽愤为内核,又兼取晋诗之工于造型,并顺应晋宋间新的自然观,一以高才博学的个性出之,创造了远较前人复杂的诗歌格局,也引起艺术手法的一系列创新,形成前所未见的诗歌境界。这是诗史上又一次重大新变,其主要表现是:
诗体——由建安偏重于情的行旅、宴游等作发展而为情景并重泊然相凑的山水诗(主要为行旅、游览)。
立意——变建安诗之任气为主而为“兴会标举”,使言志抒情向兴趣转化,遂使玄风之影响化为理趣。
结构——变建安诗之以情驭景、景以衬情的单线结构而为情景双线、明暗交相为用、曲折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也引起了诗作章句位置上一系列艺术手法的创新。
意象——变建安诗多基于印象的、情意显豁的粗线条的景物描写而为基于细致体察的、情意深蕴的多层次的工笔写景造型。刘勰所说的“隐秀”,实由谢诗发轫。
语言——变建安诗之清健自然为由钻砺而返之自然,从而也引起遣词造句、使典用事技巧的一系列新变。
风格——变建安诗之磊落慷慨、清刚发越为潜气内转、密丽深秀。韩愈以“清奥”评谢诗,
 可谓一语破的。
可谓一语破的。
风格是以上诸艺术因素的总和,由建安诗之清刚到谢灵运诗之“清奥”,体现了诗史演进上一个有趣的循环上升的过程。建安诗中情对事的超越升华,加以语言的明健,遂使格局向疏朗发展,于是清刚之气便洋溢于字里行间。谢客依游程顺序摅写幽愤的诗作,看来情与事重归合一,加以刻画精工,格局遂向密致演变(这个苗头在晋诗中已可见出);但是这并非简单的回归。因为作为其内核的幽愤,渗透并左右着每个诗歌形象,又婉转于每一结构环节中,成为伏波潜流般的诗歌内脉。所以谢诗的精髓实在于能密中见疏、奥中见清,从典丽精工中见出幽愤之气、逸荡之势与悠远情韵来。对此,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中的一段评论最为形象:“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词采,求故实,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这是读谢诗的正法眼藏。唯有把握得住谢诗意中之神理,即感情线,方可见其一切形模、比似、词采、故实,无一而非神龙喷吐的缭绕烟云;反之必将为其密丽的外观闪射得目迷心茫。诸如谢诗“不辨首尾”“有句无篇”“有景无人”“玄言尾巴”等等苛评,盖起于此。以上论析,在更具体地探索谢诗源于建安而不同建安的新格局形成过程后,将更为明确。
谢集中山水诗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广泛拟古,达22%强。且尤多效建安体。其《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王粲》序云:“遭乱流寓,自伤情多”,《陈琳》序云:“述丧乱事多”,《应玚》序云:“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平原侯植》序云:“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总序(兼序《魏太子》)云“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等,所论实启《文心雕龙》先声,可见其于建安精神领会之深。尤其论曹植一条,可视作谢客遨游以抒幽愤的夫子自道。不过,由于两晋诗风熏染,谢客拟汉魏诸作体格一般较建安诸子更增华彩,稍多刻炼。由此而观谢客与山水有关诸诗,就可见其演进之迹。大体分四期。
永嘉之贬前为萌生时期(永初三年,422前):此期虽无典型的山水诗,然于宴游、赠别(与行旅相关)诗中已可初见写景才能及寓孤愤于景象的特点。《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即此期的代表作:
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鸣葭戾朱宫,兰卮献时哲。饯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归客遂海隅,脱冠谢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阕。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
此诗谢瞻有同题作。瞻诗起写节序时景,继写祖饯,末写别孔相惜之意。工稳丰茸,却平弱无深意,是典型的晋人饯送诗。当时被推为首唱,然而后人均以为远逊谢客。

灵运诗前半脉络大体同瞻。至“弭棹”二句写行人于斜光余乐中走向舣舟处,惜别之意弥满,本可作结;但“河流”二句又另起波澜,悬拟孔令去舟水程与己送人后陆归景象。“有急澜”“无缓辙”,感情激荡之际,又以“岂伊”反问,折入“宿心”有愧古人,托出未能如孔令归隐以遂素志之旨。原来当时刘裕篡晋之意已显,谢客家世受晋恩,更素亲裕之政敌刘毅;对未来的大变故,他不能不忧心忡忡,遂将应酬之作变为微显不平的抒怀之诗。明此,方可见起处语已为下文伏线:秋日凄凄,百卉病黄,寒潭清冽,皎洁可鉴,正暗寓时势动摇,去者孤洁;而旅雁违霜之暗射去祸,其意也在不言之中,这就是势——意中之神理。可见谢客早期诗已于晋人风华中寓卓然拔萃的建安风力。而永嘉之贬后终于发展成了自己的体格。
永嘉之贬(422秋—423秋),可视为谢客山水诗的形成期。此期山水诗已由行旅诗中脱胎而出。其景物描写一变晋人之丽而欠融,也不尽同建安之浑而欠秀;而善以缜密的观察,刻炼的笔墨,描画出多层次的、秀句卓特却一体融和的景物,在密丽中见出幽峭之致。同时典实运用也更纯熟灵活,多用《庄》《骚》《易》语而能融洽于景物。不过,这一时期谢客的山水诗,即使是游览之作,写景成分同抒情成分在比例上也不占优势,因此章法较单纯,带有明显的从行旅性咏怀诗中蜕出的痕迹。如《过始宁墅》诗中“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一联传诵为秀句,其实佳处更在于它在篇中的地位与意蕴。诗分三层,前八句反复剀陈二纪仕途有违初志,末四句则写告别乡亲,期以三载归隐之想,中间一层则为景语。诗人帆沧海,过旧山,感叹万千,又山行溪涉,历经叠山环涯,重重掩抑,步步盘曲。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忽然清景顿开:洁白的云絮,抱护着向壁空立的幽峭山岩;而山下清波涟漪,翠筱飘拂,照镜自媚。这景象正隐隐遥接前段抒情“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之意,遂在明丽清净中透出一种孤傲不群的气韵来,反映出诗人面对代表勋业彪炳与归隐明智两重意义的先祖故宅时,那复杂的心态,故自然转入下文归隐之想,且暗用《左传》“枌槚”(棺木之材)典以表现出内在的孤愤。全诗幽愤之思鼓荡而下,复潜注于精美的景物描写中,再由景中浮现出来,形成显——隐——显的感情线曲折。全篇结构虽大体承建安以来行旅诗的线索,但景语增加、形象趋实,表明谢客在结构技巧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因而景物实而不滞,起到了渟蕴感情的作用。谢客诗与建安诗任气使才特点的联系,及行旅诗向山水诗过渡之迹于此明显可见。
永嘉之贬后谢客绝大部分诗作均取这种显——隐——显的深化感情的形式,诸名篇中如《登池上楼》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过白岸亭》之“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游赤石进帆海》之“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登江中孤屿》之“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等,均当合全篇通看,方可悟其佳处非特为句秀而已。《过始宁墅》与《登池上楼》结构笔法大体相同,一为行旅,一为游览,正可见山水诗之从行旅到游览转化的轨迹。谢客山水诗至此可说确然成立。
永嘉时期尤可注意的是《晚出西射堂》《游南亭》两诗,其造型与结构方式已初逗后一期特征,试举后者为例: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久痗昏垫苦,旅馆眺郊歧。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药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起笔先写春晚雨后清景,复以“久痗”“旅馆”二句逆笔补出观景前谪宦羁旅又逢久雨阴霾,如同陷溺般的昏沉心境。起处清景是偶一临眺所见,但逆笔写来便觉不群。诗人为清景引动而漫步“郊歧”,自然折入第二层景:泽畔,雨前方生方长的兰草已繁茂向老;而当时一望绿叶的池荷,也已朵蕾初绽。这在他人或许是赏心悦目的美景,但在谢客却足以牵动幽愤的潜意识,于是由“物移”而触发“人老”之叹,而本望借自然灏气澡雪精神的郊游,也转而为后半万事皆虚,归隐旧山的浩叹。在这里情景的关系已变为景——情——景——情,二隐二显(有时为二显二隐)的结构。因此过接的技巧也相应复杂。起处“时竟”(春竟),中腰“朱明移”(夏来),结末“秋水”,诗脉依时令为序展开;而“久痗”“戚戚”二联,一逆,一顺作顿束收放,使思绪曲屈变化,将二景二情打成一片。更巧妙的是“泽兰”以下四句均化用楚辞《招魂》《大招》语,遂于层层写景中隐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之意,遥逗篇末“乘秋水”之想,由《骚》入《庄》,既以屈子之放自比,又以玄道解脱为依皈,情思复杂,正可见儒理性抒情向玄理性抒情转化之迹。恐难任“尾巴”之讥,否则建安诗之儒理结尾岂非亦成“儒言尾巴”?
《游南亭》的写景笔法也更精致,起四句各五字,前二句各含两个层次: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字凝句炼,构成复杂而富于动态美的大背景。三、四句“含余清”“隐半规”分接一、二“夕澄霁”“日西驰”,又拈入“密林”“远峰”二物,组成新的层次;近处是密林清霭,远处是青山半日,与大背景共成三个层次而一体融和的景物群。再缀以一个“含”字,一个“隐”字,遂在季节交替、晴雨变化、昼夜叠代的动景中酝酿出清澄恬美的远韵来,也隐现诗人由“昏垫”中苏生的复杂心态。如对比陶潜《杂诗十二首》其二起处“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之简素宽远,可悟谢诗由刻炼返之自然之特征。这种高超的造型技巧及融贯多重层次景物、情景交叠、屈曲以达意的格局,不仅在前代绝无仅有,即在谢客永嘉诗中也不多见,然而这正是极可注意的雏形。
始隐始宁(景平元年423秋)至再隐始宁(元嘉五年428—七年430)约八年左右,是谢客山水诗高度发展时期。特点是:游览诗中多层次的景物群与情景隐显交替的多重结构,由前一期之偶见,发展为主要模式,形成典型的以游程为明线而奇景叠出,以感情变化为伏线而屈曲潜注的格局。同时其行旅诗也反过来受游览诗影响,终于也完全具备了山水诗的品格。此期,诗中景象更形繁密,意脉也更深隐,与建安诗之发越疏朗,神虽通而貌迥异,最能体现谢诗的个性。这当然要求有更精巧的构思。其诸多佳作,诚如王世贞所评“天质奇丽,运思精凿”
 ,典型地体现了六朝自然美观念,但也时或用之过当,而有滞累之病。
,典型地体现了六朝自然美观念,但也时或用之过当,而有滞累之病。
情景交替的格局,至此期出现了三重以上的交替,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田南树园激流植楥》《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诸作均是。后者取法曹植《赠白马王彪》,但一变子建之摅写骨肉相残,宗臣去国之思,景物仅为情志烘托的单纯格局;而并写远游佳兴与离别悲恨外贬牢愁。因此结构上以游兴和离愁并起双收,中间则用侧注、收放等技巧使每一景物都成为两种情思转换的环节,在深曲中见出慷慨之情,最见开合擒纵之功。这一点,充分显示了谢客诗法建安而变之的特性。
此期由情景交替又发展出新的以描画和叙述交替的体式。篇中不用情语,只以叙述性的记游将几个含蕴不同的景物群连缀成整体。叙述既是游程的环节,又是心情转化的过渡,只是这感情已完全隐注于景物的更叠之下,至篇末才发扬出来。如《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起笔“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先刻画了晨初幽微中渐显明丽的景物,萌动游兴,接着以叙述法先写越岭,再写缘溪,排比而下。峰回溪转后,忽见“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别一番清秀开朗景象。于是佳兴飞动,遐想驰骋,“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但传说中的山鬼——现实中的知音终不可见,于是深感唯自然美景为我真赏,世事万物均为外累,终于超升到庄生所云同物我、遣是非的境界。诗至结尾方可悟出起笔那幽微中渐见明丽的佳景,其实隐蕴着出游前迷惘而渴欲冲破迷惘的心境,这种心境几经高扬后终于归为篇末玄气氤氲中的灵明一点,真所谓“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
最能见出谢客此期布局结构技巧进境的是《登石门最高顶》:
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长林罗户穴,积石拥阶基。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驶,噭噭夜猿啼。沉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荑。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
此诗不是顺登山顺序节节铺写,而是到山顶后,以绝顶高馆为中心一一回溯来路景物,起笔先得峻拔之势,中间以“来人”“去子”应接,篇末则以“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照应。遂使茫惘夜景,朦胧山色中浮现出一种狷介傲兀之气。是谢客以结构之险驱遣多种景物以见逸荡之势、拗峭之致的范例。
临川之贬后(元嘉八年431—元嘉九年432),可视为谢客山水诗的第四阶段。这一时期留存作品不多,但可以看出一种由整密向疏荡回归的趋势,更多地预示了后来杜甫、韩愈诗的特征,是谢诗的胜境。如《入彭蠡湖口》: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诗以“倦”“难”二字双起立一篇纲目。“洲岛”两句从“难具论”生发,总写洞庭水势之凶险浩荡,隐隐见出诗人烦扰心潮。然第五句起笔势陡转,二句一组勾出一夜一朝两幅恬美的静景。但静景其实不静,“千念”二句打转,方知于寥夜清晨的秀静中,诗人仍在苦苦参悟那“难具论”的冥冥之理。但月夜朝昏,百思千虑,似乎仍只是个“难具论”,于是诗人再不耐静思默想。他攀登悬崖登上庐山之东的石镜山;更牵枝扳藤穿过四十里夹路青松,进入湖中三百里的松门山顶,登高远望,企望灵迹仙踪能照彻心中的疑难。但往事已矣,其理难究,“天地闭,贤人隐”,对于这莫可理究的一切,诗人再也“倦”于理会,于是江天之中他奏起了《千里别鹤》的古琴曲。然而断弦一声,万籁俱寂,唯有那无尽的愁思在江天回荡……
本诗较前此诸作第一个明显进展是边幅趋于广远,它打破了游程的格局,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洞庭后三百里内景物,以少总多,气势磅礴。且词气飞动,格局也较前疏越。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虽仍保持着谢诗密致的思理,但开合甚大,转换间泯去了针痕线踪。前析朝夜静景,全由空间运神,更深得张弛、浓淡相间之理。
其三是情景理的进一步融洽,全诗所要表现的是由难究的自然之理而生的对人生的厌倦与愤懑。却以“三江”“九派”一联作中峰回互,将旅途实见与往古传闻,组成叠出层现的景象,情思如伏洄潜注,百折千转;最后以铮然断弦结束全篇,有无穷的象外之意,弦外之音。
表现出这些倾向的尚有《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诗。可惜一年多后,谢客就因故被诛,新进境刚开始也就结束了。尽管如此也足令后人觅迹寻踪,总结出谢、鲍、杜(甫)、韩(愈)、黄(庭坚)这一诗史上以奇险深曲之体抒奇崛不平之思的重要诗歌流派来。

至此,山水诗起源于建安以来以行旅为主的传统诗体可以无疑;并可对谢诗历史地位及陶谢高下说作新的评价了。
陶谢同时,因环境、性情相异,分别开创了田园诗与山水诗;后者主要从宴游、行旅诗而来,前者主要从杂诗蜕变。
陶谢都受玄风影响,但其诗既植根生活而以咏怀为内核;所以也都继承了建安诗重意气与个性的特点。由任气到重兴,化玄风为理趣,虽体貌迥异而神理与共。他们继建安以来情对事超越的丕变,从不同角度完成了诗史上又一次创新。
“自然”是陶谢的共同目标。但渊明多承先秦道家,故复古通变,以古淡淳清矫时世采丽之弊;谢客得力新兴玄学,故激浊扬清,以精研探微疗当时肤廓之疾。
陶之归隐是彻悟,加以田园之景多素淡,故宜于静观默照;谢之退居是牢愁,加以山水之景多宏阔,故宜于探胜放浪。陶诗之景多片断,体气静穆宜短制;谢诗之景多游程,体气磅礴宜大篇;陶诗单纯,一气舒展,如风行水上;谢诗深复,夭矫连蜷,似神龙驱云。陶诗是深入浅出,疏中有密;谢诗是深入深出,密中见疏。陶诗之味如清茶,淡而后醇;谢诗之味似陈曲,辛而后甘。
陶谢又分启后世不同的创作倾向,学者各以性之所近而得绍箕裘。迹近山野者,如王绩、孟浩然、李白、储光羲多承陶;心仪世系者,如杜甫、韩愈、柳宗元、黄庭坚多法谢。又有出此入彼、折衷以自成一体者,前有谢朓,后有王维。其间世变文移,风气迭代,而倚轻倚重,参互交取则为三派兴衰之又一参数。加上前此之汉魏风骨,后此之梁陈宫体,凡五种体格,为唐以后诗人主要取法对象。虽然文苑波诡,各逞其能;但细心探究,实万变不离其宗。
陶诗之佳,多赖天才;谢诗之美,更倚人力。故陶之空灵之境,谢不能到。然而天才难踪,后世学陶成风,却难得其三、五;人工有迹,故谢客开山,反启后人无数法门。试以柳宗元《南涧中题》并谢客《游南亭》对读,杜甫《咏怀五百字》与灵运《过始宁墅》对看,前者虽变化有加,篇制更巨,然青蓝之承,历历可循。故若以对后世诗体变迁及技巧发展之影响而论,谢诗其实更甚于陶。如果说陶谢有所高下,亦仅于此二节各执一左券而已。陶谢在晋宋之交,正如李杜在盛中唐之际,均未可以高下论之,这也许正是诗史演进中又一个有趣的循环。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