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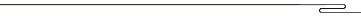
谈到建安诗歌的传承,各种文学史著作都只谈汉乐府的影响。一九五六年,马茂元先生在其《古诗十九首探索》序言中提出:《古诗十九首》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诗风的前奏。然而这一富于启发性的观点,却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其实这并非是“标新立异”的见解,而是总结了历代诗论家上百次指出过的一个文学史现象。兹略举数例以证之:
(古诗)《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又论刘桢云: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梁钟嵘《诗品》)
《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中略)邺中七子……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唐皎然《诗式》)
读《古诗十九首》及曹子建“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类,皆思深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宋吕本中《童蒙诗训》)
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明胡应麟《诗薮》)
建安、黄初之诗,因于苏、李与《十九首》者也。(清叶燮《原诗》)
(《十九首》)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所以风格和建安体格相近。(近代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以上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诗评家都指出《十九首》与建安诗一脉相承之联系。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十九首》与建安诗的联系除大家注意到的五言诗形式外,可以皎然所论:《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邺中七子“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二语来概括。此评道出了两点联系:(一)主情任气,尤重感兴:二者都继承了国风至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二)始见作用之功,婉丽而不失自然之致:二者在古典诗歌表现手法方面构成一个有特殊地位的阶段。这二点也就是本文论述的主旨。
无视《十九首》与建安诗的联系,其理论根源首先是囿于这样一个公式:先对现实主义作极片面的理解,然后以此为界把文学史分成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个阵营,两军对垒,一线单传,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了。某些同志一方面贬低《十九首》,甚至加以唯美主义的帽子,将它向右推;一方面则对建安风骨作片面的理解,抬到不适当的高度,将它向左拉:于是血肉相联的二者被生拉硬扯地割裂开来了。
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可见离开了“历史”,离开对史实的全面占有分析;离开了辩证法,离开一切存在均处于流动变化中的观点,那么“唯物主义”就不是“彻底的”。要弄清《十九首》与建安诗的联系,首先要破除对那种似是而非的“唯物主义”的敬畏,切实把握建安诗的特质。
答案可说是现成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是每一部文学史著作都引用的;答案又是远未解决的,因为文学史在引述刘勰的论断时又都掐头去尾曲解了本意。对于这种做法,王运熙先生曾提出过批评
 ,这里从另一角度作申论,以与王先生所论互参。刘勰曾云:
,这里从另一角度作申论,以与王先生所论互参。刘勰曾云:
古诗佳丽(中略),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中略)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中略)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心雕龙·明诗》)
(三曹七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同上《时序》)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同上《乐府》)
细按彦和所论,建安诗的特质实包含以下几点:
首先是成因:汉末“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是建安诗歌高潮形成的社会原因;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发展的历史经验则是其内部原因。缺少任何一方面,这一高潮都不可能出现,故彦和论建安五言诗首先就上溯到古诗。
其次,在上述背景下,建安诗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气与才,是建安诗之所以可贵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
所谓“慷慨以任气”,主要是指建安诗人表现于诗中的气质——宽广的胸襟与昂扬的气魄。这种气质,“或述酣宴,或伤羁戍”,甚至“怜风月,狎池苑”,“洒笔”“和墨”间,都可以得到表现。显然这是传统的“充实论”“文气论”的发展;而非如今人常理解的只指反映社会动乱,歌唱雄心壮志。这些并非刘勰一家之论,而反映了我国抒情诗的传统。试看几位以风骨见称的唐代诗人的见解。高适《答侯少府诗》云:“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在他看来诗具真性情就可风骨超伦。皮日休在《郢州孟亭记》中将孟浩然与李杜并称为“大得建安体”,而其理由是孟诗“涵涵然有平大之风”。元结云:“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今夕岂不能道达情性,成一时之美乎!”这段话一直被视作“现实主义”诗论,然而它却偏偏出于一首宴筵诗——《刘侍御月夜宴会诗》的小序中。可见,谈建安风骨,只局限于《苦寒》《蒿里》等二三十章,而置数百首其他内容的诗作于不顾,实乃“题材决定论”在古典诗歌研究中的反映。
刘勰所谓“磊落以使才”,又指出了建安诗另一特质:它已不尽同于先此诗作之“天予真性,发言自高”,而已开始注意“才”了。不过它又没有晋宋后诗人任才而伤气的通病,而是“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二者结合,表现于风格上,就是刘勰所说的“气爽才丽”(《乐府》),“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明诗》);就是钟嵘所称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曹植》)。总之,气才并重,以气驭才,以才达气,气爽才丽,是建安诗歌的总体特点。下面举曹植一首“怜风月”“叙酣宴”的诗歌来略作分析。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摇放志意,千秋长若斯。(《公宴》)
诗称曹丕为公子,则武帝尚在。时曹氏之文治武功蒸蒸日上,内部矛盾尚未激化,故虽写宴筵而绝无以后齐梁同类诗作之淫靡情调。全诗以“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起,以“飘摇放志意,千秋长若斯”结,中以高华的笔触描绘了初秋清夜万物竞腾的景象,从而情景交融地表现了曹氏集团当时广阔的胸襟与奋亢的进取精神。首尾四句实乃曹操慷慨任气的豪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的另一种方式的表达。此诗艺术表现上丽而不弱,宋范晞文评云“皆直写其事,今人虽毕力竭思不能到也”
 。正指出其具有“磊落以使才”的建安诗的一般特点。我们不妨从发展无产阶级新文艺的角度给曹操《苦寒》《蒿里》更高的评价;却不能因题材不那么重大,而斥《公宴》类作品为糟粕,因为它们实乃同一精神在不同题材、不同场合的反映。弄清了建安诗“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确切内含,它对《十九首》的继承关系就清楚了。
。正指出其具有“磊落以使才”的建安诗的一般特点。我们不妨从发展无产阶级新文艺的角度给曹操《苦寒》《蒿里》更高的评价;却不能因题材不那么重大,而斥《公宴》类作品为糟粕,因为它们实乃同一精神在不同题材、不同场合的反映。弄清了建安诗“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确切内含,它对《十九首》的继承关系就清楚了。
《十九首》首先在“慷慨以任气”方面为建安诗人前奏。这是汉末一组富于现实意义的怨歌。刘勰评曹氏父子“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移以评《十九首》亦很洽切。从《十九首》的怨歌到建安诗人之高歌,是当时寒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从痛苦中挣扎、奋斗而终于崛起的历史过程在文学上的曲折反映。而其消极面也同时“遗传”给了建安诗人。
否认《十九首》与建安诗的思想联系的主要依据是它受玄学影响,表现出任诞倾向。论者多是以下述三段式进行推理的。
大前提:汉末玄学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思想工具;其任诞倾向正是没落阶级人生观的反映。
小前提:《十九首》正表现了这种思想。
结论:因此它应当否定,至少在这一点上应当否定。为支持这一三段论,人们又往往引用恩格斯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致康·施米特》信中的一段话,“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根据这一论述,又因玄学及其前身道家思想历来被视作没落阶级人生观,于是人们就按前举三段式“顺理成章”地推出了上述结论;而很少去想受玄学影响的《十九首》会与“慷慨以任气”的建安诗有什么思想联系。
然而,恩格斯在这段话后又写道:“(但是)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
 这里,恩格斯指出了一种传统的思想材料,由于经济的支配作用(往往通过政治),其发展方向总是在发生改变的。因此,对于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形态,我们都应当按辩证逻辑的观点,在流动中研究它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手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而不能仅据形式逻辑的三段式作简单推理。对于《十九首》所表现的玄学影响及其颓放倾向,也必须作如是观。
这里,恩格斯指出了一种传统的思想材料,由于经济的支配作用(往往通过政治),其发展方向总是在发生改变的。因此,对于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形态,我们都应当按辩证逻辑的观点,在流动中研究它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手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而不能仅据形式逻辑的三段式作简单推理。对于《十九首》所表现的玄学影响及其颓放倾向,也必须作如是观。
玄学在汉末魏初的兴起具有两重性。它反映了人们对传统儒学伦理准则与思辨方式的怀疑。这种怀疑可以导致醉生梦死的人生观,也可以被用作反对传统思想束缚,批判现存制度的思想武器。我们不妨承认汉魏世族的玄风是没落阶级人生观的反映,然而这只是玄学思想在这一阶层中的反映,是一个分支;而决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凡受玄学影响的各阶层与个人一概指作具有没落阶级的人生观。因为归根到底,经济(往往通过政治)是会改变这一思想的“发展的方式”的。
《十九首》的作者是一群游子,是争取走上政治舞台一展抱负的寒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缩影。汉代外戚、宦官、官僚三大势力在角逐中利用了他们,又抛弃了他们。然而其从政的企望已被唤醒而再也不可能被压制。成千上万的士子拥向州郡京城,可是“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于是转而对现存秩序产生怀疑。他们并非真抛弃了儒家“兼济”与“独善”的传统,而是痛感于儒道之崩坏,故转而吸取玄学解经中解放的一面,以放达排遣块垒。如将《十九首》联系起来考察,可清楚地感到其思想感情有三个特点:颓放中寄寓着对社会的隐忧;感愤中透露着对世态的嘲讽;羁愁中寄托着心田处真诚的情愫。
,于是转而对现存秩序产生怀疑。他们并非真抛弃了儒家“兼济”与“独善”的传统,而是痛感于儒道之崩坏,故转而吸取玄学解经中解放的一面,以放达排遣块垒。如将《十九首》联系起来考察,可清楚地感到其思想感情有三个特点:颓放中寄寓着对社会的隐忧;感愤中透露着对世态的嘲讽;羁愁中寄托着心田处真诚的情愫。
《青青陵上柏》的作者看来是斗酒驽马,游戏宛洛,而清人陈沆则别具只眼地看到他是“以斗酒之足乐,反刺富贵者之无所厌求。故推之冠带,又推之王侯,又推之两宫、双阙”
 。既然整个上层社会直至帝王均安坐火山“极宴娱心意”,我又“戚戚何所迫”呢?诗的结语是沉痛的,故前人评曰:“结语强作旷达,正是戚戚之极者。”
。既然整个上层社会直至帝王均安坐火山“极宴娱心意”,我又“戚戚何所迫”呢?诗的结语是沉痛的,故前人评曰:“结语强作旷达,正是戚戚之极者。”
 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颓放之中又往往深自反省。“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的作者无法排遣愤懑,正企图在声色的追求中聊以自适,这时听到了歌女的一支清曲,深自震动,于是他“驰情整中带,沉吟聊踯躅”。“整中带”的细节与“何为自结束”的颓语相映照,表明作者心中严肃的情感被感召,于是终于产生“愿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的渴望正常生活的遐想(这种企望在《十九首》抒写恋情的篇章中表现尤切)。《十九首》作者的强烈怨愤往往难以压抑,而迸发为渴求进取的呼唤:“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鸿鹄远飞,一举千里”,“慷慨有余哀”的弦歌声终于激发出诗歌高亢的尾音,这是对当路者的抗争,也是对自身颓放思想的自我批判。在这压抑中破空而去的歌声中,已可听到“慷慨以任气”的建安诗的前奏了。因此《十九首》作者的放达任诞思想虽有其消极面,然而与统治者的醉生梦死不能等量齐观。他们的颓放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汉末社会的深刻矛盾:世族统治者与寒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崛起与反崛起、压抑与反压抑的矛盾;汉代思想史中进步因素与其局限性的矛盾;知识分子愤于现实,却脱离人民看不到出路的矛盾。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嵇康阮籍等否定名教,实因名教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在骨子里他们倒是尊重名教的。以嵇阮为代表的正始诗风是建安诗风的直接延续,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十九首》的放达的怨歌是建安诗人慷慨悲歌的先声。
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颓放之中又往往深自反省。“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的作者无法排遣愤懑,正企图在声色的追求中聊以自适,这时听到了歌女的一支清曲,深自震动,于是他“驰情整中带,沉吟聊踯躅”。“整中带”的细节与“何为自结束”的颓语相映照,表明作者心中严肃的情感被感召,于是终于产生“愿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的渴望正常生活的遐想(这种企望在《十九首》抒写恋情的篇章中表现尤切)。《十九首》作者的强烈怨愤往往难以压抑,而迸发为渴求进取的呼唤:“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鸿鹄远飞,一举千里”,“慷慨有余哀”的弦歌声终于激发出诗歌高亢的尾音,这是对当路者的抗争,也是对自身颓放思想的自我批判。在这压抑中破空而去的歌声中,已可听到“慷慨以任气”的建安诗的前奏了。因此《十九首》作者的放达任诞思想虽有其消极面,然而与统治者的醉生梦死不能等量齐观。他们的颓放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汉末社会的深刻矛盾:世族统治者与寒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崛起与反崛起、压抑与反压抑的矛盾;汉代思想史中进步因素与其局限性的矛盾;知识分子愤于现实,却脱离人民看不到出路的矛盾。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嵇康阮籍等否定名教,实因名教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在骨子里他们倒是尊重名教的。以嵇阮为代表的正始诗风是建安诗风的直接延续,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十九首》的放达的怨歌是建安诗人慷慨悲歌的先声。
必须指出,慷慨一词并非一定指豪言壮语。《说文》:“忼(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也。”司马相如《长门赋》:“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武帝陈皇后的宫怨也是一种慷慨。可见慷慨是指一种感于哀乐的或悲或喜的奋亢的精神状态。《十九首》之所以是“慷慨以任气”的,就是因作者从自身的被压抑中,激发出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而形于歌唱,从而继承了《诗经》、汉乐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它们与建安的高歌是汉末“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在不同阶段的反映。随着寒族地主阶层的壮大和胜利,怨歌自然就转化为高歌;而高歌者在地位沉降时也会怨歌哀婉。建安诗人的绝大部分篇章不正与《十九首》表达着同一主题、同一情感吗?因此从发展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史实,而不是对史实任意取舍或停留于现象的机械类比上,就必能看到建安诗与《十九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
《十九首》更在“磊落以使才”方面为建安诗人之先声。皎然《诗式》曾对由汉至晋宋的诗风演变作过如下概括:西汉苏李诗是“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东汉《十九首》是“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魏诗《邺中集》是“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晋宋间谢灵运诗是“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均见《诗式》卷一)。
从这一分析可见,从《十九首》至建安诗歌,正形成诗歌从前古的“天予真性”,“未有作用”,至中古“尚于作用”的过渡阶段。其特点是“始见作用之功”。对于《十九首》与建安诗艺术上的联系,必须从这一高度来考察。
所谓“始见作用之功”,即“磊落以使才”,是说在“天予真性,发言自高”的基础上,已开始注意艺术构思,而表达真挚的情感,始终是这一时期艺术构思的中心。《十九首》首先具备这一特点,与其渊源有关。
按今存汉乐府诗与古诗,篇目与语句大量雷同。乐府中如《白头吟》《怨歌行》之属,体裁与《十九首》无异;今题“古诗”者如《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等,又与乐府民歌同辙。因可见乐府诗与无名氏古诗必为时期相近、性质相通之作品。入乐则称乐府,未入乐或虽入乐却失其调名则为古诗。舍去音乐因素,这批诗作实可分为二类:一类劳动人民所作;一类下层文士所为。二类血脉相通而风格稍异。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分道扬镳;至《昭明文选》取其中抒情性文学性特强之十九首立为一类,题作“古诗”,二者分野始判。
古诗与汉乐府歌辞性质之异同决定了它们风格之异同:(a)感兴:二者均一事一诗,情事交融;而民歌较多铺叙,叙事以见情,古诗则重在抒情,以情融事。(b)结构:二者均结构浑成,无斧凿之迹;而民歌多以事情之自然顺序为线索,古诗则按感情的起伏节奏驱遣裁剪事实。(c)语言:二者均自然天成,富于感染力;而民歌如胡应麟所称“质而不鄙,浅而能深”
 ,古诗则如谢榛所云,是“秀才说家常话”
,古诗则如谢榛所云,是“秀才说家常话”
 ,故又如胡应麟所称“随语成韵,随韵成趣”
,故又如胡应麟所称“随语成韵,随韵成趣”
 。(d)境界:由以上三点决定,二者均风格浑厚,境界深远;而其中民歌“遒深劲绝”
。(d)境界:由以上三点决定,二者均风格浑厚,境界深远;而其中民歌“遒深劲绝”
 ,其境深远,古诗则“怊怅切情”
,其境深远,古诗则“怊怅切情”
 ,其境旷远。
,其境旷远。
这种异同遂形成了马茂元先生曾论述过的一个“分流”与一个“结合”,即东汉末年叙事诗与抒情诗分流的明朗化;东汉末年,分离了三四百年之久的民间文学语言与文人创作语言在《古诗十九首》中的重新结合。于是产生了《十九首》那样“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抒情短诗。它与乐府民歌一起直接成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诗的前奏。下面从抒情诗艺术的几个要素:结构、意象、音节,来就此略作考察。
(1)“势逐情起”——结构。
古典诗论以情意为上,意立得势,形成决定诗体开合的气脉;而气势无形质,又须通过一定的结构来传达。随着抒情诗的发展,结构问题愈益被重视;因抒情诗不像叙事诗那样有情节作结构的主干,它以抒发无定质的感情为主,必须在结构上多费一番“作用”的功夫。前人屡屡指出,建安诗气势充盈,颇得力于布局成功。如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评曹植《杂诗》,“文法高妙,宋以后人不知此矣,此与《十九首》、阮公同其神化”。此评不仅指出曹诗“文法高妙”,亦即结构有匠心而自然浑成,且点明这一特点肇始于《十九首》,而与正始诗共同构成区别于刘宋后作品的诗史中的特定阶段。现特以古诗《明月何皎皎》与曹丕、曹睿各一诗作比较,以明演进之迹。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明月何皎皎》)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曹丕《杂诗一》)
昭昭素明月,辉光烛我床。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微风吹闺闼,罗帷自飘扬。揽衣曳长带,屣履下高堂。东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鸟向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巷。(曹睿《昭昭素明月》)
《明月何皎皎》和《十九首》其他篇章一样,与乐府诗血缘最近,故保存了较多的叙事成分。它们在结构上一般均以一个抒情主旋律为中心,来组织某一生活片断中的若干细节,构成抒情境界。《明月》诗表现的是月夜乡思,粗看仅写了乡思驱遣下的几个下意识的动作;细味则其结构已初见匠心。“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是中心句,它置于“揽衣起徘徊”后,这样“客行”句就承上点明了不寐之因;又因“客行”故生“早旋归”之想,则又自然勾出以下出户彷徨,引领遥望的无端寻觅。这二句抒情的中心句,既是情之所至的自然心声,又是全诗开合的关锁,由此形成诗势的起伏。加上取材上着重于一出一入,起兴处笼罩全篇的皎皎月色,真是“始见作用”。
曹丕《杂诗一》结构如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所指出:“从古诗两《明月》篇来”,“总以多悲思为骨,以思乡为筋”。然而它又突破了连续动作的限制。长夜北风,不眠而起,前四句起法与《明月》诗同辙。接着“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却别开生面。“已久”是说在外时间很长了,而其间诗人干了什么却一字不着,仅以“白露沾裳”点出其愁思似梦之情态,既逼真,更避免了与下文的重复。露沾衣裳而由“梦”中惊醒,又插入清秋寒夜,星月参横,虫鸣鸿飞的大段景物描写,以增强抒情气氛。复以“郁郁多愁思”一句由景入情,收束上文,引出欲归无途的呼号。末以向风长叹与首句长夜北风呼应作结。全诗结构比起《明月》诗来同样浑成而更见“作用”之功。
曹睿《昭昭素明月》的结构,更结合了上二诗的特点。它将主人公的动作与景物穿插交织,渐次将感情推向高峰。吴淇评云:“此首从《明月何皎皎》翻出,古诗俱是寐而复起,俱以‘明月’作引,俱有‘徘徊’‘彷徨’字。但彼于户内写‘徘徊’,户外写‘彷徨’,态在出户入房上;此首‘徘徊’‘彷徨’俱在户外,中却于离床以后,下阶以前,先写出一段态来:各极其妙。‘东西安所之’,莫我知也夫;‘舒愤诉穹苍’,知我其天乎!”此评正道出了魏明帝此诗结构上对《明月》诗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以上三诗结构都如皎然所论有势逐情起,即诗势随感情节奏开合之特点,又都见出一定的剪裁组织功夫;而后一首学习前一首,一首精细于一首,可见在结构上“磊落以使才”,《十九首》已肇其始,而建安诗人又有了发展。
(2)“语与兴驱”——意象。
《十九首》善于通过自然而明丽,凝炼而富于暗示,工整而善于变化的语言指事写怀,构成富于意蕴的诗歌意象,显示出熔民歌与文人语言精华于一炉的高度成就
 ,这一点亦为建安诗人所继承发展。
,这一点亦为建安诗人所继承发展。
建安诗人在意象构成上借用或化用《十九首》句意者颇多。上举《明月何皎皎》等三诗可见一斑,兹更举二例:曹丕《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云:
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身体忽迁移。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
此诗开头“与君”二句化用古诗《冉冉孤生竹》中“与君为新婚”与《行行重行行》中“与君生别离”二句。“凉风”二句又取古诗“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的故辙。“寒蝉”二句更从古诗《明月皎夜光》“秋蝉鸣树间”蜕出。“枯枝时飞扬”至“会合安可知”六句,与《冉冉孤生竹》中“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意同,实即皎然所说“偷意”诗例。结末二句则是古诗《西北有高楼》末“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改造。此诗实可谓借化《十九首》之集大成者。
又如古诗《西北有高楼》发端“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二句,以萧瑟的西北方的齐云高楼起兴,造成笼罩全诗的抒情气氛;而建安诗人借化这一意象的不下十例。如:
西山亦何高,高高殊无极。(曹丕《折杨柳行》)
遥遥山上亭,皎皎云间星。(曹丕《于明津作》)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曹植《七哀》)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曹植《杂诗六首》之一)
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曹植《杂诗六首》之三)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曹植《杂诗六首》之六)
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曹植《赠徐幹》)
高殿郁崇崇,广厦凄泠泠。(徐幹《情诗》)
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阮瑀《杂诗二首》之一)
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应瑒《建章台诗》)
从这一组例子不仅可见建安诗人在诗歌意象上多借化《十九首》,更说明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在抒情诗意境构成中极重要的发端问题上,《十九首》的历史地位。《诗经》中的起兴,除个别篇章(如《蒹葭》)外,尚处于“先言他物,引起所咏之物”的较原始的阶段。通过发端,造成笼罩全诗的抒情气氛,产生贯注全体的诗歌气脉,这种手法至《十九首》才作为群体而成熟。这是抒情诗发展到成熟期的必然现象。《十九首》中他如《青青河畔草》《明月皎夜光》《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凛凛岁云暮》《行行重行行》《孟冬寒气至》等,发端均称警绝。评家每称建安诗人工于发端,其实正是对《十九首》的发展。二是建安诗人学习《十九首》又非刻板模仿,而总是根据诗意加以变化。或取其意,或熔其辞;或旖旎,或劲遒,其语言又均比《十九首》更多文人意味。许学夷《诗源辨体》说:魏诗较汉诗同者三,异者七。同者皆“情兴所至,以不意得之”,“委婉”而有“天成之妙”;异者则更见“作用之迹”,“此汉人潜流而为建安,乃五言之初变也”。这正是对在意象上,由《十九首》至建安诗人,“作用”之迹渐显的科学总结。
(3)“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诗品》语)——音节。
建安诗中已有不少句子暗合后世律调,《四溟诗话》曾裒录多则,评曰“以上虽为律句,而全篇高古,及灵运古律相半,至谢朓全为律矣”。我们并不认为建安诗人已有声律说的概念,然而他们在实践中如刘勰所称“宰割辞调”,令其和谐动听,却也是无法否认之事实。而这也正由《十九首》启其渐。
费滋衡《汉诗总说》称“古诗唯《十九首》音调最圆”。梁启超甚至说:“《十九首》虽不讲究声病,然而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为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其用字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试拿来和当时的歌谣乐府比较,虽名之为汉代的律诗亦无不可。此种诗格,盖自西汉末五言萌芽之后,经历多少年,才到这纯熟谐美的境界。后此五言诗虽内容实质屡变,而格调形式总不能出其范围。”
 按梁氏所论古诗平仄虽不无夸大,然论点却极可注意。他指出了《十九首》虽不讲声病而较之当时民歌,和谐纯熟,可称为“汉代的律诗”,且为后世五古所沿袭。这就点明了建安乃至嗣后诗人对《十九首》在音节上“始见作用”的继承发展。
按梁氏所论古诗平仄虽不无夸大,然论点却极可注意。他指出了《十九首》虽不讲声病而较之当时民歌,和谐纯熟,可称为“汉代的律诗”,且为后世五古所沿袭。这就点明了建安乃至嗣后诗人对《十九首》在音节上“始见作用”的继承发展。
梁氏所论《十九首》音调有二端:从全篇观,大率四句一解,一解转一意。今按:这也是建安五古的特征,它本于汉乐府相和歌,也成为后世五古最通常的组织形式。
梁氏又指出《十九首》多平仄相间,亦为事实。后世五律音节规律首要即在二四字的平仄相反上,清人声调谱论五古亦以此为重要特点。今按《十九首》共有句236,其中二四字平仄相反者约140例,达百分之六十;加上暗合后世拗救句法者,达百分之七十以上,真所谓是“蜂腰鹤膝,闾里已具”(钟嵘《诗品序》)。
《十九首》这种合于后世声调说的现象,并非有绳墨规定,而是在实践中自发调节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叠字的连用。连用叠字,是民歌常用手法,《十九首》多借用而常平仄互间。《青青陵上柏》首二句“青青”“磊磊”一平一仄。《迢迢牵牛星》凡十句,六句用叠,均二二平仄相对(迢迢对皎皎,纤纤对札札,盈盈对脉脉)。《青青河畔草》首六句用叠字,前四句“青青”对“郁郁”,“盈盈”对“皎皎”均一平一仄;五六句“娥娥”对“纤纤”,虽为同平,却一清一浊。此诗共十句,又有八句,每句二四字平仄相间。这样在民歌化的句法中,参以平仄清浊的自发调配,读来真是珠润玉圆,一片宫商。《十九首》在音节上“始见作用”却又口吻调利、清浊通流;执建安诗多合律调之先鞭,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上面就结构、意象、音节——诗歌艺术三个要素方面探讨了建安诗人对《古诗十九首》的继承与发展。可见在“慷慨以任气”的基础上,从《十九首》到建安诗人都已“始见作用之功”,越益重视诗歌的才情。以气运才,以才达气,“磊落以使才”与“慷慨以任气”,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建安时期诗歌创作的高潮,是诗人们对汉代后期血缘相亲的两类作品——汉乐府民歌和以《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创作精神与艺术成就的发扬光大,它们共同构成了“汉魏风骨”这一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而《十九首》在这一历程中还占有某种特殊地位:即从《十九首》到建安诗,完成了诗史上从抒情言志的不自觉的文学作品到自觉的抒情言志的文学作品的过渡。诗史上“重文”的时代,由此渐渐揭开了序幕。
(本文原载于《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