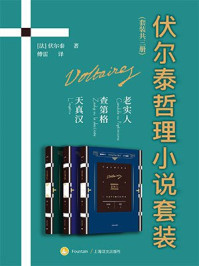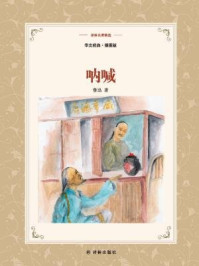我们一同走在街上。虽已出了大主教们的住宅区,眼前还是有许多大房子。其中一幢前面,卫士正在修整草坪。这些草坪干净整洁,房子外观气派典雅,整修一新;看起来就像以往印在杂志上有关家居装修的精美插图。这里同样人迹罕见,同样是一片沉睡不醒的景象。整条街活像个博物馆,又好比建来向人们展示昔日生活方式的城市模型中的一条街道。这里和那些插图、博物馆或城市模型一样,也不见孩子的踪影。
这里是基列共和国的心脏,是除了在电视中,战争无法侵入的地方。它的边界延伸至哪里,我们无法确定,因为它随着进攻和反击的情况而不断变化。但它是国家中心,这里的一切都不可动摇。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基列共和国无边无际,基列就在你心中。
过去这里曾有过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但现在再也见不到律师,大学也关闭了。
从前,我有时会和卢克一道沿着这些街道散步。我们常常谈起要买一幢这样的房子,古老的大房子,把它好好整修翻新一下。我们要有个花园,花园里有供孩子们玩耍的秋千。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虽然我们明白很可能压根儿就养不起孩子,但它却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星期日必不可少的保留游戏。这种自由如今似乎已无足轻重。
拐了个弯,我们来到一条大街,这里车辆行人多了些。汽车疾驰而过,大多数是黑色的,也有一些是灰褐色的。提着篮子的女人中,有的身着红色,有的身穿单调乏味的绿色马大
 装,还有的穿着条纹长裙,红、绿、蓝三色相间,一副粗俗寒酸的模样。那是穷人家太太的装束。经济太太,人们这么称呼她们。这些女人干什么没有具体分工,只要力所能及,什么都得干。偶尔也能看到一身黑衣的寡妇,过去很多,现在似乎渐渐少了。
装,还有的穿着条纹长裙,红、绿、蓝三色相间,一副粗俗寒酸的模样。那是穷人家太太的装束。经济太太,人们这么称呼她们。这些女人干什么没有具体分工,只要力所能及,什么都得干。偶尔也能看到一身黑衣的寡妇,过去很多,现在似乎渐渐少了。
在人行道上是见不到大主教夫人们的,只能在车里见到。
这里的人行道是水泥的,我像孩子一样小心避开裂缝处。我想起过去在这条人行道上行走的双脚,以及脚上穿的鞋子。有时是跑鞋,鞋跟富有弹性,鞋面有透气孔,还有星星形状的荧光纤维点缀,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虽然那时我晚上从不跑步,白天也只在行人较多的路上跑。
那时女人不受保护。
我还记得那些从不用讲,但每个女人都心知肚明的规矩: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哪怕他自称是警察。让他把身份证从门缝下塞进来。不要在路当中停车帮助佯装遇上了麻烦的开车人。别把上锁的车门打开,只管朝前开。要是听到有人朝你吹口哨,随他去,不要理他。夜里不要独自一人上自助洗衣房。
我想着自助洗衣房。想着我走去时穿过的衣服:短裤,牛仔裤,运动裤。想着我放进去的东西: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肥皂,自己的钱,我自己赚来的钱。想着自己曾经是驾驭这些东西的主人。
如今我们走在同样的大街上,红色的一对,再没有男人对我们口出秽言,再没有男人上来搭讪,再没有男人对我们动手动脚,再没有人朝我们吹口哨。
自由有两种,丽迪亚嬷嬷说。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
在我们的右前方是定做裙子的地方。有人把我们的裙子称为habits(修女服),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名字,因为该词又指“习惯”,而习惯是牢不可破的。店门口有个巨大的木招牌,形状像朵金黄色的百合花,店名就叫“田野中的百合”。这个店名原来写在百合的下面,后来被油漆盖掉了,因为他们觉得即便是店名,对我们也有太大的诱惑。如今许多地方只有招牌,而无名称。
“百合”过去是家电影院,是学生们常去的地方。每年春天那里都要举行汉弗莱·鲍加
 节,前来参加的嘉宾有他的遗孀、著名演员劳伦·巴考尔
节,前来参加的嘉宾有他的遗孀、著名演员劳伦·巴考尔
 或是凯瑟琳·赫本,她们都是自食其力、自主自强的女人。她们身穿前面有一排纽扣的衬衫,暗示着解开这个字眼随时可能发生。她们可以解开,也可以不解开。她们看起来有能力自行选择。当时我们似乎也能选择。丽迪亚嬷嬷说,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
或是凯瑟琳·赫本,她们都是自食其力、自主自强的女人。她们身穿前面有一排纽扣的衬衫,暗示着解开这个字眼随时可能发生。她们可以解开,也可以不解开。她们看起来有能力自行选择。当时我们似乎也能选择。丽迪亚嬷嬷说,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
我不知道从何时起不再举行这种节日了。我准是长大了。所以不在意了。
我们没有进“百合”,而是过了马路来到一条小街上。我们先在一家挂着另一块木招牌的店铺前停了下来。木招牌上画着三个鸡蛋,一只蜜蜂,一头奶牛。这是“奶与蜜”
 食品店。店里排着队,大家两个两个地等候着。我看到今天有橘子卖。自从宗教信仰自由主义战士占领中美地区以来,橘子就很难买到:有时有,有时没有。战争切断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橘子运输。遇到置放路障或铁轨被炸事故,就连佛罗里达的橘子也难保证能运进来。看着这些橘子,我真想买一个,但我没带买橘子的代价券。回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丽塔,她听了准高兴。能见到橘子确实不同寻常,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成就了。
食品店。店里排着队,大家两个两个地等候着。我看到今天有橘子卖。自从宗教信仰自由主义战士占领中美地区以来,橘子就很难买到:有时有,有时没有。战争切断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橘子运输。遇到置放路障或铁轨被炸事故,就连佛罗里达的橘子也难保证能运进来。看着这些橘子,我真想买一个,但我没带买橘子的代价券。回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丽塔,她听了准高兴。能见到橘子确实不同寻常,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成就了。
那些挨到柜台前的人把代价券交给站在柜台里面身穿卫士军服的两个男人。谁也没有多说话,只有衣服摩擦发出的窸窣声,另外还可见到女人们悄悄转动脑袋,左顾右盼的诡秘模样。在这儿买东西可能会碰上熟人,有的是从前就认识的,也有的是在“红色感化中心”认识的。只要能见到熟人的面孔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要是我能见到莫伊拉,只要知道她还活着,便已足矣。在现在这种时候,能拥有一个朋友,真是让人想都不敢想。
可是,奥芙格伦站在我旁边,却不见她东张西望。或许她现在不再认识什么人,或许她们全都消失了,那些她认识的女人。或许也可能她不希望让人看见。她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站立着。
就在我们两个两个排队等候的时候,门开了,又进来两个女人。两人都是使女打扮,都穿着红裙,戴着白色双翼头巾。其中一个挺着大肚子;虽然衣裙很宽,肚子仍趾高气扬地高高挺着。店里寂静的气氛顿时被打破,四周响起一片低语声。大家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我们俩也不管不顾地大胆转过头去看她;手痒痒的,真想摸她一下。对我们而言,她浑身好像有一股魔力,既让人嫉妒,又让人渴望。她宛若山顶上的一面旗帜,向我们表明只要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我们同样能够拯救自己。
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耳语声由低到高,显然个个都激动不已。
“这是谁啊?”我身后有人问道。
“奥芙维纳。不对,是奥芙沃伦。”
“啧,显摆来了。”有人低声嘘道,此话不假。因为孕妇大可不必出门,不必上街采购。每日散步,让腹部肌肉处于运动状态不再是医嘱的内容。她需要的只是做做自由体操或是一些呼吸运动。挺着大肚子出门不安全,她可以待在家里。店门口肯定有一个卫士守着等她出来。如今她身上孕育着生命,因此也就更接近死亡,需要特别的保安措施。别人的嫉妒心就可能要了她的命,这种事曾经发生过。如今孩子个个都是宝贝,但并非人人视其为宝贝。
不过,出来走走也许只是她一时兴起,既然肚里的孩子已快足月,至今也从未发生过意外,此类的心血来潮他们也就放任迁就了。或者也许她是那种人吧,那种“放马过来,我还可以”的烈女。这时,恰好她抬起头来四处张望,我瞥见了她的脸。身后那人说得没错。她是来这儿炫耀自己的。因为她红扑扑的脸上神采飞扬,显然这里的每一刻都让她陶醉不已。
“安静。”柜台里的一个卫士喝道。顿时,我们像一群小女生一样安静下来。
轮到奥芙格伦和我了。一个卫士接过我们给他的代价券,把上面的号码输入专用电脑,扣去用额,另一个则把我们要买的蛋和牛奶递给我们。把东西放进篮子后,我们走了出去,从那个大肚子女人和她的同伴身旁经过。她的同伴看起来跟我们一样瘦弱、憔悴。那位孕妇的大肚子简直就像一只硕大的水果。奇大无比,我儿时爱用这个字眼。她把手放在肚子上,像是为了保护它,又像是要从那儿汲取温暖和力量。
当我走过时,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认出了她。她也在感化中心待过,深得丽迪亚嬷嬷的欢心。可我从未喜欢过她。那时她的名字叫珍妮。
珍妮看着我,接着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她把目光扫过我红裙下扁平的肚子,双翼头巾遮住了她的脸。我只能看到她露出来的一部分前额和粉红色的鼻尖。
接着我们进了起名“众生”的肉店。招牌是用两根链子吊起来的一块猪排形状的木头。这里人不多,不用排队。肉很贵,就连大主教们也不是天天能吃上。但奥芙格伦还是买了牛排,这已是这个星期的第二次了。我要把这件事告诉马大们:她们最爱听这类消息。对别人家怎么过兴致盎然。此类鸡毛蒜皮的谈资让她们有机会得意或是不满。
我买了鸡,这些宰好的鸡用纸包着,外面用线捆扎。现在塑料包装已难得见到。我还记得从前去超市买东西带回来的数不清的白色塑料包装袋;因为舍不得扔掉便全塞在洗涤槽下面的橱柜里。有时多得只要一开橱柜的门,它们便“扑”的一声掉到地上。对此,卢克常大发牢骚,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把袋子统统扔掉。
女儿会把袋子套到头上去的,卢克总是说。你知道,孩子们总喜欢那么玩。不会的,我总是反驳。她已经长大了(要么就说她聪明过人,或是幸运过人),不会这么干的。但随即我内心会感到一丝恐惧的寒意,会为自己的粗心感到内疚。确实,我对许多事情太想当然了;我过去总相信命运。我会把袋子收在高一点的橱柜里,我说。别留着,他会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可以当垃圾袋,我会说。他又会说……
不行,此时此地,众目睽睽,不能这样胡思乱想。我转过身,看到自己映在厚玻璃窗上的影子。我们已经走了出来,来到大街上了。
远处有一群人朝我们走来。看起来像是从日本来的游客,也许是一个贸易代表团,来此地观看名胜古迹或出来见识地方风情。他们个个身材矮小,但着装整齐;男男女女都拿着相机,面带微笑。他们环顾四周,两眼发亮,像知更鸟一样歪着头,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肆无忌惮。我忍不住盯着他们看。我很久没看到女人穿那么短的裙子了。长度刚过膝盖,只穿着薄薄丝袜的两条小腿公然裸露在外。高跟鞋细细的带子襻在脚上,看上去仿佛是精美的刑具。由于鞋跟又细又高,她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像在踩高跷;腰陷进去,整个背成了弓形,屁股向外撅着。她们头上无遮无盖,一头秀发暴露在外,油黑亮泽,性感十足。湿润的嘴唇上沿着唇线涂着红色的唇膏,就像从前厕所墙上常见的胡抹乱画。
我停住脚步。在我身旁的奥芙格伦也停了下来。我知道她同样也在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些女人。她们看起来既让人着迷,又让人反感。在我们眼里,她们就像没穿衣服一样。对此类事情,我们的观念转变得真够快的。
接着我想,过去我也曾这么穿过。那便是自由。
西化,过去人们这么形容。
那些日本游客谈笑风生地朝我们走来。这时要掉开脸已为时过晚: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脸。
人群中的一个显然是翻译。他身穿一套普通的蓝色西装,红格子领带上面别着翼眼别针。他走上前来,站到我们面前,挡住了去路。别的游客也拥上来,其中一个举起了相机。
“对不起,”他彬彬有礼地对我们说,“他们问是否可以拍你们。”
我低头看脚下的人行道,摇头表示不同意。他们看到的不过是白色双翼头巾,一点点面孔,下巴和部分嘴巴。绝对看不到眼睛。我知道还是不要直视翻译为妙。许多翻译都是眼目,起码人们都这么说。
我也知道此时绝不能回答同意。谦逊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丽迪亚嬷嬷说。永远不要忘记。要是让人看到——要是让人看到——便意味着——她的声音发颤——能够被人看透。而你们,姑娘们,必须使自己成为看不透的人。她把我们称为姑娘们。
我身旁的奥芙格伦也缄口不言。她已把戴着红手套的双手缩进袖子里,藏了起来。
翻译转向人群,断断续续地对他们说着什么。我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我知道那套说辞。他会告诉他们这里的女人与别处风俗不同,用相机镜头对准她们,对其来说是一种冒犯。
我低头看着人行道,那些女人的双脚简直令我着迷。其中一位穿着露出脚指头的凉鞋,脚指甲涂成粉红色。我还记得指甲油的味道,记得第一遍没干透,第二遍就匆匆涂上去后起皱的样子,记得薄薄的连裤袜与皮肤的轻柔相触,记得脚指头在全身重量的压迫下挤向鞋子前端的感觉。涂了脚指甲油的女人两脚交替了一下,我仿佛觉得她的鞋就在我的脚上。指甲油的味道令我如饥似渴。
“对不起。”翻译又转身朝我们说。我点点头,表示听到了。
“这位游客问,你们快乐吗?”翻译说。我能想象得出,他们对我们有多么好奇:她们快乐吗?她们怎么可能快乐?我能感觉到他们亮晶晶的黑眼睛片刻不离我们,身子微微前倾,等着我们回答,女人们尤其如此,男人们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神秘莫测,不可接近,我们令他们亢奋。
奥芙格伦一声不吭。顿时出现一片静寂。有时不说话同样危险。
“不错,我们很快乐。”我喃喃道。我总得说些什么。除此之外,我又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