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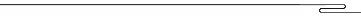
我入宫过继给同治和光绪为子,同治和光绪的妻子都成了我的母亲。我继承同治兼祧光绪,按说正统是在同治这边,但是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不仅不管这一套,而且使用太后权威把敢于和她争论这个问题的同治的瑜、珣、瑨三妃打入冷宫,根本不把她们算做我的母亲之数。光绪的瑾妃也实际得不到庶母的待遇。遇到一家人同座吃饭的时候,隆裕和我都坐着吃,她却要站着吃。直到隆裕去世那天,同治的三个妃和瑾妃联合起来找王公们说理,这才给她们明确了太妃的身份,从那天起,我管她们一律叫“皇额娘”。
我有过这么多的母亲,按说应该得到几倍于平常人的母爱,何况她们又把我抢来抢去的。可是今天回想起来,她们表现出的母爱,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每次送菜和听太监们汇报我“进得香”之类的事情。
事实上我小时候并不能“进得香”。我从小有胃病,得病的原因也许正和母爱有关。我六岁时有一次吃栗子太多,撑着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隆裕太后只许我吃糊米粥,尽管天天嚷肚子饿,也没有人敢给我什么别的吃。这天我随太后游中南海,太后叫人拿来干馒头,让我喂鱼玩,这种鱼食突然引起了我的食欲,一时情不自禁就塞到嘴里去了。我这副饿相不但没有让隆裕悔悟过来,反而让她布置了更严厉的戒备。他们越是戒备,越是刺激了我抢吃抢喝的欲望。有一天,各王府给太后送来贡品,停在西长街,叫我看见了,凭着一种本能,我直奔其中的一个食盒,打开了盖子,一看是满满的一盒酱肘子,这自然比干馒头更叫我眼红了,我抓起一只就咬。跟随的太监大惊失色,伸手来抢,我拼命抵抗,终于我人小力薄敌不过他们人多势众,好香的一只肘子刚到嘴又跑了。

 隆裕(居中者)和慈禧在一起(裕勋龄摄于1900年1月1日)
隆裕(居中者)和慈禧在一起(裕勋龄摄于1900年1月1日)
我恢复了正常饮食之后,也常免不了受罪。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卷,被一个领班太监知道了,他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使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蹾了我一阵儿。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卷撑着都亏那个治疗方法。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难以置信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情理和难以置信的呢。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疗:“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多数是毓庆宫里面的那间放“毛凳儿”的屋子,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自然又哭又喊,可是无论我怎么叫骂,踢门,央求,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败了火”,才把我释放出来。这种奇怪的诊疗,并不是太监们的擅自专断,甚至也不是隆裕太后的个人发明,而是皇族家庭的一种传统,我的弟弟妹妹们在王府里,都受过这样的待遇。
隆裕太后在我八岁时去世了。我对她的“慈爱”只能记得起这些。和我相处较久的是四位太妃。
我和四位太妃平常很少见面。坐在一起谈谈,像普通人家那样亲热一会儿的事,根本没有过。每天早晨,我要到每位太妃面前请安,每到一处,太监给我放下黄锻子的跪垫,我跪了一下,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太妃那几句例行公事的话。这时候太妃正让太监梳着头,一边梳着一边问着:“皇帝歇得好?”“天冷了,要多穿衣服。”“书念到哪儿啦?”全是千篇一律的枯燥话,有时也给我一些泥人之类的玩意儿,最后都少不了一句:“皇帝玩去吧!”一天的会面就此结束,这一天就再也不见面了。
太后太妃都叫我皇帝,我的亲生父母和祖母也这样称呼我。其他人都叫我皇上。虽然我也有名字,也有乳名,不管是哪位母亲也没有叫过。我从父亲的日记里“贴黄”的地方,撕开那块黄绫,知道了自己的乳名叫“午格”,已是五十岁以后的事情。我听人说过,每个人一想起自己的乳名,便会联想起幼年和母爱来。我并没有这种联想。有人告诉我,他离家出外求学时,每逢生病,就怀念母亲,想到幼年病中在母亲怀里受到的爱抚。我在成年以后生病倒是常事,也想起过幼年每逢生病必有太妃的探望,却丝毫引不起我任何怀念之情。
我在幼时,一到冷天经常有伤风感冒的小病。这时候,轻易不到养心殿来的太妃们便分批出现了。每一位太妃来了都是那几句话:“皇帝好些了?出汗没有?”不过两三分钟,就走了。印象比较深的,倒是那一群跟随来的太监,每次必挤满了我的小卧室,也把冷空气带了进来。在这几分钟之内一出一进必使屋里气流发生一次变化。这位太妃刚走,第二位就来了,又是挤满一屋子。一天之内就四进四出,气流变化四次。好在我的病总是第二天就见好,卧室里也就得以风平浪静。
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宫的药房煎药。永和宫是端康太妃住的地方,她的药房比其他太妃宫的药房设备都好,是继承隆裕太后的。端康太妃对我的管束也比别的太妃多,俨然代替了隆裕原先的地位。这种不符清室先例的现象却是出于袁世凯的干预。隆裕去世后,袁世凯曾派过段祺瑞和荫昌向清室内务府提出,应该给同、光的四妃加以晋封和尊号,并且表示承认瑾妃列四妃之首。袁世凯为什么管这种闲事,我不知道,有人说这是由于瑾妃娘家兄弟志琦的活动,也不知确否。但我确知我父亲载沣和其他王公妃们都接受了这种干预,给瑜、珣皇贵妃上了尊号(敬懿、庄和),瑨、瑾二贵妃也晋封为皇贵妃(尊号为荣惠、端康),端康成了我的首席母亲。从此,她对我越管越严,直到发生了一次大冲突为止。
我在“母亲们”的那种“关怀”下长到十三四岁,也还像别的孩子那样很喜欢玩,喜欢一些新鲜玩意儿。有些太监为了讨我高兴,不时从外面买些有趣的东西给我。有一次,一个太监给我制了一套民国将领大礼服,帽子上还有个像白鸡掸子似的翎子,另外还有军刀和皮带。我穿戴起来,洋洋得意。谁知叫端康知道了,大为震怒,经过一阵检査,知道了我还穿了太监从外面买来的洋袜子。在她看来这都是不得了的事,就把买军服和洋袜子的太监李长安、李延年都叫到永和宫,每人责打了二百大板,发落到打扫处去充当苦役。发落完了太监,把我叫了去,对我大加训斥:“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还像话吗?”我不得已,收拾起了心爱的军服洋刀,脱下洋袜,换上裤褂和绣着龙纹的布袜,心里开始种下了怨恨。
如果端康对我的管教仅限于军服和洋袜子,我并不一定会有后来的不敬行为。因为这类的管教只能让我更觉得自己与常人不同,更能和毓庆宫的教育合上拍,印证着我的皇帝的身份。我相信她让太监挨一顿板子和对我的训斥,也是出于这个教育目的。但这位一心一意想模仿慈禧太后的瑾妃,虽然她的亲姐姐珍妃死于慈禧之手,慈禧仍然被她看作榜样。她忘掉时代早已起了变化。她不仅学会了毒打太监,还学了派太监监视皇帝的办法。她发落了我身边李长安、李延年这些人之后,派了她身边的太监到我的养心殿来,每天到她那里报告我的一举一动,就和西太后对待光绪一样。不管她是什么目的,这大大伤害了皇帝的自尊心。加上我的老师陈宝琛也为此愤愤不平,他的嫡庶之分的理论更打动了我的心,我肚里的怒气,因此有了发展。

 溥仪老师陈宝琛(摄于1925年)
溥仪老师陈宝琛(摄于1925年)
过了不久,太医院里一个叫范一梅的大夫被端康辞退,成了爆发的导火线。范大夫是给端康治病的大夫之一,这事本与我不相干,可是这时我耳朵里装了不少鼓动性的议论。陈老师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那个曾经把我关起来“唱一唱败火”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李长安挨板子本来由于他的挟嫌告发,这时也变成了“帝党”)发出同样的不平之论,在我耳朵边说:“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了吗?再说太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连奴才也看不过去。”听了这些话,我的激动立刻升到顶点。于是我气冲冲地来到了永和宫,自然照例的请安也没有了,看见了端康就嚷道:“你凭什么辞掉了范一梅?你这是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咱是谁说了话算数,真是专擅已极了……”
我大嚷了一通,不顾气得脸色发白的端康说什么,一甩袖子跑了出来。回到毓庆宫,师傅们都把我夸了一顿。
气急败坏的端康太妃没有找我,却叫人把我的父亲和别的几位王公找了来,向他们大叫大哭,叫他们给拿主意。这些王公们谁也没敢出主意。我听到了这消息,又把他们叫到上书房里,慷慨激昂地说:“她是什么人?不过是个妃。本朝历代从来没有皇帝管妃叫额娘的!嫡庶之分要不要?如果不要,怎么溥杰不管王爷的侧福晋叫一声呢?凭什么我就得叫她,还要听她的呢……”
这几位王公听我嚷了一顿,仍然是什么话也不说。
这时,早就不服端康的敬懿太妃也乘机对我表示了支持,并且特意来告诉我:“听说永和宫要请太太奶奶来,皇帝可要留神!”
果然,我的祖母和母亲都被端康叫来了。她对王公们没办法,对我祖母和母亲一阵叫嚷可发生了作用,特别是祖母吓得厉害,最后和我母亲一齐跪下来恳求她息怒,答应了劝我赔不是。我到了永和宫配殿里见到了祖母和母亲,听到正殿里端康还在和我父亲嚷叫,我本来又要去吵,可是禁不住祖母和母亲流着泪的苦苦哀劝,结果也就软了下来,答应了她们,去向端康赔个不是。
这个不是赔得我很堵心。我走到端康面前,看也没看她一眼,请了个安,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皇额娘,我错了”,就又出来了。端康有了面子停止了哭喊。但是这件事后来却落得这么一个结果:过了两天,传来了我的亲生母亲自杀的消息。
据说,我母亲从小也没受过别人申斥过一句,她的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我不知道她是否就是因此自杀,但后果却是这样:端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担心我对她追究,因此对我一改过去态度,不但再不加以管束,而且变得十分随和。于是紫禁城里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和太妃们之间又恢复了母子关系。然而,牺牲品却是一位亲生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