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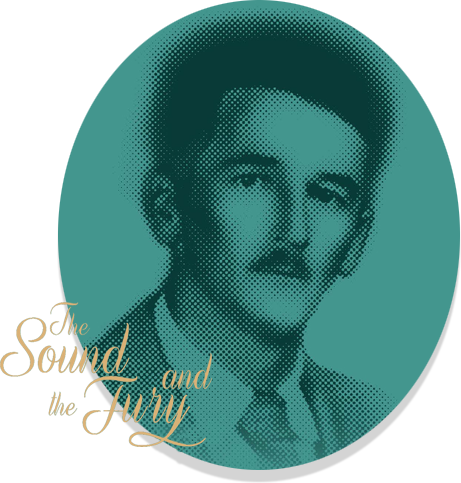


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的空当,我看见他们在打球。他们朝插着小旗的地方走过来,我顺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在那棵开花的树旁草地里找东西。他们把小旗拔出来,打球了。接着他们又把小旗插回去,来到高地
 上,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他们接着朝前走,我也顺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离开了那棵开花的树,我们沿着栅栏一起走,这时候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我透过栅栏张望,勒斯特在草丛里找东西。
上,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他们接着朝前走,我也顺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离开了那棵开花的树,我们沿着栅栏一起走,这时候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我透过栅栏张望,勒斯特在草丛里找东西。
“球在这儿,开弟
 。”那人打了一下。他们穿过草地往远处走去。我贴紧栅栏,瞧着他们走开。
。”那人打了一下。他们穿过草地往远处走去。我贴紧栅栏,瞧着他们走开。
“听听,你哼哼得多难听。”勒斯特说,“也真有你的,都三十三了,还这副样子。我还老远到镇上去给你买来了生日蛋糕呢。别哼哼唧唧了。你就不能帮我找找那只两毛五的镚子儿,好让我今儿晚上去看演出。”
他们过好半天才打一下球,球在草场上飞过去。我顺着栅栏走回到小旗附近去。小旗在耀眼的绿草和树木间飘荡。
“过来呀。”勒斯特说,“那边咱们找过了。他们一时半刻间不会再过来的。咱们上小河沟那边去找,再晚就要让那帮黑小子捡去了。”
小旗红红的,在草地上呼呼地飘着。这时有一只小鸟斜飞下来停歇在上面。勒斯特扔了块土过去。小旗在耀眼的绿草和树木间飘荡。我紧紧地贴着栅栏。
“快别哼哼了。”勒斯特说,“他们不上这边来,我也没法让他们过来呀,是不是。你要是还不住口,姥姥
 就不给你做生日了。你还不住口,知道我会怎么样。我要把那只蛋糕全都吃掉。连蜡烛也吃掉。把三十三根蜡烛全都吃下去。来呀,咱们上小河沟那边去。我得找到那只镚子儿。没准还能找到一只掉在那儿的球呢。哟。他们在那儿。挺远的。瞧见没有。”他来到栅栏边,伸直了胳膊指着,“看见他们了吧。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来吧。”
就不给你做生日了。你还不住口,知道我会怎么样。我要把那只蛋糕全都吃掉。连蜡烛也吃掉。把三十三根蜡烛全都吃下去。来呀,咱们上小河沟那边去。我得找到那只镚子儿。没准还能找到一只掉在那儿的球呢。哟。他们在那儿。挺远的。瞧见没有。”他来到栅栏边,伸直了胳膊指着,“看见他们了吧。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来吧。”
我们顺着栅栏,走到花园的栅栏旁,我们的影子落在栅栏上,在栅栏上,我的影子比勒斯特的高。我们来到缺口那儿,从那里钻了过去。
“等一等。”勒斯特说,“你又挂在钉子上了。你就不能好好地钻过去不让衣服挂在钉子上吗。”
凯蒂把我的衣服从钉子上解下来,我们钻了过去。
 凯蒂说,毛莱舅舅关照了,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们,咱们还是猫着腰吧。猫腰呀,班吉。像这样,懂吗。我们猫下了腰,穿过花园,花儿刮着我们,沙沙直响。地绷绷硬。我们又从栅栏上翻过去,几只猪在那儿嗅着闻着,发出了哼哼声。凯蒂说,我猜它们准是在伤心,因为它们的一个伙伴今儿个被宰了。地绷绷硬,是给翻掘过的,有一大块一大块土疙瘩。
凯蒂说,毛莱舅舅关照了,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们,咱们还是猫着腰吧。猫腰呀,班吉。像这样,懂吗。我们猫下了腰,穿过花园,花儿刮着我们,沙沙直响。地绷绷硬。我们又从栅栏上翻过去,几只猪在那儿嗅着闻着,发出了哼哼声。凯蒂说,我猜它们准是在伤心,因为它们的一个伙伴今儿个被宰了。地绷绷硬,是给翻掘过的,有一大块一大块土疙瘩。
把手插在兜里,凯蒂说。不然会冻坏的。快过圣诞节了,你不想让你的手冻坏吧,是吗。
“外面太冷了。”威尔许说,
 “你不要出去了吧。”
“你不要出去了吧。”
“这又怎么的啦。”母亲说。
“他想到外面去呢。”威尔许说。
“让他出去吧。”毛莱舅舅说。
“天气太冷了。”母亲说,“他还是待在家里得了。班吉明。好了,别哼哼了。”
“对他不会有害处的。”毛莱舅舅说。
“喂,班吉明。”母亲说,“你要是不乖,那只好让你到厨房去了。”
“妈咪说今儿个别让他上厨房去。”威尔许说,“她说她要把那么些过节吃的东西都做出来。”
“让他出去吧,卡罗琳。”毛莱舅舅说,“你为他操心太多了,自己会生病的。”
“我知道。”母亲说,“有时候我想,这准是老天对我的一种惩罚。”
“我明白,我明白。”毛莱舅舅说,“你得好好保重。我给你调一杯热酒吧。”
“喝了只会让我觉得更加难受。”母亲说,“这你不知道吗。”
“你会觉得好一些的。”毛莱舅舅说,“给他穿戴得严实些,小子,出去的时间可别太长了。”
毛莱舅舅走开去了。威尔许也走开了。
“别吵了好不好。”母亲说,“我们还巴不得你快点出去呢。我只是不想让你害病。”
威尔许给我穿上套鞋和大衣,我们拿了我的帽子就出去了。毛莱舅舅在饭厅里,正在把酒瓶放回到酒柜里去。
“让他在外面待半个小时,小子。”毛莱舅舅说,“就让他在院子里玩得了。”
“是的,您哪。”威尔许说,“我们从来不让他到外面街上去。”
我们走出门口。阳光很冷,也很耀眼。
“你上哪儿去啊。”威尔许说,“你不见得以为是到镇上去吧,是不是啊。”我们走在沙沙响的落叶上。铁院门冰冰冷的。“你最好把手插在兜里。”威尔许说,“你的手捏在门上会冻坏的,那你怎么办。你干吗不待在屋子里等他们呢。”他把我的手塞到我口袋里去。我能听见他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我能闻到冷的气味
 。铁门是冰冰冷的。
。铁门是冰冰冷的。
“这儿有几个山核桃。好哎。蹿到那棵树上去了。瞧呀,这儿有一只松鼠,班吉。”
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铁门冷了,不过我还能闻到耀眼的冷的气味。
“你还是把手插回到兜里去吧。”
凯蒂在走来了。接着她跑起来了,她的书包在背后一跳一跳,晃到这边又晃到那边。
“嗨,班吉。”凯蒂说。她打开铁门走进来,就弯下身子。凯蒂身上有一股树叶的香气。“你是来接我的吧。”她说,“你是来等凯蒂的吧。你怎么让他两只手冻成这样,威尔许。”
“我是叫他把手放在兜里的。”威尔许说,“他喜欢抓住铁门。”
“你是来接凯蒂的吧。”她说,一边搓着我的手,“什么事。你想告诉凯蒂什么呀。”凯蒂有一股树的香味,当她说我们这就要睡着了的时候,她也有这种香味。
你哼哼唧唧的干什么呀,勒斯特说。
 等我们到小河沟你还可以看他们的嘛。哪。给你一根吉姆生草
等我们到小河沟你还可以看他们的嘛。哪。给你一根吉姆生草
 。他把花递给我。我们穿过栅栏,来到空地上。
。他把花递给我。我们穿过栅栏,来到空地上。
“什么呀。”凯蒂说,
 “你想跟凯蒂说什么呀。是他们叫他出来的吗,威尔许。”
“你想跟凯蒂说什么呀。是他们叫他出来的吗,威尔许。”
“没法把他圈在屋里。”威尔许说,“他老是闹个没完,他们只好让他出来。他一出来就直奔这儿,朝院门外面张望。”
“你要说什么呀。”凯蒂说,“你以为我放学回来就是过圣诞节了吗。你是这样想的吧。圣诞节是后天。圣诞老公公,班吉。圣诞老公公。来吧,咱们跑回家去暖和暖和。”她拉住我的手,我们穿过了亮晃晃、沙沙响的树叶。我们跑上台阶,离开亮亮的寒冷,走进黑黑的寒冷。毛莱舅舅正把瓶子放回到酒柜里去。他喊凯蒂。凯蒂说,
“把他带到炉火跟前去,威尔许。跟威尔许去吧。”她说,“我一会儿就来。”
我们来到炉火那儿。母亲说:
“他冷不冷,威尔许。”
“一点儿不冷,太太。”威尔许说。
“给他把大衣和套鞋脱了。”母亲说,“我还得跟你说多少遍,别让他穿着套鞋走到房间里来。”
“是的,太太。”威尔许说。“好,别动了。”他给我脱下套鞋,又来解我的大衣纽扣。凯蒂说:
“等一等,威尔许。妈妈,能让他再出去一趟吗。我想让他陪我去。”
“你还是让他留在这儿得了。”毛莱舅舅说,“他今天出去得够多的了。”
“依我说,你们俩最好都待在家里。”母亲说,“迪尔西说,天越来越冷了。”
“哦,妈妈。”凯蒂说。
“瞎说八道。”毛莱舅舅说,“她在学校里关了一整天了。她需要新鲜空气。快走吧,凯丹斯
 。”
。”
“让他也去吧,妈妈。”凯蒂说,“求求您。您知道他会哭的。”
“那你干吗当他的面提这件事呢。”母亲说,“你干吗进这屋里来呢。就是要给他个因头,让他再来跟我纠缠不清。你今天在外面待的时间够多的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坐下来陪他玩一会儿吧。”
“让他们去吧,卡罗琳。”毛莱舅舅说,“挨点儿冷对他们也没什么害处。记住了,你自己可别累倒了。”
“我知道。”母亲说,“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怕过圣诞节。没有人知道。我可不是那种精力旺盛能吃苦耐劳的女人。为了杰生
 和孩子们,我真希望我身体能结实些。”
和孩子们,我真希望我身体能结实些。”
“你一定要多加保重,别为他们的事操劳过度。”毛莱舅舅说,“快走吧,你们俩。只是别在外面待太久了,听见了吗。你妈要担心的。”
“是咧,您哪。”凯蒂说。“来吧,班吉。咱们又要出去啰。”她给我把大衣扣子扣好,我们朝门口走去。
“你不给小宝贝穿上套鞋就带他出去吗?”母亲说,“家里乱哄哄人正多的时候,你还想让他得病吗。”
“我忘了。”凯蒂说,“我以为他是穿着呢。”
我们又走回来。“你得多动动脑子。”母亲说。别动了,威尔许说。他给我穿上套鞋。“不定哪一天我就要离开人世了,就得由你们来替他操心了。”现在顿顿脚,威尔许说。“过来跟妈妈亲一亲,班吉明。”
凯蒂把我拉到母亲的椅子前面去,母亲双手捧住我的脸,接着把我搂进怀里。
“我可怜的宝贝儿。”她说。她放开我。“你和威尔许好好照顾他,乖妞儿。”
“是的,您哪。”凯蒂说。我们走出去。凯蒂说,
“你不用去了,威尔许。我来管他一会儿吧。”
“好咧。”威尔许说。“这么冷,出去是没啥意思。”他走开去了,我们在门厅里停住脚步,凯蒂跪下来,用两只胳膊搂住我,把她那张发亮的冻脸贴在我的脸颊上。她有一股树的香味。
“你不是可怜的宝贝儿。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有你的凯蒂呢。你不是有你的凯蒂姐吗。”
你又是嘟哝,又是哼哼,就不能停一会儿吗,勒斯特说。
 你吵个没完,害不害臊。我们经过车房,马车停在那里。马车新换了一只车轱辘。
你吵个没完,害不害臊。我们经过车房,马车停在那里。马车新换了一只车轱辘。
“现在,你坐到车上去吧,安安静静地坐着,等你妈出来。”迪尔西说。
 她把我推上车去。T.P.拉着缰绳。“我说,我真不明白杰生干吗不去买一辆新的轻便马车。”迪尔西说,“这辆破车迟早会让你们坐着坐着就散了架。瞧瞧这些破轱辘。”
她把我推上车去。T.P.拉着缰绳。“我说,我真不明白杰生干吗不去买一辆新的轻便马车。”迪尔西说,“这辆破车迟早会让你们坐着坐着就散了架。瞧瞧这些破轱辘。”
母亲走出来了,她边走边把面纱放下来。她拿着几枝花儿。
“罗斯库司在哪儿啦。”她说。
“罗斯库司今儿个胳膊举不起来了。”迪尔西说,“T.P.也能赶车,没事儿。”
“我可有点担心。”母亲说,“依我说,你们一星期一次派个人给我赶赶车也应该是办得到的。我的要求不算高嘛,老天爷知道。”
“卡罗琳小姐
 ,罗斯库司风湿病犯得很厉害,实在干不了什么活,这您也不是不知道。”迪尔西说,“您就过来上车吧。T.P.赶车的本领跟罗斯库司一样好。”
,罗斯库司风湿病犯得很厉害,实在干不了什么活,这您也不是不知道。”迪尔西说,“您就过来上车吧。T.P.赶车的本领跟罗斯库司一样好。”
“我可有点儿担心呢。”母亲说,“再说还带了这个小娃娃。”
迪尔西走上台阶。“您还管他叫小娃娃。”她说。她抓住了母亲的胳膊。“他跟T.P.一般大,已经是个小伙子了。快走吧,如果您真的要去。”
“我真担心呢。”母亲说。她们走下台阶,迪尔西扶母亲上车。“也许还是翻了车对我们大家都好些。”母亲说。
“瞧您说的,您害臊不害臊。”迪尔西说,“您不知道吗,光是一个十八岁的黑小伙儿也没法能让‘小王后’撒腿飞跑。它的年纪比T.P.跟班吉加起来还大。T.P.,你可别把‘小王后’惹火了,你听见没有。要是你赶车不顺卡罗琳小姐的心,我要让罗斯库司好好抽你一顿。他还不是打不动呢。”
“知道了,妈。”T.P.说。
“我总觉得会出什么事的。”母亲说,“别哼哼了,班吉明。”
“给他一枝花拿着。”迪尔西说,“他想要花呢。”她把手伸了进来。
“不要,不要。”母亲说,“你会把花全弄乱的。”
“您拿住了。”迪尔西说,“我抽一枝出来给他。”她给了我一枝花,接着她的手缩回去了。
“快走吧,不然小昆丁看见了也吵着要去了。”迪尔西说。
“她在哪儿。”母亲说。
“她在屋里跟勒斯特一块儿玩呢。”迪尔西说,“走吧,T.P.,就按罗斯库司教你的那样赶车吧。”
“好咧,妈。”T.P.说,“走起来呀,‘小王后’。”
“小昆丁。”母亲说,“可别让她出来。”
“当然不会的。”迪尔西说。
马车在车道上颠晃、碾轧着前进。“我把小昆丁留在家里真放心不下。”母亲说,“我还是不去算了。T.P.。”我们穿过了铁院门,现在车子不再颠了。T.P.用鞭子抽了“小王后”一下。
“我跟你说话呢,T.P.。”母亲说。
“那也得让它继续走呀。”T.P.说,“得让它一直醒着,不然就回不到牲口棚去了。”
“你掉头呀。”母亲说,“把小昆丁留在家里我不放心。”
“这儿可没法掉头。”T.P.说。过了一会儿,路面宽一些了。
“这儿总该可以掉头了吧。”母亲说。
“好吧。”T.P.说。我们开始掉头了。
“你当心点,T.P.。”母亲说,一面抱紧了我。
“您总得让我掉头呀。”T.P.说。“吁,‘小王后’。”我们停住不动了。
“你要把我们翻出去了。”母亲说。
“那您要我怎么办呢。”T.P.说。
“你那样掉头我可害怕。”母亲说。
“驾,‘小王后’。”T.P.说。我们又往前走了。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一走开,迪尔西准会让小昆丁出什么事的。”母亲说,“咱们得快点回家。”
“走起来,驾。”T.P.说。他拿鞭子抽“小王后”。
“喂,T.P.。”母亲说,死死地抱住了我。我听见“小王后”脚下的嘚嘚声,明亮的形体从我们两边平稳地滑过去,它们的影子在“小王后”的背上掠过。它们像车轱辘明亮的顶端一样向后移动。接着,一边的景色不动了,那是个有个大兵的大白岗亭
 。另外那一边还在平稳地滑动着,只是慢下来了。
。另外那一边还在平稳地滑动着,只是慢下来了。
“你们干什么去。”杰生说。他两只手插在兜里,一支铅笔架在耳朵上面。
“我们到公墓去。”母亲说。
“很好。”杰生说,“我也没打算阻拦你们,是不是。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一点,没别的事了吗。”
“我知道你不愿去。”母亲说,“不过如果你也去的话,我就放心得多了。”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杰生说,“反正父亲和昆丁也没法再伤害你了。”
母亲把手绢塞到面纱底下去。“别来这一套了,妈妈。”杰生说,“您想让这个大傻子在大庭广众又吼又叫吗。往前赶车吧,T.P.。”
“走呀,‘小王后’。”T.P.说。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母亲说,“反正要不了多久我也会跟随你父亲到地下去了。”
“行了。”杰生说。
“吁。”T.P.说。杰生又说,
“毛莱舅舅用你的名义开了五十块钱支票。你打算怎么办?”
“问我干什么。”母亲说,“我还有说话的份儿吗。我只是想不给你和迪尔西添麻烦。我快不在了,再往下就该轮到你了。”
“快走吧,T.P.。”杰生说。
“走呀,‘小王后’。”T.P.说。车旁的形体又朝后面滑动,另一边的形体也动起来了,亮晃晃的,动得很快,很平稳,很像凯蒂说我们这就要睡着了时的那种情况。
整天哭个没完的臭小子,勒斯特说。
 你害不害臊。我们从牲口棚当中穿过去,马厩的门全都敞着。你现在可没有花斑小马驹骑啰,勒斯特说。泥地很干,有不少尘土。屋顶塌陷下来了。斜斜的窗口布满了黄网丝。你干吗从这边走。你想让飞过来的球把你的脑袋敲破吗。
你害不害臊。我们从牲口棚当中穿过去,马厩的门全都敞着。你现在可没有花斑小马驹骑啰,勒斯特说。泥地很干,有不少尘土。屋顶塌陷下来了。斜斜的窗口布满了黄网丝。你干吗从这边走。你想让飞过来的球把你的脑袋敲破吗。
“把手插在兜里呀。”凯蒂说,“不然的话会冻僵的。你不希望过圣诞节把手冻坏吧,是不是啊。”

我们绕过牲口棚。母牛和小牛犊站在门口,我们听见“王子”“小王后”和阿欢在牲口棚里顿脚的声音。“要不是天气这么冷,咱们可以骑上阿欢去玩儿了。”凯蒂说。“可惜天气太冷,在马上坐不住。”这时我们看得见小河沟了,那儿在冒着烟。“人家在那儿宰猪。”凯蒂说。“我们回家可以走那边,顺便去看看。”我们往山下走去。
“你想拿信。”凯蒂说。“我让你拿就是了。”她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我的手里。“这是一件圣诞礼物。”凯蒂说。“毛莱舅舅想让帕特生太太喜出望外呢。咱们交给她的时候可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好,你现在把手好好地插到兜里去吧。”我们来到小河沟了。
“都结冰了。”凯蒂说。“瞧呀。”她砸碎冰面,捡起一块贴在我的脸上。“这是冰。这就说明天气有多冷。”她拉我过了河沟,我们往山上走去,“这事咱们跟妈妈和爸爸也不能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想,这件事会让妈妈、爸爸和帕特生先生都高兴得跳起来,帕特生先生不是送过糖给你吃吗。你还记得夏天那会儿帕特生先生送糖给你吃吗。”
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栅栏。上面的藤叶干枯了,风把叶子刮得格格地响。
“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毛莱舅舅不派威尔许帮他送信。”凯蒂说。“威尔许是不会多嘴的。”帕特生太太靠在窗口望着我们。“你在这儿等着。”凯蒂说。“就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把信给我。”她从我口袋里把信掏出来。“你两只手在兜里搁好了。”她手里拿着信,从栅栏上爬过去,穿过那些枯黄的、格格响着的花。帕特生太太走到门口,她打开门,站在那儿。
帕特生先生在绿花丛里砍东西。
 他停下了手里的活,对着我瞧。帕特生太太飞跑着穿过花园。我一看见她的眼睛我就哭了起来。你这白痴,帕特生太太说,我早就告诉过他
他停下了手里的活,对着我瞧。帕特生太太飞跑着穿过花园。我一看见她的眼睛我就哭了起来。你这白痴,帕特生太太说,我早就告诉过他
 别再差你一个人来了。把信给我。快。帕特生先生手里拿着锄头飞快地跑过来。帕特生太太伛身在栅栏上,手伸了过来。她想爬过来。把信给我,她说,把信给我。帕特生先生翻过栅栏。他把信夺了过去。帕特生太太的裙子让栅栏挂住了。我又看见了她的眼睛,就朝山下跑去。
别再差你一个人来了。把信给我。快。帕特生先生手里拿着锄头飞快地跑过来。帕特生太太伛身在栅栏上,手伸了过来。她想爬过来。把信给我,她说,把信给我。帕特生先生翻过栅栏。他把信夺了过去。帕特生太太的裙子让栅栏挂住了。我又看见了她的眼睛,就朝山下跑去。
“那边除了房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勒斯特说,
 “咱们到小河沟那边去吧。”
“咱们到小河沟那边去吧。”
人们在小河沟里洗东西。其中有一个人在唱歌。我闻到衣服在空中飘动的气味,青烟从小河沟那边飘了过来。
“你就待在这儿。”勒斯特说,“你到那边去也没有什么好干的。他们会打你的,错不了。”
“他想要干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勒斯特说,“他兴许是想到那边人们打球的高地上去。你就在这儿坐下来玩你的吉姆生草吧。要是你想看什么,就看看那些在河沟里玩水的小孩。你怎么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规规矩矩呢。”我在河边上坐了下来,人们在那儿洗衣服,青烟在往空中冒去。
“你们大伙儿有没有在这儿附近捡到一只两毛五的镚子儿。”勒斯特说。
“什么镚子儿。”
“我今天早上在这儿的时候还有的。”勒斯特说,“我不知在哪儿丢失了。是从我衣兜这个窟窿里掉下去的。我要是找不到,今儿晚上就没法看演出了。”
“你的镚子儿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小子。是白人不注意的时候从他们衣兜里掏的吧。”
“是从该来的地方来的。”勒斯特说,“那儿镚子儿有的是。不过我一定要找到我丢掉的那一只。你们大伙儿捡到没有。”
“我可没时间来管镚子儿。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你上这边来。”勒斯特说,“帮我来找找。”
“他就算看见了也认不出什么是镚子儿吧。”
“有他帮着找总好一点。”勒斯特说,“你们大伙儿今儿晚上都去看演出吧。”
“别跟我提演出不演出了。等我洗完这一大桶衣服,我会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我敢说你准会去的。”勒斯特说,“我也敢打赌你昨儿晚上准也是去了的。我敢说大帐篷刚一开门你们准就在那儿了。”
“就算没有我,那儿的黑小子已经够多的了。至少昨儿晚上是不少。”
“黑人的钱不也跟白人的钱一样值钱吗,是不是。”
“白人给黑小子们钱,是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要来一个白人乐队,反正会把钱都捞回去的。这样一来,黑小子们为了多赚点钱,又得干活了。”
“又没人硬逼你去看演出。”
“暂时还没有。我琢磨他们还没想起这档子事。”
“你干吗跟白人这么过不去。”
“没跟他们过不去。我走我的桥,让他们走他们的路。我对这种演出根本没兴趣。”
“戏班子里有一个人,能用一把锯子拉出曲调来。就跟耍一把班卓琴似的。”
“你昨儿晚上去了。”勒斯特说,“我今儿晚上想去。只要我知道在哪儿丢的镚子儿就好了。”
“我看,你大概要把他带去吧。”
“我。”勒斯特说,“你以为只要他一吼叫,我就非得也在那儿伺候他吗。”
“他吼起来的时候,你拿他怎么办。”
“我拿鞭子抽他。”勒斯特说。他坐在地上,把工装裤的裤腿卷了起来。黑小子们都在河沟里玩水。
“你们谁捡到高尔夫球了吗。”勒斯特说。
“你说话别这么神气活现。依我说你最好别让你姥姥听见你这样说话。”
勒斯特也下沟了,他们都在那里玩水。他沿着河岸在水里找东西。
“我们早上到这儿来的时候还在身上呢。”勒斯特说。
“你大概是在哪儿丢失的。”
“就是从我衣兜的这个窟窿里落下去的。”勒斯特说。他们在河沟里找来找去。接着他们突然全都站直身子,停住不找了,然后水花乱溅地在河沟里抢夺起来。勒斯特抢到了手,大家都蹲在水里,透过树丛朝小山冈上望去。
“他们在哪儿。”勒斯特说。
“还看不见呢。”
勒斯特把那东西放进兜里。他们从小山冈上下来了。
“瞧见一只球落到这儿来了吗。”
“该是落到水里去了。你们这帮小子有谁瞧见或是听见了吗。”
“没听见什么落到水里来呀。”勒斯特说,“倒是听见有一样东西打在上面的那棵树上。不知道滚到哪儿去了。”
他们朝河沟里看了看。
“妈的。在沟边好好找找。是朝这边飞过来的。我明明看见的。”
他们在沟边找来找去。后来他们回到山冈上去了。
“你拾到那只球没有。”那孩子说。
“我要球干什么。”勒斯特说,“我可没看见什么球。”
那孩子走进水里。他往前走。他扭过头来又看看勒斯特。他顺着河沟往前走着。
那个大人在山冈上喊了声“开弟”。那孩子爬出河沟,朝山冈上走去。
“瞧,你又哼哼起来了。”勒斯特说,“别吵了。”
“他这会儿哼哼唧唧的干什么呀。”
“天知道为的是什么。”勒斯特说,“他无缘无故就这样哼起来。都哼了整整一个上午了。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吧,我想。”
“他多大了。”
“他都三十三了。”勒斯特说,“到今天早上整整三十三岁了。”
“你是说,他像三岁小孩的样子都有三十年了吗。”
“我是听我姥姥说的。”勒斯特说。“我自己也不清楚。反正我们要在蛋糕上插三十三根蜡烛。蛋糕太小。都快插不下了。别吵了。回这边来。”他走过来抓住我的胳膊。“你这老傻子。”他说,“你骨头痒痒欠抽是吗。”
“我看你才不敢抽他呢。”
“我不是没有抽过。马上给我住声。”勒斯特说。“我没跟你说过那边不能上去吗。他们打一个球过来会把你脑袋砸碎的。来吧,上这儿来。”他把我拽回来。“坐下。”我坐了下来。他把我的鞋子脱掉,又卷起我的裤管。“好,现在下水去玩,看你还哭哭啼啼、哼哼唧唧不。”
我停住哼叫,走进水里
 这时罗斯库司走来说去吃晚饭吧,凯蒂就说,
这时罗斯库司走来说去吃晚饭吧,凯蒂就说,
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呢。我可不去。
她衣服湿了。
 我们在河沟里玩,凯蒂往下一蹲把衣裙都弄湿了,威尔许说,
我们在河沟里玩,凯蒂往下一蹲把衣裙都弄湿了,威尔许说,
“你把衣服弄湿了,回头你妈要抽你了。”
“她才不会做这样的事呢。”凯蒂说。
“你怎么知道。”昆丁说。
“我当然知道啦。”凯蒂说,“你又怎么知道她会呢。”
“她说过她要抽的。”昆丁说,“再说,我比你大。”
“我都七岁了。”凯蒂说,“我想我也应该知道了。”
“我比七岁大。”昆丁说,“我上学了。是不是这样,威尔许。”
“我明年也要上学。”凯蒂说,“到时候我也要上学的。是这样吗,威尔许。”
“你明知道把衣服弄湿了她会抽你的。”威尔许说。
“没有湿。”凯蒂说。她在水里站直了身子,看看自己的衣裙。“我把它脱了。”她说,“一会儿就会干的。”
“我谅你也不敢脱。”昆丁说。
“我就敢。”凯蒂说。
“我看你还是别脱的好。”昆丁说。
凯蒂走到威尔许和我跟前,转过身去。
“给我把扣子解了,威尔许。”她说。
“别替她解,威尔许。”昆丁说。
“这又不是我的衣服。”威尔许说。
“你给我解开,威尔许。”凯蒂说,“不然,我就告诉迪尔西你昨天干的好事。”于是威尔许就帮她解开了扣子。
“你敢脱。”昆丁说。凯蒂把衣裙脱下,扔在岸上。这一来,她身上除了背心和衬裤,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于是昆丁打了她一下耳光,她一滑,跌到水里去了。她站直身子后,就往昆丁身上泼水,昆丁也往她身上泼水。水也溅到威尔许和我的身上,于是威尔许抱我起来,让我坐在河岸上。他说要去告诉大人,于是昆丁和凯蒂就朝他泼水。他躲到树丛后面去了。
“我要去告诉妈咪你们俩都淘气。”威尔许说。
昆丁爬到岸上,想逮住威尔许,可是威尔许跑开了,昆丁抓不到他。等昆丁拐回来,威尔许停住了脚步,嚷嚷说他要去告发。凯蒂跟他说,如果他不去告发,他们就让他回来。威尔许说他不去告发了,于是他们就让他回来。
“这下你该满意了吧。”昆丁说,“我们两个都要挨抽了。”
“我不怕。”凯蒂说,“我要逃走。”
“哼,你要逃走。”昆丁说。
“我是要逃走,而且永远也不回来。”凯蒂说。我哭了起来。凯蒂扭过头来说,“别哭。”我赶紧收住声音。接着他们又在河沟里玩起来了。杰生也在玩。他一个人在远一点的地方玩。威尔许从树丛后面绕出来,又把我抱到水里。凯蒂全身都湿了,屁股上全是泥,我哭起来了,她就走过来,蹲在水里。
“好了,别哭。”她说。“我不会逃走的。”我就不哭了。凯蒂身上有一股下雨时树的香味。
你倒是怎么的啦,勒斯特说。
 你就不能别哼哼,跟大家一样好好玩水吗。
你就不能别哼哼,跟大家一样好好玩水吗。
你干吗不带他回去。他们不是关照过你别让他跑出院子的吗。
他仍旧以为这片牧场还是他们家的呢,勒斯特说。反正从大房子那里谁也看不到这地方。
我们可看到了。谁愿意看见傻子啊。看见了要倒霉的。
罗斯库司走来说去吃晚饭吧,凯蒂说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呢。

“不,已经到了。”罗斯库司说。“迪尔西说让你们全都回去。威尔许,把他们带回来。”他往小山上走去,那头母牛在那里哞哞地叫唤。
“没准等我们走到家,我们身上就会干了。”昆丁说。
“都怪你不好。”凯蒂说。“我倒希望咱们真的挨上一顿鞭子。”她套上衣裙,威尔许帮她扣好扣子。
“他们不会知道你们弄湿过衣服的。”威尔许说,“看不出来。除非我和杰生告发你们。”
“你会告发吗,杰生。”凯蒂说。
“告谁的事啊。”杰生说。
“他不会告发的。”昆丁说,“你会吗,杰生。”
“我看他肯定会。”凯蒂说,“他会去告诉大姆娣
 的。”
的。”
“他可告诉不了大姆娣了。”昆丁说,“她病了。要是我们走得慢点,天就会黑得让他们看不出来。”
“我才不在乎他们看出来看不出来呢。”凯蒂说,“我自己跟他们说去。你背他上山吧,威尔许。”
“杰生是不会说的。”昆丁说,“你还记得我给你做过一副弓箭吧,杰生。”
“都已经断了。”杰生说。
“让他去告发好了。”凯蒂说,“我一点儿也不怕。你背毛莱
 上山呀,威尔许。”威尔许蹲下身来,我趴到他的背上去。
上山呀,威尔许。”威尔许蹲下身来,我趴到他的背上去。
今儿晚上咱们看演出时见,勒斯特说。我们走吧。咱们非得找到那只镚子儿不可。

“如果我们慢慢走,等我们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昆丁说。

“我不想慢慢走。”凯蒂说。我们朝山冈上爬,可是昆丁却不跟上来。等我们走到能闻到猪的气味的地方,他还待在河沟边。那些猪在角落里猪槽前哼着拱着。杰生跟在我们后面,两只手插在兜里。罗斯库司在牲口棚门口挤牛奶。
那些母牛奔跑着从牲口棚里跳出来。

“又吼了。”T.P.说。“吼个没完。我自己也想吼呢。哎唷。”昆丁又踢了T.P.一脚。他把T.P.踢进猪儿吃食的木槽,T.P.就躺倒在那里。“好家伙。”T.P.说,“他以前也是这样欺侮我的。你们都看见这个白人又踢我了吧。哎唷。”
我先没哭,可是我脚步停不下来了。我先没哭,可是地变得不稳起来,我就哭了。
 地面不断向上斜,牛群都朝山冈上奔去,T.P.想爬起来。他又跌倒了,牛群朝山冈下跑去。昆丁拉住我的胳膊,我们朝牲口棚走去。可是这时候牲口棚不见了,我们只得等着,等它再回来。我没见到它回来。它是从我们背后来的,接着昆丁扶我躺在牛吃食的木槽里。我抓紧了木槽的边儿。它也想走开,我紧紧地抓住了它。牛群又朝山冈下跑去,穿过了大门。我脚步停不下来。昆丁和T.P.一边打架一边上山冈。T.P.从山冈上滚下来,昆丁把他拽上山冈。昆丁又打T.P.。我脚步停不下来。
地面不断向上斜,牛群都朝山冈上奔去,T.P.想爬起来。他又跌倒了,牛群朝山冈下跑去。昆丁拉住我的胳膊,我们朝牲口棚走去。可是这时候牲口棚不见了,我们只得等着,等它再回来。我没见到它回来。它是从我们背后来的,接着昆丁扶我躺在牛吃食的木槽里。我抓紧了木槽的边儿。它也想走开,我紧紧地抓住了它。牛群又朝山冈下跑去,穿过了大门。我脚步停不下来。昆丁和T.P.一边打架一边上山冈。T.P.从山冈上滚下来,昆丁把他拽上山冈。昆丁又打T.P.。我脚步停不下来。
“站起来。”昆丁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儿。我不回来你不许走。”
“我和班吉还要回进去看结婚呢。”T.P.说,“哎唷。”
昆丁又揍了T.P.一下。接着他把T.P.按在墙上撞。T.P.在笑。每回昆丁把他往墙上撞他都想叫哎唷,可是他嘻嘻地笑着喊不出来。我不哭了,可是我脚步停不下来。T.P.跌倒在我身上,牲口棚的门飞了开去。门朝山冈下滚去,T.P.自己一个人在乱打乱蹬,他又倒了下来。他还在笑,可是我脚步停不下来,我想爬起来却又倒了下来,我脚步停不下来。威尔许说,
“你们闹够了。真要闹翻天了。别吼啦。”
T.P.还在嘻嘻地笑。他重重地瘫倒在门上,笑了又笑。“哎唷。”他说。“我和班吉还要回进去看结婚呢。沙示汽水
 啊。”T.P.说。
啊。”T.P.说。
“轻点儿。”威尔许说,“你在哪儿弄到的。”
“在地窖里拿的。”T.P.说,“哎唷。”
“轻点儿。”威尔许说,“地窖的什么地方。”
“到处都是。”T.P.说。他笑得更疯了。“还有一百多瓶呢。有一百多万瓶呢。注意啦,黑小子,我可要吼啦。”
昆丁说:“把他拖起来。”
威尔许把我拖了起来。
“把这个喝下去,班吉。”昆丁说。玻璃杯是热的。
 “别喊了,快。”昆丁说,“把这个喝下去。”
“别喊了,快。”昆丁说,“把这个喝下去。”
“沙示汽水。”T.P.说,“让我来喝,昆丁少爷。”
“你给我闭嘴。”威尔许说,“昆丁少爷要把你抽得昏过去呢。”
“按住他,威尔许。”昆丁说。
他们按住了我。那东西流在我下巴上和衬衫上,热乎乎的。“喝下去。”昆丁说。他们抱住我的头。那东西在我肚子里热烘烘的,我又忍不住了。我现在大叫起来了,我肚子里出了什么事儿,我叫唤得更厉害了,他们就一直按住了我,直到肚子里平静下来了。这时我住声了。那东西还在周围转悠,接着一些人影出现了。把谷仓的门打开,威尔许。他们走得很慢。把那些空麻袋铺在地上。他们走得快些了,可以说是很快了。好,现在提起他的脚。他们继续往前走,又平稳又明亮。我听见T.P.在笑。我随着他们往前走,爬上明亮的山坡。

到了小山冈顶上威尔许把我放下来。 “上来呀,昆丁。”他喊道,回头朝山冈下望去。昆丁仍然站在河沟边。他正朝阴影笼罩的河沟扔石子。
“让这个傻瓜蛋待在那儿好了。”凯蒂说。她拉着我的手,我们就往前走,经过了牲口棚,走进院门。砖砌的走道上有一只癞蛤蟆,它蹲在路当中。凯蒂从它头上跨了过去,拉着我继续往前走。
“来呀,毛莱。”她说。它还蹲在那儿,杰生用脚尖去捅捅它。
“它会让你长一个大疣子的。”威尔许说。癞蛤蟆跳了开去。
“来呀,毛莱。”凯蒂说。
“家里今儿晚上有客人。”威尔许说。
“你怎么知道的。”凯蒂说。
“灯全亮着。”威尔许说,“每扇窗子里都亮着灯呢。”
“依我看,只要高兴,没有客人也可以把灯全都开着的。”凯蒂说。
“肯定是有客人。”威尔许说,“你们最好还是打后门进去,悄悄地溜上楼去。”
“我不怕。”凯蒂说,“我要大大咧咧地走到客人坐着的客厅里去。”
“你这样做,你爸爸准会抽你一顿。”威尔许说。
“我才不怕呢。”凯蒂说,“我要大大咧咧地走到客厅里去。我要大大咧咧地走进餐厅去吃晚饭。”
“有你坐的地方吗。”威尔许说。
“我就坐在大姆娣的座位上。”凯蒂说,“她现在在床上吃饭。”
“我饿了。”杰生说。他越过我们,在走道上跑了起来。他双手插在兜里,他摔倒了。威尔许过去把他扶了起来。
“你把手从兜里拿出来,走路就稳当了。”威尔许说,“你这么胖,等快摔跤时,再把手从兜里抽出来稳住身子,可就来不及了。”
父亲站在厨房台阶前。
“昆丁在哪儿。”他说。
“他正在小道上走来呢。”威尔许说。昆丁在慢慢地走来。他的白衬衫望过去白蒙蒙的一片。
“哦。”父亲说。灯光顺着台阶照下来,落在他身上。
“凯蒂和昆丁方才打水仗了。”杰生说。
我们等待着。
“真的吗。”父亲说。昆丁走过来了,父亲说:“今天晚上你们在厨房里吃饭。”他弯下身子把我抱起来,顺着台阶泻下来的灯光也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可以从高处望着凯蒂、杰生、昆丁和威尔许。父亲转身朝台阶走去。“不过,你们得安静些。”他说。
“干吗要我们安静,爸爸。”凯蒂说,“家里来客人了吗。”
“是的。”父亲说。
“我早告诉你们家里有客人嘛。”威尔许说。
“你没说。”凯蒂说,“是我说有客人的。反正我有这个意思。”
“别吵了。”父亲说。他们不作声了,父亲开了门,我们穿过后廊走进厨房。迪尔西在厨房里,父亲把我放进椅子,把围嘴围好,又把椅子推到桌子跟前。桌子上放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你们现在都听从迪尔西的指挥。”父亲说,“迪尔西,让他们尽量声音轻点儿。”
“好的,老爷。”迪尔西说。父亲走了。
“记住了,现在要听迪尔西指挥了。”他在我们背后又说了一句。我把脸伛到饭菜上去。热气直往我脸上冲来。
“今天晚上让大伙儿听我指挥吧,爸爸。”凯蒂说。
“我不要。”杰生说,“我要听迪尔西的。”
“要是爸爸说了,那你就得听我的。”凯蒂说,“让他们听我的吧。”
“我不嘛。”杰生说,“我不要听你的。”
“别吵了。”父亲说,“那你们就听凯蒂的得了。迪尔西,等他们吃完了,就走后楼梯把他们带上楼去。”
“好咧,老爷。”迪尔西说。
“行了吧。”凯蒂说,“现在,我看你们都得听我的了吧。”
“你们都给我住嘴。”迪尔西说,“今天晚上你们得安静点。”
“干吗我们今天晚上得安静呀。”凯蒂压低声音问道。
“不用多问。”迪尔西说。“到时候你们自会知道的。”她拿来了我的碗。碗里热气腾腾的,挠得我的脸直痒痒。“过来,威尔许。”迪尔西说。
“什么叫‘到时候’,迪尔西。”凯蒂说。
“那就是星期天。”
 昆丁说,“你怎么连这个也不懂。”
昆丁说,“你怎么连这个也不懂。”
“嘘。”迪尔西说。“杰生先生没说你们都得安安静静的吗。好,快吃晚饭吧。来,威尔许。把他的勺子拿来。”威尔许的手拿着勺子过来了,勺子伸进碗里。勺子升高到我的嘴边。那股热气痒酥酥地进入我的嘴里。这时,大家都停了下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声不吭,接着我们又听见了,这时我哭了起来。
“那是什么声音。”凯蒂说。她把手按在我的手上。
“那是妈妈。”昆丁说。勺子上来了,我又吃了一口,接着我又哭了。
“别响。”凯蒂说。可是我没有住声,于是她走过来用胳膊搂着我。迪尔西走去把两扇门都关上了,我们就听不见那声音了。
“好了,别哭了。”凯蒂说。我收住声音,继续吃东西。昆丁没在吃,杰生一直在吃。
“那是妈妈。”昆丁说。他站了起来。
“你给我坐下。”迪尔西说,“他们那儿有客人,你们一身泥,不能去。你也给我坐下,凯蒂,快把饭吃完。”
“她方才是在哭。”昆丁说。
“像是有人在唱歌。”凯蒂说,“是不是啊,迪尔西。”
“你们全都给我好好吃晚饭,这是杰生先生吩咐了的。”迪尔西说,“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道的。”凯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没告诉你们这是在开舞会吗。”她说。
威尔许说:“他全都吃下去了。”
“把他的碗拿来。”迪尔西说。碗又不见了。
“迪尔西。”凯蒂说,“昆丁没在吃。他是不是得听我的指挥呀。”
“快吃饭,昆丁。”迪尔西说,“你们都快点吃,快给我把厨房腾出来。”
“我吃不下了。”昆丁说。
“我说你得吃你就非吃不可。”凯蒂说,“是不是这样,迪尔西。”
那只碗又热气腾腾地来到我面前,威尔许的手把勺子插进碗里,热气又痒酥酥地进入我的嘴里。
“我一点儿也吃不下了。”昆丁说,“大姆娣病了,他们怎么会开舞会呢。”
“他们可以在楼下开嘛。”凯蒂说,“她还可以到楼梯口来偷看呢。待会儿我换上了睡衣也要这么做。”
“妈妈方才是在哭。”昆丁说,“她是在哭,对吧,迪尔西。”
“你别跟我烦个没完,孩子。”迪尔西说,“你们吃完了,我还得给那么些大人做饭吃呢。”
过了一会儿,连杰生也吃完了,他开始哭起来了。
“好,又轮到你哭哭啼啼了。”迪尔西说。
“自从大姆娣病了,他没法跟她一起睡以后,他每天晚上都要来这一套。”凯蒂说,“真是个哭娃娃。”
“我要告诉爸爸妈妈。”杰生说。
他还在哭。“你已经告诉过了。”凯蒂说,“你再也没什么可以告诉的了。”
“你们都应该上床去了。”迪尔西说。她走过来,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用一块热布擦我的脸和手。“威尔许,你能不能从后楼梯把他们悄悄地带到楼上去。行了,杰生,别那样呜噜呜噜的了。”
“现在去睡还太早。”凯蒂说,“从来没人这么早就让我们睡觉。”
“你们今天晚上就是得这么早就睡。”迪尔西说,“你爸爸说了,让你们一吃完饭就马上上楼。你自己听见的。”
“他说了要大家听我的。”凯蒂说。
“我可不想听你的。”杰生说。
“你一定得听。”凯蒂说,“好,注意了。你们全都得听从我的指挥。”
“叫他们轻着点儿,威尔许。”迪尔西说,“你们都得轻手轻脚的,懂了吗。”
“干吗今天晚上我们得轻手轻脚呀。”凯蒂说。
“你妈妈身体不太好。”迪尔西说,“现在你们都跟着威尔许走吧。”
“我跟你们说了是妈妈在哭嘛。”昆丁说。威尔许抱起我,打开通往后廊的门。我们走出来,威尔许关上门,周围一片黑暗。我能闻到威尔许的气味,能触摸到他。大家安静。我们先不上楼去。杰生先生说过叫大家上楼去。他又说过叫大家听我指挥。我并不想指挥你们。可是他说过大家要听我的话。他说过的吧,昆丁。我能摸到威尔许的头。我能听见大家的出气声。他说过的吧,威尔许。是这样的吧,没错儿。好,那我决定咱们到外面去玩一会儿。来吧。威尔许打开门,我们都走了出去。
我们走下台阶。
“我的意思是,咱们最好到威尔许的小屋
 去,在那儿人家就听不见咱们的声音了。”凯蒂说。威尔许把我放下来,凯蒂拉着我的手,我们沿着砖砌的小路往前走。
去,在那儿人家就听不见咱们的声音了。”凯蒂说。威尔许把我放下来,凯蒂拉着我的手,我们沿着砖砌的小路往前走。
“来呀。”凯蒂说,“那只蛤蟆不在了。到这会儿它准已经跳到花园里去了。没准咱们还能见到另外一只。”罗斯库司提了两桶牛奶走来。他往前走去了。昆丁没有跟过来。他坐在厨房的台阶上。我们来到威尔许的小屋前。我喜欢闻威尔许屋子里的气味。
 屋子里生着火,T.P.正蹲在火前,衬衫后摆露在外面,他把一块块木柴添进火里,让火烧旺。
屋子里生着火,T.P.正蹲在火前,衬衫后摆露在外面,他把一块块木柴添进火里,让火烧旺。
后来我起床了,T.P.给我穿好衣服,我们走进厨房去吃饭。迪尔西在唱歌
 ,我哭了,于是她就不唱了。
,我哭了,于是她就不唱了。
“这会儿别让他进大屋子。”迪尔西说。
“咱们不能朝那边走。”T.P.说。
我们就到河沟里去玩。
“咱们可不能绕到那边去。”T.P.说,“你没听妈咪说不能去吗。”
迪尔西在厨房里唱歌,我哭起来了。
“别哭。”T.P.说,“来吧。咱们上牲口棚去吧。”
罗斯库司在牲口棚里挤牛奶。他用一只手挤奶,一边在哼哼。有几只鸟雀停在牲口棚大门上,在瞅着他。一只鸟飞了下来,和那些母牛一起吃槽里的东西。我看罗斯库司挤奶,T.P.就去给“小王后”和“王子”喂草料。小牛犊关在猪圈里。它用鼻子挨擦着铁丝网,一边哞哞地叫着。
“T.P.。”罗斯库司说。T.P.在牲口棚里应了句“啥事,爹”。阿欢把脑袋从栅门上探了出来,因为T.P.还没喂它草料。“你那边完事啦。”罗斯库司说,“你得来挤奶啊。俺的右手一点不听使唤了。”
T.P.过来挤奶了。
“您干吗不找大夫去瞧瞧。”T.P.说。
“大夫有什么用。”罗斯库司说,“反正在这个地方不管用。”
“这个地方又怎么啦。”T.P.说。
“这个地方不吉利。”罗斯库司说,“你挤完奶就把牛犊关进来。”
这个地方不吉利,罗斯库司说。
 火光在他和威尔许的背后一蹿一蹿,在他和威尔许的脸上掠动。迪尔西安顿我上床睡觉。床上的气味跟T.P.身上的一样,我喜欢这气味。
火光在他和威尔许的背后一蹿一蹿,在他和威尔许的脸上掠动。迪尔西安顿我上床睡觉。床上的气味跟T.P.身上的一样,我喜欢这气味。
“你知道个啥。”迪尔西说,“莫非你犯傻了。”
“这干犯傻什么事。”罗斯库司说,“这兆头不正躺在床上吗。这兆头不是十五年来让人家看得清清楚楚的吗。”
“就算是吧。”迪尔西说,“反正你跟你这一家子也没吃亏,不是吗。威尔许成了个壮劳力,弗洛尼
 让你拉扯大嫁人了,等风湿病不再折磨你,T.P.也大了,满可以顶替你的活儿了。”
让你拉扯大嫁人了,等风湿病不再折磨你,T.P.也大了,满可以顶替你的活儿了。”
“这就是俩了。”
 罗斯库司说,“还得往上饶一个呢,俺都见到兆头了,你不也见到了吗。”
罗斯库司说,“还得往上饶一个呢,俺都见到兆头了,你不也见到了吗。”
“头天晚上我听见一只夜猫子在叫唤。”T.P.说,“丹儿
 连晚饭都不敢去吃。连离开牲口棚一步都不干。天一擦黑就叫起来了。威尔许也听见的。”
连晚饭都不敢去吃。连离开牲口棚一步都不干。天一擦黑就叫起来了。威尔许也听见的。”
“要往上饶的哪止一个啊。”迪尔西说,“你倒指给我看看,哪个人是长生不死的,感谢耶稣。”
“光是人死还算是好的呢。”罗斯库司说。
“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迪尔西说,“你把那个名字说出来可要倒霉的,除非他哭的时候你跟他一起坐起来
 。”
。”
“这个地方就是不吉利。”罗斯库司说,“俺早先就有点看出来,等到他们给他换了名字,俺就一清二楚了。”
“再别说了。”迪尔西说。她把被子拉上来。被子的气味跟T.P.身上的一样。“你们都别说话,先让他睡着了。”
“俺是看到兆头了。”罗斯库司说。
“兆头。T.P.不得不把你的活儿全都接过去呗。”迪尔西说。
 T.P.,
把他和小昆丁带到后面的小屋去,让他们跟勒斯特一起玩儿,弗洛尼可以看着他们的,你呢,帮你爹干活儿去。
T.P.,
把他和小昆丁带到后面的小屋去,让他们跟勒斯特一起玩儿,弗洛尼可以看着他们的,你呢,帮你爹干活儿去。
我们吃完了饭。T.P.抱起小昆丁,我们就上T.P.的小屋去。勒斯特正在泥地里玩儿。T.P.把小昆丁放下,她也在泥地上玩儿。勒斯特有几只空线轴,他和小昆丁打了起来,小昆丁把线轴抢到手。勒斯特哭了,弗洛尼过来给了勒斯特一只空罐头玩儿,接着我把线轴拿了过来,小昆丁打我,我哭了。
“别哭了。”弗洛尼说,“你不觉得害臊吗,去抢一个小娃娃的玩意儿。”她从我手里把线轴拿走,还给了小昆丁。
“好了,别哭了。”弗洛尼说,“别哭,听见没有。”
“别哭呀。”弗洛尼说,“真该抽你一顿,你骨头痒痒了。”她把勒斯特和小昆丁拉起来。“上这儿来。”她说。我们来到牲口棚。T.P.正在挤奶。罗斯库司坐在一只木箱上。
“他这会儿又怎么啦。”罗斯库司说。
“你们得把他留在这儿。”弗洛尼说,“他又跟小娃娃打架了。抢他们的玩意儿。你跟着T.P.吧,看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现在把奶头好好擦干净。”罗斯库司说,“去年冬天你挤的那头小母牛后来都不出奶了。要是这一头也不出奶,他们就没牛奶喝了。”
迪尔西在唱歌。

“别上那儿去。”T.P.说,“你不知道妈咪说了你不能上那边去吗。”
他们在唱歌。
“来吧。”T.P.说,“咱们跟小昆丁、勒斯特一块儿去玩吧。来呀。”
小昆丁和勒斯特在T.P.小屋前的泥地上玩。屋子里有堆火,火头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罗斯库司坐在火前,像一团黑影。
“这就是仨了,老天爷啊。”罗斯库司说,“两年前俺跟你们说过的。这个地方不吉利。”
“那你干吗不走呢。”迪尔西说。她在给我脱衣服。“你尽唠叨什么不吉利,都让威尔许动了念头跑到孟菲斯
 去了。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去了。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但愿威尔许就只有这么点晦气,要那样倒好了。”罗斯库司说。
弗洛尼走了进来。
“你们活儿都干完了吗。”迪尔西说。
“T.P.也马上完了。”弗洛尼说,“卡罗琳小姐要你伺候小昆丁上床睡觉。”
“我也只能干完了活尽快地去。”迪尔西说,“这么多年了,她也应该知道我没生翅膀。”
“俺不是说了吗?”罗斯库司说,“一个人家,连自己的一个孩子的名儿都不许提起,
 这个地方是肯定不会吉利的。”
这个地方是肯定不会吉利的。”
“别说了。”迪尔西说,“你想把他吵醒,让他哭闹吗。”
“养育一个孩子,连自己妈妈叫什么也不让知道,这算是哪档子事呢。”罗斯库司说。
“你就甭为她瞎操心了。”迪尔西说,“他们家小孩都是我抱大的,再抱大一个又怎么啦,别瞎叨叨了。他想睡了,快让他入睡吧。”
“你们就指名道姓地说好了。”弗洛尼说,“说谁的名儿他都不懂的。”
“你倒说说看,瞧他懂不懂。”迪尔西说,“你在他睡着的时候说,我敢说他也听得见。”
“他懂得的事可比你们以为的要多得多。”罗斯库司说,“他知道大家的时辰什么时候来到,就跟一只猎犬能指示猎物一样。要是他能开口说话,他准能告诉你他自己的时辰什么时候来到,也可以说出你的或是我的时辰。”
“你把勒斯特从那张床上抱出来吧,妈咪。”弗洛尼说,“那孩子会让他中邪的。”
“给我住嘴。”迪尔西说,“你怎么这么糊涂。你干吗去听罗斯库司的胡言乱语。上床吧,班吉。”
迪尔西推推我,我就爬上了床,勒斯特已经在上面了。他睡得很熟。迪尔西拿来一块长长的木板,放在勒斯特和我当中。“你就睡在自己的一边。”迪尔西说,“勒斯特小,你不要压着了他。”
你还不能去,T.P.说。你等着。

我们在大房子的拐角上望着一辆辆马车驶走。
“快。”T.P.说。他抱起小昆丁,我们跑到栅栏的拐角上,瞧它们经过。“他走了。”T.P.说,“瞧见那辆有玻璃窗的了吗。好好瞧瞧。他就躺在那里面。你好好看看他。”
走吧,勒斯特说,
 我要把这只球带回家去,放在家里丢不了。不行,少爷,这可不能给你。要是那帮人看见你拿着球,他们会说你是偷来的。别哼哼了,好不好。不能给就是不能给。你拿去又有什么用呢。你又不会玩球。
我要把这只球带回家去,放在家里丢不了。不行,少爷,这可不能给你。要是那帮人看见你拿着球,他们会说你是偷来的。别哼哼了,好不好。不能给就是不能给。你拿去又有什么用呢。你又不会玩球。
弗洛尼和T.P.在门口泥地上玩。
 T.P.有一只瓶子,里面装着萤火虫。
T.P.有一只瓶子,里面装着萤火虫。
“你们怎么又全都出来了。”弗洛尼说。
“家里来了客人。”凯蒂说,“爸爸说今天晚上小孩子都听我的。我想你和T.P.也必须听我指挥。”
“我不听你的。”杰生说,“弗洛尼和T.P.也用不着听你的。”
“我说了要听他们就得听。”凯蒂说,“没准我还不打算叫他们听呢。”
“T.P.是谁的话都不听的。”弗洛尼说,“他们的丧礼开始了吗。”
“什么叫丧礼呀。”杰生说。
“妈咪不是叫你别告诉他们的吗。”威尔许说。
“丧礼就是大家哭哭啼啼。”弗洛尼说,“贝拉·克莱大姐
 死的时候,他们足足哭了两天呢。”
死的时候,他们足足哭了两天呢。”
他们在迪尔西的屋子里哭。
 迪尔西在哭。迪尔西哭的时候,勒斯特说,别响,于是我们都不出声,但后来我哭起来了,蓝毛
迪尔西在哭。迪尔西哭的时候,勒斯特说,别响,于是我们都不出声,但后来我哭起来了,蓝毛
 也在厨房台阶底下嗥叫起来了。后来迪尔西停住了哭,我们也不哭不叫了。
也在厨房台阶底下嗥叫起来了。后来迪尔西停住了哭,我们也不哭不叫了。
“噢。”凯蒂说,
 “那是黑人的事。白人是不举行丧礼的。”
“那是黑人的事。白人是不举行丧礼的。”
“妈咪叫我们别告诉他们的,弗洛尼。”威尔许说。
“别告诉他们什么呀。”凯蒂说。
迪尔西哭了,声音传了过来,我也哭起来了,蓝毛也在台阶底下嗥叫起来。
 勒斯特,弗洛尼在窗子里喊道,把他们带到牲口棚去。这么乱哄哄的我可做不成饭啦。还有那只臭狗。把他们全带走。
勒斯特,弗洛尼在窗子里喊道,把他们带到牲口棚去。这么乱哄哄的我可做不成饭啦。还有那只臭狗。把他们全带走。
我不去嘛,勒斯特说。没准会在那儿见到姥爷的。昨儿晚上我就见到他了,还在牲口棚里挥动着胳臂呢。
“我倒要问问为什么白人就不举行丧礼。”弗洛尼说,
 “白人也是要死的。你奶奶不就跟黑人一样死了吗。”
“白人也是要死的。你奶奶不就跟黑人一样死了吗。”
“狗才是会死的。”凯蒂说,“那回南茜掉在沟里,罗斯库司开枪把它打死了,后来好些老雕飞来,把它的皮都给撕碎了。”
骨头散落在小沟外面,阴森森的沟里有些黑黢黢的爬藤,爬藤伸到月光底下,像一些不动的死人。接着他们全都不动了,周围一片昏黑,等我睡醒重新睁开眼睛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听到急匆匆地走开去的脚步声,我闻到了那种气味。
 接着房间的样子显出来了,但我却闭上了眼睛。可是我并没有睡着。我闻到了那种气味。T.P.把我被子上扣的别针解开。
接着房间的样子显出来了,但我却闭上了眼睛。可是我并没有睡着。我闻到了那种气味。T.P.把我被子上扣的别针解开。
“别出声。”他说,“嘘——”
可是我闻出了那种气味。T.P.把我拖起来,急急忙忙地帮我穿好衣服。
“别出声,班吉。”他说,“咱们上我家的小屋去。你喜欢上咱们家去,是不,弗洛尼在那儿呢。别出声。嘘——”
他给我系上鞋带,把帽子扣在我头上,我们走出房间。楼梯口亮着一盏灯。从走廊那头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嘘——班吉。”T.P.说,“咱们马上就出去。”
有一扇门打开了,这时候那种气味更浓了,有一个脑袋从门里探出来。那不是父亲。父亲生病了,在里面躺着呢。
“你把他带到外面去好吗。”
“我们正是要到外面去呢。”T.P.说。迪尔西正在楼梯上走上来。
“别出声。”她说,“别出声。带他到咱们家去,T.P.。让弗洛尼给他铺好床。你们都好好照顾他。别出声,班吉。跟T.P.去吧。”
她上母亲发出声音的那个地方去了。
“最好让他待在那儿。”说话的人不是父亲。他关上了门,可是我仍然能闻到那种气味。
我们走下楼去。楼梯朝下通进黑黢黢的地方,T.P.拉着我的手,我们走出门口,进入外面的黑暗之中。丹儿坐在后院的地上,在嗥叫。
“它倒也闻出来了。”T.P.说,“你也是这样知道的吗。”
我们走下台阶,我们的影子落在台阶上。
“我忘了拿你的外衣了。”T.P.说,“你应该穿外衣的。可是我又不想回去拿。”
丹儿在嗥叫。
“你别哼哼了。”T.P.说。我们的影子在移动,可是丹儿的影子并不移动,不过它嗥叫时,那影子也跟着嗥叫。
“你这样嚷嚷,我可没法带你回家。”T.P.说,“你以前就够叫人讨厌的了,何况现在又换上了这副牛蛙一样的嗓子。走吧。”
我们拖着自己的影子,顺着砖砌的小道往前走。猪圈发出了猪的气味。那头母牛站在空地上,对着我们在咀嚼。丹儿又嗥叫了。
“你要把全镇都吵醒了。”T.P.说,“你就不能不喊吗。”
我们看见阿欢在河沟边吃草。我们走到沟边时月亮照在水面上。
“不行,少爷。”T.P.说,“这儿还太近。咱们不能在这儿停下来。走吧。好,你瞧你。整条腿都湿了。跨过来,上这边来。”丹儿又在嗥叫。
在沙沙响着的草丛里,那条小沟显现出来了。那些白骨散落在黑藤枝的四周。
“好了。”T.P.说,“你想吼你就只管吼吧。你前面是黑夜和二十英亩牧场,你吼得再响也不要紧。”
T.P.在小沟里躺下来,我坐了下来,打量着那些白骨,以前那些老雕就是在这儿啄食南茜的,后来慢腾腾、沉甸甸地拍打着黑黑的翅膀,从沟里飞出来。
我们早先上这儿来的时候,它还在我身上呢,勒斯特说。
 我拿出来给你看过的。你不是也看见的吗。我就是站在这儿从兜里掏出来给你看的。
我拿出来给你看过的。你不是也看见的吗。我就是站在这儿从兜里掏出来给你看的。
“你以为老雕会把大姆娣的皮撕碎吗。”凯蒂说,
 “你疯了。”
“你疯了。”
“你是大坏蛋。”杰生说。他哭起来了。
“你才是个大浑球呢。”凯蒂说。杰生哭着。他两只手插在兜里。
“杰生长大了准是个大财主。”威尔许说,“他什么时候都攥紧了钱不松手。”
杰生哭着。
“瞧你又弄得他哭起来没个完了。”凯蒂说,“别哭了,杰生。老雕又怎么能飞到大姆娣的房间里去呢。爸爸才不会让它们去呢。你会让老雕来给你脱衣服吗。好了,别哭了。”
杰生收住了哭声。“弗洛尼说那是丧礼。”他说。
“谁说的,不是的。”凯蒂说,“是在举行舞会。弗洛尼知道个屁。他想要你的萤火虫呢,T.P.。给他拿一会儿吧。”
T.P.把那只装着萤火虫的瓶子递给我。
“我说。要是咱们绕到客厅窗子底下去,咱们肯定能瞧见点什么的。”凯蒂说,“到时候你们就会信我的话了。”
“我已经知道了。”弗洛尼说,“我用不着去看了。”
“你快别说了,弗洛尼。”威尔许说,“妈咪真的要抽你的。”
“那你说是什么。”凯蒂说。
“反正我知道。”弗洛尼说。
“来吧。”凯蒂说,“咱们绕到屋子前面去。”
我们动身走了。
“T.P.要他的萤火虫了。”弗洛尼说。
“让他再拿一会儿怕什么,T.P.。”凯蒂说,“我们会还给你的。”
“你们自己从来不逮萤火虫。”弗洛尼说。
“要是我让你和T.P.也去,你让他拿着不。”凯蒂说。
“没人关照过我和T.P.也得听你的指挥。”弗洛尼说。
“要是我说你们可以不听,那你让他拿着不?”凯蒂说。
“那也行。”弗洛尼说,“让他拿着吧,T.P.。我们去看看他们是怎样哭哭啼啼的。”
“他们不会哭哭啼啼的。”凯蒂说,“我跟你们说了是在举行舞会。他们是在哭哭啼啼吗。威尔许。”
“我们老站在这儿,怎么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呢。”威尔许说。
“走吧。”凯蒂说,“弗洛尼和T.P.可以不用听我的指挥。其他的人可都得听。你还是把他抱起来吧,威尔许。天擦擦黑了。”
威尔许抱起了我,我们绕过了厨房的拐角。
我们从屋子拐角朝外看,可以看到马车的灯光从车道上照射过来。
 T.P.拐回到地窖门口,打开了门。
T.P.拐回到地窖门口,打开了门。
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吗,T.P.说。有苏打水。我见到过杰生先生两手抱满了从下面走出来。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T.P.走过去朝厨房门里张望了一下。迪尔西说,你鬼头鬼脑地偷看什么。班吉在哪儿呢。
他就在外面,T.P.说。
去看着他吧,迪尔西说。只是别让他进大宅子。
好咧,您哪,T.P.说。他们开始了吗。
你快去看好那孩子,别让他进来,迪尔西说。我手上的活忙不过来哪。
一条蛇从屋子底下爬了出来。
 杰生说他不怕蛇,凯蒂说他肯定怕,她倒是不怕,威尔许又说,他们俩都怕,凯蒂就说都给我住嘴,她的口气很像父亲。
杰生说他不怕蛇,凯蒂说他肯定怕,她倒是不怕,威尔许又说,他们俩都怕,凯蒂就说都给我住嘴,她的口气很像父亲。
你现在可不能嚷起来呀,T.P.说。
 你要来点儿这种沙示水吗。
你要来点儿这种沙示水吗。
这东西冲得我的鼻子和眼睛直痒痒。
你要是不想喝,就给我喝好了,T.P.说。行了,拿到了。趁现在没人管我们,我们不如再拿它一瓶吧。你可别出声啊。
我们在客厅窗子外面那棵树底下停住脚步。
 威尔许把我放下,让我站在湿湿的草地上。这个地方很冷。所有的窗户里都亮着灯光。
威尔许把我放下,让我站在湿湿的草地上。这个地方很冷。所有的窗户里都亮着灯光。
“大姆娣就在那一间里面。”凯蒂说,“她现在每天每天都生病。等她病好了,我们就可以出去野餐了。”
“反正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弗洛尼说。
树在沙沙地响,草也在沙沙地响。
“再过去那间就是咱们出麻疹时候睡的地方。”凯蒂说,“你和T.P.是在什么地方出麻疹的呢,弗洛尼。”
“也就在我们天天睡觉的地方吧,我想。”弗洛尼说。
“他们还没有开始呢。”凯蒂说。
他们马上就要开始了,T.P.说。
 你先站在这儿,让我去把那只板条箱搬过来,这样我们就能看见窗子里的事了。来,咱们把这瓶沙示水喝了吧。喝了下去,我肚子里就像有只夜猫子在咕咕直叫似的。
你先站在这儿,让我去把那只板条箱搬过来,这样我们就能看见窗子里的事了。来,咱们把这瓶沙示水喝了吧。喝了下去,我肚子里就像有只夜猫子在咕咕直叫似的。
我们喝完沙示水,T.P.把空瓶子朝花铁格子里推,推到屋子底下去,接着就走开了。我听得到他们在客厅里发出的声音,我用双手攀住了墙。T.P.在把一只木箱朝我这儿拖来。他跌倒了,就大笑起来。他躺在地上,对着草丛哈哈大笑。他爬起来,把木箱拖到窗子底下,他使劲憋住不笑。
“我怕自己会大嚷大叫起来。”T.P.说,“你站到木箱上去,看看他们开始没有。”
“他们还没有开始,因为乐队还没来呢。”凯蒂说。

“他们根本不会要乐队的。”弗洛尼说。
“你怎么知道的。”凯蒂说。
“我自然知道啦。”弗洛尼说。
“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凯蒂说。她走到树前。“推我上去,威尔许。”
“你爹关照过叫你别爬树的。”威尔许说。
“那是好久以前了。”凯蒂说,“我想连他自己都忘掉了。而且,他关照过今天晚上由我指挥的。他不是说过由我指挥的吗。”
“我不听你指挥。”杰生说,“弗洛尼和T.P.也不听。”
“把我推上去,威尔许。”凯蒂说。
“好吧。”威尔许说,“以后挨鞭子的可得是你啊。跟我可没关系。”他走过去把凯蒂推到第一个丫杈上去。我们都望着她衬裤上的那摊泥迹。接着我们看不见她了。我们能听见树的抖动声。
“杰生先生说过,你要是折断了这棵树的枝条,他可是要抽你的。”威尔许说。
“我也要告发她。”杰生说。
那棵树不再抖动了。我们抬头朝一动不动的枝条上望去。
“你瞧见什么啦。”弗洛尼悄声说。
我瞧见他们了。
 接着我瞧见凯蒂,头发上插着花儿,披着条长长的白纱,像闪闪发亮的风儿。凯蒂凯蒂
接着我瞧见凯蒂,头发上插着花儿,披着条长长的白纱,像闪闪发亮的风儿。凯蒂凯蒂
“别出声。”T.P.说。“他们会听见你的。快点下来。”他把我往下拉。凯蒂。我双手攀住了墙。凯蒂。T.P.把我往下拉。“别出声。”他说。“别出声。快上这儿来。”他使劲拉着我朝前走。凯蒂。“快别出声,班吉。你想让他们听见你吗。来吧,咱们再去喝一点沙示水,然后再回来瞧,只要你不吵吵。咱们最好再喝它一瓶。不然的话咱们俩都会大叫大嚷的。咱们可以说是丹儿喝的。昆丁先生老说这条狗多么聪明,咱们也可以说它是一条爱喝沙示水的狗的。”
月光爬到了地窖的台阶上。我们又喝了一些沙示水。
“你知道我希望什么吗。”T.P.说,“我希望有一只熊从这地窖的门口走进来。你知道我要怎么干吗。我要笔直地走过去朝它眼睛里啐上一口唾沫。快把瓶子给我,让我把嘴堵上,不然的话我真的要嚷出来了。”
T.P.倒了下去。他笑了,地窖的门和月光都跳了开去,不知什么东西打了我一下。
“快别嚷嚷。”T.P.说,他想忍住不笑。“天哪,他们都要听见我们的声音了。起来。”T.P.说。“起来呀,班吉,快点儿。”他浑身乱打哆嗦,笑个不停,我挣扎着想爬起来。在月光下,地窖的台阶直升到小山冈上,T.P.在山坡上倒下来,倒在月光里,我跑出去一头撞在栅栏上,T.P.在我后面追,一面喊着“别出声,别出声”。接着他哈哈大笑地跌进了花丛,我跑着一头撞在木箱上。可是我正使劲往木箱上爬的时候,木箱跳了开去,打着了我的后脑勺,我嗓子里发出了一声喊叫。接着又发出了一声,我就干脆不爬起来了,它又发出了一声喊叫,于是我哭起来了。T.P.来拉我,我嗓子里不断地发出声音。它不断地发出声音,我都搞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哭了,这时T.P.倒下来,压在我的身上,他哈哈大笑,我的嗓子不断发出声音,这时昆丁用脚踢T.P.,凯蒂伸出胳膊来搂住我,她那闪闪发亮的披纱也缠在我的身上,我一点也闻不到树的香味,于是我就哭起来了。
班吉,凯蒂说,班吉。
 她又伸出胳膊来搂住我,可是我躲了开去。
“你怎么啦,班吉。”她说。“是不喜欢这顶帽子吗。”她脱掉帽子,又凑了过来,可是我躲开了。
她又伸出胳膊来搂住我,可是我躲了开去。
“你怎么啦,班吉。”她说。“是不喜欢这顶帽子吗。”她脱掉帽子,又凑了过来,可是我躲开了。
“班吉。”她说,“怎么回事啊,班吉。凯蒂干了什么啦。”
“他不喜欢你那身臭美的打扮。”杰生说,“你自以为已经长大了,是吗。你自以为比谁都了不起,是吗。臭美。”
“你给我闭嘴。”凯蒂说,“你这坏透了的小浑蛋。班吉。”
“就因为你十四岁了,你就自以为已经是个大人了,是吗。”杰生说,“你自以为很了不起。是吗。”
“别哭了,班吉。”凯蒂说,“你会吵醒妈妈的。别哭了。”
可是我还是又哭又闹,她走开去,我跟着她,她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等我,我也停住了脚步。
“你到底要什么呀,班吉。”凯蒂说,“告诉凯蒂吧。她会给你办到的。你说呀。”
“凯丹斯。”母亲说。
“哎,妈。”凯蒂说。
“你干吗惹他。”母亲说,“把他带进来。”
我们走进母亲的房间,她病了,躺在床上,脑门上盖着一块布。
“又是怎么回事啊。”母亲说,“班吉明。”
“班吉。”凯蒂说。她又凑过来,可是我又躲开了。
“你准是欺侮他了。”母亲说,“你就不能不惹他,让我清静一会儿吗。你把盒子给他,完了就请你走开,让他一个人玩会儿。”
凯蒂把盒子拿来,放在地板上,她打开盒子。里面都是星星。我不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动。我一动,它们乱打哆嗦,闪闪发光,我不哭了。
这时我听见凯蒂走开去的声音,我又哭了。
“班吉明。”母亲说,“过来呀。”我走到房门口。“叫你呢,班吉明。”母亲说。
“这又怎么啦。”父亲说,“你要上哪儿去呀。”
“把他带到楼下去,找个人管着他点儿,杰生。”母亲说,“你明知我病了,偏偏这样。”
我们走出房间,父亲随手把门关上。
“T.P.。”他说。
“老爷。”T.P.在楼下答应道。
“班吉下楼来了。”父亲说,“你跟T.P.去吧。”
我走到洗澡间门口。我听得见流水的哗哗声。
“班吉。”T.P.在楼下说。
我听得见流水的哗哗声。我用心地听着。
“班吉。”T.P.在楼下说。
我听着流水声。
我听不见那哗哗声了,接着,凯蒂打开了门。
“你在这儿啊,班吉。”她说。她瞧着我,我迎上去,她用胳膊搂住我。“你又找到凯蒂了,是吗。”她说。“你难道以为凯蒂逃掉了吗。”凯蒂又像树一样香了。
我们走进凯蒂的房间。她在镜子前坐了下来。她停住了手里的动作,盯着我看。
“怎么啦,班吉。是怎么回事啊。”她说。“你千万别哭。凯蒂不走。你瞧这个。”她说。她拿起一只瓶子,拔掉塞子,把瓶子伸过来放在我鼻子底下。“香的。闻呀。好闻吧。”
我躲开了,我的哭声没有停下来,她手里拿着那只瓶子,瞅着我。
“噢。”她说。她把瓶子放下,走过来搂住我。“原来是为了这个呀。你想跟凯蒂说,可你说不出来。你想说,可又说不出,是吗。当然,凯蒂不再用了。你等着,让我穿好衣服。”
凯蒂穿好衣服,重新拿起瓶子,我们就下楼走进厨房。
“迪尔西。”凯蒂说。“班吉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她弯下身子,把瓶子放在我的手里。“好,你现在给迪尔西吧。”凯蒂把我的手伸出去,迪尔西接过瓶子。
“噢,真了不起。”迪尔西说,“我的好宝贝儿居然送给迪尔西一瓶香水。你倒是瞧呀,罗斯库司。”
凯蒂身上像树那样香。“我们自己不爱用香水。”凯蒂说。
她像树那样香。
“好了,来吧。”迪尔西说。
 “你太大了,不应该再跟别人一块儿睡了。你现在是个大孩子了。都十三岁了。你够大的了,应该到毛莱舅舅房里去一个人睡了。”迪尔西说。
“你太大了,不应该再跟别人一块儿睡了。你现在是个大孩子了。都十三岁了。你够大的了,应该到毛莱舅舅房里去一个人睡了。”迪尔西说。
毛莱舅舅病了。他的眼睛病了,他的嘴也病了。
 威尔许用托盘把他的晚饭送到楼上他的房间里去。
威尔许用托盘把他的晚饭送到楼上他的房间里去。
“毛莱说他要用枪打死那个流氓。”父亲说。“我告诉他,他若是真的要干,最好事先别在帕特生面前提这件事。”父亲喝了一口酒。
“杰生。”母亲说。
“开枪打谁呀,爸爸。”昆丁说,“毛莱舅舅干吗要开枪打他呀。”
“因为人家跟他开个小小的玩笑他就受不了。”父亲说。
“杰生。”母亲说,“你怎么能这样说。你会眼看毛莱受伏击挨枪,却坐在那儿冷笑。”
“要是毛莱不让自己落到让人伏击的地步,那不更好吗。”父亲说。
“开枪打谁呀,父亲。”昆丁说,“毛莱舅舅要打谁呀。”
“不打谁。”父亲说,“我这儿连一支手枪都没有。”
母亲哭起来了。“要是你嫌毛莱白吃你的饭,你干吗不拿出点男子汉气概来,当面去跟他说呢。何必背着他在孩子们面前讥笑他呢。”
“我当然不嫌弃他。”父亲说,“我喜欢他还来不及呢。他对我的种族优越感来说是个极有价值的例证。别人若是拿一对好马来跟我换毛莱,我还不干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昆丁。”
“不知道,父亲。”昆丁说。
“Et ego in Arcadia
 ,还有干草在拉丁语里该怎么说我可忘了。”父亲说。“没什么,没什么。”他说。“我不过是在开玩笑罢了。”他喝了一口酒,把玻璃杯放下,走过去把手放在母亲的肩上。
,还有干草在拉丁语里该怎么说我可忘了。”父亲说。“没什么,没什么。”他说。“我不过是在开玩笑罢了。”他喝了一口酒,把玻璃杯放下,走过去把手放在母亲的肩上。
“这不是在开玩笑。”母亲说,“我娘家的人出身跟你们家完全是同样高贵的。只不过毛莱的健康状况不大好就是了。”
“当然啦。”父亲说,“健康欠佳诚然是所有人的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痛苦中诞生,在疾病中长大,在腐朽中死去。威尔许。”
“老爷。”威尔许在我椅子背后说。
“把这细颈玻璃瓶拿去,给我把酒斟满。”
“再去叫迪尔西来,让她带班吉明上床去睡觉。”母亲说。
“你是个大孩子了。”迪尔西说,
 “凯蒂已经不爱跟你睡一张床了。好了,别吵了,快点睡吧。”房间看不见了,可是我没有停住哭喊,接着房间又显现出来了,迪尔西走回来坐在床边,看着我。
“凯蒂已经不爱跟你睡一张床了。好了,别吵了,快点睡吧。”房间看不见了,可是我没有停住哭喊,接着房间又显现出来了,迪尔西走回来坐在床边,看着我。
“你做一个乖孩子,不要吵闹,好不好。”迪尔西说,“你不肯,是不是。那你等我一会儿。”
她走开去了。门洞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接着,凯蒂出现了。
“别哭啦。”凯蒂说,“我来了。”
我收住了声音,迪尔西把被单掀开,凯蒂钻到被单和毯子当中去。她没有脱掉睡袍。
“好啦。”她说。“我这不是来了嘛。”迪尔西拿来一条毯子,盖在她身上,又给她掖好。
“他一会儿就会睡着的。”迪尔西说,“你房间里的灯我让它亮着。”
“好的。”凯蒂说。她把头挤到枕头上我的脑袋旁边来。“晚安,迪尔西。”
“晚安,宝贝儿。”迪尔西说。房间变黑了。 凯蒂身上有树的香味。
我们抬起头,朝她待着的树上望去。

“她瞧见什么啦,威尔许。”弗洛尼悄没声儿地说。
“嘘——”凯蒂在树上说。这时迪尔西说了,
“原来你们在这儿。”她绕过屋角走过来,“你们干吗不听你们爸爸的话,上楼去睡觉,偏偏要瞒着我溜出来。凯蒂和昆丁在哪儿。”
“我跟她说过不要爬那棵树的嘛。”杰生说,“我要去告发她。”
“谁在那棵树上。”迪尔西说。她走过来朝树上张望。“凯蒂。”迪尔西说。树枝又重新摇晃起来。
“是你啊,小魔鬼。”迪尔西说,“快给我下来。”
“嘘。”凯蒂说。“你不知道父亲说了要安静吗。”她的双腿出现了,迪尔西伸出手去把她从树上抱了下来。
“你怎么这样没脑子,让他们到这儿来玩呢。”迪尔西说。
“我可管不了她。”威尔许说。
“你们都在这儿干什么。”迪尔西说,“谁叫你们到屋子前面来的。”
“是她。”弗洛尼说,“她叫我们来的。”
“谁告诉你们她怎么说你们就得怎么听的。”迪尔西说。“快给我回家去。”弗洛尼和T.P.走开去了。他们刚走没几步我们就看不见他们了。
“深更半夜还跑到这儿来。”迪尔西说。她把我抱起来,我们朝厨房走去。
“瞒着我溜出来玩。”迪尔西说,“你们明明知道已经过了你们该睡觉的时候。”
“嘘——迪尔西。”凯蒂说,“说话别这么粗声大气。咱们得安静。”
“你先给我闭上嘴安静安静。”迪尔西说,“昆丁在哪儿。”
“昆丁气死了,因为今天晚上他得听我指挥。”凯蒂说,“他还拿着T.P.的萤火虫瓶子呢。”
“我看T.P.没这只瓶子也不打紧。”迪尔西说,“威尔许,你去找找昆丁。罗斯库司说看见他朝牲口棚那边走去了。”威尔许走开了。我们看不见他了。
“他们在里面也没干什么。”凯蒂说,“光是坐在椅子里你瞧着我,我瞧着你。”
“他们做这样的事是不用你们这些小家伙帮忙的。”迪尔西说。我们绕到厨房后面。
你现在又要去哪儿呢,勒斯特说。
 你又想回那边去瞧他们打球吗。我们已经在那边找过了。对了。你等一会儿。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回去拿那只球。我有主意了。
你又想回那边去瞧他们打球吗。我们已经在那边找过了。对了。你等一会儿。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回去拿那只球。我有主意了。
厨房里很黑。
 衬着天空的那些树也很黑。丹儿摇摇摆摆地从台阶下面走出来,啃了啃我的脚脖子。我绕到厨房后面,那儿有月亮。丹儿拖着步子跟过来,来到月光下。
衬着天空的那些树也很黑。丹儿摇摇摆摆地从台阶下面走出来,啃了啃我的脚脖子。我绕到厨房后面,那儿有月亮。丹儿拖着步子跟过来,来到月光下。
“班吉。”T.P.在屋子里说。
客厅窗子下面那棵开花的树并不黑,但那些浓密的树是黑的。我的影子在草上滑过,月光底下的草发出了沙沙声。
“喂,班吉。”T.P.在屋子里说,“你藏在哪儿。你溜出去了。我知道的。”
勒斯特回来了。
 等一等,他说。上这边来。别到那边去。昆丁小姐和她的男朋友在那儿的秋千架上呢。你从这边走。回来呀,班吉。
等一等,他说。上这边来。别到那边去。昆丁小姐和她的男朋友在那儿的秋千架上呢。你从这边走。回来呀,班吉。
树底下很黑。
 丹儿不愿过来。它留在月光底下。这时我看见了那架秋千,我哭起来了。
丹儿不愿过来。它留在月光底下。这时我看见了那架秋千,我哭起来了。
快打那边回来,班吉,勒斯特说。
 你知道昆丁小姐要发火的。这时秋千架上有两个人,接着只有一个了。
你知道昆丁小姐要发火的。这时秋千架上有两个人,接着只有一个了。
 凯蒂急急地走过来,在黑暗中是白蒙蒙的一片。
凯蒂急急地走过来,在黑暗中是白蒙蒙的一片。
“班吉。”她说,“你怎么溜出来的,威尔许在哪儿。”
她用胳膊搂住我,我不吱声了,我拽住她的衣服,想把她拉走。
“怎么啦,班吉。”她说。“这是怎么回事。T.P.。”她喊道。
坐在秋千架上的那人站起来走了过来,我哭着,使劲拽凯蒂的衣服。
“班吉。”凯蒂说,“那不过是查利呀。你不认得查利吗。”
“看管他的那个黑小子呢。”查利说,“他们干吗让他到处乱跑。”
“别哭,班吉。”凯蒂说,“你走开,查利。他不喜欢你。”查利走开去了,我收住了哭声。我拉着凯蒂的衣裙。
“怎么啦,班吉。”凯蒂说,“你就不让我待在这儿跟查利说几句话吗。”
“把那黑小子叫来。”查利说。他又走过来了。我哭得更响了,使劲拉住凯蒂的衣裙。
“你走开,查利。”凯蒂说。查利过来把两只手放在凯蒂身上,于是我哭得更厉害了。我的哭声更响了。
“别,别。”凯蒂说,“别。别这样。”
“他又不会说话。”查利说,“凯蒂。”
“你疯了吗。”凯蒂说。她呼吸急促起来了。“他看得见的。别这样。别这样嘛。”凯蒂挣扎着。他们两人呼吸都急促起来了。“求求你。求求你。”凯蒂悄声说。
“把他支开去。”查利说。
“我会的。”凯蒂说,“你放开我。”
“你把不把他支开。”查利说。
“我会的。”凯蒂说。“你放开我。”查利走开去了。“别哭。”凯蒂说。“他走了。”我停住了哭声。我听得见她的呼吸,感到她的胸脯在一起一伏。
“我得先把他送回家去。”她说。她拉住我的手。“我就回来。”她悄声说。
“等一等。”查利说,“叫黑小子来。”
“不。”凯蒂说,“我就回来。走吧,班吉。”
“凯蒂。”查利悄声说,气儿出得很粗。我们继续往前走。“你还是回来吧。你回来不回来。”凯蒂和我在小跑了。“凯蒂。”查利说。我们跑到月光里,朝厨房跑去。
“凯蒂。”查利说。
凯蒂和我跑着。我们跑上厨房台阶,来到后廊上,凯蒂在黑暗中跪了下来,搂住了我。我能听见她的出气声,能感到她胸脯的起伏。“我不会了。”她说。“我永远也不会再那样了。班吉。班吉。”接着她哭起来了,我也哭了,我们两人抱在一起。“别哭了。”她说。“别哭了。我不会再那样了。”于是我收住哭声,凯蒂站起身来,我们走进厨房,开亮了灯,凯蒂拿了厨房里的肥皂到水池边使劲搓洗她的嘴。凯蒂像树一样的香。
我没一遍遍地关照你别上那边去吗,勒斯特说。
 他们急匆匆地在秋千座上坐起来。昆丁伸出双手去理头发。那个男的系着一条红领带。
他们急匆匆地在秋千座上坐起来。昆丁伸出双手去理头发。那个男的系着一条红领带。
你这疯傻子,昆丁说。我要告诉迪尔西,你让他到处跟踪我。我要叫她狠狠地抽你一大顿。
“我也管不住他呀。”勒斯特说,“回这儿来,班吉。”
“不,你是管得住的。”昆丁说。“你只是不想管就是了。你们俩都鬼头鬼脑地来刺探我的行动。是不是外婆派你们上这儿来监视我的。”她从秋千架上跳下来。“如果你不马上把他带走,再也不让他回来,我可要叫杰生用鞭子抽你了。”
“我真的管不住他。”勒斯特说,“你以为管得住你倒试试看。”
“你给我闭嘴。”昆丁说,“你到底把不把他带走。”
“唉,让他待在这儿吧。”那个男的说。他打着一条红领带。太阳晒在那上面红艳艳的。“你瞧这个,杰克
 。”他划亮了一根火柴,放进自己嘴里。接着又把火柴取出来。火柴仍然亮着。“你想试一试吗。”他说。我走了过去。“你张大嘴。”他说。我把嘴张大。昆丁一扬手,把火柴打飞了。
。”他划亮了一根火柴,放进自己嘴里。接着又把火柴取出来。火柴仍然亮着。“你想试一试吗。”他说。我走了过去。“你张大嘴。”他说。我把嘴张大。昆丁一扬手,把火柴打飞了。
“你真浑。”昆丁说,“你想惹他哭吗。你不知道他会吼上一整天的吗。我要去跟迪尔西说你不好好管班吉。”她跑开去了。
“回来,小妞。”他说,“嗨。快回来呀。我不捉弄他就是了。”
昆丁朝大宅子跑去。她已经绕过厨房了。
“你在捣乱,杰克。”他说,“是不是这样啊。”
“他听不懂你的话。”勒斯特说,“他又聋又哑。”
“是吗?”他说,“他这样子有多久啦。”
“到今天正好是三十三年。”勒斯特说,“生下来就是傻子。你是戏班子里的人吗。”
“怎么啦。”他说。
“我好像以前没有见过你。”勒斯特说。
“嗯,那又怎么样。”他说。
“没什么。”勒斯特说,“我今儿晚上要去看演出。”
他瞧了瞧我。
“你不是拉锯奏出曲子来的那个人吧,是不是。”勒斯特说。
“花两毛五买一张门票,你就知道了。”他说。他瞧了瞧我。“他们干吗不把他关起来。”他说,“你把他领到外面来干什么。”
“你这话不要跟我说。”勒斯特说,“我是一点儿也管不着他的。我不过是来找丢掉的一只镚子儿的,找到了今天晚上才能去看演出。看样子我是去不成的了。”勒斯特在地上找着。“你身上没有多余的镚子儿吧,是吗。”勒斯特说。
“没有。”他说,“我可没有。”
“那我看我只好想法找到那只镚子儿了。”勒斯特说。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兜里。“你也不想买只高尔夫球吧,是吗。”勒斯特说。
“什么样的球。”他说。
“高尔夫球。”勒斯特说,“我多了不要,只要两角五分。”
“有啥用呢。”他说,“我要它有什么用。”
“我琢磨你也不会要的。”勒斯特说。“咱们走吧,蠢驴。”他说,“上这边来瞧他们打球吧。拿去。给你这个,你可以拿来跟吉姆生草一起玩。”勒斯特把那东西捡了起来,递给了我。那东西亮光光的。
“你在哪儿找到的。”他说。他那根在太阳光底下红艳艳的领带一点点地挨近我们。
“就在这丛矮树底下找到的。”勒斯特说,“我一时之间还以为是我丢失的那只镚子儿呢。”
他走过来把那东西拿过去。
“别叫。”勒斯特说,“他看完就会还给你的。”
“艾格尼斯、梅比尔、贝基。
 ”他说,眼睛朝大房子那边看去。
”他说,眼睛朝大房子那边看去。
“别嚷嚷。”勒斯特说,“他肯定会还给你的。”
他把那东西给我,我就不叫了。
“昨儿晚上什么人来看过她。”他说。
“我可不知道。”勒斯特说,“每天晚上都有人来,她可以从那棵树上爬下来的。我可不爱打听别人的秘密。”
“他们当中的一个倒是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了。”他说,他朝大房子看去。接着他走开去,在秋千座上躺了下来。“走吧。”他说,“别来跟我捣乱了。”
“快走吧。”勒斯特说,“你闯祸了。昆丁小姐肯定已经在迪尔西面前告过你的状了。”
我们来到栅栏边,透过盘绕的花枝朝外面张望。勒斯特在草丛里找东西。
“我在这儿的时候钱还在身上呢。”他说。我看见那面小旗在扑闪,太阳斜斜地落在宽阔的草地上。
“一会儿她们就会来的。”勒斯特说,“来过几个了,可是又走了。你过来帮我找呀。”
我们沿着栅栏往前走。
“别闹了。”勒斯特说,“她们不来,我又有什么法子让她们来呢。等一会儿。过一分钟就会来的。瞧那边。可不是来了吗。”
我顺着栅栏一直走到大铁门那儿,背书包的姑娘们总打这儿经过。“喂,班吉。”勒斯特说,“你回这边来呀。”
你从大门里往外瞧有什么用啊,T.P.说。
 凯蒂小姐早就不知上哪儿去了。嫁了人了,离开你了。你拽着门哭哭喊喊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她可听不见你。
凯蒂小姐早就不知上哪儿去了。嫁了人了,离开你了。你拽着门哭哭喊喊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她可听不见你。
他想要什么呀,T.P.,母亲说。你就不能陪他玩让他安静些吗。
他想到门口去看大门外面,T.P.说。
哦,那可不行,母亲说。在下雨呢。你只有好好陪他玩,让他不要吵。你乖点儿,班吉明。
根本没法儿让他安静,T.P.说。他以为只要他到大门口去,凯蒂小姐就会回来的。
胡说八道,母亲说。
我听见她们在说话。我走出屋门,就听不见了,我一直走到大铁门,姑娘们背着书包打这儿走过去。她们看了看我,把头扭开去,走得更快了。我想说话,可是她们只管往前走,我就沿着栅栏跟着她们,想说话,可是她们走得更快了。接着她们跑起来了,我走到栅栏拐弯处,没法往前走了。我拽住栅栏,眼看她们走远,我想说话。
“你呀,班吉。”T.P.说,“你溜了出来想干什么。你不知道迪尔西会抽你一顿的吗。”
“你这样做有什么用,隔着栅栏朝她们哼哼唧唧,嘟嘟哝哝。”T.P.说,“你把这些小女孩都吓坏了。你瞧瞧,她们都打马路对面走了。”
他怎么出去的,父亲说。
 你进院子时没插上门吧,杰生。
你进院子时没插上门吧,杰生。
怎么会呢,杰生说。我怎么会这么马虎呢。您以为我愿意出这样的事吗。咱们家的名声已经够糟糕的了,老天爷呀。这话我早就该跟您说了。我看这一来您总该把他送到杰克逊去了吧。要不柏吉斯太太真要开枪打死他了。
别说了,父亲说。
这话我早就该跟您说了,杰生说。
我手碰上大铁门,它是开着的,我就在暮色里拽住了门。
 我没有喊,我使劲不让自己哭,看着小姑娘们在暮色里走过来。我没有喊。
我没有喊,我使劲不让自己哭,看着小姑娘们在暮色里走过来。我没有喊。
“他在那儿呢。”
她们停住了脚步。
“他走不出来。反正他是不会伤害人的。走过去吧。”
“我不敢走过去。我不敢。我想到马路对面去。”
“他出不来的。”
我没有喊。
“别像一只胆小的猫儿似的。走过去呀。”
她们在暮色里朝前走。我没有喊,我拽紧了门。她们走得很慢。
“我害怕。”
“他不会伤害你的。我每天都打这儿走。他光是顺着栅栏跟着走。”
她们走过来了。我拉开铁门,她们停了步,把身子转过来。我想说话,我一把抓住了她,想说话,可是她尖声大叫起来,我一个劲儿地想说话想说话,
 这时明亮的形影开始看不清了,我想爬出来。我想把它从面前拂走,可是那些明亮的形影又看不清了。她们朝山上走去,朝山坡往下落的地方走去,我想喊她们。可是我吸进了气,却吐不出气,发不出声音,我一心想不让自己掉到山下去,却偏偏从山上摔下来,落进明亮的、打着旋的形影中去。
这时明亮的形影开始看不清了,我想爬出来。我想把它从面前拂走,可是那些明亮的形影又看不清了。她们朝山上走去,朝山坡往下落的地方走去,我想喊她们。可是我吸进了气,却吐不出气,发不出声音,我一心想不让自己掉到山下去,却偏偏从山上摔下来,落进明亮的、打着旋的形影中去。
喂,傻子,勒斯特说。
 来了几个人了。快别嘟嘟哝哝、哼哼唧唧的了,听见没有。
来了几个人了。快别嘟嘟哝哝、哼哼唧唧的了,听见没有。
他们来到小旗旁边。有一个把小旗拔出来,他们打了球,接着他又把小旗插回去。
“先生。”勒斯特说。
他回过头来。“什么事。”他说。
“您要买高尔夫球不。”勒斯特说。
“给我看看。”他说。他走到栅栏前,勒斯特的手穿过栅栏把球递了过去。
“你从哪儿得来的。”他说。
“捡到的。”勒斯特说。
“我可知道是怎么来的。”他说,“从哪儿来的。从别人的高尔夫球袋里。”
“我是在这儿院子里找到的。”勒斯特说,“给我两毛五分就让给你。”
“你凭什么说这球是你的。”他说。
“是我捡到的嘛。”勒斯特说。
“那你再去捡一个吧。”他说。他把球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就走开了。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去看演出呀。”勒斯特说。
“是吗。”他说。他走到台地上。“让开,开弟
 。”他说。他打了一下球。
。”他说。他打了一下球。
“你这人真是。”勒斯特说。“你没看见他们的时候瞎吵吵,等到看见了,你又瞎吵吵。你就不能住嘴吗。你不明白别人老听到你瞎吵吵会讨厌的吗。拿去。你的吉姆生草丢了。”他把草捡起来,还给了我。“得再给你摘一枝了。这一枝已经快给你弄蔫儿了。”我们站在栅栏前看着他们。
“那个白人可不好对付啊。”勒斯特说。“你看见他把我的球抢去了吧。”他们朝前走。我们也顺着栅栏朝前走。我们来到花园里,再也走不过去了。我拽住了栅栏,从花枝间看过去。他们不见了。
“现在你没什么可哼哼唧唧的了吧。”勒斯特说,“快别吱声了。该唉声叹气的是我,而不是你。拿去。你干吗不拿好你的草呢。一会儿又要因为没了它大哭大闹了。”他把一枝花给我,“你又往哪儿跑。”
我们的影子落在草地上。影子比我们先碰到树。我的影子第一个到。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到了,然后影子又离开了树。瓶子里有一枝花。我把另外一枝也插进去。
“你早就是个大人了。”勒斯特说,“还玩这种往瓶子插两枝草的游戏。你知道卡罗琳小姐一死他们会把你怎么样吗。他们要把你送到杰克逊去,那儿本来就是你该待的地方。杰生先生这样说的。到了那边,你就能跟一大帮傻子白痴待在一起,整天拽着铁栅栏不放,爱怎么哼哼就怎么哼哼了。怎么样,你喜欢过这种日子吗。”
勒斯特一挥手把花儿打飞了。“在杰克逊,只要你一叫唤,他们就这样对付你。”
我想把花儿捡起来。勒斯特先捡走了,花儿不知到哪儿去了。我哭了起来。
“哭呀。”勒斯特说,“你倒是哭呀。你得有个因头哭。好吧,给你个因头。凯蒂。”他悄声说,“凯蒂。你哭呀。凯蒂。”
“勒斯特。”迪尔西在厨房里喊道。
花儿又回来了。
“快别哭。”勒斯特说,“哪,这不是吗。瞧。这不是跟方才一样,好好地在瓶子里吗。行了,别哭了。”
“嗨,勒斯特。”迪尔西说。
“嗳,您哪。”勒斯特说,“我们来了。你太捣乱了。起来。”他扯了扯我的胳膊,我爬了起来。我们走出树丛。我们的影子不见了。
“别哭了。”勒斯特说,“瞧,大家都在看你了。别哭了。”
“你把他带过来。”迪尔西说。她走下台阶。
“你又把他怎么的啦。”她说。
“一点也没招惹他呀。”勒斯特说,“他无缘无故就哭喊起来了。”
“你就是招惹他了。”迪尔西说,“你准是欺侮他了。你们刚才在哪儿。”
“就在那边的那些雪松下面。”勒斯特说。
“你把小昆丁都惹火了。”迪尔西说,“你就不能把他带开去,离她远点儿吗。你不知道她不喜欢班吉在她左右吗。”
“我为他花了多少时间。”勒斯特说,“他又不是我的舅舅。”
“你敢跟我顶嘴,臭小子。”迪尔西说。
“我根本没惹他。”勒斯特说,“他在那儿玩得好好的,忽然之间就又哭又喊的了。”
“你碰他的‘坟地’
 了没有。”迪尔西说。
了没有。”迪尔西说。
“我没碰他的‘坟地’呀。”勒斯特说。
“别跟我撒谎,小子。”迪尔西说。我们走上台阶,走进厨房。迪尔西打开炉门,拉过一把椅子放在炉火前,让我坐下来。我不哭了。
你干吗要惹她
 生气呢,迪尔西说。你就不能把他带开去吗。
生气呢,迪尔西说。你就不能把他带开去吗。
他不过是在那儿瞧火,凯蒂说。母亲正在告诉他,他的新名儿是什么。我们根本没想惹她生气呀。
我知道你是没有这样的意思,迪尔西说。他在屋子里的这一头,她在另外一头。好,我的东西你们一点也不要动。我走开的时候你们可什么都别动啊。
“你不害臊吗。”迪尔西说,
 “这样捉弄他。”她把那只蛋糕放在桌子上。
“这样捉弄他。”她把那只蛋糕放在桌子上。
“我没捉弄他。”勒斯特说,“他前一分钟还在玩那只装满了狗尾巴草的瓶子,马上就突然又是哭又是叫的了。这您也是听见的。”
“你没有动他的花儿吗。”迪尔西说。
“我没碰他的‘坟地’啊。”勒斯特说,“我要他的破烂干什么。我只不过是在找我的镚子儿。”
“你丢了,是吗。”迪尔西说。她点亮了蛋糕上插着的蜡烛。有些是小蜡烛。有些是大蜡烛,给切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我早就跟你说过要把它藏好。这会儿我看你又得让我跟弗洛尼去要了吧。”
“反正我要去看演出,不管有没有班吉。”勒斯特说,“我不能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跟在他屁股后面。”
“他要干什么,你就得顺着他,你这黑小子。”迪尔西说,“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我不是一直在这么干吗。”勒斯特说,“他要什么,我不老是顺着他的吗。是不是这样,班吉。”
“那你就照样干下去。”迪尔西说,“他大吵大闹,你还把他带到屋里来,惹得小昆丁也生了气。现在你们趁杰生还没回来,快把蛋糕吃了吧。我不想让他为了一只蛋糕对着我又是跳又是叫,这蛋糕还是我自个儿掏腰包买的呢。我要是在这厨房里烘一只蛋糕,他还要一只一只地点着数鸡蛋呢。你现在可得留点神,别再惹他了,不然你今儿晚上休想去看演出。”
迪尔西走了。
“你不会吹蜡烛。”勒斯特说,“瞧我来把它们吹灭。”他身子往前靠,胀鼓了脸颊。蜡烛都灭了。我哭了。“别哭。”勒斯特说,“来。你瞧这炉火,我来切蛋糕。”
我能听见时钟的嘀嗒声,我能听见站在我背后的凯蒂的出气声,我能听见屋顶上的声音。
 凯蒂说,还在下雨。我讨厌下雨。我讨厌这一切。接着她把头垂在我的膝盖上,哭了起来,她搂住我,我也哭了起来。接着我又看着炉火,那些明亮、滑溜的形体都不见了。我能听见时钟、屋顶和凯蒂的声音。
凯蒂说,还在下雨。我讨厌下雨。我讨厌这一切。接着她把头垂在我的膝盖上,哭了起来,她搂住我,我也哭了起来。接着我又看着炉火,那些明亮、滑溜的形体都不见了。我能听见时钟、屋顶和凯蒂的声音。
我吃了几口蛋糕。
 勒斯特的手伸过来又拿走了一块。我能听见他吃东西的声音。我看着炉火。
勒斯特的手伸过来又拿走了一块。我能听见他吃东西的声音。我看着炉火。
一根长长的铁丝掠过我的肩头。它一直伸到炉门口,接着炉火就看不见了。我哭了起来。
“你又叫个什么劲儿。”勒斯特说。“你瞧呀。”那炉火又出现了。我也就不哭了。“你就不能像姥姥关照的那样,老老实实坐着,看着炉火,安静一些吗。”勒斯特说,“你真该为自己感到害臊。哪。再拿点蛋糕去。”
“你又把他怎么啦。”迪尔西说,“你就不能让他安生一会儿吗。”
“我正是在让他别哭,不让他吵醒卡罗琳小姐呢。”勒斯特说,“不知怎么的他又觉得不自在了。”
“我可知道谁让他不自在。”迪尔西说,“等威尔许回家,我要让他拿棍子来抽你。你这是在讨打。你一整天都不老实。你是不是带他到小河沟去了。”
“没有啊。”勒斯特说,“我们就照您吩咐的那样,整天都在这儿院子里玩。”
他的手伸过来,还想拿一块蛋糕。迪尔西打他的手。“还拿,瞧我用这菜刀把你的爪子剁掉。”迪尔西说,“他肯定连一块也没吃着。”
“他吃了。”勒斯特说,“他已经比我多吃一倍了。您问他是不是吃了。”
“你再伸手试试看。”迪尔西说,“你倒试试看。”
一点不错,迪尔西说。
 我看下一个就该轮到我哭了。我看毛莱也准愿意让我为他哭一会儿的。
我看下一个就该轮到我哭了。我看毛莱也准愿意让我为他哭一会儿的。
现在他的名字是班吉了,凯蒂说。
这算是哪档子事呢,迪尔西说。他生下来时候起的名儿还没有用坏,是不是啊。
班吉明是《圣经》里的名字
 ,凯蒂说。对他来说,这个名字要比毛莱好。
,凯蒂说。对他来说,这个名字要比毛莱好。
这算是哪档子事呢,迪尔西说。
母亲是这样说的,凯蒂说。
哼,迪尔西说。换个名儿可帮不了他的忙。但也不会让他更倒霉。有些人运气一不好,就赶紧换个名儿。我的名字在我记事前就是迪尔西,等人家不记得有我这个人了,我还是叫迪尔西。
既然人家都不记得你了,迪尔西,又怎么会知道你叫迪尔西呢,凯蒂说。
那本大书上会写着的,宝贝儿,迪尔西说。写得清清楚楚的。

你认识字吗,凯蒂说。
我用不着认识字,迪尔西说。人家会念给我听的。我只要说一句,我在这儿哪。这就行了。
那根长铁丝掠过我的肩膀,炉火不见了。
 我又哭了。
我又哭了。
迪尔西和勒斯特打起来了。
“这回可让我看见了。”迪尔西说,“哦嗬,我可看见你了。”她把勒斯特从屋角里拖出来,使劲摇晃他,“没干什么事招惹他,是不是啊。你就等着你爹回来吧。但愿我跟过去一样年轻,那我就能把你治得光剩下半条命了。我一定要把你锁进地窖,不让你今天晚上去看演出。我一定要这样干。”
“噢,姥姥。”勒斯特说,“噢,姥姥。”
我把手伸到刚才还有火的地方去。
“拉住他。”迪尔西说,“把他拉回来。”
我的手猛地蹦了回来,我把手放进嘴里,迪尔西一把抱住了我。我透过自己的尖叫声还能听到时钟的嘀嗒声。迪尔西把手伸过去,在勒斯特脑袋上打了一下。我的声音叫得一下比一下响。
“去拿碱来。”迪尔西说。她把我的手从我嘴巴里拉出来。这时我的喊声更加响了,我想把手放回嘴里去,可是迪尔西握紧了不放。我喊得更响了。她撒了一些碱末在我的手上。
“到食品间去,从挂在钉子上的抹布上撕一条下来。”她说,“别喊了,得了。你不想再让你妈犯病吧,是吗。好,你瞧炉火吧。迪尔西一分钟里就让你的手不疼。你瞧炉火呀。”她打开了炉门。我瞧着炉火,可是我的手还疼,因此我没有停住喊叫。我还想把手塞进嘴里,可是迪尔西握得紧紧的不放。
她把布条缠在我的手上。母亲说,
“这又是怎么的啦。连我生病也不让我安生。家里有两个成年黑人看着他,还要我爬起床下楼来管他吗。”
“他这会儿没事了。”迪尔西说,“他马上就会不喊的。他不过是稍稍烫了一下手。”
“家里有两个这么老大的黑人,还非得让他到屋子里来大吵大闹。”母亲说,“你们明知道我病了,就存心招惹他。”她走过来站在我身边。“别哭了。”她说,“马上给我住嘴。这个蛋糕是你给他吃的吗。”
“是我买的。”迪尔西说,“这可不是从杰生的伙食账里开支的。是我给他过生日吃的。”
“你是要用这种店里买来的蹩脚货毒死他吗。”母亲说,“这就是你存心要干的事。我连一分钟的太平日子都没法过。”
“您回楼上躺着去吧。”迪尔西说,“我一分钟就能让他止住痛,他就不会哭了。行了,您走吧。”
“把他留在这儿,好让你们再变着法儿折磨他。”母亲说,“有他在这儿又吼又叫,我在楼上又怎么能躺得住呢。班吉明。马上给我停住。”
“他没地方去。”迪尔西说,“咱们可不跟以前那样有那么多房间。他又不能老待在院子里让所有的街坊都看他哭。”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说,“这都是我不好。我反正快要不在人世了,我一走你们和杰生日子都会好过了。”她哭起来了。
“您也快别哭了。”迪尔西说,“这样下去又该病倒了。您回楼上去吧。勒斯特这就带他到书房里去,好让我把他的晚饭做出来。”
迪尔西陪着母亲走出去了。
“住嘴。”勒斯特说,“你给我住嘴。你想要我把你另外一只手也烫一下吗。你根本不痛。别哭了。”
“给你这个。”迪尔西说,“好了,快别哭了。”她递给我那只拖鞋
 ,我就停住了哭声。“带他到书房去吧,”她说,“要是再听见他哭,我就自己来抽烂你的皮。”
,我就停住了哭声。“带他到书房去吧,”她说,“要是再听见他哭,我就自己来抽烂你的皮。”
我们走进书房。勒斯特开亮了灯。几扇窗户变黑了,墙上高处显出一摊黑影,我走过去摸摸它。它像一扇门,只不过它不是门。
在我背后,炉火升了起来,我走到炉火前,在地板上坐了下来,手里拿着那只拖鞋。火头升得更高了。它照亮了母亲座椅上的垫子。
“别嚷嚷了。”勒斯特说,“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我在这儿给你生起了火,你连看也不看一眼。”
你的名字是班吉。
 凯蒂说。你听见了吗。班吉。班吉。
凯蒂说。你听见了吗。班吉。班吉。
别这样叫他
 ,母亲说。你把他领到这边来。
,母亲说。你把他领到这边来。
凯蒂把手插在我胳肢窝底下,抱我起来。
起来,毛——我是说,班吉,她说。
你不用抱他嘛,母亲说。你不会把他领过来吗。你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明白吗。
我抱得动他的,凯蒂说。
“让我抱他上楼吧,迪尔西。”

“你走吧,小不点儿。”迪尔西说,“你自己还只有一点点大,连只跳蚤都拖不动呢。你走吧,安安静静的,就跟杰生先生
 吩咐的那样。”
吩咐的那样。”
楼梯顶上有一点灯光。父亲站在那儿,只穿着衬衫。他那副模样就像是在说“别出声”。
凯蒂悄声说,“妈妈病了吗。”
威尔许把我放下,我们走进母亲的房间。
 屋子里生着火。火在四面墙上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镜子里也有一堆火。我能闻到生病的气味。那是母亲头上搁着的一块叠起来的布上发出来的。她的头发散开在枕头上。火光达不到那儿,可是照亮了她的手,那几只戒指一跳一跳地在闪闪发亮。
屋子里生着火。火在四面墙上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镜子里也有一堆火。我能闻到生病的气味。那是母亲头上搁着的一块叠起来的布上发出来的。她的头发散开在枕头上。火光达不到那儿,可是照亮了她的手,那几只戒指一跳一跳地在闪闪发亮。
“来,去跟妈妈说声晚安。”凯蒂说。我们来到床前。火从镜子里走出去了。父亲从床上站起来,抱我起来,母亲伸手按在我头上。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母亲说。她的眼睛闭着。
“七点差十分。”父亲说。
“现在让他去睡还太早了点。”母亲说,“天不亮他就会醒来的,再像今天这样过一天,我真要受不了啦。”
“又来了,又来了。”父亲说。他拍拍母亲的脸颊。
“我知道我对你只不过是一个负担。”母亲说,“不过我也快要走了。到时候我再也不会拖累你了。”
“别说了。”父亲说,“我带他到楼下去玩一会儿。”他把我抱起来,“来吧,老伙计。咱们下楼去玩一会儿。昆丁正在做功课,咱们得轻一点儿。”
凯蒂走上前去,把头伛倒在床上,母亲的手进到火光里来了。
她那几只戒指在凯蒂的背上跳跃。
母亲病了,父亲说。
 迪尔西会带你们上床去睡的。昆丁在哪儿啦。
迪尔西会带你们上床去睡的。昆丁在哪儿啦。
威尔许找他去了,迪尔西说。
父亲站在那儿,瞧着我们走过去。
 我们能听到母亲在她卧房里发出的声音。凯蒂说:“嘘。”杰生还在上楼。他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我们能听到母亲在她卧房里发出的声音。凯蒂说:“嘘。”杰生还在上楼。他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你们今天晚上都得乖些。”父亲说,“要安静些,不要惊吵妈妈。”
“我们一定不吵。”凯蒂说。“杰生,现在你可得安静些了。”她说。我们踮起了脚。
我们能听到屋顶上的声音。我也能看见镜子里的火光。凯蒂又把我抱了起来。
“好,来吧。”她说,“一会儿你就可以回到炉火边来的。好,别哭了。”
“凯丹斯。”母亲说。
“别哭,班吉。”凯蒂说,“母亲要你过去一会儿。你要乖点儿。马上就可以回来的。班吉。”
凯蒂把我放了下来,我不哭了。
“就让他待在这儿吧,妈妈。等他不要看火了,您再告诉他好了。”
“凯丹斯。”母亲说。凯蒂弯下身子把我抱了起来。我们跌跌撞撞的。“凯丹斯。”母亲说。
“别哭。”凯蒂说,“你还是可以看到火的。别哭呀。”
“把他带到这边来。”母亲说,“他太大,你抱不动了。你不能再抱他了。这样会影响你的脊背的。咱们这种人家的女子一向是为自己挺直的体态感到骄傲的。你想让自己的模样变得跟洗衣婆子一样吗。”
“他还不算太重。”凯蒂说,“我抱得动的。”
“反正我不要别人抱他。”母亲说,“都五岁了。不,不。别放在我膝上。让他站直了。”
“只要您抱住他,他就会不哭的。”凯蒂说,“别哭了。”她说,“你一会儿就可以回去的。哪。这是你的垫子。瞧呀。”
“别这样,凯丹斯。”母亲说。
“只要让他看见垫子,他就会不哭的。”凯蒂说,“您欠起点儿身子,让我把垫子抽出来。哪,班吉。瞧呀。”
我瞧着垫子,就住了声。
“你也太迁就他了。”母亲说,“你跟你父亲都是这样的。你们不明白到头来吃苦头的还是我。大姆娣把小杰生惯成那样,足足花了两年才把他的坏习惯改过来,我身体不好,再要叫我教好班吉明精力是不够的了。”
“您不用为他操心。”凯蒂说,“我喜欢照顾他。是不是啊,班吉。”
“凯丹斯。”母亲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这样叫他。你父亲一定要用那个愚蠢的小名叫你,这已经是够糟糕的了,我可不允许人家用小名叫他。叫小名顶顶俗气了。只有下等人才用小名。班吉明。”她说。
“你看着我呀。”母亲说。
“班吉明。”她说。她用双手托住我的脸,把我的脸转过来对着她的脸。
“班吉明。”她说,“把那只垫子拿走,凯丹斯。”
“他会哭的。”凯蒂说。
“把那只垫子拿走,照我吩咐的做。”母亲说,“他必须学会要听大人的话。”
那只垫子拿走了。
“不要哭,班吉。”凯蒂说。
“你上那边去给我坐下来。”母亲说,“班吉明。”她把我的脸托住,对准她的脸。
“别这样。”她说,“别这样。”
可是我没有住声,母亲就搂住我哭了起来,我也哭着。接着垫子回来了,凯蒂把它举在母亲的头上。她把母亲拉回到椅子里去,母亲仰靠在红黄两色的椅垫上哭着。
“别哭啦,妈妈。”凯蒂说,“您回楼上去躺着,养您的病去。我去叫迪尔西来。”她把我带到炉火前,我瞧着那些明亮、滑溜的形体。我能听见火的声音和屋顶上的声音。
父亲把我抱了起来。
 他身上有一股雨的气味。
他身上有一股雨的气味。
“嗨,班吉。”他说,“你今天乖不乖啊。”
凯蒂跟小杰生在镜子里打了起来。
“你怎么啦,凯蒂。”父亲说。
他们还在打。杰生哭起来了。
“凯蒂。”父亲说。杰生在呜呜地哭。他不打了,可是我们可以看见凯蒂还在镜子里打,于是父亲把我放下,走到镜子里去,也打起来了。他把凯蒂举了起来。凯蒂还在乱打。杰生赖在地上哭。他手里拿着剪刀。父亲拉住了凯蒂。
“他把班吉所有的纸娃娃都给铰了。”凯蒂说,“我也要铰破他的肚子。”
“凯丹斯。”父亲说。
“我要铰。”凯蒂说。“我要铰嘛。”她在挣扎。父亲抱住了她。她用脚踢杰生。杰生滚到角落里去,离开了镜子。父亲把凯蒂抱到炉火边。他们全都离开了镜子。只有炉火还在那里面。就像是火在一扇门里似的。
“别打了。”父亲说,“你又要让母亲躺在她房间里生病吗。”
凯蒂不挣扎了。“他把毛——班吉和我做的娃娃全给铰坏了。”凯蒂说,“他是存心捣乱才这样干的。”
“我不是的。”杰生说。他坐了起来,一边还在哭。“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他的。我还以为是些废纸呢。”
“你不会不知道。”凯蒂说,“你完全是存心的。”
“别哭了。”父亲说。“杰生。”他说。
“我明天再给你做多多的。”凯蒂说,“咱们再做许多许多的。哪,你还可以看看这只垫子嘛。”
杰生进来了。

我不是一直叫你不要哭吗,勒斯特说。
这又是怎么的啦,杰生说。
“他这是在存心捣乱。”勒斯特说,“今天一整天他都这样。”
“你不惹他不就完了吗。”杰生说,“要是你哄不住他,那你就把他带到厨房里去。我们这些人可不能像母亲那样,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
“姥姥说要等她做完了晚饭才能让班吉进去。”勒斯特说。
“那你就陪他玩,别让他瞎吵吵。”杰生说,“莫非我忙了整整一天,晚上还要回到一所疯人院里来不成。”他打开报纸,看了起来。
你可以看火,看镜子,也可以看垫子的,凯蒂说。
 你用不着等到吃晚饭的时候才看垫子的。我们能听到屋顶上的声音。我们也能透过墙壁听见杰生哭喊的声音。
你用不着等到吃晚饭的时候才看垫子的。我们能听到屋顶上的声音。我们也能透过墙壁听见杰生哭喊的声音。
迪尔西说:“你回来啦,杰生。你没惹他吧,惹了吗。”

“没惹,姥姥。”勒斯特说。
“昆丁小姐在哪儿。”迪尔西说,“晚饭快要好了。”
“我不知道。”勒斯特说,“我没看见她。”
迪尔西走开了。“昆丁。”她在门厅里嚷嚷,“昆丁。晚饭得了。”
我们能听到屋顶上的声音。昆丁身上也有雨的气味。

杰生干了什么啦,他说。
他铰坏了班吉所有的娃娃,凯蒂说。
母亲说了别再叫他班吉,昆丁说。他在我们身边的地毯上坐了下来。我真希望天不要下雨,他说。什么事情都没法干。
你跟别人打过架了,凯蒂说。打了没有。
就只打了几下,昆丁说。
一眼就看出来了,凯蒂说。父亲会看出来的。
我不怕,昆丁说。我真希望天别下了。
昆丁
 说:“迪尔西不是说晚饭得了吗。”
说:“迪尔西不是说晚饭得了吗。”
“是的,您哪。”勒斯特说。杰生瞧了昆丁一眼。接着他又读他的报。昆丁进来了。“她是说快得了。”勒斯特说。昆丁重重地往母亲的椅子上坐下去。勒斯特说:
“杰生先生。”
“什么事。”杰生说。
“给我两毛五分钱吧。”勒斯特说。
“为什么。”杰生说。
“让我今天晚上去看演出。”勒斯特说。
“不是迪尔西要替你向弗洛尼讨两毛五吗。”杰生说。
“她给了。”勒斯特说,“我丢了。我和班吉找那只镚子儿找了一整天呢。你可以问他。”
“那你向他借一个好了。”杰生说,“我的钱都是干活挣来的。”他又读报纸。昆丁在看着炉火。火光在她的眼睛里和她的嘴上跳动。她的嘴是血红血红的。
“我是一直留心,不想让他到那边去的。”勒斯特说。
“你少跟我啰嗦。”昆丁说。杰生盯着她看。
“我没跟你说过,要是我看见你再跟那个戏子混在一起,我要怎么办吗。”他说。昆丁瞧着炉火。“你难道没听见吗。”杰生说。
“我当然听见了。”昆丁说,“那你怎么不办呢。”
“这可不用你操心。”杰生说。
“我才不操心呢。”昆丁说。杰生又读起报来。
我能听见屋顶上的声音。父亲伛身向前,盯着昆丁看。

喂,他说。谁赢啦。
“谁也没赢。”昆丁说,“他们把我们拉开了。老师们。”
“对手是谁呢。”父亲说,“你能讲给我听吗。”
“没什么好说的。”昆丁说,“他跟我一般大。”
“那就好。”父亲说,“你能告诉我是为了什么吗。”
“不为什么。”昆丁说,“他说他要放一只蛤蟆在她的书桌里,而她肯定不敢用鞭子抽他。”
“哦。”父亲说,“她。后来呢。”
“是的,爸爸。”昆丁说,“后来不知怎么的我就打了他一下。”
我们可以听见屋顶上的声音、炉火的声音和门外抽抽噎噎的声音。
“十一月的天气,他上哪儿去找蛤蟆啊。”父亲说。
“那我就不清楚了,爸爸。”昆丁说。
我们能听见那些声音。
“杰生。”父亲说。我们能听到杰生的声音。
“杰生。”父亲说。“快进来,别那样了。”
我们可以听见屋顶上的声音、炉火的声音和杰生的声音。
“别那样,行了。”父亲说。“你想让我再抽你一顿吗。”父亲把杰生抱起来,放进自己身边的椅子里。杰生在抽抽噎噎。我们能听见炉火和屋顶上的声音。杰生的抽噎声更响了。
“再跟你说一遍。”父亲说。我们能听见炉火和屋顶上的声音。
迪尔西说,行了。你们都可以来吃晚饭了。

威尔许身上有雨的气味。
 他也有狗的气味。我们能听见炉火和屋顶上的声音。
他也有狗的气味。我们能听见炉火和屋顶上的声音。
我们能听见凯蒂急急地走路的声音。
 父亲和母亲看着门口。凯蒂急急地走着,掠过门口。她没有朝门里望一眼。她走得很快。
父亲和母亲看着门口。凯蒂急急地走着,掠过门口。她没有朝门里望一眼。她走得很快。
“凯丹斯。”母亲说。凯蒂停住了脚步。
“嗳,妈妈。”她说。
“别说了,卡罗琳。”父亲说。
“你进来。”母亲说。
“别说了,卡罗琳。”父亲说,“让她去吧。”
凯蒂来到门口,站在那儿,看着父亲和母亲。她的眼睛扫到我身上,又移了开去。我哭起来了。哭声越来越大,我站了起来。凯蒂走进房间,背靠着墙站着,眼睛看着我。我边哭边向她走去,她往墙上退缩,我看见她的眼睛,于是我哭得更厉害了,我还拽住了她的衣裙。她伸出双手,可是我拽住了她的衣裙。她的泪水流了下来。
威尔许说,现在你的名字是班吉明了。
 你可知道干吗要把你改名叫班吉明吗。他们是要让你变成一个蓝牙龈的黑小子。妈咪说你爷爷早先老给黑小子改名儿,后来他当了牧师,人们对他一看,他的牙龈也变成蓝颜色的了。他以前牙龈可不是蓝颜色的。要是大肚子的娘们在月圆的夜晚面对面见到他,她们生出来的小孩也是蓝牙龈的。有一天晚上,有十来个蓝牙龈的小孩在他家门口跑来跑去,他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捕负鼠的人后来在树林里找到了他,已经给吃得光剩一副骨头架子了。你可知道是谁把他吃掉的吗。就是那帮蓝牙龈的孩子。
你可知道干吗要把你改名叫班吉明吗。他们是要让你变成一个蓝牙龈的黑小子。妈咪说你爷爷早先老给黑小子改名儿,后来他当了牧师,人们对他一看,他的牙龈也变成蓝颜色的了。他以前牙龈可不是蓝颜色的。要是大肚子的娘们在月圆的夜晚面对面见到他,她们生出来的小孩也是蓝牙龈的。有一天晚上,有十来个蓝牙龈的小孩在他家门口跑来跑去,他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捕负鼠的人后来在树林里找到了他,已经给吃得光剩一副骨头架子了。你可知道是谁把他吃掉的吗。就是那帮蓝牙龈的孩子。

我们来到门厅里。凯蒂还盯看着我。
 她一只手按在嘴上,我看见她的眼睛,我哭了。我们走上楼去。她又停住脚步,靠在墙上,盯看着我,我哭了,她继续上楼,我跟着上去,边走边哭,她退缩在墙边,盯看着我。她打开她卧室的门,可是我拽住她的衣裙,于是我们走到洗澡间,她靠着门站着,盯着看我。接着她举起一只胳膊,掩住了脸,我一边哭一边推她。
她一只手按在嘴上,我看见她的眼睛,我哭了。我们走上楼去。她又停住脚步,靠在墙上,盯看着我,我哭了,她继续上楼,我跟着上去,边走边哭,她退缩在墙边,盯看着我。她打开她卧室的门,可是我拽住她的衣裙,于是我们走到洗澡间,她靠着门站着,盯着看我。接着她举起一只胳膊,掩住了脸,我一边哭一边推她。

你把他怎么啦,杰生说。
 你就不能不去惹他吗。
你就不能不去惹他吗。
我连碰都没有碰他呀,勒斯特说。他一整天都这样别扭。他真是欠揍。
应该把他送到杰克逊去,昆丁说。在这样一幢房子里过日子,谁受得了。
你要是不喜欢这儿,小姐,你满可以走嘛,杰生说。
我是要走的,昆丁说。这可不用你操心。
威尔许说:“你往后去点,让我把腿烤烤干。”
 他把我往一边推了推。“得了,你别又开始吼了。你还是看得见的嘛。你不就是要看火吗。你不用像我这样,下雨天还得在外面跑。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在炉火前四仰八叉地躺了下来。
他把我往一边推了推。“得了,你别又开始吼了。你还是看得见的嘛。你不就是要看火吗。你不用像我这样,下雨天还得在外面跑。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在炉火前四仰八叉地躺了下来。
“你现在知道干吗你名儿改成班吉明了吧。”威尔许说,“你妈太骄傲了,觉得你丢了她的脸。这是我妈咪说的。”
“你老老实实给我待在那儿,让我把腿烤干了。”威尔许说,“要不你知道我会怎么样。我要扒掉你屁股上的皮。”
我们能听见火的声音、屋顶上的声音和威尔许出气的声音。
威尔许急忙坐起来,把腿收了回来。父亲说:“行了,威尔许。”
“今天晚上我来喂他。”凯蒂说,“威尔许喂他有时候他爱哭。”
“把这只托盘送到楼上去。”迪尔西说,“快回来喂班吉吃饭。”
“你不要凯蒂喂你吗。”凯蒂说。
他还非得把那只脏兮兮的旧拖鞋拿到餐桌上来吗,昆丁说。
 你为什么不在厨房里喂他呢。这就好像跟一口猪一块儿吃饭似的。
你为什么不在厨房里喂他呢。这就好像跟一口猪一块儿吃饭似的。
要是你不喜欢这种吃饭的方式,你可以不上餐桌来嘛,杰生说。
热气从罗斯库司身上冒出来。
 他坐在炉子前面。烘炉的门打开着,罗斯库司把两只脚伸了进去。热气在碗上冒着。凯蒂轻巧地把勺子送进我的嘴里。碗里面有一个黑斑。
他坐在炉子前面。烘炉的门打开着,罗斯库司把两只脚伸了进去。热气在碗上冒着。凯蒂轻巧地把勺子送进我的嘴里。碗里面有一个黑斑。
行了,行了,迪尔西说。他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碗里的东西落到了黑斑下面。
 接着碗里空了。碗不见了。“他今天晚上肚子很饿。”凯蒂说。那只碗又回来了。我看不见那个黑斑。接着我又看见了。“他今天晚上饿坏了。”凯蒂说,“瞧他吃了多少。”
接着碗里空了。碗不见了。“他今天晚上肚子很饿。”凯蒂说。那只碗又回来了。我看不见那个黑斑。接着我又看见了。“他今天晚上饿坏了。”凯蒂说,“瞧他吃了多少。”
哼,他会的,昆丁说。
 你们都派他来监视我。我恨这个家。我一定要逃走。
你们都派他来监视我。我恨这个家。我一定要逃走。
罗斯库司说:“看样子要下整整一夜的雨了。”

你早就一直野在外面了,也就差三顿饭没在外面吃了,杰生说。

你瞧我跑不跑,昆丁说。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迪尔西说,
 “我大腿关节疼得不行,动弹都动弹不了。一个晚上上楼下楼没个完。”
“我大腿关节疼得不行,动弹都动弹不了。一个晚上上楼下楼没个完。”
哦,那是我意料之中的,杰生说。
 我早就料到你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我早就料到你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昆丁把她的餐巾往桌子上一摔。
你就少说两句吧,杰生,迪尔西说。她走过去用胳膊搂住昆丁。快坐下,宝贝儿,迪尔西说。他应该感到害臊才是,把所有跟你没关系的坏事都算在你的账上。
“她又在生闷气了,是吗。”罗斯库司说。

“你就少说两句吧。”迪尔西说。
昆丁把迪尔西推开。
 她眼睛盯着杰生。她的嘴血红血红的。她拿起她那只盛着水的玻璃杯,胳膊往回一收,眼睛盯住了杰生。迪尔西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们打了起来。玻璃杯掉在桌子上,摔碎了,水流得一桌子都是。昆丁跑了开去。
她眼睛盯着杰生。她的嘴血红血红的。她拿起她那只盛着水的玻璃杯,胳膊往回一收,眼睛盯住了杰生。迪尔西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们打了起来。玻璃杯掉在桌子上,摔碎了,水流得一桌子都是。昆丁跑了开去。
“母亲又生病了。”凯蒂说。

“可不是吗。”迪尔西说,“这种鬼天气谁都会生病的。孩子,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几口饭吃完呀。”
你这天杀的,昆丁说。
 你这天杀的。我们可以听到她跑上楼去的声音。我们都到书房去。
你这天杀的。我们可以听到她跑上楼去的声音。我们都到书房去。
凯蒂把垫子递给我,这样我就可以又看垫子又看镜子又看火了。

“昆丁在做功课,咱们可得轻声点。”父亲说,“你在干什么呢,杰生。”
“没干什么。”杰生说。
“那你还是上这儿来玩吧。”父亲说。杰生从墙旮旯里走出来。
“你嘴巴里在嚼什么。”父亲说。
“没嚼什么。”杰生说。
“他又在嚼纸片了。”凯蒂说。
“上这儿来,杰生。”父亲说。
杰生把那团东西扔进火里。它发出了嘶嘶声,松了开来,变成了黑色。接着变成了灰色。接着就不见了。凯蒂和父亲和杰生都坐在母亲的椅子里。杰生使劲闭紧了眼睛,嘴巴一抿一抿的,像是在尝什么滋味。凯蒂的头枕在父亲的肩膀上。她的头发像一团火,她眼睛里闪着小小的火星,我走过去,父亲把我也抱上了椅子,凯蒂搂住了我。她身上有树的香味。
她身上有树的香味。墙旮旯里已经是黑黑的了,可是我能看得见窗户。
 我蹲在墙旮旯里,手里拿着那只拖鞋。我看不见它,可是我的手能看见它,我也能听见天色一点点黑下来的声音,我的手能看见拖鞋,可是我看不见自己,可是我的手能看见拖鞋,我蹲在墙旮旯里,听着天色一点点黑下来的声音。
我蹲在墙旮旯里,手里拿着那只拖鞋。我看不见它,可是我的手能看见它,我也能听见天色一点点黑下来的声音,我的手能看见拖鞋,可是我看不见自己,可是我的手能看见拖鞋,我蹲在墙旮旯里,听着天色一点点黑下来的声音。
原来你在这儿,勒斯特说。瞧我这儿有什么。他拿出来给我看。知道我从哪儿弄来的吗。是昆丁小姐给我的。我知道总不会看不成戏的。你一个人躲在这儿干什么。我还以为你溜到外面去了呢。你今天哼哼唧唧、嘟嘟哝哝还嫌不够吗,还要蹲在这空屋子里呜噜呜噜个没完。快上床去睡吧,免得戏开场了我还不能赶到。我今天晚上可是要少陪了。那些大喇叭一吹响,我就要颠儿了。
我们没有回我们自己的房间。

“这是我们出麻疹时候睡的地方。”凯蒂说,“干吗我们今儿晚上得睡在这儿呀。”
“你们管它在哪个房间睡。”迪尔西说。她关上门,坐下来帮我脱衣服。杰生哭了。“别哭。”迪尔西说。
“我要跟大姆娣一块儿睡。”杰生说。
“她在生病。”凯蒂说,“等她好了,你再跟她一块儿睡。是不是这样,迪尔西。”
“好了,别哭了。”迪尔西说,杰生住了声。
“咱们的睡衣在这儿,别的东西也都在这儿。”凯蒂说,“这真像是搬家。”
“你们快快穿上睡衣吧。”迪尔西说,“你帮杰生把扣子解掉。”
凯蒂解杰生的扣子。他又哭起来了。
“你欠揍是不是。”迪尔西说。杰生不吱声了。
昆丁,母亲在楼道里说。

什么事,昆丁隔着墙说。我们听见母亲锁上了门。她朝我们房间里看了看,走进来在床上弯下身子,在我的额上吻了一下。
等你让他睡下了,就去问问迪尔西她反不反对我用热水袋,母亲说。告诉她要是她反对呢,那我就不用算了。告诉她我只想问问她的意思怎么样。
好咧,您哪,勒斯特说。过来,把裤子脱了。
昆丁和威尔许进来了。
 昆丁把脸扭了开去。“你哭什么呀。”凯蒂说。
昆丁把脸扭了开去。“你哭什么呀。”凯蒂说。
“别哭了。”迪尔西说,“你们大家都脱衣服睡吧。你也可以回去了,威尔许。”
我脱掉衣服,我瞧了瞧自己,我哭起来了。
 别哭了,勒斯特说。你找它们有什么用呢。它们早不在了。你再这样,我们以后再不给你做生日了。他帮我穿上睡袍。我不吱声了,这时勒斯特停下了手,把头朝窗口扭过去。接着他走到窗边,朝外面张望。他走回来,拉住我的胳膊。她出来了,他说。你可别出声。我们走到窗前,朝外面望去。那黑影从昆丁那间房的窗子里爬出来,爬到了树上。我们看见那棵树在摇晃。摇晃的地方一点点往下落,接着那黑影离开了树,我们看见它穿过草地。这以后我们就看不见它了。好了,勒斯特说。哎唷。你听喇叭声。你快上床,我可要撒丫儿了。
别哭了,勒斯特说。你找它们有什么用呢。它们早不在了。你再这样,我们以后再不给你做生日了。他帮我穿上睡袍。我不吱声了,这时勒斯特停下了手,把头朝窗口扭过去。接着他走到窗边,朝外面张望。他走回来,拉住我的胳膊。她出来了,他说。你可别出声。我们走到窗前,朝外面望去。那黑影从昆丁那间房的窗子里爬出来,爬到了树上。我们看见那棵树在摇晃。摇晃的地方一点点往下落,接着那黑影离开了树,我们看见它穿过草地。这以后我们就看不见它了。好了,勒斯特说。哎唷。你听喇叭声。你快上床,我可要撒丫儿了。
房间里有两张床。
 昆丁爬上了另一张床。他把脸扭了过去,对着墙。迪尔西把杰生抱到他那张床上去。凯蒂脱掉了衣裙。
昆丁爬上了另一张床。他把脸扭了过去,对着墙。迪尔西把杰生抱到他那张床上去。凯蒂脱掉了衣裙。
“瞧瞧你的裤衩。”迪尔西说,“你真走运,因为你妈没看见。”
“我已经告发过她了。”杰生说。
“你还会不告发吗。”迪尔西说。
“你告了又捞到什么好处啦。”凯蒂说,“搬弄是非。”
“我捞到什么好处啦。”杰生说。
“你怎么还不穿睡衣。”迪尔西说。她走过去给凯蒂脱掉了背心和裤衩。“瞧你。”迪尔西说。她把裤衩卷起来,用它来擦凯蒂的屁股。“全都湿透了。”她说。“不过今儿晚上没法洗澡了。穿上。”她帮凯蒂穿上睡衣睡裤,凯蒂爬上床来,迪尔西走到门口,手按在开关上。“你们现在都别出声了,听见没有。”她说。
“听见了。”凯蒂说,“母亲今天晚上不来看我们了。”她说,“所以大家还得听从我的指挥。”
“行。”迪尔西说,“好了,快快睡吧。”
“母亲病了。”凯蒂说,“她和大姆娣都在生病。”
“别出声了。”迪尔西说,“你们快睡吧。”
房间变黑了,只有门口是亮的。接着门口也变黑了。凯蒂说:“别响,毛莱。”她伸出手来摸摸我。于是我就不吱声了。我们能听见大家的出气声。我们能听见黑夜的声音。
黑暗退开去了,父亲在看着我们。他看了看昆丁和杰生,然后走过来吻了吻凯蒂,把手按在我的头上。
“母亲病得厉害吗。”凯蒂说。
“不厉害。”父亲说,“你好好当心毛莱,行吧。”
“好的。”凯蒂说。
父亲走到门口,又看看我们。接着黑暗又回来了,他站在门口,变成了一个黑影,接着门口也变黑了。凯蒂搂住了我,我能听见大伙儿的出气声,能听见黑夜的声音,还有那种我闻得出气味来的东西的声音。这时候,我能看见窗户了,树枝在那儿沙沙地响着。接着黑暗又跟每天晚上一样,像一团团滑溜、明亮的东西那样退了开去,这时候凯蒂说我已经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