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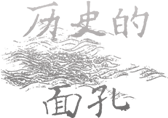
此后,容闳虽然未向曾国藩提起他的教育计划,但他并未放弃,一有机会,他便向包括丁日昌在内的官员们鼓吹自己的想法。其间,他还翻译了《契约论》《格尔屯氏万国图志》的大部分内容,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传播西方文化知识。
1870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状况的稳定,容闳完成了曾国藩的重托,“教育救国”的使命又重新回到容闳最重要的日程里。
他等待了16年之久的机会来了。
有一次,曾国藩视察工厂,容闳指着工厂里的洋技工跟曾国藩说,你看,那些洋技工,工资高,还有风险,不可靠,中国人应该培养自己的人才,彻底把制造能力本土化。曾国藩从谏如流,立刻同意在制造局内设立机械学校。
这一次教育计划的初步尝试让容闳备受鼓舞。这时候,他的老朋友、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告诉他:“彼当上之文相国,请其代奏。文祥……时方入相,权力甚伟也。”大概意思是,他和军机大臣文祥关系很好,他可以帮容闳把计划给文祥,借文祥的力量上奏朝廷。
经过多年官场历练,此时的容闳也学会了官场套路。他上书的条陈没有只写留学计划一条,而是一次性提出了四条建议。他还聪明地将“幼童海外留学计划”放到了第二条——一个似乎重要又似乎不那么重要的微妙位置。
这是中国古代谋士们惯用的一招。面对上级提出的问题,他们不会只提出一套方案,而是提出一个明显激进的方案,一个明显保守的方案,最后提出中庸的方案。因此,中庸的方案就显得特别合理,容易被采纳。
然而,文祥的离世使得容闳的计划又被搁置了。
直到“天津教案”事件爆发,留学计划才迎来了转机。借着担任翻译的机会,容闳再次向丁日昌提出教育计划。丁日昌与曾国藩召集了多位大臣私下对此进行会谈,最终决定联名上书,恳请清政府重启留学计划。
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这次中外冲突,进言指出:症结源自民众对西方的无知,无知生猜忌,猜忌生谣言,谣言生冲突。根本办法还是启动留学计划,培养能同时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才,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此类问题。
知道联名上书这一消息时,容闳彻夜未眠,“……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
1870年,曾国藩带回皇帝的朱批,“普照所请”四个字赫然在目。也就是说,不仅他的幼童留美的提议通过了,其他三条提议也通过了。
在丁日昌和曾国藩的指导下,他们还采取了一个更老练的做法:请了一位不得志的守旧派官员担任主官。这样一来,守旧派官僚就不会太抵触这件事,而这个官员有差可当,也就成了“自己人”。真正的决定权恰恰在容闳手上。
容闳大喜过望,觉得自己当不当官根本不重要了。从1854年回国到1870年达成心愿,他已经为此奋斗了整整16年。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出发,赶赴美国。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理解异国文化,容闳安排他们寄宿在美国家庭,跟美国人同吃同住,而且将他们分散安排在不同的学校学习。这些孩子以惊人的速度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在学校成绩优秀,而且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表现得活跃和耀眼。
这群留美的孩子回国后,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了继续承担使命的“容闳”。
这里面有詹天佑,他和自己的同学加入了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英勇作战,后来又主持设计和修建了京张铁路;有主持开采当时北方最重要煤矿开滦煤矿的工程师吴仰曾;有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可惜的是,幼童留美计划只持续了十年。
“幼童留美”中断数年后,在甲午海战中,一海之隔的日本用隆隆炮声让清政府认清了现实,清政府才又开启留学计划。然而,他们依旧没有改变短视的病根:他们不再选拔“不定性”的幼童,而是选拔20岁左右的、“更可靠”的年轻人去日本“速成”,归来后成为政府的“工具人”。
但历史吊诡之处常常就在这里。
按理说这些人三观已定,忠君之心难改,不料世界潮流更能洗涤人心。留日学生后来纷纷参加革命,成为主力,最终推翻了清王朝。清庭苦心孤诣想培养鹰犬,最后却培养了掘墓人。
晚年的容闳越来越看清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他在自传里写下了自己深深的失望之感:“……尊自太后,贱及胥吏,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他提出过两个方案:建立中国国家银行,修建津镇铁路。然而,这些却都被盛宣怀半路截和,变成其个人财富和权势的杠杆。
容闳放弃了对原来清政府上层社会圈子的幻想,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启发民智,呼吁变革”。这依然是“教育救国”使命的延伸,却更加直接地指向了核心问题。
他逐渐走向了“革命”这一条路。
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容闳担当了精神领袖和导师的角色。他的寓所成为戊戌年主要改革者的会见场所,维新变法的许多主张也来自他的思想、观点和态度。变法失败后,容闳成了通缉犯。
此后余生,容闳始终在帮助各种反抗力量。他曾引荐康有为拜访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制订过“红龙计划”全力帮助孙中山。
临终前,容闳叮嘱两个儿子回国效命。容闳的两个儿子都是耶鲁大学高才生,在美国已经有了体面的职业和丰厚的薪水,不愿意回国。容闳斥责道:“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才,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费我所望于汝二人者。”
两个儿子感佩于父亲拳拳爱国之心,赶赴国内参加革命。
容闳一生都在放弃,一生也都在争取。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回国争取为国效力的机会。初到国内,他放弃了当律师、当买办发财的机会,宁可贫穷,也要争取尊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都像孔子所说的“丧家之犬”,在自己的祖国成了游民。
结识曾国藩后,他暂时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去争取一个长远的机会。戊戌变法后,他放弃了平稳的生活,宁可成为通缉犯,也要选择革命救国。
容闳的一生,无愧于“赤子”的称号。他的美国朋友约瑟夫·特维切尔牧师对他的评价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他是一位爱国者,从头到脚,乃至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并坚信它将会有灿烂辉煌的成就,以不负这壮丽山河和伟大历史。
容闳由广东出发,在美国成长,回中国历练,周游世界办厂,为了革命逃亡,一路辗转,用一生在努力完成“教育救国”的使命。
作为入海的第一滴水,他激起了更多浪花,同时他也留下了一个更艰难的命题给他的后继英豪:如果教育在短时间里救不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更猛的一剂药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