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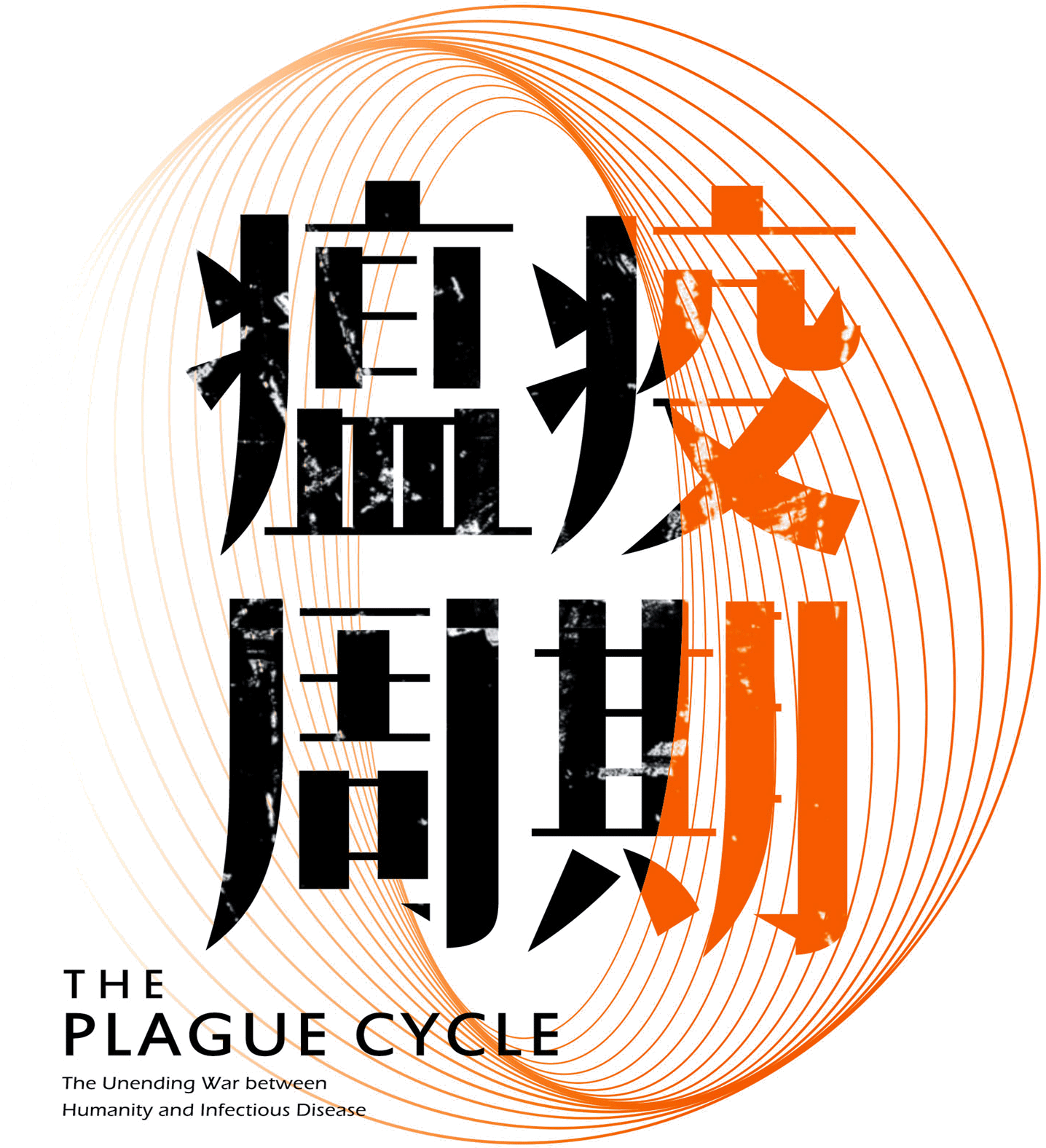
尸体的臭味非常浓烈。我们的父辈祖辈纷纷死于疾病,半数人都逃到了旷野中。豺狗和秃鹫贪婪地吞食着尸体。
——《喀克其奎语年鉴》

因传染性疾病而数次失利的拿破仑,用手指去触碰一名腺鼠疫患者。安托万-让·格罗画作《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细部
(资料来源:《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1799年3月11日,安托万-让·格罗,1804年。维基共享资源。)
大概两万年前,人类生活的大陆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有一座大陆桥,但在冰期末期,这座大陆桥被淹没了。冰川消退之后,幸存下来的人们跟欧亚大陆隔绝开来,但是他们可以向美洲的纵深扩展。不过2 000年,他们就在这片富饶的猎场上星罗棋布,从现在的加拿大一直到南美洲的最南端,到处都有了他们的身影。

没过多久,很多本地的大型哺乳动物灭绝了。这个过程可能受到了狩猎、气候变化和人类自身带来的疾病的推动。这也可能是人们开始进入农业社会的原因之一,但是到这个时候,可供驯化的物种已经没剩下多少了,也就是豚鼠、火鸡、鸭子、美洲驼和羊驼而已。
 而且刚好,以这几种动物为储存宿主并很容易传播到人身上的微生物种类也非常少。这些最早来到美洲的人既跟欧亚文明的绝大部分疾病相互隔绝,自身又没有发展出什么新的疾病,因此折磨他们的主要是来自史前的微生物,包括疱疹病毒、炭疽、寄生虫,可能还有跟梅毒有关的雅司病。
而且刚好,以这几种动物为储存宿主并很容易传播到人身上的微生物种类也非常少。这些最早来到美洲的人既跟欧亚文明的绝大部分疾病相互隔绝,自身又没有发展出什么新的疾病,因此折磨他们的主要是来自史前的微生物,包括疱疹病毒、炭疽、寄生虫,可能还有跟梅毒有关的雅司病。
 因此,接下来的几千年里,美洲人口都在稳步增长。农业中没有了猪、牛、马这几种可能会抑制人口数量的家畜,而伴随这几种家畜而来的细菌和病毒也不会在美洲出现,这对人类的健康是有益的。
因此,接下来的几千年里,美洲人口都在稳步增长。农业中没有了猪、牛、马这几种可能会抑制人口数量的家畜,而伴随这几种家畜而来的细菌和病毒也不会在美洲出现,这对人类的健康是有益的。
查尔斯·曼恩在《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中描述道,到15世纪80年代,南北美洲都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城市和帝国的文明。不同来源给出的估计是,当时整个美洲大陆上生活着4 000万到8 000万人(可资比较的是,当时欧洲的人口数量为7 400万到8 800万)。
中描述道,到15世纪80年代,南北美洲都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城市和帝国的文明。不同来源给出的估计是,当时整个美洲大陆上生活着4 000万到8 000万人(可资比较的是,当时欧洲的人口数量为7 400万到8 800万)。
 新大陆的那些文明建造了金字塔,在山上开凿了台阶,制定了复杂的历法,还用金属制作了精美的艺术品。
新大陆的那些文明建造了金字塔,在山上开凿了台阶,制定了复杂的历法,还用金属制作了精美的艺术品。
 1491年,印加人控制着全世界最大的帝国,比中国的明朝还要大。
1491年,印加人控制着全世界最大的帝国,比中国的明朝还要大。
 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以及墨西哥的特拉特洛尔科组成的大都市圈,比巴黎及其周边的近郊地区要大得多,那可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大都市。
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以及墨西哥的特拉特洛尔科组成的大都市圈,比巴黎及其周边的近郊地区要大得多,那可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大都市。
 但也不过几十年间,这些文明就都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微生物入侵者面前化为齑粉。
但也不过几十年间,这些文明就都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微生物入侵者面前化为齑粉。
黑死病过去之后没多久,蒙古帝国就分崩离析了。继之而起的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从小亚细亚到巴尔干半岛的土地,并一直往南延伸到印度洋。这个帝国向从远东到西方的贸易征收过路费,于是欧洲的冒险家变得越来越喜欢考虑沿着另一条路线——从海上抵达东方,得到丝绸和香料。试想拿马或是骆驼的运力跟哪怕是相当普通的一艘船做个比较,显然从海上长途运输货物比追随马可·波罗穿越欧亚大草原所需要的时间更短,也不用那么辛苦,不用到处跟人谈判。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对《马可·波罗游记》爱不释手,这本书也帮助他开启了自己的冒险之旅。
 葡萄牙探险家在计划着绕过非洲抵达印度洋的路线,而哥伦布设想中的路线更加直接——直接穿过大西洋抵达“契丹”(这是中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诸多叫法之一)。但他的第一次航行既没有发现中国和香料,也没有发现大量黄金,而是带回了黄铁矿——愚人金——以及树皮,而非桂皮,辣椒,而非胡椒。
葡萄牙探险家在计划着绕过非洲抵达印度洋的路线,而哥伦布设想中的路线更加直接——直接穿过大西洋抵达“契丹”(这是中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诸多叫法之一)。但他的第一次航行既没有发现中国和香料,也没有发现大量黄金,而是带回了黄铁矿——愚人金——以及树皮,而非桂皮,辣椒,而非胡椒。

哥伦布也发现了一些人,觉得他们“体格健壮、面容俊美……整体来讲高高大大的,四肢纤细、身材匀称”。他还记录:“他们手无寸铁……所有居民都很容易就可以被带到西班牙去,或是留在岛上当奴隶,因为只需要50个人,我们就可以征服他们所有人,让他们唯命是从。”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他告诉自己的王室赞助人,如果再组织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远征,他可以做得更多:“只说这次非常仓促的远征带来的结果,各位殿下可以看到,他们想要多少黄金,我就能给他们多少……当然,他们想要的香料和棉布,无论要多少,我也都能给他们。”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他告诉自己的王室赞助人,如果再组织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远征,他可以做得更多:“只说这次非常仓促的远征带来的结果,各位殿下可以看到,他们想要多少黄金,我就能给他们多少……当然,他们想要的香料和棉布,无论要多少,我也都能给他们。”
虽然哥伦布第二次远航之后未能兑现其承诺,但随着时间推移,美洲将把他的承诺全都补足,甚至比那还要慷慨得多。
 但是,新大陆的人们将为哥伦布的野心付出的代价,在这位探险家第一次返航的路上就有所体现:哥伦布带了七名被当作奴隶的美洲人回西班牙,既用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也为了给下次远征当翻译,但只有两人熬过了这段航程。
但是,新大陆的人们将为哥伦布的野心付出的代价,在这位探险家第一次返航的路上就有所体现:哥伦布带了七名被当作奴隶的美洲人回西班牙,既用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也为了给下次远征当翻译,但只有两人熬过了这段航程。
包括哥伦布在内的欧洲人,刚开始描述美洲原住民的时候都称赞他们身体很好、很强壮,而美洲印第安人则彼此传说,欧洲人个子很小,闻着很臭,还体弱多病。最后这一点非常确切,但也极为致命,因为他们这些闯入者把这些疾病都传染给了毫不知情,也不会心甘情愿的宿主。与此同时,西班牙征服者虽说也要长途跋涉穿过新大陆,但他们病死的人数并没有大幅增加——美洲人身上没有多少他们此前从未接触过的一系列新的致命传染病。一位西班牙定居者1502年来到伊斯帕尼奥拉岛。18年后,他回顾了一下岛上这些年发生的变化。据埃尔南多·戈尔洪记载,很多西班牙人都已经离开,然而大部分原住民都因“他们传染给印第安人的天花、麻疹、流感和其他疾病”而丧命。

欧洲人“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死亡人数随着西班牙人迁往新大陆而不断攀升。西班牙征服者、总督书记员埃尔南·科尔特斯于16世纪初第一次登上尤卡坦半岛时,墨西哥中部仍然有1 600万到2 500万人。1519年,他率领1 200名西班牙士兵进入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受到了帝国皇帝蒙提祖马的欢迎。结果,科尔特斯将国王抓住,囚禁在水面王宫里,但也没囚禁多久,因为国王很快就死了。蒙提祖马的弟弟库伊特拉瓦克很快起来为国王报仇,然而科尔特斯侥天之幸,在深夜带着剩下的一半兵力通过一座临时搭建的桥逃脱了。但库伊特拉瓦克并没有乘胜追击,也许是因为科尔特斯登上新大陆前后这几个月里激增的极其凶险的传染病疫情已经让他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有些疾病可能搭乘了首批从非洲驶向新大陆的西班牙奴隶运输船。

因此,两年后,科尔特斯在当地盟友的帮助下第二次尝试征服阿兹特克帝国时,他最重要的武器已经部署完毕:传染病正在肆意摧残他的对手,杀死了多达一半的人口——就连新任国王库伊特拉瓦克也已经在1520年病故。
 《喀克其奎语年鉴》中记录了生活在今天危地马拉的玛雅人的生活,其中描写道:“尸体的臭味非常浓烈。我们的父辈祖辈纷纷死于疾病,半数人都逃到了旷野中。豺狗和秃鹫贪婪地吞食着尸体。”
《喀克其奎语年鉴》中记录了生活在今天危地马拉的玛雅人的生活,其中描写道:“尸体的臭味非常浓烈。我们的父辈祖辈纷纷死于疾病,半数人都逃到了旷野中。豺狗和秃鹫贪婪地吞食着尸体。”
 科尔特斯率领军队抵达特诺奇蒂特兰后,打败了剩下的反对力量——尽管幸存下来的人也很多,但科尔特斯在抵达当天就一举屠杀了四万余人。死亡枕藉,尸横遍野,这位探险家自吹自擂道:“我们不得不踩着尸体走路。”
科尔特斯率领军队抵达特诺奇蒂特兰后,打败了剩下的反对力量——尽管幸存下来的人也很多,但科尔特斯在抵达当天就一举屠杀了四万余人。死亡枕藉,尸横遍野,这位探险家自吹自擂道:“我们不得不踩着尸体走路。”

科尔特斯的胜利告诉我们,新殖民者的残暴对这些传染病来说堪称为虎作伥。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仅仅10年就来到了这里。1502年,18岁的他成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地主,还拥有了一些奴隶。8年后,他被任命为牧师,但也是在这一年,多明我会修士拒绝接受他的忏悔,因为他是奴隶主。尽管要等到4年以后,但多明我会的信息到底还是产生了影响:1514年,卡萨斯开始认为,对当地人大肆杀伐,或是奴役他们,这么可怕的方式恐怕不是基督教应该采取的。他的余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让他们得到更好的对待而奔走。1542年,他写下了《西印度毁灭述略》,介绍了侵略者发起的“邪恶、残忍、血腥、暴虐”的战争。他控诉道:“只留妇孺的活口,是西班牙人在战争中的习惯。”接着,他又补充描述了他们对劫后余生的人们的压迫:“这是人类或畜生所能受到的最严厉、最恶劣、最令人发指的奴役。”
 到1620-1625年,在天花、鼠疫和麻疹等疾病轮番侵袭之后,再加上暴力和虐待,墨西哥中部的人口数量呈断崖式下跌。
到1620-1625年,在天花、鼠疫和麻疹等疾病轮番侵袭之后,再加上暴力和虐待,墨西哥中部的人口数量呈断崖式下跌。
欧洲传来的疾病比欧洲探险家走得更快更远。这意味着到征服者和殖民者到来的时候,南北美洲的本土文明已经疲弱不堪,乃至分崩离析。
 例如,欧洲疾病在感染了阿兹特克帝国后又大举南下,在印加帝国的道路上横冲直撞。1524年,天花来到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不仅消灭了皇族,而且夺走了数千名壮士的性命。印加文明因此陷入水深火热的内战旋涡。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借此机会,于1532年俘虏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瓦尔帕。
例如,欧洲疾病在感染了阿兹特克帝国后又大举南下,在印加帝国的道路上横冲直撞。1524年,天花来到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不仅消灭了皇族,而且夺走了数千名壮士的性命。印加文明因此陷入水深火热的内战旋涡。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借此机会,于1532年俘虏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瓦尔帕。
1541年,皮萨罗同父异母的兄弟贡萨洛率领一支探险队进入亚马孙,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虽然他没能找到黄金之城,但他的副手弗朗西斯科·德·奥雷亚纳倒是成了首位在亚马孙河上航行的欧洲人。陪同奥雷亚纳的一位多明我会牧师写道,“我们走得越远”,大河两岸的土地上“人烟就越是稠密”,各个村庄鸡犬相闻,还有无数的大城市。看来在1492年以前,亚马孙河及其主要支流两边约80千米乃至更宽的范围内可能都有很稠密的人口,一直延伸到秘鲁和安第斯山脚下,而那里距离海岸线4 000多千米之遥。

传染病在亚马孙河沿岸造成的破坏规模极大,可以说这些疾病在美洲做到了黑死病在欧洲没能做到的事情:整个社会彻底崩溃。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一夜之间回到石器时代的森林生活,今天我们可以在像是雅诺马马人部落这样的“世外桃源”中找到他们的后代。认为文明发展总会因热带气候而停滞不前的观点,在亚马孙盆地根本不成立。在这里,文明的发展是被逆转了,部分原因是旧大陆的疾病来到这里之后,在热带气候下反而大显神威。

当然,这样的逆转并没有局限在南美洲和中美洲。查尔斯·曼恩认为,在哥伦布时代以前,多达三分之二的美国领土上已经出现了农业。刘易斯和克拉克在为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远征时遇到的那些星罗棋布的村落,就是大规模的农耕文明被疫病摧毁之后留下的遗迹。
在很多殖民者看来,在疫病方面占尽优势是上天赐给他们的恩惠。朝圣者和传教士们都认为,天花疫情杀死那么多美洲原住民,是“上帝仁慈的大手”进行的干预——全知全能的上帝借此表示,他“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土地让给新来的人”。
 上苍这样表示首肯,也就说明剥削他们是顺天法理,而西班牙殖民者也确实很依赖本地原住民提供廉价的奴隶劳动力——虽然后来西班牙国王禁止殖民者直接奴役这些人。
上苍这样表示首肯,也就说明剥削他们是顺天法理,而西班牙殖民者也确实很依赖本地原住民提供廉价的奴隶劳动力——虽然后来西班牙国王禁止殖民者直接奴役这些人。
原住民人口数量在传染病的重压下一落千丈,殖民者别无选择,只能到其他地方找人来开采金属矿,收获烟草和甘蔗。在新大陆的有些地方,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契约工:根据契约,欧洲人必须为种植园主人工作,直到还清他们跨越大西洋的旅程所需的费用为止。一直到17世纪中叶,弗吉尼亚的定居者中仍有四分之三左右是有契约义务在身的人,加勒比海地区田地里的劳力也一大半都是。
从殖民早期开始,欧洲人就一并引入了非洲奴隶和仆役,用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奴隶贩子打广告的时候经常说,他们的商品身上有天花幸存者留下的伤疤,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再次被感染。但是,奴隶身上也带着不少热带疾病,而这些疾病不仅会杀死美洲原住民,对殖民者来说也是致命的。
到17世纪末,疟疾更致命的一种形式——恶性疟疾,已经从非洲传入美洲。一起到来的还有黄热病,它会让人先是因头痛和肌肉痛而卧床不起,随后吐出大量黑色的呕吐物,遭受一阵阵精神错乱,陷入昏迷,最后一命呜呼。殖民者的死亡率一路攀升,找到新的契约工变得越来越难,对奴隶的需求进一步增加。
即便奴隶们在三角贸易横跨大西洋的“中间通道”中能够幸免于难,也仍会受到比牲口还不如的待遇。任何人只要想逃跑,就要么会被活活烧死,要么会被挂在绞刑架上示众,直到腐烂。
 挨打、遭强暴和营养不良,是留下来的那些人的命运。海地岛上的一名奴隶描述了这样的情形:“他们不是会把人吊死,装在麻袋里淹死,在木板上钉死,活埋,甚至直接炮决吗?他们不是还会强迫他们吃屎吗?”
挨打、遭强暴和营养不良,是留下来的那些人的命运。海地岛上的一名奴隶描述了这样的情形:“他们不是会把人吊死,装在麻袋里淹死,在木板上钉死,活埋,甚至直接炮决吗?他们不是还会强迫他们吃屎吗?”

但是,尽管这些奴隶的生活条件如此不堪,跟欧洲人和美洲原住民比起来,他们患上恶性疟疾的可能性还是要小得多,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恶性疟原虫的“洗礼”,而且由于镰状细胞的特性,有些奴隶生来就对疟疾有更强的抵抗力。在殖民地时期驻守牙买加的英国士兵中,欧洲血统的死亡率比非洲血统的要高两倍多,而疟疾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因素。
 来自疟疾横行地区的奴隶抵抗力更强,这一点很快也变得显而易见:在拍卖时,这些受奴役的工人逐渐被抬到了特别高的价格,甚至能高出六成之多。
来自疟疾横行地区的奴隶抵抗力更强,这一点很快也变得显而易见:在拍卖时,这些受奴役的工人逐渐被抬到了特别高的价格,甚至能高出六成之多。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埃莱娜·埃斯波西托揭示了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方,奴隶也越多。在美国境内的不同县份也同样如此,患恶性疟疾风险越高的地方,输入的奴隶也越多。
 埃斯波西托指出,就算一直到1860年,从患恶性疟疾风险非常低的地方到风险非常高的地方,奴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都仍会高出至少四分之一。
埃斯波西托指出,就算一直到1860年,从患恶性疟疾风险非常低的地方到风险非常高的地方,奴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都仍会高出至少四分之一。
在更北边,气候并不适合热带疾病,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那些欧洲人会比他们待在旧大陆臭气熏天的村庄和城镇里时更健康。而且,因为他们已经在会在寒冷气候中滋生的传染病(比如说流感、百日咳和麻疹等)中历练过,所以也比非洲奴隶更能适应新出现的疾病生态。
 从1620年到1642年,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的英国人中只有二十分之一把新英格兰当作目的地。但在这些刚刚变得简直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不但活了下来,而且繁荣兴旺,而不是疾病缠身。
从1620年到1642年,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的英国人中只有二十分之一把新英格兰当作目的地。但在这些刚刚变得简直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不但活了下来,而且繁荣兴旺,而不是疾病缠身。
科尔特斯在天花的助攻下取得重大胜利一个世纪后,朝圣先辈们也得到了跟科尔特斯差不多的好处:就在“五月花号”抵达前一两年,一场流行病几乎把马萨诸塞地区的阿尔冈昆人赶尽杀绝。
 于是有了大片大片人烟稀少、预先开发过又非常容易从得了天花的阿尔冈昆人手中夺取的土地,朝圣者的人数很快成倍增加。马尔萨斯牧师之所以写下《人口原理》,部分原因是受北美殖民者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启发。他估计,那里的人口数量每25年就会翻一番。
于是有了大片大片人烟稀少、预先开发过又非常容易从得了天花的阿尔冈昆人手中夺取的土地,朝圣者的人数很快成倍增加。马尔萨斯牧师之所以写下《人口原理》,部分原因是受北美殖民者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启发。他估计,那里的人口数量每25年就会翻一番。
 如果他知道这样的人口增长背后的所有因素,也许会对疫病控制人口的作用有更好的认识。
如果他知道这样的人口增长背后的所有因素,也许会对疫病控制人口的作用有更好的认识。

到最后,无论是在南美洲还是北美洲,旧大陆的人和疾病几乎完全取代了美洲原住民。截至2000年,“新大陆”部分地区完全由来自旧大陆的人组成,包括牙买加和海地。还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古巴、阿根廷和巴西——新大陆原住民的后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10%。旧大陆后裔只占少数的美洲国家屈指可数。

美洲人口锐减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对劳动力来源地产生了剧烈影响,尽管他们全都不情不愿。实际上,历史会证明,奴隶贸易只是欧洲帝国主义对非洲重拳出击的开始。非洲的文明,就这样被一扫而空。
1482年,葡萄牙探险家迪奥戈·康探索了非洲第二大河流刚果河的河口,还跟刚果国王的代表见了面。到了1526年,刚果国王阿方索就已经落得只能向葡萄牙国王写信乞怜,希望他管管奴隶贩子在刚果的所作所为:
奴隶贩子每天都在抢走我们的亲人、我们这片土地的儿女、我们的贵族、我们的封臣、我们亲属的子女,因为那些小偷,那些坏良心的人……抓走他们,把他们卖出去;陛下啊,他们是那么腐败堕落、那么道德败坏,我们国家的人口正在归零。

刚果国王要求控制奴隶贸易的呼吁被置若罔闻——实际上,奴隶贸易还在迅速扩大。15到19世纪,有1 200万名奴隶被运出非洲——尽管这还是比死于征服者的疫病大军的美洲原住民人数少,但也已经相当于17世纪英国人口的两倍。

最终的结果就是,刚果等王国瓦解了。贩奴活动不仅是王国和王国之间的对抗,也是村庄和村庄之间的对抗,大家都在争相抓获足够多的奴隶,卖了换成武器。这既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以后可以抓到更多奴隶。奴隶贩子向因传染病而失去人口的新大陆提供劳动力,是让这些王国和村庄陷入霍布斯陷阱的最好方式——尽管他们也许并非有意为之。
另外,奴隶贸易本身也会传播传染病,也许最终死于这个原因的人比登上贩奴船的人还多。在欧洲人开始探险和贩奴之前,贸易路线就已经在非洲大陆上纵横延伸好几百年了。但是,这些路线运转的基础是一个中继体系——货物会由当地人运送到他们控制区域的边缘,然后转交给来自另一个民族的搬运工往下转运。这个办法可能是为了避免传播疾病而演变出来的。
 当然,这么做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让非洲大陆保留了好多种疾病,成了一个死水微澜的疫病池。
当然,这么做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让非洲大陆保留了好多种疾病,成了一个死水微澜的疫病池。
这样一棒接一棒的中继体系显然不适合贩奴活动,因为把人运来运去正是这种贸易活动的精髓。其结果就是,天花在非洲大陆传播开来,恶性疟疾可能也是借由同样的路线扩大了自己的范围。有人估计,如果没有受奴隶贸易的影响,19世纪中期的非洲人口会是实际情形的两倍。
包括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殖民带来的疫病负担可以解释当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异。这是因为在殖民者会很快因疫病而丧命的地方(包括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留下来的制度都更适合少数的精英阶层在疫病威胁面前撤退时尽快捞一把就走。
 这些制度在去殖民化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让本来就在日益恶化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同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内森·努恩也指出:“今天非洲最贫困的那些国家,正是当年被抢走奴隶最多的国家。”
这些制度在去殖民化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让本来就在日益恶化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同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内森·努恩也指出:“今天非洲最贫困的那些国家,正是当年被抢走奴隶最多的国家。”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斯特利奥斯·米哈洛普洛斯和埃利亚斯·帕帕约安努的研究同样指出,非洲那些在殖民时代以前由强大的中央政权管辖的地区今天也更加富有。
 他们对一个地区有多富裕的衡量标准是,夜晚从太空中能看到多少灯光——路灯更多、从窗户里散发出的房屋内的光线也更多的地方,比路上没有路灯、屋子里也黑洞洞的地方要富裕得多。结果表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地方的人均收入是个很好的指标。几百年前由更强大的国家统治的地方,现在的晚上也会更明亮。考虑到奴隶贸易对这些殖民时代以前的非洲国家的可怕影响,要是有外星人造访地球,他们不需要落地就能看到,奴隶贸易以及在奴隶贸易刺激下到处传播的传染性疾病留下了什么遗产。
他们对一个地区有多富裕的衡量标准是,夜晚从太空中能看到多少灯光——路灯更多、从窗户里散发出的房屋内的光线也更多的地方,比路上没有路灯、屋子里也黑洞洞的地方要富裕得多。结果表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地方的人均收入是个很好的指标。几百年前由更强大的国家统治的地方,现在的晚上也会更明亮。考虑到奴隶贸易对这些殖民时代以前的非洲国家的可怕影响,要是有外星人造访地球,他们不需要落地就能看到,奴隶贸易以及在奴隶贸易刺激下到处传播的传染性疾病留下了什么遗产。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是真正世界性大流行威胁时代的开始。性病梅毒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这很可能是由哥伦布第一次远航中的水手带回欧洲的一种新大陆疾病。
 在最早侵袭欧洲时,这种疾病的毒性比现在要大得多,会导致溃疡、肿瘤和剧痛,也经常令患者一命呜呼。
在最早侵袭欧洲时,这种疾病的毒性比现在要大得多,会导致溃疡、肿瘤和剧痛,也经常令患者一命呜呼。
 梅毒于1499年传到了中东,10年后传到了中国。
梅毒于1499年传到了中东,10年后传到了中国。
 这也是本来死水微澜的全球疫病池越来越浑然一体的迹象之一。印度受到梅毒的侵袭要快得多,是在1498年,
这也是本来死水微澜的全球疫病池越来越浑然一体的迹象之一。印度受到梅毒的侵袭要快得多,是在1498年,
 这是因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5年后,瓦斯科·达伽马成为现代第一个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欧洲人,而在他的船员中,不乏梅毒患者。
这是因为在哥伦布发现美洲5年后,瓦斯科·达伽马成为现代第一个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欧洲人,而在他的船员中,不乏梅毒患者。
欧洲的帆船环绕地球航行的时候,路过的岛屿也一个接一个遭受了传染病暴发的类似后果。探险时代的最后一个大发现出现在1769年。那一年,詹姆斯·库克在澳大利亚登陆,开启了最后一次对整片大陆上从未为人所知的人群的大规模杀戮。北美人口的重新填充靠的是奴隶和契约工,澳大利亚则是从英国罪犯开始的。其间差异,对当地原住民来说区别不大。跟北美幸存下来的原住民一样,澳大利亚原住民最后也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今天,他们的收入、教育和健康水平处于全面劣势,想要翻身难于上青天。
日本在全球微生物大交换带来的世界末日面前又坚守了90年,部分原因是日本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闭关锁国,几乎全面禁止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旅行和贸易往来。疫病负担较轻,是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的重要原因。江户城在18世纪初约有100万人口,比当时伦敦的人口还要多很多。
 但是到了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船驶进东京湾,第二年又带着一支规模更大的海军舰队返回,与含垢忍辱的江户幕府签署了《神奈川条约》(又名《日米和亲条约》),要求日本开放两个港口,给美国船只加煤,并提供补给。疾病接踵而至,流行性斑疹伤寒和腺鼠疫纷至沓来。
但是到了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四艘船驶进东京湾,第二年又带着一支规模更大的海军舰队返回,与含垢忍辱的江户幕府签署了《神奈川条约》(又名《日米和亲条约》),要求日本开放两个港口,给美国船只加煤,并提供补给。疾病接踵而至,流行性斑疹伤寒和腺鼠疫纷至沓来。

但是,全球化与传染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疾病会限制城市的发展,同样也会限制帝国的成长。这是因为从最早的帝国开始,远离家乡出征异国的军队都特别容易感染疾病——既有所到之处的本土微生物作祟,也有总是会让聚在一起却没有足够好的卫生条件的人不堪其扰的传染病。
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对军队杀伤力最大的都是传染病,死于传染病的兵员远远超过在战斗中受伤而死亡的人。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汉斯·津瑟于1935年就传染性疾病对历史的影响撰写了一部既引人入胜又富有开创性的研究专著,他在书中写道:
从事实的角度观照,行军、射击乃至我们称为战略战术的各种技巧,都只是战争悲剧的一部分——虽然栩栩如生、引人注目,但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些只不过是在营地流行病中幸存下来的残余部队所进行的扫尾行动。

古代世界的圣贤也都非常清楚营地不够卫生会有什么危险。按照《申命记》(23:12-14)中的记录,摩西在保持营地清洁这个问题上非常严苛,他说:“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
但是,只关心营地清洁问题并不足以解决历史上大量士兵死于传染病的问题。举个例子,前后有三次十字军东征,就分别因三种不同的疾病而裹足不前:鼠疫、痢疾和伤寒。1098年到1099年,一支占领了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军队从30万人减员到6万人,主要原因就是传染病。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50多万人的军队,也几乎都因类似的原因而殒命。

还不仅仅是军队,甚至带给军队的伤亡都不算什么:17世纪由德国的宗教冲突引发的“三十年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它是由远远没那么致命的微生物大军如影随形造成的大屠杀。法国的死亡率可能翻了一番,而神圣罗马帝国这边损失了五六百万人,超过整个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斑疹伤寒和鼠疫一样,也是历史上最杀人如麻的杀手之一。这种疾病于15世纪末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并很快成为能击垮大军的特别有效的武器(尽管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三十年战争”等战争冲突中大显神威。斑疹伤寒靠虱子传播,比如体虱,也可以叫衣虱。受感染的虱子通过叮咬宿主填饱自己肚子时还会排出满是细菌的粪便,受害者如果抓挠被叮咬过后发痒的地方,就会将虱子的粪便涂到被挠破的伤口上。
这对宿主来说糟糕透顶,然而对虱子来说,这也同样不是什么赏心乐事。汉斯·津瑟满怀同情地写道:
要是虱子会害怕,它们生命中的梦魇必定是害怕有一天会住在被感染的老鼠或人身上。因为宿主有可能活下来,但这只倒霉的虱子要用自己的吸器刺穿受感染者的皮肤,吸入讨厌的病毒作为自己的营养,因此注定回天乏术。8天后,这只虱子就会生病;10天后,来到鬼门关;十一二天的时候,它那小小的身躯会变红,因为血在从它体内渗出来,而它的小命这时候也就玩儿完了。

斑疹伤寒细菌会在小血管的内壁繁衍生息,受到感染的细胞会脱落下来,堵住血管,阻塞血液流动,让血管周围的组织得不到营养和氧,导致血管破裂。患者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会打寒战、发烧、头疼,还会起疹子,随后是背痛、咳嗽、失眠,到最后关头则是神志不清、陷入昏迷,最后死去。三十年战争期间,斑疹伤寒是由军队散播到各地的,他们濒临绝望,不讲卫生,缺衣少食,又掠夺成性。在宗教分歧中站错队的当地民众对他们恨之入骨。

欧洲人在热带的殖民活动一直到19世纪都还很有限,面临疫病的威胁也是原因之一。1805年,苏格兰探险家芒戈·帕克带领一支探险队前往今西非马里共和国的廷巴克图,结果这支40多人的欧洲探险队只回来了两个人,其他人都死于传染性疾病。这个结果远远说不上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19世纪20年代,驻扎在本土的英国军队的死亡率约为千分之十五,而印度驻军的死亡率是其2~5倍,西印度群岛是其6~9倍,西非则是其32~45倍。驻扎在西非的英国军队,每年大概有一半人会死掉——几乎都是病死的。
 只有在有可能得到高额回报(比如制糖业)或接触有限(比如非洲奴隶贸易)的情况下,冒着死亡的风险才值得。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型殖民地政府在热带的很多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士兵死得太快了,无法保证控制权。
只有在有可能得到高额回报(比如制糖业)或接触有限(比如非洲奴隶贸易)的情况下,冒着死亡的风险才值得。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型殖民地政府在热带的很多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士兵死得太快了,无法保证控制权。
拿破仑一世皇帝可能是最后一个看到踏平全球的野心被微生物击得粉碎的伟大帝王。他成功将自己的统治强加给西班牙、瑞士、意大利诸邦国、普鲁士、瑞典和奥地利,或者说让这些国家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国,并将法国的边界扩大,向北一直延伸到丹麦,向南则抵达了意大利南部的山麓。但他的野心比这个范围还要大得多——拿破仑曾梦想建立一个巨大的帝国,国土从路易斯安那的海湾一直延伸到欧亚大草原上的俄罗斯平原,以及尼罗河上游。但在这三个地理上最遥远的地方,他的军队都被疫病摧残得溃不成军。1798年,拿破仑将军侵入埃及和叙利亚,但这次冒险并不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光辉的一笔。瘟疫令他军中的数千名士兵丧命,再加上计划极不周全,也缺乏装备,这次军事行动最后只能草草收兵。1801年,在英国军队的帮助下,埃及回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怀抱。
就在同一年,拿破仑派自己的妹夫维克托——埃马纽埃尔带领两万名士兵前往海地,镇压杜桑·卢维杜尔的奴隶起义。卢维杜尔以前是一名奴隶,数年前开始起兵反抗帝国统治。拿破仑想把海地当成去密西西比河河谷建立殖民地的基地。维克托——埃马纽埃尔·勒克莱尔将军刚开始连战连捷,取得了巨大胜利,但1802年1到4月,他自己、他这支部队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员,还有增援部队中的三万多人,都因黄热病而丧命。
 1803年,海地的战争失败了。拿破仑放弃了美洲的殖民地,把路易斯安那的领土以1 500万美元的超低价格卖给了美国。
1803年,海地的战争失败了。拿破仑放弃了美洲的殖民地,把路易斯安那的领土以1 500万美元的超低价格卖给了美国。
接下来10年,拿破仑在欧洲的命运相对来讲要好很多。到1812年,帝国及其附属国的疆域已经东至波兰首都华沙,西至西班牙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但也是在那一年,他进军俄国的行动主要因斑疹伤寒而受阻。那年6月,渡过涅曼河进入俄国的军队约有50万之众,但12月渡河而还的可能只有两万人。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斑疹伤寒是众所周知的疫病威胁。皇帝在波兰行军时,军医就告诫过他,当地正在流行这种疾病。于是,拿破仑命令自己的士兵不得接触波兰人。但军队后方的给养列车陷在不适合重型货车行驶的道路上动弹不得,部队总得自己去找些吃的。这时候,皇帝的命令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雅各布·沃尔特是位石匠,也被征召加入了拿破仑的军队。后来他写了一部自传,描述了自己随大军出征俄国的经历。他说,部队在抵达俄国边境时已经饥肠辘辘,甚至把活猪身上的肉切下来生吃。进入俄国三天后,他们在一片无法找到任何粮草和燃料的沼泽中行军,沃尔特“躺在帐篷里,浑身湿透,饥寒交迫”。但很快他就感到喜出望外,因为其他同袍“走了进来,躺在我身上,成了一层暖和的被子”。
 不用想,他们身上的虱子也会有完全一样的感觉。
不用想,他们身上的虱子也会有完全一样的感觉。
根据皇帝的总医官多米尼克——让·拉里医生的记录,有6万人经他们的司令官认定为已患病,但实际数字可能是它的两倍。
 痢疾、肝炎以及很多其他疾病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只有斑疹伤寒正在变成流行病。到8月中旬,也就是进军开始刚刚两个月的时候,法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就已经只剩下6月份时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而且这样的减员在他们发起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前就已经发生。
痢疾、肝炎以及很多其他疾病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只有斑疹伤寒正在变成流行病。到8月中旬,也就是进军开始刚刚两个月的时候,法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就已经只剩下6月份时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而且这样的减员在他们发起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前就已经发生。

9月7日,法军和俄军终于在博罗季诺短兵相接。美国作家斯蒂芬·塔尔蒂在描写这次进军的历史著作《光荣覆没》中写道:
到这天结束时,法军损失约28 000人……俄军损失约45 000人,差不多是他们整个前线兵力的一半……这是当时战争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遭遇战。直到100年后“一战”期间的索姆河战役,这个死亡人数才被超过。
但是,当俄国人最后败退时,拿破仑并没能摧毁他们的军队,也没能让俄国人达成城下之盟。塔尔蒂指出,斑疹伤寒带走了拿破仑要取得决定性胜利所需要的军队,“同时带走的还有这场战役、整个战争,以及帝国的未来”。

可以想象一下,博罗季诺战役后法军这边的战地医院是什么场景:光是总医官拉里医生自己,在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做了200例截肢手术。在每例手术之间,甚至在每两个病人之间,他几乎没有工夫停下来擦一擦手术器械。开膛破肚的伤口多半会被直接认定为太凶险,无法手术。伤员就搁在那儿等着恢复——或者说等死。对于那些遭到炮击,连内脏都给炸出来了的人,医生会把一团糟的肠子尽可能清理干净,塞回体内,然后用亚麻绷带包起来。房间里到处都是失去了消化道(或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消化道)的人的粪便,与之相伴相随的还有坏疽散发出来的恶臭。空气中也都是未经麻醉的伤员在被外科医生用已经钝了的锯子锯掉一只胳膊或一条腿时惨烈的尖叫,而锯齿间也许还残留着上一个伤员的软骨和骨头。挨着墙边的是那些已经神志不清的斑疹伤寒患者,他们也已经到了这种疾病的最后关头,只会让这个地方更加嘈杂。那些遭受痛苦的人死后,虱子大军会带着疾病找到新的宿主。那些即便足够幸运没有因伤口或医生的锯子而严重感染的伤员,面对这支大军往往也在劫难逃。
拿破仑继续向莫斯科进军。步兵雅各布·沃尔特记录道,城市周围有大量甜菜和卷心菜可供食用。在寒冷的天气里,他们也可以稍事休息,但全都好景不长。
 俄国完全没有缴械投降的意思,法军只能驻扎下来。又过了几周,在疾病、营养不良和饥饿侵袭下出现了更多减员之后,皇帝下令撤军,将数千名伤病员弃之不顾,听任即将回归的俄国政府处置。在终于开始长途跋涉返回德国时,他的军队已经只剩下7.5万人,还不到开始进军时的六分之一。
俄国完全没有缴械投降的意思,法军只能驻扎下来。又过了几周,在疾病、营养不良和饥饿侵袭下出现了更多减员之后,皇帝下令撤军,将数千名伤病员弃之不顾,听任即将回归的俄国政府处置。在终于开始长途跋涉返回德国时,他的军队已经只剩下7.5万人,还不到开始进军时的六分之一。
法国军队艰难地穿过贫瘠的田野,这里就算曾有什么出产,也已经在他们进军时就已被搜刮干净。气温继续下降,俄国军队也紧追不舍,每天都在对撤退中的法军发起攻击。所有人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只有寄生虫反而得其所哉。沃尔特写道:“战斗、尖叫、大大小小的枪炮开火的声音,我们又饥又渴,所有能想到的折磨,都令永无休止的混乱加剧。实际上,就连虱子都似乎在争夺控制权,无论是军官还是列兵,身上的虱子都有成千上万只。”
 沃尔特的少校叫他帮忙弄死自己衬衣领子里的虱子,“但是我解开他的领口之后,看到他的皮肉上全是贪婪的小野兽咬下的伤口,我感到一阵阵恶心,不得不把目光移开”。在认识到自己身上也同样长满了虱子之后,沃尔特试图用一句格言来安慰自己:“虱子只会长在健康的人身上。”
沃尔特的少校叫他帮忙弄死自己衬衣领子里的虱子,“但是我解开他的领口之后,看到他的皮肉上全是贪婪的小野兽咬下的伤口,我感到一阵阵恶心,不得不把目光移开”。在认识到自己身上也同样长满了虱子之后,沃尔特试图用一句格言来安慰自己:“虱子只会长在健康的人身上。”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是撤退的终点。只有2.5万人抵达这座城市,接下来能够离开这座城市的,更是只有3 000人。2001年8月,维尔纽斯的建筑工人打算拆除以前的一座苏联军营。在清理地基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丛葬墓——在将近20米见方的一块土地上,每平方米有7具尸体,总数有两三千具。这些尸体仍然穿着法兰西帝国军队的制服,不过已经变成了碎片。地中海大学(艾克斯-马赛第二大学,现已与另外几所大学合并为艾克斯-马赛大学)的研究人员详细检查了这些尸体,想找出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士兵殒命。这些科学家发现,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人感染过由虱子传播的疾病。

沃尔特记录道,他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但在他经过德国符腾堡回家时,“大家看我们就像看麻风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他们还被一起锁在一栋房子里。这么做也于事无补——德国死于军队从波兰和普里佩特沼泽带回来的斑疹伤寒的人多达25万。
 沃尔特自己也经历了一场热病,不过最后还是恢复了,他自认为是多亏用醋和放血疗法来治疗。因伤残退伍后,他至少活到了1856年——这在拿破仑的侵略大军中是个非常幸运的例外。拿破仑自己孤注一掷,继续战斗了三年,直到最后在滑铁卢一役中兵败如山倒,他建立全球帝国的梦想也化为泡影,最后落得被监禁在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上的郎伍德府中,了此残生。
沃尔特自己也经历了一场热病,不过最后还是恢复了,他自认为是多亏用醋和放血疗法来治疗。因伤残退伍后,他至少活到了1856年——这在拿破仑的侵略大军中是个非常幸运的例外。拿破仑自己孤注一掷,继续战斗了三年,直到最后在滑铁卢一役中兵败如山倒,他建立全球帝国的梦想也化为泡影,最后落得被监禁在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上的郎伍德府中,了此残生。
如果说文明造就了疫病的大风暴,那么也可以说疫病限制了城市化的规模。而如果说全球化搅浑了疫病池,那么也可以说疫病池对殖民和商业的性质和范围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应对传染病的唯一有效的方式是敬而远之,这也让疫病加在我们头上的箍儿挥之不去。只有在卫生革命之后,城市化和一体化才能摆脱传染病的束缚,也只有在有了疫苗和抗生素之后,城市化和一体化的进程才能走向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