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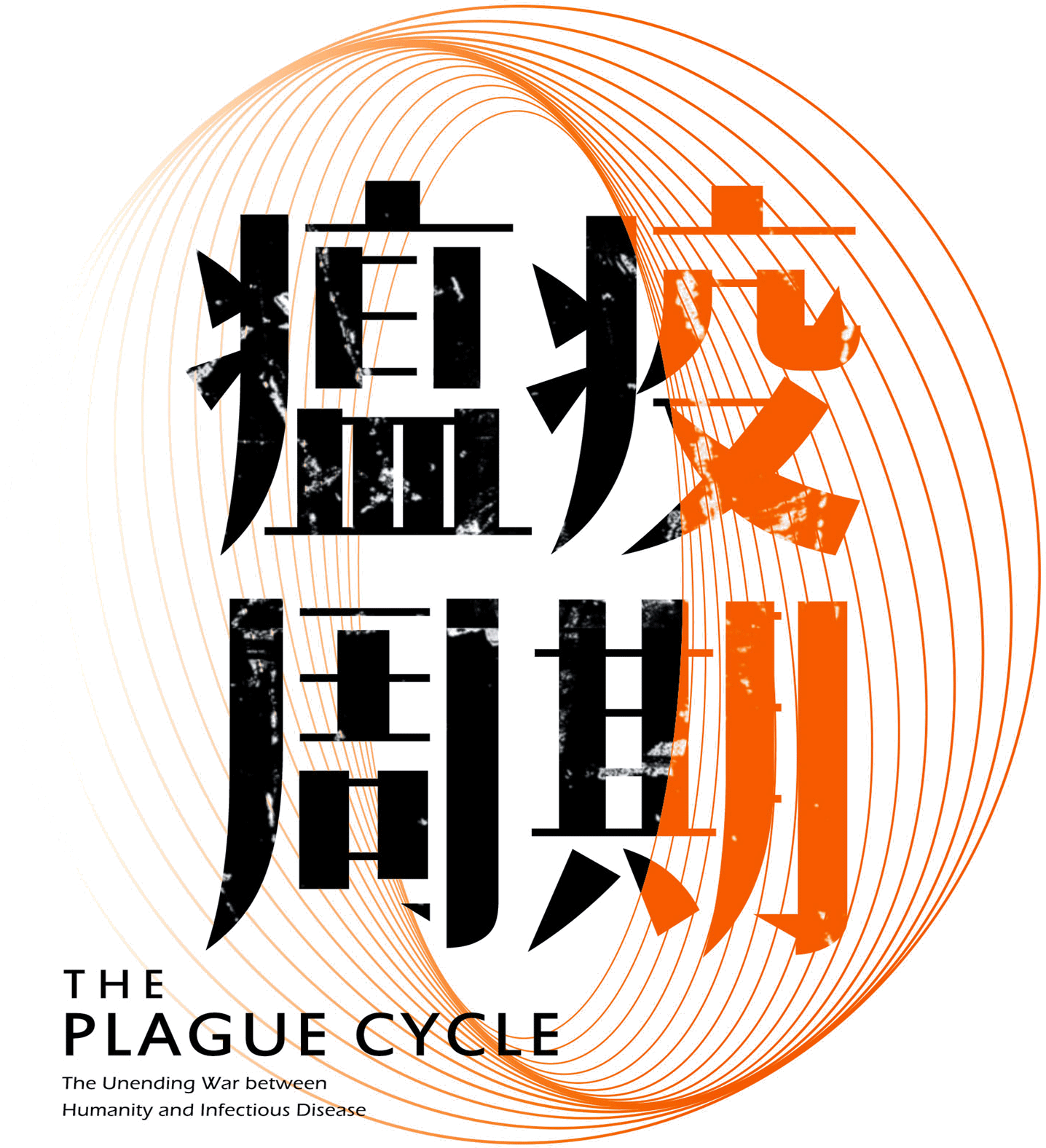
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疾病的来源很少,因此不需要任何治疗。
——卢梭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为雅典瘟疫的受害者进行治疗,但他拒绝了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的礼物。波斯同样瘟疫肆虐,国王正在寻求良方
(资料来源:《希波克拉底拒绝了阿尔塔薛西斯的礼物》,吉罗代·特里奥松,1792年。维基共享资源。)
人们管她叫“线粒体夏娃”,但她不是由上帝造出的,而是以对她的后代——我们——进行的基因分析为基础的科学理论的产物。1987年,一组人口遗传学家分析了来自全球各地147个人的线粒体DNA。我们所有人的每个细胞中都有这样的遗传密码,由母亲传给儿女,而且只来自母亲。研究人员估算了DNA突变需要多长时间,并据此计算了今天人类线粒体中全部的DNA信息如果是从单一祖先进化而来的,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进化成今天这样。在这个理论中,今天这颗星球上的所有人都是她的直系后代,而她是人类的最近的线粒体共同祖先。
根据DNA证据,我们这位共同祖先生活在10多万年前。
 那时候,线粒体夏娃可能和一个小部落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需要占领大量土地才能通过狩猎和采集找到足够食物,因此大型聚落根本不切实际。
那时候,线粒体夏娃可能和一个小部落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需要占领大量土地才能通过狩猎和采集找到足够食物,因此大型聚落根本不切实际。
 她生活的时代过去很久之后,文明的曙光才慢慢出现,农业和城市才慢慢兴起。而且在她生活的时代,这个世界上最凶险的传染病杀手——天花、麻疹和流感等疾病——都还没有进化出来,更未曾声名远播。
她生活的时代过去很久之后,文明的曙光才慢慢出现,农业和城市才慢慢兴起。而且在她生活的时代,这个世界上最凶险的传染病杀手——天花、麻疹和流感等疾病——都还没有进化出来,更未曾声名远播。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史前寄生虫困扰着人类。有个例子是麦地那龙线虫,它们现在已经快被根除了。这种虫子的幼虫漂在池塘中,直到其中少数交上好运,被剑水蚤(一种很小的水蚤)吞食。进入剑水蚤体内后,这种线虫就会开始生长,以剑水蚤的卵巢或睾丸为食,并等着它们的宿主接下来又被吞食——就是人类喝下这些水的时候。对这些剑水蚤来说,被吞掉并不怎么好受,我们人类也同样不会甘之如饴。随着剑水蚤在人体的消化液中消融,更扛得住的麦地那龙线虫幼虫会钻进人类的肠道,随后在腹壁短暂安顿下来。如果雌性幼虫找到了一条雄性幼虫,让自己受孕,这只雌性幼虫最后就会设法钻到人类的腿部,在那里安营扎寨,大吃大喝,用长达一年的时间慢慢长大——最长能长到大概90厘米长。这么长的身体里大部分是一个巨大膨胀的子宫,里面满满当当地塞着50万个胚胎。
人类宿主遭受的痛苦是,在虫子的末端有一个刺激性的水疱,破了就会露出这条虫子的子宫。伤口灼痛、瘙痒,为了缓解不适,病患经常会跌跌撞撞地走向最近的水坑,拿水来浇这个水疱。病患这么做的时候,虫子就会排出胚胎,把下一代麦地那龙线虫释放到水池里。
 临床寄生虫学家罗斯玛丽·德里斯德尔认为,这种虫子可能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蛇杖上那条暴躁的巨蛇的来历,而那根蛇杖是医疗的象征——因为移除麦地那龙线虫的传统方法是用一根棍子将虫的一端卷起来,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慢慢地将虫子的身体缠在棍子上,直到整条虫子被拉出来。
临床寄生虫学家罗斯玛丽·德里斯德尔认为,这种虫子可能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蛇杖上那条暴躁的巨蛇的来历,而那根蛇杖是医疗的象征——因为移除麦地那龙线虫的传统方法是用一根棍子将虫的一端卷起来,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慢慢地将虫子的身体缠在棍子上,直到整条虫子被拉出来。
遭遇、追猎和食用野生动物也会让早期的女性及其配偶暴露在兔热病(与腺鼠疫有关)、弓形虫病、出血热、炭疽、坏疽、肉毒中毒和破伤风面前。不用说,还有生长在这些野生动物身上的蜱虫和跳蚤(可能携带鼠疫或睡眠病),以及在患有黄热病的灵长类动物身上吃饱了之后又会跑到人身上吸一口人血当零食的蚊子。

但是,尽管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本能有巨大影响,无疑也在控制非洲最早的人口数量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它们可能并非主要因素。很多疾病在地理上很集中,而且人类特有的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杀伤力也不是很大——因为人口太少,也太分散,如果不能转而依靠大量动物受害者,很多致命疾病会难以为继。
 另外,狩猎和采集需要的人均占有土地的面积远远高于农业,而且早期人类居无定所,一直在迁徙。这会让他们远离满是寄生虫的粪便或蚊子吞噬人类同胞血液的地方,继而降低被寄生虫和蚊子感染的风险。任何疾病,如果过于致命,都会在遇到新的受害者之前杀死自己的宿主。
另外,狩猎和采集需要的人均占有土地的面积远远高于农业,而且早期人类居无定所,一直在迁徙。这会让他们远离满是寄生虫的粪便或蚊子吞噬人类同胞血液的地方,继而降低被寄生虫和蚊子感染的风险。任何疾病,如果过于致命,都会在遇到新的受害者之前杀死自己的宿主。
 这也表明,那时候人们的自然预期寿命也许相对较长。
这也表明,那时候人们的自然预期寿命也许相对较长。

有些因素会让全球人口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其一可能是狩猎——采集者的出生率并不高。历史上属于桑族部落(南部非洲的布须曼人)的女人一生会生育4~5次,跟澳大利亚原住民妇女的生育率很接近。
 来自非洲其他狩猎——采集部落(昆族和埃费族)的证据表明,活过了整个生育期的妇女一生会生育2.6~4.7次。
来自非洲其他狩猎——采集部落(昆族和埃费族)的证据表明,活过了整个生育期的妇女一生会生育2.6~4.7次。
 相比之下,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生育率在1980年接近7。石器时代的人较低的生育率也许反映了好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包括性成熟的年龄较晚、哺乳的时间更长,以及搬迁的次数要多得多。
相比之下,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生育率在1980年接近7。石器时代的人较低的生育率也许反映了好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包括性成熟的年龄较晚、哺乳的时间更长,以及搬迁的次数要多得多。

暴力在控制人口数量上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甚至可能比后来这些年代起到的作用更大。斯蒂芬·平克在他关于暴力的历史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中指出,前文明时代暴力事件的平均比例要比从那时以来我们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高,只有一个例外是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科学家研究了南加州史前狩猎——采集人群的遗骸,发现五分之一的男性骨架上有被长矛这样的投掷武器或箭伤害过的痕迹。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阿扎尔·盖特在对狩猎——采集时代战争所做的总结中,认为暴力造成的死亡在所有死亡中最多能占到15%。
中指出,前文明时代暴力事件的平均比例要比从那时以来我们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高,只有一个例外是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科学家研究了南加州史前狩猎——采集人群的遗骸,发现五分之一的男性骨架上有被长矛这样的投掷武器或箭伤害过的痕迹。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阿扎尔·盖特在对狩猎——采集时代战争所做的总结中,认为暴力造成的死亡在所有死亡中最多能占到15%。
 另一些人则认为暴力造成的死亡数量总体上没那么多,估算出来的结果因时因地有很大差异。
另一些人则认为暴力造成的死亡数量总体上没那么多,估算出来的结果因时因地有很大差异。
 但是,低出生率、暴力和确实存在的史前传染病,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全球人口数量可能只有几百万——跟今天的全球人口比起来,这不过是九牛一毛。
但是,低出生率、暴力和确实存在的史前传染病,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全球人口数量可能只有几百万——跟今天的全球人口比起来,这不过是九牛一毛。
对智人情有独钟的最早的寄生虫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热带——它们可以选择的受害者在地球上存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只生活在非洲,别的地方看不到。直到人类文明兴起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传染病时,细菌、病毒、寄生虫和其他以人类为家的有机体,都已经在非洲进化到完成它们完整的生命周期。
即使在今天,热带地区的病原体多样性(在一个地区能感染人类的不同种类微生物的数量)仍然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但是,由于这些微生物往往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大显神威,能致残甚至致死,而在这些地方生活的大部分是穷人,治疗这些疾病的新药不赚钱,所以它们并没有引起医学研究的太多注意。说来颇有些讽刺,人类身上一些最古老的寄生虫,现在都被算在了“被忽视的热带病”这个总称下面,但原因也就在这里。
但是,由于这些微生物往往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大显神威,能致残甚至致死,而在这些地方生活的大部分是穷人,治疗这些疾病的新药不赚钱,所以它们并没有引起医学研究的太多注意。说来颇有些讽刺,人类身上一些最古老的寄生虫,现在都被算在了“被忽视的热带病”这个总称下面,但原因也就在这里。
学会用火,发明衣物,让人类得以度过寒冬,也让我们有了进入温带地区生活的可能。在迁往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过程中,我们战胜了一些寄生虫。尽管全球化进程最终还是把非洲很多最早的热带病带到了这些新居的热带地区,但人类传染病在热带气候下的长期进化和集中,仍然是今天生活在热带南北两侧温带地区的人比热带地区的人健康的原因之一。

如果某种生物发现自己远离了以往通常的捕食者和猎物,有时候就会导致种群数量激增,比如日本的藤本植物葛种植在美国,以及兔子被引入澳大利亚的例子。走出热带的人类也同样受益于“生态释放”,人类新到欧洲南部和亚洲这些季风带以北的温带地区生活时,早年就属于传染病很少、猎获物很多的时期。
 这种情形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人类就遍布全球。从公元前40000年开始,在大概3万年的时间里,人类抵达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
这种情形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人类就遍布全球。从公元前40000年开始,在大概3万年的时间里,人类抵达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

由此导致的人口数量激增也许是很多大型猎物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最早的人类前去定居之前,南美洲原本是马和骆驼的家园,但这些动物很快就消失了。
 就算它们消失的原因并非如此,人口增加也意味着有更多创造力。这个因素推动了技术创新,并最终创造了农业。
就算它们消失的原因并非如此,人口增加也意味着有更多创造力。这个因素推动了技术创新,并最终创造了农业。
尽管《圣经》的前几章中没有提到瘟疫,但在开始提及埃及文明之后,就满篇都是关于瘟疫的故事了——不仅有青蛙带来的灾害,还有虱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以及各种叫不上名字的灾害。
 这个景象也许反映了传说背后真实的历史面貌:农业和文明引发了全球性的疫病风暴。
这个景象也许反映了传说背后真实的历史面貌:农业和文明引发了全球性的疫病风暴。
就算是最低效的早期农业社会,每平方千米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也是游牧社会的10~20倍。有大规模耕作就会有粮仓,而粮仓周围的景象和灌溉系统就意味着很多人必须定居下来——早期文明让附近的牧民变成奴隶,以耕种那些田地。
 尽管不再搬来搬去意味着也不会接触到那么多新疾病,但人口密度增加和定居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对传染病的增长至关重要。
尽管不再搬来搬去意味着也不会接触到那么多新疾病,但人口密度增加和定居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对传染病的增长至关重要。
刚开始,在一个地方居住很长时间会对史前人类一直以来遭受的病痛起到促进作用——比如说蚊子会发现有了更多人让自己填饱肚子,也有了更多灌溉过、清理过的土地可供生存。以蚊子为媒介的疟疾会传播得更快,因为同一只昆虫先叮一口感染了的病患,接着再去叮一口没感染的人,使被感染的概率增加了好几个数量级。
 公元前3000年,埃及一张谈到医药的纸莎草纸药书中提到了也许是疟疾的“年度害虫”,那个时期的木乃伊也有生前感染过疟疾的迹象。
公元前3000年,埃及一张谈到医药的纸莎草纸药书中提到了也许是疟疾的“年度害虫”,那个时期的木乃伊也有生前感染过疟疾的迹象。

能够支持这个论断的是,人类越是四处游荡,患病的可能性就越大:跟排泄在森林里比起来,被排泄在乡间小路上、田地里或池塘附近的寄生虫,找到办法进入另一个人体内的机会要大得多。那些只能在宿主体外短时间存活的微生物,包括导致麻风病的细菌,在熙来攘往的城镇里通常更容易传播开来。
 最后,人类永久定居总是会带来成堆的垃圾,而垃圾堆吸引了苍蝇、野狗和老鼠,它们都有传播疾病的极大潜力。
最后,人类永久定居总是会带来成堆的垃圾,而垃圾堆吸引了苍蝇、野狗和老鼠,它们都有传播疾病的极大潜力。
因为文明总是涉及大量人口跟家养动物生活在一起,彼此靠得很近,所以文明也为跨物种的传染性杀手提供了完美的传播环境。看看猪的例子:长久以来,对于收垃圾这件事,猪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在2009年的埃及体现得淋漓尽致:政府做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宣称为了阻止猪流感在全国蔓延,在全国选择性地宰杀了30万头猪。不到一年后,埃及议会就召开了一次群情激愤的会议,强烈谴责这项政策,因为正是这项政策让全国各地的垃圾堆积如山。国会议员、医师协会主席哈姆迪·赛义德称之为“国家丑闻”。
 但也正是因为猪几乎什么都吃,所以会成为主要的感染源。很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才都告诉人们不要吃猪肉。《申命记》就这样告诫大家:“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
但也正是因为猪几乎什么都吃,所以会成为主要的感染源。很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才都告诉人们不要吃猪肉。《申命记》就这样告诫大家:“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
旋毛虫病就是由猪肉里的寄生虫引发的一种疾病,这种寄生虫最长可以达到三毫米。谁要是特别草率地吃了被感染的未煮熟的香肠或猪排,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寄生虫侵入他的身体。除了引发呕吐、腹泻和发烧,跑到肌肉细胞里安营扎寨的幼虫还会伤害受害者的心脏和横膈。事实证明,寄生虫引起的呼吸、心脏和肾功能衰竭都可能会让人丧命。猪感染寄生虫,一般都是因为吃了含有生肉或动物残骸的垃圾,或是同类相残,吃了以前的农场伙伴的肉,再或是吃了刚好被同样的垃圾吸引了的老鼠。

爱吃香肠的人可能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但猪和人确实都会感染猪肉绦虫。被感染的人可能会得囊虫病,就是寄生虫幼虫的包囊扩散到了大脑里面。囊虫病会引起癫痫、卒中乃至死亡,每年仍有多达5万人死于这种疾病。
 虽然早在猪被驯化前,人类就已经有被猪肉绦虫感染的历史了,但猪被驯化之后,肯定会增加感染的概率。
虽然早在猪被驯化前,人类就已经有被猪肉绦虫感染的历史了,但猪被驯化之后,肯定会增加感染的概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千年内,文明和驯养的另一个更隐蔽的影响也出现了:进化出了新的传染病。人类文明化后的有些疾病可能是从家畜疾病进化而来的,杂交繁殖的驯养动物跟密集的人口近距离生活在一起,为传染病发展变化并跨物种传播提供了相当大的机会。例如,我们已经知道,流感跟猪和鸭子身上的疾病很相似,而白喉和轮状病毒也很可能是由驯化的牛羊传给人的(结核病的传播路径可能刚好相反,是由人传给牛)。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千年内,文明和驯养的另一个更隐蔽的影响也出现了:进化出了新的传染病。人类文明化后的有些疾病可能是从家畜疾病进化而来的,杂交繁殖的驯养动物跟密集的人口近距离生活在一起,为传染病发展变化并跨物种传播提供了相当大的机会。例如,我们已经知道,流感跟猪和鸭子身上的疾病很相似,而白喉和轮状病毒也很可能是由驯化的牛羊传给人的(结核病的传播路径可能刚好相反,是由人传给牛)。

对于因为文明才出现的很多最致命的单一物种疾病来说,人口密度确实极为重要,因为传染病维持下去所需要的最低人口密度取决于这种疾病传播得有多快、多致命,以及九死一生的感染者是否能终身免疫。
靠很小的宿主人群就能存活下去的微生物,往往是那些很容易传播,可以在宿主体外存活很长时间,也会在宿主体内生存很长时间的。也就是说,这些微生物很少置人于死地,人类也不会形成免疫力。这样的疾病也是人类独有的,在文明肇始以前的时代面对那么低的人口密度也能生存下来的那些。以会引起唇疱疹的那种疱疹病毒为例,在我们的祖先直立人进化成人类之前,这种病毒就已经在感染我们了。很有可能你身上就带有这种病毒,这样的人占三分之二。但大部分情况下,这种病毒只会引发唇疱疹。在你的神经细胞中,这种病毒也会过着相对来说风平浪静的生活,直到你命归黄泉。

我们拿没精打采的疱疹病毒和像伏地魔一样冷酷无情的麻疹做个比较,后者是历史上杀人如麻的凶手。这种病毒会跨物种传播,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由牛传给了人。麻疹最初的症状是咳嗽和打喷嚏,这也是病毒借以传播的方式;随后才会出现特征性的皮疹。宿主可能会死于并发症,比如脑炎引发的脑水肿、腹泻、脱水或肺炎。
麻疹或天花这样的疾病最早接触到人类时会横扫所有人口,引起大面积感染,让那些因年龄、营养不良或基因变异等原因而体质特别差的人死于非命。但幸存下来的人会获得免疫力,也往往是终身免疫。如果大部分人都曾被感染了,就会形成群体免疫:潜在受害者数量减少,于是咳出来的麻疹病毒接触到未免疫宿主的概率也降低了。如果这个概率大大降低,平均每个麻疹患者感染的新患者不足一人,这场流行病最终就会销声匿迹。
但是很不幸,对麻疹的免疫力并不能遗传给新生儿。新一代潜在宿主成长起来之后,群体免疫就会失败,麻疹卷土重来,在以前没接触过麻疹病毒的孩子中大开杀戒。如果整个人群都没经历过麻疹,那么一个麻疹患者可能会将这种传染病传给12个甚至更多的人。也就是说,要形成群体免疫,让麻疹不再暴发的话,人群中至少要有92%的人已经免疫。这反过来表明,新出生的人口只需要几年时间,就可以让已免疫人口的比例降到维持群体免疫所需要的比例之下,让麻疹疫情死灰复燃。
据估计,麻疹病毒要想生存下来并不断复发,感染以后的世代,至少要有50万人住在很近的范围内才行,否则就会逐渐消失。也只有更大的紧密相连的人群,才能让麻疹这样的疾病从流行病(在新一代潜在受害者的人数增加到足够多的时候一波波复发)变成地方病(一直存在,感染年轻人和之前没接触过这种病毒的人)。麻疹要想生存下来乃至蓬勃发展,需要文明昌盛。
从驯化作物和牲畜最早的证据到开始出现永久城镇,有3 000年的时间跨度;再到像两河流域的乌尔和基什这种最早的有纳税土地的城邦出现时,又过了大概3 000年。
 就算是这样的城市,一开始也只有一两万人居住,根本不足以承受麻疹这样的疾病。
就算是这样的城市,一开始也只有一两万人居住,根本不足以承受麻疹这样的疾病。
 但是,随着文明进一步繁荣昌盛,麻疹和天花都开始跨物种传播,让人类成了它们永久的家园。
但是,随着文明进一步繁荣昌盛,麻疹和天花都开始跨物种传播,让人类成了它们永久的家园。

在更大的人群中,这些新疾病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了生活背景的一部分。日本天花的历史就是一个例证。到17世纪,这种疾病已经成为日本城市地区的地方病。遭受天花之苦然后免疫复原,成为庆祝儿童成年的仪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在人口较少,也没那么多紧密关联的边远岛屿,天花仍然只是周期性发作的流行病。不同地方对天花的态度也明显不同,从日本中部地区来到小岛上的访客会惊讶地发现,岛民会逃离受感染的人,把病人隔离起来,甚至还经常遗弃家庭成员。
按照历史学家铃木晃仁的说法,“这些行为”在从城里来的访客中间“引发了各种情绪,他们又是困惑又是好奇,或者对……想象不到的野蛮行为……大加道德谴责”。
 但这种跟城市里大相径庭的行为有其完全出于理性的成分。在地方病的环境中,暴露在天花面前总是会发生——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宿命论也合情合理;而在疾病每隔几年才会出现一次的地方,避免感染或许也是有可能的。
但这种跟城市里大相径庭的行为有其完全出于理性的成分。在地方病的环境中,暴露在天花面前总是会发生——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宿命论也合情合理;而在疾病每隔几年才会出现一次的地方,避免感染或许也是有可能的。
就算不同地区的不同反应各有道理,这些反应可能也会让我们对历史的感觉产生扭曲。我们往往会把并非有规律地出现但集中的死亡跟每天都有但规模很小的死亡区别对待(想想飞机失事和车祸,前者造成的死亡会有更多人关注,但死于后者的人更多)。由于司空见惯,我们变得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再做出任何反应,要不然就没法解释,为什么尽管全球每年死于流感的人少说也有50多万,但大部分有条件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人都不去接种。
 但是,人们会关注规模巨大的流行病,并称之为瘟疫。潜在受害者避之唯恐不及,编年史家奋笔疾书,诗人赋到沧桑。有时候,瘟疫甚至能终结一个帝国。然而,每天都在发生的地方性传染病几乎连诗人的一句话都得不到,更不用说会有人为此逃之夭夭了。
但是,人们会关注规模巨大的流行病,并称之为瘟疫。潜在受害者避之唯恐不及,编年史家奋笔疾书,诗人赋到沧桑。有时候,瘟疫甚至能终结一个帝国。然而,每天都在发生的地方性传染病几乎连诗人的一句话都得不到,更不用说会有人为此逃之夭夭了。
尽管如此,数千年来仍然是经常出现的地方性传染病(例如疟疾,以及会在更大人群中成为地方病的天花和麻疹)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引人注目的瘟疫。每天都有人中招的地方性传染病会让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活不到成年。说到底,这类疾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要大得多。
我们可以看到,以前从未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农业和城市疾病的人群暴露在这些疾病面前时会带来多大的卫生负担。一项对亚马孙盆地最近才与外界建立联系的238个巴西原住民社群进行的分析表明,在跟来自现代巴西城市和乡村的外来者持续接触后,9年间,这些社群的人口数量平均下降了43%。

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从狩猎过渡到农业这一时期的人的骸骨,也再次发现其中农业人口的骸骨与狩猎祖先的比起来样子要糟糕一些,上面有损伤,是被感染过的迹象。贫血(血液的携氧能力低,往往跟受到感染有关)经常会在骨头两端连接处的骨松质上留下痕迹,而且牙齿的釉质含量低,这跟童年不够健康有关系。
但农业生活的压力并非仅限于此。考古学家在骸骨腹部找到保存下来的人类粪便(粪化石)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人类的农业革命越来越深入,他们体内保存下来的肠道寄生虫也越来越多。
除了感染风险更高,在早期文明时代,人类的营养状况也更糟糕。土里刨食的人民群众更加依赖少数几种主要作物,不像采集时代那么营养丰富,吃的蛋白质也更少。我们大体上知道他们的饮食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它们很可能跟今天最贫穷的人吃的食物非常相似。几年前,摄影记者彼得·门泽尔和作家费斯·达卢伊西奥伉俪合撰了一部调查报告《饥饿的星球》,其中采访了乍得东部布雷德津难民营的阿布巴卡尔一家,我们拿他们家举个例子。有援助机构给这家人提供主食,但他们的饮食结构仍然非常单一。阿布巴卡尔家每周吃约20千克谷物,其中大部分是高粱。每周他们还能吃到2.3千克豆子、1.1千克蔬菜,另外还有几升食用油和一些糖。但这个六口之家一星期一共只吃了半斤羊肉和三两半鱼。仅有的水果是五个酸橙,一人连一个都不到。奶制品一点都没有。
至少这些各式各样的卡路里足够让人不至于成为冻死骨——难民营外面的很多穷人情形更糟。看看这个生活在越南的穷人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描述:“早上,吃红薯,干活。中午,不吃饭。晚上,吃红薯,睡觉。”

在最早的文明中(今天最贫穷的人生活也是如此),人们就算能吃到肉,吃到的也更有可能是长满了寄生虫的。这些虫子会把在人体中的生活当作自己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并甘之如饴。营养不良和传染病也会相辅相成。如果无法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你就更容易生病。比如缺乏维生素A会增加患腹泻、疟疾和麻疹等疾病的风险,而缺乏锌会让整个免疫系统的整体效力大打折扣。
 尤其是寄生虫,它们会从人类宿主体内吸取养分——很多寄生虫都会在肠道里直接把养分先吸收了。
尤其是寄生虫,它们会从人类宿主体内吸取养分——很多寄生虫都会在肠道里直接把养分先吸收了。
 数千年来,在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的共同影响下,人类真的是“越活越抽抽”了——跟史前祖先比起来,女性的平均身高下降了4厘米。
数千年来,在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的共同影响下,人类真的是“越活越抽抽”了——跟史前祖先比起来,女性的平均身高下降了4厘米。
直到最近,这个趋势才开始逆转:人类身高的低谷很可能是到工业革命时代,出现在那些地狱般的城市中。
 1841年,英国利物浦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到26岁——这跟当时热带非洲预期寿命的估计值相当,甚至更低。
1841年,英国利物浦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到26岁——这跟当时热带非洲预期寿命的估计值相当,甚至更低。
 1842年,曼彻斯特劳工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17岁。而在拉特兰郡的乡村地区,绅士阶层的平均寿命为52岁,农村劳动力为38岁,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平均死亡年龄17岁,这可比史前狩猎——采集人群的估计值低太多了。
1842年,曼彻斯特劳工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17岁。而在拉特兰郡的乡村地区,绅士阶层的平均寿命为52岁,农村劳动力为38岁,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平均死亡年龄17岁,这可比史前狩猎——采集人群的估计值低太多了。

文明的影响对女性来说更加恐怖。
 城市化和农业带来的各种传染病轮番上阵,使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要能与此持平,必须保持很高的出生率才行。
城市化和农业带来的各种传染病轮番上阵,使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要能与此持平,必须保持很高的出生率才行。
 因此,在有据可查的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平均来讲女性从青春期到更年期的这段人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怀孕和哺乳。
因此,在有据可查的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平均来讲女性从青春期到更年期的这段人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怀孕和哺乳。

而且这也往往削弱了女性的自主权。在石器时代的很多群体中,两性在角色和决策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平等。但是,在巴比伦第六任国王汉谟拉比的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明肇始之后的时代变迁。汉谟拉比在大约3 770年前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他的法典是已知最早的成文法之一。这些法条对待女性只比财物稍好一点:“如果一个男人打了一个自由出生的女人,使她失去了尚未出生的孩子,那么这个男人应该因她的损失而赔给她10谢克尔……如果这个女人死了,这个男人的女儿也应被处死。”

文明带来的一系列疾病,足以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土地的承载能力以下。
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在她1965年出版的著作《农业增长的条件》中,对马尔萨斯关于土地限制和食物供应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她指出,人口增加可能也会使用于农业的土地面积增加,但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带来集约化——在同一块土地上生产出更多食物。有个很直接的变化就是将用于牧场的土地转为种植农作物。
她指出,人口增加可能也会使用于农业的土地面积增加,但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带来集约化——在同一块土地上生产出更多食物。有个很直接的变化就是将用于牧场的土地转为种植农作物。
 此外,博塞拉普也指出,增加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技术,比如轮作,在被大面积推广前很久就已为人所知。
此外,博塞拉普也指出,增加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技术,比如轮作,在被大面积推广前很久就已为人所知。
 她认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大多数地方,无论是技术障碍还是土地缺乏,都从未成为提高产量的限制因素。
她认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大多数地方,无论是技术障碍还是土地缺乏,都从未成为提高产量的限制因素。
地球科学家杰德·卡普兰及其同事认为,公元1600年,人们用到的土地还不到我们现在用于食物生产的土地面积的一半,而公元100年时,更是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
 确实,要把更多土地利用起来,需要干更多的活,有时候还艰辛异常,还会有营养不良的风险。而且,有些土地如果没有重犁、灌溉等创新,也是无法耕种的。尽管如此,似乎在整个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明显都在远远低于可能承载的最大值的水平上下浮动。
确实,要把更多土地利用起来,需要干更多的活,有时候还艰辛异常,还会有营养不良的风险。而且,有些土地如果没有重犁、灌溉等创新,也是无法耕种的。尽管如此,似乎在整个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明显都在远远低于可能承载的最大值的水平上下浮动。
实际上,我们可能还得感谢(或是归罪于)传染病限制人口数量的调控机制。人口数量增加时,人口密度会让发病率提高,这种让人口变得更稀疏的机制在大多数地方可能都是最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尤其是在人类以种田为生的那些岁月里。
马尔萨斯提出的不同控制机制的相对作用,其证据来自我们对历史上大规模饥荒的了解。爱尔兰经济史学家科马克·格拉达在《饥荒简史》一书中描述了世界上最严重的几次饥荒,并提供了相关数据。其中有两点值得一提。首先,大部分饥荒跟战争或一连串的恶劣天气有关(通常都是干旱,大雨和洪水要少见一些)。并不是土地正常的生产能力只能让人们勉强维持生计,而是一场极为严重的冲击把生产率推向了十分接近甚至低于仅供糊口的水平。其次,他列举的饥荒中就算是最饿殍遍野的那些(1740-1741年和1846-1852年的爱尔兰,1876-1879年的中国,1975-1979年的柬埔寨),也最多“仅仅”带走了1 500万~2 500万人的生命,也就是全部人口的13%左右。像黑死病那样的大流行病成功地在大得多的区域内造成了严重得多的影响,而像天花那样的地方性疾病,长期来看造成的常规死亡人数也比饥荒大得多。

人口数量受传染病的影响有多深——与营养不良和挨饿的影响不同——同样可以通过历史上富人阶层记录下来的健康状况得到展现。有钱人吃得起更好的饭菜,然而,奥地利历史学家瓦尔特·沙伊德尔对自然死亡的罗马皇帝、参议员及其家人的研究表明,就算是精英阶层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也不到30岁。
 他们这群人可是以饮食习惯和菜谱而闻名的。公元1世纪成书的罗马的《论烹饪》一书,单是列出的鸟类食谱就有如下名目:野鸡、鹅、孔雀、鸡、火烈鸟、鹦鹉、鹤、鸭、林鸽、乳鸽、莺、山鹑、斑鸠、丘鹬和鸵鸟。填饱肚子似乎并不能让人长命百岁。
他们这群人可是以饮食习惯和菜谱而闻名的。公元1世纪成书的罗马的《论烹饪》一书,单是列出的鸟类食谱就有如下名目:野鸡、鹅、孔雀、鸡、火烈鸟、鹦鹉、鹤、鸭、林鸽、乳鸽、莺、山鹑、斑鸠、丘鹬和鸵鸟。填饱肚子似乎并不能让人长命百岁。
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为了让像罗马这样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保持规模,需要源源不断的农村移民——因为城市人口无法生出足够多的孩子来追平死亡率。尤其是在早期文明中,这种迁移很少是自愿的。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在《反谷》一书中指出,古代国家“用在战争中抓到的俘虏和从专门从事奴隶贸易的野蛮人手中大批购买的奴隶来补充人口”。

那些规模最大的城市从方圆数百千米的偏远地区吸引新的受害者前来,并号称自己有相对来说更加先进的卫生系统。但长期来看,它们仍然无法自我维持下去。如果战争或帝国陷落让城市失去了吸引移民的能力,城市人口就会迅速缩水。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特尔蒂乌斯·钱德勒的说法,从公元前430年到前100年,因为被罗马比了下去,雅典人口足足减少了一半;而接下来从公元100年到600年,随着罗马帝国开始土崩瓦解,罗马城的人口减少了将近90%。
 这一点我们还是需要好好说清楚。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马尔萨斯的结论在很多局部地方来看还是屡见不鲜:随着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和消费量都会下降。但似乎只有在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有时会有气候变化的因素),食物匮乏才会成为人口数量的限制因素。埃斯特·博塞拉普是对的:并不是因为土地不够。让人口数量保持低位而且很分散的,是传染病导致的高死亡率。传染性疾病带来的死亡率在19世纪和20世纪逐步下降后,人口、城市化、集约化、土地使用和欣欣向荣的局面全都水涨船高,在全世界范围内攀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水平。
这一点我们还是需要好好说清楚。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马尔萨斯的结论在很多局部地方来看还是屡见不鲜:随着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和消费量都会下降。但似乎只有在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有时会有气候变化的因素),食物匮乏才会成为人口数量的限制因素。埃斯特·博塞拉普是对的:并不是因为土地不够。让人口数量保持低位而且很分散的,是传染病导致的高死亡率。传染性疾病带来的死亡率在19世纪和20世纪逐步下降后,人口、城市化、集约化、土地使用和欣欣向荣的局面全都水涨船高,在全世界范围内攀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