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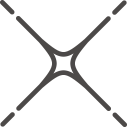
许多教授倾向于认为自己孩子的智商是先天遗传的,却把他们学生的智力归为是后天培养的。
——罗杰·马斯特斯 1
任何的分歧都源于不确定。19世纪60年代,尼罗河源头在哪儿还未有定论,由此引发了两位英国探险家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和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之间的激烈争论。两人共享一个营地长达数月之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分歧才会这般剧烈。斯皮克认为尼罗河的源头是维多利亚湖,他发现这个大湖泊时,伯顿还在坦桑尼亚西部塔波拉的帐篷里养病;而伯顿坚信源头位于坦噶尼喀湖或其附近。1864年,争端终于落下帷幕,因为斯皮克死于一场枪杀(也许是意外),那天他本打算和伯顿展开一场公开辩论。顺便提一句,斯皮克的观点是对的。
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从皇家地理协会的高度来俯视这场争端,偶尔还支持伯顿,令争论火上浇油,他就是弗朗西斯·高尔顿。此人命中注定在同年掀起了一场影响力更大,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争端:先天与后天之争。这有点类似于尼罗河源头之争,二者都是源于未知,了解得越多,可以争执的就越少;而且二者都涉及许多无谓的琐碎之事。当然,比尼罗河之源位于哪个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探知到非洲有两个大湖泊,这对于当时的西方科学界来说是新的发现。同样,人性是先天形成的或是后天习得的,这一点不太重要,关键是能了解到这两方面都对人性成长有所影响。尼罗河是成千上万条河流的汇总,没有哪一条可以确切称之为源头;人性的形成同样也并非只依赖一种因素。
高尔顿的热情可通过量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他有许多发明创新,涉及的领域极其宽泛:探知北纳米比亚、反气旋天气系统、双胞胎研究、问卷调查、指纹识别、复合相片、统计回归和人类优生。不过他留给子孙后代最伟大的东西或许是发起了先天与后天之争,并创造出这个术语。高尔顿出生于1822年,外祖父伊拉斯姆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诗人和发明家,祖母是其第二任妻子。高尔顿发现,算是半个表哥的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既令人信服,又可启发灵感。他毫不谦虚地将其归为“心智的遗传,自然选择论杰出的创立者和我本人都是从我们共同的祖辈伊拉斯姆斯·达尔文博士那里继承了这种遗传倾向。”因此,他受到血统的激励,认清自己的科学使命是在遗传统计学上。1865年,他放弃地理学,转向遗传学,在《麦克米兰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上发表了“遗传的才能与性格”,文中提出杰出的人物之间存在特殊的亲缘关系。1869年,他将这篇文章扩充为著作《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
高尔顿断言天赋在家族内得以传递承接,他详尽而又热情地描述出许多著名人物的家谱,他们的职业包括法官、政治家、贵族、指挥官、科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牧师、桨手和摔跤选手。“太多才能或多或少有些出众的人都有杰出的亲属,如此多的例子足以证明天才是遗传的。” 2 这并不是非常高深复杂的推论。毕竟,旁人可以完全予以反驳,那些出身卑微之人发迹成为成功人士,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才能帮助他们克服了环境的各种劣势;家族里天才辈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共享着优等教育。大多数评论家认为,高尔顿夸大了遗传的作用,却忽视了后天培养和家庭的贡献。1872年,瑞士植物学家阿尔方斯·德·康多尔(Alphonse de Candolle)用长篇大论驳斥了高尔顿的观点。他指出,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伟大的科学家都来自那些具有宽容的宗教氛围、广泛的贸易往来、温和的气候和民主的政府的国家或城市。这表明成就更多取决于环境和机会,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3
康多尔的驳斥刺激高尔顿在1874年完成第二部著作《英国科学家:他们的天赋与教养》(English Men of Science:Their Nature and Nurture)。在书中,他首次采用问卷调查以辅助研究,并重申他的结论:科学天才是遗传的,而不是培养出的。正是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创造出这个著名的押韵短语:
“先天与后天”这个短语是绝妙的对偶,它将构成人格发展的不计其数的要素归入两个不同的类别里。 4
这个短语也许是借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The Tempest),剧中普洛斯彼罗(Prospero)曾这样侮辱过凯列班(Caliban),
“一个魔鬼,天生的魔鬼,后天教养也改不过来他的先天本性。” 5
莎士比亚并不是第一个将先天和后天这两个词并置的人。《暴风雨》初次公演前30年,一位伊丽莎白时期的教育家,也是莫切特泰勒学校的首任校长,理查德·穆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就极其喜爱先天和后天这一组押韵对偶的词语,他在1581年出版的著作《关于儿童教育的立场》(Positions Concerning the Training Up of Children)里四次使用了这个短语。
(父母)要尽最大努力培养自己的孩子,无论是在哪里,也无须争论由谁来做,要努力让他们深爱的,也是先天馈赠给他们的孩子得到良好的后天培养。上帝赐予孩子先天的力量,并没有意图让这种力量的发展在后天方面出现例外。孩子的先天能力,若是没有被本应该注意到的人察觉,那就要谴责这些人。他们或者是出于无知而无法判断,或者是由于忽视而未做寻找,孩子有哪些特质是先天带来的,需要通过后天培养使其发展得更好。既然孩子身上具有这些特质,无知者就可以通过事实了解,有学识之人可以通过阅读明白。因此,通过了解人具有先天才能这一事实以及哲学道理,我们知道,年轻的少女也需要接受教育,因为她们也拥有先天馈赠的天赋,应该得到更好的后天发展。 6
在1582年出版的下一本著作《论小学》(Elementaries)中,他又重复了这个短语:“先天决定了一个人的方向,后天推动他沿此向前发展。”穆尔卡斯特的个性有些古怪。他出生于卡莱尔,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他会和学校管理者发生激烈争执,也会充满激情地倡导足球运动。“足球运动可以强身健体。”他曾这样说过。他还涉及戏剧领域,曾为王室写过许多历史剧作。他从教的学校也培养出托马斯·凯德(Thomas Kyd)和托马斯·洛基(Thomas Lodge)两位戏剧作家。有些人认为他就是《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中那位空爱一场的校长的原型,因此莎士比亚很有可能认识穆尔卡斯特,或读过他的作品。
高尔顿后来的一些思想也可能是从莎士比亚那里得到了灵感启发的。莎士比亚有两部戏剧都和混淆的双胞胎有关,分别是《错误的喜剧》(The Comedy of Errors)和《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他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双胞胎的父亲,以这对被认错的双胞胎为主题,设计出精妙绝伦的情节。但是,正如高尔顿所言,在《仲夏夜之梦》中,莎士比亚引入了一对“虚拟双胞胎”——两个没有血缘关系却在一起长大的人。尽管赫米娅和海伦娜被描述为“并蒂的樱桃,看似分离,却连生在一起” 7 ,但她俩不仅外貌相差甚远,爱的男人也迥异,最终两人以激烈的吵架收场。
高尔顿沿袭了这一暗示。第二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双胞胎的历史——先天后天孰轻孰重》(The History of Twins,as a Criterion of the Relative Powers of Nature and Nurture)。最终他有了一个体面的方法来检测自己创立的遗传假设,这也让他免于被别人针对他的家谱说提出反驳。值得注意的是,他推论双胞胎有两种类型——同卵双生,出自“同一个卵子的两个胚点”;异卵双生,来自“不同的卵子”。这种说法还不错。如果把胚点理解为细胞核,那就距事实更近一步了。然而,这两类双胞胎会接受相同的后天培养。因此,如果同卵双胞胎在行为上比异卵双胞胎更为接近,那遗传的影响就是有根据的。
高尔顿写信给了35对同卵双胞胎和23对异卵双胞胎,收集一些能表现他们相似和差异的趣闻轶事。他兴高采烈地叙述了这次调查的结果,那些从出生就非常相似的双胞胎在其一生中都保有这种相似性,不仅在外貌上,而且体现在所患疾病、个性和兴趣上。有一对双胞胎在同一年龄同一颗牙齿剧烈疼痛;另一对双胞胎住在国家的两端,他们竟在同一时间买了同样一套香槟酒杯当成礼物送给对方。出生就有差异的双胞胎随着年岁渐长,则会体现出更明显的差别。“他们在外貌和心智上都不相似,这种差异与日俱增,”一位回信者这么写,“而且外部环境给予他俩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从未分离过。”对于如此有力的结论,高尔顿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毋庸置疑,先天本性极大地优先于后天培养……我担心的是,提供的证据太多反而惹人质疑,因为这些证据似乎与一些经验相悖,竟然指出后天培养的作用微乎其微。” 8
按照“马后炮”的说法,一个人可尽情在高尔顿的双胞胎研究里挑出各种漏洞,可以说其研究是基于趣闻轶事,取样范围小,搞循环论证:外貌相似的双胞胎具有相似的行为。他没有从基因的角度区分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然而,他的研究还是颇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晚年时,高尔顿终于看到他的遗传论由饱受怀疑的观点转为正统理论。“先天限制了心智的力量,就如同先天限制了身体的力量一样毋庸置疑,”1892年《民族报》(The Nation)中这样写,“在这些方面,(高尔顿的)观点已优于各地的理论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9 过去约翰·洛克、大卫·休谟和约翰·穆勒奉行经验论,将心智视为一张白纸,经验可在纸上尽情书写并塑造它。当时,这种经验论已被新加尔文主义的遗传决定命运的观念取而代之。
评价高尔顿的理论有两种方式。你可以谴责高尔顿,说他蛊惑的“绝妙对偶”其实是错误的二分法。你可以将他视为20世纪的精神恶魔之一,他的咒语让三代人像钟摆一样,摇晃在环境决定论和基因决定论这两个荒谬的极端之间。你还可以心怀恐惧地指出高尔顿的动机是要优化人种。1869年出版的《遗传的天才》第一页里,他就吹捧了“明智婚姻”的好处,哀叹不合适的婚配与遗传导致了“人性的退化”,并呼吁政府当局承担“义务”,执行权力,通过优化生育来改善人性。这些提法会发展成为鼓吹优生的伪科学。因此,你可以“马后炮”般地斥责,他的观点令接下来一个世纪里的千百万人身陷惨境。不仅在纳粹德国,即便在一些最具宽容精神的国家里,许多人都因此饱受痛苦。 10
这样说当然没错。不过,若是认为如果没有高尔顿,上述那一切就不会发生,这未免有点太苛刻了;更不能说他应该预料到他的理论会带来什么后果。即使没有高尔顿,也会有其他人想出先天后天这个绝妙的对偶。如果更为宽容地解读历史,高尔顿可以被视为一个超前于所在时代的人,他揭开了一个伟大的真相:我们的许多行为方式都是源于我们自身,我们并不听凭社会的摆布,也没有遭受周边环境的侵害。你甚至可以断言——也许这有些夸张——在20世纪环境决定论占主导时,他的观点有助于自由之火熊熊燃烧。考虑到当时高尔顿对基因一无所知,他对遗传的洞察力还是相当值得称赞的。他可能要等到100多年后,才能看到双胞胎研究最终会证实他曾经做出的大部分预测。严格来说,若先天和后天可以分离,那先天基因的影响必定优先于(共有的)后天培养,这种说法主要用于界定 同一个社会里 人类个性、智力和健康方面存在的 差异 。请注意这里的限定说明。
双胞胎研究是近期才发展起来的。20年前,情况截然不同。20世纪70年代,通过研究双胞胎以探知遗传的观念已湮没无闻。自高尔顿以后关于双胞胎的大型研究中,有两个是极不光彩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对双胞胎的狂热嗜好已人尽皆知。他把新进集中营的双胞胎挑选出来,把他们隔离到特别区域以便研究。讽刺的是,这种“特殊照顾”竟导致双胞胎比单生儿有更高的存活率——大多数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活下来的小孩是双胞胎。他们常常接受残酷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实验,作为交换,他们至少会吃得更好一些。尽管如此,存活下来的双胞胎仍是极少的。 11
同时在英国,教育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渐进地收集了一组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的资料,以此推测出智力是由遗传决定的。1966年,他把调查研究的结果出版,声明已取样53对这样的双胞胎。这是一份大到超乎寻常的样本,伯特的智商具有高度遗传性这一结论也影响了整个英国的教育政策。然而,后来人们却得知他的一些数据几乎可以肯定是伪造的。心理学家利昂·卡明(Leon Kamin)注意到,尽管伯特的研究历经几十年时间,可是他给出的智商与遗传的相关性数据一直是相同的,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都一样。与此同时《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也登出伯特的两个合作作者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不过后来还是有一个出现了)。 12 有了这样的研究史,双胞胎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无疑是一个有污点的题材。但是,时至今日双胞胎研究已得以重生,成为行为遗传学这门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尤其是在美国、荷兰、丹麦、瑞典和澳大利亚,行为遗传学的研究遍地开花。它深奥复杂、充满争议、精确度高并且花销不菲——拥有现代科学所要求的一切要素。但是,双胞胎研究的核心仍体现出高尔顿的洞察力:人类双胞胎提供了美妙的自然实验素材,我们可以由此解析先天和后天对人类的各自贡献。
从这方面来看,人类实在是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动物世界里罕有同卵双胞胎的生育,例如,我们至今仍未发现老鼠可以生育同卵双胞胎,它们一般都是生产一窝异卵幼仔。人类偶尔也能生育出异卵多胞胎。在白人中,每125次生育里会有一次产出异卵双胞胎,他们源于两个受精卵。这个概率在非洲人中更高,在亚洲人中更低。如果不做基因检测,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一般不能准确地区分开来。但是也会有一些迹象表明他们之间的差异,同卵双胞胎的耳朵一般是完全一样的。 13
行为遗传学这门学科主要就是检测同卵双胞胎有多么相似,异卵双胞胎有多么不同,以及如果由不同的家庭分开养育他们,那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分别又会怎样。这样得到的结果便是对任何特征的“遗传度”的一个估计。遗传度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很容易被误解。首先,它是全体人的平均数,对于任何个人来说毫无意义,例如,你不能说赫米娅的遗传智力比海伦娜高。当一个人说身高的遗传度是90%,他并不是也不能说身高尺寸的90%来自基因,剩下的10%来自食物。他指的是, 在特定人群的样本中, 身高差异的90%归因于基因,10%归因于环境的影响。但个人的身高没有可变性,因此也就没有遗传度一说。
此外,遗传度只能测量相对差值,不能测量绝对值。大多数人生来有十根手指。那些手指少于这个数字的人通常是在事故中丧失了其中的一些——这是环境带来的影响。因而,手指数目的遗传度接近于零,但是,说环境造成了我们有10根手指无疑也是荒唐的。我们长出10根手指,是因为基因是这样设定的。手指数目的变异是环境决定的;事实上,我们有10根手指,这是遗传的。因此,这像是一个悖论,遗传度最小的人类特征,却最受基因决定。 14
智力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说赫米娅的智力完全来自基因。很显然,如果没有食物、父母的养育、教育和书本,一个人不可能拥有智力。然而,在一些拥有同样优势的人组成的样本中,那些在考试中得高分的人和低分的人之间的差异,可以确由基因造成。
由于地理位置、阶层或金钱等偶然因素,大多数学校的学生都有相似的背景。也就是说,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是相似的教育。由此可见,环境影响造成的差异降到最小化,学校在不知不觉中将遗传的作用提到最大化,得高分学生和得低分学生之间的差异一定归因于基因,因为只剩下它能带来改变。这再一次说明,遗传度测量的是什么在变化,而不是什么在决定。
同样,在一个真正实行精英统治的社会中,所有人有着均等的机会,接受同样的训练,那些最优秀的运动员通常有最好的基因。运动能力的遗传度接近于100%。在一个与之相反的社会中,只有少数有权势的人才能有充足的食物,有机会参与训练,那么背景和机会将决定谁可以赢得比赛。在这种情况下,遗传度为零。因此,这又造成了一个悖论。我们越是让社会平等,遗传度就越高,基因体现的作用就越大。
为了避免误解,我已做了上述说明,之后我将谈到现代双胞胎研究的结果。故事开始于1979年,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家报纸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来自俄亥俄州西部的一对同卵双胞胎兄弟吉姆·斯普林格(Jim Springer)和吉姆·刘易斯(Jim Lewis),在出生几周后就被分开由不同的家庭养育,相隔40年后他俩重新相聚。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对此深感兴趣,他提出要见兄弟俩以记录他俩的相似及不同之处。在兄弟俩重聚的一个月里,布沙尔和他的同事们花了一天时间来考察他俩,结果两个吉姆之间的相似之处令他们大为震惊。虽然两人的发型不同,可他们的面庞和声音几乎难以区分。他们的医学史也十分相似:高血压、痔疮、偏头痛、弱视、烟不离口、爱咬指甲,以及在同样的年龄体重增加。和预料中的一样,他们的身体各方面高度相似,心智也一样相似。他们两人都关注赛车,不喜欢棒球;都有自己的木工车间;两人都在花园里的大树边放了一张白色椅子;他们度假时去过同一个佛罗里达的海滩。有些巧合真的很巧。他们都有一条叫作托伊的狗;他们的妻子都叫贝蒂,又都曾与一个叫琳达的女人离婚;他俩都给第一个孩子取名为詹姆斯·艾伦(尽管一个拼写成Alan,另一个拼写为Allen)。
布沙尔想,也许分开养育的双胞胎不仅非常相似,而且要比那些一起长大的双胞胎更为相似。在同一个家庭里生活,也许双胞胎之间的差异会被夸大,其中一个会说话说得更多,另一个则会说得少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时有发生。我们现在已知道这是有些许道理的。在某些方面,幼年时就分开长大的双胞胎要比后来才分离的双胞胎体现出更多的相似性。
首次报道吉姆这对双胞胎的新闻记者,在布沙尔见过兄弟俩以后采访了他,由此写出的报道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兴趣。吉姆兄弟俩登上了《今夜秀》节目(Tonight),与强尼·卡森(Johnny Carson)一起登台,之后这事就像滚雪球一样,影响力越来越大。兄弟俩对接下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布沙尔邀请他俩去明尼苏达州,参加一连串的生理和心理测试,测试小组由18个人组成。到了1979年年底,12对重逢的双胞胎联系了布沙尔。1980年年底,这个数字变成了21对;再过一年以后,又变成了39对。 15
就在这一年,苏珊·法伯(Susan Farber)出版了一本书,明确斥责所有关于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研究,认为它们全都不可靠。 16 她指出,这些研究都夸大了相似之处,忽略了差异,并对一些重要的事实视而不见。比如同卵双胞胎在被分开养育之前,曾在一起共度过几个月;又或者在科学家们对他们展开考察以前,双胞胎已经重聚了几个月。有一些研究,例如西里尔·伯特的研究,甚至可能都是捏造的。法伯的这本书在当时被视为对这个问题的定论,但布沙尔认为这将敦促他去完成一项完美无瑕的研究。他决定绝不让自己受到这种指责,于是详细地记录了有关他研究的那些双胞胎所有的一切。他将轶事搁置一边,收集有关相似之处的真实并可量化的信息。当他发表研究结果的时候,对于法伯提出的质疑,他所有的数据都显得无懈可击。但这并没有足以撼动当时的主流观念,他的批评者仍指出,布沙尔只不过是在证明自己的假设。这并不特别,这些人会很相似,他们生活在相似的城市里,住在相似的中产阶层居住的市郊;他们在同样的文化之海里畅游,也学习同样的西方价值观。
那么,好吧,布沙尔说,于是他着手寻觅一些分开养育的异卵双胞胎。这些人曾共享一个子宫,也共享西式养育环境。如果那些批评他的人是对的,那么这些异卵双胞胎也会表现出非常相似的心智。 17 他们会吗?
借用宗教原教旨主义来帮个忙。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通过问卷调查他们的信仰,布沙尔对这些信奉宗教的双胞胎们展开考察。从评分结果来看,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的相关性是62%,分开养育的异卵双胞胎的相关性只有2%。布沙尔又用了一份不同的问卷调查来重复同卵、异卵双胞胎实验,这次是更广义地去测量这些人对宗教的虔诚度,这次的结果是58%对27%。之后他指明,一起养育的同卵双胞胎和一起养育的异卵双胞胎之间,有着类似的比率。他的同事凯瑟琳·科森(Kathryn Corson)也用了一份不同的问卷调查来做研究,该调查旨在发现问卷对象的“右翼态度”。同样,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的相关性高达69%,而分开养育的异卵双胞胎则没有任何相关性。之后,布沙尔又给出一份问卷调查,这上面只简单地列出一些单独的短语,被调查者只需回答同意或不同意。问卷内容包括:移民、死刑、限制级电影,等等。那些不同意移民,同意死刑及诸如此类的人就会被认为是更加“右倾”。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的相关性是62%,分开养育的异卵双胞胎的相关性是21%。澳大利亚展开的类似大型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体现出巨大的差异。 18
布沙尔并不是努力想要证明,有这样一种上帝基因或反堕胎基因存在;他也不是想声明,环境在决定宗教仪礼的细节方面不起任何作用。如果说意大利人是天主教徒而利比亚人是穆斯林,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基因,这种说法无疑是荒谬的。他只是想要表达,即使是在宗教这样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里,基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并且可以得到测量,这的确令人震惊。人性中一部分可以遗传的特性,称作“对宗教的虔诚度”,绝不同于个性中的其他特征。(它与个性的其他量度的相关性极弱,例如外向。)简单的问卷调查就可以帮我们了解到这一点,而这个特性也相当准确地预测了谁最终会成为任何一个社会中虔诚的宗教信徒。
请注意,这样一个简单的研究,如何来驳倒行为遗传学的批评者提出的反对意见呢?很多人质疑问卷调查既粗略又不可靠,不能测出人们真实的想法;但其实问卷调查反而使研究结果相对保守。如果可以排除测量误差,显示的效果可能会更明显。很多人又说那些分开的同卵双胞胎并不像声称的那样过得真的是完全分离的生活,而且他们在被考察之前的若干年里就经常重聚。如果他们所言属实,那么这对异卵双胞胎也同样成立。有人还反驳说,布沙尔的研究对象都是他挑选出来的双胞胎,这也有偏颇地吸引了那些更为相似的双胞胎参与其中。 19 但是,在布沙尔的研究中,最具启示作用的是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之间的差异,而非两者的绝对相似性。还有一些人说不能将先天与后天分离开,因为二者交互作用。的确如此,但是与一起长大的双胞胎相比,分开养育的双胞胎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差异,这说明这种交互作用并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强大。
在为这本书做研究工作时,我了解到一些人对布沙尔的研究持有一种刻薄的观点。他们一定不会满意上一段中的许久前就作为答复的论断,而可能会直截了当地提醒我去了解布沙尔的研究资金来源:先锋基金会。它于1937年由纺织业的一位亿万富翁创立,曾公然支持优生学。基金会章程这样写道:“实施或协助实施人类种族中遗传和优生一般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人类遗传性的动植物研究,尤其是针对美国人的人种改良问题研究。” 20 该基金会设在纽约,其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一群年迈的战地英雄和律师。
他们支持布沙尔研究的动机可能是,他们乐于相信基因可以改变行为,因而提供资金给这样一位研究者,他似乎能够带来支持这个结论的研究成果。难道这就意味着布沙尔和他的同事们(更不用提在弗吉尼亚州、澳大利亚、荷兰、瑞典和英国类似的双胞胎研究者了),都在伪造数据来取悦资金赞助者吗?这也太牵强附会了吧。而且,你只要和布沙尔会见几分钟,就会知道他不是个懦夫,更不是个傻子,更别说他会遵循宿命论者的胡言乱语,在全世界煽动一场新的优生运动。他接受先锋基金会的资金,是因为对方无需任何附带条件。“我的原则就是,他们不对我做任何限制——我所想的、我所写的和我所做的,这样我才会接受他们的钱。” 21
当然,问题还在于如何报道这样的研究。“X基因”的标题会造成诸多祸害,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因积累起这样的名声,它们会像来势迅猛的推土机一样,把一切挡路的东西一扫而光。然而,后天论的捍卫者必须首先为基因有这样的名声而负责,他们争辩既然行为不是必然性的,那么基因就不该包括在内,于是在争论中基因就成了必然性的东西。他们还反复申明,“X基因”是一个始终并唯一导致某种行为的基因;先天论的捍卫者回应,他们是想说明,相比于同一基因的其他版本,X基因更能增加X行为的发生概率。 22 1999年,英国双胞胎研究者塔莉娅·埃利(Thalia Eley)宣布,来自英国和瑞典的1500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研究证据表明,基因遗传会强烈影响一个小孩在将来是否成为校园恶霸。如果此时有一个记者将她的结论按照惯用的方式简写为“霸凌行为是遗传的”,那么她对此是会抱怨呢,还是感到抱歉呢? 23 稍微合理的表述应该是,“西方社会里霸凌行为中的相对差异也许是有遗传性的”。但是很少有记者会希望新闻编辑加上这样的附加说明。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当双胞胎的对照研究首次出现时,它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直到那时,人们还真的认为,甚至西方中产阶级中的个性差异都是源于经验差异,与基因无关。当时需要得到论证的预设不是“一切都在基因里”,而是“一点儿都不关基因的事”。这句引言来自1981年出版的关于个性心理学的一本主要教科书:“想象一下,一对有着同样遗传天赋的双胞胎,如果在不同的家庭长大,他们在个性上将会体现多么大的差异。” 24 当时每个人都这样想,包括布沙尔。“看吧,”他坦然地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相信这些会受到基因的影响。是证据说服了我。” 25 在理解人类个性方面,双胞胎研究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然而,行为遗传学的成功也成了它垮台的根源。它的结果如此乏味,不用思考便能知道:一切东西都是可遗传的。它并没有像高尔顿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将影响人类进化的因素分为基因和环境两类,双胞胎研究只是发现了一切东西都具有同等强度的遗传性。布沙尔着手这项研究时,他期待可以发现个性中有些方面比另一些方面遗传性更强。但是,经过20年来对许多国家里的越来越多分开养育的双胞胎进行研究后,他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从所有衡量个性的尺度来看,西方社会里的双胞胎遗传度都很高: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比分开养育的异卵双胞胎体现出更多的相似性。 26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差异更多地归因于两者的基因差异,而不是家庭背景。如今,心理学家从五个维度,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五大因素”来定义个性——开放性(O)、尽责性(C)、外向性(E)、随和性(A)和情绪稳定性(N),可简称为OCEAN。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在每一维度的得分,它们是独立变化的。你的个性可以是开明的(O)、吹毛求疵的(C)、外向的(E)、爱嫉妒的(A)和冷静的(N)。在每一案例中,个性差异的40%多一点是源于直接的遗传隐私;不到10%是由于大家都有的环境影响(大多是指家庭的影响);大约25%受到个体所经历的独有的环境影响(包括个人病史、偶然事故以及在学校结交的伙伴等);余下的25%归为测量误差。 27
在一定程度上,双胞胎研究证实了“个性”这个词是有所指代的。当你描述某人有某种个性时,你是在指对方本性中内在的、不受他人影响的东西。借用一个流行的词,这就是一个人的“性格的内在力”。按照定义,你是在指他们所独有的特性。但是,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弗洛伊德观念的洗礼后,我们却发现人们的内在特性很少受到家庭生长环境的影响,这似乎有违常理。 28 在一些方面,个性就像体重一样,具有遗传性。根据一项研究,兄弟俩或姐妹俩在体重上的相关度为34%;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关度稍小一些,是26%。这样的相似性有多少该归因于他们住在一起,吃着同样的食物;又有多少该归因于他们共享一些同样的基因呢?这是个好问题。同一家庭养育的同卵双胞胎在体重方面的相关性为80%,而一起养育的异卵双胞胎的相关性只有43%。这表明基因比共同的饮食习惯更为重要。那被收养者的情况又怎样呢?养子养女和其养父母的体重相关性只有4%,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的相关性只有1%。与之大为不同的是,由不同家庭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在体重方面仍有72%的相似度。 29
于是我们有了结论,体重主要归因于基因的作用,而不是饮食习惯。那么,是否我们就可以将饮食建议抛在一边,尽情享用冰激凌了呢?当然不能。以上研究并没有涉及体重多或少的原因,只是揭示出一个特定家庭里成员之间体重差异的原因。给定同样的饮食,有些人的体重会比别人更重。西方社会里的人越来越胖,不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改变了,而是因为他们吃得越来越多,锻炼也越来越少。但是,如果每个人的饮食都完全一样,那些体重增加最快的人一定是由于基因造成的。因此,体重的相对差异具有遗传性,尽管平均体重的变化归为环境的影响。
什么类型的基因会导致基因变化呢?一个基因相当于合成一个蛋白质分子的一组指令。由这种数字式的简单缩写跳跃到构成个性的复杂层面,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现在这个似乎不可能的想象首次实现了。人们正在探索导致个性变化的基因序列中的变化:虽说是大海捞针,毕竟已可以捞到几根了。让我们以构成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这种蛋白质(BDNF)的基因为例,它位于11号染色体上,是一个短基因,其DNA片段只由1335个字母组成——实属巧合,恰好与本段原文的英文字母数一样。该基因组成4个字母的遗传密码,指导蛋白质分子的合成。这个蛋白质就像是大脑中的肥料,可以促进神经元的发育,以及其他更多。在大多数动物中,该基因的第192个字母是G,但在有些人中是A。人类中大约有3/4的人该基因带有G版本,余下的带有A版本。一个微小的差异,仅仅是一个长段中的一个字母,合成了一个稍有不同的蛋白质——在该蛋白的第66个位置上有的是蛋氨酸,有的是缬氨酸。因为每个人体内的每个基因都有两份拷贝,这就意味着有三种情况出现。一些人的BDNF中有两个蛋氨酸,一些人的BDNF则有两个缬氨酸,余下的人则是各带一个蛋氨酸和一个缬氨酸。如果你发一份问卷调查来测试人们的个性,并同时确定他们带有何种BDNF,你会得到一个令人大为吃惊的结果。带有两个蛋氨酸的人的神经过敏程度明显弱于各带一个蛋氨酸和一个缬氨酸的人,而后者的神经过敏程度又明显弱于带有两个缬氨酸的人。 30
抑郁、害羞、焦虑和脆弱,它们构成了心理学家说的“神经过敏症”6个层面中的4个,带有两个缬氨酸的人在这4个层面表现得最为强烈,带有两个蛋氨酸的人则症状最轻。在其他关于个性的12个层面中,只有一个(感情的开放度)体现出相关性。换一句话说,这个基因尤为影响神经过敏程度。
不要太得意忘形了。这个发现只能够解释人类差异中的很小一部分,大约是4%。也许它只能证明研究所在地,即密歇根州的蒂卡姆西地区的257个家庭所独有的特征。它绝不是什么神经过敏基因。但是,至少在蒂卡姆西地区,该基因的差异解释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些个性差异,而且这种解释与描述个性的标准方式是相符合的。它也是所发现的第一个与抑郁有紧密关系的基因,这给医学界带来了一线希望,也许我们可以应付这一现代生活中最难治疗又最常见的疾病了。我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体会,这个特殊的基因并不是多么意义重大,但它证明了一点,由DNA密码中的一个拼写变化就可轻而易举地跳跃至一个真正的个性差异。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人,都无法说出这样一个微小的变化是如何或者为什么导致了不同的个性,但它的确做到了。行为遗传学的批评者总喜欢带着质疑的态度:“基因只是用来维持蛋白质合成的,绝不可能成为个性的决定因素。”这样的说法已经行不通了。蛋白质合成中的一个变化确实导致了个性的变化。此外,其他的一些类似基因也呼之欲出。
因此,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无稽之谈:相比于那些在不同家庭长大的人,拥有不同基因的人体现出的个性差异会更大。赫米娅和海伦娜在一起长大,但她俩的相似程度远不及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和维奥拉(Viola)之间的相似度,尽管这对孪生兄妹从小就被分开养育了。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发现,丝毫不能让人激动。任何有不止一个孩子的父母都会注意到孩子们个性上的明显差异,而且知道并不是他们造成了这些差异。之后他们也一定会发现孩子们有一些天生的差异,这是由于父母在同一个家庭养育孩子,孩子们的成长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分开养育的双胞胎研究的奇妙发现在于,即使环境有所改变,双胞胎个性的差异仍然大多是天生的。即使家庭环境变了,它也没有给个性的形成留下些许痕迹。双胞胎研究对这个结论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它也充分获得了其他诸如收养子女研究以及双胞胎与收养子女关系研究的支持。
在同一个家庭长大所形成的对心理特征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31
或者,
在形成成人个性差异方面,共享的环境所起到的作用极其微小,几乎无关紧要。 32
不知不觉中,这样的表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成了一种断言,家庭一点也不重要。这样的逻辑似乎在说,放手向前吧,别在意你的孩子,他们的个性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一些人谴责研究者带给大家这样的想法。可是,稍微读些细节,你会发现书中一直在小心地否定这种谬见。一个快乐的家庭会给你除了个性以外的东西,例如幸福。家庭对个性的形成也很重要;一个孩子绝对需要在家庭中成长,这样才能使个性得到好的发展。只要她可以生活在家庭里,那么无论这个家庭是大还是小,是穷困还是富裕,是群居还是隐居,是成立已久还是新近组成的,这些都无所谓。一个家庭就像是维生素C,你需要它,否则你会生病。但是你一旦拥有了,储备过多也不会使你更健康。
对于那些信奉精英统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发现。它意味着,人们没有理由去歧视出生于低层次背景的人;也不必用异样的眼光打量那些来自不寻常家庭的人。一个各方面条件匮乏的童年并不会令一个人形成某种个性。环境决定论和基因决定论一样,都是不合理的,我在整本书中都会谈到这一点。幸运的是,我们不必相信其中任何一种。
双胞胎的个性研究引发这样一种批判意见,我会将它穿插到接下来的论述里,即基因是后天的代理人,其程度至少相当于它们是先天的代理人。该批判依赖这样一个事实,遗传度完全取决于环境。在一群经历同等甚至是相同的培育模式的美国人中,个性的遗传度也许会很高。但是,把几个来自苏丹的孤儿或新几内亚人的后代丢到他们之中去,个性的遗传度就会迅速下降,现在就是环境在起作用了。如果维持环境稳定不变,那就是基因起决定作用。多么神奇啊!“在法庭上我都可以证明,”研究记忆基因却无暇从事双胞胎研究的蒂姆·塔利(Tim Tully)说,“遗传度和生物学毫不相干。” 33 在某种程度上,双胞胎研究者若是说测量遗传度就是他们的研究目的,那就是在自我欺骗。而且,他们已经得到明显的证据,显示基因的确影响个性,那接下来他们还会做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在揭示到底哪些基因能发挥影响作用方面,孤立的双胞胎研究一向都爱莫能助。
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通常情况下,人性中某些特征的遗传度最高,这些特征由众多基因所决定,而不是受单独几个基因作用的影响。而且,越多的基因参与其中,遗传度就越高,这是由基因的附带影响而非直接影响造成的。例如,犯罪就有相当高的遗传度。一些收养的孩子后来留有犯罪记录,他们的行为更像是其亲生父母的,而非养父母的。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定的犯罪基因,而是因为他们特殊的个性让他们容易违反法律,这些个性是遗传下来的。正如双胞胎研究者埃里克·特克海默(Eric Turkheimer)所言:“难道真的有人认为,那些愚笨的、讨人厌的、贪婪的、冲动的、情绪不稳的人或酗酒的人不会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成为罪犯吗?这些性格特点真的完全不受基因遗传的影响吗?” 34
尽管双胞胎研究大获成功,但人类行为中的少数特征仍显示出较低的遗传度。幽默感就是一个低遗传度的例子,被收养的、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有着相似的幽默感,但分开养育的双胞胎的幽默感却相当不一样。人们的饮食偏好也几乎没有遗传度——你的饮食偏好来自早时的经历,而不是由基因决定(老鼠也是如此)。 35 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来自共享环境的强烈影响——自由派或保守派父母也会将自己的偏好传给子女。宗教派别也是通过文化而非基因传递的,不过不包括宗教虔诚度。
那智力呢?有关于IQ遗传度的争论自从出现以来便饱受争议。最初的IQ测试设计粗陋并带有文化偏见。20世纪20年代,由于相信智力具有高遗传度,并担心智商低的人过度生育,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下令给心智缺陷者做绝育手术,以防止他们将不好的基因遗传下去。之后,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自此以后,甚至有关IQ可遗传的论断都会遭到尖刻的谴责,反对者会抨击提出者的声誉,并强烈要求他们撤销此言论。第一个遭难的便是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他于1969年在《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立刻受到不少攻击。 36 到了20世纪90年代,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理·默瑞(Charles Murray)在《弧线排序》(The Bell Curve)中宣称,社会正由于人们都按照选型婚配的方式,即按照和自己相符的智力以及种族来选择配偶,而自我割裂、划分出不同阶层。这个论断引起了一大批学者和记者的又一波愤怒抨击。 37
但是,我怀疑,如果你在普通人中展开一次民意调查,你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几乎没有改变。大多数人相信有“智力”这回事,即是否具有与生俱来的才能来进行脑力活动。他们的孩子越多,就越相信这一点。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相信,可以发掘有天资的孩子的智力,然后将其通过教育的方式传给没天分的孩子。但他们仍然认为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
分开养育的双胞胎研究明确支持以下观点,尽管一些人擅长做这些事,一些人擅长做那些事,但仍然有整体智力这回事。这就是说,智力的大多数测量尺度相互关联。那些在综合测试或词汇测试中得分高的人,通常也擅长抽象推理或数字归纳推理的任务。一个世纪以前,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首次发现了这一点。他是高尔顿的追随者,以g因素来指代一般智力。如今,不同的相互关联的IQ测试中所得到的g因素,仍然是一个有力的标尺,可以预测孩子将来在学校的表现。在心理学领域,对g因素的研究比其他任何研究都要多。多元智力理论总是来来去去,但智力的关联性研究一直是热点。
什么是g因素?它是统计测验中得到的一个真实数据,以大脑中的智力活动的方式体现出来。它关乎思维速度或大脑尺寸吗?或者,它是一种难以察觉的东西吗?首先我要说的是,到目前为止,对g基因的寻找只带来了莫大的失望。一些基因在遭到破坏后会造成智障,但它们若只是发生细微的变化,还没有哪个基因能导致智力程度的改变。在智力超凡的人中,研究者随机调查他们的基因,以求发现在哪些方面与常人的基因不同,可迄今为止,他们只发现一个像样的统计相关性(指的是位于6号染色体的IGF2R基因),以及其他2000多个未经证实的相关性。这就像大海捞针,大海太大,针又太小。一些候选基因,例如可能会影响神经元信号传递速度的PLP基因,却只能在很小程度上解释反应时间的长短,与g因素并没有多少相关性。由此可见,高智力等于高速运行的大脑的说法看来没什么希望。 38
一个可以清楚预测智力的物理特征是大脑尺寸。脑容量和IQ的相关性约为40%,这个数字为大脑小的天才和大脑大的笨蛋的存在留有很大余地,但这仍是较强的相关性。大脑由白质和灰质组成。2001年,大脑扫描仪已经可以用来比较人们大脑中的灰质容量。在荷兰和芬兰两地分别展开的独立研究中,研究者发现g因素和灰质容量有很强的相关性,尤其是在大脑中一些特定部位。两地的研究还发现,同卵双胞胎的灰质容量相关性高达95%,而异卵双胞胎的灰质容量相关性只有50%。这些数据说明有一些东西完全受到基因的控制,它没给环境影响留有多少余地。用荷兰研究者丹尼尔·波斯迪玛(Danielle Posthuma)的话来说,灰质容量“完全归因于基因因素,与环境因素无关”。这些研究虽没有让我们更接近了解哪些属于真正的智力基因,但它们确定了智力基因的存在。灰质由各组神经元组成,这个新发现的相关性说明了,比起普通人,更聪明的人在理论上会有更多的神经元,或者神经元之间有更多的连接。在研究者发现ASPM基因可以通过神经元数目决定大脑尺寸以后(见第1章),g因素的某些基因似乎很快也会浮出水面了。 39 然而,g因素不是一切。双胞胎研究也揭示了环境对智力的影响作用。和个性不同,智力受到家庭的强烈影响。对双胞胎遗传度的研究、对收养子女遗传度的研究,以及对这两类的综合研究最终汇成同样的结论。IQ大约有50%是“叠加遗传”的,25%是受共享环境的影响,剩下的25%是受个人独有的环境因素影响。因此,智力和个性截然不同,它更容易受到家庭的影响。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的确令你更容易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不过,这些平均数值掩盖了两个更加有趣的特征。首先,你可以找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样本,与平均值相比,他们的IQ相对差异更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非基因的影响。埃里克·特克海默发现,IQ的遗传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在由350对双胞胎组成的样本中,有一些人曾在极端穷困的环境中长大,最富有的双胞胎和最贫穷的双胞胎之间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差异。在最贫穷的孩子们之间,个人的IQ分数体现的可变度几乎可完全归因于他们共享的环境,而不是基因类型。在富裕的家庭里,事实恰恰相反。换句话说,每年只有几千块钱的生活会严重降低你的智力。但是,每年有4万美元或40万美元的生活,则不会造成人们的智力产生多少差别。 40
这个发现具有显著的政策意义。它暗示,比起减少中产阶级中的不平等,提高贫困人口的安全保障更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的机会均等。它也强有力地证实了我之前提及的一点:即使个人成就的相对差异可以完全解释为基因的作用,也并不代表环境就不重要。在大多数样本中,你之所以发现基因有强烈的影响,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非常幸福、相互关心、富裕满足的家庭里。如果没有这些,那基因也无能为力。这一点对个性也同样成立。你的父母不可能因为对你更严厉一点便改变了你成年以后的个性。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他们曾经把你每天都锁在房间里长达10小时,每周如此,那么你的个性一定会有所改变。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体重的遗传度。在西方社会里,人们有充足的食物,那些体重增加更快的人一定带有刺激他们吃得更多的基因。但是在苏丹或缅甸的荒凉之地,极端贫困是普遍现象,人们随时面临饥荒,每个人都深受饥饿之苦,那么那些胖人无疑是那里最富裕的。在这里,体重的相对差异由环境造成,而不是基因。按照科学家的行话来说,环境影响是非线性的。在两个极端之处,它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在稍微居中之处,环境的微小变化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隐藏在那些平均数值中的第二个惊喜就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基因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共享环境的影响则越来越小。你的年龄越大,家庭背景对IQ值的影响程度就越小,你的基因则起到决定性作用。亲生父母聪明的孤儿,被一对愚钝的父母收养,他也许在学校的时候表现不怎么样,但当到了中年时候,他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量子力学教授。而一对愚笨父母留下的孤儿,被双双获得诺贝尔奖的父母收养,也许在学校时表现相对出色,但到了中年时候,他可能会从事一份对阅读技能和思维能力要求都不高的工作。
从数字上看,西方社会里20岁以下的人之中,“共享环境”对IQ相对差异的影响大约为40%。但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中,这个百分比骤降为零。反之,在婴儿时期,基因对IQ相对差异的影响为20%;到了儿童阶段,百分比上升为40%;在成人阶段,又升为60%;到中年以后,甚至升为80%。 41 换句话说,当你和他人生长在同样的环境里,而且你仍处于这个环境中,那么环境的确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它不能持续至你离开共享环境后的阶段。收养子女在童年时期生活在一起时,他们有相似的IQ值。但是当成年以后,他们的IQ值基本上不相关联。对于成年人来说,智力和个性一样,大多受到遗传的影响,部分程度上受到个人经历中独有的因素影响,极少一部分受到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这是一个有违直觉的观点,它摧毁了以往那种认为基因先起作用,后天影响在后的观点。
这似乎能够反映,孩子的心智经验来自旁人;而成人则自己发起智力上的挑战。“环境”并不是什么僵化的实物,而是由本人主动挑选的一系列独特的影响因素。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套固定基因,将预先设定他倾向于经历某种环境。拥有“运动”基因将让你想在体育场上锻炼;拥有“知识性”基因将让你想要参加智力活动。基因是后天的代理人。 42
类似地,基因又如何影响体重呢?大概是通过控制食欲。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那些最胖的人通常最容易感到饿,因而他们吃得更多。一个因基因而肥胖的西方人和一个因基因而偏瘦的西方人的差别在于,前者更有可能买一个冰激凌吃。到底是基因还是冰激凌导致了他的肥胖呢?当然是二者兼而有之。基因导致一个人外出并置身于某种环境带来的影响中,冰激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然,在智力方面,情况也是一样。基因影响的是你的求知欲望,而不是能力。它们不会让你聪明,只会让你更喜欢学习。因为你喜欢学习了,因而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于是你就更聪明。先天只能通过后天来起作用。它只会刺激人们来寻求满足自己渴望的环境因素。环境则放大了这些微小的基因差异,将喜欢运动的孩子推向会给他们回报的运动,将求知欲强的孩子推向会给他们回报的书本。 43
行为遗传学得到的主要结论似乎极其不合常理。它告诉你,在决定个性、智力和健康方面,先天起了作用,即基因的确重要。但它并没有说这一定要以牺牲后天为代价。它证明了后天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只不过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目前研究者还不太能阐明后天是如何起作用的。(环境实验中还没有什么研究能达到先天实验中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研究的效果。)在一个重要的方面,高尔顿大错特错。先天并没有主宰后天;它们不是在相互竞争;它们不是对手;先天与后天根本没有相互对立。
矛盾的是,如果西方社会里的智力遗传度已达到很高的程度,那就意味着我们将贴近精英统治这种状态,此时一个人的背景一点儿也不重要。但这也揭示了有关基因的一些令人惊奇的真相。基因变化是在人类行为的正常范围以内。你也许会预想,基因就像是维生素C或维生素家族,只有在其功能失常时才会使人在某方面受限。因而,受到损害的基因可能会导致罕见的心智受损,如同它们可能会导致罕见的疾病。严重的抑郁、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都可能由罕见的基因变异所导致,但是它们也可能是源于罕见、怪异的养育方式。这样一来,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将会出现,只要你有正常的基因和一个正常的家庭,那大家就会有相同的潜在个性与智力。一些具体的细节就交给偶然事故或环境来决定。
但事实并非如此。行为遗传学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一些基因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正常人的经验范围内影响我们的个性。我们中有些人有两个缬氨酸,有些人有两个蛋氨酸,这不仅位于BDNF基因,也位于那些影响个性、智力和心智其他方面的基因。有些人的肌肉力量天生比其他人更强,这是由17号染色体上的ACE基因版本所决定。 44 因此,有些人天生就更善于汲取知识,这也是源于某个未知基因的某个版本。这样的基因变异并不罕见,它们很普遍。
从进化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则丑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正常”基因的变异呢,或给它一个专有名称:多态性?当然,这些“聪明”的基因变体会逐渐将那些“愚钝”的基因变体推向灭亡,迟钝的基因变体会淘汰那些易兴奋的基因变体。在提供、体现生存和择偶优势方面,一种基因变体一定会优于另一种。这种优越的变体会赋予他的拥有者更强的能力,从而成为繁殖力旺盛的祖先。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一些基因会以这种方式灭绝。在全人类中,基因的不同版本似乎可以和谐共存。
令人费解的是,人类中存在的基因变异,要比科学预测的更多。回想一下,行为遗传学并非发现什么决定了行为,而是发现什么在变化。答案就是基因在发生变化。与大众想法相反,大多数科学家喜欢难解之谜。他们的工作就是寻找新的谜题,而不是收集事实。在实验室中穿着白大褂的那些人的人生里总会带着一线希望,去解答一个真正的未解之谜或悖论。这里便有一个机会。
对于这个未解之谜,有大量的理论可以予以解释,但没有哪一个完全令人满意。也许,我们人类已经简单地放宽了自然选择的要求,依赖迅速增生的基因变异而维持生存。但是其他动物为什么有同样的基因变异呢?也许有这样一种精妙的平衡选择,它始终眷顾那些罕见的基因变体,以防止它们灭绝。这个想法肯定地解释了免疫系统中的变异性,因为疾病会攻击基因的常见版本,而不会光顾那些罕有的版本。但是,我们不能立刻明显地了解,为什么个性里要维持多态性。 45 也许婚配选择鼓励了多样性的存在,或者,将来会出现某个新观点对此现象做出解释。对多态性的各种对立的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里就已经导致演化论者中出现各个派系,至今仍未有定论。
通常在这个时候,一本关于行为遗传学的书会在先天后天争论的两方之间摇摆不定,要么尖刻批评先天论者,要么恶意抨击后天论者。我也许会提出双胞胎研究的动机是含糊的,设计上有缺陷,解释显得愚蠢可笑,而且它可能会鼓动法西斯主义和宿命论;或者我可能会说,这些研究可以适当且合理地矫正白板说疯狂而又武断的观点,这种教条式的理论迫使大众以为天生的个性或心智并不存在,一切都是社会的错误。
我对这两种观点都有些赞同。但是我决不会被诱导而做出此类评论,给先天后天之争火上浇油。哲学家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准确地抓住了要点:“如果你跟进这场辩论中任何反对一方观点的说法,你会感到很震惊,因为他们会错误地引用对方的言论,常常脱离语境,将对方所说的话做出最坏的阐释。于是误解盛行于世。” 46 以我的经验来看,当科学家互相批判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最常犯错误的时候。当他们断言他们偏好的观点是对的,因而另一种观点是错的时,他们在第一点上是对的,在第二点上即是错的,因为两种观点都可能在部分程度上是对的。就如同探险者争论尼罗河源头位于哪条支流一样,他们漏了一点,即尼罗河可能源于两条支流,否则它只是一条小溪。任何遗传学者如果说他发现了基因的某种影响,因而环境一点也不重要,那么他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任何一个营养学家如果说他发现了某种起作用的环境因素,于是基因没有任何作用,那么他说的也是废话。
IQ的例子就清晰地体现出这种现象。此现象被称为弗林效应,由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发现,它发现人类的平均IQ测试分数在以每十年增加至少5分的速度稳步提高。这表示环境的确影响了IQ;它暗示着,与我们的祖父母相比,我们可称得上全都徘徊于天才的边缘,这似乎难以置信。不过,现代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无论是营养、教育还是心理激励,都使得每一代人比其父母获得更高的IQ测试分数。因此,有那么一两位营养学家(不是弗林)自信地说,基因的作用比想象中要小。但身高的类推情况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由于营养更好,每一代的身高都比他们的父母高,但没有人会因此提出基因对身高的影响比想象中小。实际上,现在更多的人的身高已充分发挥了其潜能,身高相对差异的遗传度可能会增加。
弗林现在认为,他所理解的这种效应,参考自欲望激发能力的这种观点。在20世纪,社会逐渐赋予孩子们更多的奖赏,以激励他们去学校中追求知识上的成就。由于得到了回报,他们的反应便是更多地运用大脑中的一些部分。以此类推,篮球的发明激励了更多的孩子来锻炼篮球技能。结果,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篮球打得更好。同卵双胞胎的篮球技能相似,因为他们在能力上的起跑线一致,又对这项运动有着同样的渴望,于是带来了同样的练习机会。到底是欲望还是能力在起作用,这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得了的。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孩子和另一个孩子有着相同的基因,因而将来也可能获得同样的经验。 47
在晚年时期,弗朗西斯·高尔顿终究没能逃过曾俘获很多杰出之士的诱惑。他写了一本乌托邦式的作品。像自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以来所有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一样,这部作品中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愿意去那里生活。它有力地提醒了人们一点,这个主题贯穿于整本书中,即人性形成原因的多元论。高尔顿在阐述遗传因素在人性中的强大力量方面是对的,但他认为因此后天培育毫不重要,这是错的。
高尔顿的这本书创作于1910年,他那时已80多岁。书名为《不能说在哪里》(Kantsaywhere),它是以一位名叫多诺霍(Donoghue)的人口统计学教授的日记的形式来叙述的。多诺霍来到了这个“不能说在哪里”的地方,这里由一个完全实行优生政策的委员会所统治。他结识了奥古斯塔·全花哨小姐(Miss Augusta Allfancy),她正打算参加优生学院的一次荣誉测试。
“不能说在哪里”的优生政策由“默默无闻”先生(Mr.Neverwas)创立,他留下所有的钱用于优化人种。那些因拥有遗传天赋而在优生测试中得分突出的人将会得到各种奖赏;那些仅仅考试及格的人只获准少量繁殖后代;而那些没能通过测试的人将被送到劳动营里,虽然任务不是特别繁重,但他们必须永远单身。不合适的人如果进行繁殖,那就是对国家犯罪。多诺霍陪同奥古斯塔参加各类聚会,在聚会上会见那些可能成为她伴侣的人,因为她要在22岁结婚。
高尔顿是幸运的。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拒绝出版这本书。高尔顿的侄孙女伊娃(Eva)也尽力不让此书流传于世 48 ,她意识到这本书将会给世人带来多少难堪。只不过,她那时没有预料到,高尔顿描述的极权统治社会竟成了对20世纪的恐怖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