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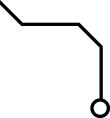
科技创新的高投入、高成本特性使得R&D经费成为影响国家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不断加大R&D经费投入以缩短与创新强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但从创新产出视角来看,我国每年的新产品上市数量和创收虽连年提升,但产品创新程度较低,原创性成果和领先国际的核心技术发明较少(吴中伦,2016 [38] )。这种R&D经费投入与创新成果产出严重不匹配现象使得如何提高R&D经费配置效率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众多研究也证实了资源配置会对企业效率产生显著影响(Bakay等,2011 [40] )。白云朴和朱承亮(2014)研究了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创新效率问题,发现R&D经费投入强度对R&D创新效率产生正效应,而R&D经费配置效率对R&D创新效率却具有负效应 [19] 。由此可见,R&D经费的配置不当是我国R&D创新效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科技研发资源,使R&D经费配置和使用效率达到最优,是今天科技创新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彭宇文,2009) [41] 。目前关于R&D经费配置结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经费来源结构、创新类型结构、创新主体结构、省域配置结构和行业配置结构五大方面。
目前普遍认为R&D经费来源主要有三条途径:政府投入、私人(企业)投入和金融机构投入。针对这三条经费来源途径,目前学术界从两个研究视角进行探讨:一是以政府投入与私人(企业)投入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视角,这些学者大多认为政府投入通过影响私人投入来影响创新效率(王俊,2011) [22] ,且私人投入对主体创新效率的影响普遍表现为促进作用;二是对比不同R&D经费来源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此达到优化经费来源配置的目的。
(1)政府投入与私人投入的关系研究
政府投入与私人投入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目前主要分为两个流派,分别是促进流派和挤出流派。促进流派学者认为,政府R&D投入能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Hamberg, 1966 [42] ;Feldman, 2006 [43] )。Hsu和Hsueh(2009) [37] 、Klette和Moen(2012) [23] 分别使用美国437家企业的业务数据、中国台湾初创企业的9年及127个研发项目数据、挪威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证实了促进效应的存在。在对航空业以及民用空间技术进行的研究中,Mowery(1985) [44] 和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l999)采用了不同的方法,研究了公共科技资金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依旧得到了互补的结论。Leyden等(1989)进一步计算出政府投入对私人投入的促进程度,他们考虑到了政府R&D经费投入对私人R&D预算的直接作用和知识共享产生的间接作用,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计算出私人投入与政府投入之间的弹性系数约为0.34 [45] 。
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反,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随着企业所接受的政府R&D资助的增加,用于研究的私人投入比例降低,由此可以解读为产生了“挤出效应”(Higgins, 1981 [46] ;Link, 1982 [45] )。Busom(1999)分析了西班牙对私人R&D经费投入及对雇用科技人员提供补贴性贷款计划的效果,认为30%的企业可能会出现完全的挤出效应 [47] 。Goldfarb(2008)以政府R&D资助为对象研究了R&D经费的不同来源对科学产出的影响问题,通过相应的调查发现:政府资助对象选择并非取决于企业或研究人员的学术优势,对于短期商业或学术价值而言,学术产出的引用数和刊物发表情况等指标经常不太实用。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和企业的职业发展和创新产出(论文)与政府关系的亲密程度呈反比 [48] 。Wallsten(1999)以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为对象,进一步研究了政府R&D资助的替代比例,发现公共研发拨款以将近1:1的比例替代了私人研发投入 [49] 。Catozzella和Vivarelli(2014)利用意大利企业级别的数据样本,最后得出在不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的情况下,政府R&D经费资助和企业投入产出为负相关的结论 [50] 。Montmartin和Herrera(2015)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政府R&D经费资助方式和补贴率两个控制变量,通过动态空间面板数据研究了25个OECD成员国的1990—2009年的数据,验证了政府R&D经费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都会对企业R&D经费投入产生挤出效应 [51] 。
以上两种看似不同的结论,究其原因在于样本数据、研究对象、变量选择等存在差异。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政府R&D经费资助时期(Dominique, 2000 [52] )、不同滞后期选择(姜宁和黄万,2010 [53] )以及不同区域(肖丁丁,2013 [54] )等因素的差异都会导致研究结果产生不同。因此未来研究应当更关注于政府R&D经费资助效果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政府R&D经费资助效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帮助政府控制资助金额和筛选资助对象,优化资助结构。现有文献已经呈现出重点探究该问题的趋势,尤其是关于企业规模(Cerulli和Potì,2012 [55] ;Meuleman和Maeseneire, 2012 [56] )对政府资助效用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却不尽相同,需要之后的学者更深入地挖掘。
(2)不同R&D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R&D经费来源不同会导致创新绩效产生差距(李成刚和吴涛,2007 [57] )。这是因为不同来源的研发经费对企业研发具有不同的监督和激励效用,因此应当优化各种经费来源的结构比例,以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Huang和Xu, 1998 [58] )。
已有研究表明,尽管政府研发经费和私人研发经费都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但相对于政府资金来说,私人资金的产出弹性更高(Huang等,2014 [59] ),梁莱歆等(2009)利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对比了企业自有资金、政府资金和金融机构资金三种资金来源途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自有资金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金融机构融资和政府资金比重过大却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60] 。这与Rajan(1992) [61] 、郑军和翟华云(2012) [62] 、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 [24] 的研究结论类似,他们指出,金融机构的信息收集和处理优势远大于其他组织机构,因此创新主体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从金融机构获取信息以谋取利益,而非通过创新来获取收益,这阻碍了企业创新。
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可以通过甄别和帮助那些具有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的企业来实现经营绩效进而促进技术创新(Schumpeter, 1912 [63] )。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了长期贷款,这些R&D经费投入不仅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风险保障,分散了科技企业发展的金融风险,在国家创新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Goldsmith, 1970 [64] ;King和Levine, 1993 [65] )。例如,Kortum和Lerner(2000)通过对美国风险投资对促进科技创新的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美国经济中风险投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效率比传统的企业投资要高得多 [66] 。George和Prabhu(2003)以印度和芬兰为例证明了金融机构在提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和国家整体创新方面的重要性,且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67] 至关重要。Hall(2000)发现风险资本对创新的影响不仅在于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这种融资渠道缓解了企业创新的高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68] 。
综上所述,政府投入、私人投入和金融机构投入不仅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三者之间也存在相关性。私人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促进作用;政府投入通过影响私人投入来影响创新绩效,且其影响效果尚存在分歧;而金融机构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也尚无定论。究其原因在于研究对象存在差异,例如,区域差异会导致R&D经费来源对创新绩效发挥不同作用(刘顺忠,2004 [69] ;刘俊杰和刘家铭,2011 [70] ),因此,不仅要研究经费来源结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应当关注其中的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创新可分为三大类型,分别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其中基础研究是不带有任何专门的或者特定应用目的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其成果以科学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反映了知识的原始创新能力。应用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其成果形式多以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为主,反映了对基础研究成果应用途径的探索。试验发展则是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知识进行产业化的过程(孙晓华和王昀,2014 [25] )。
早在21世纪之前,学者就证明了基础研究会提高社会回报率(Griliches, 1958 [71] ;Evenson等,1979 [72] ;Norton和Davis, 1981 [73] ;Huffman, 1994 [74] ),在此基础上Toole(2012)、Guellec和Van(2003)等采用求偏指标弹性法,计算了基础研究对不同产业创新成果的弹性系数 [75] [76] 。随后,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不同创新阶段研发投资的作用,温珂和李乐旋(2007)、李宾(2010)指出我国的R&D投资存在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偏低、企业对基础研究投资不足的问题 [77] [78] ,这种结构性“比例失调”对产业核心技术创新产生了消极影响(柳卸林,2011 [79] )。这个结论得到了大量学者的支持,例如杨立岩和潘慧峰(2003)通过构建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基础研究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80] 。而关于基础研究的强度,肖广岭(2005)认为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强度与经济水平、中央政府R&D经费资助比例,以及科研院所和机构在整个国家R&D经费执行结构中占比呈正相关 [81] 。Czarnitzki(2011)等将R&D活动分为“R”和“D”两部分,即基础创新和实践创新,他通过OECD调研中得到的1999—2007年比利时企业数据,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具有促进作用,且对于基础创新类项目作用效果更好 [82] 。与Czarnitzki(2011) [82] 不同的是,Clausen(2009)运用挪威的数据,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的“研究补贴”(research subsity)起到促进作用,而“发展补贴”(development subsity)却会产生挤出效用 [83] 。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结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王金妹等(2011)通过对福建省R&D经费配置结构研究发现,在不同科技活动类型配置中基础研究对科技活动产出影响最大,实验发展次之,应用研究影响较小 [84] 。严成樑和龚六堂(2013)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R&D驱动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基础研究支出占R&D总支出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该结论 [85] 。孙晓华和王昀(2014)构建了反映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与生产率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OECD的23个国家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了不同研发投资对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从作用时期来看,试验发展对当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功能发挥则存在一定的时滞,且基础研究的滞后期更长;从影响效果来看,基础研究的偏效应大于应用研究,而试验发展的作用显现虽然非常迅速,但其对生产率的带动效果相对较弱。因此,过多地依靠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并不是提高一国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应充分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和积累,以发挥其在促进生产率中的核心地位和长效作用 [86] 。黄苹(2015)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算了各地区不同活动类型技术创新要素投入的单效率,结果显示:基础研究的各创新要素投入单效率高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要素投入单效率 [26] 。与这些研究不同,蒋殿春和王晓娆(2015)测算了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发现R&D投入对试验发展的效果最强,余下依次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是因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更多的是创新产出,而非生产效率 [14] 。
综上所述,从创新效率视角来看,大量研究表明,基础研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明显大于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Czarnitzki, 2011 [82] ;Clausen, 2009 [83] ;黄苹,2015 [26] );从经济发展视角来看,一些学者认为基础研究的滞后期过长(孙晓华和王昀,2014 [86] ),因此试验发展的R&D投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蒋殿春和王晓娆,2015 [14] )。这些研究多是对比分析了不同创新类型的R&D经费投入效率,并为政策向基础研究倾斜提供理论依据,但针对R&D资金在创新的三种类型中应当如何配置,每个阶段的配置比例如何,并未做出科学的回答和解释。因此,未来学者应当在各阶段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对R&D资金的配置结构进行研究,从而实现R&D资金的优化配置。
关于不同创新主体R&D投入绩效的评价研究。大多数研究认为,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三大研发主体中,高等院校的R&D效率最高,科研机构的R&D活动无效率,企业的R&D效率有待提高。例如张浩和孟宪忠(2005)运用DEA方法对1996—2001年科研院所、企业和高等院校三类机构R&D效率进行的评价和比较分析表明,1996—1998年高等院校的R&D效率最高;科研机构R&D活动无效率,但在1999年之后有所改善;企业的资金和人员投入最多,但效率却最低且随着投入的增加无明显改进,说明投入不足并不是造成R&D效率低下的关键因素 [87] ;余晓等(2010)从总量和结构等角度对浙江省三大研发主体R&D投入状况及相对效率所做的评价分析表明,浙江省R&D投入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R&D效率都较高,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效率规模报酬递增明显,而企业呈现下降趋势 [88] ;樊维等(2011)运用DEA方法对2003—2008年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三大研发主体R&D投资结构与效率进行的比较分析认为,高等院校的R&D效率最高,企业的R&D效率在2008年达到了有效水平,科研机构的R&D效率始终处于无效状态 [89] 。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带动作用弱于企业。如吴玉鸣(2006)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模型研究全国31个省份高等院校的科研能力以及企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作用不显著,高等院校与企业研发结合尚没有发挥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而企业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贡献 [90] 。王楚鸿和杨干生(2010)以全国高校1992—2006年R&D经费投入和1993—2007年科技产出面板数据为依据,采用AHP、DEA等方法,分析了全国高等院校R&D经费投入的产出效率。结果发现:1992—2006年,全国高等院校R&D经费投入产出效率整体偏低且波动较大,且适当减少经费投入有利于提高高等院校的科技效率 [21] 。
在此基础上,最新研究已经不单单对三大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做出评价,而是更关注于产学研合作方向,也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协同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形成是基于多元主体彼此间核心能力的互补与融合,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引导高等院校的知识成果符合市场需求,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利用丰富的基础资源为企业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三者核心能力的互补与融合,能够充分释放彼此间创新要素活力,提高创新效率(周正等,2013 [27] )。国外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例如Soh和Subramanian(2014)认为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可以提高企业专利水平,而相对于理论研究,技术重组性创新的合作效果更好 [28] 。Scandura(2016)研究了高等院校和企业的研发合作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他认为研发合作之所以能够促进创新是因为高等院校—企业合作相当于共享了R&D人员,而R&D人员的增加会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29] 。
综上所述,针对创新主体的R&D经费投入效率研究,一些学者对比了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三大主体的创新效率,大多数研究发现高等院校的创新效率最高,科研机构无效率,企业的创新效率有待提高(张浩和孟宪忠,2005 [87] ;余晓等,2010 [88] ;樊维等,2011 [89] );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认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核心能力合作创新,实现资源互补和创新效率的提升(周正等,2013 [27] ;Soh和Subramanian, 2014 [28] ;Scandura, 2016 [29] )。这些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R&D政策制定和提高创新效率具有指导意义,但在产学研体系中,R&D经费在三大创新主体间如何分配、如何控制创新资源在主体间的流动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学者在研究R&D经费配置效率时,往往会分区域研究,最常见的分区方式就是分省域研究。大量学者对比分析了不同省域的R&D经费投入的产出效率,例如,王晓红等(2009)运用面向投入的C2R模型和超效率DEA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十五”期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R&D效率,结果显示:“十五”期间我国各省市的R&D效率整体处在下行区间,且省(自治区、直辖市)间差异先扩大再减少,但整体差异仍较为显著 [91] ;曹霞和于娟(2015)选用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们认为中国省域研发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较大的无效率现象,且各省域研发创新效率差异性较大,发展不均衡 [31] ;曹贤忠等(2015)从投入产出效率视角,构建研发资源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中的CRS、VRS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变化趋势以及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从空间格局上来看,江苏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显著高于上海和浙江,且长三角城市群研发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分异程度正在逐渐缩小 [32] ;宗声(2014)也承认了这种R&D投入效率的空间差异性,并认为这是R&D投入规模和资源利用效率不同,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拥挤程度和纯技术效率的差异导致的 [92] 。
在上述学者对比分析R&D经费投入产出效率的省域差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对R&D经费内部配置结构做了进一步探究。如肖泽磊等(2012)在此基础上利用改进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0—201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R&D效率和经济绩效,不仅对比了各地区的投入产出效率,更是对资金配置结构进行了研究,发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研发的无效率因素中政府冗余投入最大,因此在这些地区应当适当降低政府投入比例 [93] ;王晓珍等(2013)使用谱分析和网络DEA,以医疗器械产业和医药产业为例分省域测度了科技经费配置效率,并对未来各省域在这两个行业之间的资金配比情况提供了政策建议 [94] ;王晓珍(2012)以高技术产业为例,更深入而具体的研究了科技经费在国家、省域和产业之间的三级配置情况,并提出了资金配置方案 [30] 。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统计数据大多以省域为单位,目前较多的学者们分省域研究了R&D经费配置效率的空间差异性,并普遍承认我国R&D效率的空间差异较为显著,由此可见,我国省域之间的R&D经费配置不均衡,存在较大的可优化之处,这也为本研究成果研究省域之间的资金配置优化方案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目前也有一些学者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资金配置研究(肖泽磊等,2012 [93] ;王晓珍,2013 [94] ),但大多研究也仅是对资金配置倾向提供了建议,鲜少有学者回答了如何配置,具体配置方案如何设计这一问题。
大多数学者在分产业研究R&D经费投入产出效率时,均以高技术产业及其五大子产业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例如吴瑛和杨宏进(2006)考虑科技资源投入的滞后性与累积性,用R&D经费存量值代替当年值,以此用DEA模型计算出1995—2004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95] 。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下不同行业的结构变化将会影响整个产业的科技配置效率;孟卫东和孙广绪(2014)使用类似的方式,以R&D经费存量代替当年值,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行业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指数不同,导致各行业的稳定性存在明显差异 [96] ;王晓珍(2012)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回归分析证明了升级和产业间的不同配置结构显著影响创新 [30] ;韩东林和徐晓艳(2015)利用2009—2013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的统计数据,采用DEA模型评价比较后也发现,高技术产业五个子行业的R&D效率差异较大 [33] ;曹勇和苏凤娇(2012)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改进的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和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通过对比分析1995—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下属五个典型行业的R&D投入效率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进一步深入剖析了差距成因 [97] 。单春霞(2011)更是通过对比分析高技术产业中五类制造行业的R&D投入产出效率,明确指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存在13.6%的投入资源浪费,应进一步合理配置资源 [98] 。
除高技术产业外,一些学者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R&D创新绩效对比分析,例如,韩东林和陈晓芳(2015)认为大型制造业企业是我国经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提高大型制造业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创新,并采取DEA模型对我国大型制造业企业20个行业的R&D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定量评价发现,我国大型制造业企业R&D投入产出效率普遍低下,不同行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大 [34] 。焦翠红等(2017)采用动态OP协方差分解方法,结合我国2001—2014年制造业数据测算R&D资源配置效率和演变趋势,进一步检验政府创新补贴对R&D配置效率演变态势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R&D资源配置整体呈现恶化趋势但恶化速度逐步趋缓,行业间R&D资源错配是配置效率恶化的主要来源;分行业来看,加工制造业R&D资源配置效率正朝优化方向演进,但装备制造业R&D配置效率加速恶化;政府R&D补贴对R&D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呈倒U型效应,且大部分行业处于倒U型左侧 [20] 。
综上所述,我国R&D创新效率整体偏低,不同行业的R&D经费配置效率差距较大,因此为了提高我国投入产出效率水平,缩小行业间的差距,必须优化资源的配置结构,发挥优势行业的带动作用,以此提高整体行业R&D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