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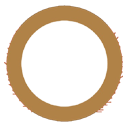
吃过晚饭,奶奶还想摸索着再捻一阵棉线。冬梅给她扫了炕,铺好褥子,安排奶奶睡了。
石头坐在天井里的一块石板上,定定地望着漆黑的天空,一动不动。天空,星星眨动着不安的眼睛,偶尔传来一两声夜游鸟的叫声。冬梅说:“石头,还坐在凉石板上干什么?睡觉吧!”
“我不睡!”石头说。
“咋哩?”
“姐姐,我又惹你生气啦?”
“没有哇!”冬梅用力笑了一下。
“不对!”黑地里,仿佛看到石头乌黑的眼睛闪跳了一下,“我看见啦,你今儿晚上没吃饭!”
“我吃过啦,吃得比你可多!”冬梅掩饰着。
“你骗人!”石头说,“过来,我看看你的脸!”
冬梅真个坐到石头面前。九岁的弟弟伸出冻得胡萝卜一般的小手,轻轻抚摸着姐姐那热得发烫的脸颊,然后,他勾住姐姐的脖子,两只黑眼珠贴紧姐姐的眼睛看了半天,又突然说:“要不,姐姐,是又想咱爹啦?”
“对,想爹啦!”
“也想陈老师吧?”
“也想陈老师!”
“区上武工队怎么不来了呢?连陈老师也不见影啦!姐,他们还回来吧?”
“还回来,”冬梅说,“说不定明天你睡醒一觉,他们就扛着枪回来了。”
“那可好!”石头高兴地说,“等陈老师回来,我就再去上学,我要赶快长大,跟武工队叔叔要杆枪,也去当个八路军,一枪崩了潘彪,给咱娘报仇……”
“对,报仇……”
停了一阵,石头又问:“明儿个,你还上虎头崖吧?”
冬梅点了点头。
“别去啦!”
“怎么?”冬梅抬起头来,“那里山柴多呀!”
石头扁了扁嘴,不以为然地说:“砍柴!哼!跑两道山梁子,砍那么一点儿柴呀—我看出来了,你心里有事,瞒着我!”
冬梅吁口气:“好,不去啦!天不早了,睡吧!”
冬梅拉起弟弟,进屋躺到炕上,给弟弟盖上那条补丁摞补丁的被子,两人都睡下了。
深秋的凉风从崮顶上扑下来,从树梢上滚过,山松林子发出一阵呜呜的吼叫,像夏天山洪暴发,铺天盖地卷过来的滚滚涛声。屋后柿子树上,几片潮红色的叶子从树枝上飘落下来,在天井里滚动着,扑跌着,呼的一声扑打在窗棂上。去冬糊的残破的窗纸,一阵阵呼嗒呼嗒扇动着。日本人封锁禁运,今年竟连一张糊窗纸也买不到,小窗上只好挡一个高粱秆穿的破锅盖。一阵风过,锅盖滚落下来,沙土沙啦沙啦落到脸上,落到那又薄又硬的被子上来。
过了许久,风势似乎小了一些。冬梅轻声喊:“石头,石头!”弟弟没有回答。这孩子翻腾了一阵,总算睡着了。
冬梅轻轻坐起来,披上衣服,悄悄打开屋门,来到天井里。她侧耳听听,山村里一片安静。于是,便从房檐底下摘下那把柴刀,推开栅栏门,走到街上。然后,沿着寂静的街巷,拐出村口,爬上东岗子,向笊篱坪悄悄奔去了。
漆黑的夜晚,山路像一条随风飘动的带子,斜挂在陡崖峭壁之间。风冰凉冰凉,扑到身上会立即吹出一片鸡皮疙瘩。冬梅一点儿也没感到冷,脑门上反而渗出一滴滴汗珠,胸口也扑扑跳动着。她跨过一棵倒下的枯树,踢翻几块路上的石子儿,脚步匆忙地朝前走去……
仔细看来,山里的黑夜并不是混混沌沌一团漆黑,有的地方黑得发蓝,有的地方黑得放亮,有的地方发出幽幽的青光。那巨石和悬崖,有的像伏虎,有的像奔牛,有的如同一条腾空而起的巨龙。草棵里沙沙响,是一只过路的刺猬吗?是一只迷路的山鸡吗?松林里黑压压一大片,里面藏着鬼子汉奸安下的暗哨吗?那突然一闪的,可是一只什么精灵怪兽的绿森森的眼睛?
一只野兔突然蹦起来,晕头转向撞到冬梅的腿上,又从她脚底逃开,跳进深涧里去了。什么东西突然拉住冬梅的衣角,她猛力一扯,衣服哧的一声撕开,原来是一丛野酸枣。那葛针扎进了肉里,流出血来了。
开头,她头皮不断一奓一奓,毛发时不时一根根竖了起来。走着走着,她逐渐放开胆子,冒汗的手握紧柴刀,迅速朝山里大步走去。
她走着,脚踏着坑坑凹凹的山路。倚天而立的青石崮,你长年累月地站在这里,对于面前这个小小的沂蒙山的女儿,你是再熟悉不过了。当她降落到你那湿漉漉的山草堆里,才第七天,母亲要上山砍柞树,去烧制潘家屋里冬天取暖的木炭,就只好把她放在你山脚下一块石板上,让从峪口扑来的山风,抽打着她那蒙着一层淡红色茸毛的小脸蛋了。有一次,山里的大蚂蚁钻进她的鼻孔,去舔噬那散发着婴儿乳香的黏液,把肉红的鼻头啃去麦粒大一块嫩肉,顺着脸蛋渗出一滴滴殷红的血珠。她在你的泥土里打滚,哭喊,长大。她那软软的小手,自己填进嘴里的第一件食物,是从你的石缝里抓到的一片苦菜叶子,把小嘴唇染得惨绿惨绿,涩得小舌头三天伸不出来。然后,她会爬了,光脚上沾满了泥巴,胳膊上挂满了草屑,小手扯住一丛刺蓬棵,用力摇晃着,大声吵嚷着,喊叫着……她越喊声音越高,把山林深处那滚滚的涛声盖住了。“真是一个山丫头!”娘流着热泪,擦着她手上的血珠说。
打从她记事,爹就在潘家当长工。
有一天夜里,爹躺在炕上,老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里,门外传来潘彪的声音:“石太兴!石太兴!”
爹蒙着被子大声哼哧起来。
娘隔着房门朝外说:“少掌柜的,真不巧,他病了,发高烧……”
“真败兴!”潘彪骂道,“挺尸也会找个好时辰!”
门外几个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这一夜,小冬梅仿佛觉得要出什么事,半宿没睡着。天蒙蒙亮,听到西山里传来两声沉闷的枪响,山峪里发出一阵阵轰轰的回声。
第二天,到西山干活的人们回来说,那两个给潘兰田修坟、雕花、做棺木的外乡匠人,死在西山深涧里了。
这两个人冬梅认识,是爷儿俩,说话是听不大懂的外路口音。小孩子一听就想笑,还故意舌头不打弯,学着他们那重浊的舌根音。这爷儿俩手艺可真巧,他们在潘兰田那磨砖对缝的坟墙上,半尺厚的柏木棺椁上,刻上云头山水,仙桃寿糕;刻上八仙过海、状元及第;还刻上青龙紫凤、玉鸟仙鹤。一出出戏文故事,刻得活灵活现。孩子们睁大惊奇的眼睛,看他们阴沉着脸,一声不响,让木屑砖末顺着刀尖流下来,落到那冻得裂开血口的大手上。他们直刻了一个冬天,昨天完了工。潘兰田摆上酒宴答谢送行,酒席上用红漆托盘捧出两人的工钱:一百元白花花的现大洋。年老的父亲把钱抖抖地装进怀里,谢了东家,说是第二天起早就要回山西老家,探望那离开一个冬天的家人老小。想不到,他们竟血肉模糊地躺到山涧里,一动不动了。
“咳!”柳泉峪的老人们含着泪花说,“碰上土匪啦!这些畜牲心真狠哪!”
过了几天,几匹快马刮旋风一般扑进柳泉峪,冲进冬梅家的栅栏门。衙役们跳下马来,进门不由分说,从腰里掏出绳子把爹娘五花大绑,死拖活拽地押到八十里以外的县城里去了。
“庄乡不幸,出了匪类!”潘兰田站在黑油大门的青石台阶上,点画着湘妃竹玉石嘴长烟管说,“两口子穷极生疯,图财害命!哪知天意不可欺,落得个这等下场!哼!”
庄里人都知道冬梅爹娘冤枉。有个叫石山根的老汉跟石太平说:“咱二兄弟叫潘兰田算计着啦!这条老狗逼着他到西峪口砸杠子,替他夺下那一百元现洋!这种烂肠子的勾当太兴自然不干,不光装病不去,还在事前朝那两个师傅露了口风。不想他们没走脱,太兴反而让老狗咬着了。”
石太平卖上二亩薄地,到县政府去告状。不用说,这几个钱连给县大堂门前的石狮子点眼都不够。石太平奔波了几个月,连张状纸也没递上,就被衙役们一顿乱棍打回来了。
不久,娘就被折磨死了。爹也被问成死罪,秋后就要处决。
一天夜里,爹从监牢里逃回来了。他头发像一蓬乱草,人瘦得皮包骨头。可那双深藏在眉棱底下的眼睛,却更像黑夜里两颗永不熄灭的火星。他伸出大手,抖抖地摸着女儿的头发:“冬梅,我走啦!记着,向前看,天不转地转,总有个天亮的时候!”
爹一去就没有了音信。有人说他下了关东,有人风传他上了口外。那潘兰田却站在十字街口的高台阶上张罗,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石太兴早被抓住,已经砍头处决,那告示就贴在济南韩复榘那府院大堂的玉石影壁上。冬梅经过这场变故,仿佛一下子长成了大人。看起人来,明澈的眼睛变得更加深邃了,仿佛要穿透皮肉看看对方的骨头是什么颜色。她一句话不说,一滴泪不流,光是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地干活,打点着一家三口的粗糠野菜、衣食用度。只有老年的奶奶知道,每当夜深人静,小小的孙女躺在炕上,从狭小的窗口望着漆黑的夜空,不断轻声自语着:“向前看,天不转地转,总有个天亮的时候!”泪水把装在枕头里的高粱壳子浸透了。
今年春天,庄里来了个名叫陈虹的女教师。这位老师真有些奇怪,竟然动员穷人的孩子去上学,而且不收学费和书钱。她来动员石头了,冬梅冷冷地望着她,一声不吱。又一天早晨,天蒙蒙亮,她踏着露水走来,送来了一封信。那个用马兰草纸做成的信封,不知经过多少人辗转传递,早磨烂了。可信纸上那颗红星,却那么闪亮,那么水灵,那么光彩照人。信是爹捎来的,上面说,他当了八路军,跟着毛主席为穷苦人打天下。信上头一句话就是:“向前看,天不转地转,总有个天亮的时候!”
冬梅扑到陈老师怀里,身子抽动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一天,梁上那对燕子从南方回来了,呢呢喃喃叫着,像有多少贴心的话要跟冬梅说,却又总也说不完。窗前的石榴树,长出第一个花骨朵,绷紧了通红的小嘴,仿佛再也兜不住满心的欢喜,眼看要笑了。母鸡生了一只大鸡蛋,飞到草垛上,老是咯咯嗒咯咯嗒叫个不停,引得树上的翠鸟、黄雀,一齐唱了起来。中午村里来了一个货郎,冬梅用半年来梳头攒下的头发,换了一支花杆铅笔,又用旧布给石头做了个小书包。日头压山,她从柳泉里一连挑了十几担水,浇了房后的小菜地,又捎带着把街口不知谁家的几棵小树也浇了浇。她脸色红红的,鬓角挂满珍珠般的汗珠,轻快地挑着瓦罐,让清水泼泼洒洒溅到石板路上……
欢乐和希望闯进这个小小的柴院。冬梅知道了毛主席,知道了共产党,明白了许多翻身解放的道理。虽然还是天天吃着粗糠野菜,可她那脸色渐渐变得又红又嫩,头发变得又黑又长。穷苦的团瓢里仿佛天天鼓荡着和煦的春风,洒满了明丽的阳光。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敌人开始秋季“扫荡”了。潘彪收起“抗日救国”的旗号,投了日本,首先朝小学校下手了。他带领一个班,放了一通手榴弹,攻进了学校。屋里没有人,只见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墙角堆着一摊纸灰,学生作业本整整齐齐放在条桌上,连最后一本的错别字也仔细改过了。黑板上写着:
同学们:
汉奸潘彪要来抓我,学校暂时放假。开学时间另行通知。
陈虹
陈老师走后,第三天,虎头崖上就开了一仗。接着就传出风声,说有个八路军伤号躲在那山峪密林之中。从那时起,冬梅一闭上眼就看到:在那陡峭的山崖上,在那密密的树丛中,有一个佩戴着八路军臂章的人,身上流着血,正在忍受着伤痛的煎熬,躲避着敌人的搜捕,经受着随时会被鬼子残害的危险。冬梅瘦了,眼窝陷了下去。在她面前,那个受伤的人,一忽儿是个男的,一忽儿又变成女的;一忽儿是她认识的区上的干部,一忽儿又是个从未见过的人。但那是一个八路军,一个同志,一个亲人。她觉得,仿佛不是那个八路军,而是她自己,一个小小的沂蒙山的女儿,肢体在经受着难熬的痛楚,生命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今天早晨,她不顾一切,以砍柴为名,到虎头崖找了半天,结果什么踪影也没有发现。正在她坐立不安、心急火燎的时候,突然听到了石头和留孩的那一段话。咳,她不该去虎头崖,应该去笊篱坪啊……
笊篱坪那迷迷茫茫的轮廓在昏暗的天幕上显露出来。然后,冬梅来到那黑黝黝的秫秸丛跟前了。
她的心口不由得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她深深地吸口气,镇静了一下自己,然后,轻轻掀开一个秫秸,仄着身子钻了进去。
“同志,同志!”冬梅压低了声音喊着。
没有回答。只有秋风翻动着秫秸叶,发出沙啦沙啦的声音。
秫秸丛里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
汗水从冬梅鬓角滚下来,她身子一软,一下子坐到枯草上。
外面,一只夜游鸟凄凉地叫了一声,迅速飞过山口。山峪里传来一两声令人毛发倒竖的怪叫—好像是真正的狼嚎……
冬梅提起柴刀,拱出秫秸丛,四外瞄了瞄,又向远处另一处秫秸丛疾步奔去……
轰隆一声,不远处一块石头从悬崖上滚了下来,落进深涧。
冬梅连忙回头一看,只见身后不远,站着一个矮矮的黑影,像半截木桩,又像一只竖起的碌碡
 。然而,黑影动起来,向自己慢慢挨过来了。
。然而,黑影动起来,向自己慢慢挨过来了。
“谁?”冬梅握紧柴刀,低沉而又严厉地喊道。
“姐姐!”迎面传来石头的声音。只见他手提短把镰刀,赤着双脚,胡乱披一件破夹袄,来到了冬梅跟前。
“你怎么来了?”冬梅生气地说。
石头嘟着嘴,不说话。
“天这么黑,你来干什么?”冬梅忙把夹袄替他穿好。
“我听着你开门出来,就跟着来了。”石头说,“你心里有事,又不告诉我……姐,说了吧,我帮你!”
冬梅摸摸石头那冻得冰凉的脸蛋,望望那一双站在山崖上的破鞋头,没有再说话。
“说了吧,姐姐!”
不能再瞒他了。冬梅说:“石头,今儿晚上的事跟谁也不能说,懂吗?”
“懂!”
“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吐口,明白吗?”
“明白!”
“那好!你来了,就帮我找吧!”
“找什么?”
“找一个人,找一个像陈老师那样的好人。”
“在哪里?”石头四处张望着。
“这个好人受了伤,就在这山里藏着。”
“是一个八路军吗?”
“对,一个八路军!”
石头一双眼在暗夜里闪动着,晶亮晶亮。他立即跟姐姐一起,沿着草丛石缝,慢慢搜寻起来。
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比作大海里捞针,也许还不能准确地表示出它的难度。笊篱坪四周,有多少石缝?多少深涧?多少石洞?多少树丛?他们找了一道山峪又一道山峪,搜了一个树丛又一个树丛,钻了一条石缝又一条石缝……他们不能呼唤,不能弄出一点点声音。只能用眼睛、耳朵和神经,去感觉,去谛听,去搜寻。只能伸出两双小手,在无边的山野里,掀开一块块石头,拨开一丛丛野草,像捉迷藏般地去寻找那个谜一样的人。高山哪,你是这么大;密林哪,你是这么深;亲人哪,你在哪里?你是否知道,有两个沂蒙山的儿女,用柳泉的乳汁养大的孩子,正在苦苦地寻找着你,为你的伤痛焦虑,为你的安全担心哪!
冷汗从他们的脊背上流下来,不知什么时候碰破的伤口,滚下一滴滴血珠……
但是要找的人没有找到。
东方露出一道白光,山下传来一两声鸡啼。
“你回去吧,石头!”冬梅顺手割下一抱山草,“背着它,要是碰上人,就说是早起进山来割草的。”
“你呢?”
“我再翻过山梁去找一找。”
“我不,”石头说,“我跟你一道。”
冬梅想了想,又说:“那咱就一道去找吧!天亮了,说不定碰上进山干活的,那更得多加小心!”
“嗯。”
两人站起来,向更远的一架山梁望去。
突然,石头惊叫一声:“姐姐,你听!”
冬梅心口一颤。在这同时,她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声音。
这声音是从不远的一棵松树下传来的。它开头十分细微,好像山溪呜咽,时断时续;突然如同人兽相搏,发出一阵撕裂金石的尖叫;然后又戛然而止,渐渐变成一阵痛楚的呻吟,仿佛一线游丝在夜空中轻轻颤动……
冬梅立即飞身向前,扑到松树脚下。
这是一棵枝叶茂密的山松。紧贴地皮,长出一层层繁枝密叶,如同一挂密不透风的帘子,把脚下的土地严严封住,不留一点儿空隙,看上去活像一座尖顶宝塔。冬梅拨开树枝,睁大眼睛瞅了一阵—枝叶间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那声音却又从树底下传了出来,而且更加清晰了。这是一个病人的呼唤,是一个昏迷了的妇女的挣扎。
冬梅一急,用力推了一下。说来也怪,那松树竟轻轻倒了下来。
看明白了!原来这松树是早已刨倒,又故意伪装把它罩到地皮上的。在它脚下,在那密不透风的枝叶掩盖下,竟藏着一个土坑,里面半卧着一个人。这是一个女八路军,短发从帽檐下露出来,臂章在夜色里发出淡淡的光亮。冬梅摸一下她的脸,竟像火炭一样烫手。肩胛上,大腿上,血水的细流滴下来,沾到冬梅手上。她两眼紧闭,鼻孔里发出阵阵呻吟,已经昏迷过去了。
突然,她猛力坐了起来。也许是战士那根内在的、永不昏睡的神经唤醒了她。她伸手习惯地朝腰里一摸,却没有抓到枪,就顺势向前打出一拳。但她伤势太重了。拳头无力地碰了一下冬梅的手臂,就软软地垂了下来。
“陈老师!”石头惊叫一声。
是她,是咱们的陈虹老师!
想是听到了呼喊,陈虹睁开眼睛。她却没有说出什么,身子一歪,就又昏迷过去了。
东天泛出一片霞光,山岭的轮廓逐渐分明起来。
冬梅说:“天亮以后,说不定敌人又来搜山!石头,快帮我扶起陈老师,我背她回家!”
“我背!”石头说。
“你还小,你背不动!”
冬梅说着,连忙蹲下身子,用那裹在破旧衣服里的瘦瘦的脊背,那十四岁贫苦女儿的幼小的脊背,那背过无数山柴、野草的脊背,迅速背起陈虹,向前走去。
用山里的大麻纳成的坚硬的鞋底,在山路上坚实有力地迅速走过……
哦,又听到柳泉那叮咚叮咚的声音了。流过家乡土地的泉水呀,你为什么永远清澈见底,一尘不染?是由于经过了沙石的千次过滤,万遍澄清,你才洁净得像面前这一双儿女那明澈纯真的眼睛一样吗?你为什么永远奔腾不息,喷珠吐翠?是由于你从大山底下涌来,汲取了地球母亲博大无边的力量,才能这样不屈不挠,永远前进吗?
霜冻真大,石板路上一片银白,冬梅头发上早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这是一九四二年秋冬之交的第一场霜冻。它预示着:今年的冬天来得早,寒冷的日子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