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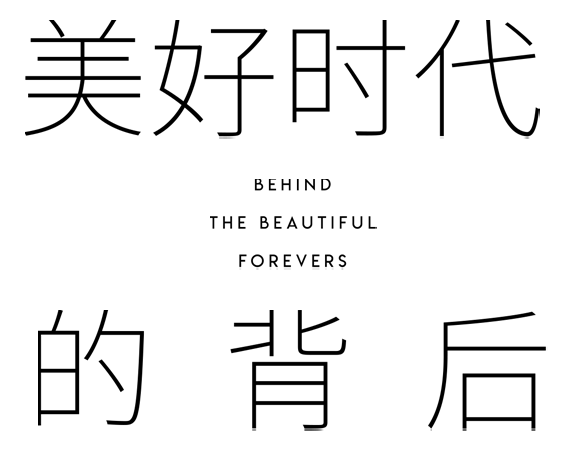
让我们暂时定格在鱼唇警察和阿卜杜勒在警察局相遇的这一刻。接着倒带,看阿卜杜勒从警察局和机场倒着跑出来,朝着家跑去。看身穿粉红花罩衫的残疾女人被火焰吞噬,火焰逐渐化为乌有,只留下地上的火柴盒。看几分钟之前的法蒂玛,随着一首嘶哑的情歌拄着拐杖跳舞,她秀气的五官完好无损。继续倒带,回到七个月前,停在二〇〇八年一月一个平常的日子。自一个小贫民窟出现在拥有全球三分之一贫穷人口的国家中最大的城市以来,这几乎是充满希望的一季。如今发展建设和金钱流动,已经让这个国家头脑发热。
黎明在狂风中到来,这在一月并不罕见,这是风筝绊在树上和伤风感冒的月份。阿卜杜勒家由于地板空间有限,不够让全部的家庭成员躺下来,阿卜杜勒因此睡在沙砾遍布的广场,这里多年来一直充当他的床。他的母亲小心翼翼地跨过阿卜杜勒的弟弟们,然后弯下身来,伏在他的耳边。“醒醒,你这傻瓜!”她充满活力地说,“你以为你的工作是做梦吗?”
出于迷信,泽鲁妮萨注意到,家里赚钱最多的日子,有时就在她辱骂过大儿子之后。一月的收入,对他们家逃离安纳瓦迪的最新计划至关重要,因此她决定把咒骂当成例行公事。
阿卜杜勒几乎没有怨言地起床,因为他母亲只能忍受她自己的牢骚。更何况,这段缓缓行进的时光,是他最不憎恨安纳瓦迪的时刻。黯淡的阳光在污水湖上投下闪闪银光。鹦鹉在湖的另一头筑巢,在喷气式客机的噪音中仍可听见它们的叫声。在有些由宽胶带和绳子粘捆在一起的棚屋外头,他的邻居们正用湿破布仔细擦洗身体。穿制服、系领带的小学生们,正从公共水龙头处拖运一桶桶水。一支懒洋洋的队伍从公厕的橘色水泥砖延伸出来。就连山羊也睡眼惺忪。在这亲密温馨的时刻过后,他们随即展开对微小市场利益的积极追求。
建筑工人陆续前往一个拥挤的路口,这是监工人员挑选临时工的地方。年轻女孩们开始把金盏花穿成花环,好在交通繁忙的机场大道上兜售。年长的妇女把布块缝在粉红色和蓝色相间的棉被上,一家公司会给她们论件计酬。在一家闷热的小型塑模工厂,袒露胸膛的男人扳动机件,把彩色珠子变成挂在后视镜上的装饰品—笑盈盈的鸭子和粉红色的猫,脖子上戴着珠宝,他们想不出谁会在哪个地方购买这些东西。阿卜杜勒蹲伏在广场上,开始整理两个礼拜以来购买的垃圾,脏兮兮的衬衫贴在他一节节的脊椎骨上。
对待左邻右舍,他普遍采用的态度是:“我越是了解你,就越讨厌你,你也会越讨厌我。因此,就让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吧。”然而,即使像这天早晨一样自己埋头干活儿,他还是能够想象,安纳瓦迪的居民们都在他身旁一起努力。
安纳瓦迪坐落于距萨哈尔机场大道近两百米处,新旧印度在这段路上彼此冲撞,延迟了新印度的发展。开着SUV的司机朝着从贫民窟某家鸡店骑自行车出来的一排送货男孩猛按喇叭,他们每个人载送三百颗鸡蛋。在孟买众多的贫民窟当中,安纳瓦迪本身并无特别之处。每间屋子都歪歪斜斜,因此不太歪斜的屋子看起来就像正的,污水和疾病看起来就像生活的一部分。
这座贫民窟在一九九一年由一群民工建成,卡车把他们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运来维修国际机场跑道。工作完成后,他们决定在机场附近诱人的建设前景中待下来。在一个几无闲置空地的地区,国际航站楼对街一小片潮湿的、群蛇遍布的灌木地,似乎是不错的居住之处。
其他穷人认为这块地太过潮湿,不宜居住,泰米尔人却着手干活儿,砍倒窝藏群蛇的灌木,挖出较干燥地区的土壤,填入泥泞之中。一个月后,他们的竹竿插在地上时,终于不再扑通倒下。他们把空水泥包装袋挂在竹竿上当作掩护,一个聚居区便形成了。附近贫民窟的居民给它取名安纳瓦迪—意为“安纳之地”,泰米尔人尊称老兄为“安纳”。事实上,对泰米尔移民的各种贬称,流传得更为广泛。然而,其他穷人目睹了泰米尔人用血汗将沼泽打造成结实土地的过程,如此的劳苦赢得了某种敬重。
十七年后,在这一贫民窟里,根据印度官方基准,几乎没有人可以被算作穷人。相反,安纳瓦迪居民属于一九九一年以来摆脱贫穷的约一千万印度人口之列。当时,约莫就在这个小贫民窟建成之时,中央政府接受了经济改革,安纳瓦迪居民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现代史中最激励人心的成功故事之一,一个仍在继续发展的故事。
的确,贫民窟的三千居民中,仅六人有固定工作。(其他人,就像百分之八十五的印度劳工,都属于非正规、无组织的经济体系。)的确,有些居民必须诱捕老鼠和青蛙,油炸后当晚餐吃;有些居民甚至吃污水湖畔的灌草丛。这些可怜人为他们的邻居们做出难以计算的贡献—让那些不炸老鼠、不吃杂草的贫民窟居民感受到他们自己有多么上进。
机场和酒店的垃圾在冬季喷涌而出,这是观光旅游、商务旅行和上流社会婚礼的高峰期。二〇〇八年的大量排放,则反映出空前高涨的股市行情。对阿卜杜勒来说更好的是,在夏季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的建设使全球废金属价格飙涨。这对一个孟买垃圾交易商来说是件开心的事,虽然这并不是路人对阿卜杜勒的称呼。有人就直呼他垃圾。
今天早晨,阿卜杜勒一边从他的破烂堆中挑拣平头钉和螺丝钉,一边努力注意安纳瓦迪的山羊,这些羊喜欢瓶罐残留物和标签底下的糨糊味。阿卜杜勒通常不在乎这些羊在旁边嗅来嗅去,可是近来它们拉出的都是液态粪便,相当恼人。
这些山羊归一个家里经营妓院的穆斯林男人所有,他认为他手下的妓女都在装病。为了扩大经济来源,他饲养山羊,以便在斋月结束时的宰牲节庆典上出售。然而,这些羊和那些姑娘们一样令人头痛。他拥有的二十二只羊,已经死了十二只,幸存的几只则有肠道疾病。这个妓院老板将此怪罪于经营当地酿酒店的泰米尔人施展的巫术,还有人怀疑是山羊的饮用水源有问题,也就是那片污水湖。
深夜,建设现代化机场的承包商会往湖中倾倒东西。安纳瓦迪居民也把东西倒在那里;最近一次,是十二只山羊的腐烂尸体。那一池水,让睡在浅滩的猪狗从水里爬出来时,肚子染成了蓝色。不过,除了疟蚊,还有一些生物在湖中幸存下来。随着清晨将近,一个渔夫涉水而过,一只手推开烟盒和蓝色塑料袋,另一只手用网子在水面泛起涟漪。他将把捕获物拿到默罗尔市场磨成鱼油,这种保健产品如今在西方极受重视,因此需求骤增。
阿卜杜勒起身甩动痉挛的小腿时,吃惊地发觉天空像机翼一样呈现褐色,阳光透过污染的雾气,显示午后的来临。整理垃圾时,他总习惯性地忘记时间。他的小妹妹们正在和“独腿婆子”的女儿们坐在一张轮椅上嬉戏,这个轮椅是用一张破塑料躺椅镶上生锈的自行车轮子组合而成的。已经放学回家的九年级学生米尔基摊开四肢靠在家门口,摆在腿上的数学课本连一眼都没看。
米尔基正不耐烦地等着他的好友拉胡尔,这个住在仅隔几户人家远的印度教男孩已成为安纳瓦迪的风云人物。这个月,拉胡尔做了米尔基梦寐以求的事:打破贫民窟世界和有钱人世界之间的隔阂。
拉胡尔的母亲阿莎是幼儿园老师,和当地的政客与警察有微妙的关系。她设法帮儿子弄到洲际酒店几个晚上的临时工作,就在污水湖对岸。拉胡尔这样一个长着大饼脸和龅牙的九年级学生,因此目睹了上流城市的富裕。
终于,拉胡尔走过来了,穿着一套由这个好运气带来的奖金购买的衣服:休闲低腰短裤,闪闪发亮、回收重量可观的椭圆扣环皮带,拉到眼睛的黑色绒线帽。拉胡尔称之为“嘻哈风”。前一天是“圣雄”甘地遇刺六十周年,印度精英分子过去认为,在这个国定假日搞豪华派对颇为庸俗。然而,当时拉胡尔却在洲际酒店的一场疯狂盛宴中干活儿,他知道米尔基非常想知道当时的每一个细节。
“米尔基,我真的没骗你,”拉胡尔咧嘴笑着说,“在我负责的大厅,有五百个穿得很少的女人,好像她们出门前忘了把下半身穿上!”
“啊,那时候我在哪里啊?”米尔基说,“快跟我说,有没有名人?”
“每个人都是名人!那是一场宝莱坞派对,有几个明星在绳子后面的贵宾区,不过,约翰·亚伯拉罕就在我附近,穿着黑色厚大衣在我面前抽烟。他老婆碧帕莎据说也在,不过我不确定那真的是她,还是只是某个美女明星,因为万一经理看见你盯着宾客看,他就会把你开除,没收你全部的薪水—他们在派对开始前跟我们说了二十次,好像把我们当白痴!你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餐桌和地毯上,当你看见一个脏盘子或一条脏餐巾,必须赶紧拿走扔进垃圾箱里。噢,那间大厅真漂亮。我们先铺上厚厚的白地毯,厚到你踩上去立刻就会陷下去。然后他们点起白色蜡烛,让房间变暗,像迪斯科舞厅一样;厨师在一张桌子上摆了两只用加味冰块雕成的大海豚,其中一只海豚的眼睛是樱桃……”
“笨蛋,别管海豚,跟我说说那些女人,”米尔基抗议道,“她们穿成那样,就是要让别人看的吧?”
“说真的,你不能看啦,就连待在有钱人的厕所都不行,你会被保安人员撵出去。不过,工作人员的厕所倒是很好,有印度式或美式供你选择。”爱国的拉胡尔选择在地上有排水孔的印度式厕所小便。
其他男孩也到侯赛因家门外,和拉胡尔会合。安纳瓦迪居民们喜欢谈论酒店和酒店里可能发生的奢靡活动。一个被药物搞得昏头昏脑的拾荒者曾指着酒店说:“我知道你们千方百计想谋害我,你这狗娘养的凯悦!”不过,拉胡尔的叙述别有价值,因为他不说谎话,或至少二十句话当中只有不超过一句谎话;加上他性格开朗,因而他的特权并未引起其他男孩的痛恨。
拉胡尔大方地坦承,与洲际酒店的正职人员相比,他不过是无名之辈。许多服务生都是大学学历、身材高大、浅肤色,拥有闪闪发亮的手机,梳头发时,甚至能用来当镜子。有些服务生嘲笑拉胡尔涂成蓝色的、长长的拇指指甲,然而在安纳瓦迪,这可是男子气概的象征。他剪了指甲后,他们又取笑他的说话方式。安纳瓦迪对有钱人的敬语“沙巴”(sa’ab),在城里的富人区不是妥当的称呼。他向朋友们报告:“那里的服务生说,这让你听起来很不入流,像流氓一样。‘阁下’(sir)才是正确的说法。”
“阁—下。”有人说道,把sir的r发成长长的卷舌音,随后,大家都开始念这个词,一同哈哈大笑。
男孩们站得很近,尽管广场空间很大。对于挨着彼此挤在房子里睡觉的人来说,皮肤碰皮肤的感觉肯定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阿卜杜勒绕过他们,在广场上弄翻了抱在怀中的一堆破行李牌,他一路追赶被吹走的牌子。其他男孩没理会他。阿卜杜勒不太讲话,就算讲话,也像是私下计划了好几个星期才说出来的话。倘若他知道怎么讲一则好故事,或许他可以有一两个朋友。
有一回,为了改正自己的缺点,他扯了个谎,说他去过洲际酒店,宝莱坞电影《迎宾》当时在那里拍摄,他还看见卡特里娜·卡芙
 穿着一身白。这是个站不住脚的谎言,立即被拉胡尔看穿。不过,每次拉胡尔带来的最新消息,都有利于阿卜杜勒丰富他未来的谎言。
穿着一身白。这是个站不住脚的谎言,立即被拉胡尔看穿。不过,每次拉胡尔带来的最新消息,都有利于阿卜杜勒丰富他未来的谎言。
一个尼泊尔男孩问起酒店里的女人。透过酒店围墙的板条,他曾经看见一些女人在抽烟,等候她们的司机把车停在门口。“她们抽的不是一根烟,是很多根烟!这些女人是从哪个村子来的?”
“听着,蠢小子,”拉胡尔说,“白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你如果连这个基本的事情都不晓得,你真的是乡巴佬。”
“哪些国家?美国吗?”
拉胡尔说不上来。“不过,酒店的客人也有很多印度人,我向你保证。”那些都是体形健康的印度人,又高又胖,不像尼泊尔男孩和这里的许多孩子一样瘦弱矮小。
拉胡尔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洲际酒店的除夕派对服务。孟买诸多豪华酒店都有众所周知的新年狂欢会,拾荒者往往可以从那里抱回一堆被丢弃的小册子。
下榻皇家艾美酒店,风光庆祝二〇〇八年!漫步在充满艺术、音乐和食物的巴黎街头,与现场表演一同绽放光芒。预订你的登机牌吧,一路顺风!每对佳偶一万两千卢比,包含香槟。
广告用铜版纸印刷,回收商每公斤给两卢比,相当于四美分。
拉胡尔对于有钱人的新年仪式感到腻了。“低能,”他下结论说,“还不就是大家喝酒跳舞,站在那里做愚蠢的事,就像这里的人每天晚上做的一样。”
“酒店那些人喝酒的时候变得很奇怪,”他告诉他的朋友们,“昨天晚上派对结束时,有个长相英俊、穿着布料昂贵的条纹西装的老板喝得醉醺醺的,他开始把面包塞进裤子和西装上衣的口袋,然后又直接往裤子里继续塞面包卷!面包掉在地上,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去捡。有个服务生说,这家伙从前肯定饿过肚子,是威士忌让他想起过去。哪天我变得很有钱,能住大酒店的话,我才不会当这种窝囊废!”
米尔基笑了,问起许多二〇〇八年在孟买的人问过自己的问题:“那么你打算做什么,阁—下,才能在这样的酒店让人款待?”
拉胡尔没有回答,径直离去,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在安纳瓦迪入口处一棵菩提树上钩破的塑料绿风筝。风筝看起来是破了,但只要把风筝的骨架压直,他估计能以两卢比的价格转卖出去。他只需趁着其他嗜钱如命的男孩尚未产生这种念头之前拿到它。
拉胡尔从他母亲阿莎身上学到这套连续创业法则。阿莎这个女人让阿卜杜勒的父母有点恐惧,她是湿婆神军政党的忠实拥护者,该党的主要成员是出生于孟买所在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印度教徒。随着大孟买地区的人口朝两千万迈进,就业和住房竞争日趋激烈,湿婆神军党指责外邦移民夺去理当属于本地人的种种机会。(该党年近九旬的创始人巴尔·萨克雷依然对希特勒的种族净化方案情有独钟。)湿婆神军党目前的鼓动目标,是清除孟买境内来自北印度各邦贫穷的移民;其对孟买少数穆斯林的仇恨更是由来已久,且持更暴力的立场。这使得阿卜杜勒这一家来自印度北方邦的穆斯林,蒙受双重的质疑。
然而,拉胡尔和米尔基之间的友谊,超越了种族、宗教和政治。米尔基有时只是为了逗乐拉胡尔,便抡起拳头,高喊湿婆神军党的问候语:“马哈拉施特拉万岁!”这两个九年级学生外表甚至有点相像,因为他们决定把前额头发留长为蓬松的刘海儿,在眼睛的部分撩开,像电影男主角阿贾耶·德乌干一样。
阿卜杜勒很羡慕他们那么亲近。他唯一的所谓的朋友,是十五岁的流浪儿卡卢,他在机场附近偷拿废品回收桶里的垃圾。不过,卡卢在阿卜杜勒入睡后的晚上干活儿,况且他们也已经很少讲话。
阿卜杜勒对他两岁的弟弟拉卢怀有深厚的感情,这让他心有所思。听着宝莱坞情歌,他断定自己的心已经变得太狭窄,他从未非常渴望得到一个女孩;即使他确信他爱他的母亲,但那并不是一股强烈涌出的感觉。然而,单是看着拉卢,他就会泪眼汪汪。阿卜杜勒畏缩不前,拉卢却无所畏惧。他的脸颊和后脑勺上,有许多因老鼠咬过而肿起来的伤口。
该如何是好?仓库变得越来越满,在高峰期这几个月,垃圾堆积在他们的棚屋里,也引来了许多老鼠。可是如果阿卜杜勒把垃圾留在户外,就会被拾荒者偷走,而他不愿意重复购买垃圾。
下午三点,阿卜杜勒正在给瓶盖分类,这是个麻烦的差事。有些瓶盖有塑料内里,必须剥除后才能归类于铝制品。有钱人的垃圾一年比一年复杂,充斥着混合材料、杂质和冒牌货。有些看起来像木头的板子,里头灌的是塑料。他该如何分类百洁布?回收厂的老板要求同一类的垃圾不能掺杂其他东西。
他的母亲蹲在他旁边,拿石块拍打湿漉漉的脏衣服,一边瞪着在门口打盹的米尔基。“怎么,学校放假啊?”她问道。
泽鲁妮萨指望米尔基在三流的乌尔都私立语言学校考过九年级,为此,他们一年缴三百卢比的学费。他们不得不缴钱,因为印度政府还没有能力普及教育。机场附近的免费市立学校止于八年级,学校的老师还经常不去授课。
“不念书,就帮你哥的忙。”泽鲁妮萨对米尔基说道。米尔基看了一眼阿卜杜勒的回收物后,便打开他的数学课本。
近来,就连看着垃圾,也让米尔基感到沮丧。对于弟弟这样的转变,阿卜杜勒尽量不让自己产生不满。非但如此,他还试着和父母怀有相同的希望:待弟弟念完中学,他那不得了的才智和魅力将战胜穆斯林在就业市场的不利条件。虽然人们认为孟买比任何其他印度城市更国际化、更重视人才,穆斯林依然被摒除在许多好工作之外,包括米尔基渴望的某些豪华酒店的工作。
阿卜杜勒明白,在一个多种语言并行的城市,人们也将他们自己分类,就像分类垃圾那样,同类归同类。孟买的人太多,不可能人人都有工作,因此,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昆比种姓
 的印度教徒,怎么会不雇用来自同邦的其他昆比种姓,而去雇用一名垃圾相关产业出身的穆斯林?但米尔基说,如今大家都混为一体,旧有的偏见已逐渐消失,只是阿卜杜勒不明白而已,因为他成天把头埋在他的垃圾堆中。
的印度教徒,怎么会不雇用来自同邦的其他昆比种姓,而去雇用一名垃圾相关产业出身的穆斯林?但米尔基说,如今大家都混为一体,旧有的偏见已逐渐消失,只是阿卜杜勒不明白而已,因为他成天把头埋在他的垃圾堆中。
此刻,阿卜杜勒要尽可能在天黑前完成工作,因为黄昏时分,魁梧的印度教男孩们便开始在广场上打板球,瞄准他分类成堆的垃圾,有时还瞄准他的头。尽管板球手们严酷地考验着阿卜杜勒的不对抗政策,但他只和两个十岁的孩子发生过一次肢体冲突,因为他们侵占了他弟弟的地盘。而这些板球手,则用他们的球拍猛砸另一个穆斯林孩子的脑袋,之后把他送进了医院。
在阿卜杜勒的头顶上空,拉胡尔正在另一棵树的树枝间跳上跳下,尝试解开另一个可供转售的风筝。树上的叶子像安纳瓦迪的许多东西一样,因为从附近水泥工厂吹来的沙砾而呈现灰色。“吸进去不会死”,老前辈向那些为浓浊空气发愁、眼睛泛红的新来者担保。然而,人们似乎不断地因病丧命,包括未经治疗的哮喘、肺阻塞、肺结核。阿卜杜勒的父亲无业在家闲荡,却提出了真正让人感到安慰的论点:水泥工厂和其他一切建设,都为这个新兴机场城市带来更多的工作;毁坏的肺,则是必须为进步付出的代价。
下午六点,阿卜杜勒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来。他击败了板球手们,在他的面前,摆好了十四大袋整理好的垃圾。四周的酒店冒出团团烟雾,通常傍晚他们以烟熏法驱赶蚊子。阿卜杜勒和他的两个弟弟将袋子拖上一辆淡绿色的破三轮老爷车。这辆小车是侯赛因家最重要的财产之一,能让阿卜杜勒把垃圾运交给回收商。这时,他来到机场大道,进入这座喇叭鸣响的城市剧院。
四轮车、自行车、公交车、摩托车、成千上万的行人……由于利拉酒店花园旁的严重交通堵塞,阿卜杜勒花了一个多钟头才开了近五公里。在酒店街角,一辆辆欧洲轿车在一家名为“汽车温泉”的公司前等候维修。城内第一条地铁轨道的一部分在此修建,是为了搭配在机场大道上方逐渐凌空而起的高架路。阿卜杜勒担心在车阵中用光汽油,不过,在天黑前的最后一道光线中,他那喘着气的老爷车总算来到名为萨基纳卡的大贫民窟。
在萨基纳卡成片的棚子中,有熔解金属和粉碎塑料的机器,拥有这些机器的人,身穿浆洗过的白色长衬衫,以显示他们自己与这一行业的肮脏之间的距离。工厂有些工人的脸因炭尘而被染黑,他们的肺肯定也因铁屑而变黑。几星期前,阿卜杜勒眼见一个男孩把塑料放进粉碎机时,一只手硬生生地被截断。男孩眼里含着泪水,却没有尖叫,只是站在那里,任截断的手流着血。他从此不再具备谋生能力,却开始向工厂老板表示歉意。“沙巴,对不起,”他对穿白衣的男人说,“我不会报告这件事,给您添麻烦。请您放心。”
尽管米尔基提过当前的进步,印度依然让一个人清楚自己的地位。阿卜杜勒认为,希望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只是一种幼稚的消遣,就好比想把你的名字写在一碗融化的雪糕里。他在他生来所属的这个被轻蔑的行业里,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而这份工作也终于不再无利可图。他决心带着完好的双手和满口袋的钱回到家里。他对他的商品所做的估价大致正确;旺季的可回收物,结合火热的国际市场,带来了一笔安纳瓦迪居民难以想象的收入。他每天赚五百卢比,相当于十一美元,这个数字已足以实行逃离安纳瓦迪的计划。
有了这份收入,加上去年的存款,他的父母不久就能为一个安静社区里一百多平方米的土地缴付头期款,此社区位于穆斯林回收者占大多数的市郊瓦塞。只要生活和全球市场都能继续走下去,他们很快就能成为地主,不再是违建户,住在一个阿卜杜勒相信再也没有人叫他垃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