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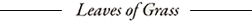
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819年5月31日出生于长岛亨廷顿附近的西山村。他年幼时只在布鲁克林上过五年学,十一岁就当了律师事务所的勤杂工,后来又在几家排字车间学排字。在1836年夏至1841年春之间的至少三年里,他在长岛各地当乡村教师,更换过将近十二所学校。不久他开始发表一些感伤主义的“墓园式”的短篇小说和少量诗歌,并于1836年办了一个周刊《长岛人》。此后他短期编辑过纽约的《曙光》和布鲁克林的《黄昏闲话》,直至二十七岁当上布鲁克林《每日之鹰》的编辑。估计于1842至1848年间,他至少曾为十一家纽约和布鲁克林的报刊投稿或工作。1840年他参加了支持范布伦竞选总统的活动,并且获得了胜利。马丁·范布伦是激进的民主派,杰克逊的继承人。之后惠特曼仍热衷于政治,曾不止一次因和报刊老板意见不合而辞职。他的政治观点在当时是激进的,他信仰“自由土地”,反对蓄奴制。所谓“自由土地”是指允许老百姓去西部开荒而不允许新开辟的土地沦为蓄奴州。他同样主张“自由贸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支持任何摧垮民族与民族之间壁垒的措施:我要求各国都大开门户。”(1888年5月)
 又说:“为什么主张自由贸易?……是为了团结:自由贸易促进团结。”(1888年12月)这个立场和杰斐逊与杰克逊的民主主义没有两样,只是在惠特曼身上多一点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味道(关于国际主义,作者在诗作和评论中还提出过许多激进的观点)。他为什么强烈要求民主?可以用他自己的两句话来概括,他说:“美国的光荣是由于她有四千万高明的普通人,他们是一些前所未有的最聪明、最伶俐、最健康、最有道德的人。”(1889年12月)参照他别的言论来说明,就是他认为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一个正在上升的阶层,就是广大的普通人,或称平常人(average persons),包括机械工、马车夫、船夫、渔民、海员、男女工人等等。他又说:“我要求人民……即那些成群的群众,人民的全体——男人、女人、小孩——我要求他们占有属于他们的一切——不只是一部分,大部分,而是全部——我支持一切能够使人民获得适当机会的任何措施——让他们过更加充实的生活……我要求人民享受应得的权利。”(1889年1月)这是他晚年说的话,足以说明诗人的这种热情与信念始终不渝,老而弥坚。
又说:“为什么主张自由贸易?……是为了团结:自由贸易促进团结。”(1888年12月)这个立场和杰斐逊与杰克逊的民主主义没有两样,只是在惠特曼身上多一点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味道(关于国际主义,作者在诗作和评论中还提出过许多激进的观点)。他为什么强烈要求民主?可以用他自己的两句话来概括,他说:“美国的光荣是由于她有四千万高明的普通人,他们是一些前所未有的最聪明、最伶俐、最健康、最有道德的人。”(1889年12月)参照他别的言论来说明,就是他认为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一个正在上升的阶层,就是广大的普通人,或称平常人(average persons),包括机械工、马车夫、船夫、渔民、海员、男女工人等等。他又说:“我要求人民……即那些成群的群众,人民的全体——男人、女人、小孩——我要求他们占有属于他们的一切——不只是一部分,大部分,而是全部——我支持一切能够使人民获得适当机会的任何措施——让他们过更加充实的生活……我要求人民享受应得的权利。”(1889年1月)这是他晚年说的话,足以说明诗人的这种热情与信念始终不渝,老而弥坚。
1848年是惠特曼一生中关键的一年。他受聘去南方名城新奥尔良当报刊《新月》的编辑。
他带着他的十四岁的弟弟杰夫经中部往南,但没有住上三四个月便辞职回到了纽约。这一旅行在惠特曼一生中是少有的,他很少长途旅行。但更加重要的是1845至1848年之间,尤其是1848年,惠特曼已在盘算是否认真当一个作家。他已发表过许多短篇小说和少量诗歌(多用传统格律)。小说中包括劝人戒酒的《富兰克林·埃文斯》(1842),据说曾畅销两万册。读书是他职业的需要:他在当《每日之鹰》编辑的时候曾写过四百二十五篇书评,其中关于小说的一百篇,历史的二十二篇,传记的十四篇,宗教的四十五篇,诗歌的二十二篇,等等。然而上述这些作品和1855年出版的《草叶集》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据西方学者考证,1845年至1848年间他已在笔记中记下了一些将成为《草叶集》内容的材料,但他还没有完全放弃编辑工作。1851年他还曾经营过一家小小的印刷店,并且兼营兴建房屋的生意。但是他已减少了政治活动,更多地转向了音乐、文学、绘画、雕塑等。十五年来(从19世纪30年代中开始),他欣赏了所有著名意大利歌剧演员——包括男高音贝蒂尼和伟大的女低音玛丽埃塔·阿尔波尼——在纽约的演出。惠特曼晚年曾说“没有意大利歌剧就没有《草叶集》”,可见影响之深。然而在文学艺术领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还只是个学徒。在此前所写的东西只是一个新闻记者和报刊编辑的分内工作,算不得真正的文学。什么是文学?应致力于哪些内容,采取什么形式?这应该是他开始认真考虑的问题了。
考虑的结果是具有伟大划时代意义的1855年版的《草叶集》,其中包括一篇综述了作者崭新的文艺观点的长序和十二篇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伟大诗篇。这两项成就说明作家的创作思想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以序文为例,有些观点作家可能早就有了,不过在这里说得有声有色。几乎所有的观点都是离经叛道,闻所未闻的。例如,在19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美国人和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认为美国是毫无文化可言的,美国生活庸俗不堪,需要虔诚地向欧洲学习。但是作者却开宗明义地说:“在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美国人的诗歌意识可能是最饱满的,合众国本身,基本就是一首最伟大的诗。”又说“合众国的天才的最佳表达者是普通人……总统向他们脱帽而不是他们向他——这些就是不押韵的诗。”“一个诗人必须和一个民族相称……他的精神应和他国家的精神相呼应……他是她地理、生态、江河与湖泊的化身。”“国家的仲裁将不是她的总统而是她的诗人。”“他是先知先觉者……他有个性……他本人就是完整的……别人也和他一样完善,只是他能看见而他们却不能。”“人们希望他指出现实和他们灵魂之间的道路。”诗人也提出了政治自由的要求。他认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所应有的态度是“鼓舞奴隶,恫吓暴君”;他的最大考验是“当前”,并从此而引申到漫长的未来。关于诗的格律,他说:“完美的诗歌形式应容许韵律自由成长,应准确而舒松地结出像丛丛丁香或玫瑰那样的花蕾,形状像板栗、柑橘、瓜果和生梨一样紧凑,散发着形式的难以捉摸的芳香。”这篇洋洋洒洒的八页长序(按照初版的对开本,双栏编排)约一万字,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新思想和强大生命力,揭开了新时代诗歌艺术,特别是美国诗歌的崭新一章。
《草叶集》初版的十二首诗充分体现了长序的精神:第一首就是居全集中心位置的长诗《我自己的歌》,所有十二首在初版中都合刊在一起,没有分篇也没有题目。按照《草叶集》最后定稿加的题目,初版还包括《职业之歌》《睡觉的人们》《我歌唱那带电的肉体》《回答问题者之歌》《欧罗巴——合众国的第七十二年和第七十三年》《一首波士顿民谣》《有那么一个孩子出得门来》。这些诗歌的次第按照作者后来的编排意图作了极大的改动,篇名也更动多次,直到1881年才最后定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十二首中绝大多数都各有特色,题材与体例多样,内容非常丰富。惠特曼诗作中有不少题目叫作“歌”(Song)。《我自己的歌》是以一个有个性的普通人为主题的史诗式长诗。《职业之歌》歌颂了工厂、农田和矿山等各种神圣的普通职业,但并非歌体作品中最佳代表(作者后来写了多首类似的“歌”,杰出的如《大路歌》《阔斧歌》《展览会之歌》等)。《睡觉的人们》最后被列在组诗《神圣的死亡的低语》前面。它描写人们在朦胧睡乡时的潜意识活动,后来受到许多评论家的高度赞赏。《我歌唱那带电的肉体》最后被安排在《亚当的子孙》中。诗人认为人体美是不会蒙受腐蚀的,只有物质的肉体才是灵魂的基础和根本:有了肉体的意识才能使灵魂的感受力和辨别力更加敏锐。他还说,诗人最感兴趣的不是人的局部而是整体,就像欣赏交响乐一样。《欧罗巴》写1848年席卷西欧的革命浪潮,虽然遇到挫折,仍然生机勃勃。诗中的名句是:“自由,让别人对你失望吧——我绝不对你失望。”《一首波士顿民谣》写一个逃跑的黑奴被一万名左右士兵戒备森严地押解着“物归原主”,这是惠特曼生平唯一的一首政治讽刺诗。《有那么一个孩子出得门来》是一首十分动人的佳作,反映了作者在早年笔记中记下的一条原则:“人们只有对他自己能够与之合而为一的东西才深感兴趣。”他写道,诗人“必须自己也像水星那样在空间旋转并疾驶——他必须像一朵云彩那样飞跑,他必须像太阳那样照耀——他必须像地球那样星球般地在空中保持平衡——他必须像蚂蚁那样爬行……他会像槐花那样在空气中喷香地成长——他会像天上的雷声那样爆炸——他会像猫一样扑向它的猎物——他会像鲸鱼那样使水花四溅……”在这首诗里自然现象在孩子身上发生了深刻影响,孩子的意识完全和自然界等同起来。大自然和外界事物成了孩子的一部分。实际上诗人不但和自然合而为一,也和人及人群合而为一(见《我自己的歌》《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
初版的《草叶集》于1855年7月上旬出现于书肆。诗人送了一些给当时美国文坛的名流。7月21日爱默生给作者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致敬信:“这是美国至今所能提供的一部结合了才识与智慧的极不寻常的作品……我因它而感到十分欢欣鼓舞……我从中找到了无与伦比的内容用无与伦比的语言表达了出来……我向你伟大事业的开端致敬……”新英格兰著名的文人梭罗和艾尔柯特访问了这位初展才华的诗人。不过普遍而主要的反应是冷淡。谩骂式的评论如纽约的《准则》上的文章认为诗集的特点是“肮脏”“淫猥”。伦敦的《评论家》上的文章认为:“沃尔特·惠特曼和艺术无缘,正像蠢猪和数学无缘一样……他应该受执法者的皮鞭。”波士顿的《通信员》上攻击它“狂妄、自大、庸俗、废话”。波士顿《邮报》上说它沉溺于繁殖之神的厚颜无耻——崇拜“猥亵”等等。同年惠特曼自己也匿名写了三篇自评文章,用坦率而通俗的文字阐述了一些他最关心的论点。这并不奇怪:初版的内容和形式,对保守的文人和一般读者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形式是奇特的,思想更加大胆。在清教主义仍占主导地位的当时,歌颂肉体,露骨地描写性行为,是不会得到人们的宽恕的。
1857至1859年之间,惠特曼时常光顾纽约的一家叫作“普发福”(Pfaff)的地下室饭馆。那里聚集了一群波希米亚式的文人与艺术家。惠特曼在那里和新成立的《星期六周报》(1858)主编亨利·克拉普交好。后者新从巴黎回国,蔑视清教主义,常常故意做出使那些彬彬君子不寒而栗的举动。惠特曼的名篇《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就是在1859年12月27日《星期六周报》的圣诞专号上作为第一篇发表的。普发福饭馆以它的名酒著称,但是在这些不拘小节的作家、评论家、诗人、演员之中,惠特曼是比较沉默而拘束的一个,从来没有喝醉过。惠特曼的艺术家生活也到此为止。作为一个靠自学取得各种知识的作家,他熟读《圣经》以及荷马、莎士比亚、司各特、彭斯、乔治·桑和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但是他散漫的生活方式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远远超过任何师承关系。他接触过许多著名文人哲士的作品,包括爱默生、卡莱尔,甚至黑格尔,但是他的思想意识和艺术方法始终强烈地保持着他个人的独特风格。
为了介绍诗人此后的创作成就,必须把《草叶集》的各个主要版本和它们的编排作一些说明。一般学者习惯于认为《草叶集》有九个版本。极为重要的是初版,已如上述。1856年的第二版增加了二十首新诗(包括名篇《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阔斧歌》和《大路歌》),并且把爱默生那封著名的来信连同自己的回信(并未寄出)作为附录与“代序”。引起爱默生十分不安的是惠特曼利用他的名声吹嘘自己,竟在书脊烫金印上了爱默生信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我向你伟大事业的开端致敬。”第三版(1860)十分重要,因为它包括了《亚当的子孙》和《芦笛》两组诗和《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这两组诗中的大部分属于作家的最佳作。这一版的第一首诗后来被题名为《从鲍玛诺克开始》,带有自传色彩。第三版之所以重要也因为作者在这里开始对全集的编排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他渐渐放弃了按照写作日期的先后编排,而是按照诗的主题和内容编排;而且随着年事日增,这些诗歌渐渐发展为作者个人的传记,即他一生的经历与感受。早在第三版的《再见吧》一诗中作者已经说:“这不是书,谁接触它就是接触一个人。”1867年第四版收入了《鼓声哒哒》和《纪念林肯总统》(内战前后的生活经历)两个诗组。自此以后的两版增添了组诗《铭文》(阐明《草叶集》全集的主题思想),直至定稿版
 (第七版,1881—1882)。在第七版中作者作了内容和文字的最后修订,作品的题目固定了下来,每一首诗编排在什么位置也定了局。此后写的诗则作为补编一、二收在全集的后面,未及在生前发表的诗则成为补编三。这一最后编排完成了诗人成长的全过程。全集开始是组诗《铭文》,点出了全集提纲挈领的主要内容;《从鲍玛诺克开始》则是自传体的开始,接着是有极大代表性的个性的史诗《我自己的歌》。《亚当的子孙》和《芦笛》描写了诗人一直关心的人际关系:男女之间的情爱,男性之间的友情,特别是后者,即诗人终生歌颂的,也是被视为民主制度基石的伙伴情谊。十多首“歌”使“自我”转向世界,并形象地描写了作者一些至感兴趣的题材,反映了作者典型的价值观。“候鸟”“海流”“路边”又泛泛地以候鸟的形象和海与大路等地点命名,写诗人的各种深刻感受。《鼓声哒哒》和《纪念林肯总统》则是他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感触;《秋天的溪流》写战后复原时的生活场景;然后从生命到死亡过渡,包括组诗《神圣的死亡的低语》《从正午到星光灿烂的夜晚》和《离别之歌》。这样的编排只勾勒了一个诗人生平的轮廓,并不是每一组诗都有严格的连贯性。每一首诗的写作年代更不在作者考虑之中。诗人自己说得好:“最好的自传不是建造成功而是自然成长起来的。”他甚至认为全集后面的两个补编
(第七版,1881—1882)。在第七版中作者作了内容和文字的最后修订,作品的题目固定了下来,每一首诗编排在什么位置也定了局。此后写的诗则作为补编一、二收在全集的后面,未及在生前发表的诗则成为补编三。这一最后编排完成了诗人成长的全过程。全集开始是组诗《铭文》,点出了全集提纲挈领的主要内容;《从鲍玛诺克开始》则是自传体的开始,接着是有极大代表性的个性的史诗《我自己的歌》。《亚当的子孙》和《芦笛》描写了诗人一直关心的人际关系:男女之间的情爱,男性之间的友情,特别是后者,即诗人终生歌颂的,也是被视为民主制度基石的伙伴情谊。十多首“歌”使“自我”转向世界,并形象地描写了作者一些至感兴趣的题材,反映了作者典型的价值观。“候鸟”“海流”“路边”又泛泛地以候鸟的形象和海与大路等地点命名,写诗人的各种深刻感受。《鼓声哒哒》和《纪念林肯总统》则是他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感触;《秋天的溪流》写战后复原时的生活场景;然后从生命到死亡过渡,包括组诗《神圣的死亡的低语》《从正午到星光灿烂的夜晚》和《离别之歌》。这样的编排只勾勒了一个诗人生平的轮廓,并不是每一组诗都有严格的连贯性。每一首诗的写作年代更不在作者考虑之中。诗人自己说得好:“最好的自传不是建造成功而是自然成长起来的。”他甚至认为全集后面的两个补编
 也应该是他那完整的一生的一部分,虽然它们的价值是无法和他的壮年之作比拟的。某些西方学者倾向于把一些结构松散的诗组说成高度有意识的安排,则显得比较牵强。这个最后编排是经过了作者七个版本的调整后才决定的,不是作者有意识地按照生活经历逐步写成的。有的西方学者把《草叶集》全集当作一首伟大的史诗,却有一定的道理。全集的这个“自我”要比《我自己的歌》中的“自我”更加宏伟,更加充实。诗人强调他的诗歌的个性力量,甚至说这不是一本诗而是一个人,这一点很重要。他说,“《草叶集》……自始至终是试图把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美国19世纪后半叶的那个我自己),自由、饱满、真实地记录下来。在当今的文学中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使我满意的类似的个人记载”。
也应该是他那完整的一生的一部分,虽然它们的价值是无法和他的壮年之作比拟的。某些西方学者倾向于把一些结构松散的诗组说成高度有意识的安排,则显得比较牵强。这个最后编排是经过了作者七个版本的调整后才决定的,不是作者有意识地按照生活经历逐步写成的。有的西方学者把《草叶集》全集当作一首伟大的史诗,却有一定的道理。全集的这个“自我”要比《我自己的歌》中的“自我”更加宏伟,更加充实。诗人强调他的诗歌的个性力量,甚至说这不是一本诗而是一个人,这一点很重要。他说,“《草叶集》……自始至终是试图把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美国19世纪后半叶的那个我自己),自由、饱满、真实地记录下来。在当今的文学中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使我满意的类似的个人记载”。
惠特曼的人生哲学中最强烈而且自始至终坚持不变的信念是美国式的民主主义。诗集名为“草叶”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详见拙译《我自己的歌》译后记)。散见在他的谈话录
 、书信、序文和评论文章中这种带浓厚感情和强烈信仰的言论真是太多太多了。专论至少有三篇:《论民主》(1867)、《论个性神圣》(1868)、《民主前景》(1871)
、书信、序文和评论文章中这种带浓厚感情和强烈信仰的言论真是太多太多了。专论至少有三篇:《论民主》(1867)、《论个性神圣》(1868)、《民主前景》(1871)
 。定稿版的《草叶集》第一首诗《我歌唱自己》(1867)写于初版问世的十二年之后。自从诗人决心把诗集编排成自传样式以后,他就想把《铭文》这组诗放在卷首,阐明诗集的中心思想,而《我歌唱自己》是其中第一首。
。定稿版的《草叶集》第一首诗《我歌唱自己》(1867)写于初版问世的十二年之后。自从诗人决心把诗集编排成自传样式以后,他就想把《铭文》这组诗放在卷首,阐明诗集的中心思想,而《我歌唱自己》是其中第一首。
我歌唱自己,一个单一的、脱离的人,
然而也说出民主这个词,全体这个词。
这是民主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独立的个人或个性,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民主,即全体。个人和个性是独立的,可以发展为完善或近乎完善;它导致多样性,导致一个一个接近于完善而各有所长的国民。民主则是全体,即集体,它要求一致性,是个统一体,即惠特曼所说的男子之间的友情,黏着性,不是涣散的而是凝结的伙伴之间的关系(诗人自称为“伙伴的诗人”)。惠特曼的民主思想不只停留在理论上。十多年的编辑生活使他熟悉了现实中的民主政体,他参加过许多政治活动,亲自经历过不少政治斗争,撰写过《第十八届总统选举》
 ,主张普通劳动者进入美国政治。在《民主前景》一文中他充分揭露了美国民主政治的阴暗面,但是他相信民主政治的远景及其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信心从未动摇过。
,主张普通劳动者进入美国政治。在《民主前景》一文中他充分揭露了美国民主政治的阴暗面,但是他相信民主政治的远景及其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信心从未动摇过。
我从头到脚歌唱生理学,
值得献给诗神的不只是相貌或头脑,我是说整个结构的价值要大得多,
女性和男性我同样歌唱。
这里诗人要求歌颂那完整的人,既有肉体,也有灵魂,整体比局部更有价值。
作者平等评价女性也是贯彻始终的。对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说来,这可能还是新鲜事物。
歌唱饱含热情、脉搏和力量的广阔生活,
心情愉快,支持那些神圣法则指导下形成的、最自由的行动,我歌唱现代人。
热情奔放、顺乎自然,而不是精雕细刻,是惠特曼诗歌的重要特点。“神圣法则”可能和初版长序中用许多篇幅阐述的“谨慎”观点
 有关。这里的“谨慎”并不意味着为人处世的“谨慎”,而是把遵循自然法则当作智者应有的道德修养。“歌唱‘现代人’”是关键,作者曾认为“诗人的最大考验是‘当代’”,而“现代”似乎还不只是“当前”,而是意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
有关。这里的“谨慎”并不意味着为人处世的“谨慎”,而是把遵循自然法则当作智者应有的道德修养。“歌唱‘现代人’”是关键,作者曾认为“诗人的最大考验是‘当代’”,而“现代”似乎还不只是“当前”,而是意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
《铭文》组诗中还有《我默默沉思》(1871),在这首诗里作者把世界当作广义的战场,而他自己的任务则是缔造勇敢的战士。《给你,古老的事业》(1871)中的事业是指“民族的进步和自由”。《事物的真象》(1876)原文是一个希腊字Eidólons,意为“幽灵”或“形象”,作者是指物体的表象后面还有一个精神的真象。《给某一女歌唱家》(1860)是献给著名女低音歌剧歌唱家玛丽埃塔·阿尔波尼的,歌剧在作者诗艺的成长中占特殊地位,在这里诗人把歌唱家和建功立业的勇敢叛逆的战士等同起来。《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1860)则是歌颂劳动者在劳动时的欢快情绪。
《亚当的子孙》及《芦笛》:前者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着重肉体;后者写男子之间的友谊,着重精神。爱默生曾规劝作者删去那些写性关系的诗篇,但是惠特曼拒绝了,他认为性、繁殖、肉体和官感是天赐的恩典,是圣洁的,而肮脏的只是人们的头脑和偏见。原印第七版(1881——1882)的出版商受到禁止出版的处分,官方特别指定《一个女人在等着我》(1856)和《给一个普通妓女》(见《秋天的溪流》,1860)必须删除。早在这以前,惠特曼还在华盛顿内政部印第安局当小职员时(1865),新任部长哈兰看见了他抽屉里的《草叶集》,就马上把这个“行为不端”的职工开除出去,引起了一场风波。惠特曼的朋友威廉·德格勒斯·奥卡诺写了著名的辩护文《白发苍苍的好诗人》(1866),并立即为他在司法部里另外找了一份工作。最近西方学者又曾对惠特曼有关肉体、性关系和繁衍意识等作了详细的考证,论述了当时流行的生理学、颅相学、优生学、招魂学等对惠特曼思想的影响。这些科学、准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的进化理论。他相信生活和人类世界的前程必然是进步的、进化的,而美丽的肉体、健康的生育本能和尽可能完善的个性便是强大的推动力。《亚当的子孙》和《芦笛》中有不少好诗,阅读时应联系惠特曼的复杂的人生哲学和广泛的生活情趣。
惠特曼的十多首“歌”是全集的许多精彩部分之一。比较重要的如《向世界致敬!》《大路歌》《阔斧歌》《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展览会之歌》《转动着的大地之歌》等。《向世界致敬!》使作家面对了全世界,艺术方法基本是“列举”,列举了世界各国。《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1856)是一首值得一读的好诗。在这首诗里不但有诗人自己,“一个单一的、脱离的人”,也有“全体”——两者构成民主的基础。这里还反映了他的一个典型思想,即人的同一性。惠特曼最感兴趣、最关切的人物和事物之一就是伙伴,就是读者,以及“其他人”。“其他人”在这首诗里就是穿着平时服装的千百万乘客,熙熙攘攘的普通人。惠特曼喜欢拥挤的人群,拥挤的大街,在那里,“个性”或“个人”完全被淹没了,只有“全体”。那么,联系着诗人个人和当前和未来的千百万乘客之间的纽带又是什么呢?首先是感官。他们看见和听见了共同的滔滔而来、滚滚而去的潮汐,特别是在摆渡过程中看见的美丽的水上风光。作者用了现在时态的词,又用了过去时态的词:过去和现在人们都有过同样的经验。时间、地点、距离都是无能为力的:它们阻碍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们不只是同时看见,还有同样的感受:“我曾经非常喜爱那些城市,非常喜爱那条庄严而湍急的河”;同样的经历(“生活过”“走过”“洗过澡”“想到过”),并且有着一个同样的肉体。甚至和“你”一样,“我”也有过同样见不得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只是在你身上才落下斑斑黑影,/昏暗也曾在我身上投下黑影。”这些客观现象被诗人称为“沉默的美丽的使者”,它们能够传递灵魂的信息,使短暂的变成了永恒的、不朽的,说明物质具有精神价值。《展览会之歌》(1871)是一首十足反映了美国生活的“歌”。诗人要求诗歌之神离开古老的欧洲,移驻到美国来。她真的来了(她“直接前来奔赴约会,为她自己有力地开辟了道路,在混乱中迈着阔步,/不怕机器的隆隆声和汽笛的尖叫声,/也丝毫没有被排水管、煤气表和人工肥料吓唬住,/微笑着,心情愉快,显然有意留下来,/她来到了这里,安置在厨房的各种设备中间!”)。诗人在这里使用了诙谐的喜剧手法,在冗长的一系列古奥的典故之后,写上了四五行地道的描写美国生活的、以通俗词汇构成的诗句。就这样让斯文的诗歌女神落脚在排水管、煤气表和厨房设备之中也许多少有些亵渎。然而这首长达二百三十八行的“歌”,自始至终使用这一手法:特别是把使用了大量玻璃与钢铁等建筑材料的美国式展览馆与古堡、大教堂和金字塔等等相比。
排列在内战的诗歌之前的另一首十分优美的诗是1859年发表的《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它仿照意大利歌剧格式,音乐性强,语言和形象十分动人。这首诗曾经受多方解释,各家评介之多,不下于《我自己的歌》。诗中那来自亚拉巴马的客人——一对雌雄学舌鸟并不是主角,中心人物是幼年和成年的诗人自己:全诗述说了他自幼儿成长为觉醒了的诗人的经过。诗的头二十二行是一个引子,描写了时间、地点和那个孩子的经历;现在成熟了的诗人又来重温旧梦。一对比翼双飞的学舌鸟在长岛的海边过着甜蜜的夫妻生活。照耀着的太阳煽动着它们的爱情:它们忘记了时间和环境。但是雌鸟突然失踪了,雄鸟变得万分孤凄。和煦的阳光也变成了劲吹的海风、星星、月亮和撞击着的浪花。这种享受过幸福后的凄凉唯诗人能够理解。他不但理解,还要歌唱。一个孩子经历了这一切,他流泪了,但是他在起步向前:一个诗人觉醒了,成熟了。那悲鸣的学舌鸟是寂寞的,那孩子和诗人也是寂寞的,但是诗人在没有完全觉醒之前,还需要一把钥匙,一点线索,以提高认识[“啊,给我提供线索吧!(在黑夜里它躲藏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啊,我既可以得到许多,那就再多给我一些吧!”]。于是大海答话了:诗人还未完全理解的那个词就是“死亡”。这是个“甜美”的词,因为“死亡”也就是永生的开始。诗人出生在海边,酷爱海洋,在他的诗歌中,他习惯于以“海岸”作为生与死的分界线:大陆代表固体的、生硬的、短暂的物质世界,而大海则代表液体的、流动的、永恒的精神世界。诗人从爱情的幸福、失恋与寂寞,从理解“死亡”,而觉醒为诗人。
组诗《海流》与《在路边》中至少有三首是杰出的短诗的范例:《泪水》《我坐而眺望》《鹰的嬉戏》。这些诗主题思想集中,语言与结构精练。这样的诗还有许多,如关于行军的若干首(详后,见《鼓声哒哒》):《转轮发出的火花》(《秋天的溪流》)、《一只沉默而坚韧的蜘蛛》(《神圣的死亡的低语》)、《致冬天的一个火车头》《曼纳哈塔》(《从正午到星光灿烂的夜晚》)等。诗人的多数作品以长或比较长的诗歌为主,句子也比较长,结构比较松散,但音律铿锵,内容十分丰富。这是诗人一个重要的思想特点:他特别留意作品的内容。他说他绝不把作品的艺术性凌驾在内容之上。他说过:“概念必须先行——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先有了清楚完美的概念才试图表达它……概念对我是如此重要,我也许忽视了其他成分……我永远避免拼凑或精心雕琢,宁可让成品像它起初形成时所暗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我粗枝大叶,使我的蛋糕味同嚼蜡。”(1888年4月)又说:“我是非常慎重的——我在用词方面十分用心,非常用心,但是我追求的是内容而不是词句的音乐性。”(1888年5月)早年他就说过:“一个装饰性的比喻都不能要,要的是透明、清澈、明智、健康——那才算得是最美最好的风格。”
惠特曼说:“在医院、军营或战地三年的那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六百次访问和巡游,总共算起来,接触了八万到十万伤病员……”“我认为这三年是我享有的最大权利和最大满足……而且当然也是我一生中所受到的最大教益……我热烈地见到了真正的‘全体’,见到了这个国家到底有多么宽阔。”(见《沃尔特·惠特曼的内战》)惠特曼在这里写的是内战时期的生活体验。北军的军事要地萨姆特于1861年4月12日受到了攻击,大战已不可避免。惠特曼于次日听到消息。比惠特曼年轻十岁的弟弟乔治参加了北军。1862年12月13日乔治作战受伤,沃尔特闻讯马上出发去找他,于19日到达前线。乔治负的伤并不严重,但沃尔特在士兵中生活了多日,同情他们艰苦的行军生活,遂决定留在华盛顿做护理伤病员的工作。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士兵们中间,用自己抄写得来的微薄工资为士兵们购买食物、邮票、信封、信纸、读物等。他还护理伤员,为他们求医问药,争取保留伤残肢体,给广大伤病员带来莫大的安慰和希望。在这些年里,他在创作方面结下了两个硕果:组诗《鼓声哒哒》和《纪念林肯总统》。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真正置身于“全体”之中了,他的伙伴意志受到了一次热情而严峻的考验。《鼓声哒哒》中的绝大多数优秀诗篇是写这种感情的,如《裹伤者》《一天晚上,我在战场上站了一班奇异的岗》《列队急行军》《在黎明的灰暗光照下扎营地所见》《我艰难地在弗吉尼亚的树林里漫步的时候》《两个老兵的哀歌》《啊,晒黑了脸的草原那边来的孩子》和《和解》,等等。诗歌中也有写号召战斗的,母亲悲悼独子战死的,还有战前就已写下的诗,等等。另有几首值得一提的是写行军和宿营的佳作,如《骑兵越津而过》《在山腰宿营》《军团在行进中》和《在野营的时明时灭的火光旁》等。
惠特曼反对脱离主义
 ,强烈要求解放三百万黑奴。在这两个政治观点上,他和林肯完全一致,他衷心爱戴、崇敬林肯总统。他从未和总统见过面,但是他多次表达了对总统的关切
,强烈要求解放三百万黑奴。在这两个政治观点上,他和林肯完全一致,他衷心爱戴、崇敬林肯总统。他从未和总统见过面,但是他多次表达了对总统的关切
 ,并在林肯遇刺后写下了不朽的悼念总统的长诗:《最近紫丁香在前院开放的时候》
,并在林肯遇刺后写下了不朽的悼念总统的长诗:《最近紫丁香在前院开放的时候》
 。其中对林肯遇刺而死的悲痛,写灵柩西运的场面确实占了不少篇幅,但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此诗又对“死亡”进行了一次哲学的探讨。
。其中对林肯遇刺而死的悲痛,写灵柩西运的场面确实占了不少篇幅,但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此诗又对“死亡”进行了一次哲学的探讨。

《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在《草叶集》第二版出书时代替了1855年初版的长序。作者用诗歌形式重复了长序的许多观点。这首诗曾经经过重大修订,1856年间长达二百八十行,其中四分之一的观点出自长序。此后又经过修订,到1867年第四版时增加了几个段落,写进了已经结束的南北战争,全诗长三百三十七行。以后又有多次修订,但只是在细节方面,到1881年定稿时,共三百三十五行,并被排列在《纪念林肯总统》组诗之后。因为战争已经结束,联邦得以巩固,生产力得到解放,国家和民主的建设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诗人在安大略湖畔沉思时,美国的守护神走来向他提出要求:“给我唱一首出自美利坚灵魂深处的诗吧。”“唱一支胜利的欢歌,/奏响‘自由’的进行曲,要比此前的进行曲更有威力,/在你未去之前,给我唱一支‘民主’诞生时的阵痛之歌吧。”全诗有相当数量的词句和初版长序的词句几乎一样。更加相同的是大体的思想内容,例如以普通人,特别是劳动者为主人公的基本思想。作者也同样提出国家最需要的是符合国情和高举“民主”旗帜的一代诗人。在这首诗里受到特别强调的是每个个人的重要性。在第三节中,诗人说:“只要产生伟大的个人,别的自会水到渠成。”在第十五节,又说:“在一切下面,是个人,/我敢说现在凡忽视个人的对我来说都不妙,/美国的契约是完全和个人结合的,/唯一的政体是那能够把个人记录下来的政体,/宇宙的全部理论是分毫不差地指向一个个人的——也就是‘你’。/(母亲
 有了你那敏锐而严格的意识,有了你手中那把出鞘的剑,/我看见你最后还是除了和个人直接打交道以外,拒绝沾染其他)。”这里的个人当然是指那个和“全体”结合的单一的、脱离的人。如果个人发育不全,民主就不能健全,惠特曼认为民主的基础就是“丰满、繁茂、多样化的神圣的个人”;又说:“一个个人而有第一流的品质、能造成一个第一流的国家的时候,个人和国家就都是第一流的。”因此,惠特曼要求每个个人都应有发展他的全部潜力的权利。
有了你那敏锐而严格的意识,有了你手中那把出鞘的剑,/我看见你最后还是除了和个人直接打交道以外,拒绝沾染其他)。”这里的个人当然是指那个和“全体”结合的单一的、脱离的人。如果个人发育不全,民主就不能健全,惠特曼认为民主的基础就是“丰满、繁茂、多样化的神圣的个人”;又说:“一个个人而有第一流的品质、能造成一个第一流的国家的时候,个人和国家就都是第一流的。”因此,惠特曼要求每个个人都应有发展他的全部潜力的权利。
《草叶集》中值得稍稍介绍的最后几首有分量的佳作也许是《风暴的豪迈音乐》(1869)、《向着印度行进》(1871)和《哥伦布的祈祷》(1874)。惠特曼素以身体健康自豪,其实在他最后瘫痪病倒(1873)的十多年前已患有头晕和头痛的病症,在他护理伤员的三四年中,曾于1863到1865年几度脑血管轻度溢血。他终于病倒时,才五十四岁。但是就在病倒之前,他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一直活到七十三岁(1892)。在1873年之后,他一直没有写出壮年时那样丰富多彩的伟大作品。在他能够行动时,曾于1879年西行,经堪萨斯、丹佛直到落基山脉,次年又去加拿大访问他的好友勃克医师;其他时间大部分花在修订、编排他的定稿版。由于1885年他又中暑,1888年又一次瘫痪,使他更加需要倚靠他人。他的年轻朋友贺拉斯·屈劳伯尔记下了自1888年1月开始的惠特曼每日谈话,即《在坎姆登和沃尔特·惠特曼一起》。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只是引用时仍应参考惠特曼的作品和其他言论。可以告慰的是惠特曼终于完成了他感到满意的“临终版”。他谆谆嘱咐希望今后以这个版本作为《草叶集》全集的最后依据。他也谆谆嘱咐《草叶集》只能作为“整体”来理解,读者不可能从中摘取什么警句、新鲜典故或比喻,把它们当作范例来吟哦:《草叶集》是一个真正壮丽饱满的“统一体”,含有普遍性意义,没有一处是雕琢而成的。
有的西方学者把《风暴的豪迈音乐》说成是惠特曼以音乐的形象写成的自传,全诗共六节。整个宇宙的音乐出现在诗人的似梦非梦的朦胧状态中,一切音乐都不是为满足诗人的乐感而是饱含各种意义唱给他那已经成熟的灵魂听的。这些席卷并震动了诗人整个精神世界的音乐包括结婚时的音乐、战争时的各种音响、远古和中世纪的音乐、大管风琴的声音、宗教仪式的曲调、管弦乐、器乐曲、风声雨声鸟雀的鸣啭声、自然界各种声音、连篇累牍的大型歌剧片段、不同国家的音乐、亚洲非洲欧洲的音乐、伟大音乐家们(如贝多芬等)的交响曲和清唱剧,等等。它们都指向灵魂,并向灵魂提供暗示。诗人敞开着心扉接受一切。在第六节,诗人醒来了,梦中的宏伟音乐给他提供了线索:它给诗人指出的,“是一种适合灵魂辨认的新的节奏”,即:“能够沟通生与死的诗篇”。
《向着印度行进》就是一首沟通生与死的诗篇,不过它的内涵比这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作者从当时已经完成的三大工程得到启发,进一步探讨了人类永远在进步、在进化这一他深感兴趣的主题。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11月17日举行了隆重的开航典礼;横跨北美东西两岸的铁路于1869年5月接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底电缆于1858年铺设完成;
 运河连接了欧亚两洲,电缆连接了欧洲与美洲,横贯北美洲的铁路连接了美洲和太平洋,亦即亚洲和美洲。不但空间完全沟通了,时间也一样:代表当前的新大陆的美洲和古老的,过去的,充满神话、寓言和宗教的亚洲也沟通了。诗人期望不但伟大的物质成就使世界连成一片,人类的精神追求也应该跟着连成一片:诗人邀请灵魂要向着印度行进,东方是人类文化的摇篮。这也是哥伦布这位探险家的梦想,他曾经志愿找一条通向印度之路,这一任务后来由葡萄牙航海家瓦斯柯·达·伽马(约1460—1524)完成了。但是哥伦布并没有完全失败,他发现了新大陆,亦即连接了全球的那代表当前的重要一角——美洲。在诗中诗人展望了运河和铁路沿线的美丽风光之后
运河连接了欧亚两洲,电缆连接了欧洲与美洲,横贯北美洲的铁路连接了美洲和太平洋,亦即亚洲和美洲。不但空间完全沟通了,时间也一样:代表当前的新大陆的美洲和古老的,过去的,充满神话、寓言和宗教的亚洲也沟通了。诗人期望不但伟大的物质成就使世界连成一片,人类的精神追求也应该跟着连成一片:诗人邀请灵魂要向着印度行进,东方是人类文化的摇篮。这也是哥伦布这位探险家的梦想,他曾经志愿找一条通向印度之路,这一任务后来由葡萄牙航海家瓦斯柯·达·伽马(约1460—1524)完成了。但是哥伦布并没有完全失败,他发现了新大陆,亦即连接了全球的那代表当前的重要一角——美洲。在诗中诗人展望了运河和铁路沿线的美丽风光之后
 ,又沿着历史的道路写亚当和夏娃直至他们的子孙
,又沿着历史的道路写亚当和夏娃直至他们的子孙
 的探索。在探险家、工程师、科学家完成了他们连接世界的事业以后,最后诗人才是上帝真正的儿子。他将和探险家、工程师、科学家完成物质文明的事业一样,完成精神领域的事业,他将把大自然和人类连接在一起,使二者融合为一体。诗的最后二节写诗人和他的灵魂在全球范围的海上航行
的探索。在探险家、工程师、科学家完成了他们连接世界的事业以后,最后诗人才是上帝真正的儿子。他将和探险家、工程师、科学家完成物质文明的事业一样,完成精神领域的事业,他将把大自然和人类连接在一起,使二者融合为一体。诗的最后二节写诗人和他的灵魂在全球范围的海上航行
 。诗人和他的灵魂是否将是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呢?有无“什么纯洁、完美、有力的计划?”有无“什么为别人而舍弃一切的心甘情愿?/为了别人而忍受一切?”诗人要求“张帆前进——只向深海处领航,/啊,灵魂要不惜一切地探索,我和你,你和我,/因为我们的去处是海员们还不敢去的,/我们将带着船、我们自己和一切,去冒一切危险”。他们将去比印度更为遥远的地方:“啊,向远些、再远再远一些的方向航驶!”第八节写诗人时常想到“时间、空间和死亡”这些问题,这样的思想并不新鲜,曾出现在他的早年诗歌中。在这里,时间、空间已连接,世界各地的距离大大缩短了,“灵魂”满足地向着死亡微笑,“死亡”意味着精神和永生。在这里,比较突出的是多次出现了“上帝”的形象,诗人要求和“上帝”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把世界连成一片,民族与邻里之间通婚,把国与国熔接在一起是“上帝”的意图;诗人和他的灵魂歌唱的将是“上帝”,他们信奉的是上帝。诗人说:“啊,上帝让我在你里面。攀登到你所在的高处,/让我和我的灵魂按照你的范围遨游。啊,你是超越一切的,没有名字,是纤维,是呼吸,/是光中之光,散布着宇宙万物,你是他们的中心,/你是真善爱的强大中心,/你是品德和精神的源泉——情感的源泉——你是蓄水池。”在这里,“上帝”似乎接近爱默生的“超灵”了。但是译者更加倾向于同意艾伦教授的分析:“超灵”是没有人的气质的,然而惠特曼的“上帝”仍然保持着人的特点。像在《我自己的歌》一诗中一样,“上帝”被称为“十全十美的同志”,是“长兄”,灵魂在完成了他的航程之后会作为“幼弟”和“长兄”亲热地拥抱在一起。还应该记得惠特曼的“人”是具有“神”的品质的,人是宇宙的中心,是史诗的主人公,而不是“上帝”。不可否认,在《草叶集》中,头三版更加强调灵魂的物质基础,他描写性活动的诗篇多属于前三个版本,这是他思想意识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渐渐使灵魂占了上风,诗人从较多的清醒的现实主义逐渐过渡到略带神秘主义的浪漫主义,“上帝”也更像是“超灵”了。这使晚年的诗人真有点预言家的味道
。诗人和他的灵魂是否将是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呢?有无“什么纯洁、完美、有力的计划?”有无“什么为别人而舍弃一切的心甘情愿?/为了别人而忍受一切?”诗人要求“张帆前进——只向深海处领航,/啊,灵魂要不惜一切地探索,我和你,你和我,/因为我们的去处是海员们还不敢去的,/我们将带着船、我们自己和一切,去冒一切危险”。他们将去比印度更为遥远的地方:“啊,向远些、再远再远一些的方向航驶!”第八节写诗人时常想到“时间、空间和死亡”这些问题,这样的思想并不新鲜,曾出现在他的早年诗歌中。在这里,时间、空间已连接,世界各地的距离大大缩短了,“灵魂”满足地向着死亡微笑,“死亡”意味着精神和永生。在这里,比较突出的是多次出现了“上帝”的形象,诗人要求和“上帝”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把世界连成一片,民族与邻里之间通婚,把国与国熔接在一起是“上帝”的意图;诗人和他的灵魂歌唱的将是“上帝”,他们信奉的是上帝。诗人说:“啊,上帝让我在你里面。攀登到你所在的高处,/让我和我的灵魂按照你的范围遨游。啊,你是超越一切的,没有名字,是纤维,是呼吸,/是光中之光,散布着宇宙万物,你是他们的中心,/你是真善爱的强大中心,/你是品德和精神的源泉——情感的源泉——你是蓄水池。”在这里,“上帝”似乎接近爱默生的“超灵”了。但是译者更加倾向于同意艾伦教授的分析:“超灵”是没有人的气质的,然而惠特曼的“上帝”仍然保持着人的特点。像在《我自己的歌》一诗中一样,“上帝”被称为“十全十美的同志”,是“长兄”,灵魂在完成了他的航程之后会作为“幼弟”和“长兄”亲热地拥抱在一起。还应该记得惠特曼的“人”是具有“神”的品质的,人是宇宙的中心,是史诗的主人公,而不是“上帝”。不可否认,在《草叶集》中,头三版更加强调灵魂的物质基础,他描写性活动的诗篇多属于前三个版本,这是他思想意识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渐渐使灵魂占了上风,诗人从较多的清醒的现实主义逐渐过渡到略带神秘主义的浪漫主义,“上帝”也更像是“超灵”了。这使晚年的诗人真有点预言家的味道
 。惠特曼曾有意把《草叶集》称作“肉体篇”,而另外再写一部“灵魂篇”,那已是暮年时的设想,因为健康的原因而不能如愿了。但是他曾一再强调他没有系统的哲学,对于《向着印度行进》,他也说:“这里没有哲学……只有进化论的内涵……展示了宇宙的最终意图。”
。惠特曼曾有意把《草叶集》称作“肉体篇”,而另外再写一部“灵魂篇”,那已是暮年时的设想,因为健康的原因而不能如愿了。但是他曾一再强调他没有系统的哲学,对于《向着印度行进》,他也说:“这里没有哲学……只有进化论的内涵……展示了宇宙的最终意图。”
作为一个辽阔博大、胸中能装下整个宇宙的诗人,他的情绪似乎只可能是欢快乐观的。但是作为一个有各种复杂感情的人,他还是有悲伤绝望的时刻。在1860年写作的《在我随着生活的海洋落潮时》里,诗人曾经说:“我至多也不过像那一点点漂上来的杂物,/拾到的一点点泥沙和枯死的叶片,/我收集起来,并把自己也当作泥沙和杂物的一部分,和它们合为一体。”在1874年(大病后的一年)写的《哥伦布的祈祷》里,更露骨地描写了一个潦倒、绝望、失意的老人的心情。哥伦布老人在祈祷时回顾了他漫长而繁忙的和笃信上帝的一生。他诉说了他的成就,他所受的苦难;贫穷、多病、受到监禁与冷落。但在他年迈智衰的迷茫中,他仿佛隐隐看见并听见远方有许多船队在传来新编的颂歌和向他致敬的声音。惠特曼自比哥伦布也因为意识到自己同样是一个探险家和创业者。
惠特曼还曾写过几首优美的政治诗,散编在各个诗组。本文尚未提到的还有:《法兰西——合众国的第十八个年头》(1860)、《给一个遭到挫败的欧洲革命者》(1856)等。他总是站在激进的革命者和正义的这一边。他毕生关心政治,他热忱的最高峰表现在南北战争时期。他是林肯的忠诚拥护者。
惠特曼对后来的美国诗歌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但主要是他所树立的个人或个性的史诗这一模式
 而不是他首创的自由诗体。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自由诗早已失去了它离经叛道的色彩,但他的诗体仍然独树一帜,只能表达他特殊的思想内容,没有人能学,不必学,也是学不来的。广大读者对他的诗体已比较熟悉,许多西方学者已多方研究。中国读者凡是熟悉郭沫若、艾青的诗歌的也知道一鳞半爪,对它并不完全陌生。尤其楚图南同志的《草叶集选》,这一部尽量忠实于原作风格的译本,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不是他首创的自由诗体。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自由诗早已失去了它离经叛道的色彩,但他的诗体仍然独树一帜,只能表达他特殊的思想内容,没有人能学,不必学,也是学不来的。广大读者对他的诗体已比较熟悉,许多西方学者已多方研究。中国读者凡是熟悉郭沫若、艾青的诗歌的也知道一鳞半爪,对它并不完全陌生。尤其楚图南同志的《草叶集选》,这一部尽量忠实于原作风格的译本,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我们已多少熟悉了惠特曼惯用的、没有规定节奏的长句以及少数有一定的诗节形式(有着同样行数的诗节,但没有规律的节奏,也不用韵)的比较紧凑的篇什和唯一的一首以传统格律写成、标格不高、但比较通俗的《啊,船长,我的船长》。读者也比较熟悉作者常用的“平行法”(由句首或句尾词类相同的句子重复出现)和“列举法”。诗句中也有时突然出现一些西班牙或法语单词,印第安名字等。还有极少数是作者在构词上的独创,如“x届总统”(presidentiad)。译者认为,惠特曼诗歌艺术的最大成就还不是上述种种,而是单句和全篇的比较含蓄却又十分丰富的音乐性。这是作者诗歌艺术的真正独创和感人之处。西方学者已经指出惠特曼的诗歌往往通篇像演说辞、意大利歌剧和汹涌的大海。这个比喻是十分准确、十分形象的。惠特曼自己说得好:“这个作家肯定不能满足当前美学作品所要求的那种精确、齐整、技巧优美。因为在当前的新旧作品中被认为是第一流的最佳作品是经过多方润色的,押韵,使用各种典雅而精致的比喻,深具匠心,说明在艺术语言和词句的严格控制下经过精雕细琢,只留下了最好的东西,然后拼凑粘牢在一起,于是出现了庙宇般的建筑美——或像一所大理石砌成的巍然矗立的宫殿,入口处是壮丽的门廊,装饰着各种雕塑,既能满足艺术感、形象感、美的享受,又能引起人们的评头品足。这个作家的诗歌却不是这样。它不像结实庄严的宫殿,不像那些装饰它的雕塑,也不像它墙上的绘画。要比就只有比海洋。诗句是流动起伏着的波浪,永远在升腾又降落:有时阳光灿烂,有时平静,有时呼啸着风暴,永远在运动着,永远自然而然像滚滚的浪涛,而每个浪头的大小、尺寸(节奏)又都不一样,从来也不会使人感到一切已完成,已固定,而是永远似乎还有更远的在前方。”(1888年7月)
总之,我们已多少熟悉了惠特曼惯用的、没有规定节奏的长句以及少数有一定的诗节形式(有着同样行数的诗节,但没有规律的节奏,也不用韵)的比较紧凑的篇什和唯一的一首以传统格律写成、标格不高、但比较通俗的《啊,船长,我的船长》。读者也比较熟悉作者常用的“平行法”(由句首或句尾词类相同的句子重复出现)和“列举法”。诗句中也有时突然出现一些西班牙或法语单词,印第安名字等。还有极少数是作者在构词上的独创,如“x届总统”(presidentiad)。译者认为,惠特曼诗歌艺术的最大成就还不是上述种种,而是单句和全篇的比较含蓄却又十分丰富的音乐性。这是作者诗歌艺术的真正独创和感人之处。西方学者已经指出惠特曼的诗歌往往通篇像演说辞、意大利歌剧和汹涌的大海。这个比喻是十分准确、十分形象的。惠特曼自己说得好:“这个作家肯定不能满足当前美学作品所要求的那种精确、齐整、技巧优美。因为在当前的新旧作品中被认为是第一流的最佳作品是经过多方润色的,押韵,使用各种典雅而精致的比喻,深具匠心,说明在艺术语言和词句的严格控制下经过精雕细琢,只留下了最好的东西,然后拼凑粘牢在一起,于是出现了庙宇般的建筑美——或像一所大理石砌成的巍然矗立的宫殿,入口处是壮丽的门廊,装饰着各种雕塑,既能满足艺术感、形象感、美的享受,又能引起人们的评头品足。这个作家的诗歌却不是这样。它不像结实庄严的宫殿,不像那些装饰它的雕塑,也不像它墙上的绘画。要比就只有比海洋。诗句是流动起伏着的波浪,永远在升腾又降落:有时阳光灿烂,有时平静,有时呼啸着风暴,永远在运动着,永远自然而然像滚滚的浪涛,而每个浪头的大小、尺寸(节奏)又都不一样,从来也不会使人感到一切已完成,已固定,而是永远似乎还有更远的在前方。”(1888年7月)
译者应该深刻感谢始终为我解答问题的来北京大学授课的柯大卫教授(Prof. David Kuebrich),他还给我提供了不少资料。经常提供我资料或解答我问题的美国朋友,还有芝加哥大学的柯尔柏教授(Prof. Gwin J. Kolb)和密勒教授(Prof.James E. Miller, Jr.),我在这里也向他们致谢。
译者最常用的主要参考资料为:
(1)盖伊·威尔逊·艾伦:《沃尔特·惠特曼手册》,1946;《新版沃尔特·惠特曼手册》,1975。(Gay Wilson Allen: Walt Whitman Handbook, 1946; The New Walt Whitman Handbook, 1975.)
(2)盖伊·威尔逊·艾伦:《孤独的歌手》修订本,1967。(Gay Wilson Allen: The Solitary Singer, 1967.)
(3)詹·埃·密勒:《〈草叶集〉评述性的指南》,1957。(James E. Miller, Jr.: A Critical Guide to“Leave of Grass” 1957.)
(4)哈罗德·布洛杰特、斯卡利·布拉德利合编:《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综合读者版》,1965。(Harold W. Blodgett and Sculley Bradley: Walt Whitman: “Leaves of Grass”, Comprehensive Reader’s Edition, 1965.)
赵萝蕤
1987年8月稿
1989年3月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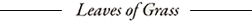
来吧,我的 灵魂 说,
让我们来为我的 肉体 写几句诗吧,(因为我们是一体,)
万一我死后不知不觉地回来了,
或是距今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来到了别的领地,
在那里又给某些同伴们歌唱,
(数说着大地的土壤、树木、风向、奔腾的浪头,)
我还可能永远喜欢地微笑着唱下去,
永远永远认下这些诗句——正像我在此时此地首先,
就在 灵魂 和 肉体 下面签上我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