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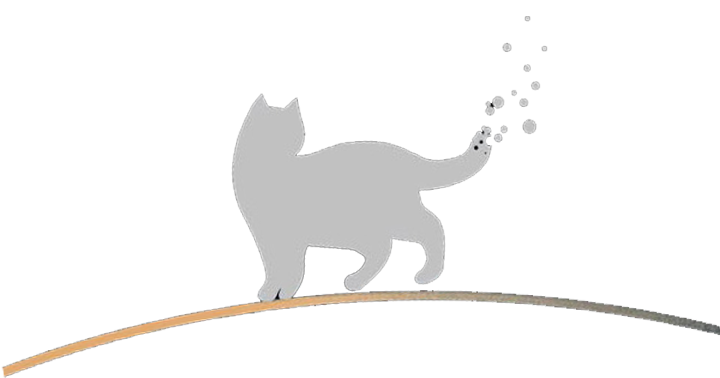
六
冬天,爷爷爱在祠堂门口享太阳,嚼舌头。老人都爱在那儿享太阳,嚼舌根,包括老保长。老保长和爷爷是一对舌头冤家,都爱嚼七舌八,却嚼不到一起,常拌嘴。老保长嚼的多是下流话,荤故事,男欢女爱,奸杀淫乱,色情淫秽。祠堂坐北朝南,堂堂正正,四通八达,五十米开外是一条沙砾铺就的国道,遇到赶集日,人来车往,尘土飞扬,热热闹闹,像一个世界在路过,勾引人看。老保长总是盯着女性看,看着嚼着,这人长,那人短,最后都嚼到床上去。他形容自己是个梦想家,在梦里和所有见过的女人都上过床。他形容最喜欢的女人叫“红烧油肉”,只要吃得到,愿意死。
红烧油肉,暗红色,油汪汪,香喷喷,绵密的香气仿佛有魔力,村里没有一个人不为它着魔。人是铁,饭是钢,肉是梦,红烧油肉是我能做的最美好的梦。但我说的红烧油肉跟老保长讲的不一样,我说的是真正的肉,猪肉;他讲的是比喻,专指那种又白又胖的女人,白得洁嫩,像剥了壳的茭白,胖得饱满,像熟透的水蜜桃。有一次,他看见这样一个女人从公路上走过,嘴巴流出口水,眼睛睁得比嘴巴大。
爷爷捉弄他,张开手掌,挡住他眼,嘲笑他:“看什么看,撑死眼睛饿死屌,有什么好看的,看了也是白看。”
老保长打掉爷爷的手,继续看,一边奚落爷爷:“饿死的是你的屌,我的屌经常吃红烧油肉,你的屌连骨头都吃不到。啊,多好的一块红烧油肉啊,跟她睡觉一定像睡在乌篷船上一样舒坦。”
爷爷骂他:“你个老流氓,下辈子一定做乌龟。”
老保长笑,“你个老巫头,下辈子保准做乌鸦。”
巫头和巫婆是一个意思,男的叫巫头,女的叫巫婆,专指那些爱用过去讲将来的人,用道理讲事情的人。爷爷就是这样的人,爱搬弄大道古理,爱引经据典,爱借古喻今,爱警世预言,爱见风识雨。享着太阳,看着人来人往,听着是是非非,爷爷经常像老保长讲下流话一样,讲一些高深莫测的大道理。
有一次,我看到爷爷像发神经,在对一只狸花猫讲:“人世间就这样,池塘大了,水就深了,水深了,鱼就多了,大鱼小鱼,泥鳅黄鳝,乌龟王八,螃蟹龙虾,鲜的腥的,臊的臭的,什么货色都有。”
我像一只狗,赶开猫,冲到爷爷面前问:“爷爷,你在讲什么?”
爷爷捋着胡子讲:“我在讲啊,一个村子就像一个池塘,池塘大了,什么鱼都有,村子大了,什么人都有,配齐的。”
我问他:“上校算什么人?”
爷爷讲:“什么上校,太监。”
我应着:“那太监是什么人?”
爷爷讲:“他是个怪胎,像前山,深山老林,什么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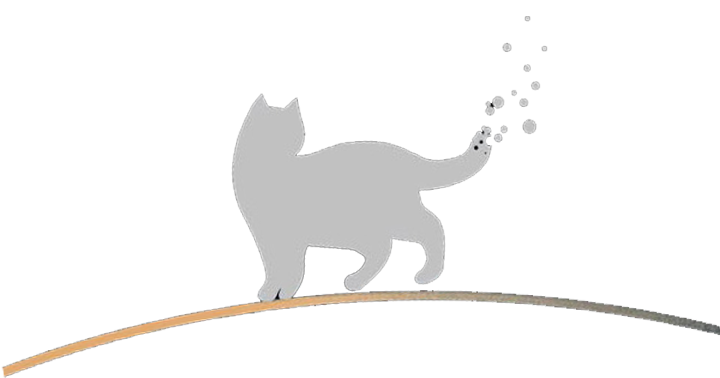
七
我们村叫双家村,大家姓蒋,小家姓陆,大大小小五千多人,是全县排头尖的大村。因着人多,怪胎也少不了,老保长是一个,门耶稣是又一个,凤凰杨花是再一个。老保长怪的是,他有一双识别婊子的火眼金睛,什么女人守不住身子,他一看一个准,所以七十多岁,而且穷得叮当响,照样有人跟他轧姘头,因为他看准对方是个婊子,要淫荡。门耶稣怪的是,他把一个光着身子的西洋人当菩萨,供在家里,日日夜里对他跪拜,跟他诉苦,有时还对他哭,眼泪一把把流。凤凰杨花怪的是,她跟一百个男人睡觉也下不了一个蛋,因为她是只石鸡,比木鸡还要木。
当然最怪的人是太监,这不用讲,大家公认,看得见,摸得着。我觉得村里所有人的怪古加起来也顶不上太监一个人,他绝对是全村最出奇古怪的人,怪古的名目要扳着指头一个一个数——
第一个,他当过国民党,理所当然是反革命分子,是政府要打倒的人,革命群众要斗争的对象。但群众一边斗争他,一边又巴结讨好他,谁家生什么事,村里出什么乱子,都会去找他商量。即使我爷爷,平时很讨厌他跟我父亲搅在一起,但只要家里遇到什么要紧事,照样要去请他拿主意,好像他才是真正的巫头,天下事都知晓。
第二个,他从前睡过老保长女人,照理是死对头,可老保长反而对他好得不得了。爷爷讲,太监最后是被解放军镇压回来的,刚回村里时各种风言风语的罪名把他涂成一个狰狞的恶鬼,跟染上麻风病似的,大家都怕他,躲他,即使父亲也一时不敢去贴他,只有老保长一人张口“侄郎”闭口“侄子”地叫他,帮衬他,宣扬他,慢慢替他立起后来的威信。最该恨他的人却对他最好,这就是古怪。
第三个,他是太监,不管是怎么落成太监的,反正是太监,那地方少了那东西。但每到夏天,大家都穿短脚裤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经常偷看他那个地方,好像还是满当当的,有模有样的。而且,好几次我看他在外面撒尿,照样像其他男人一样,脚站着,手把着,一点儿不像太监。据说,古代太监撒尿跟女人一样,是蹲着的。
第四个,他向来不出工,不干农活,不做手工(包括他的老本行木工),不开店,不杀猪,总之什么生活都不做,可日子过得比谁都舒坦,天天空在家里看报纸,嗑瓜子,抽大前门香烟,穿三接头皮鞋和华达呢中山装。更气人的是,他家灶屋好像公社食堂,经常飘出撩人的鱼香肉味。
第五个,他养猫的样子,比任何人家养孩子都还要操心,下功夫,花钞票,肉疼、宝贝得不得了,简直神经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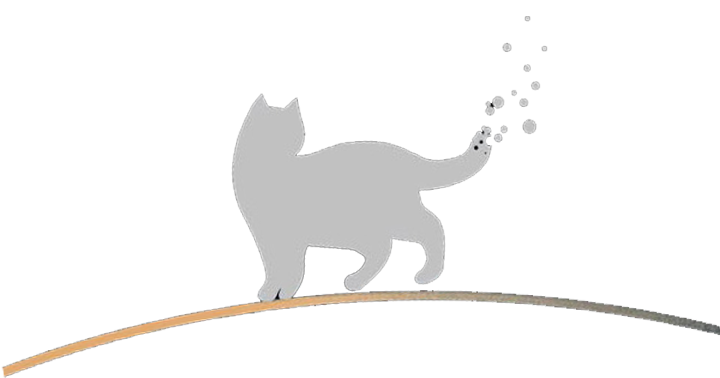
八
村里无人不知晓,太监家有两只猫,一只全黑,一只全白,都跟小豹子一样,腰身长长的,头圆圆的,走路一脚是一脚,慢腾腾的,雅致得很。我经常看见他用香皂给猫洗澡,用长柄木梳给它们梳毛,从头梳到脚,用金子小剪刀给它们剪趾甲,剪完又用砂纸磨。最气人的是,还专门给它们买上好的鲞吃!我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好过,我吃过的鲞还没有他家猫多。
我宁愿做他家的猫。我敢说,这也是我身边所有小孩子的想法。
表哥说,他还跟猫一起睡觉。但表哥也承认,只是听人说,没有亲眼见过。我倒是亲眼见过他跟猫讲话,而且猫好像也听得懂他讲的话。那年我才五岁,父亲给我三分钱,叫我去跷脚阿太开的小店买香烟。父亲告知我,三分钱可以买八支半前进牌香烟,如果他给我九支,我要对他鞠一个躬,叫一声“七阿太”;如果只给八支就不理他,甚至可以骂他跷脚佬,反正他是跷脚,追不上我。
跷脚阿太的小店开在祠堂门前,太监家在祠堂背后,我去小店必须经过他家门口。跟大多数人家不一样,他家有围墙,围着一个小院子——爷爷讲是以前的猪圈改造的,猪圈里放过毒炮弹壳。院门平时间不开,因为怕狗欺负他家的猫,那天却开着,我看见院子里有一畦菜地,种着香葱和芹菜,他满头白发的老母亲拎着一只洋铁桶在给菜地浇水,自己则像个老爷一样,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享着太阳,抽着香烟,看着报纸,脚跟边躺着一白一黑两只猫。
白猫最先发现我,对我昂头咪地叫一声,好像在通知主人,有人在门口。太监听了,放下报纸,抬起头,看见我。看了两眼,笑了,问我是不是老巫头的孙子。我摇头——那时我还不知道爷爷的绰号呢。
他母亲笑道:“怎么可能不是,简直跟他爹生一个模样。”
他哈哈大笑,扮着我爷爷的样子和口气招呼我:“哎,我的乖乖,进来吧。”
我看着两只虎视眈眈的猫,不敢进门。
他对它们一挥手,发命令:“你们进去。”
两只猫完全是听懂的样子,甩甩尾巴,立起身,对我龇一下牙,掉转身,一前一后,往黑暗的屋子里去。我不知道为什么阳光那么白亮,台地上明晃晃的,连太监手上的烟在冒气我都看得清明,可几步之后的屋子里,却是那么一团黑,一片黑,像被阳光抹黑似的。五岁的我不知道这是自然现象,以为这是鬼屋的现象,又想到刚才猫对我龇牙,好像要吃我,吓得我拔腿就跑。
事后我跟爷爷讲起这事,爷爷一把搂住我,兴高采烈又满怀感激地对我讲:“啊哟,我的乖乖,你不进去是对的,以后也不要去,那就是个鬼屋,那家伙就是个鬼。”
我嚷嚷:“他跟猫说话,还跟猫睡觉。”
爷爷讲:“所以他不是人,是鬼,鬼投胎的。”
以后好几年,我去小店买东西或去祠堂玩,都不从他家门口走。我宁愿绕一个大圈也不走他家门口,因为我怕遇到鬼。表哥说他家的两只猫是鬼变的,我说他满头白发的老母亲也是鬼变的;表哥说鬼已经把他爹吃掉了,我说可能就是那死老太婆吃的。我们经常这样数落太监和他老母亲,我和表哥的友谊也因此变得更加深厚牢固,好像我们有一个共同敌人,我们必须团结一起,不弃不离。
有一天,我和表哥正在这么乱讲太监时,被正在茅坑里解溲的父亲听到。父亲从茅坑里出来,一边系着裤腰带一边追着我们骂,恼羞成怒的样子,好像太监是他亲爹,我们是茅坑里的臭石头。
表哥问我:“舅舅为什么对太监那么好?”
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因为他鬼附身了。”好似我早备好答案,其实是爷爷的话。
确实,爷爷经常骂父亲被鬼魔附身,给死人摸过额头。爷爷讲,运气是阳气,鬼魔是阴气,阴阳是相克的,甘苦是作对的,人一旦阴盛阳衰,苦头当道,就要倒霉头,背祸水,吃水也要呛死。据说以前父亲蛮听从爷爷的,父子俩像兄弟一样亲,我们家像谷仓一样让人羡慕,老小和睦,儿女顺当,人畜兴旺。但自从太监回到村里后,父亲老是淘爷爷的气,家里老是吵吵闹闹,搞得爷爷老是担惊受怕,怕霉运随时落到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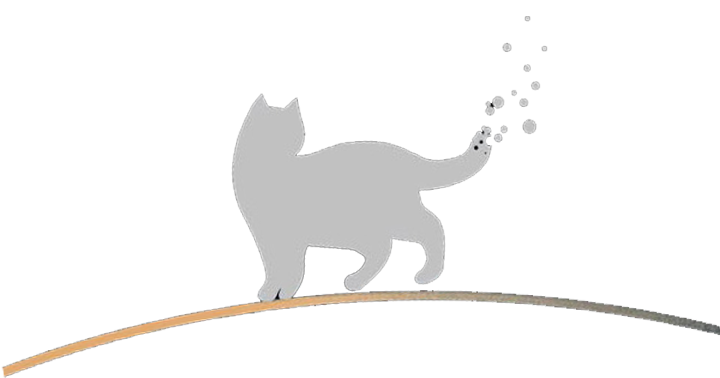
九
吃水会不会呛死人我不知道,但吃农药笃定要死人。记得,五岁那年我就见过一个吃农药死的人,七岁时也见过一个:都是女人家,一个老太婆,一个大姑娘。村里几乎年年有人寻死,上吊,投井,跳水库,吞剪刀,割手腕子、颈脖子,什么手法都会冒出来。但最常见的是吃农药,因为便当,拧开瓶盖,眼睛一闭,倒进喉咙完事,门都不用出,也不要做任何准备。这不,一个皓月当空的晴夜,爷爷和我睡得死死的,突然被人活活叫醒,因为门耶稣吃农药寻死了——这也算得上是我家倒霉头吧。门耶稣是爷爷堂兄弟,虽不是一家人,总归是自家人,我要叫小爷爷的。
小爷爷年轻时在上海拉过三年黄包车,经常有个西洋人坐他车子,每次付账都不要找零头。小爷爷觉得他比菩萨道士都好,对他百依百顺,最后顺了他心,信了耶稣,张口闭口“阿门”“阿门”的,铁铁地落一个门耶稣的绰号。耶稣是要行善的,这日下午他照耶稣的托付去镇上做善事,花掉两块钱,把他儿媳妇气得要死。媳妇是江北人,绰号红辣椒,撒起泼来水牛野鬼都怕,敢当众撕开胸脯赖你耍流氓。她当然不会气死自己,只会气死别人,她把小爷爷天天阿门的耶稣像从墙上一把扯下来,扔进灶膛烧成灰。这是小爷爷的命根子,根子烧灰了他去哪儿活?只有去死。
农药在小爷爷肚皮里像灶火一样熊熊燃烧,要不是太监——不,必须尊称上校——及时赶来,一定会把他烧死。我亲眼看见,上校是怎么把小爷爷肚皮里的熊熊大火浇灭的,他先是往小爷爷嘴巴里塞进一块肥皂,灌他吞下去;然后扒掉他裤子,把他头朝地吊起来;然后又用打农药的喷壶往小爷爷屁洞里注水。农药壶有一个喷头,通过控制压力杆,可以把农药喷上树,射得比屋檐高。上校把喷头塞进小爷爷屁洞里,按住,一边拉压力杆,把满满一壶水都压进他屁洞里。这一定是痛的,小爷爷啊呀啊呀叫,叫着叫着,水从嘴巴哗哗吐出来。这水比屙出来的屎还要臭,熏得上校睁不开眼。
上校睁开眼,对小爷爷儿子讲:“你爹死不了啦,给我去烧面吧。”这是老规矩,上校救活谁,谁家要烧碗肉丝面给他吃。有这样的老规矩,指明他不是第一次这样救人,只是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年我十一岁,已经跑得比爷爷快,所以爷爷派我去叫上校,要不我也看不到。
没等上校吃完面,小爷爷已经能开口讲话,讲的话却难听,不感谢,反而骂,无情无义的。“你作孽啊!”他骂上校,一边呜呜地哭,“我要死你干吗救我,我该死不死比死还要罪过啊。”
上校讲:“是耶稣派我来救你的,你被我救活就是不该死。”
小爷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耶稣像烧了,我没脸皮活了。”
上校讲:“烧了可以再买,买得到的。”
笑话,小爷爷就是被两块钱作死的,哪有钱去买新耶稣?这总得要更多钱吧。上校得知情况后,当场从身上摸出十块钱,递给小爷爷,像递着一支香烟,轻巧又客气地发话:
“喏,给你,不就是几块钱的事嘛,值得用性命去抵。世上命最值钱,我被人骂成太监都照样活着,你死什么死,轮不上。”
小爷爷做梦似的,看着钞票,不敢拿,也好像是拿不动,因为手抖得厉害。上校豪爽地把它塞入小爷爷哆嗦的手心里,安慰他:“没事,拿着吧,只是别同我妈讲,她迷信观音菩萨,跟你的耶稣是犯冲的。她要得知我出钱给你买耶稣像,搞不好也要气死。”说完哈哈大笑,笑声腾腾地扬上天。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看到上校的眼睛,果然是明明亮亮的,比洁白的月光还要亮,一点不像个祟的鬼,像个英雄,堂亮得很。这是我重要的一个经历,我开始对上校生出好感,他救了小爷爷的命,也救了自己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像被他吸着似的,跟着他出门,目送他远去,皎洁的月光披在他身上,照得他隐隐生辉。他走路的样子横竖不像太监,倒真是有些大军官的威风头,大踏步,高抬手,腰笔直,脚生风,一步是一步,昂首挺胸,雄赳赳,气昂昂,怎么看也不像裤裆里缺了东西。我想,他本事这么大,可以把死人救活,即便裤裆里真缺了东西,也一定可以补得上。我猜他一定是把那东西补上了,所以看上去还是“满当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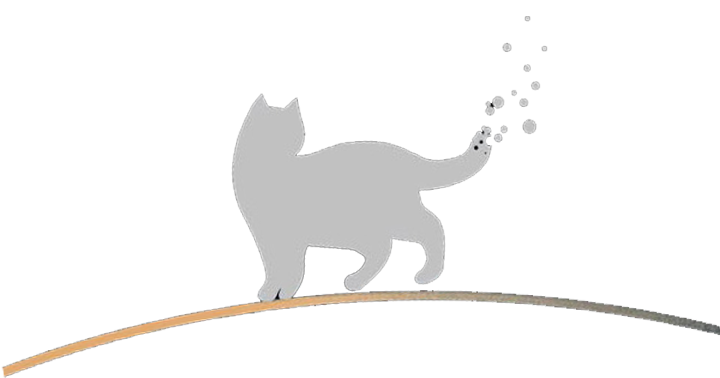
十
从此,我对上校的看法和态度发生大变样,以前爷爷总罩着我,我是爷爷的奴才,爷爷怎么看上校我都认下,像狗吃肉,吃得干净,骨头都嚼碎,咽下。结果,上校在我心目中的样子总体是脏的、坏的、怪的、鬼祟的。我怕他,躲他,讲他坏话,瞧不起他,唯一保下来一点好奇心,想了解他,因为怪嘛。他像一座尘封久远、织出多个鬼故事的老房子,你怕它又忍不住想进去看。以前爷爷讲不许看,我就不看,百依百顺,一副奴才相。现在我不要再做爷爷的奴才,因为我觉得他“不像鬼,像个英雄”。
秋天到了,柿子树叶开始变色,发黄,发褐,脱落,原来青绿扁圆的柿子也开始变色变样,变得发黄,泛红,赤红,红得火辣辣的,变得圆滚滚的,像一盏盏小红灯笼。灯笼密密匝匝的,挂满枝枝丫丫、节头梢头,远看整棵树像着火似的。这时,收获开始了,树上摘柿子、板栗、猕猴桃、酸勾子,地里刨红薯、洋芋、花生,水下挖藕、摸蚌。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不仅因为有收获,也因为风和日丽,天高气爽,可以出门远行。
小爷爷大致就在这时节收到了有人从杭州捎来的耶稣像,簇新,油亮,且比原先的大一号。当天夜里,小爷爷焦急又骄傲地在老地方挂好神像,在蒲团上足足坐到天亮,呜呜咽咽一个通宵,有点弥补配齐的意思。第二天上午,稍歇的小爷爷起床后直奔我家,向爷爷来报喜,一坐几个钟头,唠唠叨叨,只讲一个人的好话,就是上校。
爷爷听着,忍着,终于忍不住,顶他嘴:“你真好笑,讲他那么多好话,好像他比耶稣还要好一样的。”
小爷爷耐心劝爷爷,小小声声讲:“好就是好,耶稣看在眼里的。你以后要改变对他的看法,别老埋汰他,这对你自己也不好。”
爷爷嘿嘿笑,是轻慢的讥笑,“你帮我问问耶稣,会怎么个不好?是要我死还是生不如死?”
小爷爷低头讲:“别把死挂在嘴上,我是死过的人,那罪不是人受的。”抬头看看天上又讲:“人在做天在看,耶稣在天上看着,你老这么埋汰一个好人要遭报应的。”
“别拿你的耶稣吓唬我。”爷爷对他翻白眼,那死相同吃过农药一样难看,“你以为我是白乌珠(瞎眼),瞎(吓)大的。”爷爷傲慢得像一只好斗的公鸡,抻长脖颈,瞪圆黑乌珠,把话甩得冒火星子,“我吃的饭比你早,识的字比你多,轮不到你来教训。”根本不把小爷爷的警告放在眼里。
爷爷像一棵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老榕树,上遮天下盖地,里三层外三层,天打雷劈都不怕,怎么会怕小爷爷莫须有的风雪预报?总之,爷爷活成一个老埠头,你要改变他是很难的,不像我。我像三月里的桃树,一夜之间变成一幅画、一本诗,花枝招展,灿烂得连自己都认不得。这决定我要反对爷爷,在这场争论中站到小爷爷一边。
我拉着爷爷手说:“爷爷你不对,上校是个好人,你要改变对他的看法。”
爷爷推开我,站起身,作模作样地放一个响屁,笑道:“变个屁。”
这蛮有意思的,听上去是死活不变的意思,看上去又是乐意变的——因为在笑嘛。到底有没有变?以我观察,有不变的内容,如爷爷仍旧不许上校来我家;但也有变的地方,比如偶尔他有事来找父亲,爷爷不会像从前一样打鸡骂狗,衅事生非,只会闷声走掉,眼不见为净。这就是变,是让一步的意思。叫我万千想不到的是,爷爷最后居然会让出这一步:许我跟父亲去上校家揩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