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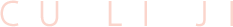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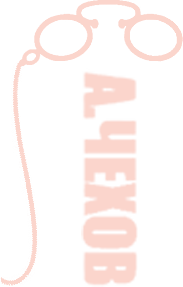
法院侦讯官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矮小、异常消瘦的庄稼汉,穿一件花粗布衬衫和一条打过补丁的裤子。他那生满毫毛和布满麻点的脸,以及藏在突出的浓眉底下、不容易让人看见的眼睛,都露出阴沉的严峻神情。他脑袋上的头发无异于一顶皮帽子,很久没有梳过,纠结蓬乱,弄得他像一个蜘蛛,越发显得阴沉了。他光着脚。
“丹尼斯·格里戈里耶夫!”侦讯官开口说,“你走过来一点,回答我的问题。本月七日,铁路看守人伊万·谢苗诺夫·阿金佛夫早晨沿线巡查,在一百四十一俄里处,碰见你在拧掉一个用来联结铁轨和枕木的螺丝帽。喏,这就是那个螺丝帽!……他把你连同螺丝帽一起扣住。事情是这样的吗?”
“啥?”
“这件事是像阿金佛夫所说的那样吗?”
“当然,就是那样。”
“好。那你为什么拧掉螺丝帽?”
“啥?”
“你不要啥啊啥的,你要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拧掉螺丝帽?”
“要是没有用处,俺才不会去拧它呢。”丹尼斯声音沙哑地说,斜起眼睛看着天花板。
“那么你要这个螺丝帽做什么用?”
“螺丝帽?俺们拿它做坠子……”
“这个俺们是谁?”
“俺们,老百姓呗……就是克里莫沃村的庄稼汉。”
“听着,老乡,你不要对我装傻,要说正经的。这儿用不着撒谎,说什么坠子不坠子的!”
“我一辈子也没撒过谎,现在撒啥谎……”丹尼斯嘟哝说,眨巴着眼睛,“再说,老爷,能不用坠子吗?要是你把鱼饵或者蚯蚓安在钓钩上,难道不加个坠子,钓钩就能沉到水底?还说俺撒谎呢……”丹尼斯冷笑道,“鱼饵这种东西,要是漂在水面上,还顶个啥用?鲈鱼啦,梭鱼啦,江鳕啦,素来在水底上钩。要是鱼饵漂在水面上,也许只有鲶鱼来吃,不过那样的事也不常有……俺们的河里就没有鲶鱼……那种鱼喜欢大河。”
“你跟我讲鲶鱼干什么?”
“啥?咦,您自己在问嘛!俺们那儿,连地主老爷也这么钓鱼。就连顶不济的孩子,没有坠子也不去钓鱼。当然,也有那种不明事理的人,嗯,他们没有坠子也要去钓鱼。傻瓜办事就说不上什么章法了……”
“这么说来,你拧下螺丝帽就是为了要拿它做坠子?”
“不为这个还为啥?又不是拿来当羊拐子
 玩!”
玩!”
“可是要做坠子,你尽可以用铅块、子弹壳……钉子什么的……”
“铅块在大路上可找不着,那得花钱去买。讲到钉子,那东西不中用。再也找不着比螺丝帽更好的东西了……它又重,又有个窟窿眼。”
“他老是装傻!好像他昨天刚生下地或者从天上掉下来似的。难道你就不明白,蠢材,这样拧掉会惹出什么乱子来吗?要不是看守人看到,火车就可能出轨,很多人就会丧命!你会害死很多人!”
“天主保佑别出这种事才好,老爷!为啥害死人呢?难道俺们不信教,或者是坏人?谢天谢地,好老爷,俺们活了一辈子,慢说是害死人,就连那样的想法也没有过……求圣母拯救和宽恕吧……您这是说的啥呀!”
“那么依你看来,火车是怎么翻的?你拧掉两三个螺丝帽,火车就翻了!”
丹尼斯冷冷地一笑,怀疑地眯细眼睛瞧着侦讯官。
“得了吧!俺们全村的人拧螺丝帽已经有年月了,天主一直保佑我们,现在却说火车出事……害死人了……要是俺把铁轨搬走,或者,比方说,把一根大木头横放在铁轨上,嗯,那就说不定火车会翻掉,可是现在……呸!一个螺丝帽罢了!”
“可是你要明白:螺丝帽是用来把铁轨钉紧在枕木上的!”
“这个俺们明白……俺们又不是把所有的螺丝帽都拧掉……还留着不少呢……俺们办事可不是不动脑筋的……俺们明白……”
丹尼斯打了个呵欠,在嘴上画一个十字
 。
。
“去年此地就有一列火车出了轨,”侦讯官说,“现在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
“您说啥?”
“我说,去年有一列火车出了轨,现在才明白那是什么缘故……我懂了!”
“您受教育就为的是懂事,俺们的恩人……主才知道该叫谁懂得事理……喏,您评断事情,就说得出道理来,可是那个看守人也是个庄稼汉,啥也不懂,揪住俺的脖领,拉着就走……你先得讲理,然后才能拉人嘛!俗语说得好,庄稼汉长着庄稼汉的脑筋……还有一件事您也要记下来,老爷:他动手两次,打俺一个嘴巴,当胸又给了俺一拳。”
“先前搜查你家的时候,又找着一个螺丝帽……你是在什么地方把它拧下来的,在什么时候?”
“您说的是放在小红箱子底下的那个螺丝帽吗?”
“我不知道放在你家里什么地方,反正是搜到了。你是在什么时候把它拧下来的?”
“那不是俺拧下来的,那是伊格纳希卡送给俺的,他就是独眼谢苗的儿子。俺说的是小箱子底下那一个。院子里雪橇上的那一个,是俺跟米特罗凡一块儿拧下来的。”
“哪一个米特罗凡?”
“就是米特罗凡·彼得罗夫呗……难道您没听说过?他在俺们村子里编渔网,卖给地主老爷们。那种螺丝帽,他可要的多。编一个渔网,估摸着,总要用十来个……”
“你听着……刑法第一千零八十一条说:凡蓄意损坏铁道,致使铁路运输发生危险,而肇事者明知此种行为将造成不幸后果……听明白了吗?明知!你不可能不知道拧掉螺丝帽会造成什么后果……当判处流放及苦役刑。”
“当然,您知道得多……俺们都是些无知无识的人……难道俺们能懂吗?”
“你全懂!你这是撒谎,装佯!”
“撒谎干啥?要是您不信,您就到村子里去打听好了……不用坠子只能钓着似鲌鱼。鲌鱼最差不过了,可是就连它,缺了坠子也还是钓不着。”
“你再讲一讲鲶鱼吧!”侦讯官微笑着说道。
“鲶鱼俺们那儿没有……俺们把没有坠子的钓丝漂在水面上,安上蝴蝶做饵,倒有大头鱥来上钩,不过就连那样的事也少有。”
“好,你别说了……”
随后是沉默。丹尼斯站在那儿,不时换一只脚立定。他瞧着铺有绿呢面的桌子,使劲眨巴眼睛,好像他眼前看见的不是呢子,而是太阳。侦讯官很快地写着。
“俺该走了吧?”丹尼斯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不。我得把你看押起来,再送到监狱里去。”
丹尼斯不再眨巴眼睛,拧起浓眉,探问地瞧着那个文官。
“怎么会要俺去坐监狱?老爷!我可没有那个闲工夫,我得去赶集。叶戈尔欠着我三个卢布的腌猪油钱,我得跟他要……”
“别说了,不要碍我的事。”
“要俺坐监狱……要真是做了坏事,那就去吧,可是现在……啥缘故也没有……俺犯了啥王法?俺觉得,俺没偷过东西,也没打过人……要是您,老爷,疑心俺欠缴了税款,那您可别听信村长的话……您去问常任委员先生好了……他,那个村长,是个没有良心的人……”
“别说了!”
“俺本来就没说啥……”丹尼斯嘟哝说,“村长造了假账,这俺敢起誓……俺们是弟兄三个,那就是库兹马·格里戈里耶夫,叶戈尔·格里戈里耶夫,和俺丹尼斯·格里戈里耶夫……”
“你碍我的事……喂,谢苗!”侦讯官叫道,“把他押下去!”
“俺们是弟兄三个,”丹尼斯一面由两个强壮的兵押着,走出审讯室,一面嘟哝说,“弟兄不一定要替弟兄还钱……库兹马没给钱,那么你,丹尼斯就得承担……这也叫法官!俺们的东家是个将军,已经死了,祝他升天堂吧,要不然他就会给你们这些法官一点厉害看看……审案子要知道怎么个审法,不能胡来……哪怕用鞭子抽一顿也可以,只要有凭有据,打得不屈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