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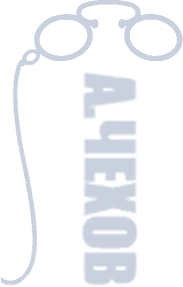
我的朋友的故事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西林大学毕业以后,在彼得堡政府机关里工作,可是到三十岁那年,他辞掉工作,去经营农业了。他经营得不坏,然而我仍旧觉得,他干这种工作不合适,还是回彼得堡的好。每逢他给太阳晒黑,周身扑满灰白的尘土,劳累得筋疲力尽,在大门外或者门道里迎接我,后来在晚饭桌上睡意蒙眬,他妻子把他当作小孩那样领去睡觉的时候,或者每逢他压下睡意,用他那柔和、热诚而且似乎在恳求什么的声调说出他那些优美的思想的时候,我总认为他不能算是个经营农业的人,也不能算是个农学家,只不过是个劳乏的人罢了。我清楚地看出,他并不需要经营什么农业,他所需要的是把日子打发过去,就此而已。
我喜欢到他家里去,有时候在他的庄园上盘桓两三天。我喜欢他的房子、花园、大果园、小河,以及他那种有点沉闷,有点浮夸,然而条理清楚的哲学议论。大概我也喜欢他本人,不过在这方面我说不准,因为我至今还不能理清我当时的感情。他是一个头脑聪明、心地善良、不讨人厌,而且态度诚恳的人,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每逢他把藏在心里的秘密告诉我,把我们的关系说成是友谊,那总会惹得我不痛快,使我觉得别扭。他对我的友情有点叫人不舒服,不好受,我倒情愿只跟他维持普通朋友的关系。
问题在于我非常喜欢他的妻子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我并没爱上她,不过我喜欢她的脸、眼睛、声调、步态,如果很久没有跟她见面,就会惦记她,在那种时候我的想象力最乐于描绘的,就莫过于这个年轻美丽而又优雅的女人了。我对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企图,也没想望什么,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次临到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我想起她的丈夫把我看作朋友,我就觉得不自在了。遇到她在钢琴上弹我喜爱的曲子,或者对我讲起一件什么有趣的事,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过同时,不知什么缘故,就会有一种想法溜进我的脑子,我想到她爱她的丈夫,他是我的朋友,连她自己也认为我是他的朋友,于是我就败了兴,变得无精打采,不自在,心里烦闷了。她看出这种变化,照例说:
“您的朋友不在,您闷得慌了。我得派人到田里去找他回来。”
等到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回来,她就说:
“喏,现在您的朋友来了。您就高兴起来吧。”
照这样过了一年半光景。
有一回,那是七月里一个星期日,我和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闲得没有事做,就坐着马车到一个大村子克路希诺去买吃晚饭用的凉菜。我们只顾在那些小铺里穿来穿去,太阳却已经下山,黄昏来了,而这个黄昏我大概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买了一些像肥皂的干酪和气味像煤焦油而硬得像石头的腊肠以后,就到小饭铺里去问一下有没有啤酒。我们的马车夫到铁匠铺去给马钉马掌,我们就对他说,我们在教堂附近等他。我们一面走路一面谈话,笑我们买下的吃食,这时候却有一个人跟在我们后面,一句话也不说,神情鬼鬼祟祟,就像暗探似的。此人在我们县里有个相当古怪的绰号:四十个殉教徒。这个四十个殉教徒就是加甫利拉·谢威罗夫,或者简单地叫作加甫留希卡,他曾在我家里做过听差,不久就因为酗酒而被我辞掉了。他在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家里也做过事,后来也因为同样的过错给辞掉了。他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而且总的说来,他的整个命运就是醉醺醺的,像他本人一样昏天黑地。他父亲是个神甫,他母亲是个贵族,按出身他属于特权阶层,可是不管我怎样细看他那张憔悴的、恭顺的、永远冒汗的脸,他那把已经变白的红胡子,他那件可怜样的破上衣和底襟不塞进裤腰里的红衬衫,我却怎么也找不出一丁点儿在我们社会生活里可以称之为特权阶层的痕迹。他自称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在神学校里读过书,可是没有毕业,因为吸烟而被开除了;后来在主教的唱诗班里唱歌,在一个修道院里待过两年左右,又被开除了,然而这回不是由于吸烟,而是由于“嗜好”了。他徒步走遍两个省,不知什么缘故向宗教法庭和各衙门递过状子,受过四次审判。最后他流落到我们县里来,做听差,做守林人,做照料猎犬的人,做教堂的看守人,跟一个寡妇——一个放荡的厨娘结了婚,从此陷入奴仆的生活,习惯于肮脏和下流,结果连他自己讲到自己的特权阶层出身,都不免带点迟疑的口气,仿佛在讲一个什么神话似的。在目前这个时期,他没有工作而在逛荡,自称是个马医和猎人。他的妻子走掉了,下落不明。
我们从小饭铺里出来往教堂走去,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坐下来,等马车夫。四十个殉教徒站得稍稍远一点,把一只手放到嘴边,为的是到必要的时候可以恭恭敬敬地对着手心咳嗽。天色已经黑下来,空中弥漫着傍晚强烈的潮气,月亮快升上来了。天空明净,布满繁星,只有两朵浮云,正巧悬在我们头顶上方,一朵大一点,一朵小一点,这两朵浮云孤孤单单,好比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在互相追逐,往晚霞正在黯淡的那边奔去。
“今天天气好得很。”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说。
“好到了极点……”四十个殉教徒同意说,恭恭敬敬地对着手心咳嗽一声,“您,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怎么会想起到这个地方来走一趟?”他用巴结的口气问,显然想搭讪。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什么话也没回答。四十个殉教徒深深叹一口气,眼睛没看着我们,小声说:
“我受苦纯粹是由于一个原因,我得为这对万能的上帝负责。嗯,当然,我是个堕落的、没出息的人,不过请您相信我的良心话,我目前连一小块面包也没有,比狗都不如。……请您原谅我这么说,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
西林没有听他讲话,用拳头支着自己的脑袋,想什么心事。教堂坐落在村街的尽头,高高的河岸上。我们隔着篱笆墙望去,可以看见那条河,看见对岸一片水淹的草地,看见一堆篝火冒出紫红色火光,有些黑色的人和马在篝火旁边活动。在篝火后面,再远一点,还有些灯火,那是个小村子。……那儿有人在唱歌。
河面上升起雾,草地上有些地方也有雾。一缕缕雾又高又细,像牛奶那么浓和白,在河面上徘徊,遮住星光,挂在柳树梢上。这一缕缕雾每分钟都变换花样,看上去好像有的互相拥抱,有的鞠躬,还有的举起胳膊来直对天空,就像教士穿着袖口肥大的法衣在祷告。……这一缕缕雾大概引得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想起鬼魂和已经死亡的人,因为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带着忧郁的笑容问道:
“告诉我,我亲爱的,为什么每逢我们想讲什么可怕的、神秘的、离奇的事,我们不从生活里找素材,却一定要到幽灵和鬼影的世界里去找呢?”
“可怕的东西就是不能理解的东西。”
“那么难道您理解生活?您说说看,莫非您对生活比对坟墓中的世界理解得清楚些?”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坐得离我十分近,我的脸颊都能感到他在呼吸。在苍茫的暮色中,他那张又白又瘦的脸显得越发苍白,那把黑胡子显得比煤烟还黑。他的眼睛忧郁而坦诚,带点惊恐的神情,仿佛他要跟我讲一件什么可怕的事似的。他瞧着我的眼睛,用他那种照例带着恳求的声调接着说:
“我们的生活和坟墓里的世界同样没法理解,同样可怕。凡是怕鬼魂的人,就一定也怕我,怕那些灯火,怕天空,因为这一切,如果仔细想一下,就都不可理解,离奇,不下于从那个世界里来的阴魂。哈姆雷特王子没有自杀是因为他怕那些在他长眠时可能显现的幽灵。我喜欢他那段著名的独白,不过老实说,它从没触动过我的灵魂。我把您看作朋友,那就要对您老实承认:有的时候,我心里愁闷,幻想我死后的情景,我的幻想描绘过成千种极其阴暗的景象,把我自己弄得又痛苦又兴奋,像是梦魇,不过请您相信,在我看来,就连那情景,也并不比现实可怕。不消说,那些幻象是可怕的,可是生活也可怕。我呢,好朋友,不了解生活,怕生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我是个病态的、发了疯的人吧。在正常而健康的人看来,凡是他耳闻目睹的事情似乎他都了解,我呢,正好失去了这个‘似乎’,天天让恐惧毒害我自己。世界上有一种害怕旷野的病,我得的是一种害怕生活的病。每逢我躺在草地上,久久地看着一只昨天才出生、对什么都不了解的小甲虫,我就觉得它的生活充满恐惧,而且在它身上我看见了自己。”
“不过您觉得可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我问。
“我觉得什么都可怕。我天生是个思想不深刻的人,不大关心死后的世界和人类命运之类的问题,向来很少想到那些深奥的事。我觉得可怕的,主要是我们谁也躲不开的日常琐事。我没法分清我的行动当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作假,这总使得我心慌。我体会到生活条件和教育把我限制在狭小、虚伪的圈子里,我的全部生活无非是天天费尽心机欺骗自己和别人,而且自己并不觉得。我想到我一直到死都摆脱不了这种虚伪,就心里害怕。今天我做一件什么事,可是到明天,我就会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原在彼得堡担任公职,后来害怕了。我到这儿来,为的是经营农业,可又害怕了。……我看出我们了解的事情很少,因此天天犯错误。我们往往不公道,对人造谣中伤,破坏彼此的生活,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浪费在我们不需要的而且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聊事情上。我觉得这种现象可怕,因为我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有谁需要这样做。我,好朋友,不了解人们,怕他们。我瞧着农民就害怕,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在受苦,为了什么缘故生活下去。如果生活是快乐,那他们就是多余的和不需要的人。如果他们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就在于贫困,就在于昏天黑地和无可救药的愚昧,那我就不明白这样活受罪有谁需要,为了什么缘故需要。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我都不明白。比方说,您就费神了解一下这个人吧!”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指着四十个殉教徒说,“您仔细想想他吧!”
四十个殉教徒发现我们两个人都瞧着他,就恭恭敬敬地对着他的空拳头咳嗽一声,说:
“在好主人家里,我素来是忠心的仆人,而毛病全出在烧酒上。要是现在有人看得起我这个不幸的人,给我找个差事,那我就会吻神像戒酒。我说这话是算数的!”
教堂看守人走过我们旁边,大惑不解地瞧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去拉钟绳。钟响了十下,猛地打破了夜晚的沉寂,声音缓慢而悠长。
“想不到已经十点钟了!”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说,“我们也该走了。对了,我的好朋友,”他说,叹口气,“要是您知道我多么害怕我那些平淡的、日常的想法就好了,而这些想法本来似乎不应当有什么可怕的地方。我为了避免思考,就专心劳动来分我的心,干得筋疲力尽,夜里好睡得酣畅。对别人来说,儿女和妻子显得稀松平常,可是他们对我来说却是沉重的压力,好朋友!”
他用手抹一抹脸,干咳一声,笑起来。
“要是我能对您说一说我在生活里扮着一种什么样的傻瓜角色,那才有意思呢!”他说,“大家都对我说:您有可爱的妻子,有可爱的孩子,您自己也是个挺好的家长。他们都以为我十分幸福,羡慕我。既然讲到这里,那我索性私下里对您说了吧:我那幸福的家庭生活纯粹是可悲的误会,我怕它。”
他那张苍白的脸由于苦笑而变得难看了。他搂住我的腰,小声说下去:
“您是我真诚的朋友,我信任您,深深地尊敬您。天赐给我们友谊,是要我们开诚相见,让我们摆脱那些压在我们心头的秘密。请允许我利用您对我的友好感情来把事情的真相统统告诉您。我这种家庭生活依您看来十分美满,其实它却是我主要的不幸,使我恐惧的主要方面。我的婚姻是古怪而愚蠢的。应当告诉您,婚前有两年光景,我一直着魔似的爱着玛霞
 ,追求她。我向她求过五次婚,她都拒绝了,因为她对我根本就不感兴趣。到第六次,我被爱情折磨得晕头转向,就在她面前跪下,像乞讨似的向她求婚,她就同意了。……她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不爱您,可是我会对您忠实。……’我欢天喜地接受了这样的条件。那时候我懂得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我当着上帝起誓,我不懂了。‘我不爱您,可是我会对您忠实’,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团雾,一片黑。……我现在仍旧跟婚后第一天那样热烈地爱她,可是我觉得她仍旧对我冷淡,每逢我走出家门,她大概暗暗高兴。她究竟爱不爱我,我拿不准,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可是事实上,我们却住在一个房顶底下,彼此用‘你’相称,睡在一块儿,有儿有女,我们的财产归两个人共有。……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缘故要这样?您能理解吗,好朋友?残忍的考验啊!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时而恨她,时而恨自己,时而恨我们两人,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我折磨自己,弄得自己头昏脑涨,她呢,仿佛故意跟我捣乱似的,反而一天天漂亮起来,变得叫人暗暗称奇。……我觉得她的头发美极了,她那笑靥任什么女人也比不上。我爱她,可又知道这种爱是没有希望的。对一个跟你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你的爱情居然没有希望!难道这种事可以理解?不可怕?难道这不比幽灵更可怕?”
,追求她。我向她求过五次婚,她都拒绝了,因为她对我根本就不感兴趣。到第六次,我被爱情折磨得晕头转向,就在她面前跪下,像乞讨似的向她求婚,她就同意了。……她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不爱您,可是我会对您忠实。……’我欢天喜地接受了这样的条件。那时候我懂得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我当着上帝起誓,我不懂了。‘我不爱您,可是我会对您忠实’,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团雾,一片黑。……我现在仍旧跟婚后第一天那样热烈地爱她,可是我觉得她仍旧对我冷淡,每逢我走出家门,她大概暗暗高兴。她究竟爱不爱我,我拿不准,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可是事实上,我们却住在一个房顶底下,彼此用‘你’相称,睡在一块儿,有儿有女,我们的财产归两个人共有。……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缘故要这样?您能理解吗,好朋友?残忍的考验啊!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时而恨她,时而恨自己,时而恨我们两人,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我折磨自己,弄得自己头昏脑涨,她呢,仿佛故意跟我捣乱似的,反而一天天漂亮起来,变得叫人暗暗称奇。……我觉得她的头发美极了,她那笑靥任什么女人也比不上。我爱她,可又知道这种爱是没有希望的。对一个跟你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你的爱情居然没有希望!难道这种事可以理解?不可怕?难道这不比幽灵更可怕?”
按他这时候的心境,他会再讲下去,讲上很久,不过,幸好,传来马车夫的说话声。我们的马车来了。我们就坐上马车,四十个殉教徒脱掉帽子,扶着我们两人上车,从他脸上的神情看来,仿佛他早已在等个机会,好接触一下我们尊贵的身体似的。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请您允许我到您那儿去吧,”他说,歪着脑袋,使劲
 巴眼睛,“求您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吧!我快要饿死了!”
巴眼睛,“求您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吧!我快要饿死了!”
“哦,行,”西林说,“你来吧,你先干三天活再说。”
“是,老爷!”四十个殉教徒高兴地说,“我今天就去。”
这儿离家有六俄里
 远。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心满意足,因为他终于把心里的话都对朋友倾吐了。他一路上始终搂着我的腰,不再伤心,也不再害怕,快活地对我说,如果他的家里平安无事,他就打算回彼得堡,在那儿研究学问。他说,那种把许多有才具的年轻人赶下乡去的潮流是一种可悲的潮流。在俄国,黑麦和小麦有很多,然而文化水平高的人却十分缺乏。应当让有才具的、健康的青年致力于科学、艺术、政治,不这样做而去干别的,那是不合算的。他愉快地大发议论,随后表示惋惜说,明天一清早他就要跟我分手了,因为他得出外去做一笔木材生意。
远。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心满意足,因为他终于把心里的话都对朋友倾吐了。他一路上始终搂着我的腰,不再伤心,也不再害怕,快活地对我说,如果他的家里平安无事,他就打算回彼得堡,在那儿研究学问。他说,那种把许多有才具的年轻人赶下乡去的潮流是一种可悲的潮流。在俄国,黑麦和小麦有很多,然而文化水平高的人却十分缺乏。应当让有才具的、健康的青年致力于科学、艺术、政治,不这样做而去干别的,那是不合算的。他愉快地大发议论,随后表示惋惜说,明天一清早他就要跟我分手了,因为他得出外去做一笔木材生意。
可是我心里不自在,愁闷,觉得我在欺骗这个人。同时我又暗暗高兴。我瞧着又大又红的月亮升起来,想象那个高高的、苗条的金发女人,白白的脸儿,老是穿得很考究,身上洒一种特别的香水,类似麝香的气味,我想到她不爱她的丈夫,不知什么缘故,心里挺高兴。
我们回到家里,坐下来吃晚饭。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笑着拿我们买来的吃食款待我们。我发现她的头发确实美极了,她的笑靥任何女人也比不上。我留神看她,希望在她的每个动作和眼光里看出她不爱她的丈夫,我觉得真好像看出来了。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不久就困得要命,努力克制着睡意。晚饭后,他跟我们一块儿坐了十分钟光景,就说:
“你们随便谈谈吧,而我明天得三点钟起床。请允许我向你们告辞。”
他温柔而热烈地吻他的妻子,带着感激的心情握一握我的手,要我答应下个星期一定来。他怕明天睡过头,就到厢房里去过夜。
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保持着彼得堡人的习惯,夜间很晚才上床。不知什么缘故,这使我暗暗高兴。
“怎么样?”我开口说,这时候只剩下我们两人了,“那么,请您费心弹个什么曲子吧。”
我并不想听音乐,可是要谈话,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谈起。她在钢琴边坐下,弹奏起来,我记不得她弹了个什么曲子。我坐在一旁,瞧着她胖胖的白手,极力想在她冰冷而淡漠的脸上看出一点什么来。可是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她微微一笑,看了我一眼。
“您的朋友不在,您闷得慌了。”她说。
我笑起来。
“要说为了友谊,我一个月到这儿来一次也就够了,可是我一个星期不止来一次呢。”
说完这话我就站起来,兴奋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她也站起来,往壁炉那边走去。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抬起她那对又大又亮的眼睛瞧着我。
我一句话也没回答。
“您说的话不实在,”她想一想,接着说,“您纯粹是要看望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才到这儿来的。就是这样,我也很高兴。在我们这个时代像这样的友谊是不多见的。”
“得!”我暗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问道,“您想到花园里去走走吗?”
“不想去。”
我走出去,来到露台上。我的脑子里好像有些小蚂蚁在爬来爬去,我兴奋得浑身发冷。我已经相信我们再谈下去也无非是些最平淡无味的话,我们彼此是不会说出什么特别的话的;不过我又相信,有一件我本来都不敢梦想的事,今天晚上却肯定会发生。今天晚上肯定会发生,要不然就永远也不会发生了。
“多么好的天气啊!”我大声说。
“对我来说,天气好不好都一样。”她回答。
我走进客厅。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照原先那样站在壁炉旁边,双手放在背后,眼睛瞧着一旁,在想什么心事。
“为什么天气好不好在您都一样呢?”我问。
“因为我闷得慌。您只有在您朋友不在的时候才闷得慌,我却老是闷得慌。不过……您对这种事是不会发生兴趣的。”
我在钢琴前面坐下,弹响几个音,等着她再说下去。
“劳驾,请您不必拘礼。”她说,生气地瞧着我,仿佛烦恼得要哭出来似的,“要是您想睡觉,那就请便。您不要认为您既然是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朋友,就不得不陪着他的妻子一起烦闷。我并不要人家为我做出牺牲。请吧,您去睡觉好了。”
当然,我没有走。她走出去,站在露台上,我一个人留在客厅里,把乐谱翻了五分钟光景。后来我也走出去。我们并排站在帘子的阴影里,下面是浸在月光里的台阶。树木的黑影盖住花坛,伸展到林荫路的黄色沙地上。
“明天我也得走了。”我说。
“当然,既是我的丈夫不在家,您就不可能留在此地,”她讥诮地说,“我可以想象,要是您爱上我,您会觉得多么倒霉!您等着就是,早晚有一天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扑到您身上,搂住您的脖子。……我倒要看看您会多么恐慌地从我身边跑开。那才有意思呢。”
她的话和她苍白的脸是气愤的,不过她那对眼睛却充满极其温柔而热烈的爱情。我已经把这个美丽的女人看作我自己的人,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出她生着金黄色眉毛,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秀丽的眉毛。我想到我马上可以把她搂在我怀里,爱抚她,摸她美丽的头发,就忽然觉得这太离奇,不由得闭上眼睛笑了起来。
“不过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晚安。”她说。
“我可不希望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我说,一面笑着一面跟她走进客厅。“要是这个夜晚安静,我倒要诅咒它了。”
我握了一会儿她的手,把她送到房门口。我在她脸上看出她明白我的意思,而且因为我也明白她的意思而暗自高兴。
我回到我的房间。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一顶便帽放在我桌子上一堆书旁边,这使我想起他的友谊。我拿起手杖,走出门外,到花园去。花园里已经升起白雾,不久以前我在河面上见过的那些又高又细的幽灵,如今正在大树和灌木旁边徘徊,拥抱它们。我却不能跟它们谈话,多么可惜!
在异常清澈的空气里,每片树叶和每颗露珠都清楚地现出它们的轮廓,似乎半睡半醒,在沉静中向我微笑。我走过那些绿色长椅,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出戏里的话:月光在这儿的长椅上睡得多么酣畅!
花园里有一座小山。我爬上小山,坐了下来。一种陶醉的感觉煎熬着我。我拿得准,不久我就会搂住她娇美的肉体,贴紧她,吻她的金黄色眉毛。不过我又想不相信这件事,想嘲笑自己。我想到她没让我费多大的力,这么快就委身于我,反而觉得不自在。
可是这时候,出人意外地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林荫路上出现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我立刻就认出他是四十个殉教徒。他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在胸前画三次十字,躺下去。过了一分钟,他坐起来,翻个身又躺下去。蚊子和夜晚的潮气不让他睡着。
“哎,生活啊!”他说,“不幸的、辛酸的生活啊!”
我瞧着他消瘦伛偻的身体,听着他沉重沙哑的叹息声,想起今天有人在我面前吐露的另一种不幸而辛酸的生活,我就不由得心惊胆战,为我的欢乐心境感到害怕。我从小山上下来,往正房走去。
“在他看来,生活是可怕的,”我暗想,“那也就不必跟生活讲客气,索性打碎它,趁它还没碾碎你,凡是可以从它那儿捞到手的,你统统拿过来就是。”
露台上站着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我默默地抱住她,开始贪婪地吻她的眉毛、鬓角、脖子。……
到了我的房间里,她对我说她爱我已经很久,有一年多了。她为她的爱情对我起誓,她哭着要求我带她一块儿走。我不止一次地把她拉到窗前,好在月光下细看她的脸。我觉得她像是一个美丽的梦,我就赶快抱紧她,好让我相信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这种狂热的时光了。……可是,在我心底里,在灵魂深处,我仍旧感到有点别扭,我心神不定。她对我的爱情让人不好受,有点沉重,如同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友谊一样。这是一种强烈而严肃的爱情,带着眼泪,带着海誓山盟,可是我希望不要有什么严肃的东西,不要有眼泪,不要有海誓山盟,不要谈将来才好。让这个月夜像一颗明亮的流星那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闪过去,就此完事。
三点钟整,她离开我,走了。我站在门口,瞧着她的背影,走廊的尽头却忽然出现了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她碰见他,打了个哆嗦,给他让路,周身表现出厌恶的样子。他有点古怪地微笑着,嗽一下喉咙,走进我的房间。
“昨天我把我的便帽忘在这儿了……”他说,眼睛没有朝我望。
他找到便帽,两只手拿起它戴在头上,然后瞧一下我那慌张的脸色,瞧一下我的拖鞋,用一种不像他嗓音的、古怪而嘶哑的声音说:
“我大概命中注定什么事也不会弄明白。如果您明白了什么,那……我就向您道喜。我的眼睛前面是一团漆黑。”
他咳嗽着,走出去。后来我站在窗前,看见他自己在马棚旁边套车。他的手发抖。他匆匆忙忙地干着,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正房,大概他觉得害怕。后来他坐上马车,带着仿佛怕人追来的古怪神情扬起鞭子抽马。
过了一会儿,我自己也走了。太阳已经升上来,昨天的雾胆怯地退缩到灌木和小山那儿去了。四十个殉教徒坐在车夫座位上,他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灌饱了酒,醉醺醺地胡扯起来。
“我是自由人!”他对马叫道,“喂,你们这些枣红马!不瞒你们说,我可是个世袭荣誉公民!”
我的脑子里老是想着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恐惧,这时候,那种恐惧也传染给我了。我想起刚才发生的事,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搞的。我瞧着那些白嘴鸦,看见它们在飞,不由得觉着奇怪,害怕。
“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我茫然而绝望地问自己,“为什么这件事要落到这样的结局而不是别样的结局?她严肃地爱我,他到我的房间里来取帽子——这种事符合谁的需要,为什么需要呢?帽子跟这有什么相干?”
就在这一天,我动身到彼得堡去了,从此再也没跟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和他的妻子见过面。据说现在他们仍旧在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