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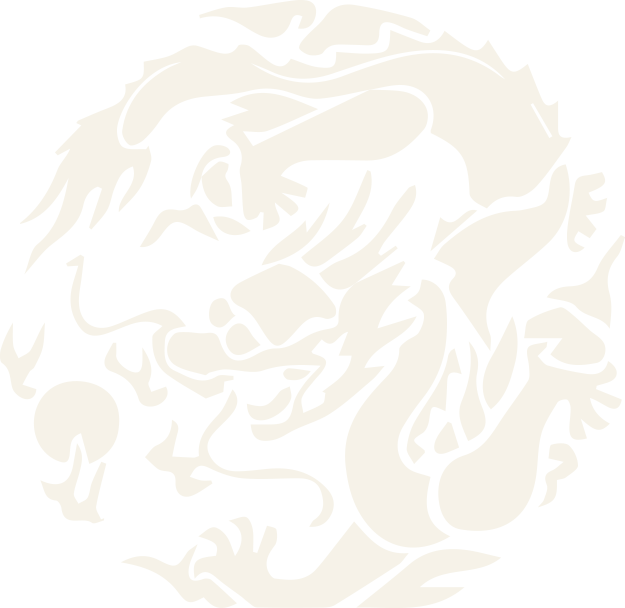
傅恒从巡抚衙门借了兵,当夜就离了太原城。这五百精兵原是雍正十年经岳钟麒在西宁前线训练过的。岳钟麒兵败和通伦,被撤去宁远大将军职衔,锁拿北京问罪。这支后备军没有用上就地裁撤。几年来陆续遣散了士兵,只留下些千把下级武官没法安排,被前任山西巡抚招了做亲兵,在中营护卫。得着这一立功的机会,这些武弁们真是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傅恒犹恐激励不起士气,将藩库拨来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全部分发了他们,二更启程,一色的骠骑牛皮甲,强弓硬弩,十名火枪手充作钦差护卫,保护着傅恒和李侍尧悄悄地出太原西门,疾速向马坊进军。第二日拂晓时分,他们便赶到了地处黑查山峪的马坊镇边。
“到了。”守在傅恒身边的廖清阁,眼看着一片黑魆魆的镇子愈来愈近,在马上用鞭子一指,说道:“中堂,前头就是马坊镇。这地方我来过两次。名儿叫作‘镇’,其实不到二百户人家,每年秋天马贩子们从中原驮茶叶到这里和蒙古人换马,也就热闹那么几天。”
傅恒浑身都是汗,被风吹得又凉又湿,冷冷地望着西北边黑森森的黑查山,又扫视一眼闪着几点光亮的马坊,问道:“镇子里有没有驿站?我们不熟这里的情势,闯进去,肯定会有通匪报信的。”“回中堂话,”廖清阁说道,“驿站倒是有一个,只十几间房,也没有专门的驿丞驿卒。镇东有一座天王庙,虽破落些,院落不小,依着我说,用一百人把镇子围了,只许进不许出。剩余的人都住到天王庙,等李道台的民兵来了再说强袭。”
“这是三不管地面。”李侍尧也在观看马坊镇,暗中看不清他的脸色,“镇上没有朝廷的官员,一个镇长,天晓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凡带刀的都由他支应——我们不亮身份,住天王庙还是对的。不过不用人围镇子。本来这地方就杂,三教九流、强梁大盗经常在此出没。谁也不管谁的账。我们旗甲鲜明地亮相,等于给人报信。”傅恒想了想,大笑道:“我们索性装作强人,点起火把!进天王庙!”
当下众人听令,点起了十几支火把,也不呐喊,由廖清阁带着,沿镇东驿道兜过去果见一大片空场旁边有一座庙,外边看去,里边房舍倒也不少,四周荒凉寂静。
“冲进去!”傅恒用鞭梢指着紧闭的大门大声命令道,“各房要挨着搜查,防着里头有人!”
几个戈什哈跳下马,发一声喊,一齐用力一推,那门却是虚掩着的,“哗”地豁然洞开,兵士们手按腰刀一拥而入。傅恒带着自己的亲随站在天井中心冷静观察。突然一个兵士舞着火把奔出来,歇斯底里大叫一声:
“这屋里有三个贼男女!”
接着便见三个黑影随后冲出来。黑地里看不清面貌,两个彪形大汉。还有一个个子极小,一手攥着香,一手提着刀,站在门口,似乎在发怔。好半晌,一个黑大个子才问道:“你们万儿?谁是心主,出来说话!”廖清阁大踏步上前,因不懂土匪黑话,学舌问道:
“你们万儿,谁是心主!”
“格拉鸡骨飞不去,毛里生虫!”那人答道,“你们万儿?”
“格拉牛骨飞不去,毛里生虫!”
三个人都是一愣,突然捧腹大笑。高个子倏地跳过来,挥刀便劈。廖清阁眼疾手快,将刀一格,顿时火花四溅,惊怒道:“日你姥姥!话没说完就动手?”
“你们是倥子!”
“你们是小倥子,倥儿子!”廖清阁道,“我们是紫荆山来的。飘高老杂毛要是这样待客,天不明我们就回去!”
傅恒原怕这院窝藏大股土匪,见只有三个人,便放了心,听廖清阁对得机警,不禁暗中点头。那三个人暗中互相张望一下,黑大个子回身对小矮个子道:“山跳蚤爷,他们不懂咱门切口,兴许是从紫荆山才过来的。飘总峰说过这事,恶虎滩那边人手不够——”他话没说完,那个诨号山跳蚤的一摆手打断了,声音又尖又亮:“你不是头儿,叫你们头儿出来!”傅恒听他口气,在驮驮峰是个不小的人物,见廖清阁暗中回头望自己,便大步走过去,闷着嗓子问道:“我是头儿。你有什么事?”
“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变了小童,见五色云中露出柬帖,菩萨拈起展开,许多无生默话!”
傅恒听了心里一紧,他在上书房见过收缴上来的卷帙浩繁的白莲教各派传教书,随便翻翻,都是些俚俗不堪的话头。对于“观音变小童”这句话出自何经何卷,已了无记忆,反正肯定在白莲教经卷中。见他考问,心里一急,憋出一句:“眼贼、耳贼、鼻贼、舌贼、身贼、意贼为六贼,真空老祖传我无字经!”
“你是飘总峰师弟!”山跳蚤似乎吃了一惊,略一怔又揖手问道:“说破无生话,决定往西方?”
这诗傅恒倒记得清爽,立即对上“花开见佛悟无生,悟取无生归去来”!那山跳蚤执礼更恭,放低了声音,似乎顿了片刻,又问:“前思后想难杀我,不知无极几时生。乱了天宫不打紧,儿女可曾回家中?”傅恒听了顿觉茫然,搜索着记忆回答道:“有表有疏径直过,有牌有号神不拣……万神归家誓有状,过关乘雾上云盘。见佛答上莲宗号,同转八十一万年!”他自谓这诗对得还算得体。不料话音刚落,山跳蚤改变了口气,恶狠狠道:
“你的切口大有毛病:一会儿大似佛,一会儿小似鬼!一会儿是正阳教,一会儿是白莲教——你他妈到底是什么人,哪个教?”
“老子是白莲教!”
“放屁!”山跳蚤怒喝道,“哪有这个说头?来路不明,我们飘总怎么会收你们?——我们走!”
“拿下!”傅恒见已露馅,“噌”地拔剑在手,大喝一声,“一个也不要放走了!”
那三个强人都是老江湖,见事情有异,早已全心戒备,呼哨一声一齐向后退。无奈傅恒人多,四周已围得铁桶一般。众人吆呼着蜂拥而上,一个回合交手,两个大个子已被按倒在地,乱中却寻不到山跳蚤。满院搜索时,却听正殿屋脊上一阵尖厉的怪笑,喋喋之声如夜半鸱鸮,笑得众人心里发瘆,抬头看时,依稀是山跳蚤蹲在兽头边。山跳蚤笑着道:“凭你们这点稀松本事,敢来黑查山闯地面?等我们飘爷擒住那个鸟傅恒再和你们算账!我这两个兄弟且留下,要当客敬,死一个换十个!”说着手一扬,寂然无声而去。傅恒觉得肩胛上一麻,用手摸时,粘乎乎不知什么,凑近火把一看,却是血,旁边廖清阁惊呼一声:“六爷,您受伤了!”
“不妨事。”傅恒小心从肩上摘下暗器观看,却是一只铁蒺藜,挤伤口看血色,颜色鲜红,并无异样,知道镖上没有喂毒。一口气松下来,傅恒才觉得钻心疼痛。当着这许多部众,他只好强咬着牙忍着疼痛。若无其事地扔了铁蒺藜,由随军医官包扎着,问那黑大个子:“你在驮驮峰上是个什么位分?叫什么名字?他呢?”
黑大个子哼了一声,说道:“我叫刘三。他叫殷长。都是山爷的亲随!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傅恒这才知道不过是捉了两个小喽啰,心里一阵失望,又问道:“山跳蚤是什么人?”
“连山爷都不知道?”刘三和殷长都抬起头。刘三惊异地望着傅恒,又打量了半日周围的人,突然惊道:“他们服色这么齐整,像是他妈的官军!”殷长却道:“官军哪来这股子人?飘祖爷会算计错了?”因离得近,傅恒看见殷长秃得寸草不生的头,加上一嘴大牙,傻乎乎的。正要再问,身边站着的李侍尧轻轻扯了扯傅恒后襟。傅恒会意,一边吩咐廖清阁:“好生问他,防着他是勾结朝廷官员的奸细。”心里暗笑着跟李侍尧过来,在西北角一片长满蒿草的空场上站定了。傅恒笑道:“你今晚怎么了?一句话也不说,阴沉沉的只是出神!”
“六爷,”李侍尧的声音发颤,似乎有点惊惧不安地说道,“我们小看了飘高。他打临县是假的。是要诱代州雁门关出兵,中途设伏袭击官军!”傅恒被风吹得打了个寒颤,良久才问道:“何以见得呢?”李侍尧道:“方才一见面,刘长就说出恶虎滩。还以为我们是飘高调请增援的匪徒。那恶虎滩紧挨着白石沟,地势凶险,又是雁门关到黑查山必经之路……”
他话未说完,傅恒已经悚然惊悟。临出发时,他和李侍尧看图志,李侍尧曾说:“幸而飘高只是小贼,兵力要大的话,中途设伏,范高杰他们可就要吃大亏了。”恶虎滩地势虽没有见过,但听这个名字,就够人心悸的了。傅恒思量着,说道:“临县是个诱饵。飘高的人马都在白石沟恶虎滩,山寨子就是空的了,我们的办法仍旧可行。”
“不但可行,而且做起来更容易。”李侍尧笑道,“不过有一条六爷得思量,我们下手早了,他们撤伏兵回山寨,范高杰他们隔岸观火,我们就苦了。我们下手晚了,范高杰他们损失太重,朝廷仍要怪罪六爷。时机不容易把握啊!”傅恒暗中瞟了李侍尧一眼,他很佩服这个小小通判,思虑周密。遂格格一笑道:“好,有你的。你来审问这两个匪痞!”李侍尧笑着答应一声“是”,变了脸大喝一声:
“把那个殷长给我拖过来!”
廖清阁正焦躁,忽听这一声,便丢下刘三放在一边,一把提起殷长,连拉带拖拽过来。刘三知道他口松,紧着叫道:“老殷,嘴上得有个把门的!——这群人我越看越不地道!”
“你地道,你嘴上有把门的。”李侍尧冷冷说道,“我这就叫你尝尝我的手段——把他扔进那边干池子里,填土活埋了他!”
几个兵士答应一声,将缚得像米粽似的刘三丢在干池,挖着土就填。刘三先还叫骂几句,后来便没了声息。殷长吓得六神无主,不停地磕头道:“好爷们哩……都是自己人,……都是一个祖脉,有话好生说呗,好爷们哩……”
“给脸不要脸,他不肯好生说么!”李侍尧满脸狞笑,手按着宽边刀柄,恶狠狠道,“爷们从紫荆山奔这门槛,上千里地,好容易的?说好了的,这里有人接应,送我们去白石沟。谁他娘封他飘高是绿林共主了么?说,飘高在哪里?我们要见他!”
“飘总峰在……恶虎滩……”
“寨子上有人没有?”
“有……留了三百弟兄,都有残疾。不能厮杀……”
“围临县的五千人是谁带领?”
殷长似乎怔了一下,笑道:“合山寨也没有五千人。那都是临时寻来老百姓充数儿吓唬官兵的,由辛五娘带着……”
“辛五娘。”傅恒从旁插话问道,“是不是还有个叫娟娟的?——长得很标致,会舞剑。”殷长摇摇头,说道:“小的没听说过‘娟娟’这名儿。五娘是无生老母莲座前玉女转生,自然标致啰!哎哟哟,那身子轻得站到荷叶上都不下沉,杏脸桃腮樱桃小口,看一眼管叫你三天三夜那个那个……”他色眯眯吸溜着口水,有点形容不来了。
李侍尧哪里晓得傅恒的心思?在旁说道:“少顺嘴胡吣!她是玉女是夜叉关我们屁事!我只问你,那个鸟山跳蚤如今跑哪里去了,是去了恶虎滩,还是奔了辛五娘?”殷长嬉笑道:“你问一我答十,干吗这么凶巴巴的?都是吃的正阳教,奉的一个无生母嘛!”李侍尧拍拍他肩头,说道:“你比刘三识趣。我亏待不了你,我们还指着你带路呢!”说罢一摆手,命人将殷长押了下去。
“我看这个蠢货不像说假话的人。”傅恒笑着对李侍尧道,“今夜虽然辛苦了点,却摸清了飘匪的计划。看来飘高为了打好出山第一仗,真的费了不少心机。他们既把我们当成紫荆山的人,那就是说,他们确实和紫荆山匪徒有联络。如今你一千民兵从离石赶来,也保不定紫荆山的人正往离石方向赶路呢!”李侍尧点头道:“六爷虑的极是!不过紫荆山的情形我略知一二,总共不足五百人,隔州隔县来为飘高卖命,他们未必有那个胆量。就是来,几百人又走了几百里山路,也没什么可怕的。”傅恒笑道:“我们就冒充紫荆山教匪,暂且在这马坊镇驻扎吧!”
李侍尧一时没有回话。两个人都坐在石坊牌下沉思默想。傅恒望着满天缓缓移动的云彩,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昨天还在太原和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们应酬,如今却又坐在这个破庙里和什么驮驮峰、紫荆山的匪徒打哑谜斗心眼。一转念间又想起娟娟,那倩倩玉影,超绝的剑术,那红绒绳上的姿态,月下赠诗,临别时深情的一瞥都历历在目。说不定日后还要疆场兵戎相见,不知是谁血洒草莱?思前想后情如泉涌,一会儿通身燥热,一会儿又寒彻骨髓……真个情随事迁,令人难以自已。李侍尧却在计算离石人马几时到达,范高杰几时经过白石沟,怎么能叫官军吃点苦头又得救,攻打驮驮峰的时辰必须掌握得分厘不差。正想着,傅恒说道:“我算着,我们要装六天土匪。你的一千人明晚能到。这几天人吃马嚼,粮饷的事很叫费心思。依着我的心,这会子就打寨子,倒省事了。”
“我和六爷一样的心。”李侍尧道,“但我们一打寨子,临县的和恶虎滩那边匪徒立刻就收兵,全力对付我们。范高杰他们并不真正为朝廷,他们为的是他们的张大帅。必定等着我们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时才来救我们。功劳是他们的且不计较,我们反倒落了吃败仗名誉儿。六爷,本来是我们救他们呀!而且那样,飘高的人马都是生力军。我们几百人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从天理、人情到军事、政治,非咬牙顶这六天,那时候,胜券就全操在我手了。”
傅恒静静听完,拍拍李侍尧肩头,深深吁了一口气,说道:“我知道你对,听你的。方才我说的是心情。”
隔了一日,李侍尧的民兵才陆续来到马坊镇。这群人其实也都是李侍尧收编的土匪和一些半匪半民的山民。衣色甚杂行伍不整,三十一群五十一伙,带着长矛、大刀片子、匕首,有的甚至背着鸟铳,腰里别着镰刀、砍柴刀什么的。
当地镇长叫罗佑垂,绰号“油锤”,其实原来也是个地棍,这地面各路土匪经常出没,士绅富户胆小不敢接待,共推了他专门和各路豪客周旋。眼见前晚有人占了天王庙,白天封门一个人也不来接洽,今天又有这么一大批不三不四的人进镇,所有的客房全部占满,连驿站也都占了。罗油锤又没见有人来寻自己,心里忐忑不安,总觉得要出大事似的。他在家兜了半天圈子终究坐不住,便拿了根旱烟管,带了几个镇丁径往天王庙来见傅恒。傅恒自忖身上毫无匪气,便命李侍尧出头接待。
“你是这里的镇长?”李侍尧一上来就使了个下马威,“老子的队伍三四千,都开过来了。飘总峰请我们到白石滩讨富贵,弄了半天是他妈的这种熊样!粮没粮,草没草,连个鬼影子也不见来接!这里离省城这么近,万一走漏了风声,我屠了你这鸟镇子回我的紫荆山!”他穿着绛红长袍,敞着怀,腰带上还别着五六把匕首,又轻轻在脸上抹了些香灰,很像割据一方的毛神。听他说话的口吻,躲在耳房窃听的傅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那罗油锤却不害怕,给李侍尧敬烟,见李侍尧毫无反应,燃了火煤子自己抽着,嬉笑道:“山主,四方有路,八面来风。马坊镇的情形瞒不了您老。这里的人信我油锤,抬举我出来侍奉远客。但来的,无论白道黑道,咱们都尽心竭力,只要护住这一方水土百姓,算我对得住祖宗。您老千万别生气。不知者不为罪,需用什么,只管冲我罗油锤要。姓罗的一定两肋插刀为朋友!”“这庙里住的是我家山主。有二百多个人,外头这些弟兄有三千多,在这里歇马四天,吃饱喝足赶道儿,你给我备两百石粮,三十车草,咱们两安无事,不然……”他看了看腰间的匕首,哼了一声。罗油锤怔了一下,仍旧变得嬉皮笑脸,江湖上的规矩不兴随便询问姓名,遂道:“好山主你哩,马坊这地方穷山恶水,出了名的赖地方。草料有,你要一百车立时就能办到。只是这粮——你老圣明,我全凭着秋天茶马交易收几个地皮税,专门建个粮仓支应各路豪杰。连飘爷都不轻易借这个粮——”
“你少拿飘高压我!爷天不管、地不收,是花果山上的自由神!”李侍尧一拍大腿,“粮,到底给是不给?”油锤嘿嘿笑着,一脸无赖相,说道:“给,当然给!仓库就在镇西北,您派人去瞧瞧,扫干净也只是一百石,爷要觉得不够用,我也没法子。要不解气,杀了我油锤就是。只求别动这里的百姓,那就是你老人家积阴功了。”
李侍尧心里谋算,一万斤粮一千五百人足可支用六天。不禁暗喜,口中却道:“我可怜你在这地面混饭不易,你人也还算晓事,这样,这一百石先支过来。你三天之内给我再征五十石,做成干粮,我赶往恶虎滩路上要吃。去吧!”
“山主……”
“滚!”
看着油锤低着头远去的背影,傅恒不禁拊掌大笑,说道:“侍尧有你的!现在万事俱备,只等着恶虎滩那边了。要派几个人到那边打听消息,我们攻寨子的消息,那边打响正好听到才成——只一条,不能让姓范的晓得我来。”
“那自然,六爷虑的是。”李侍尧笑道,“省城带的人不会装土匪。还是叫离石的人去吧!”
二人正说笑,外边戈什哈带着一个人进来。未及禀报,傅恒一眼就看见是吴瞎子,眼睛陡地一亮,笑道:“腿子好快呀!我估着你明天才能到呢!”见李侍尧发愣,待吴瞎子请安毕,一把拉过介绍道:“这是朝廷特许的联络招安绿林的小总管。有他来,我们办事就方便了。”又介绍了李侍尧,“第五天夜里我们攻驮驮峰,你就跟定我。院外那些士兵叫侍尧去经理。”
“我还带着朝廷的廷寄呢!”吴瞎子取出一封用火漆密缄的通封书简,双手递给傅恒,“省城的人都传说钦差大臣亲自到雁门关督军去了。幸亏我带了延清大人给喀中丞的信,见着中丞,才知道六爷在这里……”“好,喀尔吉善会办事,我就是要人们都知道我‘去了代州’!”说着便拆开廷寄。乾隆的旨意中严厉申斥傅恒,要他接旨后立刻就地驻扎待命。傅恒一笑,将朱批谕旨塞进了袖子里。李侍尧试探着问道:“万岁爷催着进兵么?”
“不是。”傅恒狡黠地眨了眨眼,“万岁叫我们把饷备足再进兵。”
六天之后范高杰带领五千兵马过岢岚城、渡界河口抵达白石沟。这一路走得都十分顺当,在东寨一带过了汾河进入吕梁山,一路走的都是从榆林到大同的古驿道。虽然年久失修,山间百姓驮煤、运粮都还在使用。他有兵部勘合,五寨岢岚的地方从来也没有支应过大军,地方官十分巴结,支粮支草,还各送了三百只风干羊,大军过城,家家香花醴酒摆在门口,取个“箪食壶浆”的意思。范高杰自然约束军队“秋毫无犯”。他和胡振彪、方劲私下里也落了三千两银子。在见傅恒之前,张广泗曾和他们会议,都觉得跟着白面书生打仗没味儿。张广泗指示他们:“这仗也没啥打头。明摆的,皇上想让六爷立一功。为他进位宰相铺路,也好堵众人的口。军事上还照咱们老办法,六爷那边要恭维着,打完仗他回北京,我另给你们记功升职。”三个人只急着赶快捣掉驮驮峰,解救临县之围,将飘高擒住完事,因而一路上虽是春光宜人,树吐新芽,桃花缤纷,危崖耸天,山溪湍流,十分好看,他们也都无心观赏,只催人马晓行夜宿赶道儿。
过了界河口,前头没了驿道,山势陡然间变得异常峥嵘,有的地方壁立千仞,高耸云端;有的地方乱石嶙峋,飞湍流急;有的地方老树参天,荆莽丛生;有的地方云遮雾漫、幽谷夹道。过大蛇头峪之后,连三位将军也只好下马走路了。范高杰一脚高一脚低地向前走,浑身的汗浸透了牛皮甲,又回头望望蚂蚁似的单行队伍,吩咐马弁叫过向导,问道:“这里离黑查山还有多远?前头的路都这么难走么?”
“回军门爷话。”向导说,“这儿已经进了黑查山。不过离驮驮峰还有三十里山路。前头已经过了蛇口峪,您看这满沟的石头都是白的,这叫白石沟。不下雨时算是‘路’。一下大雨就成河道。夏天是不敢走这道儿的。这边左手往南,是恶虎滩,过了恶虎滩就和驿道接上了。”
“向后传令,”范高杰命道,“在恶虎滩收拢营伍!叫后头快跟上。实在跟不上的,叫后卫收容!”方劲在旁说道:“军门,这里山势太险,我看不要一窝蜂过前头峪口,分成三部,过去一部,再过一部,这样就有埋伏,还能策应一下。”
胡振彪气喘吁吁满脸油汗从后头赶上来,冲范高杰吼道:“你带过兵没有?五千人拉了几十里长,像他妈一条蚰蜒!要我是飘高,两头一堵,从山上滚石头就把我们砸个稀烂!”
“把你的匪气给我收收,你这是和我说话?”范高杰腾地涨红了脸,“再敢胡说八道扰乱军心,我就地惩办了你!”又回身下令:“各营按营就地集结,三个营组成一队,快过前头的峪口了!”
蜿蜒长蛇一样的队伍走得慢了,慢慢变成了双行,又变成四行,五千人马前后用了半个时辰总算集中在二里长的一段狭路里。范高杰刚刚下令第一拨开拔,便听山上有人扯着嗓子高唱:
此地山高皇帝远啰——
不上税也不纳捐!
老子头顶一片天,
一脚踩踏吕梁山!
远客到这为啥子?
请你吃碗疙瘩面哟……
歌声刚落,便听一群人轰然和唱:
请你吃碗疙瘩面!
随着山歌声,“哗”地一声巨响,仿佛打开了什么闸门。满山坡的白石头并排地滚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