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到我女儿的来信是在周五,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是在昏醉中度过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星期一早上,尽管洗了个长长的冷水澡,我上班还是迟到了两个小时。在办公室待了不到四十五分钟,我就支撑不下去了。我的脑子要爆炸了。那地方像个坟墓。我先溜到复印间,然后躲到卫生间,再蹿到电梯间,我没有穿外套,也没有拎公文包,这样,就算有人注意到我的走动,也不会想到我是要从公司开溜。
那样做蛮愚蠢的。根本没有人注意我。那是一家大公司。我的存在与否,丝毫不会影响到公司。现在看来,在电梯到停车场的那段路上,我走完了作为那家公司雇员的最后一段旅程。
※
接下来,我用公用电话给我的前妻拨了个电话。她在上班。
“为什么?”她一拎起话筒我就问。
“鸡仔?”
“为什么?”我重复了一遍。积蓄了三天的焦躁、愤怒,爆发出来的就只有那么三个字。“为什么?”
“鸡仔。”她的语气弱了下来。
“连个邀请都没有?”
“那是他们的想法。他们觉得……”
“觉得什么?安全?怕我来搞破坏?”
“我不知道……”
“我成了瘟神了?是不是?”
“你在哪里?”
“我是瘟神?”
“别说了。”
“我看我还是走了算了。”
“听着,鸡仔,她也不是小孩子了,而且如果……”
“那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
我听到她吸了一口气。
“你要去哪里?”
“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
“我很抱歉。事情挺复杂的。还有他的家庭。而且他们……”
“有人陪你去参加婚礼吗?”
“噢,鸡仔……我在上班,知道吗?”
那一瞬,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那孤单好像压住了我的肺,让我根本无法呼吸。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不论是这事,还是其他任何事。
“好吧。”我无力地说:“打扰了。”
话筒那端又传来片刻的寂静。
“你要去哪里?”她问。
我挂上电话。
※
接着,我又喝醉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先去了泰德酒吧。那里的酒保是一个身材瘦削、长圆脸的小伙,可能和我女儿嫁的人差不多大。回家后,我又往肚子里灌了一点酒。我撞在了家具上,还在墙上乱涂乱画。我好像还把那两张结婚照扔进了垃圾桶。大约是在午夜时分,我决定要回家,我的意思是回椒谷海滩镇的老家,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那地方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但我已经有好多年没回去了。我在屋子里转着圈,像是要为回家做准备。但终结之旅并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我到卧室里,从抽屉里拿了把枪。
我摇摇晃晃走到车库,找到我的车,把枪放在方向盘旁的储物箱里,把夹克衫扔到后座,或者是前座,也有可能那件夹克衫早就在车上了,我不清楚。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开上了街道。城市很安静,街灯闪着微黄色的光,我准备回到人生开始的地方,结束我的生命。
跌跌撞撞回到上帝那里。就这么简单。
我们骄傲地宣布:
查尔斯·亚历山大·贝奈特出生了
8磅11盎司重
诞生于11月21日,1949年
雷奥纳多和宝琳·贝奈特
(来自鸡仔贝奈特的文件中,19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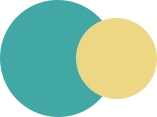
天很冷,且飘着小雨,幸运的是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我的车在四条车道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你可能会想,会希望醉成像我这样的司机,应该会被警察拦下,可奇怪的是,居然没有。途中,我还把车开进一个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从一个留小胡子的亚裔店员手中买了六罐啤酒。
“来张福利彩票?”他问。
多年来,我已经练就了在烂醉如泥时保持正常嘴脸的本事——能让“酒鬼”变成“行人”——于是我假装把这个问题琢磨了一下。
“这次就算了。”我说。
他把啤酒装在一个袋子里。看到他的注视,我注意到他眼睛里的那两个黑眼珠,心想: 这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后一张脸了。 他把找零的钱,推到我面前。
※
路牌上写着:“椒谷海滩,出口,1英里”。在公路上看到这块牌子的时候,两罐啤酒已经下肚了,还有一罐倒在了前面的座椅上,洒得到处都是。刮雨器左右摇摆,我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闭上。我恍恍惚惚想着:“出口,1英里”,想着,想着,就看到了另一块路牌,写着另外一个小镇的名字,这才意识到已经错过了出口。我狠狠地敲着汽车的仪表板,然后在公路中间就地来了个急转弯,逆向行驶起来。路上没有其他车辆,就算有,我也顾不上了。看到那个出口近了,我猛踩油门。突然,一个坡道就出现了——可居然是一条进入式的,而不是出口坡道——车轮擦着地面,发出尖厉的啸叫声冲入坡道。那条坡道绕了好几个圈,我打足了方向盘,车子转着圈,急速下行。
突然,两股巨大的光束冲我直射过来,像两个大太阳,然后传来了卡车喇叭的轰鸣,接着是猛烈的撞击,我的车飞出护栏,重重落在地上,然后往下冲。到处是碎玻璃,啤酒罐飞来撞去,我紧紧抓住方向盘,车突然向后仰,让我的肚子压住了方向盘。不知怎么我拉开了车门把手。我记得眼前闪过黑色的天空,绿色的野草,耳边传来雷鸣般的巨响,有样东西从高处结结实实地砸下来。
※
睁开眼,我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湿漉漉的草地上。车被半埋在一块被撞倒的大广告牌下。显然是我的车把这块雪佛兰经销商的广告牌给撞翻,并碾了过去。在古怪的物理力学的作用下,我肯定是在汽车翻转之前,被甩了出去。你刻意去寻死,死却放你一马。谁能对此做出解释呢?
我慢慢地,痛苦地站起来。后背全湿透了,浑身疼痛。天依旧在下雨,周围很安静,只有几只蟋蟀的鸣叫。通常,到了这种地步,你肯定会想,我一定庆幸自己还活着。但其实我没有那样想。我抬头去看高速公路。雨雾中,我看到了那辆迎面撞上来的卡车。它躺在那里,像一艘巨大的沉船。卡车的前车厢被狠狠砸过,好像被人拗断了脖子一般。有一个车头灯还亮着,射出的光柱照着泥泞的坡道,玻璃碎片发出钻石般的光芒。
那个驾驶员去哪里了?他还活着吗?受伤了吗?他还活着吗?在流血吗?在呼吸吗?那一刻,如果是个真汉子,应该爬上去查看一下情况。但在那一刻,勇气却不是我的强项。
所以,我没有那样做。
我垂着双手,掉头向南走,那是家的方向。我是个懦夫。我已经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我像一具僵尸,一个机器人,意识中没有了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我早把自己给忘了。我忘了我的车,撞上的卡车,车厢里的手枪,我都扔在了脑后。碎石在我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还有蟋蟀在鸣叫,像是嘲笑我的存在。
※
走了有多久,我说不清。反正走着走着,雨停了,天边传来第一缕曙光。我已经到了椒谷镇边上,那里有座大水塔。水塔的外壳已经有些生锈,它就矗立在棒球场的后面。在这样一个小镇,爬水塔是每个人的童年的组成部分。我和棒球伙伴们常常在周末,腰里插着喷漆罐,爬上这座水塔。
现在,我又站在了这座水塔前。湿漉漉的我,一把年纪,失魂落魄,浑身酒气,恐怕还害别人丧了命,因为在事故现场,我压根没有看到卡车司机。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已经完全无须考虑了,我坚定地认为,这会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我在水塔下找到了往上爬的梯子。
我开始往上爬。
梯子绕着水塔转来转去。我爬了很长时间。终于爬到了塔顶,我喘着粗气,一下子瘫倒在那里。虽然糊里糊涂的,但记得我脑海里还有个声音在责备自己:怎么临了还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不堪呢!
站在塔上往下看是一片树林。树后面是那个棒球场。我爸爸就是在这个棒球场上教我如何打棒球的。眼前的景象还是勾起了一些让人悲伤的回忆。为什么童年总是缠着人不放,就算你潦倒至此,就算你自己也难以相信自己以前也是个孩子。
天慢慢亮了起来。蟋蟀的叫声更响亮了。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回忆:小玛丽亚躺在我的胸脯上,她的皮肤散发着痱子粉的香味;然后,我好像看到自己闯进她的婚礼,湿漉漉的,脏兮兮的,就像我当时那样。音乐停住了,每个人都惊恐地看着我——玛丽亚是最为惊恐的那一个。
我低下头。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留恋我。
我跑了两步,抓住扶手栏杆,翻越而过,人飞了出去。
※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无法解释。我撞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会还活着,我没法告诉你。我所能想起来的就是旋转和噼里啪啦的声音,擦着,碰着,最后是“嘭”的一声。我脸上的这些疤痕?我估摸着就是那时候留下的。我应该下落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周围全是掉落的树枝、树杈、树叶。石头压着我的胸口和肚子。抬起下巴,我看到了:年少时的棒球场,沐浴在晨光中,还有球场边的两个球员候场区,以及投手站立的地方那撮隆起的尘土。
还有,我妈妈,我去世多年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