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猜猜。你想知道我为啥要自杀。
你想知道我怎么没死成。为什么我失踪了。这些年我去了哪里。但首先我为什么要自杀,对吧?
没问题。人人都这样问。他们都在拿我和自己做比较。大家都觉得人生可能存在某种底线,如果没有越过那条底线,人是不会去考虑跳楼啊,吞安眠药啊——但如果你超越了底线,就有可能那样做。大家觉得我肯定是过了底线。大家还会想:“我会走到他那一步吗?”
但事实是,没有什么底线。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把生活搞砸了,搞砸了之后,有没有人来拯救你。
或者,那个可以拯救你的人,是不是在那里等着你。
追忆往事,我试图弄清楚,我妈过世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她过世的时候,我不在她身旁。我应该在的。所以,我撒了谎。这是个馊主意。这样的秘密在葬礼上是瞒不住的。我站在她的墓碑旁,努力让自己相信,我没有在最后时刻陪在她身旁不是我的错。就在那时,我十四岁的女儿拉起我的手,轻声说:“爸爸,我很抱歉你连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她的话,让我崩溃。我跪了下来,泣不成声。湿漉漉的草地弄脏了我的裤子。
葬礼后,我烂醉如泥,昏睡在沙发上。生活起了变化。一天可以改变一生。对我而言,那一天彻底压垮了我。我的生活,曾经被笼罩在母亲的影响下——她的意见,她的批评,她那让人窒息的母爱。我还曾一度暗自希望她不要再来管我了。
但她真的去了。她死了。没有了探望,没有了电话。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放任自己,好像被连根拔起的草,让生活的波浪把我推向边缘。妈妈的存在给孩子们某种有关自我的幻觉。我的一个幻觉就是:我对自己的状态挺满意的,因为她挺满意的。而她一过世,那个幻觉就随之消失了。
实际上,我对自己一点也不满意。我本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有前途的年轻运动员,但那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也不再是运动员了。我成了个中年推销员,早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母亲去世差不多一年后,我做了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投资决定。我听信了一个女人的花言巧语。她年轻、漂亮、自信、态度可人,衣服总是敞着两粒扣子。上了年纪的男人从她身边走过,难免恨由心生,懊恼自己生不逢时——除非她主动和他搭话。然后,那男人就昏了头。我们见了三次面,讨论投资的事情:两次在她的办公室,一次在一家希腊餐厅。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但我的脑子显然被她的香水熏懵了,我把几乎所有的存款都投到了那个现在已经一钱不值的股票基金里。她很快被“调任”到西海岸,留下我面对我老婆凯瑟琳,向她解释我们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那以后,我喝酒更凶了——我们那个时代的球员都爱喝上几口——但那成了一个问题,以至于让我两次遭人解雇。而解雇又加重了我的酗酒。我睡不好,吃不好,迅速衰老。有工作的时候,在见客户前,我都得迅速冲到卫生间里,用随身带着的漱口水和眼药水,掩饰一下自己的酒气。钱成了一个问题;凯瑟琳和我总是为此争吵。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婚姻完蛋了。她厌倦了我的萎靡,而我有什么理由去责备她呢。一天晚上,她在地下室找到了躺在地板上神志不清的我。我的嘴唇摔破了,怀里抱着棒球手套。
不久以后,我离开了家——或者说,家离开了我。
我对自己的痛恶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搬进了一间公寓。我变得顽固、自我封闭。除了酒友,我不再和任何其他人往来。如果母亲还在世,她说不定有办法帮我,因为那是她擅长的事情,她或许会拉着我的胳膊说,“好了,查理,说说看你到底怎么了?”但她不在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了父母,无论去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在孤军作战,没有了那个永远在那里守候你的后援。
后来,一个晚上,一个十月初的晚上,我决定要去自杀。
或许你会觉得惊讶。或许你会想,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参加过棒球世界系列赛的人,怎么着也不至于沦落到要自杀的地步啊,因为至少有过了梦想成真的辉煌。但你错了,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不过是一个缓慢的、渐渐融化的过程,让你发觉,这跟你想象的是两回事。
那个东西救不了你。
※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真正把我推下了悬崖、让我彻底完蛋的,是我女儿的婚礼。那时她二十二岁,有一头直直的褐色长发和性感丰满的嘴唇,和她妈一个模样。婚礼是在某个下午举行的,她嫁了一个“非常棒的男人”。
我知道的,就那么多,因为她就写了那么多。我是在婚礼举行过几个星期之后,才从她寄给我的短信里知道这件事情的。
显然,因为我的酗酒、抑郁,以及其他种种糟糕的行为,对于任何家庭活动来说,我都成了一个巨大的、令人尴尬的包袱。所以,我只配收到一封信和两张照片。一张照片上我女儿和她的新婚丈夫手拉手,站在一棵树下;另一张照片上这对快乐的小夫妻正举杯庆贺。
把我打倒的是第二张照片。那是一张极其生动的抓拍照,那个精彩的瞬间永远无法再现:他们看起来像是话讲到一半,笑了起来,手里的杯子有点倾斜。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纯真,那么年轻,那么……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永远过去了。照片像是在嘲笑我的缺席。 你不在那里。 这个现在和我女儿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认都不认识。而我的前妻认识他。我们的老朋友们认识他。 你不在那里。 再一次,我在重大的家庭事件上缺席了。这一次,我的小姑娘不会再拉起我的手,安慰我;她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他们连问都没有问我。他们只是通知了我。
我看看信封上,落款用了夫家的姓氏(玛丽亚·朗,而不是玛丽亚·贝奈特)。信封上没留他们的地址(为什么?难道害怕我去看望他们吗?)我沮丧到了极点,万念俱灰。我唯一的孩子拒绝我介入她的生活,好像锁上一扇铁门不让我进去。你去敲门,他们听不到。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无人理睬,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活着没有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不自我了断呢?
所以,我决定自杀。
那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样做更多的是因为:做了又怎么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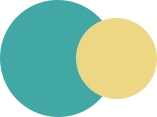
跌跌撞撞回到上帝怀抱,
歌谱了一半,曲唱了半首,
有谁知道,他肿胀的双脚跋涉了怎样的路途,
征服过哪些平静的,或是痛苦的山峰?
我希望上帝给他微笑,拉起他的手,
说:“你这个逃学的可怜虫,多情的傻瓜啊!
生命之书难以破解;
你如何能够不留在学校里呢?”
(诗歌,作者查尔斯·汉森·唐维,被抄录于鸡仔贝奈特的记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