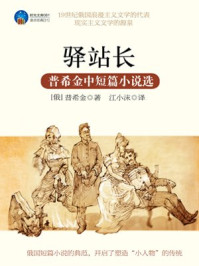透析仪不断发出细微的声响。
医生曾告诉我们,床边有监控装置,在进行洗肾的过程中,护理师与临床工学技师可以随时观察血液量及透析液的温度等数值。许多医院都禁止病患洗肾时家人陪在旁边,但由香里挑选了一家没有这个规定的医院。
“唉,没事做——好无聊,好无聊——”夏帆咕哝道。
我想办法挤出与外孙女的共同话题。
“对了,夏帆,你不是在踢足球吗?最近还有射门成功吗?”
“我不踢了。”
“不踢了?身体变得那么差吗?”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透析室里,没办法跟其他队友一起练习。”夏帆的声音有气无力,简直像是发条松了的机关玩偶。
“你知道吗?医生跟我说过,还有其他洗肾的方式呢。”
“腹膜透析,对吧?”
“对,就是那个。”
所谓的腹膜透析,是事先在腹部插入导管,病人每隔数小时自行更换透析液包。虽然配件的清洁维护有些麻烦,但好处是不必到医院,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排除血液中的废物。
“我很讨厌那个方法。以前体育课换衣服时,同学说我肚子上有根管子很恶心。”夏帆说道。
“腹膜透析不管用了。”后方传来由香里的声音,“听说持续了五年之后,腹膜就会渐渐失去机能,所以我们才换成了血液透析。”
“原来如此——”
“妈妈,帮我拿那本书。”夏帆对由香里说道,似乎是不想再与我交谈。
“来,拿去吧。”
听说血液透析通常使用的是非惯用手的手腕静脉,必须插两根针管,所以人没有办法自由活动。
我默默地坐着,坚持了三十分钟左右,每隔几分钟,我就会听见翻动书本的声音。
“——外公,你知道‘かんじん’这个词的汉字怎么写吗?”夏帆突然说道。
“肝脏的肝,肾脏的肾,‘肝肾’?”我回答。
“嗯,因为肝脏跟肾脏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肝肾’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重要’。但是我的‘肝肾’已经坏掉了其中一个——不对,肾脏有两个,所以是坏掉了其中两个。”
夏帆或许是在强忍悲伤,这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简直像是在诉说童话故事中的公主的遭遇。然而,这样的态度更令我感到心疼。
“外公,你的眼睛不是看不见吗?为什么会看不见?”
“这个嘛——”
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不晓得该不该说。由香里曾提过,夏帆在小学里跟健康的同学们相处时,总是郁郁寡欢,连老师都必须提心吊胆地随时注意着她。但是在透析室里,她跟年龄、性别都与自己不相同却同样必须洗肾的病人们相处时,却显得相当开朗。这种必须目睹他人的不幸才能让自己振作起来的精神状态,实在令人感叹。但若我的不幸遭遇能成为她的精神食粮,那就无所谓。不如就跟她说吧。
“应该是在中国生活造成的。至少外公是这么认为。”
母亲曾跟我提过,一九二九年美国发生大萧条,日本也遭到波及,城市里有几百万人失业,农村里卖女儿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两年后,日本东北地区桑叶严重歉收,养蚕业者无法继续养蚕,再加上蚕丝价格因大萧条而暴跌,蚕茧卖价跌落至每贯两日元八十钱,不到往年的三分之一。母亲的老家正是经营养蚕业的,生计因而遭受严重打击。
就在这个时期,区公所职员开始大力鼓吹农民到中国东北开垦。他们声称只要过去,就可获得十町步的农地,能够栽种出大量农作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于是,这些满怀希望的农民便在日本国旗及“万岁”呼声的欢送下,搭船自新潟港出海,来到了三江省桦川县
 。开拓团周围一带尽是农地,必须走上很久才能看见森林或河川。
。开拓团周围一带尽是农地,必须走上很久才能看见森林或河川。
虽然地广人稀,但就像当初区公所职员所说的,每一户都分到了一头牛、一匹马,以及十町步的农地。跟当初住在日本时相比,农地面积是原来的十倍以上,加上土壤肥沃,大豆、玉米等农作物年年丰收。母亲一家人不仅雇用了三名苦力,而且还扩大耕种面积,三年后收获的谷物已多达十二吨。
我便是出生在这片广大的中国土地上。
在东北生活的点点滴滴,此时历历在目,令我有种错觉,仿佛人生的轨道硬被拉成了V字形,现在与过去已联结在一起。多次听母亲提起的生活琐事,与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已难以区别。岁月的界线变得模模糊糊,全没入了记忆的奔流之中。
有一次,我发高烧昏睡了一整天。到了三更半夜,我偶然醒来,从棉被里坐了起来。转头一看,哥哥就睡在我身边,父亲则盘腿坐着,不眠不休地照顾着我,我左右张望,却看不到母亲。
“——妈妈呢?”
“在外头熬夜为你祈福。”
当时我的烧已经退了,于是我打开门向外望去。苍白的月光,母亲正独自用毽拍将毽子往上打。母亲身上穿着颜色朴素的雪袴,黑色头发盘在头上并用手帕包住。
咚——咚——咚——
除了毽拍一次又一次将毽子往正上方送的声音外,我还听见了母亲的清澈歌声。
一是最初一之宫
二是日光东照宫
三是佐仓宗五郎
四是信浓善光寺
五是出云的大社
六是各村镇守神
七是成田不动明王
八是八幡的八幡宫
九是高野弘法大师
十是东京的招魂社
祈求各方神明庇佑
让吾子平安无病痛
母亲看见了我,蓦然停下动作,毽子跟着落到地上。她小跑步朝我奔来。“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休息!”
“好——”我点了点头,“刚刚那是什么歌?”
“妈妈在向神明祈求让你早点恢复健康。”
我回到房间,听着母亲的歌声沉沉睡去,隔天早上,身体已完全恢复健康。
后来母亲告诉我,毽子是用“无患子”的果实制成,因为其字面上的意思,经常被使用于祈祷孩子平安无事的仪式。
仪式中所唱的歌,似乎是日本孩童之间流行的手鞠
 歌。前面的十句,举出了十种神佛寺社的名称,借以沾其法力;后面的两句,则据说典出小说《不如归》。在这部小说中,有个名为浪子的少女,因此歌词原本唱的是“让浪子平安无病痛”。但是中文的“浪子”带有不肖子、坏儿子的意味,所以母亲将歌词改成了“吾子”。
歌。前面的十句,举出了十种神佛寺社的名称,借以沾其法力;后面的两句,则据说典出小说《不如归》。在这部小说中,有个名为浪子的少女,因此歌词原本唱的是“让浪子平安无病痛”。但是中文的“浪子”带有不肖子、坏儿子的意味,所以母亲将歌词改成了“吾子”。
后来母亲病倒了的时候,我也以拍毽子唱数字歌的方式为母亲祈福。当时正下着大雪,我一边冷得发抖,一边拍着毽子。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在第七句或第八句处失败,但持续练了好几小时之后,我终于能够将数字歌唱完一轮了。
“和久!”父亲喊了我一声,“快回房间去吧,别把身体冻坏了。那个歌只能为孩子祈福,对父母没效的。”
当时我才四岁,个性却比任何人都顽固。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在外头拍着毽子唱数字歌,直到被硬拉进屋里为止。母亲在四天后恢复了健康,我一直为此感到自豪。
对我而言,相较后来的人生,在东北生活的那段日子要幸福得多。那时候,我的父母每天一大早便忙于农务。当时他们采用的是“犁杖农法”,将一种名为犁杖、外形类似锄头的农具套在马身上,牵着马耕田。这跟故乡的农耕方式不同,虽然不太适应,但好处是能活用牛、马的力量,不必做得腰酸背痛。
鸡都放养在住家的周围,我只要发现鸡蛋,就会偷偷吃掉。此外,开拓团的加工厂还能生产酒及酱油,在食物上完全不虞匮乏。
我跟哥哥经常与开拓团的其他孩子一起游玩,有时我们会比赛吐西瓜籽,看谁吐得远。家里雇用的苦力们也对我很好,我经常跟他们要馒头吃。如今回想起来,那些馒头应该是他们的珍贵粮食,但雇主的孩子在一旁不断吵着要吃,他们不敢不给。
我们虽然没有玩具,但还是能想出玩的法子。哥哥在相扑游戏上特别有一套,虽然身材矮小,却能将年纪比他大的中国少年摔出去。对方往往也不甘示弱,不管被摔倒多少次都会爬起来继续挑战,但哥哥一次都不曾输过,久而久之,每个孩子都把哥哥当成了老大。当时我年纪还小,在孩子群中拥有“横纲”地位的哥哥一直是我心中的骄傲。
但是就在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风云突变,苏联开始攻打东北日军。在一个月前的全体动员令(以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男性为对象的征召令)中,包含父亲在内的所有开拓团男人都被征召了,开拓团内只剩下老弱妇孺。
就在这时,一名传令兵骑着马来到了开拓团的驻扎地。
“大事不好了!苏联军队终于要打过来了!”
聚集在一起的开拓团成员们都吓得说不出话来。
“不快点逃会没命的!”
所有人吵成了一团,几乎听不见传令兵的声音。该不该抛下好不容易建立的家园?苏联军队应该打不过日本关东军吧?
“我们应该相信日本的军队!”母亲大声说,“在崇山峻岭之间乱窜实在是太危险了!”
“听说关东军早已抛下我们独自逃走了。”
“不可能,军队绝对不会对我们见死不救的。”
“我也不愿意相信这种事,但是——”
“我们应该对军队有信心!”
开拓团成员们出现了意见分歧。大部分成员都将身家财产及粮食分别装上数辆马车,离开了驻扎地。但包含我们家在内,有二十多人选择留下。
过了两天之后,留下来的人也逐渐失去了信心。向关东军发电报,却得不到任何回应,甚至有人听到谣言,其他开拓团已被全灭。
“我们还是快逃吧。”留在驻扎地的妇人们开始带着孩子整理起行李,“再不逃,恐怕真的会被那些苏联兵杀光。”
“可是——难道要抛弃这个家?”母亲疑惑地问道。
“是啊。”
“再等一天——不,再等半天看看吧。”
“天一亮,容易被发现,要走就得趁现在。”
其他开拓团成员的态度相当强硬,母亲最后只好屈服。打包完行李后,母亲在家里的柱子上用日文及中文刻下了一家人的姓名及日本岩手县的老家地址。当然,中文的部分我是看不懂的。
“爸爸要是回到家里却找不到我们,一定会很焦急,得让他知道我们已经回日本了。”母亲说道。
就在我们即将出发之际,突然有个中国孩童朝哥哥奔了过来,他先用中国话吆喝了几句,接着又用别扭的日语说道:“老大,别死,再来比相扑,约好了。”
哥哥将拳头举到下巴前,接着与中国孩童互相拥抱。之后,我们与将近三十人的开拓团成员一同出发,所有的食物及毛毯都堆放在一辆由一匹马拉着的马车上。
我们趁着夜色不断赶路,有时会看见天上飞着宛如恶魔眼珠的红色光点,伴随着可怕的轰隆声。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机枪扫射。
在阳光耀眼的大白天,我们一行人躲藏在高粱地里头。从前这种里头可以躲人的高耸农作物是被禁止栽种的,没想到此时高粱地反而成了逃亡时的最佳掩蔽。
我每跨出一步,前方开了口的鞋子便发出“啪啪”的声响,裸露在外的脚指甲沾满了污泥,变成了茶褐色。
一架苏联飞机陡然朝我们飞来,在轰隆声中迅速下降,用机枪对着我们扫射。地面的泥土不断弹跳,宛如承受着骤雨的水面。灰尘满天飞舞,妇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几乎每个人都陷入半疯狂的状态,甚至有精神错乱的母亲带着孩子跳进了附近的井里。
那简直跟地狱没两样。放眼望去,尽是遭机枪子弹撕裂的尸体,地上随处可见残缺不全的手或脚。
敌机离去后,幸存者面面相觑,五官皆因恐惧而扭曲变形。敌机随时有可能带着其他敌机返回,要活命就得尽快离开此地,每个人都以类似这样的话互相催促,匆忙捡拾散落一地的行李。马匹卧倒在血泊中,早已肚破肠流,这意味着众人失去了马车。
每个人各自背起行李,匆匆迈开步伐。
太阳逐渐没入山峦的棱线后方,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都被夕阳染成了深红色。数不尽的高耸穗株在风中摇摆,形成了波浪状的景色。当时在我眼里,那就像是大量战场亡魂的鲜血所汇聚成的大海。
就在我们走到第五天的时候,西方一片宛如白骨的白桦林的另一头,传来了枪响及爆炸声。
看来是死定了——
不知是谁发出的悲恸呢喃,宛如传染病一般蔓延开来,感染了所有人的心情。开拓团成员一个接一个跪倒在地上。
团长身上携带的手枪及手榴弹,是一行人唯一的武器。
“——现在是让敌人见识大和魂的时候了。”年老的团长环顾众人说道。
妇人们的扭曲面孔上,流露出了某种觉悟。团长掏出数颗胶囊,分给了几个人,没有人开口询问胶囊里塞的是什么。
“药不够,其他人我会另外想办法。”
“——这很有营养哟。”一位头发盘在脑后的妇人带着半哭半笑的表情将胶囊塞进怀中婴儿的嘴里,自己也吞了一颗,接着以宛如捧着佛珠一般的姿势双手合十,念起了佛号。
“把这个药吃下去吧。”另一位瘦削的妇人对着年幼的女儿说道,“这样就能到佛祖的身旁,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瘦得头上清晰可见头盖骨形状的女儿抬头问母亲:“妈妈也能吃好吃的东西吗?”
“当然,我们一起去极乐世界吧。”
过了一会儿,吞下胶囊的那些人开始猛抓喉咙,痛得在地上打滚,口中不断喷出鲜血。我瞪大了眼睛,看着这惨绝人寰的景象。身旁其他人的表情各自不同,有的别过了脸,有的开始啜泣,有的大声哀号。
哥哥神色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噩梦,突然摇了摇头。
“不能死——”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得活下去才行——”
但孩童基于本能所发出的呢喃,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年老的团长接着要剩下的妇人及孩童排成一行。每个人都跪在地上,凝视着前方的某个点。团长站在所有人的后方,用手枪朝着每个人的后脑勺一一开枪。
开了六枪后,第七名妇人双手交握,闭上了眼睛。但第七声枪响迟迟没有响起,妇人似乎是等得心焦,睁开眼睛望向身后。团长紧握手枪,对着她摇头说道:“只剩下一颗子弹了。”
“既——既然还有一颗——”妇人抱住了团长的脚,“请用这颗子弹杀了我吧。”
“我得为自己留一颗才行,抱歉。”
“求求你行行好——请你一定要杀了我——下一个明明轮到我了——”
团长紧咬嘴唇,举起手枪将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妇人的脑门。接着团长环顾剩下的人,取下腰际的手榴弹高高举起。
“所有人都过来吧。这是最后的法子了——”
十多个人全都凑了过去,为了尽量靠近握着手榴弹的团长,所有人你推我挤。团长的手宛如生了病一般颤抖个不停。
“我不想死——妈妈——我想活着回日本——”哥哥抬头看着母亲。
我与哥哥手牵着手,被母亲抱在怀里。
“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团长这么一问,所有人都点了点头,一位抱着小女孩的妇人念起了南无阿弥陀佛。
“天皇陛下万岁!”
团长拔下了手榴弹的插销。就在这时,白桦林的深处走出了几道人影,那是身穿军服的日本人,是自己人。所有人察觉这一点后,都急忙站起,想要远离团长手中的手榴弹。团长的手指或许是僵住了,没有做出扔掷的动作,一声轰天巨响,泥沙喷上了天空,数人的身体像纸片一样飞了出去。
浓浓的烟雾遮蔽了我的视线,幸好我一直紧握着哥哥的手,才不至于离得太远,勉强爬到哥哥的身边。母亲及哥哥都还活着,虽然三人身上的衣服都沾满了鲜血与肉块,但都没有受重伤。
之后我们便与那几个幸存的关东军士兵一同行动,有的士兵甚至还带着孩子。那些士兵对我们说,他们一群人没有赶上避难的列车,只好在山中东逃西窜,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使得同伴不断减少。那些士兵皆满脸胡楂,身上的军服脏污不堪且破损严重。
在手榴弹爆炸后,存活的开拓团成员仅剩八人,包含四位妇人、三名孩童及一个婴儿。至于关东军士兵那边,则有五名士兵及一名孩童。双方聚集在一起,重新展开逃难行动。
当时是八月,正值东北的雨季,夜晚下起了滂沱大雨。
“苏联的军舰都守在松花江上。这孩子的哭声比铜锣还响,必须封住他的嘴才行!”
就在一行人来到松花江支流附近时,一名士兵如此说道。哥哥为了保护婴儿,背上遭士兵砍了一刀。这件事发生之后,关东军残党决定跟开拓团分道扬镳,提早半天渡河。说穿了,就是扔下不断发出婴儿哭声的开拓团一行人。
我们忍受着豪雨,等了半天的时间,直到旭日开始绽放光芒,为我们掩藏身影的夜色逐渐遭到晨曦驱赶,才站了起来,朝着松花江支流的岸边迈步。母亲扔下身上所有行李,将包扎了伤口的哥哥背在背上,我则跟在母亲的身旁,紧紧抓住了母亲所穿的雪袴。
因雨季而水量大增的河面,将大地切割成了两半。河的对岸笼罩在灰色的大雨及薄雾之中,朦朦胧胧看不清楚。气势惊人的波涛浊流不断冲刷着岸边的土石,将枯木及杂草卷入河中。关东军的残党们全都站在河岸边,不知如何是好,放眼望去根本不见苏联军舰的影子,看来那只是讹传而已。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将婴儿杀死。
看来只能等雨停了之后水势减弱再渡河——某人如此提议。但没过多久,远方传来了枪响及爆炸声。此外,还有强而有力的车辆引擎声及随之而来的大地颤动,那恐怕是战车吧。这次真的是苏联军队逼近了。
士兵们只好抱着横竖都是死的心情开始渡河。如今河面的浊流正激起阵阵漩涡,就算是卡车恐怕也会遭到吞噬。士兵们的身影一道道消失在大雨形成的幕帘及薄雾之中。就算士兵能勉强渡河,女人跟小孩又该如何是好?就在妇人们都望河兴叹的时候,竟有一名士兵走了回来。这个人正是当初企图杀死婴儿的士兵,他的身上绑着一条麻绳。
“我把绳子的另一头绑在对岸的树干上了,你们拉着这条绳子过河吧。”
关东军士兵早已全身湿透,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由于这一侧的岸上没有能够绑麻绳的大树,他只能像拔河一样奋力将麻绳拉撑。
一行人于是踏入了颜色如枯叶一般的混浊河水中。
母亲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哥哥。
“不用担心我。”脸上冒着汗珠的哥哥笑着说道,“有绳子,我可以拉着过河。妈妈,你背和久吧。”
哥哥那勉强挤出来的笑容,如今依然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当时他才七岁,只比我大了三岁,却抱持着保护弟弟的责任感。
母亲迟迟无法下决心,但她知道自己绝对没有体力来回两趟,而且年仅四岁的我不可能独自渡河,因为当我站在河底时,河面会淹过我的头顶。
母亲最后只能选择背着我过河。浊流不断以强大的力量朝我们推来,我感觉背后仿佛有只手要把我拉入水中。由于母亲的双手紧紧抓住了绳索,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攀附在母亲的背上。大浪一次又一次淹过我的头顶,我必须等浪潮过后努力将头探出水面呼吸。鼻孔一进水,脑袋里顿时变得一片空白。
就在隐约可看见对岸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哥哥松开了抓着麻绳的手,下一瞬间已遭浊流吞噬。
母亲尖叫一声“龙彦”,朝着哥哥消失的河面伸出手臂,却差一点连自己也被卷走,赶紧重新抓住了绳索。
倾盆大雨中,母亲一边哽咽一边渡过了河。来到河岸上时,她整个人瘫倒在地上,哀伤地凝视着滚滚河水。
这条河的下游似乎有个东北人的村子,沿着河往下游寻找实在是冒太大的风险。开拓团每个人都告诉母亲:“只能放弃了。”
一行人继续朝着东北方不断前进。
当我们来到了某个荒废的开拓团旧址时,我们全被送进了一间仓库,这间仓库如今被当成了难民收容所使用。
窗户玻璃早已破损,进入十月后,风雪不断从窗外灌入。此地冬季的气温,有时甚至低于零下三十摄氏度。每个人都只能将麻布袋的底部挖个圆洞,套在身上勉强抵御寒风。更可怕的是,这里蔓延着大肠黏膜炎、痢疾、感冒、肺炎、流行性斑疹伤寒等在当时的中国被合称为“伤寒病”的各种疾病。每当有人断气,活着的人身上就多了一点御寒的衣物。
收容所里永远弥漫着死亡与绝望的氛围。有一位妇人流着眼泪剪下死去的女儿的指甲,期盼在回归祖国后能为女儿盖座坟墓;另一位妇人的儿子生了病,却因为没钱买药,只好到中国人的店里恳求对方“收养这孩子”;还有一个男孩总是拿一顶钢盔在街上乞讨,那顶钢盔似乎是他父亲的遗物。
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则像子宫中的胎儿般蜷曲在地上整日昏睡,这些孩子的头上满是虱子,白得像是撒上了一层石灰。
我总是紧紧抱住母亲,躺在粟梗编成的草席上头。每天的食物只有少许高粱粥,除此之外,只能找些烤地瓜的皮、白菜的根、白萝卜的叶子等食物残渣来充饥。我们总是拿钢盔当锅子,或许是因为里头渗入了汗水的关系,煮出来的开水都是咸的。
由于泥土都已冻结,无法挖掘墓穴掩埋尸体,大家只能将一天比一天多的尸体胡乱堆叠在一起,在上头盖上一层雪了事。每天早上总是会出现啃咬死尸的野狗。我亲眼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一边歇斯底里地挥舞铲子,一边大喊“别吃我的孩子”,但赶走了野狗后,她还是挥舞个不停,直到数小时后断气为止。野狗围绕在尸堆周围的景象,如今依然清晰地残留在我的脑海里,自从失明之后,每当听见狗叫声,当时的可怕记忆就会宛如从坟墓里被挖了出来。
到了来年,我们才得以被送回日本。后来我看到报纸上的统计,死亡的八万名开拓团成员之中,有六万名是死于难民收容所。
当时每个日本人都拿到了一张用蓝墨水写在粗纸上的“退去证明书”。当看到遣返船时,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终于能回祖国了。通过港口的检疫关卡时,每个人都被撒上了大量除虱用的杀虫剂,全身白得像是拿了一整只麻布袋的太白粉倒在头上一样。但一想到这是回归日本的最后一道程序,大家就都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回国之后,我的眼前犹如蒙上了一层薄纱,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原因大概是收容所的生活条件太不卫生,以及营养失调吧。我到医院就诊,并且摄取正常标准的营养,视力渐渐有了改善;但疾病的种子,此时已潜藏在我的眼球之中。在接近四十岁的时候,我的视力开始快速恶化,到了四十一岁时终于完全失明。
说完了这一长串悲惨的经历后,夏帆语带哽咽:“好可怜——外公,原来你吃过那么多苦——”
回想起来,就像遣返船的船底破了个洞一样,自从搭上那艘船,我的人生便不断往下沉。
“是啊,外公吃过很多苦。”
“我是不是比那些人幸运得多?至少我还活着。”
“——幸不幸运没有必要跟别人比较。夏帆吃了多少苦,只有夏帆自己最清楚。”
“能够活着回到日本,对外公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日本刚战败时也有很多问题,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
“完全没办法玩游戏?”
“不,正因为每天都活得很辛苦,所以更加热衷于微不足道的游戏。”
“‘微不足道’?要怎么玩?”
“‘微不足道’不是游戏的名称,而是一点也不重要的意思。小陀螺、尪仔标、剑玉、抓鬼、跳绳——虽然娱乐不像现在那么多,但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大家都热心助人——”我苦笑着摇了摇头,“算了,别说这个了。一聊起过去的事,就会忍不住抱怨。每个人都必须活在当下,不能活在回忆之中。夏帆,外公并没有瞧不起现在这个你所生活的时代。”
身旁传来八音盒的童谣旋律。洗肾似乎终于结束了,我听见夏帆疲惫不堪地吁了口气,接着是护理师们匆忙来去的声音。夏帆似乎下床想要穿上拖鞋,却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好痛!妈妈,我的脚——我的脚抽筋了!”
我听见了由香里奔近的脚步声。
“对——就是那里——”夏帆重重叹了口气,说道,“每次洗完肾,都很容易抽筋,而且还会头痛——呜呜,好想吐——”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为她找到肾源呢?遗体肾脏移植的排队等候人数实在太多,希望相当渺茫。除非能找到愿意将肾捐给夏帆的六等亲之内的血亲——
倘若如今跟母亲在老家一起生活的哥哥是假货,那或许真正的哥哥还活在世界上的某处。只要能把他找出来,也许就能说服他捐出肾脏。我揭穿哥哥真面目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了。
一回到家,又收到了俳句信。这已经是第七封了。我用指腹读了上头横书的点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