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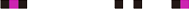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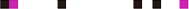

本章译自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部第二章。中译本所根据版本及页数如下: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pp.199—211; Economy and Society (ed.G. Roth & C. Wittich),pp.339—355;《共同体の经济的关系じついこの一般的考察》。本章正文初稿为黄国钟根据英译本所译,经康乐校改定稿。
大多数社会团体皆介入经济活动。与通常惯用(而不恰当)的说法相反的是,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目的性(zweckrationale)的行为皆为经济性的,以此,祈求精神幸福并非一经济行为,尽管它可能有一个依据某些宗教教义的明确目标。我们也不当将所有经济化的活动皆列入,不管是概念形成时的知识经济化,还是美学上的“手段之经济”,艺术的创造,就针对简化的不断更新的企图而言,经常是大为无利可图的结果。同样的,仅只固守“最适条件”之技术格言——以最少之花费取得相对而言最丰硕之成果——也很少被视为经济行为;毋宁视其为目的理性的技术。只有在下述情况时,我们才会道及经济行为,此即,需求的满足(依行动者之判断)乃仰赖相对而言 稀少 的资源及 有限的 、可能采取的行动,且仅在此一情境激起具体的反应时。当然,这个理性行动的决定要素,乃基于稀少系由 主观 认定,而该行动则针对其而发此一事实上。
此处我们不拟涉及任何枝节的“诡辩”及专门术语。不过,我们还得区分两种类型的经济行为。(一)满足个人任何可理解之需求,从食物一直到宗教启迪,如果是在财货及服务相对于需要量显得匮乏的情况下。使用“经济”一词时,我们通常习惯于只考虑日常所需——所谓物质需要。然而,祈祷与弥撒亦 可能 成为经济之对象,如果有资格主持这些仪式的人不够,且只有在付钱时才能得到的情况下,就像日常面包一样。常被认为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南非洲)布须曼人(Bushmen)的素描,并非经济对象,就经济意义而言,甚至连劳务产品都算不上,然而有些评价远为不如的艺术产品,仅因其相对地稀少,却可视为经济对象。(二)第二种经济行为则关系到控制及处分稀有财货,以求取利润。
社会行动(Soziales Handeln)有可能以多种形式而与经济发生联系
 。
。
理性控制之行动(Gesellschaftshandeln)有可能导向(依行动者观点)纯粹经济的结果——满足需求或追求利润。在此情况下,就会产生 “经济团体” 。然而理性控制的行动,也有可能借经济之运作以达成其他的目的。此一情况,我们即称之为“ 有经济 作用的团体 ”(wirtschaftende Gemeinschaft)。社会行动是有可能包含经济及非经济的目标,否则上述情况即不致出现,具有主要经济利益之团体与以经济为次要利益之团体间的分界线并不清楚。严格说来,第一种情况仅出现在利用匮乏此一条件以图利的团体,亦即营利之企业,因为只有在供求关系紧张而有需要时,所有团体才会采取经济行动以解决满足需求的问题。准此,家庭、慈善基金、军事行政、开发森林或狩猎的合作团体,其经济活动并无区别。当然,在社会行动间似乎是有区别的,有些行动之所以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满足经济的需求,例如开发森林,而有些具有目的的行动(例如军事训练)之所以有采取经济行为的必要,则仅仅是由于匮乏的因素。不过,实质上此一区别微不足道,且仅在无任何匮乏而社会行动仍然不变的情况下,始能清楚厘定。
由社会行动所构成的一个不具有主要或次要经济利益的团体,也有可能在许多方面受到匮乏因素的影响,而在此一程度内,受经济所制约。反过来说,此等行动亦可能决定经济行为的本质及过程。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影响皆交互发生作用。无关乎上述两种团体的社会行动亦非罕见。一起散步即为一例。经济上无甚重要性的团体亦甚平常。不管怎么说,下述这种与经济有关而又为特殊例子的团体,我们称之为“经济统制团体”(wirtschaftsregulierende Gemeinshaften):团体的规范节制着所有参与者的经济行为,然其组织并未经由直接介入、具体指示(或禁止)而持续性地指导经济活动。这类团体包括了所有的政治团体、许多宗教团体以及其他许多的团体,例如为了经济规范而特别组成的渔民或农民合作社。
如前所述,完全不受经济性制约的团体极为罕见。虽然如此,经济影响的程度却也大有差异,毕竟,社会行动所受到的经济决定是暧昧不明的——适与所谓历史唯物论之假设相反。经济分析中应视为常数的现象,尽管(从社会学观点言之)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包含有这些现象(或与之共存)的团体间,通常还是可相容的,不管这些团体是以经济为主或为次。认为社会结构与经济有“功能性”相关联的意见,也还有所偏颇,就算假定有一明确相互依存的关系,此一观点亦不宜视为历史通则。盖社会行动之形式乃遵循“自身之法则”,这点我们不断会看到,就算不管此一事实,这些形式也还是有可能(在一特定情况下)永远受经济以外之其他因素所共同制约。虽然如此,对于几乎所有的社会团体,至少是那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团体,经济制约有时在因果关系上似乎的确有其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的,反过来说,经济通常也会受到其所置身之社会行动的自律性结构的影响。此种情况何时及如何发生,无法归纳出有意义的通则来。不过,社会行动的具体结构与经济组织的具体形式间,其选择性亲和力的程度则可归纳之,换言之,我们可以用一般性的词汇来叙述其彼此之间,究竟是互益、互阻或互斥——究竟其彼此“相配”与否。我们此后得经常检讨此种配合的关系。再者,至少我们可以归纳出经济利益促成某种社会行动的方式。
常见的一个经济决定因素乃是为生计的竞争——官职、顾客及其他的赚钱机会。当相对于利润幅度的竞争者数目增加时,参与者会有意缩小竞争。通常一群竞争者会以其他(实际或潜在的)竞争者外在可见之特征——种族、语言、宗教、地方或社会性出身、血统、住区等——作为排斥的借口。在个案中究竟选择何种特征并不重要,最容易达成的即可,此种集体行动可能会激发受制团体的相对反应。
尽管内部竞争持续,但是共同行动的竞争者如今形成对外的“利益团体”,设立某种具有合理规则的组合的趋势,亦有增长的现象;假如独占利益继续存在,竞争者或他们所能影响的团体(例如政治团体)即会借由正式的垄断建立起限制竞争的法律秩序;从此,某些人士即充任保护独占的“机构”,必要时并得使用强制方式。在此情况下,该利益团体即发展为“ 法制性 特权团体 ”(Rechtsgemeinschaft),而参与者则成为“特权成员”(Rechtsgenossen)。此种封闭——如我们通常称呼者——是周而复始的,它是土地财产以及所有行会与其他集体垄断的起源。
朝向垄断特定的、且通常为经济性的机会的趋势,一直是下列情况的驱动力,“合作组织”总是意味着封闭的独占团体,例如在某渔区注册的渔夫、工程师校友会的成立,以确保法律上——或至少实际上——对某些职位的独占
 ;排斥外人,不让他们分享村落的田地及公有土地;商店职员之“爱国”组织
;排斥外人,不让他们分享村落的田地及公有土地;商店职员之“爱国”组织
 ;某一地区的“家士”(ministeriales)、骑士、大学毕业生及工匠,可转任文职之退伍军人——所有这些团体首先只采取某些共同行动(Gemeinschaftshandeln),稍后则干脆组织社团。此种垄断乃直接针对那些具有某种正面或负面特征的竞争者而来,其目的则不外乎封锁外人的社会与经济机会。其程度可有极大变化,尤以团体成员分享独占利益的配额时为然。这些独占利益对所有持有独占权者可能仍然维持开放,他们因此得以自由竞争,拥有职业专利权者可为明证(够格担任某些职位的毕业生,有特权挑选顾客及雇用学徒的职工师父)。然而,这种机会也有可能对
圈内人
封闭,方法甚多:(a)职位轮替:官职俸禄持有者任期短暂即有此一目的;(b)授予得撤销,如在一严密组织的农村共同体中(例如俄国的密尔),个人对土地的支配;(c)终身授予,例如成为规则的所有俸禄、官职,职工师父的独占权,使用公地的权利,以及早期大多数村落共同体皆有的分配田地的权利;(d)〔利益团体的〕成员及其继承人有可能得到固定的赠与,条件是这些赠与不得给予他人,要不然也只能给予团体成员:西洋上古之武士俸禄,“家士”之服务采邑,以及世袭职位或行业之垄断,皆为明证;(e)最后,股份之数额得加以限制,不过持有者得自由处分其股份而无须通知其他成员或得到他们允许,例如持股公司。这些不同的内部封闭的阶段,得称之为该团体对其所独占之社会与经济机会所
占有
的阶段。
;某一地区的“家士”(ministeriales)、骑士、大学毕业生及工匠,可转任文职之退伍军人——所有这些团体首先只采取某些共同行动(Gemeinschaftshandeln),稍后则干脆组织社团。此种垄断乃直接针对那些具有某种正面或负面特征的竞争者而来,其目的则不外乎封锁外人的社会与经济机会。其程度可有极大变化,尤以团体成员分享独占利益的配额时为然。这些独占利益对所有持有独占权者可能仍然维持开放,他们因此得以自由竞争,拥有职业专利权者可为明证(够格担任某些职位的毕业生,有特权挑选顾客及雇用学徒的职工师父)。然而,这种机会也有可能对
圈内人
封闭,方法甚多:(a)职位轮替:官职俸禄持有者任期短暂即有此一目的;(b)授予得撤销,如在一严密组织的农村共同体中(例如俄国的密尔),个人对土地的支配;(c)终身授予,例如成为规则的所有俸禄、官职,职工师父的独占权,使用公地的权利,以及早期大多数村落共同体皆有的分配田地的权利;(d)〔利益团体的〕成员及其继承人有可能得到固定的赠与,条件是这些赠与不得给予他人,要不然也只能给予团体成员:西洋上古之武士俸禄,“家士”之服务采邑,以及世袭职位或行业之垄断,皆为明证;(e)最后,股份之数额得加以限制,不过持有者得自由处分其股份而无须通知其他成员或得到他们允许,例如持股公司。这些不同的内部封闭的阶段,得称之为该团体对其所独占之社会与经济机会所
占有
的阶段。
假使所占有的独占机会开放给团体之外交易,则成为完全“自由”的财产,原有的垄断团体即告瓦解,其残余为处分之拨付权力,出现在市场上则为个人的“获得的权利”。因为一切自然资源的财产,历史上之发展皆来自团体成员独占性股份之逐步占有。与目前不同的是,〔在过去〕不但具体的财物,各种各样的社会与经济机会也是占有的对象。当然,占有的方式、程度及难易,依对象与机会的技术性质而有极大差异,可能适合于占有的程度亦大为不同。譬如说,赖耕种一块田地为生(或由此取得其收入)的人,是被束缚于一具体且清楚可见的物质对象,而顾客则不然。对象仅借改良即可产生收获此一事实,并不能导致占有,因为在某个程度内,这实在是使用者劳力的产物,对于受束缚的“佣客”更是如此,虽然其方式不同,然而顾客就不像不动产那么容易“登记”。占有的程度系基于对象间的此种不同显然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如此,此处我们要强调的是,纵然占有的途径有别,两者之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垄断的社会与经济的机会有时甚至对圈内人都是“封闭的”。因此,各团体在有关对外或对内的“开放”或“封闭”上,程度有所不同。
当团体是由具备共同特质的人所组成,而此特质又是经由抚育、传授与训练才能 获得 时,这种垄断的倾向会呈现特殊的形式。这些特征可能是够资格从事某些经济活动,担任同样或相似的职位,骑士或苦行的生活方式,等等,假若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社会行动而导致组织出现,则此一组织极可能成为“行会”。具备完整资格的成员,借独占精神、知识、社会与经济之财物、职责与职位而取得“职业”(Beruf)。只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才得以不受限制地从事该项职业:(一)接受完整的修行而得到适当训练者;(二)证明其资格者;(三)有时得经历待用期且符合其他要求者。从少年同学会、骑士组织、职工行会,一直到近代官员及雇员所需资格,各团体之发展常循一典型之模式。诚然,在各处希望有效执行能得到保证的倾向,或许皆有其重要性,尽管彼此间的竞争仍可能持续,参与者可能为了精神或物质的因素而需要此种保证:地方工匠为其商誉,属于某一组织的“家士”及骑士为了其专业声望及本身的军事保障,禁欲团体则恐惧鬼神可能会因其错误的操作而迁怒于所有的成员(例如,几乎在所有的原始部落中,凡是在祭典舞蹈时唱错歌者,早期皆被处死以赎罪) [3] 。不过,对于有效执行的这种关切,较之于设法限制某一具有荣誉与俸禄之职位的候选人的兴趣而言,通常还是得屈居其下。见习期、待用期、杰作及其他要求——特别是团体成员昂贵的娱乐活动——比起专业资格考试,经常是更经济的〔阻挡〕方式。
这种垄断的倾向及类似的经济考虑,在 妨碍 团体的扩张上,经常扮演重要角色。例如,雅典的民主制逐渐设法限制能够享受公民权者的人数,因此也限制了其自身的政治扩张。教友派之传道,也因经济利益最根本上相类似的安排,而陷于停顿。伊斯兰教传教之热诚,最初原本是宗教义务,最后也因身为征服者的伊斯兰教武士希望能有一些非伊斯兰教徒——因此也就没有特权——的人口,以便能供养享有特权的信徒而受到限制。这是许多类似现象的一个典型。
另一方面,个人以代表团体利益维生,或以其他方式在意识形态或经济上依赖团体的存在以维生的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因此社会行动可以经由宣传、保存而转化为一个组织,虽然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该发生的。此种兴趣可能有最歧义的知识根源:十九世纪之浪漫主义观念论者及其追随者唤醒无数属于“有利害关系”之民族的、衰微的语言团体,使其致力于发扬自己的语言。德国的高中及大学的教师曾帮忙拯救微小的斯拉夫语系团体,并感到知识上有必要写书来讨论这些团体。
然而,如此纯粹观念性团体的存在,其杠杆作用显然不若经济利益来得有效。如果团体聘请某人担任其共同利益的长期性且计划性的“机构”,或者此一利益代表可从其他地方获酬,则组织成立,且能强力保证在所有情况下协同行动之持续。准此,某些人职业上对保留旧会员、招募新会员感到有兴趣。他们是否接受报酬以代表(隐藏性或赤裸裸的)性别的利益 [4] 、其他“非物质性”或最后是经济性的利益(工会、管理协会及类似组织),他们是否计件论酬或支薪秘书式的公开代言人,在此皆不重要。间歇及不合理的行动样式,为制度化之理性“经营”(Betrieb)所取代,而且在参与者为其理想所鼓舞起来的当初的热情都早已消失之后,仍能运作。
“资本家”的利益本身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在鼓动某些特定的社会行动上发生利害关系。例如,德意志帝国时,德文“哥德”式铅字版的所有人,就想要保留这种代表“爱国”的字母,〔而不肯用拉丁的字体〕;同样的,旅馆主人允许社会民主党的聚会,虽然他们的前提——不让军事机关人员进入——还得看党员规模大小而定。类似这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大家都可想到很多例子。
不管我们处理的是雇工或资本家雇主,所有此类经济利益之个案,有一共同特征:实质共同理想之利益,必然屈居于维持团体持续或扩张的利益之下,不管其行动的内容为何。最引人注意的例子厥为美国政党意识形态内涵的消失,但最重要的例子乃是长久以来资本家的利益与政治共同体扩张之间的联系。一方面,这些共同体可对经济发挥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它们又能攫取巨额收益,因此资本家可从它们取得最多利润,直接方面如给付有偿劳务,或在预期收益的条件下先为垫款,间接方面如经由剥削政治共同体领域内的对象。西洋古代及近代时期开端,资本家利得的焦点,集中于此种政治性制约的“帝国主义式”利润,今日资本家的营利亦日渐往此方向迈进。一个国家权力领域的各方拓展,增加了资本家相关利益的潜在机会。
有利于团体扩张的这些经济利益,(可能)不但会受上述垄断倾向的阻挠,同时也会受到由于团体的封闭及排他性而得到的其他经济利益的阻挠。我们已概略陈述过,通常自愿性团体容易超越其理性的首要目标,而在各异其志的参与者间建立起关系:结果是,一个包含性的共同体关系(übergreifende Vergemeinschaftung)会附着于结合体关系(Vergesellschaftung)之上
 。此一说法当然亦非永远为真,它仅发生在假定社会行动具有某些个人——而非仅业务——的接触上。例如,个人可获得股份而与其本人资格无关,仅须靠经济性的交易,而且通常无须通知其他股东或得到他们同意。类似之方针,通行于那些靠纯粹形成条件或成就来决定其成员资格——而非考验个人本身——的社团。此一现象常出现于某些纯粹经济性团体,以及某些自愿性的政治团体,一般而言,不论在哪儿,此一方针愈为可行,则团体的目标愈为理性及特定。然而,有许多团体则明示或暗喻加入系基于资格,包含性的共同体关系即告出现。此种情况尤其发生于成员入会许可系之于对候选人个人之才能的调查与许可时。至少一般而言,候选人不但得就其是否对组织有用一点接受考察,而且也必须就其他成员所珍视的个人资质之“存在”与否接受考察。
。此一说法当然亦非永远为真,它仅发生在假定社会行动具有某些个人——而非仅业务——的接触上。例如,个人可获得股份而与其本人资格无关,仅须靠经济性的交易,而且通常无须通知其他股东或得到他们同意。类似之方针,通行于那些靠纯粹形成条件或成就来决定其成员资格——而非考验个人本身——的社团。此一现象常出现于某些纯粹经济性团体,以及某些自愿性的政治团体,一般而言,不论在哪儿,此一方针愈为可行,则团体的目标愈为理性及特定。然而,有许多团体则明示或暗喻加入系基于资格,包含性的共同体关系即告出现。此种情况尤其发生于成员入会许可系之于对候选人个人之才能的调查与许可时。至少一般而言,候选人不但得就其是否对组织有用一点接受考察,而且也必须就其他成员所珍视的个人资质之“存在”与否接受考察。
此处我们无法依照排他性的程度来划分各种不同的社团。可确定的是,此种选择存在于各式各样的社团中。不仅是宗教教派,而且社交联谊会,如退伍军人协会甚至保龄球俱乐部,通常这些团体会拒绝任何受到团体成员反对的人加入。这个事实对于“正当化”新进成员的重要性,远超过对团体目标而言非常紧要的才能。会员资格对他所能提供的有利关系,也同样远超过组织的特定目标。因此,常见到有一些人虽然对组织的目标并不真正感兴趣,他们还是会加入该组织,只因为会员资格所能带来的、那些具有经济价值的正当性与各种关系。就此动机本身而言,或许含有强烈诱因可促使人加入,因之而扩大团体。然而由于成员有意垄断那些好处,并想借限制〔可能得到好处的人〕于最小的范围以扩大其经济价值,而导致相反效果。圈圈愈小且愈排外,会员资格的经济价值及社会声望愈高。
最后,我们必须简单讨论另一种经常存在于经济与团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意地提供经济利益,以维持并扩大基本上为非经济性的团体。当几个相近似的团体互相争取成员时,此一情况尤其常见:政党及宗教共同体可为明证。例如,美国的教派安排艺术、体育及其他娱乐,并降低离婚者再婚的条件,结婚标准之无止境地降低一事,直到最近才因正常的联合运作而扼制住。除安排郊游及类似的小型活动外,宗教及政治团体成立青年会与妇女会,并热切参与纯粹社区或其他基本上非政治性的活动,这些活动使得他们可以施经济恩惠予地方上的私人利益。在极大程度上,这些团体对自治性、合作性或其他机构的入侵,实有直接的经济动机,借着职位俸禄及社会地位,它可帮助这些团体维持其职员,并将运作费用转嫁至这些机构。适合此一目的的是自治市镇、生产者及消费者合作社,医疗保险基金,工会及类似组织的职位,更大范围的话,当然可以算上政府职位及俸禄,其他有地位或有给付的职位——所有可以从政治权威取得的,包括教授一职在内。在一个议会政府的制度中,一个团体如果够强大,即可为其领导人及成员筹得此种支持,就像政党一样。对政党,这可是必要的。
此处我们只想强调一个普通的事实,非经济性团体也同样成立经济性组织,特别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许多宗教团体的慈善活动有此目的,基督教、自由党、社会党、爱国工会、互助基金、储蓄及保险机构以及(更大规模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社,更是如此。例如,某些意大利的合作组织,在雇用工人之前,要求其提供表白信仰的证书。1918 年以前的德国波兰人以非比寻常、令人注目的方式筹组信用贷款、抵押付款及农地购买;1905—1906年的俄国革命时,许多俄国政党立刻遵循类似的现代政策。有时成立商业企业:银行、旅馆(如社会党在奥斯腾德[Ostende]的“人民旅社”),甚至工厂(比利时也有)。当此现象发生时,政治共同体内的支配团体,特别是文官系统,亦采取类似手段以便继续掌权,从筹组经济上有利可图的“爱国”组织及行动,到国家控制的贷款(如普鲁士银行),无所不为。至于有关此种宣传方式的技术枝节问题,此处不拟深论。
此节我们只想概括性地叙述,并以某些典型的例子阐明,在不同的团体内部扩张与垄断的经济利益既共存而又相对立的现象。我们必须放弃深究细节,盖此举非对各种团体进行研究不可。代之则为对存在于团体行动与经济之间最常见的关系,作一概要性讨论:事实上,为数极多的团体皆有附带的经济利益。通常这些团体必已发展出某种合理性的组织,只有自家计发展出来的,才有例外情况。
社会行动转变成理性组织后,如果需要财货或劳务以供运作,则得有一个确定的满足需求的秩序。基本上,获得这些财货与劳务的方式有五种典型——此处我们尽可能举政治团体为例,因为它们的处理方法是最成熟的:
(一)集体式自然经济的
庄宅
(Oikos)型
 。团体成员必须付出固定的个人劳力,这种劳务可能是全体平等的,例如普遍性地征调所有强壮适任的男人服兵役,或者特殊性的如征调工匠(Ökonomie-Handwerker);再者,他们也必须缴纳固定配额的实物贡纳,以供应君主餐桌或军事当局的需要。因此,这些财货及劳务并非为市场而生产,而是为了团体的集体经济(例如,自给自足的庄园或皇室家计——“庄宅”的纯粹类型——或完全依赖劳务与实物供给的军事当局,如古埃及)。
。团体成员必须付出固定的个人劳力,这种劳务可能是全体平等的,例如普遍性地征调所有强壮适任的男人服兵役,或者特殊性的如征调工匠(Ökonomie-Handwerker);再者,他们也必须缴纳固定配额的实物贡纳,以供应君主餐桌或军事当局的需要。因此,这些财货及劳务并非为市场而生产,而是为了团体的集体经济(例如,自给自足的庄园或皇室家计——“庄宅”的纯粹类型——或完全依赖劳务与实物供给的军事当局,如古埃及)。
(二) 市场导向的贡纳 ,使团体得以提供购置设备、雇用工人、官员及佣兵等需求,贡纳可以是强制税、定期规费或某种场合之规费,也可能来自成员入会时的贡献,不过这个成员可以(a)从某些好处或机会(例如地籍管理处或其他机构),或者物质的设施(如道路)而获利——所采取的原则是给予劳务的补偿:技术意味之规费;个人也可能被征取贡献,只要他(b)恰好在团体的权力范围内(例如从土著居民征取贡纳,抽取从此团体领土通过的人及货物的规费)。
(三) 营利经济型 :企业销售其产品与服务,并将其利润交给所属的团体。此种企业可以不是正式独占的,如普鲁士的“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与“大酒厂”(Grande Chartreuse),也可以是(过去与现在常有的)独占形态,如邮局。显然上述这三种概念上最为一贯的类型间,各种的结合方式皆有可能。货币可以取代实物给付,自然产物得售于市场,资本财可直接取之于实物给付,或以摊派方式取得。通常这三种类型的主要部分皆彼此混合。
(四) 赞助型 (mäzenatisch):有些人对某团体有物质或理想上的利益,并且力能负担,因此自愿捐助之,至于此人在捐助人外是否为此团体成员则无关紧要。(就宗教与政治团体的例子而言,标准形式是宗教献金及大赞助者的政治献金。此外,托钵修道会及早期历史上对王侯的“乐捐”亦可算上。)此种类型并无固定的规则与义务,捐献与其他形式的参与也没有必然的关系——赞助者可以完全置身于团体之外。
(五)
特权化的负担分配
:(a)优势特权的负担分配。当某种经济或社会的垄断受到保障,或相反的,当某些特权身份团体或垄断式团体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负担时,即出现优势特权类型。准此,捐献与劳务并非根据一般通则来要求,亦即并非依照不同的财产及收入的阶层或——至少在原则上——按照可知的财产与职业来要求;反之,捐献与劳务是根据大共同体赋予某人或某团体的具体的经济、政治权力与垄断权而决定的,例如领主庄园、税捐优惠、行会或某些身份团体的特别捐献。要点是这些〔捐献与劳务〕的征取是与保障(或占有)特权相关联的,或者作为给予这些特权的补偿,以致满足需求的方式,由于对团体各个阶层关闭了社会与经济的机会,造成了(或稳定了)团体垄断的分化。一个重要的特殊个案即为,许多不同形式的封建或家产制政权管理机构,由于其占有特权的权力地位,因此可以提供一致行动所必要的〔需求〕数额。例如在身份制国家里(Ständestaat),君侯必须从自己家产制财产中提供政府所需费用
 ;同样的,政治或家产制权力与身份的拥有者,如封臣、家士等,也必须运用自己的资源。此种满足需求的方式经常涉及实物贡献。然而在资本主义情况下,类似现象亦可能发生:政府当局可以用某种方式授予某企业团体独占权,然后再要求它直接(或经由税收)提供捐献。此一方法在重商主义时代甚为风行,现在也再度得势——德国之酒税即为一例
;同样的,政治或家产制权力与身份的拥有者,如封臣、家士等,也必须运用自己的资源。此种满足需求的方式经常涉及实物贡献。然而在资本主义情况下,类似现象亦可能发生:政府当局可以用某种方式授予某企业团体独占权,然后再要求它直接(或经由税收)提供捐献。此一方法在重商主义时代甚为风行,现在也再度得势——德国之酒税即为一例
 。
。
(b)劣势特权的负担分配。经由劣势特权以满足需求的方式,称为
赋役制
(Liturgie)
 :如果经济上巨大的义务紧紧联系于某种水准的财产上,而这些财产所有者并未拥有任何独占的特权,最多只能轮流负担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阶级赋役制”。雅典的trierarchoi
[5]
与chorego
[6]
,以及大希腊化时代国家的强制义务性之包税者皆为其例。如果义务是以此种方式附着于独占团体,使得团体成员无法单方面退出,而仍然存在着满足更大政治单位需求的连带责任,我们称之为“身份赋役制”。古埃及与西洋上古的强制义务性行会;俄国农民世袭性地依附于村落(对税收有连带责任);通贯整个历史(其移动性的限制或松或紧)的“部曲”与农民,他们也有付税的连带责任以及(可能)提供劳役;古罗马的“市镇议员”(decuriones)
[7]
,他们负责收取税捐,因此也集体负责,以上皆为明证。
:如果经济上巨大的义务紧紧联系于某种水准的财产上,而这些财产所有者并未拥有任何独占的特权,最多只能轮流负担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阶级赋役制”。雅典的trierarchoi
[5]
与chorego
[6]
,以及大希腊化时代国家的强制义务性之包税者皆为其例。如果义务是以此种方式附着于独占团体,使得团体成员无法单方面退出,而仍然存在着满足更大政治单位需求的连带责任,我们称之为“身份赋役制”。古埃及与西洋上古的强制义务性行会;俄国农民世袭性地依附于村落(对税收有连带责任);通贯整个历史(其移动性的限制或松或紧)的“部曲”与农民,他们也有付税的连带责任以及(可能)提供劳役;古罗马的“市镇议员”(decuriones)
[7]
,他们负责收取税捐,因此也集体负责,以上皆为明证。
通常,最后第五型之满足需求的方式,基本上限于强制性团体,尤其是政治团体。
满足需求的方式之所以多样化,永远是不同利益间斗争的结果,通常会产生超越其直接目的的深远影响,而可能导致相当程度的“经济统制的”秩序;尤以赋役式的需求满足为然。纵非直接如此,这些多样的满足需求的模式也可能强烈影响经济的发展与方向。例如,身份赋役制极有助于社会与经济机会的“闭锁”、身份团体的稳定及由此而消除私人资本的形成。抑有进者,若一个政治共同体依赖公营企业或营利经济以满足其需求,私人的营利经济亦不易出现,独占性的满足需求方式也同样影响私人资本主义,但也有可能既刺激同时又妨碍私人资本的形成,端视政府支持的独占的个别性质而定。西洋古代的资本主义奄奄一息,因为罗马帝国逐渐恢复到身份赋役制以及(部分)公营事业的满足需求方式。目前,自治区或国家经营的资本主义式企业,部分地重新导向(同时也部分地取代了)私人资本主义:德国证券交易所自从铁路国有后,即不再报价铁路股票,此点不但对其地位,并且对财产形成的性质皆甚为重要 [8] 。若独占事业由国家保障,并获补贴(如德国的酒税),则私人资本主义受到压抑(如,私人酿酒厂之成长)。反之,在中古及近代早期,贸易及殖民的垄断最初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只有垄断可以提供给资本主义企业足够的利润幅度。但其后于十七世纪之英国,这些垄断妨碍了资本家的利益,招来甚多激烈抨击而终至崩溃。因此,奠基于税捐的垄断,其影响常是双关的。虽然如此,以税捐及市场方式来满足需求显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极端的情况例如尽可能地利用开放性市场以应付行政需要,甚至连军队的招募及训练皆由私人企业家包办,至于资源则借税收取得。要这样做的话,其前提自然是得有一个完全成熟的货币经济,以及一个极端理性及有效率的管理机构:官僚体系。
当考虑到个人“动”产课税的问题——不管在何处都是个难题,特别在民主体制下——此一前提尤为要紧。此处我们得稍微探讨这些难题,盖其深切影响到近代资本主义之兴起。就算在无产阶级取得支配的地方,只要有产者可自由离开共同体,个人动产的课税就会受到限制。流动的程度,不但取决于有产者在此特定共同体中成员地位的相对重要性,而且也取决于财产的性质。在强制性组织中,特别是政治共同体,财产的利用主要是依赖不动产者,其性质是静态的,有别于货币或容易交换的个人动产。如果有产者家庭离开一个共同体,留在原地的就必须支付更多的税捐;而在一个依赖市场经济的共同体,特别是劳力市场,无产者可能会发现,有产者的离去会导致他们经济机会的大量萎缩,因此不得不放弃任何鲁莽地向有产者征税的企图,甚至还得格外向其示惠。此一情况是否真会发生,系于该共同体之经济结构而定。在民主制的雅典,对于有产者课税的诱因,要超过上述之考虑,盖雅典城邦主要是依赖其附庸的贡纳,并且在其经济体系内,(现代意义上的)劳力市场也还未发展到能决定大众的阶级状况的程度。
在近代的状况下,则通常恰好相反。今日无产者掌权之共同体,通常对有产者皆极为谨慎。社会主义者控制的市镇,如卡塔尼亚市(Catania),以大量的优惠税率招徕工厂,盖社会主义之大众对更佳之工作机会及直接改良其阶级处境的兴趣,超过对“公道地”分配财富及“公平地”征税的兴趣。同理,尽管在某个个案中有利益冲突,地主、建地投机者、掮客及工匠,倾向于优先考虑他们切身的、阶级制约的利益;因此,在所有类型的共同体中,各种形态的“重商主义”皆为惯见现象,尽管其间有甚大差异。那些关切自身在共同体内相对的权力地位的人,也希望能维持税基及那些可以供给他们贷款的大量财富,使得上述现象益发如此;因此,他们被迫审慎处理个人财产。准此,纵使在无产者掌权之处, 如果 有许多共同体彼此竞争,使得有产者可选择其住所的话,则个人财产可以期望享有“重商主义”之特权,或者至少可以免除赋役及税捐。美国即为一例,各州之分离主义,导致所有想认真结合消费者利益之企图皆归于失败;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市镇而言,上述论断稍有限制,不过也还适用;最后,各个独立国自身亦然。
至于分配负担的方式,当然主要得取决于共同体内各个不同团体之相对权力地位,以及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实物满足需求愈增长,愈导向赋役制。因此,在埃及,赋役制度起自法老时代,而仿自埃及的晚期罗马赋役制国家,则是因为征服的内陆地区主要皆为自然经济体系,以及资本家阶层的相对式微;而这些阶层之失去其重要性,乃在于罗马帝国的政治与管理的转变,消除了包税者及资本家利用高利贷对附庸民的剥削
 。
。
如果个人“动”产占支配地位,则不管何处的有产者都会解除加于自身的赋役式满足需求的负担,并将税赋转嫁给一般大众。在罗马,兵役曾经是依照财产而划分的赋役制,有产公民且得自备武器;然而,接着是骑士阶层免除了兵役,而由国家装备的无产阶级军队取代,他处则代之以佣兵,至于其费用则来自一般大众的税捐。中世纪时,各处皆以付利息的贷款、土地抵押、关税及其他摊派来满足特殊的公共需求,而不再用征收财产税以及无息的强制性贷款——亦即有产者的赋役义务——来解决;因此,有产者利用推动公共需求,来谋取利润及定期收入。有时这些措施几乎使得城市的管理机构及税收制度,沦为债权人之工具,热那亚有一段时期就是这样。
最后,在近代初期,卷入权力斗争的各国,由于政治原因及货币经济的扩大,需要更多的资金。结果则导致新兴国家与受仰慕且具特权的资本家力量之间可资追忆的结盟。这是创造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将此一时代之政策名为“重商主义”,可说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在古代及近代,当几个政治共同体借扩大税基及促进资本形成(为了得到私人贷款)的方式彼此竞争时,作为保护个人“动”产的“重商主义”同样存在,此一用语仍然正确。在近代史初期的“重商主义”之所以有特殊的性格及影响,有两个原因:(一)互相竞争的国家及其经济的政治结构,此点容后再述,以及(二)逐渐出现的近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新奇结构,是不见于西洋古代的,而且最后还大大得力于国家的保护。无论如何,从那时起,欧洲庞大的、大致相等的与纯政治性的结构之间的竞争性斗争,有其全球性的影响。众所周知,此一政治竞争仍然是资本制度保护主义的最重要动机之一,保护主义出现于当时,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延续着。不了解这段奇特的政治竞争,以及在过去五百年来存在于欧洲各国间的“均势”(兰克在其第一部作品中认为此一现象乃是这个时代具有世界史性的特点),我们即无法了解现代国家的贸易及金融政策——最与现代经济制度核心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 [9] 。
[1] cf. M. Weber, Ges.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 1. Bd., S.4.——德注参照《宗教与世界》,p.452。——中注
[2] K. Bücher,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 I. Bd., 16. Aufl., Tübingen, 1922; E.Durkheim,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 Paris, 1893, 4.Aufl., 1922.
[3] 韦伯于《经济与社会》第六章第八节提及此事,认为是美洲印第安人习俗。菲朔夫(Fischoff)在译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时,将之译为“印度”。但是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认为此一习俗乃来自波利尼西亚,参见 The Tree of Culture ,New York, 1955,p.192。——英注
[4] 韦伯此处提到的可能是当时的事件:亦即鼓吹自由恋爱与私生子权利的女性宣传者,还有主张“性共产主义”的弗洛伊德派精神病学者,都出现在海德堡并激怒了韦伯。不过,韦伯绝非反女性主义者。当他的妻子 1910 年在海德堡组织“德国妇联会”(Bund deutscher Frauenvereine)会议时,一个教授在报纸为文抨击此会议为老处女、寡妇、犹太女人及不孕妇女之大杂烩,最后一类显然是把韦伯之妻都骂进去了。韦伯替他的妻子写公开答辩,不过这又导致人家批评他只会躲在妻子背后,却不敢挺身为其战斗。结果是另一场官司。此外,韦伯亦曾帮助他的第一位博士班女学生艾尔泽·冯·里希特霍芬(Else von Richthofen)成为巴登邦的第一位女性工厂监督,该学生之妹妹即为D. H. 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作者)的妻子。见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 pp.429—430。——英注
[5] trierarchy是古代雅典人为了建立海军的一种制度。为了建造三层桨的战舰(trireme),雅典人从公元前五世纪初开始,每年自富裕的市民中挑选若干人,责成他们建造战舰,招募桨手,并负担此一战舰的一切开销,包括桨手的费用、修补费用等,出钱的人即成为此一战舰的“司令官”(trierarch),而此一制度即称为“trierarchy”,于公元前四世纪末废止。参见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 p.1094。——中注
[6] choregia也是古雅典人为了提供酒神节的娱乐节目而推行的制度。为了提供祭典所需的合唱团、悲剧与喜剧节目的演出,自公元前五世纪开始,每年自富裕的市民中挑选若干人,责成他们负担一切的开销。参见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 pp.230—231。——中注
[7] decuriones指古罗马时期地方自治市镇的“议员”。各自治市镇依其大小选出若干名额的终身制议员,选取的标准相当严格,主要皆来自当地富有的望族。他们的权力相当大,例如协助当地首长(magistrate)处理公务,负责与中央或省区总督交涉,因此实际上控制了当地社区的一切公共事务。此外,他们也负责税收,不足时并须负责补足(这就是为何需要富人充任的缘故)。早期罗马帝国强盛时,各自治市镇皆相当繁荣,出任“议员”是相当荣耀之事,等到帝国晚期,内乱外患频仍,人民负担过重,不得不流亡他乡,赋役的短缺日形严重,“议员”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最后罗马皇帝索性下令“议员”世袭,以便能巩固政府赋役的来源,“议员”一职遂由荣誉变为义务,从一个统治阶级降为负责税收的阶级,自治市镇的制度亦告崩溃。参见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 p.318。——中注
[8] 到 1875 年止,迅速发展的德国铁路,还有一半控制在私人手中。铁路股票一直到 1873年大崩溃为止,也始终是投机的主要对象。普鲁士自 1847 年开始筑铁路,到了 1878 年后即考虑大规模收归国有。不过,国有化的主要考虑,与其说是为了防止股票投机,毋宁说是为了军事目的。参见Gustav Stolper, German Economy: 1870—1940 , New York,1940,p.725。——英注
[9] Leopold von Ranke, 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1494—1514 , London,1909.——英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