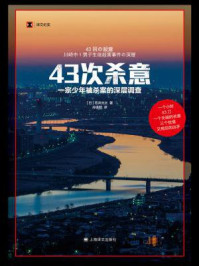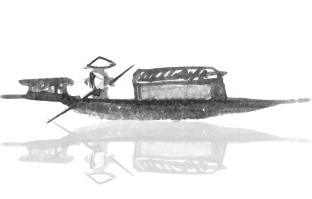
这得从北宋有名的“乌台诗案”谈起,这是一桩中国文化史上相当著名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又称“眉山诗案”,当事者苏轼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和文坛领袖,他因诗祸而被捕入狱,对他本人及其周围的文人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仿佛是无端飞来的横祸,然而从当时的客观社会政治环境和苏轼本人主观方面的因素来看,这“诗祸”的产生又有它的必然性。
事件的起因是苏轼反对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苏轼与王安石同为宋代著名的散文大家,又一同受知于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中坚。两人在文学创作方面是同道,有文字之交,私下的情谊也不错,而且在政治上也都具有忧国忧民的儒者襟怀和强烈的议政参政意识。他们对表面承平的社会背后所隐藏着的财政危机、政治危机和边务松懈等弊端,也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反对因循守旧,主张革新朝政,曾先后提出过自己除旧立新的改革措施。然而正是在具体的改革措施方面,两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王安石在早年写的《上仁宗皇帝书》里认为,国家陷于内外交困而难于久安的原因是“不知法度”,所以出路在于“变革天下之弊法”。他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措施,主张立刻进行大张旗鼓的变法。而苏轼则在其应制科试所作的二十五篇《进策》中,强调“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明确指出两者之中,“任人之失”才是主要的,如果用人不当,变法也未必有济于国事。他还认为当时赵宋王朝的状况,就像一个闷闷不乐的病人,连自己哪里有病也说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朝政必须慢慢来,不能鲁莽地下猛药。也就是说他主张渐变,反对骤变。尽管苏轼不反对进行政治改革,但在改革的内容和方法等具体问题上,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有明显的对立,形成了两人政见的不同。
应当承认,相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而言,苏轼的政治主张具有温和改良的保守性质。这使他与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有了某种思想上的认同,进而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士大夫阶层由于政见不同而形成的党争和倾轧,一直是封建专制集权社会的官僚政治中难以克服的痼疾。党争一起,双方固执己见而意气用事,相互非难,其间难免有人乘机挟私报复。政治斗争中掺杂了许多非政治的因素,其是非曲直就非简单的“进步”或“保守”所能论定的了。

王安石像
王安石在仁宗朝就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但一直未能实施,所以与苏轼等人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冲突。宋神宗即位后,很欣赏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于熙宁二年(1069)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由于有皇帝的支持,王安石很快把自己的变法理论变为变法实践,制定出“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等一系列的“新法”。对此,苏轼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曾批评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宋史·本传》)。当神宗表示愿意采纳时,他又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根据自己的政见,对“新法”进行全面批评,要求废除“新法”,言论十分激烈,这就使他站到了与变法派人物完全对立的旧党立场上去了。
当许多旧党的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而纷纷辞官离京后,苏轼也要求出外任地方官,先通判杭州,后改知密州、徐州等地。在地方官任上,苏轼一面以诗酒自娱,化解政治上的失意,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做些好事;一面则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被采纳而满腹牢骚。见到新法有不便士民者,便用《诗经》“六义”的比兴美刺之法,写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文,以示对新法的不满。
苏轼尤为不满的,是王安石的“用人之失”。如果说他与王安石之间的冲突还仅限于政治见解的不同,双方对彼此的学问和人品都还极为推重的话,那么他对王安石提拔的那些“新进”们,就完全是看不上眼了。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苏轼迁居浙江湖州,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皇上知道自己愚笨,老成不合时宜,所以让自己出外任地方官,自己也不愿意与朝中那些无事生非的“新进”们为伍。这本为牢骚之语,但却捅了马蜂窝。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等一批“新进”纷纷上章弹劾苏轼,众口一词,说苏轼讪上骂下,包藏祸心,无人臣之节,并收集和列举苏轼讽刺新法的诗文为证。在这种情形之下,神宗只好命令御史台派人去湖州拘捕苏轼,入京立案审问。因御史台又别称乌台,故这件案子就称为“乌台诗案”。

宋神宗帝后坐像
用人不当是导致王安石推行“新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对于他来说,此乃不得已之事。因变法一开始就触犯了一些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朝中守旧派的激烈反对,许多原来与他关系不错的人都离他而去。王安石因此而一度罢相。他要推行新法,只有起用那些善于曲意迎合但心怀野心的“新进勇锐之人”,如吕惠卿、李定、舒亶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品行差的人是靠不住的。如吕惠卿本为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副相,但他却因窥视相位而揭发王安石给他的私信中有“无使上知”之语,迫使王安石不得不再度罢相,退居金陵。这样一来,围绕着变法而进行的党争,就演变成了一场争夺权力、排斥异己的恶劣的政治倾轧。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刚接到被拘捕文书时,他还处变不惊,保持着一份固有的镇静和洒脱,对受惊吓而痛哭流涕的妻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 宋真宗时,有一位能作诗的隐士杨朴,不愿做官,却被皇帝召入宫中。皇帝问他能否作诗,他回答说不能,又问他临行时是否有人作诗送行,他说只有老妻作了一首,诗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皇帝听后大笑,于是放杨朴还山。 如今苏轼自己也因为作诗而被“捉将官里去”,他希望妻子也像杨朴的老妻那样,作一首诗为他送行(《东坡志林》)。
可是,当身为太守的苏轼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态度专横的官差和狱卒像鸡犬一样押持过市时,他立刻就感受到了事态的险恶和此行的凶多吉少,大概真要“断送老头皮”了!途经太湖时,见月色如昼而风涛倾倒,顿生投水自尽以免连累他人的轻生念头。只是想到自己一死,弟弟苏辙必不愿独生,苏轼才没有像屈原那样举身自投湖中。
到了京师,关在狱牢里,常被提审,苏轼忧在必死,把自己日常服用的丹药收藏起来,准备一旦有不测即服了自杀(《孔氏谈苑》)。在入狱前,苏轼曾与长子苏迈约定,平时送饭只送菜与肉,如有不测,则改为送鱼。有一次因苏迈有事外出,托一亲戚代为送饭,那亲戚忘记了先前的约定,送一条鱼到狱中。苏轼见鱼大为惊骇,以为难免一死(《避暑录话》)。他在狱中作了两首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即《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其一云: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人间未了因。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苏轼的忠君观念是很强的,处于生死关口,还忘不了颂扬天子的圣明和恩泽万物,把一切不幸全归之于自己的愚笨和不明事理。他想到初入仕途时,曾与弟弟苏辙以将来归隐山中、勿苦爱高官相约,而且前年在徐州相别时,还说过“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的话。可如今自己年未老而要“先偿债”,在此地的青山埋骨,留下一家十口,让弟弟“更累人”和“独伤神”。
这已带有死别时以后事相托的意味了。正因为苏轼此时深信自己必死无疑,所以才会在第二首诗里写出这样的句子: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把临死之人那种魂飞魄散的不安心理,表现得极为真切生动。狱卒得诗后不敢隐藏,上奏朝廷。据说神宗见诗后颇为动心,觉得苏轼还是爱君的,遂有从宽发落之意。
但当时朝中的一些人,如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以及副相王珪之流,却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李定过去因继母死时不服丧而遭士论谴责,苏轼曾上章弹劾过他,这下正好公报私仇。他们把作为苏轼主要罪证的《钱塘集》里的诗加以引申发挥,指控苏轼攻击新法。如说苏轼诗中的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是攻击农田水利法;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是讽刺朝廷盐法等等。
苏轼是个襟怀坦荡的文人,从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反对“新法”的思想是一贯的,而且早在《上神宗皇帝书》里就明确提出来过。所以他不仅不否认李定等人的揭发,而且还对李定等人举报的诗歌里蕴含的讥讽之意加以疏解,使其更明白。如他承认自己所写的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是“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 ,是“以讥新法行后,公事鞭棰多也”。意在歌咏民瘼,以上达朝廷。
李定等人知道,仅说苏轼讥讽新法,似还不足以让神宗杀掉苏轼,于是不惜深文周纳,捕风捉影,指控苏轼对神宗有“不臣”之意。其根据是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
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惟有蛰龙知。
苏轼的这首诗为咏物之作,写桧树不仅树干挺拔向上,直指碧空,连地下的树根也是笔直的。如果不是恶意中伤的话,只能说成是苏轼在借物咏怀时抒发自己刚正不阿的情怀。但是王珪却根据李定、舒亶等人对诗意的曲解,抓住“蛰龙”一词大做文章。
王珪对宋神宗说:“苏轼于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改容道:“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如此解诗,还可进一步把“蛰龙”说成是苏轼的自喻,而“龙”在封建社会是王权的象征,那简直就是要谋反了。当时在场的章惇听出了这里面暗含的杀机,从旁为苏轼开脱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亦可以言龙也。”神宗也还清醒,他认为自古称龙的很多,如孔明非人君,但也称卧龙,所以他觉得王珪的解释未免太牵强附会了,于是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石林诗话》)
苏轼在狱中也感觉到“蛰龙”一词关系重大,在回答狱吏的询问时,他举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为据,说自己诗里说的蛰龙就是王安石所讲的龙。这样一来,想陷害苏轼的人也就无话可说了,总不能因涉及“龙”字而让两颗人头落地。
苏轼毕竟是声名在外的一代奇才,当时有不少人想营救他。如苏辙上书朝廷,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苏轼赎罪。宰相吴充,甚至新党人物章惇等人,也都从旁为苏轼说话。王安石虽已退居金陵,但也上书劝说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是个好名而畏人议论的君主,这些对他的思想不会没有影响。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能免于一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说神宗本来就无意于杀苏轼,也有人说得力于曹太后的出面干预。还有人说是王安石的话起了作用,因宋代还未曾杀过士大夫,神宗朝是“圣世”,哪有开杀戒之理,故此事遂以王安石的“一言而决”。苏轼在狱中关了四个多月后被放了出来,连削两个官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判。所谓“安置”带有管制的意思,实际是戴罪流放。当时受此案牵连的士大夫文人,因“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讽政事”,以及因“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而不举报等罪名,被贬官和远谪的多达数十人。

苏轼《寒食帖》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果不算太坏,但对信奉儒家经世济民的信条、存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士人来说,所造成的思想震荡和心理压力都是巨大而深重的。
从北宋中叶,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的“庆历新政”开始,宋代士大夫文人就把议政、论政作为诗文创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欧阳修就要求作家创作必须“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以求文学的经世致用之效。但“时病”是那么好批评的么?文学果真能有救世济民的力量么?像“乌台诗案”这样拿当代文坛领袖开刀,牵涉面又如此之广的“文字狱”的出现,无疑是对存有这种想法的文人作家的当头棒喝,使他们意识到士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源于儒家思想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兼济参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不能坐视国家的弊政和民生疾苦,免不了循儒家诗教的美刺讽谏传统,借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见解,希望能有补于国政,为君王尽忠心。可是另一方面,若批评时政而得罪了朝廷和君王,又会使自己陷于国家罪人的境地,被指责为不忠不义。忠心为国,反为国法所不容,这是何等的悲哀!
按照儒家的政治信仰,国家、君王、天下是三位一体的,君王不仅是天子,而且是国家的当然代表,君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君王若认为你错,哪怕他是听信了谗言,你纵有千条理由也是错定了。如果像屈原那样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就只有以死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清白了。所谓“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屈原的悲剧也就是中国后来历代文人的悲剧,文死谏,武死战,一直被作为臣子应尽的本分和义务。但这还只是就儒家所讲的那一套君臣父子的社会纲常伦理而言,现实中发生的事远比这复杂得多。假如苏轼在被押解回京的途中就投水自尽,也许并不能展现他的忠诚,反而会给想陷害他的人以口实,作为他“不臣”而畏罪自杀的证据。 有时,死毕竟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在身处逆境时依然顽强地活着,倒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
更为主要的是,一个朝代,当它处于升平阶段,虽有小病痛而无碍大局时,政治往往比较清明,士人要批评时政,充当忧国忧民的先知先觉,当政者一般都不会太在意。可是,当社会的各种弊端都暴露出来,真正需要医治或医治无效时,政治就陷于黑暗动荡之中。当政者或专横独断,病笃忌医;或严法峻刑,排斥异己,哪容你说三道四,因此“文字狱”的产生也就是必然的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士人又该怎么办呢?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另谋出路,寻找新的生命寄托?
只有明白当时积极入世的士人所面临的这种生存困境,才能体会出苏轼所说的“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深重和无奈。士人因识字而读书,由读书中举而步入仕途,学而优则仕,心怀大志,博取功名。但也有可能因“文字狱”而断送前程,饱尝理想失落、性命难保的人生忧患。更何况文人的生命情调,本来就与政治有一层隔膜,搞政治须胸有城府,老谋深算,而真正的文人却过于天真,富于幻想,容易轻信他人。
苏轼少年时即熟读经史,胸怀壮志,听母亲读后汉书的《范滂传》而“奋厉有当世志”,准备为国家建立功业。与弟弟的老成稳重不同,他性格豪放开朗,口无遮拦,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计后果,而且喜欢开玩笑,很洒脱。这曾使他的父亲深感不安。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说,他给两个儿子取名轼与辙,概括了两人的基本性格。“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故苏洵认为苏辙能“善处乎祸福之间”。“轼”是车上用来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凭轼而望,可以看得很远,故苏轼字“子瞻”。这也意味着苏轼性格外向,爽朗不羁,不知掩饰而锋芒毕露。故苏洵叹息道:“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后来苏轼所遭遇的一切,证明苏洵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
性格即命运。苏轼走上仕途后,即因绝顶聪明而心直口快和善于“戏谑”,常使同僚感到不自在。他说自己心里藏不住事,心有不快则“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曲洧旧闻》)。如在凤翔任职时,他曾与章惇一同出游,一日两人游南山,抵达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仅有一横木架在上面。章惇请苏轼过去题字,苏轼不敢冒这个险,他就平步走过去,在石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然后又神态自若地返回原地。苏轼松了一口气,用手抚拍着章惇的背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大为不解,问:“何也?”苏轼回答:“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哈哈大笑(《宋史·章惇传》)。又如熙宁年间,王安石颁布《三经新义》,并作《字说》作为自己解经的根据。《字说》的一个特点是以汉字的偏旁解释字意,多有牵强附会之处。苏轼很不满意,去向王安石请教“波”字是什么意思,王安石说:“‘波’乃水之皮。”苏轼戏谑道:“如此‘滑’则水之骨也!”令王安石无言以对。
这些虽为日常生活里的小事,可大事往往是由小事积成的,当苏轼在政治生活中也顺着自己坦荡的天性,把对新法的不满像吐苍蝇一样吐出来时,得罪的就不是某个朋友和同僚,而是朝中因推行新法而获重用的一大批新党人物,以及支持新法的神宗皇帝了。即使从苏轼的个人性格等主观方面的因素来看,他的因诗获罪也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
一种办法是收敛身心,抑制个性,夹着尾巴做人,但这不符合文人的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乌台诗案”结束时,苏轼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能在街上自由行走,立刻就好了伤疤忘了痛。他当天作诗二首,其一云:
出门便旋风吹面,
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
试拈诗笔已如神。
其二说: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寒上纵归他日马,
城中不斗少年鸡。
如果说前一首主要写自己重获自由后的喜悦,尚无问题的话,那么第二首才说文字给自己一生带来不少麻烦,却又化用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安慰自己。似乎只要能诗笔“如神”,那么因“诗祸”而入狱也算是一种福分。更要命的是 “城东不斗少年鸡” 一句,这句诗用《东城老父传》的典故,言贾昌少年时因斗鸡取媚于皇上,唐明皇将他当作弄臣和倡优豢养起来,以此讥讽朝中的得势小人是倡优,颇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这样的诗句若传到了御吏们的耳中,不知又要惹出多少是非。难怪苏轼作完诗后就骂自己:“犹不改也!”(《孔氏谈苑》)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大凡文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和创作冲动,自幼习文作诗养成的习惯,使文学创作已成为他们生命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苏轼谪贬黄州以后,多次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自己“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答李端叔书》)。按理应无文字流传了,然而正是在他到达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之后,才创作出了大量能流传千古的作品,成为他生平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不过,像青少年时期所写的那种评说古今、考论是非、直言进谏的长篇宏论和进策是没有了,以经世济民为主题的批评时政、议论风发的政治诗也不写了。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创作的重心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转向人生问题的探讨,即如何对待严峻的生存困境中所面临的人生忧患,如何超越生死,超越是非荣辱,使自己的生命体验与自然天趣融为一体,在审美的观照中获得精神的自由和解脱。既然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难以在现实社会政治中实现,那么,只有到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去寻觅,在物我合一的审美观照中去体验,这样便可以乐而忘忧。
对于一个士大夫文人来说,这种创作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意味着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的转变。我们可以“乌台诗案”为分界线,把苏轼一生的思想经历和心路历程分为前后两期。尽管前期对我们了解苏轼的思想也很重要,但苏轼之所以为苏轼,并以苏东坡的名字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文化伟人,是由他后期的思想经历所奠定的。他那种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的精神,那种历经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处世态度,是在这以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
在苏轼后期的处世心态里,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生命忧患意识。这导致了他对社会政治的厌倦,对人世间种种摆脱不了是非善恶束缚的做人教条的怀疑,主张顺应自然生命,无可无不可,随缘自适,逍遥旷达。但他又十分热爱生活,执着生命,虽自称“东坡居士”,并没有真正隐退和“归田”。他在理论上从未放弃儒家那一套入世的人生哲学,但是他后期的许多作品却充满了无所寄托的空漠之感,在对自然高远、超尘出世的审美境界的描绘里,充满了对此尘世无常的盛衰悲慨,给人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之感。
他很清楚,既托生于世,要脱离现实社会,完全不过问政治,对于士人来说是绝无可能的。你可以不关心社会政治,但社会政治却要来关心你。事实上,苏轼一生都未能摆脱“文字”之祸的纠缠,可他却能在逆境中保持做人的洒脱,通过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方式,于审美创作活动中获得生命的升华和精神的自由,形成中国文人所特有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