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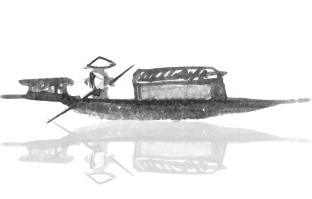
所谓“处世心态”,关系到在社会如何做人的问题,属于中国士人生命追求的根本方向与智慧方向的问题。宋代士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既源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体验,又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儒治世、以佛修心和以道养生的行为模式。
儒学作为入世的人生哲学,有内外两个方面,于内可正心、修身,于外可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的是“内圣外王”。但“内圣”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一种价值信仰和人格追求,具有相当的自主性;而“外王”属于社会政治方面的功业,是实实在在之事,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很大。从逻辑上讲,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真正的“内圣”之人,未必能建立起政治上的实际功业,而那些在历史上能成王称霸的人,很难说就一定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但儒家的学说却将两者视为一体,鼓吹王道合一、政教合一的“王道”,以道德即政治的说辞,把重视个体人格道德修养的“内圣”,导入“外王”社会的王道政治之中,要求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人必须是圣人和贤人。自己做个套,然后往里钻。在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中国士人里,以天下为己任的忠君报国成为主要的人生追求,其济世救民的高尚情操,多出于为君国分忧的考虑,具有强烈的社会功利目的。
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士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进退失据,以致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因为从王、道合一的官本位理论出发,自然会得出道德即政治的结论,大权在握的君王成为至高无上的道德评判者。当“志于道”的士人在政治上无功业可言,甚至还遭政治权威君王的贬谪时,他就很难再以具有完满道德人格的圣贤自恃,只能自称罪人,所谓“君王圣明,臣罪当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什么道理!所以自魏晋之后,中国士人尽管在理智上和思想上仍信奉儒家学说,可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却更喜爱佛老之说了。
宋代是儒学复兴时期,这种复兴首先体现为唤起士大大阶层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范仲淹提出的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口号,激起了一代读书人的治国豪情,所以北宋的士大夫文人多具政治改革热情,希望通过改良或变法富国强兵。当时,欧阳修、王安石和青年苏轼等一大批文人作家,写了大量议论时政的文章和诗歌,充分体现出“有为而作”的经世致用精神。但论政、议政是一回事,实际的政治运作又是一回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固然痛快,可政治斗争中的你争我斗、福祸难测却令人生畏,以至生厌。随着“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失败,党争愈演愈烈,士人在政治运动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宦海沉浮,于是有才华、有抱负的文人作家心里,充满了失望和痛苦、压抑与悲愤,需要一种精神上或生理上的慰藉和存养。
这种时刻,道家那种人生贵“适意”的逍遥哲学和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中国化的禅宗那种“性自清净”的觉悟解脱,就成为士人化解痛苦和忧愤、保持心理或生理健康的良药。道家认为人处在“人间世”是有待的,无半点自由可言,只有无用于社会,摆脱了名誉、利害和物欲的束缚,以超功利、超道德的眼光看待生活,返回到生命的自然存在状态,才能保持住人格的完整。故庄子主张顺应自然,无思无虑,让自身的生机显发,保持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心灵适意,达到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逍遥游,以成就所谓的“真人”、“至人”。
道家所讲的本然生命之“真”,在物我冥合的虚静状态下才能把握,据说它与“人间世”各种人为的名教仁义不同,是人生来就具有的。而佛家所说的“佛性”,作为人能成佛的内在根据,也被说成是人人生来具有的。佛性论是佛教的生命哲学,曰“常、乐、我、净”,法身是常,归寂为乐,真我即佛,净无烦恼;明心见性而顿悟圆成“涅槃”境界,又谓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中国的士人在用“格义”的方法去诠释佛学时,常用带有庄玄色彩的“真如”一词去说明“佛性”,用道家所说的“无”(虚无)比附释家的“空”(空寂)。寂静之中感觉生机流行,生机流行而归于寂静。当中国化(实即士大夫化)了的佛学禅宗产生之后,佛老庄禅在许多方面都趋于一致。不同的是,道家返归自然的生命哲学到后来更偏重于向炼气养生方面发展,成为一种功夫和气术;而佛性为悟理之本,禅宗的“以心传心”的觉悟解脱方法,更注重本心的直觉顿悟。参禅者证空而观生,归寂而知化,将道家追求的人生适意升华为更加空灵、更加无滞无待的禅悦。
禅宗觉悟成佛的心性论和道家返归自然的逍遥、齐物之旨相结合,作为一种生存智慧,不仅能使士人在人生失意时得到解脱,而且也契合文人创作中追求个性发挥和精神自由的生命格调。自苏轼之后,宋代作家在将生活艺术化的审美创作活动中,往往以禅喻诗和以禅论诗,将诗道与禅道相提并论。而作家的诗文作法,常常就是他的活法,是其处世态度的表现形式。道、释的精神自由思想和适意禅悦的空灵境界,对于中国文人尤为重要,成为他们在社会上为文做人的最终出路。它能使士大夫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道德和政治的重负,有一种自然行文的潇洒气度,活得不至于太累,避免了西方作家那种因理想与现实难以妥协而导致的精神分裂和自杀行为的产生。
但是,在生命意义的根本追求方面,道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的至人境界,佛家视人生如苦海而追求一切解脱的真如佛性,是一种解决人生问题的消极办法。它只能解决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而且带有追求个体生命适意和精神自由而反社会、反权威、反价值的倾向。这虽有利于文人在文艺创作活动中的神与物游,极尽潇洒自得之趣,但若施之于社会生活,则有可能使儒家那一套维系社会稳定的名教纲纪的价值标准失去约束力。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自由总是有限的,个体的个性意识必须符合群体的道德规范,正是在这一点上,以天下为己任而追求成圣成贤的理学家,要对以佛老庄禅为依归的文人生活和文学创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理学家认为人生的第一要义是学做人,要以圣贤为榜样,做品德高尚的仁人志士。尽管他们的为学都要经历过一个出入佛老而返归儒学的阶段,并在修养方法和思维方式方面吸收和改造佛老庄禅学说,但却坚决反对“以佛老为圣人”。在他们看来,“圣人”具有无限的道德人格,承担着替天行道、保育万民乃至万物的义务与责任,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哪能只追求个人超越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精神自由和人生解脱呢?不过,这种“圣人”观是从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中推导出来的,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理想化的成分。儒者心目中的大圣人孔子,虽被汉儒说成是“素王”,但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王”者。“内圣”并不一定能开出“外王”,而“外王”又非常人所能做到。对于一般士人而言,要学做圣人,行“圣人之道”,实际上只有“内圣”一条路可走。
“内圣”之学即心性之学。在宋代理学兴起之前,儒家“正心”、“诚意”的心性之学隐而未显,士人在治心养气方面多以佛老的心斋和静坐为基础,以致宋儒要弘扬儒家的“内圣”之学时,往往还得从佛老庄禅入手。如二程一见门人静坐便叹其善学,故程门后学以静坐默观心体,作为提高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水平的心性存养工夫,将老庄的守虚静、佛家的禅定,与儒家的持敬、克己融为一体。但儒家之道是入世之道,存于“人伦日用”之间,这与佛老两家那种超越现实、摒弃世情的空无之道是很不相同的。当朱熹逃禅归儒,决定终身奉行儒家“士志于道”的传统之后,就放弃了当诗人和文章家的想法,主张以持敬的存养工夫代替空理悟入,以应事穷理代替内心体认,强调人当常存“敬畏”之心,不可有丝毫怠懈,使心时刻处于提厮警觉状态,而后可以格物穷理。
为了突出“理”的本体地位和绝对性,理学家常在“理”字前加一“天”字,以显示其价值之重大,不容怀疑。“道”即“天理”,道的尊严要靠培养士阶层道德人格的内圣之学来彰显,只有对天理存敬畏之心而克己复礼,方能体道或行道,成为圣人之徒。这样一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为宋儒为人处世的一个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的做人标准了。它要求士人在日常生活中依靠内心的持敬察识体会天理,将儒家讲的代表外在社会道德规范的“礼”,内化为道德自律的“理”。依此而正心、诚意,而克己复礼,入世做事时才会有敬业精神,才能自觉自愿地、发自内心地遵守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国家君王做事尽忠心,居家事父尽孝心,与朋友交往讲信义,以求“心安理得”,这就是宋儒所说的做人的“天理”和“良心”。

苏轼《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行书,台湾故宫博物院藏
儒家的“内圣”之学,原本是针对能读书明理的士及士以上的人立教的,而当理学大行于世之后,它就渐渐地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积淀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成为一般中国人处世做人的道德信条和价值评判标准了。如果谁在生活里潇洒不起来,只能说他活得太累;如果谁肆无忌惮,丧尽“天理”,没有“良心”,那简直就不配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