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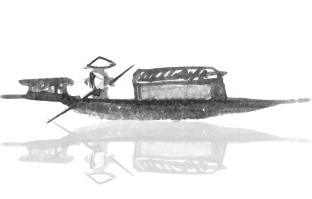
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思想意识来看,中国古代的士人都是一个品类极为繁杂的阶层,难以有一个确切的定位。从先秦的武士、文士,两汉的经师、博士,到六朝名士和唐代诗人,以至宋代的文人与儒者。他们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可上可下之间,上则为朝廷重臣,达官贵人,钟鸣鼎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下则贬谪荒野,或浪迹江湖,薄汤淡饭,说不尽的穷愁潦倒和清贫。人生的大起大落,世事的白云苍狗,使他们在如何处世、如何做人,如何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如何在身处逆境时求得心理上的平衡等一系列重大的人生问题上,有着异于常人的深入思考和表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担负着知识传播和思想文化承传的任务。达则兼济天下,建立功业;穷则独善其身,以文明道。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为社会一般人提供处世的方法和行动准则,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和性格气质,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正能以自己的独特人格和博大思想影响他人,成为代表一个时代思想文化发展成就的主脑式的文化伟人,毕竟是少数。他们巨人般地矗立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峰巅,引导着一代以至无数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价值走向。宋代的苏轼和朱熹就是这样的杰出人物。
提到苏轼,我们会想到他那“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放词,想到他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瑰丽诗篇,想到他那清新神逸、蕴含丰富人生哲理的前后《赤壁赋》,以及他那“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的文人画,和“刚健含婀娜”而无半点俗气的书法艺术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他都堪称文艺天才,是宋代最杰出的大文豪。读他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一种腾踔横溢的生命力的跃动,坦荡开阔的胸襟,潇洒自如的气度,一派乐观旷达、参透人生底蕴和自然奥秘的大家风范。可是谁能想到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有着十分深微沉重的人生忧患和心灵痛苦呢?
苏轼曾说自己“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尽管他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远大的抱负,二十二岁通过进士考试而名震京师,可步入仕途后却命运多蹇,屡遭不幸。如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料定自己必死无疑,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晚年又一再遭政治迫害,贬官英州、惠州、雷州、儋耳等蛮荒边地,白发飘潇而携子渡海,流放到天涯海角。可以说,对人生虚幻和命运无常的痛苦体验,当时的作家中很少有人能赶得上苏轼。但他却能在身处逆境时,也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以及潇洒走一回的无畏,令想置他于死地的政敌也奈何不得。

苏轼《枯木竹石图》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人格和处世心态呢?是何种精神力量和人生哲学,使他坦然面对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磨难,懂得生活的艺术,在审美创作中得到心灵的升华和解脱,因此乐而忘忧呢?在当时,不仅文人潇洒自如的生命格调难以见容于王权专制的社会政治生活,就是以“卫道”者自居、把封建社会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视为“天理”而心存敬畏之意的儒者,也常常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进退失据,饱尝道德理想失落的痛苦。这在朱熹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被视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儒。他死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朱文公”,赐太师名号,追封信国公。明永乐年间,他所著的《四书集注》被列为国学,明成祖亲自作序,将其与“五经”一道颁行于天下,作为一切士子必读之书。到了康熙年间,清帝玄烨又命人编《朱子全书》、《性理精义》,诏令颁行全国,他称朱熹“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尊祀在十哲之列。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都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把朱熹神化为圣人,要子民们顶礼膜拜。可就是这样一位儒家圣人,生前却不被统治者所重视。他自幼颖悟好学,年仅十九就登科中举,可谓少年得志。作为儒者,他抱有绍道统、立人极、为帝王师而治国平天下的宏愿,认为士人应该像范仲淹一样,以天下为己任。可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却以少量的祠禄,过着讲学著书的隐居生活,当他想把自己理学的“毛”附着于朝中相党的“皮”上,使之成为一种有作为的政治力量时,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在庆元党禁中被列入伪逆党籍,成为朝廷法律确定的大逆不道的罪人。
这或许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一出冤假错案,但对于一个有志于“补天”的卫道者来说,无疑是一场人生灾难和信念危机。那么,朱熹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呢?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支撑着他度过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人生悲剧的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从当时士人所特有的处世心态入手,把一个时代士人的人生观和政治态度,还原为现实中活生生的文化心态和人格追求,方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