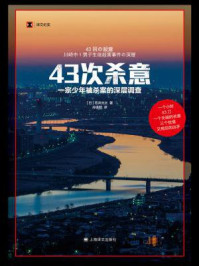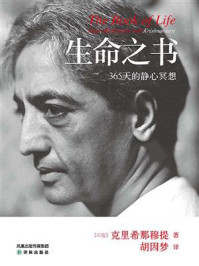受家庭环境和师友讲习的熏陶,苏轼接触佛、道两家思想的时间比较早。这对他一生的思想言行和处世心态,有着非常隐蔽而深刻的影响。
在《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里,苏轼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均笃信佛教,爱作佛事,在《十八阿罗汉颂叙》里,他又记述幼时家中曾供有十八罗汉像。这些对于幼时的他不会没有影响。他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说: “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 表明他与弟弟苏辙在少年时代就已开始阅读佛道典籍了。他八岁时入眉州天庆观北极院从道士张易简读书,对道教的飞仙悟真之说也多有耳闻。

释迦牟尼佛
佛、道两家视人生如梦幻的思想,在苏轼年少的心里早已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使他对世事的飘忽变幻和人生的偶然无常,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当他与弟弟和父亲一道赴京师应试而名震朝野时,忽然传来了母亲病故的消息,父子三人匆忙离京奔丧。归家后所见,已是一片人亡家破的荒凉景象。在服母丧期满而启程还朝时,苏轼于《浰阳早发》一诗中写道: “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 已对自己追求的仕途功名产生了怀疑,有一种人生荣枯难料的虚无之感。
当苏轼再次踏上仕途,路过以前与弟弟赴京应试时住过的渑池县,得知所投宿寺庙的僧人奉闲已圆寂归天,当年兄弟俩留在僧舍壁上的题字也看不清了。一种岁月飘忽、生死难定的虚无缥纱之感油然而生,他在《和子由渑池怀旧》里抒发了这样一种人生感慨: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这几句诗被认为是最能反映作者性情本色的神逸之作,蕴含着某种彻悟人生底蕴的禅机,为后代无数中国文士所喜爱。清人查慎行在为苏轼的这几句诗作注时,引禅宗天衣义怀禅师教人参悟之语为说,即:“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用鸿雁飞过空中时,无意间留影迹于水中的意象,喻示世间万物的虚幻不实和似有而非真,要人摆脱一切执着和迷妄,以无住无念之本心,对待世间万物的迁流不息、生灭无常。这与苏轼所说的空中鸿雁偶然于雪泥上留印迹,飞时不计东西,意思是很相近的。或者说,在苏轼以雁喻人所表达的人生体验中,已清楚透露出他早年受释老空无思想影响的消息。
正因为如此,在苏轼刚踏上仕途,任凤翔签判时,本应一展其治世济民宏愿的他,却对宣扬出世哲学的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凤翔八观》第四首的《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中,表达了对佛教著名人物维摩居士的神往,以为 “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 在凤翔任职期间,他开始向同事王大年学习佛法,如他在《王大年哀辞》中所说: “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 但这只是苏轼正式习佛的一个开端。
凤翔任满后,苏轼回到朝中任职,不久因政见与主张变法的王安石不合,被迫离开京师,出任杭州通判。到杭州后,他遍游江南名山寺庙,广泛地与禅师和诗僧交往,成为著名僧人的方外之交。当时与苏轼交往较密、被他敬为师友的僧人有:海月法师慧辨、辩才法师元净、大觉禅师怀琏、佛日禅师契嵩、了元禅师佛印,以及诗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参寥等。苏轼在《海月辨公真赞》里说,每当他与法师 “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 可以从中得到心灵的安慰和解脱。这是他热衷于与僧人交往,主动接受佛家思想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轼的习佛,并不以超然玄悟的出世间法为目的,而是想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以便自己在变幻无常的人生历程和风浪险恶的政治生活中,求得身心的清净和安宁。随缘自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把出世与入世融为一体,才能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做到进退有据,在充满不平和烦恼的现世生活中,保持一份超脱情怀和安宁心境。而佛学的某些看待人生问题的观点,特别是禅宗的解脱方法,是有助于做到这一点的。
在“乌台诗案”发生之前,睿智的苏轼就已预感到了政治风浪的险恶和命运之神的飘忽无常。他原以为自己离开朝中政治斗争的漩涡,出外任地方官,优游山水,访僧谈禅,即能避开社会政治的纷扰。然而愈演愈烈的党争,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在《百步洪》诗中,他以急流飞舟的描写,暗喻“险中得乐虽一快”的政治生活,透露出诗人对党争将导致的社会政治动乱的感慨,涛声喧哗中已有一片空漠之感。人生短暂而仕途忧患日深,怎么办才好?苏轼在诗中说: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 所谓“无所住”,本于《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亦即禅宗六祖慧能在《坛经》中所说的“以无住为本”,意思是要保持性自清净的“本心”和“实相”,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不为外物所动。这样才能超然于纷纭世态之上,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解脱。
据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所说,苏轼读释氏书而能“深悟实相”,还是在他谪居黄州之后。也许只有真正在人世间经历过生死体验和种种人生磨难的人,才会对佛教那种视人生如苦海、似梦幻,为摆脱烦恼而寻求解脱良方的出世哲学产生深刻的内心共鸣。更何况苏轼戴罪流放到黄州后,许多官场上的亲朋好友都与他断绝了音信往来,生怕由此得罪了朝廷,于自己的仕途不利。在苏轼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可以理解。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处境艰难的时候,过去结识的一些释、老方面的朋友,却不远千里寄信来问候,情义之厚,胜过平时。真是患难见真情啊!苏轼不由得感叹道: “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 (《与参寥子书》)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苏轼才把佛法的清心、节欲、慈悲为怀,看作是优良人格的德行,认为是人的“聪明”和“德力”的表现,这更增加了他习佛的主动性。
与僧人交游唱和,论诗参禅,亦俗亦僧,在宋代文人中是一种时尚。因为这不仅可以在仕途失意时求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还可以表现出身在官场红尘中士人的潇洒脱俗和大彻大悟。在宋代文人的笔记杂录和僧人的传灯录里,留下了许多苏轼与名僧交往的趣闻轶事,其中尤以他和佛印禅师之间“斗机锋”的佳话,为人们津津乐道。
据说,有一次佛印禅师上堂宣讲佛法,苏轼闻讯赶去旁听,可堂上早已人满为患。佛印对苏轼说:“此间人已满,无学士坐处。”苏轼灵机一动,立刻回答说:“既无坐处,何不以禅师四大五蕴身为座!”这是一句含有佛理机锋的禅语。按佛教的说法,人的身体是由“四大”和“五蕴”构成的。“四大”指的是地、水、风、火等四种物质元素,可代表构成人体的客观要素;“五蕴”指色、受、想、行、识,为构成活人的主观因素。如此说,那么禅师的身体就应当是与天地同其大,而且有包容感应万物之心,何愁没有坐处。佛印知道这是苏轼借机与他谈佛论禅,就提出想问苏轼一个问题,如果能回答,他甘愿以自己的身体充当座位,如果回答不了,苏轼得把身上的玉带留下来。苏轼欣然同意。于是佛印便问:“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请问学士坐何处?”苏轼一时语塞,回答不了,只好把自己的玉带留了下来,承认自己是还没有参透性空佛法和禅学机锋的钝根之人。
佛印所说的“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是建立在般若“缘起性空”学说基础上的佛教大乘教义。其基本思想是说:世界上的一切客观事物和现象,都是因缘所生的假相和幻影,不是本来就有的,没有独立不灭的自性,所以是“性空”。从缘起方面说,万法因缘而生,迁流不已,也都是假的、空的,是人的一种主观幻象,并非实有。如《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另外,从人自身来看,人生也同样只是一个意念不住的流转过程,是没有自性的。人身的“五蕴”也是因缘所生,人若执着于自身,不仅有生、老、病、死诸苦,还会给人带来各种感觉、欲望和意念无法满足的心灵痛苦,无法得到解脱。总之一切都是假象,思想是错误的,情感是痛苦的,意志是薄弱的,最后面临的总是死亡。只有了悟人生的空无和虚妄,进入五蕴非有的寂灭、圆寂、涅槃的境界,才能斩断贪欲痴想,灭尽烦恼。
换言之,无论从人所置身的客观现实,还是人自身的主观念想来说,一切都是毕竟空,没有自性可言。只有以空、无以为本的“清净”的“本心”,才是唯一的世间“实相”,这就是《华严经》所说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在其他佛书里,又称为“本有真心”、“真如”、“佛性”、“涅槃”等等,意思都差不多。故《金刚经》说:“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据《坛经》所言,南宗禅的创立者六祖慧能就是因为听人诵读《金刚经》而悟“自身净心”的。慧能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主张僧人修行时应“无念”、“无相”、“无住”。只有了悟自心自性本来是佛,“本心”即真如佛性,直指心源,明心见性,才可以得到顿悟解脱。后来,这便成为禅宗的最基本思想,是僧人参禅悟道的“不二法门”。
苏轼涉足佛教的时间比较长,交往的僧人也很多,所以他对以上所说的般若“性空”思想和禅宗的“明心见性”之说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自己以“四大五蕴身为坐”的说法执着于实有的意念,并不符合把人生当作苦海无边的假象而求“常乐我净”的了悟解脱的佛教教义。一经佛印禅师点破,即甘拜下风。不过,苏轼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人,有一次他写了这样一首偈: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意思是说自己的禅定功夫已到达一心具万法而自足圆寂的境界,能不为世俗的毁、誉、利、诱、成、败等所动。偈子写成后,他派人给住在江对面的佛印禅师送去。佛印看后不说话,只在上面批了两个字:“放屁!”让人把偈子又带了回来。苏轼看到批语后十分恼火,随即乘船过江,当面责问佛印为何竟这样不通情理,以骂人的秽语相加。哪知佛印若无其事地说:“此话怎讲?”当苏轼提起“放屁”的批语时,他呵呵大笑说:“汝已‘八风吹不动’,何为一屁过江来?”令苏轼无言以对,自愧弗如。
类似这样的轶事趣闻,在宋人有关苏轼与佛印交往的记录中还有不少。两人你问我答,有如名士清淡,庄谐杂出;又像聪明人在显辩才,抖机灵,其结果常常是禅师佛印显得要比诗人苏轼在禅理上更胜一筹。这里面不排除当时记言者的好佛偏向,但也说明苏轼的习佛和出家僧人的谈禅,不仅有程度深浅的不同,在目标追求上也是不一样的。僧人谈禅往往以出世的顿悟圆成或寂灭涅槃为最高境界,而苏轼则在《答毕仲举书》里明确表明:自己并不赞赏“所谓超然玄悟者”,所以对佛书的妙处亦不能通晓,只是取其有益于人生实际的粗浅假说以自洗濯,难以做到心空一切。这就像农夫除草,旋去旋生。他还把论禅比作龙肉,自己习佛则是猪肉,龙肉是吃不到口里的,猪肉却可以饱腹。

热贡唐卡《释迦牟尼佛》
本来,佛教所讲的“实相”或“自性清净”,指佛心佛性而言,是以灰心息智摆脱一切人生执着的寂灭、涅槃境界,是一种对现实人生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宗教教义。但经过禅宗六祖惠能的宗教革命后,所谓“直指心源”、“见性成佛”,却成为针对现实人生而求顿悟解脱的说教。惠能在《坛经》中就常常以“人心”谈“佛心”,以“人性”说“佛性”。他说:“世人性本清净,万法在自性。”“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念,性自清净。”又说:“内调心性,外敬他人”,“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惠能还反复强调:“佛法在世外,不离世间觉。”“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发展到后来,便成为马祖道一禅师所说的“自心是佛”和“平常心是道”了。郁郁黄花,莫非般若;搬水运柴,皆为妙道。由传统佛教的出世解脱,变成为入世得解脱。这是非常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也是他们容易做到的。
如此说来,“无所住的清净心”并不玄妙,它只是一种平淡自然、无所系念的生活态度和为人处世之道。苏轼在《和蒋夔寄茶》中说:“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他在《书焦山纶长老壁》诗中又说:“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屦。譬如长鬣人,不以长为苦。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归来被上下,一夜着无处。展轻遂达晨,意欲尽镊去。”苏轼认为,这虽是日常生活中很浅近的凡俗之事,但也说明了无挂碍的清净心的重要。他“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
用自自然然为人、平平淡淡是真的态度对待生活,心无妄念奢想,不仅能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得自在些,而且也可以把富贵、功名看得淡一些。因为富贵难长久,功名身外物,越是享尽荣华富贵,越易转眼顿成凄凉,生前功名显赫,死后也还是枯骨伴黄土。苏轼在黄州所写的《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有 “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 之语。在贬居黄州的五年时间里,他每隔一两天就要到安国寺去焚香默坐,深自省察。通过静坐冥想的修习方式,达到一种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精神境界,真可谓 “一念清净,染污自落” (《黄州安国寺记》)。这样一种清净心,不仅让人忘却烦恼忧愁,不为富贵贫贱所扰,而且能使心灵处于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的自然状态,有益于身心的健康。
元祐更化时期,贬官在外的苏轼被意外地召还朝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连升官,青云直上,由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三品大臣,素有“内相”之称。骤然间的位极人臣,并没有改变苏轼已形成的视富贵为过眼烟云的人生态度。他虽然身居高位,却淡泊名利,向往山林自然平淡的生活,经常与文友、高僧相聚,追求林下风流的清旷之乐。对于朝中你争我夺的官场生活,他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不久就一再连上章疏,要求出任地方官,先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
要真正做到心地清净、无所系念而随缘自适,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相对说来,不贪恋富贵功名并不难,难的是面临一连串的人生噩运时,处变不惊,受辱不屈,始终以自然旷达的“平常心”去看待一切。元祐更化不久,新党再度当政,被视为“元祐党人”的苏轼就大难当头了。先是被贬谪到岭南的惠州,后又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原来曾是苏轼朋友的章惇在朝中执掌大权,可他反目为仇,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在苏轼携家带口窜流岭海的七年时间里,家中先后有九人丧亡。他饱尝晚年失子丧妾的悲痛,以致当他辞别家人,让幼子苏过陪同乘船前往海南岛时,已做好了老死海外荒蛮之地的打算。到达儋州后,苏轼父子曾借一间废旧的官屋暂避风雨,因官屋破漏,一夜三次移动地方。就是这样,朝廷知道后,还遣使臣过海,把苏轼父子逐出官舍。苏轼无处可居,只好自己买地盖了几间简陋的茅屋,又因生活困难,尽卖随身携带的酒器以供衣食。如此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他还能安然地活着,最终还能渡海北归,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北归不久,苏轼就病逝了。大约在去世前一月,苏轼看到大画家李公麟为他画的肖像,作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篇作品又名《照容偈子》,是苏轼对自己后半生思想和经历的一个简要概括。“已灰之木”是对彻悟人生、看破红尘之后平静心境的形容,近于佛家所说的自性清净的寂灭境地。“不系之舟”则是对无所系念而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的形象表达,含有随波漂泊于生灭流转的人生苦海而毫不在乎的意思。如此则平常心就是道,不离世间也能得到解脱。
苏轼真正归诚于佛僧,是从黄州开始的,以习佛求道的“功业”除去“恶业”,也自黄州始。后来他贬谪惠州时,远在江浙的佛印禅师曾托人千里致书,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佛印还告诉苏轼自己从前求佛的经历,说自己曾问法师:“佛法在什么处?”法师对他说:“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尿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他以此开导苏轼,说你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可“到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聪明要做什么”?如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那么是可以达佛业的功德圆满之境的。
其实,不用佛印劝导,苏轼就已把自性清净的佛法作为应物处事、化解人生噩运所带来的一切不幸的法宝了。如在谪贬赴惠州的途中,他曾到金陵的崇因禅院礼拜新造的观音菩萨像,求菩萨保佑。南行经过曹溪时,专门到六祖惠能传法之地的南华寺拜见南华长者。他于《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已在南华相待数日矣。感叹不已,故先寄此诗》中说:
水香知是曹溪口,
眼净同看古佛衣。
不向南华结香火,
此生何处是真依。
“曹溪口”指南华寺,“古佛衣”据说是五祖弘忍大师传给六祖惠能的衣钵,当时犹存于寺中。“此生何处是真依”表明了苏轼皈依佛法,以曹溪南宗禅为精神寄托的人生抉择。在谪居惠州期间,自愿陪同苏轼一起流放边地,最了解苏轼思想和为人的侍妾朝云不幸染病去世。朝云也是个虔诚的信佛者,苏轼曾把她比作“天女维摩”。据说她临死前还在念《金刚经》里那首著名的偈语,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亦如电。她死后,苏轼把她葬于寺庙旁边,并建了一座“六如”亭来纪念她。
北归时,苏轼再次到达南华寺拜佛许愿。他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写了一篇《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面对慧能的灵塔,诉说自己窜流岭南以来的不幸遭遇,以及一生的忧患常倍于他人的感慨,以为这是因前世罪业而堕入恶道之故。他起誓:“轼敢不自求本心,永离诸障;期成道果,以报佛恩。”如果说苏轼早期的习佛还只是一种仕途失意时的安慰的话,那么到了晚年,已是人生自我拯救的强烈要求了。他作《六观堂赞》和《六观堂老人草书诗》,自注云:“六观,取《金刚经》梦、幻等六物也。”所以“六观”也就是“六如”,名为观,说明它已成为苏轼用来看待一切人间事物生死起灭的人生观。如果考虑到禅宗六祖惠能也是闻《金刚经》悟道的话,那么苏轼的这种看破生死、荣辱的人生领悟,与曹溪禅的出世思想和人生信仰已是十分接近的了。
以自求本心的佛法求解脱,以虚无空寂为本的“六观”去看待世界,就会把世间的一切都认为是一种生灭流转的过程。不仅世事是虚幻的、短暂的,人生更是虚幻的,什么都没有计较的必要,何苦呢?人世的功名既是没有价值的,人生的祸福苦乐也只是相形而现的幻影。这样一想,对于苦难的现实就能采取淡然处之、顺应自然的态度,同时也可以断除迷惑,荡相遣执,心无所住,清净无妄而随缘自适了。
毫无疑问,这种主观唯心的人生观是十分消极的,但对于缺乏革命精神的中国古代士人来说,他们既无力改变既成的苦难现实,更不可能对造成苦难的封建专制集权制度存有反抗之念,那么当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也只有用宗教鸦片来麻醉自己,寻求一种内心的解脱和平衡,提高自己对苦痛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至于因烦恼与绝望而自杀,也可避免因失去心理平衡而发疯发狂或精神分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处忧患时保持无所住的清净心,也不失为一种生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