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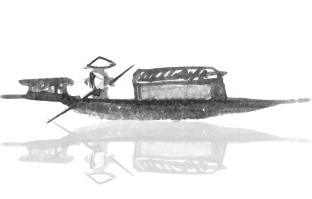
如前所说,忧患意识的产生,基于人的愿望行为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的离异和对立,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不相符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对于中国古代士人来说,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他们具有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历史责任感,而他们的才学和思想在实际政治中却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为拥有政治权势的人所忌恨和排斥。政治运作不是诗,也不是书斋里的玄想,而是权力意志和功利行为,不能文质彬彬,不能温良恭俭让,要有审时度势的谋略和硬心肠,要口蜜腹剑,关键时刻,一剑封喉。这与文人的生命情调和儒者的做人理想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因为他们过分富于理想和玄思而缺少实际政治斗争的才干,不懂政治操作的技术,他们的政治理想很美好,而现实政治则完全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专制政体下,不懂政治权术而又不能忘怀政治,还要议政、参政,其悲剧命运就是难免的了。从“乌台诗案”到“元祐更化”,苏轼由于改不了自己心无城府、口无遮拦的个性,陷于新、旧两党的夹击之中,使他较早地觉悟到了这一点。一次上朝归来,苏轼饭后扪腹徐行,回头问身后的婢妾他肚里是什么?有人说是一肚子文章,还有的说是知识,他都认为不对。深知苏轼为人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梁溪漫志》)他听后捧腹大笑,深以为然。也就是说,苏轼也明白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并不适宜于在朝中做官,他不善于也不会玩政治游戏,断绝了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博取功名的念头,觉得那样的生活没有意义,但他又不可能弃官归隐,完全脱离仕途而隐居山林。
对于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做官不仅是立身扬名的机会,也是维持生计的手段,功名可以不顾,自己和一家人的生存温饱却不可或缺。苏轼不愿扭曲自己的个性去做蝇营狗苟的政客,可也没有从仕途抽身而超然于社会政治之外,只是但求自己一心之所是,不与流俗苟同,随缘自适,在内心领域保持个性的纯真自然。这种独立的个性意识的觉悟,导致苏轼后期人生态度和处世行为的重大变化。他主张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在自己内心别有一种生命精神和思想自由足资寄托,不为外物所累,能在充分发挥自己个性和艺术想象力的审美创作活动中,获得心理的平衡和快乐。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追求生命的快乐和幸福是人的一种本能。快乐和幸福,除了必要的客观物质条件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自我感觉和人生态度所决定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体验过程。尽管中国士人都知道生于忧患、死于逸乐的道理,可谁也不愿意身处逆境而一直生活在忧患之中,所以一旦仕途失意,总要寻求某种自我解脱的办法。
苏轼谪贬黄州之后,一方面到佛寺道庵寻访安心法,不时焚香默坐,深自省察,通过研究佛、道两家的思想,探讨心灵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用诗人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即使是在别人看来贫困和平凡的生活中,也能寻到一种超然于物质享受之上的精神快乐和幸福。佛道的空无思想虽使他有“人生如梦”之感,有超尘出世之想,但诗人的情怀又让他将这种感想转化为突破具体时空限制的审美想象,从而将平凡的生活也艺术化了。
如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苏轼曾在黄州城东的东坡上请得了荆棘丛生的废地数十亩,自己开荒种地,甚是辛苦,但他却作《东坡八首》,想象来年的丰收能使自己“忘其劳”。这样自食其力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在一首《东坡》诗中写道: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把自己往来于坎坷不平的山坡田野的农居生活,表现得像曳杖出游一样轻松潇洒,充满了自得适意的快感。他还在东坡上修建了一间房屋,屋壁上绘上雪景,命名为雪堂。其《与言上人》书说:“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所谓“梦想”,也就是诗人的一种艺术想象,或称白日梦,能使本来没有多少意义的生活也都因注入了诗情而有意义起来。
苏轼是个喜欢饮酒的诗人,饮酒能忘忧和解闷。中国文人常借饮酒来获得某种暂时忘却痛苦的解脱,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苏轼在《次韵胡完夫》中也说:“相从杯酒形骸外,笑说平生醉梦间。”他的酒量很有限,稍饮即醉,但他常与朋友相聚宴游,在消酣耳热、半醉半醒的松弛状态下,神与物游,写下了不少风格高迈的绝妙诗文。有一次,他与客人在东坡雪堂里夜饮大醉,归家时但见江水连天、风露浩然,心意自由舒展,颇有适意之感,于是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词的上片写出了醉意朦胧中的奇妙感觉,诗人于夜深人静之时,独自伫立于门外听江声,陶醉于自然界一片永恒的静穆和流逝之中,有一种与天地并立的伟大孤独感。词的下片抒发人生感慨,想象自己能忘却世俗生活和社会政治的束缚,乘一叶小舟飘流江海,透露出对人生自由适意的无限向往。据说第二天,这首词传出去后,人们纷纷传言苏轼已挂冠服于江边,乘船长啸而去了。黄州郡守闻讯甚为惊恐,以为苏轼真的逃走了,急忙赶来查证,却见苏轼仍在家中酣睡,“鼻鼾如雷”云云(《避暑录话》)。
由这则轶闻可以看出,苏轼所追求的人生快乐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艺术想象和审美创造,并不具备可实践的行为特质。但这种白日梦般的文学创作活动,就像饮酒和做梦一样,可以给人以某种愉悦和宽慰,进而传达某种人生感受和幻觉经验,使不堪忍受和缺乏自由的现实生活变得轻松自在一些。

苏轼《致季长尺牍》

在宋代文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中,饮酒作诗与观妓听歌常常是连在一起的,醇酒和美女,成为触发作家创作灵感的媒介。如果说在政治生活中,由于有“文字狱”的威胁,文人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难免写些官样文章的话,那么在个人生活的娱乐方面,他们则享有相当的开放度,言论自由随便。朝廷不仅在各级官府配有官妓,供官员享受,而且允许士人蓄妓纳妾,所以士大夫文人在公、私酒宴上与歌妓交往厮混,也就是寻常的事了。德高望重者如欧阳修,也常与歌妓有风流韵事,作艳词传播人口。但这样一来,也易使文人作家在仕途失意之时,沉湎于歌诗、酒宴和女人,在世俗生活中寻求感官刺激和声色娱乐,于是超越名教束缚而放浪形骸,遂有名士风流和文人无行之说。
苏轼也常与歌妓打交道,参加各种有佳丽陪伴的宴饮。但在他眼里,感官的生活和性灵的生活应当是一致的,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他说自己酒量极小,见到酒杯就会醉,可却喜欢看别人饮酒, “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 (《书东皋子传后》)。也就是说,他追求的并不是感官的刺激,而是精神的满足,以达胸中浩然洒落、旷然天真的无我之境。这样才有可能随物赋形,写出风神潇洒的美文来。诗人若一味沉溺于口腹和声色的享乐中,就会为物欲所累而伤身,有如饮鸩止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自由和人生快乐可言的。
这也是苏轼对待异性的态度。他在黄州时曾出席一位豪士的家宴,席间有十余名颇有姿色的侍姬相伴。其中一位名叫“媚儿”的歌妓特别善舞,天生丽质但身体壮实,豪士要她向苏轼求诗。苏轼戏作四句云: “舞袖翩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撼半天风雨寒。” (《遁斋闲览》)表面看似颂扬,而含有调侃的意味,却无伤大雅。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的士人间被传为美谈,作为苏轼善于“戏谑”的口实,但也说明苏轼对两性关系的超然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 (《宝绘堂记》)。这样才能住心与物游时,深于情而不为情所累,始终保持一段审美距离,一片自由想象的空间。
在与异性的交往中,苏轼看重的是一种情调,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而不是感官肉欲。尽管他写了不少描写女性的诗词,或幽默,或风趣,或深婉,但绝无单纯写妇女姿色和媚态的靡靡之音。他把宋词从花间樽前的浅斟低唱的传统风格中解放了出来,一洗香艳脂粉旧习,用以诗人词的方法,写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奇思妙想,表现超然物外的情怀和自由潇洒的想象。如《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据《古今词话》所言,苏轼贬谪到惠州时,当地有一位叫“超超”的温氏女子,爱慕他的才华,常在其住所的窗外徘徊,听他吟咏诗词,一心想嫁给他。苏轼知道后,曾打算为她另择佳偶。后来苏轼渡海归来时,“超超”已死,葬于沙际,苏轼因此而作了这首词,寄托一份幽渺哀思。还在宋代就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此词是写鸿雁的咏物词,当别有寄托,不能以世俗之情来附会。确实,这篇作品语意高妙,似不食人间烟火,若要将其坐实,难免就显得“俗”气了。
苏轼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能不离世俗,又能脱俗。他在生活中并不拒绝酒色,可又能以诗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并不沉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追求一种富有诗意的充满心灵自由、不为外物所累的自然适意的人生。它能使人的生命精神摆脱社会政治和现实生活的桎梏,沉醉于艺术创作活动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精神满足。如果要说“解脱”的话,可以称为审美的解脱。残缺的人生经验升华为审美幻象之后,能化解种种现实忧患,使情感得到宣泄,生命得到补偿。这与自我个性意识觉醒之后,走向及时寻乐的纵欲和玩味感官刺激的艳情之类的享乐主义,是有很大不同的。前者更注重抒写性灵,后者难免为肉欲所支配。
尽管如此,理学家还是对文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朱熹在谈到欧阳修、苏轼等作家时说:“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是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语类》卷一三〇)在以“醇儒”自居的理学家看来,沉溺于吟诗、饮酒和与女人戏谑,都属于“玩物丧志”的表现。他们守身崇“敬”,主张“向身上做工夫”,是不赞成这一套生活作风的。

理学家所说的“做工夫”,指“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而言。这需要清心寡欲,敬存性理,而诗、酒、女人则与情欲有关,易使人胡思乱想,迷失本性。程颐就公开提出“作诗无益”的主张,认为作诗使人闲邪走作,思虑纷杂,无助于人的道德修养。他说:“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它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苏轼对理学家这种鄙视辞章、视情欲为人生大敌的态度颇不以为然,曾针对二程及其弟子那种一本正经的作风说:“何时打破这‘敬’字?”
但“敬”之一字被理学家视为“做工夫”的最吃紧处,岂能随便打破。朱熹确立了自己生平学问大旨后,继承二程理学思想的衣钵,立身严谨,言行持重,反对多作诗,反对亲近女色,怕溺于情而有伤义理,因为有时情与欲是连存一起的,很难分开。如胡铨是朱熹素所敬重的一位著名的主战派人士,南宋初年因反对秦桧议和而被贬,放逐边地十年,秦桧死后才被赦免。他归朝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既言“一醉”,当然是喝酒了,梨颊之“微涡”又是对身边侍女笑脸的描写,女人一笑起来是很有迷人的魅力的。人若醉心于此,难免“丧志”之嫌了。朱熹感叹之余,在《宿梅溪胡氏客馆观壁间题诗自警》中说:
十年江海一身轻,
归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
几人到此误平生。
意思是说在奸臣当道的恶劣政治环境中,胡铨能刚正不阿、不畏江海流放的艰难困苦,那么一定是能把功名利禄乃至生死置之度外的君子了,想不到大难不死,归来后却陷溺于儿女私情之中。可见人心中人欲之险恶和难除,胜过了外在客观环境的世路坎坷,玷污了他的一世英名。自然,这只是固执地把“立德”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的理学家的一孔之见。
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里,不仅文人作家,就是抗金英雄和正直的儒臣,喜欢饮酒狎妓的也不在少数。朱熹的好友辛弃疾的生活就很奢侈,常有歌妓相伴,朱熹肯定他在立功和立言方面的志向和才能,但又亲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的字幅相赠,也含有道德规劝的意思在。当时与朱熹相识、深知其道学性格的人,也只把他的这些道德说教视为儒者的迂腐之谈,并不在意。后来胡铨受命推荐人才时,还把朱熹作为诗人向朝廷举荐,可这又引起了朱熹的不满,因为他自己绝不愿意以诗人自立,而是立志做一个修身明道、德高望重的醇儒。
从儒者的立场来看,人生的最高追求应是学做圣人贤者,德性的完满自足是圣贤人格的可靠保证,这需要通过心学的道德实践和精神修炼工夫来实现,如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和集义养气。朱熹说他九岁时读《孟子》,即立志发奋想做“圣人”,并且“以为圣人亦易做”(《语类》卷一〇四)。但后来才发现要做圣人是很难的,这不仅由于圣人那种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难以实现,而且儒者在正心诚意的道德人格修养过程中,还要面对人心中人欲的挑战。
朱熹在隆兴元年的入都奏事失败后,归家潜心于学问,在福建建阳芦山峰顶的云谷建了三间草堂,称为“晦庵”,打算过晦居山林的淡朴生活。他还在附近的寒泉坞构筑寒泉精舍,接纳前来向他问学的士子,开始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在寒泉精舍的著书讲学生活。清心寡欲,探求圣人之道。不仅写出了一系列阐明儒家心性义理的理学著作,还通过讲学和与朋友之间的讨论,确立了“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可偏废的入圣之途和修养工夫。他在《卜居》一诗中谈及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时,说:
静有山水乐,而无身世忧。
著书俟来哲,补过希前修。
所谓“静有山水乐”,本于孔子在《论语·雍也》里所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是用君子比德的方式,对圣人道德人格所做的形容。仁者的博爱和仁慈,代表一种完满的道德人格,像巍巍山峰一样,给人以德高望重之感。将这种做人的德性推衍开来,博施济众,像水一样普遍而无私地周济万物,流到之处就有生命的成长。仁者无忧,如程颢在《识仁篇》里所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于是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获得一种超然于个人名利富贵等私欲束缚而与天地合德的快乐。
仁山智水,据二程所说,言其体动静如此,知乐者,所运用处皆乐;仁者寿,以静而寿。仁可兼知,而知不可兼仁。静有山水乐,是仁者高尚的精神境界,一种经过持敬存养的长期修炼后所具有的德性圆满而充实的心境。在朱熹看来,只要寻到了人生的这种乐处,就可以免除身世之忧,自足自乐,得到精神的满足。他根据对儒家圣人之道的这种认识和体验著书立说,寄希望于后人。如能读书明理,在反求诸己的为学过程中改过迁善、克己复礼,于是乎人欲尽处,天理流行,有希望达到前辈圣贤那种功德圆满的至善境地。
这样一种以希圣成贤为目的的书斋生活,就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来说,自然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如果真能在阅读圣贤经典的过程中明了圣人之心,进而把握天理,充实自己,做到心安理得,那么对于能识文断字的士人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德性自足的精神追求。朱熹根据儒学传统,把这称之为“为己”之学,认为这就像吃饭,是为了自己吃饱肚子,并不是要把饭桌摆在家门口,让别人知道自家有饭。他还主张下学而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并把“中庸”的“庸”解释为平常,要人们从日常生活和身边近处做起,如学事亲,学事长,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
儒学是强调社会关怀的入世哲学,儒者是从事道德教化活动的布道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让全社会的人都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重建以德治天下的社会秩序。这是理学家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所谓的修、齐、治、平,即从“反求诸己”开始,由修身逐步推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统治集团中的士以及士以上阶层的人,特别是皇帝。在封建专制社会,帝王之一心常系天下之安危,故理学家总不放弃要求天子做“圣君”的主张,并希望自己能做帝王之师,以正君心的方式来正天下人之心。
程颐在担任崇政殿说书时,就一再劝年仅十二岁的哲宗皇帝要尊儒重道,不要亲近女色和小人,不要随便摧残生物,甚至连小皇上在花园里折了一节树枝,也要板起脸来教训一番。朱熹但凡有机会上朝奏事,总要在皇帝面前讲一通正心诚意的修身大道理,想用儒家的圣人之道对君权起某种约束作用。权力需要制约,但用道统制衡政统,以道德即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其效果非常有限。因为要一般人做清心寡欲的圣人,已是比较困难的了,要让能享受很多权力和富贵的人做圣人,就更难了。哲宗皇帝对程颐的教诲本来就十分反感,后来一接触女色,就更认为还是女人好,程颐不好。宋孝宗虽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但始终对朱熹所讲的正心、诚意的大道理不感兴趣,以至于让朱熹长期赋闲在家,弃而不用。
程颐和朱熹堪称宋代的大儒了,大儒的命运尚且如此,怎能不令天下儒者有吾道难行的严重失落感,产生忧患批判意识,引发出道德的愤慨呢!
出于道德义愤的社会批判,往往流于坐而论道的清议,除了能证明儒者具有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良心外,常常无补于时政。既然如此,求人不如求己,寄希望于别人做圣人,不如先从自己做起,在为富不仁、天下无道的现实社会里,儒者所能做的只能是自己希圣希贤的理想人格塑造。或许在克己复礼的心性存养过程中,真能获得一种无私天地宽的崇高心理体验和情感愉悦,于是不为名利所动,不为情欲所牵,居陋巷而能自得其乐。尽管在实际生活里,很少有人能达到这种超凡入圣的完美境界,但对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士人来说,确实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激励作用。
更为主要的是,虽然理学家所鼓吹的圣人之道和道德人格理想不可能对君王和朝政有直接的影响,但借助政治力量将这种人生追求推行于社会,则会对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作用。程颐对宋哲宗的道德教诲毫无效果,可当统治阶级用他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教化社会下层的老百姓时,却造就出了许多“节妇”、“贞女”。朱熹正心诚意的内圣之学不为宋孝宗采纳,但随着程朱理学在社会上的流行,却成为一般中国人希圣希贤的人生信仰。
按照程朱的说法,一个人只要顺天理而行,凭良心办事,为国家社会服务尽忠心,侍奉父母尽孝心,同辈之间交往尽爱心,便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尽自己做人的本分而心安理得了。要说识仁,心安理得便是仁;要说解脱,这种心安理得便是解脱。否则便会良心不安,死也难以瞑目。这种朴实的人生信仰,对中国士人的生命价值观,以及一般百姓的做人处世态度,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儒家文化伦理精神的巨大社会作用就体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