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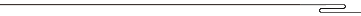
从京城来的三位电视记者向我提出,要拍陕西地方戏秦腔演出的盛况,还想拍关中民间的文化娱乐方式。我真有点犯难了,据我所知,秦腔作为西北五省尤其是陕西关中地区的名牌大戏种,至少在十年前就已经退出了西安各家剧院的舞台,包括一些大腕级的名角也都流落到适时而兴的“秦腔茶社”里去被尚有秦腔戏瘾的人点唱,原先几乎每个县都有的秦腔剧团的演员们也都流散了,说来真是令人伤感的。如我一样还喜欢听听秦腔旋律品品秦腔韵味儿的人,要想在西安某家剧院看一场名家大腕的演出,还是很难觅到机会的。至于民间的文化活动,他们三位来得也不是时候,清明都过了,民间文化娱乐集中展示的春节的气氛,早已冷却了,农民们已经从春节的欢乐和慵怡中清醒过来,进入田野进入果园开始新的一年的劳作了。然而三位远道而来的记者仍不死心,让我再想想办法,再三申述作为这个专题片的地方文化氛围和土壤是不可或缺的。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区文化馆一位搞摄影的朋友不经意间告诉我,渭河岸边的漕渠村农历三月三日适逢古庙会,有秦腔剧团的演出,有当地青年男女的秧歌表演,有邻近几个村庄的锣鼓队凑兴。遗憾的是高跷被取消了,据说出于安全的考虑,怕人群过于拥挤而摔伤了表演的人。三位北京来的年轻记者闻讯竟欢呼起来,真是应了“起得早不如赶得巧”的俗话。这样一来,关于秦腔演出和地方文化娱乐特色的东西便全部都可以得手了。
三月三日一早,我便陪三位年轻人上路了。我所存活的白鹿原下的灞河川道,其实只是渭河平原的边缘地带,南岸是古原的北坡,北岸是骊山南麓纵横起伏的丘陵或者说山岭,中间蜿蜒着以柳色愉悦缠绵过古代离人的灞河。车行不过十余公里,便驶出虽然原青岭秀却也显得狭窄的河川,进入坦荡如砥气势恢宏的渭河平原了。那情景如同从一个细杆喇叭里钻出来,进入一个四野再无遮拦的令人舒展也令人惊悸的开阔境地。这是我跟着班主任到灞桥赶考初中第一次走出灞河河川时发生的感受。这种纯粹由地理地形造成的心理感受,一直延续到今天重复到现在。每一次走出家乡灞河川道时都像钻出喇叭细杆儿,每一次回乡也就有从敞开的喇叭口里钻进细杆的感觉。我喜欢走出那个细杆儿似的河川享受无边原野的气度和舒展,也更喜欢重新进入那个狭窄的灞河河川感受南原北岭动态的生动和变幻莫测的气象,甚至包括那一份狭窄造成的拘束。钻进来拘束一段时日,钻出去舒展畅放一回,我的心理秩序和心理感受便处于某种动态的颠簸里,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
无边无际的麦子刚刚努出穗儿来。满眼都是饱满丰腴的青春的绿色,成熟的含羞带娇的女子就是这种气韵。笼罩着村庄的泡桐织成一片又一片淡紫粉红的花云。天虽然阴沉着,依然罩不住大地青春的气象。
我要到漕渠村去赶三月三日的庙会了。我的心里竟然激动起来了。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进入这种关中农民狂欢的庙会场合了。我在少小时候接受过狂欢的场景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现在的乡村庙会与我过去逛过的庙会的气氛会有什么变化吗?淡了还是浓了?三位京城来的年轻的文化人,至少怀着一种猎奇的兴奋,在我则是对一种古老仪式的温习和膜拜。大约还有一公里的路程,我听到了一声火铳的震响,像是远天云层里奔突的沉闷而又撼人心腑的雷声。火铳是一种最具声威最具张力的爆响器,它蕴聚鞭炮家族炸响时的热烈之外,便是深沉如地出的震撼。这应该是民间庆典或狂欢场合里最具煽动性的响器了。即使极阴郁寡淡的人,也会在火铳的爆响里昂起头来。
庙会是漕渠村的庙会。
漕渠村在一道浅坡下。漕渠村是个大村子,自古就是一个大村子。村里有一座古庙,供奉着佛家的一位神灵,何年建庙何年立神已经无考,所有关于庙堂的文字典籍,以及庙堂内栩栩如生的神像、精美的壁画和梁栋上的彩绘,都被后来屡屡发生的一次火过一次的“革命行动”扫荡净尽了,后来连三月三日的古庙会日也被禁止了多年。古庙能够存留下来是一个奇迹,说穿了却属无意,仅仅是贫穷的生产队需要用它做库房而没有被摧毁。有形的东西破坏或消灭十分容易,只有无形的传说却能依赖当地人的嘴巴流传下来。可以推断的是,三月三日的庙会是建庙之初就择定了的,庙会的历史也就是古庙的历史,同样是悠久古远得不能再古远悠久了。还可以推断的是,建庙立神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用意,便是崇拜,或者说是寻求和平安宁所需要的一个祈祷偶像。于是,在渭河南岸广阔的沃野和星罗棋布的大小村庄之中,便形成了以这个古庙为中心的朝拜圣地,三月三日便成为十里百村乡民寄托祈愿和狂欢的盛日。
漕渠村村庄的历史肯定比古庙的历史更为久远,这是常识而毋庸置疑的。一个漕字已注释了这个村子令人敬畏的历史。西汉王朝设都长安,为解决急骤繁荣急骤膨胀的城市吃粮问题,开凿了黄河、灞河、渭河连通长安城的一条可以浮船运粮的运河。关中人却称它为渠,可见当地人的自大和狂妄了。为了逛好漕渠村的古庙会,我专意儿查阅了《辞海》。漕渠词条下准确无虞地注释着这样的内容——
汉唐时自长安(今西安市)东至黄河的运渠。创始于西汉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 年),在大司农郑当时主持下,发卒数万人,由水工徐伯督率开凿。渠傍南山(秦岭)下,长三百余里,三年而成,漕运大便,渠下民田亦颇得灌溉之利。初以灞水为源,其后凿昆明池,又穿昆明渠使东绝灞水合于漕渠。东汉时尚可通航。北魏时已无水。隋开皇初改自长安西北引渭水为源,浚复旧渠通运,定名广通渠,但习俗仍称漕渠。唐时通时塞。天宝初陕郡太守韦坚、太和初咸阳令韩辽两度修复,壅渭水作兴成堰,傍渭东注至永丰仓(即隋开皇中广通仓,仁寿末改名)下合渭入河,规制略如隋旧。末年迁都洛阳,渠遂堙废。
哦哟!这个漕渠村的历史至少可以前推到公元前 129 年西汉元光年间。甚至可以设想元光年间开凿漕渠之前这个村子就存在不知多少年了。现在仍保存着这个村庄的子孙们用嘴传留下来的当年的盛况,西汉初年漕渠开凿始成,除了为长安城运输粮食,包括渠下村民农田的灌溉,更有各种商船通过漕渠进出长安,漕渠村当时已形成一个周转码头,南北商贾,车船互转,客店饭馆买卖铺店,成一时之盛,漕渠村成为渭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一大商埠。而古庙肯定在几百年后才形成心灵祈祷的圣地,有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限定出来一个大致的历史轮廓。
我在即将进入漕渠村的时候,感到了这个村庄古远的历史对人的威压。如果不是《辞海》作证和指点迷津,纵然在这个村子的古庙会逛过十回,我也只会以为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庙会而已,关中乡村类似的古庙会多不胜逛。从《辞海》的词条里可以看出,漕渠的开凿便形成漕渠村水陆码头的繁荣,而败毁于王朝灭亡之后的乱世;漕渠的再度浚通和漕渠村的重新繁华,又是隋和盛唐的时代,堙废的结局正好是大唐王朝的没落。这条漕渠的兴衰简史,正好注释了从西汉至唐的中国历史的起落,自然可以想见如漕渠村的乡民的饥饱寒暖了。哦!我的关中,我的渭河平原,单是保存有 2000 多年的漕渠村这个村名,就够我咀嚼不尽了。我家门前的灞水,曾经是漕渠初开时的水源,我在敬畏的同时,顿然又有了一种沟通历史沟通地域的亲近感。
漕渠村倚靠着的南面的那道浅坡,亦因漕渠而得名为漕渠坡,一道虽然低浅却声名远播的坡。狭义的漕渠村单指这个自然村,而泛义的漕渠村则指漕渠坡下的大围墙村、小围墙村、宋家村、陈家村、王家堡、米家堡、田鲍堡、陶家村、万盛堡、宋家滩等十数个大小村堡,散落在渭河南岸的平原上,绵延十余里,通称十里漕渠。站在漕渠坡头远眺起来,以稠密的村树和村树的绿叶笼罩下的房脊和屋墙组成的村庄,依次渐远,或大或小,坐落在绿色苍郁的麦田之中。我忽然想起,前年曾在临近入渭的灞河河道里,掏沙取石的农民挖出来一条大船的遗骸,距离漕渠村不过十余里,又是怎样令人顿生想象的一条谜一样的古船啊!
一位做豆腐买卖的中年农民笑嘻嘻地告诉我:“下了漕渠坡,尽是豆腐锅。”这儿盛产豆腐。漕渠坡下的豆腐远近闻名。据说这儿做成的豆腐烧了烩了不仅不烂,而且鲜嫩异香,做成臊子,浇到面条里,豆腐飘浮在上而不沉底。更具商家利益的是,同样 10 公斤黄豆在别处通常只能做出 20 公斤豆腐,在漕渠村却能产出 30 公斤,甚至 35 公斤。这个额外的利润,对于那些常年经营豆腐生意的豆腐客(主户)来说,是“天赐良水”令其窃自得意的幸事。除去公社化时代的极左政策施虐造成的萧条不计,漕渠坡下无以数计的豆腐作坊自古至今生意兴隆,现在更是许多农户赖以挣钱过日子的把稳的门路。豆腐客戏言:汉家爷江山败了,唐家爷江山也败了,爷们感念修漕渠占了农人的田地,再没啥可补偿了,就赐给咱漕渠人一井好水,让咱做豆腐过日子……爷们还是有良心的。云云。
我顿然失笑了。顿然从悠远的极富想象的漕渠村的历史烟云里清醒过来。顿然抖落了不无酸渍气味的幽思。顿然轻松地接受了这恩赐给豆腐客们的一眼好井……
农历三月三日逢着庙会的漕渠村,展示着一个纯粹属于农民的世界。
漕渠村的正街和各条小巷,现在都拥挤着农民。南北走向的公路与通往漕渠村的大路正好构成一个“丁”字,从公路的南面和北面,骑车的步行的男人女人源源不断涌入漕渠村。绝大多数尤其是中年以上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修饰,与拥挤着的同类在街巷里拥挤。在这里,没有谁会在乎衣服上的泥巴和皱褶,没有谁会讥笑一个中老年人脸上的皱纹蓬乱的头发和荒芜的胡须。女人们总是要讲究一些的,中老年女人大都换上了一身说不上时髦却干净熨帖的衣裤。偶尔可见描了眉涂了唇甚至在黑发上染出几绺黄发的女孩子,尽管努力模仿城市新潮女孩的妆饰打扮,结果仍然让人觉得还是乡村女孩。无论男人或女人,无论年龄长者或年轻后生,无论修饰打扮过或不修边幅的,他们都很兴奋,又都很从容自信,在属于他们的这个世界里,丝毫也看不到他们进入城市在霓虹灯下在红地毯上在笔挺的西装革履面前的拘束和窘迫。他们如鱼得水。他们坦荡自在。他们构成他们自己的世界。
我在这条长长的街道里和支支岔岔的小巷里随着拥挤的人流漫步。我的整个身心都在感受着这种场合里曾经十分熟悉而毕竟有点陌生了的气氛。这种由纯粹的农民汇聚起来的庞大的人群所产生出来的无形的气氛和气场,我可以联想到波澜不兴却在涌动着的大海。我自然联想到我的父辈和爷辈就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一员或一族。我向来不羞于我来自这个世界属于这个世界壮大于这个世界,说透了就是吮吸着这个世界的气氛感应着这个世界的气场生长的一族。我现在混杂在他们之中,和他们一起在漕渠村的大街小巷里拥挤,尽管我的穿着比他们中的同龄人稍微齐整一点,这个气场对我的浸淫和我本能似的融入,引发了我心里深深的激动。这一刻,我便不由自主地自我把脉,我其实还是最容易在这个世界的气场里引发心灵悸颤的。
村街两边摆着小饭摊、农具、种子、铁器、服装、搪瓷和塑料厨具餐具,以及不可或缺的老鼠药,举凡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用的一切东西,现在都摆置在村街两边供农民选购。最令我动心的是那些传统小吃摊子,仍然保存着在我少不更事时见到过的那种老式饸饹担子,几乎原样未改地摆在这里或那里。摊主抓起一把紫红色的饸饹,在案板上反复弹着,抛进敞口浅底的花边瓷碗里,用小勺挖盐用木勺撩醋用小木板挑辣椒的动作像是一种舞蹈。我小时候跟随大人去庙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坐在矮条凳上接过摊主送过来的那一碗饸饹。更奢侈一点儿,还会有临近摊位的油锅上递过来一个油饼或油糕,久久盼望赶庙会的全部目的就在这时实现了。现在,饸饹摊子和油锅前,男人和女人随意地在小条凳上坐下去,包括他们牵引着的男孩和女孩,接过饸饹或油饼油糕,吃罢了抹了嘴就又掺和到人流里去了。我的根深蒂固的关于吃饸饹的记忆就是这种形式。我后来在一些饭店的豪华餐桌上也吃到这种被学者研究出可以防癌可以降血压的所谓绿色食品,却总是尝不出庙会上摊子主人舞蹈似的动作之后的那种香味,更不必说那高得吓人的价码了。
我敢说,坐在这个摊子前品尝的男人或女人,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掏六七毛钱就可以享到的口福,城里人在大饭店却要花几乎一斗麦子的钱才能吃到一碗,准会嘲笑发了财的城里人傻得不会花钱了。
秧歌队扭过来了。这是经过费心操练的一支颇为壮观的秧歌队伍。纯一色的农家姑娘农家媳妇,还有一些堪称大娘辈儿的农家女人,一律的红绸衫绿绸裤,一律的粉红色剪花别在右耳上方的黑发里,手里舞着一律的大红绸扇子,一律的弓前殿后左扭右摆的舞步,一律的优雅,从村子中间的大街里自西向东扭过来。她们可能刚刚放下锄头或给猪呀鸡呀添过食料,换上这一身艳丽的服装就结队扭起来了。她们的公婆她们的丈夫(或未婚夫)她们的孩子,此刻就拥挤在街巷两边的人群里看她们舞蹈。她们同样具有强烈的展示自己表现自己的欲望。她们或欢欣或自信或妖媚或沉稳或娇羞的眉眼里,都透见出这种展示自己风姿的欲望。
秦腔戏的戏台搭在村庄背后的一片空地上。我是循着乐队的响声拐进小巷寻到这里的。一个用木头搭建的戏台,横额上标明长安县剧团。我一眼便可看出来,台上正在演唱着的是《铡美案》中的“杀庙”一场。这是这部堪称秦腔经典剧目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从戏剧艺术上来看也应是最为精彩的一章。一个被主子差遣来杀人的差官韩琦,一个怀着满腹委屈的乡村女人和她的一双儿女,两个人的冲突两个人的命运在一座小小的庙堂里展示得淋漓尽致波澜起伏,堪称戏剧创作上的绝妙一笔。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这部戏剧,尤其喜欢这精彩绝伦的一折。我在小小年纪初看这部戏时,大约也就只看懂了这部戏的这一折,仅只是剧情而言。从剧情的发展和剧中多个人物的命运的转化来看,“杀庙”这一折正好是这部戏的关捩。我早已从这部戏的情感里跳了出来,而进入一种艺术创造和艺术表演的欣赏中了。
台下几乎是纯一色的中老年农民。台前的人坐在自带的小凳上,两边和后边的人站立着,几乎全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清脆的梆子声紧密的扁鼓声从响亮的板胡缠绵的二胡声中跳蹦而出,敲击着在台下看戏的农民的耳膜和胸膛。他们自小就接受这种乐曲曲调的敲击。他们乐于接受这种时而强烈时而委婉时而铿锵时而绵软的旋律的抚慰。他们并不太在乎是否完全听明白了那些唱词。我也习惯于接受这种旋律的敲击和抚慰。我也不太在乎是否完全听清楚了那些唱词,主要的是接受这种旋律的敲击和抚慰。
下雨了。一把一把五颜六色的伞撑开来,在短暂的一阵骚动后,很快又平静下来。我此刻才发现与我同行的三位北京来的记者正跳上戏台的左角,支起摄像机的三角架,随之就把镜头对准了正处在杀人与自杀两难中的“韩琦”,又把镜头调整过来对着台下的农民观众。
我在来去戏场的路上看到了两顶就地搭起的巨大的帆布帐篷,离地大约一尺透着空当。有小孩子趴在地上往里边窥视。我问一位男孩看见了什么。男孩嘻嘻笑着说,光腿。从那个全封闭的神秘的帐篷里传出震人的音乐,偶尔发出一两声女子的尖叫。帐篷开口处坐着一位男青年用电喇叭做着广告,招徕诱惑围观的男女进去观赏,语言像是刀刃上的游鱼。不时有人花一块钱买票入场,几乎是纯一色的男青年。一位站在门外的小伙子和一位刚刚走出帐篷的小伙子搭话:
“里头弄啥哩?”
“跳舞哩。”
“跳啥舞哩?”
“扭尻子舞。”
“穿没穿衣裳?”
“穿着哩。”
“穿的啥衣裳?”
“不好说。”
“这有啥不好说的?”
“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不知值不值得花一块钱。”
……
搞不清这些就地支帐票价一元的演出团队来自哪里,只是可以肯定绝不是渭河岸边的人。谁家的女子要是在那神秘的帐篷里跳光腿舞,可能不需半天就臭名远扬难寻婆家了,谁家的老少都要被指指戳戳闲言碎语了。这些演出团体游牧一样流动在乡村里的集镇上,逢着某村的庙会更是赚钱的最好时机。他们和古老的秦腔对台。他们在乡村里传播什么冲击什么,他们一般是不会从“意义”上考虑的,只是更多地争取那一元钱的门票所包含的利益。愿意花一元钱进帐篷去的乡村青年,自然是为了看看扭尻子舞蹈以及除他们的媳妇之外的女人的光腿。应该说与城市里富丽堂皇超级豪华的歌舞厅里的看客们的原始目的并无二致,只是演出的水准和票价相差太远了。
现在该去听锣鼓了。锣鼓队在村委会门口摆开着架势。这是一支远路而来的锣鼓队,按习俗的说法是前来送香火的。送香火的锣鼓队的多少,成为某个庙会盛大景况的重要标志。龙旗前导,锣鼓敲打,响炮放铳,最具声望的老者端着装满紫香黄裱的木盘,浩浩荡荡又肃穆端恭地一路走去,把香火送进庙门,跪拜,点蜡,上香,焚烧黄裱,再叩头。庙门外的广场上,常常摆开十余家从各个村子赶来送香火的锣鼓队,对着敲,看看谁家能把逛会的人吸引过去的最多,自然是优胜的标志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盛景,我留下这样的印记是无法淡漠的。现在的漕渠村庙会上,只有两家锣鼓队。我觉得悦耳好听的这一家占据着村委会门前绝好的地盘。一位两腮凹进牙槽的精瘦老头握着鼓槌儿,眼睛上扣着一副茶色石头镜子,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那种既富于灵性而又有点倔强执拗的老头形象了。他不看任何人,也用不着看鼓面儿,微微偏着头发稀疏亮着红光的脑袋,两手两把溜光的木质鼓槌儿,在米黄色的牛皮鼓面儿上敲出风摆乱花一样的鼓点儿。鼓是锣鼓队的指挥和灵魂。铜钹和大小铜锣在鼓点儿的指挥下变换着交响着,一个好的鼓手常常成为一方地域里受人钦敬的名人。
这样的锣鼓队现代被命名为“长安锣鼓”。流行在秦岭北边渭河平原的锣鼓曲谱源自唐代,被现在的一些搞民间文化的音乐工作者发掘整理出来,颇多抢救国宝的意味。在我的印象里,整个关中稍微像样的村庄都有一支锣鼓队,诸如我的生地蒋村新中国成立时不过 30 余户的小村子,同样有一套锣鼓响器,这是整个村子在合作化以前唯一的公有财产,靠一家一户捐赠的粮食置备起来的。每到逢年过节,村里的锣鼓队就造起声势来,把整个村庄都震动起来颠簸起来,热烈的锣鼓声灌进每一座或堂皇或破旧的屋院,把一年的劳累和忧愁都抖落到气势磅礴震天撼地热烈欢快的锣鼓声中了。可以肯定的是,乡村锣鼓这种民间音乐,是我平生里接受的第一支旋律。岂止是我,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乡村人,出生后焐在火炕被窝里的第一个春节到来时,就被这种强烈震撼的锣鼓声震得在被窝里哭叫起来,锣鼓的敲击声响从此就注入血液。
现在在漕渠村村委会门前演出的这支锣鼓队,是一支真正的民间锣鼓队,除那位显示着执拗自信的鼓手老头儿,还有四五个抓着脸盆一样大小的铜钹(当地俗称家伙),五六个左手手指上挂着碗口大的铜锣右手执着短粗锣槌儿的青壮年农民。令我遗憾的是,这支精当的锣鼓队里缺少至少两三个敲那种比蛋糕稍大一点的铜锣的角色。缺少小铜锣而突出了大铜锣,显然是一支以瓷硬为风格的锣鼓队,而那种以大小铜锣为主体的锣鼓队的风格被称为“酥”。酥在演出风格上的突出特点是细述婉转。然而这个缺少了小铜锣作点缀作调节的锣鼓队,敲出一曲又一曲传统的也许真是自唐代流传下来的锣鼓曲调。这样原始的曲调在我尚未识字之前就听过许多回了,时而如瀑布自天覆倾而下,时而如清溪般流淌;时而如密不透矢的暴风骤雨,时而如疏林秀风;时而如洪流激浪一泻千里,时而如蜻蜓点水微风拂柳。在这样急骤转换的奏鸣里,我的心时而被颠得狂跳,时而又被抚慰,锣鼓的声浪像一只魔女妖精的手,把人撩拨得神魂激荡而又迷离沉醉。我又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锣鼓的记忆和感受,依然保持着那份敏感那份融洽而没有隔膜和冷漠。也许应该是我的生命之乐。
我沉浸在锣鼓声中。这一帮由老汉壮年和青年组成的锣鼓队,没有化妆没有统一服饰,也没有由专业乐界行家导演训练出来的统一动作和表情,他们敲到得意时,有的咬牙有的瞪眼有的摇头晃脑,各见性情。常常使我产生错觉,把他们的脸孔和我儿时印象中的我村的某个人重叠起来混淆起来。
我沉浸其中,我已经多年没有接受这种生命之乐的冲撞和震颤了。人的五脏六腑也许需要这种纯属民间的乐器来一番冲撞和洗涮的。无论如何,在民间锣鼓的乐曲里,我心中沉积着的污泥和浊水,顿然扫荡清除了,获得的是清爽和轻松,好继续上路。
我还会再去寻求这种纯粹民间的锣鼓,为生命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