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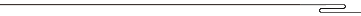
按照当今已经注意营养分析的人们的观点,麦饭是属于真正的绿色食物。
我自小就有幸享用这种绿色食物。不过不是具备科学的超前消费的意识,恰恰是贫穷导致的以野菜代粮食的果腹本能。
早春里,山坡背阴处的积雪尚未退尽消去,向阳坡地上的苜蓿已经从地皮上努出嫩芽来。我掐苜蓿,常和同龄的男女孩子结伙,从山坡上的这一块苜蓿地奔到另一块苜蓿地,这是幼年记忆里最愉快的劳动。
苜蓿芽儿用水淘了,拌上面粉,揉、搅、搓、抖均匀,摊在木屉上,放在锅里蒸熟。出锅后,用熟油拌了,便用碗盛着,整碗整碗地吃,拌着一碗玉米糁子熬煮的稀饭,可以省下一个两个馍来。母亲似乎从我有记忆能力时就擅长麦饭技艺。她做得从容不迫,干、湿、软、硬总是恰到好处。我最关心的是,拌到苜蓿里的面粉是麦子面儿还是玉米面儿。麦子面儿俗称白面儿,拌就的麦饭软绵可口,玉米面拌成的麦饭就相去甚远了。母亲往往会说,白面断顿了,得用玉米面儿拌;你甭不高兴,我会多浇点熟油。我从解知人言便开始习惯粗食淡饭,从来不敢也不会有奢望寄予;从来不会要吃什么或想吃什么,而是习惯于母亲做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道理也没有解释,贫穷造就的吃食的贫乏和单调是不容选择或挑剔的,也不宽容娇气和任性。
麦子面拌就的头茬苜蓿蒸成的麦饭,再拌进熟油,那种绵长的香味的记忆是无法泯灭的。
按照家乡的风俗禁忌,清明是掐摘苜蓿的终结之日。清明之前,任何人家种植的苜蓿,尽可以由人去掐去摘,主人均是一种宽容和大度。清明一过,便不能再去任何人家的苜蓿地采掐了,苜蓿要作为饲草生长了。
苜蓿之后,我们便盼着槐花。山坡和场边的槐花放白的时候,我便用早已备齐的木钩挑着竹笼去采捋槐花了。
槐花开放的时候,村巷屋院都是香气充溢着。槐花蒸成的麦饭,另有一番香味,似乎比苜蓿麦饭更可口。这个季节往往很短暂,家家男女端到街巷里来的饭碗里,多是槐花麦饭。
按照今天已经开始青睐绿色食品的先行者们的现代营养意识,我便可以耍一把阿Q式的骄傲,我们祖宗比你阔多了,他们早早都以苜蓿槐花为食了。
到了难忘的 20 世纪 60 年代,被史称“三年困难”的 20世纪 60 年代初,家乡的原坡和河川里一切不含毒汁的野菜和野草,包括某些树叶,统统都被大人小孩挖、掐、拔、摘、捋回家去,拌以少许面粉或麸皮,蒸了,食了,已经无油可拌。这样的麦饭已成为主食,成为填充肚腹的坐庄食物。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别无选择,漂亮的脸蛋儿和丑陋的黑脸也无法挑剔,都只能赖此物充饥,延续生命。老人脸黄了肿了,年轻人也黄了肿了,小孩子黄了肿了,漂亮的脸蛋儿黄了肿了时尤为令人叹惋。看来,这种纯粹以绿色野菜野草为食物的实践,却显示出残酷的结果,提醒今天那些以绿色食物为时尚为时髦的先生太太们切勿矫枉过正,以免损害贵体。
近日和朋友到西安大雁塔下的一家陕北风味饭馆就餐,一道“洋芋叉叉”的菜令人费解。吃了一口便尝出味来,便大胆探问,可是洋芋麦饭?延安籍的女老板笑答,对。关中叫麦饭,陕北叫洋芋叉叉。把洋芋擦成丝,拌以上等白面,蒸熟,拌油,仍然沿袭民间如我母亲一样的农家主妇的操作规程。陕北盛产洋芋,用洋芋做成麦饭,原也是以菜代粮,变换一种花样,和关中的麦饭无本质差别。不过,现在由服务生用瓷盘端到餐桌上来的洋芋叉叉或者说洋芋麦饭,却是一道菜,一种商品,一种卖价不小的绿色食品,城里人乐于掏腰包并赞赏不绝的超前保健食品了。
家乡的原野上,苜蓿种植已经大大减少。已经稀罕的苜蓿地,不容许任何人涉足动手掐采。传统的乡俗已经断止。主人一茬接着一茬掐采下苜蓿芽来,用袋装了,用车载了,送到城里的蔬菜市场,卖一把好钱。乡俗断止了,日子好过了,这是现代生活法则。
母亲的苜蓿麦饭槐花麦饭已经成为遥远而又温馨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