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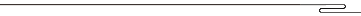
头一回听到骡马市,竟然很惊讶。原因很直白,城里怎么会有以骡马命名的地方呢?问父亲,父亲说不清,只说人家就都那么叫着。问村里大人,进过骡马市或没去过骡马市的人也都说不清渊源,也如父亲一样回答,自古就这么叫着,甚至责怪我多问了不该问的事。
我便记住了骡马市。这肯定是我在尚未进入西安之前,记住的第一条街道的名字。作为古城西安的象征性标志性建筑钟楼和鼓楼,我听大人们神秘地描述过多少次,依然是无法实现具体想象的事,还有许多街巷的名字,听过多遍也不见记住,唯独这个骡马市,听一回就记住了。如果谁要考问我幼年关于西安的知识,除了钟鼓楼,就是骡马市了。这个道理很简单,生在西安郊区的我,只看见各种树木和野草,各种庄稼的禾苗也辨认无误,还有一座挨着一座破旧的厦屋,一院连一院的土打围墙,怎么想象钟楼和鼓楼的雄伟奇观呢?晴天铺满黄土,雨天满路泥泞,如何想象西安大街小巷的繁华,以及那些稀奇古怪乃至拗口的名字呢?只有骡子和马,让我不需费力不需想象就能有一个十分具体的形象。我在惊讶城市怎么会有以骡马命名的街区的同时,首先感到的是这座神秘城市与我的生存形态的亲近感,骡子和马,便一遍成记。
我第一次走进西安也走进了骡马市,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进城念初中的事。骡马市离钟楼不远,父亲领我观看了令人目眩的钟楼之后,就走进了骡马市。一街两边都是小铺小店小饭馆,卖什么杂货都已无记,也不大在意。只记得在乡下人口边说得最多的戏园子“三意社”那个门楼。父亲是个戏迷,在那儿徘徊良久,还看了看午场演出的戏牌,终于舍不得掏二毛钱的站票钱,引我坐在旁边一家卖大碗茶的地摊前,花四分钱买了两大碗沙果叶茶水,吃了自家带的馍,走时还继续给我兴致勃勃地说着大名角苏育民主演《滚钉板》时,怎样脱光上衣在倒钉着钉子的木板上翻身打滚,吓得我毛骨悚然。
还有关于骡马市的一次记忆,说来有点惊心动魄。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一年,即1963年冬天,我已是乡村小学教师,期考完毕,工会犒赏教师,到西安做一天一夜旅行。先天后晌坐公交车进城,在骡马市“三意社”看一场秦腔,仍然是最便宜的站票。夜住骡马市口西安最豪华的西北旅社,洗一次澡,第二天参观两个景点,吃一碗羊肉泡馍,大家就充分感受了作为人民教师的光荣和幸福了。唯一令我不愉快乃至惊心动魄的记忆发生在次日早晨。走出西北旅社走到骡马市口,有一个人推着人力车载着用棉布包裹保温的大号铁锅,叫卖甑糕。数九天的清早,街上只有零星来往的人走动。我已经闻到那铁锅弥漫到空气里的甑糕的香气儿,那是被激活了的久违的极其美好的味觉记忆。我的腿就停住了,几乎同时就下定决心,吃甑糕,哪怕日后挨一顿饿也在所不惜。我交了钱也交了粮票。主人用一个精巧晶亮的小切刀——切甑糕的专用刀——很熟练地操作起来,小切刀在他手里像是舞蹈动作,一刀从锅边切下一片,一刀从锅心削下一片,一刀切下来糯米,又一刀刮来紫色的枣泥,全都叠加堆积在一张花斑的苇叶上。一手交给我的同时,另一只手送上来筷子。我刚刚把包着甑糕的苇叶接到手中,尚未动筷子,满嘴里都渗出口水来。正当此时,“啪”的一声,我尚弄不清发生了什么,苇叶上的甑糕一扫而光,眼见一个半大孩子双手掬着甑糕窜逃而去。我吓得腿都软了,才想到刚才那一瞬间所发生的迅捷动作,一只手从苇叶刮过去,另一只手就接住了刮下来的甑糕。动作之熟练之准确之干净利索,非久练不能做到。我把刚接到手的筷子还给主人,把那张苇叶也交给他回收,谢拒了卖主要我再买一份的好意,离开了。卖主毫不惊奇,大约早已司空见惯。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诸多至今依然不泯的生活记忆里,吃甑糕的这一幕尤为鲜活。在骡马市街口。
朋友李建宁把一册装潢精美的《骡马市商业步行街图像》给我打开,看着主街次街内街外街回廊街漂亮的景观,一座座既有汉唐风韵又兼欧美风味的建筑,令我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心向往之。
西安在变。其速度和规模虽然比不得沿海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然而西安确实在变化,愈变愈美。一条大街一条小巷,老城区与新开发区,老建筑物的修复和新建筑群的崛起,一行花树一块草皮一种新颖的街灯,都使这座同这个民族古老文明血脉相承的城市逐渐呈现出独有的风姿。作为这个城市终身的市民,我难得排除地域性的亲近感和对它变化的欣然。骡马市几乎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是古老西安从汉唐承继下来的无数街区坊巷变化的一个缩影。我最感动的是“骡马市”这个名字,从明朝形成延续到清朝,都在繁荣着从事骡马交易的特殊街坊,把农业文明时代的城市和乡村的脐带式关系,以一个骡马市融会贯通了。
无论西安日后会靓丽到何种状态,无论这个骡马市会靓丽到何种形态,只要保存这个名字,就保存了一种历史的意蕴,一种历史演进过程中独有的风情和韵味,而没有谁会较真,真要牵出一头骡子或一匹马来。
哦!骡马市。永远的骡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