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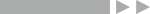
如果仅从表面上考察现实主义小说的两重因素,那么会发现它近乎一个矛盾性的概念:“小说”(Fiction)意旨着一个想象的世界,它产生于作家积极的创造力实践;但同时,现实主义宣称在文本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对应性,这又暗示着对作家创造者身份的抹杀。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表明,概念的含混并非一个语言学事故。尤其是在现实主义发展的初期,小说总是以作者否认故事中他本人的介入为开端,小说被当做是“见闻录”(撒姆尔·理查逊:《帕米拉》)、记者的报道(贝恩夫人:《奥奴诺克》)或是真实的谈话录(笛福:《莫尔·福兰德斯》)呈现给读者。作者自称只是作品的编辑者或出版者,但永远不会是故事的创造者。这样一来,在作品与作者之间就出现了一种距离,它赋予了作品的某种高度的自主性和合法性(当然也为作家开脱了散播流言蜚语的恶名)。随着公众阅读日趋成熟,作家自我推卸的伎俩已变成一种惯例,只能愚弄最天真的人。然而,作为一种形式因素,它还存留着,因为它反映了现实主义小说根本的歧义、它与现实和虚构的暧昧关联。其实雷纳德·J.戴维斯(Lennard J.Davis)已将早期英语小说称为“事实的虚构”,它“既是对世界的报导又是对报导的创造性模拟”。 [1] 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一条普遍的规律:现实主义对纯粹指涉性的追求,涉及到对作品发生中作家想象力作用的削减,即:否认作品的虚构性。这一追求有点口是心非,聪明的读者从不会信以为真,但也恰恰是作品在“真实”临界线上含混的位置,为他们带来了愉悦。
现实主义小说所设定的距离,不仅存在于文本与作家之间,也存在于单个的文本与所有先在的文学之间。在现实主义真实性诉求当中,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它假定了作品直接产生于对生活的描摹,而非源于其他作品。这意味着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不但要否认以作家想象力为起点,还要否认它对传统文学范本的借鉴;它必须宣扬一种基本的独创性。这一要求同样有点言不由衷;实际上,读者在进入一部小说的时候总会带着对该文本的确定期待,而且也会在个体创作中发现前人的痕迹。但是,现实主义者常常采用讽刺和戏仿的方式,以暴露文本之中对文学传统的挪用。譬如,被誉为第一部真正的小说的《堂吉诃德》,就几乎可以看作对骑士罗曼司的滑稽模仿。而许多后世作品更是明确地以颠覆那些“非现实”的文学所制造的虚假偶像为己任(例如,包法利夫人就因模仿她所阅读的小说中的冒险生活而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哈里·列文(Harry Levin)曾指出:现实主义“小说并不是靠掩饰而是靠展示艺术手段来贴近真实的”。 [2] 饶有意味的是,谴责其他文类的矫揉造作恰恰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诉求的基础。而戏拟与讽刺间的亲和性却显然表明了一种高度的艺术自觉:现实主义在表面上只关注外部世界,但随后的创作却远非如此纯真。但是,至少是在理论层面,现实主义打破了文学与想象和传统的关联,在作家的精密的观察之中找到了自己的起点。
现实主义小说的经典形象是一面镜子,虽然依照通常的理解,它隐喻了如何将外部现实直接转化成小说素材,但更为有趣的是,它或许还向我们昭示出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批判自我的生成以及主体因素间接性的表现。依照这种隐喻,小说仅仅是一面漠然悬起的镜子;在司汤达著名的《红与黑》中,小说被比作“道路上移动的镜子”,良莠不分地映射着路上的一切。 [3] 但是,一个镜像所能标识的至多是真实世界的可疑片断,随着观察者视野的推移而变化。因而,该隐喻也说明了对世界的人工再现必须从一个确定的视角开始。这种“视角主义”,接近现实主义概念中的“焦点”(或“视点”)和“主体性客观”,是现代西方特殊的哲学及美学立场。中世纪与非西方的艺术传统一般准许创造性的想象自由地来往于文化形象的总体空间之中。比如,中国传统的“赋”就是一种铺张的“描写”形式,它从各种可能的角度逼近描述的对象,精心刻画,引譬连类。然而,现实主义描写,却将对象嵌入与观察主体的特殊关联之中,严格地受制于时空的限制。如果作家越雷池一步,就会破坏镜像,瓦解批判的观察者的权威。
现实主义对观物之客观立场的强调与这样一种启蒙观念息息相关,即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实践从迷信和偏见中解放自身。诚如伽达默尔所言,启蒙主义根本的“偏见”(或“前判断”)是对偏见本身的偏见。
 作为一种认识论实践,现实主义小说可以看作是这样一项探索:探索意识如何将外部现实转化为语言结构,以及如何借助偏见理解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探索外部现实如何纠正、重设这些偏见。然而,观察者之所以发现自身的独立性,感受到自由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抽身而出,与传统对峙。现实主义所假设的对外部世界的冷静观察,由此便显现为一种内在的搏斗,使思想摆脱对传统的依赖。正如主体能够通过某种批判的姿态确立自身的完整,现实主义真实性诉求对文化偏见的批判也是如此。在作品当中,它自我呈现为一种“非神秘”化的活动:现实主义方案往往戏剧性地表现了对陈腐的表象、欲望或理想的失望。作为失望的动因,客观真实的世界能够有力地揭穿文化的偏见,从而使精神摆脱传统的束缚。在此过程中,精神被分为两个部分:理性的客观因素与一种超越历史的洞察相结合(或者是马克思-黑格尔传统中的一种对“更高历史阶段”的充分觉悟);与之相对的主观因素则沿袭了非理性的传统积习。由此,当情感和偏见,这些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主观的因素遭到贬斥的时候,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便不无矛盾地拔高了主体的地位(作为一个独立不羁的观察者)。
作为一种认识论实践,现实主义小说可以看作是这样一项探索:探索意识如何将外部现实转化为语言结构,以及如何借助偏见理解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探索外部现实如何纠正、重设这些偏见。然而,观察者之所以发现自身的独立性,感受到自由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抽身而出,与传统对峙。现实主义所假设的对外部世界的冷静观察,由此便显现为一种内在的搏斗,使思想摆脱对传统的依赖。正如主体能够通过某种批判的姿态确立自身的完整,现实主义真实性诉求对文化偏见的批判也是如此。在作品当中,它自我呈现为一种“非神秘”化的活动:现实主义方案往往戏剧性地表现了对陈腐的表象、欲望或理想的失望。作为失望的动因,客观真实的世界能够有力地揭穿文化的偏见,从而使精神摆脱传统的束缚。在此过程中,精神被分为两个部分:理性的客观因素与一种超越历史的洞察相结合(或者是马克思-黑格尔传统中的一种对“更高历史阶段”的充分觉悟);与之相对的主观因素则沿袭了非理性的传统积习。由此,当情感和偏见,这些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主观的因素遭到贬斥的时候,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便不无矛盾地拔高了主体的地位(作为一个独立不羁的观察者)。
作家对创作过程中的主观介入的否认,却使文学的人工性特征凸显出来,使它与作品产生的背景分离开来,并赋予它一种独立的品质。作为一件艺术品,作品可能而且最终会被放置在与它声称所要描摹的现实的等级性关系中去比较、评价。但如此一来,这件艺术品便十分可疑了,因为无论它多么精确地描摹了现实,它也永远不能取代现实。柏拉图对艺术的质疑激起了后世西方人为诗歌进行辩护,它就产生于这种艺术模仿真实世界的基本感受。而中国传统美学,从未发展过这种支配了西方美学讨论的模仿理论,
[4]
也从未从这个角度怀疑艺术的目的。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件文学作品并不是自然世界的摹本,而只是自然及社会世界背后诸多基本呈现方式的一种而已。这种观点最为鲜明地表露于16世纪理论家刘勰的文章当中,他依据“文”一词的多义性,它的含义可以是“天文”(pattern)也可以是“人文”(writing),以一种简洁的迂回论证解释了文学的起源,将文学与宇宙的基本秩序相联。“文”(“天文”)是“与天地并生”的,而宇宙之间惟有人乃性灵所钟,是天地之心或天地之灵。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自然之道”也显现于语言,而借助语言,“文”(“人文”)也随之出现。
 斯蒂芬·欧文在讨论这一段文字时指出,对于刘勰来说,“文学作为一种终极的、圆满实现的形式,是宇宙进程的显现——而作家不是‘再现’外部世界载体,他实际上只是通往即将到来的世界之终极阶段的中介。”
[5]
斯蒂芬·欧文在讨论这一段文字时指出,对于刘勰来说,“文学作为一种终极的、圆满实现的形式,是宇宙进程的显现——而作家不是‘再现’外部世界载体,他实际上只是通往即将到来的世界之终极阶段的中介。”
[5]
刘勰的论断表明,“天文/人文”在某种意义上先于并且源于人的意识,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写作的发生观念。事实上,他反复论证的是写作与意识间的一种等同性,在下面一段话中刘勰将其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认为文“实天地之心”。
 作为人类意识以及天地之文的外化,文学绝不能如柏拉图所言及的那样,被简化为真实世界的影子。它的本体上的充足性不容置疑。因而,中国美学家们对艺术客体与真实世界间的模仿关系缺乏兴趣,他们关注的是艺术的感染及训诫能力,这种能力感人至深,既能使读者与作品所激发的情感世界发生共鸣,又能向他们揭示出作为自然与社会世界之奠基的原则体系。然而,中国人对于作家个体所经验的创作过程并非无动于衷:在中国美学理论中,文学表现论(凝聚在永远说不尽的格言“诗言志”中)的影响其实十分深远(从古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正如我将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
作为人类意识以及天地之文的外化,文学绝不能如柏拉图所言及的那样,被简化为真实世界的影子。它的本体上的充足性不容置疑。因而,中国美学家们对艺术客体与真实世界间的模仿关系缺乏兴趣,他们关注的是艺术的感染及训诫能力,这种能力感人至深,既能使读者与作品所激发的情感世界发生共鸣,又能向他们揭示出作为自然与社会世界之奠基的原则体系。然而,中国人对于作家个体所经验的创作过程并非无动于衷:在中国美学理论中,文学表现论(凝聚在永远说不尽的格言“诗言志”中)的影响其实十分深远(从古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正如我将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
 但即便是在表现论中,作家作为创造者的自主性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更多地被看作是自然之文与社会之文得以彰显自身的媒介或通道。
但即便是在表现论中,作家作为创造者的自主性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更多地被看作是自然之文与社会之文得以彰显自身的媒介或通道。
如果中国传统的确提供了一种考察艺术作品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维框架的话,那么它是来自新儒家的“格物”之说。在讨论中国科技史时,它常常被引述为中国哲学中与将个体看作客观观察者的启蒙观念最为相近的学说。
[6]
曾对“以物观物”和“以我观物”作出区分的哲学家邵雍,较早阐发了“格物”之说,在他那里这一概念的确类似于西方的唯理主义。但如果深入检讨,可以明显地发现,邵雍不是将物质世界当做是分析性观察的对象,而是以一种冥想的方式将其纳入了自我教养的过程当中:观物“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
 在外部世界的客体当中发现天理,是为了帮助主体反思性地洞察天理如何运作于自身之中,并从褊狭的、私人的“情”中提炼出普遍恒常的“性”。在其后的新儒家思想当中,西方的科学式观物概念与“格物”之说的亲和性似乎更加脆弱。程颐和朱熹已逐渐将“格物”之中包含的客观精神,从对自然及外部世界的探索,引向了伦理的玄想和思辨。而其后的王阳明则反对心外之物中存有天理的假设,他将“格物”修正为一个严格的伦理概念“致良知”。
在外部世界的客体当中发现天理,是为了帮助主体反思性地洞察天理如何运作于自身之中,并从褊狭的、私人的“情”中提炼出普遍恒常的“性”。在其后的新儒家思想当中,西方的科学式观物概念与“格物”之说的亲和性似乎更加脆弱。程颐和朱熹已逐渐将“格物”之中包含的客观精神,从对自然及外部世界的探索,引向了伦理的玄想和思辨。而其后的王阳明则反对心外之物中存有天理的假设,他将“格物”修正为一个严格的伦理概念“致良知”。
虽然对客观性或现实主义时而也有所承诺,但“格物”概念在文学上的应用,如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一类,同样贯穿着这种道德关怀。金圣叹将施耐庵对典型人物的出色塑造归之于他多年来对人事的冷静考察,但他还说道:“格物为法,以忠恕为门”
 。通过实践这些美德,一个人就能够认识万物,即便是最卑微的窃贼或贱民,也能不由自主地表达它们存在的内在要求。如果这种存在,这种生物的本性能够被捕捉到,那么艺术家完成的作品就会有一种丰满的真实感。在金看来,较之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观察,对事物及存在的精神品质的追寻显然要更为重要。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批评的方式,金圣叹首先考虑的不是作品一旦完成,其内容与真实世界的关系,而是先于创作的作家与世界之间的互动。中西美学间的这种差异还显现于“镜子”的隐喻当中:在中国文学中,“镜子”从未暗示作品对真实世界的反映,它隐喻的是一种精神境界,通过沉思默想,作家使自我从主体性的遮蔽中摆脱出来,从而向“道”自由地敞开。
。通过实践这些美德,一个人就能够认识万物,即便是最卑微的窃贼或贱民,也能不由自主地表达它们存在的内在要求。如果这种存在,这种生物的本性能够被捕捉到,那么艺术家完成的作品就会有一种丰满的真实感。在金看来,较之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观察,对事物及存在的精神品质的追寻显然要更为重要。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批评的方式,金圣叹首先考虑的不是作品一旦完成,其内容与真实世界的关系,而是先于创作的作家与世界之间的互动。中西美学间的这种差异还显现于“镜子”的隐喻当中:在中国文学中,“镜子”从未暗示作品对真实世界的反映,它隐喻的是一种精神境界,通过沉思默想,作家使自我从主体性的遮蔽中摆脱出来,从而向“道”自由地敞开。

[1] 雷纳德·J.戴维斯(Lennard J.Davis):《事实的虚构》( Factual Fictions ),第212页,戴维斯在一定程度上讨论了早期英语小说中存在的“作者否认”现象,见第6、8、9章。
[2] 哈里·列文(Harry Levin):《号角之门》( The Gates of Horn ),第51页。
[3] 司汤达:《红与黑》( Paris:Editions Gallimard ,1972),第414页。
[4] 刘若愚(James,J.Y.Liu)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讨论了文学模仿论在中国的缺乏,第49—73页。维廉姆·F.杜邦斯(William F.Touponce)为该书写了一篇挑剔的书评:《刍狗: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中模仿问题的解构阅读》(Straw Dogs:A Deconstructive Reading of the Problem of Mimesis in James Liu’s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淡江评论》( Tamkang Review ,no.1[Summer 1981]:pp.359-390),在文中,他对刘模仿论在中国文学思想中并不重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他混淆了雷内·吉拉德(René Girard)基本上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模仿论(他认为牺牲模仿了作为所有文化基础的原始暴力行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模仿论(将诗歌当做现象世界的模拟)。无疑,这二者之间确实有联系(吉拉德显然认为自己的理论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但是,这种联系应当得到仔细的说明。杜邦斯最后也不得不作出缓和的让步,承认:“或许可以说,在中国没有发展出文学模仿的理论。”而这正是刘的观点。
[5] 斯蒂芬·欧文:《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第20页。浦安迪(Andrew H.Plaks)《中国叙事理论批评探考》(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一文也讨论了这一段论述及其与小说发展的关联,见《中国叙事学》( Chinese Narrative ),第311—316页。
[6] “格物”一词出自《大学》,是哲学探讨关注的对象:它有多种含义,包括“抵抗或拒绝事物”、“纠正事物”、“度量事物”、“即近事物”等,其中最后一种理解为新儒家所接受,意为“探索事物的基本原理”。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手册》(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第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