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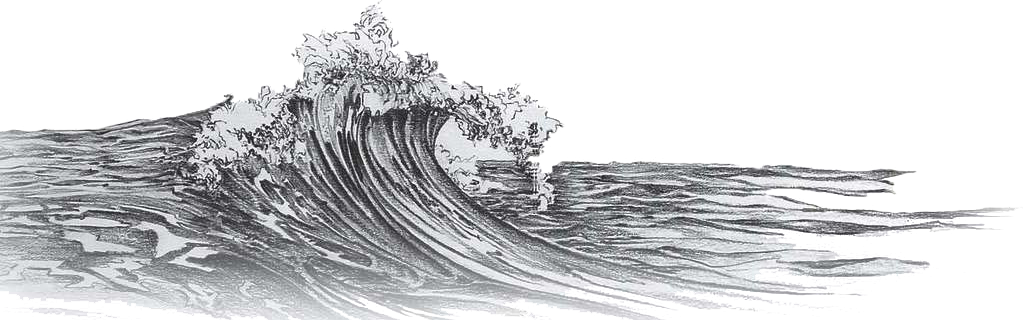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一场个人剧变或危机,有的人还不止经历一场。有些危机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化解,有些则不行。同样地,国家也会遭遇危机,有些危机可通过国家自身的变革而顺利解决,有些则不行。心理治疗师积累了大量关于解决个人危机的案例和见闻,并试图从中找寻规律。那么,这些结论可否帮助我们找到化解国家危机之道?
在本书的开端,我打算通过讲述自己经历的两个故事来解释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据说,孩子大概从4岁开始记事,当然,有关特定事件的记忆能够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的情况并不特殊。我最早的记忆是5岁生日后不久发生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尽管我很幸运没有亲历这场大火,但从我那做外科医生的父亲口中,我间接地体验了这一可怕的事件。
1942年11月28日,人潮涌动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突发一场大火。火情迅疾,俱乐部唯一的逃生出口却被堵住。最终,492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还有数百人因窒息、吸入烟雾、被踩踏而受伤或灼伤。波士顿的医疗系统任务艰巨——需要治疗的不仅有那些在大火中遭受身体伤害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心灵受到重创的人。其中有遇难者的亲属,他们因失去至亲而悲痛欲绝,还有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被大火吞噬,自己在幸存的内疚中辗转反侧。十点一刻以前,人们一如往常地相约在椰林俱乐部,庆祝感恩节周末,观看橄榄球比赛,或者是拥抱休假归家的军人。时钟敲响11下,欢声笑语戛然而止,只残留冰冷的躯体,遇难者的亲属和幸存者的生活就此天翻地覆,他们预期的生活脱离了轨道。那些遇难者的亲属为亲人死去自己却活着而感到羞愧,他们失去了在自我身份认同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人。这场大火动摇了幸存者以及其余的波士顿人(包括当时只有5岁的我)对公正世界的信念。那些受到惩罚的人并非顽劣之辈,更不是恶人:他们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无故丧生的平凡人。
有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终其一生被伤痛折磨。有少部分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经历最初几周的极度痛苦后,开始逐渐进入一个缓慢的恢复阶段,他们从最初的不愿接受现实,到重新审视自己,尝试重返正轨,然后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并没有全然崩塌。许多在那场大火中失去配偶的人后来再婚了。不过,数十年后,哪怕是对于恢复得最好的人而言,在椰林俱乐部大火中涅槃而来的全新身份和火灾发生前旧的自我也只能“马赛克式”地共存。在本书中,我们会多次使用“马赛克”这个比喻,这是一种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况。
椰林俱乐部大火提供了个人危机的一个极端案例。我之所以称其为极端,仅仅是因为这场灾难同时降临在多个人身上。事实上,这场灾难中受害者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引发了另一种危机,导致心理治疗领域亟须找到新的解决路径(我将在第一章谈到)。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中会直接经历危机,或者间接地体验亲属或朋友所经历的危机。无论是只有一个受害者的危机,还是导致多达492人丧生的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对于受害者而言,它们带来的痛苦同样沉重。
我们再举一个国家危机的例子做比较。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旅居英国。当时,我和我的英国朋友都未全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处在一场缓慢的危机之中。曾经的英国独领风骚,科技水平领先世界,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其国人为之自豪。彼时,英国人仍沉湎于往日的荣光——坐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舰队、数之不尽的财富,还有辽阔的帝国版图。不幸的是,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版图范围逐渐缩减,国家实力式微,英国对自己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感到迷茫,并且不知如何解决长期存在的阶级差异和骤然袭来的移民浪潮。1956—1961年,这一昔日巨人迎来了紧要关头:它解散了余下的舰队,经历了首次种族暴乱,其在非洲的殖民地陆续独立,苏伊士运河危机更是揭露了一个屈辱的事实——英国已不再是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强权了。我的英国朋友很努力地去理解这些事件,并试图把它们解释给我这个外乡人听。英国民众和政治家关于自己国家身份和角色的讨论在种种冲击中愈演愈烈。
60年之后的今天,英国成为新我和旧我共存的“马赛克式”国家,它褪下了往日帝国的华服,换上了多元社会的新衣。英国通过高水平的福利制度和高质量的公立教育体系来缩小不同社会阶级间的差异,但它曾享誉世界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再未能恢复如初,在处理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关系方面(“脱欧”事件)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但英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富裕的6个国家之一,仍然在象征性的君主制下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并且在科技领域名列世界前茅,还继续使用英镑而不是欧元作为国家货币。
这两个故事呈现了本书的主题。个人、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比如个人遭遇离婚、丧偶,或者是一国受到他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来自内部压力,比如个人身体不适,或国家内部出现纷争战乱。不管应对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地进行改变,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这里的关键词是“选择性”。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过往的一切,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变。在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直面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一方面,他们必须判断出自身的哪些方面仍然适用,从而将其保留。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鼓足勇气识别那些必须改变的方面。这就要求个人或国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条件的应对危机的新方法。与此同时,他们要划清界限,明确那些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绝不可以改变的元素。
以上就是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的相似之处,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一场“危机”?简单来说,英文中的“crisis”(危机)一词来自希腊语中的名词“krisis”和动词“krino”,它们有以下几种解释:“使分开”“做决定”“加以区分”“转折点”。因此,我们可以把危机看成一个紧要关头、一个转折点。和“大多数”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前后的情况会“极其”不同。我之所以要强调“大多数”“时刻”“极其”这几个词,是因为要决定一个转折点是“危机”,还是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流光或者是循序渐进的自然进化过程,我们要实际地考虑这一时刻应当有多么短暂,前后情况的变化应当有多么剧烈,以及和大部分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应当有多么罕见。
转折点意味着挑战。当以往的处理方法不再适用于应对新挑战时,危机感会使我们产生压力,这种压力激励我们去寻找新的解决方法。如果个人或国家找到了新的且更好的应对方法,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危机被成功地化解了。不过,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其实成功化解危机和未能成功化解危机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成功可能仅仅是局部的或一时的,相同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例如,在1973年,英国通过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来“解决”它在国际上的角色定位危机,但在2017年,出于同样的目的,英国又以公投的方式离开欧盟。)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实际问题:一个转折点要多短暂、多关键、多罕见,才能被称为“危机”?在人的一生中,或在上千年的区域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时刻应当被贴上“危机”的标签?这些问题有不止一种答案,不同的答案为不同的目的服务。
其中一种极端的解释把“危机”一词界定为长间隔、极罕见、戏剧性的剧变:人的一生仅会发生几次,国家更是几百年才一见。举个例子,根据这一定义,在一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看来,在大约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后,古罗马经历的能被称得上“危机”的只有三次事件:首先是头两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264—前241年及公元前218—前201年),其次是古罗马从共和国时期进入帝国时期(约公元前23年),最后是日耳曼人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约476年)。当然,这位历史学家并不会就此认为其他发生在公元前509—公元476年的事情都微不足道,他只是把“危机”一词留给了最非同寻常的三件事。
(公元前264—前241年及公元前218—前201年),其次是古罗马从共和国时期进入帝国时期(约公元前23年),最后是日耳曼人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约476年)。当然,这位历史学家并不会就此认为其他发生在公元前509—公元476年的事情都微不足道,他只是把“危机”一词留给了最非同寻常的三件事。
另一种极端的解释可见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戴维·里格比与他的助手皮埃尔–亚历山大·巴兰、让·博西玛曾共同发表的关于美国城市“技术危机”的精细研究。他们给出了“技术危机”的操作性定义,即专利应用的持续低迷时段,其中“持续”一词被量化。根据这些定义,三位学者发现,美国的城市平均每12年会经历一场平均持续4年的技术危机,一个中等的美国城市每10年当中有3年处于这样的技术危机阶段。戴维等三人发现,这有助于理解一个与实际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美国城市能够避免上述定义中所描述的技术危机,有些城市却不能?不过,那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戴维等人的研究对象不过是一些暂时存在的小事,而戴维等人则会反对古罗马历史学家对长达985年的古罗马历史谱系中的其他事件视而不见的行为。
我的观点是:“危机”的定义可以随着不同的发生频率、不同的持续时间以及不同的影响范围而变化。我们无论是研究罕见的大型危机,还是分析频繁的小型危机,都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在这本书中,我采纳了从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范畴。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在书中所论述的国家都经历过“重大危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更频繁出现的小型转折点。
不管是个人危机还是国家危机,我们通常只关注单个的紧要关头,比如妻子告知丈夫她要提出离婚申请的那一刻,或者是(智利历史上的)1973年9月11日,也就是智利军方推翻民主政府,智利总统自刎的那一天。有些危机的降临确实毫无预兆。比如,发生在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海啸,带走了20万人的生命。又比如,我正值盛年的表弟在驾车过程中不幸在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留下了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不过,大部分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都是多年里渐进式变化累积的结果,就像上述的夫妻在离婚前就已长期存在婚姻问题,智利在遭遇政变前一直面临政治和经济难题。这样的“危机”是对长期累积的压力的一种突然的觉知或反应。澳大利亚前总理魏德伦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本质(我们会在第七章谈到)。1972年12月,他在短短19天内出台了一个包含重大变革的旋风计划,但他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些改革只是“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的问题的承认”。
国家不是个人的放大化,二者明显在许多层面上各有特点。那么,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
我在和朋友及学生讨论国家危机的时候经常谈到其中一个优点,那就是,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个人危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所以,从个人危机的视角出发可使普通受众更容易“联想到”国家危机,从而弄清楚其中的复杂性。
另外一个优点是,在个人危机的研究方面,人们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得出了个人危机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危机的不同结果。这些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使我们可以着手描绘国家危机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理解国家危机的不同结果。我们会看到,有些个人危机的影响因素同样适用于国家危机。例如,遭遇危机的个人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也会向盟国求助。个人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案时会参考其他人解决类似危机的经验,国家也会借鉴和采纳其他国家面对相同挑战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案。个人会从过往危机的解除中获得自信,国家也一样。
以上情况下,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不过,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影响着个人危机的结果,却不直接存在于国家危机中,不过这些因素仍然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启发我们寻找影响国家危机的相关因素。比如,心理治疗师发现,界定“自我力量”这一个人特质很有用。虽然国家不具备心理层面上的自我力量,但这一概念能引导我们去思索一个相关概念——对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国家认同”。无独有偶,人们往往觉得自己在处理危机时选择的自由会受到现实因素的约束,比如育儿的责任和工作的需求。当然,国家选择的自由不受限于这些因素,但受限于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地缘政治的约束或是国家财富的多寡。
这种比较还能使那些与个人危机并无相似之处的国家危机的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两种危机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国家拥有领导者,显然个人是没有的,因此关于领导者角色的问题会常规性地出现在有关国家危机的讨论中,但不会出现在有关个人危机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是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究竟是非凡的领导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即“伟人史观”),还是说即使换成其他领导者,历史依旧会沿着相似的路径发展?(例如,要是1930年的那场车祸当真使希特勒丧生,二战还会爆发吗?)国家拥有个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危机的处理总离不开群体互动和决策,而个人通常能够自行做决定。国家危机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例如1973年的智利)或和平演变(例如二战后的澳大利亚)的方式解除,而单独的个体不会进行暴力革命。
正是因为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之间存在这些明显的相似性、隐含的相近性和不同之处,我发现对两者进行对比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国家危机。
在阅读时,读者和书评人时常会逐渐发现,某本书的内容和写作方法并非他们所预想或期待的那样。那么,本书包括了什么内容,使用了什么方法,又不包括什么内容,没有使用什么方法呢?
本书是针对7个现代国家在数十年间所经历的危机和选择性变革进行的一种比较性、叙述性、探索性研究。这7个国家都是我亲身所至,并且以个人危机的选择性改变的视角去做过观察的,它们是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
让我们来逐个理解。
本书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本书不单单讨论1个国家,而是对7个国家进行比较。非虚构类作品的写作通常需要在单一案例研究和多案例比较研究之间做抉择。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在给定的篇幅内,单一案例研究显然可以提供关于案例的翔实细节,但比较研究能够展现多元的视角,并发现单一案例研究无法涉及的问题。
历史比较法会引发人们思考单一案例研究所没有涉及的问题:为什么某一特定事件在一个国家导致了结果R1,在另一个国家却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R2?举个例子,我很喜欢阅读的一本有关美国内战历史的书用了整整6页去描绘葛底斯堡战役爆发次日的情形,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内战不像西班牙内战和芬兰内战那样以胜者豁免败者而告终。从事单一案例研究的作者经常批判比较研究过于简单和浅薄,而从事比较研究的作者会认为单一案例研究对重大问题探讨不足。“那些只研究一个国家的人最终一个国家都不了解。”后者的观点在这句话中展露无遗。本书做的是比较研究,当然这就意味着它包含了比较研究的优点和不足。
我意识到一个痛苦的现实:因为这本书要讲7个国家,所以我对每个国家的描述都必须化繁为简。当我坐在书桌旁转过头去看时,发现身后的地板上堆着一摞摞书籍和文献,每一摞都有5英尺
 高,它们分别是每一章的阅读材料。对我来说,要思考如何把整整5英尺高的关于战后德国的材料浓缩成短短一章的内容,实在是不易,因为有那么多的内容要舍去!当然,简练也有好处:这样有助于读者比较战后德国与其他国家的重大议题,而不会被大量繁复的细节、预期、假设和转折分散注意力,不会觉得眼花缭乱。想要更深入地了解细节的读者,可以在本书最后的部分查看每一个案例研究的相关书单。
高,它们分别是每一章的阅读材料。对我来说,要思考如何把整整5英尺高的关于战后德国的材料浓缩成短短一章的内容,实在是不易,因为有那么多的内容要舍去!当然,简练也有好处:这样有助于读者比较战后德国与其他国家的重大议题,而不会被大量繁复的细节、预期、假设和转折分散注意力,不会觉得眼花缭乱。想要更深入地了解细节的读者,可以在本书最后的部分查看每一个案例研究的相关书单。
本书采用叙述性写作风格,这是历史学家传统的写作方式,最早可追溯至2 400多年前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将历史发展为一门学科时。“叙述性”意味着论证过程是以散文式推理的方式来推进的,无须依靠等式、数据表格、图形或者数据显著性检验,而且研究的案例数量不多。叙述性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所青睐的新型定量研究方法非常不同,后者大量使用等式、明确的可测试性假设、数据表格和图形,样本规模较大(即研究的案例数量较多),从而使得数据显著性检验变得可行。
我很欣赏现代定量研究方法的作用。我在关于73个波利尼西亚岛屿的森林砍伐状况的统计研究中采纳了定量研究方法,
 这样得出的结论的说服力显然是针对少数岛屿的叙述性研究所不能及的。在我与别人合著的一本书
这样得出的结论的说服力显然是针对少数岛屿的叙述性研究所不能及的。在我与别人合著的一本书
 中,我的合著者巧妙地利用了定量研究方法去解决那些进行叙述性研究的历史学家争论不休、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拿破仑在战场上的征伐对欧洲随后的经济发展到底有利还是有弊。
中,我的合著者巧妙地利用了定量研究方法去解决那些进行叙述性研究的历史学家争论不休、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拿破仑在战场上的征伐对欧洲随后的经济发展到底有利还是有弊。
我原打算在本书中采用现代定量研究方法。我在这上面花了几个月的心思,却发现这个任务只能留到以后的项目中去完成了。这是因为,本书的任务是通过叙述性研究识别假设和变量,随后才能通过定量研究测试这些假设和变量。我的样本只有寥寥7个国家,不足以得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论。要把一些叙述性的定性概念,比如“成功解决危机”和“诚实的自我评估”变得“可操作化”,也就是把这些口头概念转化为可以通过数据进行衡量的指标,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所以,本书仅是一个叙述性的探讨,我希望它能够引发定量的试验。
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在这本书中仅仅讨论自己熟悉的7个国家。我曾不止一次探访这7个国家,在其中的6个国家长时间居住过,最早可追溯到70年前。我会讲或者曾经会讲其中6个国家的语言。我喜爱并欣赏所有这些国家,在过去两年内,我愉快地再次一一探访这些国家,并且认真考虑过移居到其中的两个国家。有了这些亲身经历,再加上我有老朋友生活在这些国家,我对这些国家的了解较为充分,这为我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也使我更能感同身受。我和朋友的经历加在一起,可以涵盖相当长的时间,足够使我们见证这些国家的主要变迁。在这7个国家当中,我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是相较有限的,因为我不会讲日语,我仅在21年前短暂地探访过这个国家。为了弥补这一点,我对日本的了解主要是基于我的日本姻亲、朋友和学生的生活经历。
当然,我根据个人经历所选取的这7个国家并非对世界各国进行随机抽样的结果。其中有5个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1个是中等富裕国家,还有1个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没有非洲国家,有2个欧洲国家、2个亚洲国家,还有3个国家分别来自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至于我从这些非随机样本中得出的结论在别的国家是否适用,就需要其他人去研究了。我接受这些局限。我之所以选择这7个国家,是因为我或多或少有在这些国家生活的亲身经历,或是有朋友在这些国家,而且我熟悉其中6个国家的语言,探讨这些国家对我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全书所讲述的国家危机基本上都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这让我能够从自己所处的当代视角出发来写作。唯一的例外是日本,我用了两章来讨论日本发生的变化,其中一章讨论的是如今的日本,另外一章讨论的是明治时代的日本(1868—1912年)。我写后一章,是因为明治时代的日本是自觉进行选择性变革的出色案例,而且这一时期尚属近代,明治时代的记忆和问题在当代日本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
当然,国家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变革在过去也频频发生,并且遗留下类似的问题。尽管我无法基于自身经历去叙述这些历史问题,但已有大量作品以它们为主题进行了论述。其中最常见的主题包括:4—5世纪时期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瓦解、19世纪非洲祖鲁王国的崛起和败落、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之后法国的重建,还有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的惨败,以及普鲁士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及军事变革。在开始写这本书的几年后,我发现与我合作的美国出版社(利特尔&布朗出版社)早在1973年就出版了一本相似主题的书——《危机、选择和改变》
 !该书和本书的不同之处是,前者包括几个历史案例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基本层面的区别。(该书由多名作者合著,使用了“系统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
!该书和本书的不同之处是,前者包括几个历史案例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基本层面的区别。(该书由多名作者合著,使用了“系统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
专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强调档案研究,也就是对保存下来的第一手文字资料进行分析。每一本新的历史书都会挖掘那些未被使用或未被充分使用的档案资料,或者是重新解释那些已经被其他历史学家用过的档案资料,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同于我罗列在最后的众多参考文献,档案研究不是我这本书的基础。实际上,我借助对个人危机的研究结果,加上明确的比较方法,再结合自己和朋友的生活经历,为本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框架。
这本书不同于评论时事的杂志文章合集,只在出版后的几周内有阅读价值,然后就会走向过时的命运。相反,这本书的定位是在数十年后仍能再版。我说这些,是希望你在发现整本书都没有谈到特朗普政府的任何具体政策、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力,或者是正在进行中的英国脱欧谈判时,不会感到惊讶。时事议题日新月异,我今天写下它们,到本书出版的时候也许早就过时了,几十年后更会变得不值一提。对特朗普总统及其政策还有英国脱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别处找到大量的讨论。不过,我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会用相当的篇幅讲述美国在过去20年间存在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在本届政府的管理下获得了更多关注度,并且很可能在至少未来10年内还会持续存在。
现在,让我来介绍本书的脉络。在第一章里,我会先对个人危机进行论述,剩下的章节则全然致力于国家危机的讨论。通过亲身经历危机和目睹亲友经历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危机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其中,最好的情况是,人们成功找到全新的、更好的应对危机的方法,在经过危机的磨炼之后变得更强大。最坏的情况是,人们被危机打垮,不愿寻找新的应对危机的方法,或者采纳了更糟糕的新方法。有些人甚至以自杀来结束危机。心理治疗师从中提炼出许多影响个人危机能否被成功化解的因素,我在第一章中会讨论到其中的12个因素。我将以这些因素为参考,探索影响国家危机处理结果的因素。
有的人可能会抱怨:“12个因素太多了,你为什么不把它们简化为几个因素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觉得人类的成果或者国家的历史可以被总结为几句简单的口号,那就太过荒谬了。要是你不幸找到一本宣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书,别读下去了,扔掉吧。反之,如果你不幸发现一本讲述影响危机应对结果的76个要素的书,那么也扔掉吧:理解生命中无限的复杂性,并从中找出重要项,从而建立一个有用的框架,这是作者的任务,不是读者的难题。对我来说,12个影响因素是对这两种极端情况的折中,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可以详尽地解释事实,同时也不会像洗衣清单那样事无巨细,毕竟洗衣清单是用来追踪衣物的,不适合用来理解世界。
在导入性的第一章过后会有三组内容,每组包括两章,将讨论同一种类型的国家危机。第一组内容关注的是由外部冲击所引发的突发式危机(以芬兰和日本为例)。第二组内容关注的也是突发式危机,不过是由于国家内部冲击所引发的(以智利和印度尼西亚为例)。第三组内容讨论的是非突发性的渐进式危机(以德国和澳大利亚为例),尤其受到二战带来的压力影响。
芬兰的危机(见第二章)随着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该国的大举进攻而爆发。在接下来的冬季战争中,芬兰事实上被所有潜在的盟国抛弃,持续蒙受沉重的损失。但是,无论如何,芬兰在与人口是自己50倍之多的苏联的对峙中赢得了独立。20年前,我在芬兰待过一个夏天,当时我的房东中有参加过冬季战争的退役老兵,也有战后的孤儿寡母。这场战争的遗产是显而易见的选择性变革,芬兰因此变得马赛克化,这个国家成了对比鲜明的元素的结合体:它是一个富裕的小型民主政体,其外交政策却是尽可能获取贫穷、庞大的苏联的信任。有很多不了解背后历史原因的非芬兰人认为这种政策是可耻的,纷纷公开抨击这一政策,称其为“芬兰化”。我在芬兰度过的那个夏天,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无知地向一位曾参加冬季战争的退役老兵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礼貌地向我解释了芬兰人在急需帮助的时刻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的悲惨教训。
另一场由外部冲击引发的危机发生于日本。1853年7月8日,一队美国战舰驶入东京湾入口,要求日本签署条约,承认美国船只及海员的权利,这件事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对外部世界实行的“锁国”政策(见第三章)。此次事件的最终结果是:日本过往的政府体系被推翻,日本自觉发动了一场大范围的激进变革,同时保留了日本传统特质。这些变革让今天的日本成为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明治时代的日本从国家层面突出展现了许多影响个人危机的因素。通过对比明治时代日本的决策过程和取得的军事成就,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做出了恰恰相反的政策决定,这些决定导致日本在二战中节节溃败。
第四章的主角是智利,它是因国家内部政治妥协失败引发危机的两个国家之一。在长期的政治僵局后,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9月11日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了智利民主政府及其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统治,在此之后,皮诺切特独掌大权近17年。我在这场政变发生前几年曾在智利生活,但我当地的朋友当时无一预料到这场政变,更没有人预料到皮诺切特那史无前例的残酷统治。实际上,那时候他们还很自豪地向我解释智利不同于其他南美洲国家的悠久的民主传统。今时今日,智利再度成为南美大陆上独一无二的民主政体,但这个国家经历了选择性变革,阿连德的影响和皮诺切特的模式都是智利的一部分。对这本书的手稿做出评价的美国朋友都认为,讲智利的这章内容是全书最可怕的部分,皆因一个民主国家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然转变为一个残酷的独裁国。
同组的第五章讨论了印度尼西亚。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内部政治妥协的崩溃引发了一场政变,但其结局和智利的军事政变相反:反政变势力用“大屠杀”的方式解决了那些被认定支持了政变的群体。印度尼西亚和本书讨论的其他国家存在明显的不同:它是7国当中最贫穷、工业化程度最低,并且最不西方化的案例;它的国家认同构建时间是最短的,国民仅在过去的40年间才开始相互团结(在此期间,我曾在那里工作)。
接下来的两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探讨了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危机,不同于上述那些平地惊雷似的突发式危机,这两国的危机都是渐进发生的。对于我这种将渐进式变化称为“危机”或“剧变”的做法,有的读者可能会有所质疑。不过,即使有人持有异议,我还是觉得把这种渐进式变化与突发式危机放在同一种框架内讨论为妙,因为两者都会引发选择性变革,而且其影响因素是相似的。除此以外,突发式危机和渐进式变化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分明:它们之间会互相转化。像智利军事政变这样的突发性转折,其背后有长达数十年紧张态势的积累,而且该国在政变发生之后又经历了数十年的渐进式变化。我把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的危机称作“表面上”的渐进式转变,因为事实上,二战后德国所经历的危机始于一场突发式灾难:1945年5月8日,德国在二战中宣布投降。类似地,二战期间,在不到三个月内,澳大利亚经历三次军事惨败,为战后该国渐进式危机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这一组所讨论的第一个非突发式危机案例是二战后的德国(见第六章),当时德国同时面临多种挑战:纳粹时期的遗留问题、有关社会等级结构的争论,还有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政治分裂带来的伤痕。在我的比较框架内,二战后德国的危机处理方式具有其独特性,这体现为代际间异常暴力的冲突、强有力的地缘政治约束以及与在战争时期被德国犯下的暴行伤害的国家之间达成和解的过程。
我的另一个非突发式危机案例是澳大利亚(见第七章),这个国家的人民在55年间对自身的国家认同进行了重塑,我正是在这个时段内探访了澳大利亚。1964年,我第一次去澳大利亚,当时它就像是英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岗哨,只能期望从英国身上获得身份认同,并且实行限制或排斥非欧洲移民的“白澳政策”。但彼时的澳大利亚正面临一场身份危机,因为这种英伦白人的身份认同和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外交政策需求、防务战略、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构成越来越格格不入。而今天,澳大利亚的贸易和政治政策都以亚洲为导向,城市街道上和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亚洲面孔,在关于撤销英国女王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的公投中,投反对票的澳大利亚人仅仅获得微弱优势。不过,正如明治时代的日本和芬兰的例子,这些变化都是选择性的:如今,澳大利亚仍旧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它的官方语言还是英语,并且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祖先都来自英国。
以上讨论的这些国家危机都被明确识别出,而且已经得到解决(或者至少解决方案已经在长期落实),我们可以对其结果进行评估。本书最后4章论述了正在发生的和潜在的危机,这些危机的结果是未知的。我以日本的案例(见第八章)作为这一部分的开头,日本也是第三章的主题。如今的日本面临着数不清的根本性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已被日本国民和政府广泛意识到,但还有很多问题并未被他们认识到,甚至被大范围地否认。此刻,日本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日本的未来走向真真切切地掌握在自己的国民手中。明治时代的日本鼓起勇气成功应对危机的记忆能否帮助现代的日本再次成就自己?
随后的两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关注的是我自己的国家——美国。我将指出在未来10年间有可能对美国的民主和实力造成破坏的4种渐进式危机,正如已经发生在智利的那样。当然,这并不是我的发现:美国人已对这4种危机展开了公开讨论。在今天,危机感正在美国社会中不断蔓延。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朝着解决的方向走,反而越走越偏。不过,就像明治时代的日本,美国也有以往克服危机的经历,特别是那场漫长而撕裂的内战,以及突然从政治孤立状态中走出来参加二战的经历。这些经历能帮美国成功化解危机吗?
最后一章的关注点转向全球(见第十一章)。诚然,我们可以就全球面临的问题列一张无限长的清单,但我在这里主要强调4个问题,它们已然存在了一段时间,而且如果继续存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对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消极的影响。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都拥有国家认同、公民自治以及群体协作的悠久历史,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则没有这样的历史。少了这样的历史印记作为引导,在首次面临可能对全球产生致命影响的问题时,我们能够成功解决吗?
本书的后记部分以前文提及的12个影响因素来检验书中7个国家和全球的危机。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只有危机才能激发国家做出重大变革?椰林俱乐部大火的冲击带来了短期心理疗法的变革,国家能不能在不经历这般灾难的情况下做出自我变革的决定呢?我还探讨了领导者在历史上能否产生决定性影响,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一些方向,还指出了人们通过审视历史能得到的不同的实际教训。如果人们,或者仅仅是那些领导者愿意反思过往的危机,那么了解过去将能帮助我们应对眼前和未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