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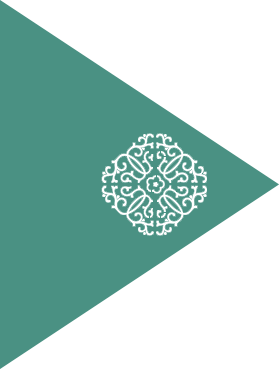
|
经学理学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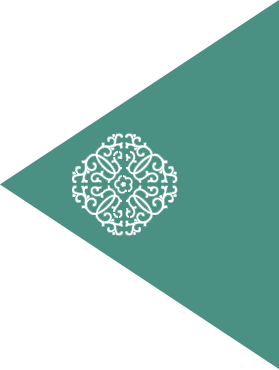
|

唐宋以降至元明时期,主导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经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由以“五经”训诂考释为主的注疏之学转向以“四书”义理阐释为主的理学。“四书”及“四书”性理之学取代了前代经学以“五经”及“五经”训诂之学为主的地位,完成了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经学的理学化,即理学对经学的改造,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经学理学化在学术发展史上的意义,促进了经学的转型和儒学的发展,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基本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确立了以儒为主、融合三教的学术发展模式。
儒家经学是以经孔子整理的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并阐发其涵义的学问。儒家经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经学在战国的起源,在西汉被定为一尊,汉学在汉唐时期的流传演变,以及宋学兴起(延续到元明),理学占据宋学发展的主导地位,清代新汉学的形成等发展演变的若干阶段。
以义理之学为主导的宋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潮,体现了儒学发展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所谓义理之学,指与章句训诂注疏之学相对应的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其道理的学问。“义理”一词,初见于《礼记·礼器》:“义理,礼之文也。”即义理是对礼的合宜得理的解说。汉晋时指经义名理,故后来学者将其作为一门讲求经义,探讨其名理的学问。宋儒治经,着重探究义理,与汉唐儒者专事训诂名物、传注疏释的治经路数不同,而重在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大义和道理。宋学的一般特征是重义理,轻训诂,以此与重训诂注疏、轻义理阐发的汉学相区别。后来将重义理、轻训诂的宋学称为义理之学,而与重章句训诂、传注疏释的汉唐经学相区别。
宋学中包括宋代诸多讲义理的宋学人物和派别,亦包括在宋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理学。到后来理学则成为宋学发展的主要内容和表现,以致有学者把理学作为宋学的代名词。然而宋学与理学之间不应画等号,宋学的内涵大于理学,在时间上宋学早于理学。应该说,宋学包括了理学和非理学的讲义理的诸治儒家经学的流派和代表人物。到后来,宋学的发展则体现为以理学的发展为主,尤其南宋以后,理学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宋学的发展便体现为理学诸派的演变发展。
回顾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如果说,中国哲学发展到汉代,随着秦汉之际的社会转型,人们讨论的核心话题是关注“天人之际”,侧重解决天人关系理论问题,其依傍的文本主要是儒家经典“五经”,而有今、古文经学之争;而隋唐时期佛教盛行,哲学依傍佛典,集中探讨“佛性”并及心、性、情问题,推本“性情之原”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发展到宋代,随着三教的互黜、互补,面临信仰失落、统治者道德沦丧和价值观念的重建等问题,人们讨论的核心话题落入对天理人欲的关注,如何为儒家伦理学寻找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问题,其依傍的文本则由“五经”转变为“四书”,通过“四书”阐发义理及哲理,而有别于汉唐对“五经”的训诂注疏之学。
天理人欲之辨成为理学家讨论的核心话题,“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为了在价值观上纠正统治者尤其是封建帝王过分放纵私欲和争权夺位而导致天下难治的局面,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观,目的是为了端正社会风气,对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加以伦理纲常的规范和约束,同时对普通民众提出道德自律的要求。亦是在核心价值观上,对先秦儒家义利之辨的传承和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理学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于天理、人欲之分,其理论针对性正是唐统治者的“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体现了在新形势下,新儒学者复兴儒学,重整纲常,纠正前代纲常失序,人无廉耻的价值取向。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统治秩序,以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和长治久安。
宋儒学者面临时代的挑战,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统一于天理,以之为纲领,构建理学思想体系,并将其贯彻到对经典的诠释之中,成为新经学的指导原则和经典诠释的标准。儒学经典诠释思想在宋代之演变主要体现在:一是经典诠释所依傍的文本重心由“五经”系统转向“四书”系统,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阐发义理和天理,这是宋代经学区别于汉唐经学的“五经”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四书”系统的形成与宋代《孟子》的由“子”入“经”有密切关系;二是经典诠释的思路和方法由重训诂转向重义理;三是经典诠释的理论深度由经学诠释转向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相结合,使中国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四是经典诠释中人文与宗教之互动——既排斥又吸取佛、道。
汉儒治经,以传记笺注、名物训诂为要务。唐儒治经,上承汉儒“家法”,依注作疏。唐初孔颖达等奉钦命编定的《五经正义》以“疏不破注”为原则,末流所及,不仅以“疑经”为背道,而且以“破注”为非法,严重桎梏、束缚了学者的思想,使以经学为载体的儒学陷于烦琐和僵化。儒学的生命智慧枯萎,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唐代士人就是在汉代和魏晋旧注的基础上来疏释经书和原有的旧注的,普遍采取疏不破注和烦琐训诂释经的方法。这种汉唐经学的传统缺乏生命力,表明旧的儒家经学已经僵化,显然不能与盛行于唐代的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相抗衡。于是宋学学者对笺注经学提出非难。他们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义理,全凭己意说经。不仅疑传、舍传,而且疑经、改经,蔚然形成疑经惑传的学术新风。学风的改变,标志着宋学的兴起,义理之学逐步取代汉唐训诂之学,成为儒家经学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二程”等理学家又在义理之学的基础上,把经学理学化、哲学化,将宋代义理之学发展为理学,以最具时代特色的“天理论”哲学开辟了宋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著《四书章句集注》,以“四书”阐发天理论哲学,并吸取佛教精致的思辨哲学的成果,集“四书”学、理学之大成,体现了宋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占据了中国经学发展的中心地位,并影响后世经学和思想学术数百年之久。
宋儒理学家为了开发儒学新的思想智慧,强调超越汉唐以来对儒家经典文本的种种烦琐复杂的解释,直接从“四书”中阐发义理。因“五经”时代久远,文字古奥,字义艰深,佶屈聱牙,晦涩难读,使初学者却步,尤其难以向民间普及。又历经秦火和战乱,残破不全,汉学学者为了弄懂五经原义,不得不下大功夫从事考据训诂,以致产生流弊,烦琐释经,白头到老,陷于文字训诂之末而失其本。这亦是汉唐儒学未能有效地回应外来宗教文化的挑战而动摇了儒学文化主体地位的重要原因,因而遭到了宋学学者的批评。而“四书”则文字易懂,说理明白,便于阐发义理,向民间普及。于是程朱等宋学学者和理学家推重“四书”,把“四书”的重要性和地位置于“五经”之上,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汉唐经学唯“五经”是尊的格局,而且在经典诠释的内容上为发明义理提供了依据,这便于把“四书”之义理推向民间,发挥其传播效果,以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普遍的社会效应,使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不仅成为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而且广泛流传民间,影响大众,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流传海外,在东亚产生了重要影响。
需要指出,就治经学的基础和宗旨而言,程朱是以“四书”为重,通过“四书”阐发义理。但程朱等理学家也并不忽视其他儒家经典,尤其对《周易》等予以关注。虽然朱熹以毕生精力诠释“四书”,著《四书章句集注》,后成为中国经学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经书,从而以“四书”作为宋学学者经典诠释的主要文本。尽管如此,朱熹也遍注群经,对儒家经典《周易》《诗》《书》《礼》《春秋》《孝经》等诸经加以注解、考释,全面总结了传统经学,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经学,成为经学史上宋学的集大成者。
与此相关,程朱虽以义理为重,但也不废弃训诂考据之学,在一定程度上,朱熹等理学家亦重训诂考据,对诸经详加训释,这是他对汉学的吸取,亦是他对宋学流弊的修正。目的是为阐发义理与天理服务。由此朱熹对传统经学做了全面总结,亦强调“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
 。从而对汉、宋学都加以总结吸取,既以宋学为主,又遍注群经,不废训诂考据之学,超越汉、宋学之对立,由此发展了传统经学,并对后世清代的新汉学产生重要影响。
。从而对汉、宋学都加以总结吸取,既以宋学为主,又遍注群经,不废训诂考据之学,超越汉、宋学之对立,由此发展了传统经学,并对后世清代的新汉学产生重要影响。
宋代理学对传统经学加以改造创新,经学的理学化促进了经学的转型和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这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创新,体现了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所谓连续性是指以“四书”为主要文本依据而阐发的天理论,其核心内涵仍是孔孟仁义思想,是对儒学价值观的一脉相承;所谓创新性是指经学理学化是对汉唐儒家经学重训诂注疏、轻理论发挥流弊的修正,把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相结合,在哲学理论上对传统儒学加以发展,它成功地回应了唐宋之际所面临的包括宗教冲击人文、统治者道德沦丧、社会动荡、儒学发展停滞等各个方面的挑战,而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正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到宋代的必然趋势。此外,理学家以道德修养而不以宗教信仰为中心来实现其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固然有加强道德自律和伦理约束的一面,但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考察,以宋代理学的伦理约束、道德修养来代替宋以前流行的人身束缚和宗教迷信,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进步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