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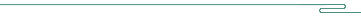
孙卿在世及其身后,其人其学声势渐盛。《史记·吕不韦列传》曰:“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
 据此可以略知荀子在战国后期影响之大,几乎一时无两,而对荀卿之徒的接受,主要来自各国君主,其著作是为政者教科书。按《史记·李斯列传》云:“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据此可以略知荀子在战国后期影响之大,几乎一时无两,而对荀卿之徒的接受,主要来自各国君主,其著作是为政者教科书。按《史记·李斯列传》云:“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既然荀卿追随者著述极多,已形成一个学派,荀卿(或孙卿)则几乎湮没于其后学的著述之中。《荀子》虽经刘向的重新删定,却依然属于此一学派集大成之著作,以致《荀子》各篇章句之间有相抵牾者,若要厘清《荀子》和荀卿之间关系,亦非易事,然而后世读者仍要诘问:荀卿本人思想和学术究竟为何物?它作为一个凝聚核心,究竟有何特点?
既然荀卿追随者著述极多,已形成一个学派,荀卿(或孙卿)则几乎湮没于其后学的著述之中。《荀子》虽经刘向的重新删定,却依然属于此一学派集大成之著作,以致《荀子》各篇章句之间有相抵牾者,若要厘清《荀子》和荀卿之间关系,亦非易事,然而后世读者仍要诘问:荀卿本人思想和学术究竟为何物?它作为一个凝聚核心,究竟有何特点?
上述《李斯列传》称荀卿之学为“帝王术”,此对了解其人其学,颇具提纲挈领的作用。而所谓“帝王术”,就是统治术,也就是帝王控制臣民之术,或称“南面之术”。《宋书·谢庄列传》记载谢庄于大明元年,奏改定刑狱:“臣学闇申、韩,才寡治术。”
 韩非亦出自荀卿之门下;王利器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六论》《十二纪》,吕不韦之帝秦策也”
韩非亦出自荀卿之门下;王利器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六论》《十二纪》,吕不韦之帝秦策也”
 。虽则均为“帝王术”,但是吕不韦《吕氏春秋》却并不迎合秦王嬴政,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商君、李斯和韩非一系的法家思想倒成为秦国制胜法宝,所以,作为帝王术,其为学之立场却歧异纷呈,遇或不遇,亦有风云际会之偶然性。王国维指出:“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
。虽则均为“帝王术”,但是吕不韦《吕氏春秋》却并不迎合秦王嬴政,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商君、李斯和韩非一系的法家思想倒成为秦国制胜法宝,所以,作为帝王术,其为学之立场却歧异纷呈,遇或不遇,亦有风云际会之偶然性。王国维指出:“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
 擅长帝王术的荀卿,属于典型的帝王派,其为学之趋向,亦奠定了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思想基础。
擅长帝王术的荀卿,属于典型的帝王派,其为学之趋向,亦奠定了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思想基础。
《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之儒家类有“《孙卿子》三十三篇”,并且注明:“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
 此处谓孙卿名况,与刘向《孙卿书录》的叙述相吻合;《汉书·艺文志》之“兵权谋家”有“《孙卿子》”,反映孙卿文武兼备的治学特征;《汉书·艺文志》之“诗赋略”有“孙卿赋十篇”,观《荀子·成相》篇,则有政治箴言的特色。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子部》之《儒家类·荀子》云:“其实诸子惟荀最醇,四子书外,所当首屈一指。杨氏注亦多古义。谢侍郎序言《小戴》所传《三年问》全出《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德行》篇大同,《大戴》所传《礼三本篇》亦出《礼论》篇,《劝学》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座》篇末见大水一则附之,哀公问五义出《哀公》篇之首,则《荀子》语在二戴《记》者甚多,而本书反鲜读者。”
此处谓孙卿名况,与刘向《孙卿书录》的叙述相吻合;《汉书·艺文志》之“兵权谋家”有“《孙卿子》”,反映孙卿文武兼备的治学特征;《汉书·艺文志》之“诗赋略”有“孙卿赋十篇”,观《荀子·成相》篇,则有政治箴言的特色。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子部》之《儒家类·荀子》云:“其实诸子惟荀最醇,四子书外,所当首屈一指。杨氏注亦多古义。谢侍郎序言《小戴》所传《三年问》全出《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德行》篇大同,《大戴》所传《礼三本篇》亦出《礼论》篇,《劝学》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座》篇末见大水一则附之,哀公问五义出《哀公》篇之首,则《荀子》语在二戴《记》者甚多,而本书反鲜读者。”
 关于《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等经典之传承,经学家称颂荀卿厥功甚伟。而荀卿之学作为帝王派帝王术之原创性,透过其三传弟子贾谊之论述,还是可以一窥其宗旨。
关于《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等经典之传承,经学家称颂荀卿厥功甚伟。而荀卿之学作为帝王派帝王术之原创性,透过其三传弟子贾谊之论述,还是可以一窥其宗旨。
贾谊受学于河南守吴公,而关于吴公其人,《汉书·贾谊传》记述:“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
 吴公是荀卿再传弟子,因此荀卿、李斯、吴公和贾谊,在学术上具有渊源关系,贾谊与荀卿之学一脉相承。《史记·李斯列传》太史公评价李斯云:“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
吴公是荀卿再传弟子,因此荀卿、李斯、吴公和贾谊,在学术上具有渊源关系,贾谊与荀卿之学一脉相承。《史记·李斯列传》太史公评价李斯云:“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
 此揭示了战国后期儒学的弊端,那就是非帝王派向帝王派之屈服,儒学向刑名法家之转移,假儒真法,儒表法里,乃至如代表孟子民本思想的平民派则收窄了置喙空间。
此揭示了战国后期儒学的弊端,那就是非帝王派向帝王派之屈服,儒学向刑名法家之转移,假儒真法,儒表法里,乃至如代表孟子民本思想的平民派则收窄了置喙空间。
观《汉书·贾谊传》、贾谊《新书》,乃在汉代文帝时期,帝王之术的实施方略,贾谊撰述的旨意,就是要构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在此大目标统摄下,各种举措无非贯彻帝王术的具体表现,贾谊必然要在削藩、铸钱、保傅尤其建立等级秩序等议题上,为文帝出谋划策。刘泽华指出:“集权是手段,攫取经济利益才是目的……在分封制下,土地所有权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他进一步阐释曰:“但是实现兼并的手段却又不是经济的,而是军事的和政治的。”
 然则实现目的之最高控制手段应该是思想的、学术的,作为人的特征,主要分两部分,肉体到思想,或者物质与精神,中国集权统治者从来就未曾忽视在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上对人民进行最彻底的控制。贾谊《新书·礼》云:“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然则实现目的之最高控制手段应该是思想的、学术的,作为人的特征,主要分两部分,肉体到思想,或者物质与精神,中国集权统治者从来就未曾忽视在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上对人民进行最彻底的控制。贾谊《新书·礼》云:“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法起到阻吓作用,所针对的是看得见的人事,谁触犯条律,则依法惩处;而礼则在看不见之处,已经塑造或规训了人的思想和行为,限制了人的自由与天性,故而礼与法实际上是同功一体者也。贾谊《新书·礼》又云:“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
法起到阻吓作用,所针对的是看得见的人事,谁触犯条律,则依法惩处;而礼则在看不见之处,已经塑造或规训了人的思想和行为,限制了人的自由与天性,故而礼与法实际上是同功一体者也。贾谊《新书·礼》又云:“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
 可见礼就是内外兼施地控制人民,所谓“使君无失其民者也”,就是让人民永远依附于君权,令人在灵魂上,亦步亦趋地追求与大一统集权政体保持一致,绝不敢越雷池半步。而贾谊这种思想,完全秉承《荀子》,二者之间,心心相印者也。
可见礼就是内外兼施地控制人民,所谓“使君无失其民者也”,就是让人民永远依附于君权,令人在灵魂上,亦步亦趋地追求与大一统集权政体保持一致,绝不敢越雷池半步。而贾谊这种思想,完全秉承《荀子》,二者之间,心心相印者也。
而帝王派之帝王术目标就是操控人民,人民任何自主意识都会被视作异端,人民噤若寒蝉,秦“黔首”之称谓就反映了一切,若要高效地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首先在生活物资上树立王权所有制的概念。《论语·阳货》云:“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所谓民以食为天;《孟子·尽心上》云:“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在饥渴状态下,人难免饥不择食,人饥渴之际就难以辨别什么是正味,所以要保持对正味的辨别力,就须处于常态之下。人心也一样,如果迫于饥渴,违心屈从,那么人心自然、健全的思考辨析能力就会丧失,而人心一旦不能守正,则行为必遭扭曲、异化,盲从、轻信就会发生,导致无所不用其极。可见统治人民,饮食饥饱的作用最不可低估。
荀卿以至后学们,提倡“化性起伪”(《荀子·性恶》),就是要在思想上确立正统,驱使天下人心以其所谓正为正,放弃个体的自由意志。由此,建立起一种不归顺者不得食的观点,以令人臣服,个体思想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毛诗·小雅·谷风之什》之《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关于此诗诠释,引发出土地、人民是否属于王权所有的问题。《春秋左氏传·昭公七年》记载:“无宇辞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宇意指在天子、诸侯领地内,人如果吃土地上生长的粮食,就确立了君臣关系,一旦确立君臣关系,就要服从统一思想,除非绝食,方能摆脱此种君臣关系以及思想束缚,此说实开千古之恶例。
《论语·学而》云:“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里仁》云:“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学而》云:“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学而》云:“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雍也》云:“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对于食和居,为何孔子强调君子仅求果腹、容身而已,因为他认识到在任何地方,都难逃“王土”“王臣”问题之困扰,为了捍卫自己独立人格,坚持己见,不受王权之左右,士人只能压缩一己之物欲,否则,人心之物欲扩张,势必会与君权发生不可自拔的牵连,就会陷于尘网,甚至媚上求荣,摇尾乞怜,士人就会放弃道和原则。
《庄子》最敏锐地感受到来自大一统观念的压迫感,所以《庄子·大宗师》讥讽:“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役人之役,适人之适,乃入国家主义、集权政体之彀中,而自适其适,则藐视群体和威权,尊重个体与自由,因此,“役人之役,适人之适”,实乃《荀子》帝王术之大旨,而“自适其适者”,相信每人都有依照个性生存的自由,此恰是《庄子》之诉求。《庄子·逍遥游》叙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关于此节文字,历来解释不清,实质上,应回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语境来理解,鲲鹏展翅,“去以六月息者也”,至于列子御风而行,“犹有所待也”,人若要追求绝对的自由,也就是逍遥之境,首先得冲决君臣关系牢笼,故而,《逍遥游》幻想有一个居于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其高洁超越俗世,其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并且行踪飘忽,然则庶几可以避免“王土”“王臣”之局囿了吧?甚至,“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岂止不食,还能利他,如此神人,王权对他无计可施,神人亦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令陷于幻想的“庄子”们也得到精神的慰藉。
而《荀子》则不然,对于想挣脱物质、精神桎梏的异议之士,它认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害群之马,必除之而后快。《荀子·宥座》篇述及:“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孔子敬重郑国政治家子产,《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叙述了“子产不毁乡校”的事迹,孔子宽容言论表达,当与子产所见略同。在文献中,此处首次见到孔子诛少正卯的记载,大致是不可信的,属于为了佐证自己观点、倾向,《荀子》故意编造之事。《左传·庄公二十年》云:“二十年春……(郑伯)曰:‘……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不管孔子是否担任过鲁摄相,还是担任《史记·孔子世家》所谓的“大司寇行摄相事”,总之擅自杀人,绝非小事。而《荀子·宥座》篇言孔子悍然处死少正卯,并列“七子”以证明杀人的正当性,此种杜撰所依据的理由,就是上述《诗经》之“王土”“王臣”之邪说。
此可以在荀卿弟子韩非那里得到求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以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此篇文字凸显狂矞、华士“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他们主动隔绝与齐太公望之间的联系,想自食其力,饮食均无求于世,企图自放于现世,做个自了汉,足见昆弟二人抵制周王朝,心怀腹诽,不肯臣服。《韩非子》继承《荀子》师法,《史记·韩非列传》载韩非痛感:“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其所谓养,也是着眼于食与不食,这是《荀子》《韩非子》思考控制人民的关节点、出发点,《荀子·议兵》云:“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韩非子》尤好以赏罚治国,《韩非子·用人》云:“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对此二位兄弟自绝于新朝,不为所用,会造成集权统治失效之隐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借太公望之口,指出此昆弟二人不愿合作,孤悬世外,恩威难加。太公望要置之于死地,绝不犹豫、手软,其振振理据就是此二者虽自耕、自掘,然其饮食出自太公望所封之地,仍属“食土之毛”,且如此孤傲,则死有余辜者也。
《孟子·万章上》云:“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咸丘蒙之所问,极有深意,他想搞清楚在王权管治下,臣民之间是否有漏网之鱼,以呼吸到自由空气,也像瞽瞍之非臣舜一样,不受君臣观之束缚。按《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实际上是质问其正当性何在。孟子的回答直接否定了为王权张目的解释,在帝王、臣民之间,颠覆了上述《春秋左氏传》无宇所论土地和权力之属性,这纯粹是本末倒置。体现《孟子》鲜明的民本意识,惜乎《孟子》声音殊为寂寥。
《庄子·杂篇·让王》载:“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当周朝新建,伯夷、叔齐作为殷商遗民,则“义不食周粟”
 ,看来“王土”“王臣”之说影响深广,他们亦将食粟与臣事新朝联系在一起,为了坚守节义,遂饿死于首阳山。《庄子·外篇·骈拇》载:“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荀子》《韩非子》将士人置于食或不食生死考验面前,让他们不得不低头屈服。上述《史记·李斯列传》有李斯所云:“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从人性角度,荀卿和李斯深知凡人热衷于追逐富贵利禄,并不甘于自居卑贱,而在王权体制中,君王掌控生杀予夺的权柄,就可以剥夺士人生存的权利,也可以剥夺其思想自由的权利,士人不得不向强权妥协,胁肩谄笑,唯唯诺诺,而追求真相、真理的勇气,亦为之折半,甚至泯灭。《史记·伯夷列传》引述贾谊《服鸟赋》云:“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
,看来“王土”“王臣”之说影响深广,他们亦将食粟与臣事新朝联系在一起,为了坚守节义,遂饿死于首阳山。《庄子·外篇·骈拇》载:“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荀子》《韩非子》将士人置于食或不食生死考验面前,让他们不得不低头屈服。上述《史记·李斯列传》有李斯所云:“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从人性角度,荀卿和李斯深知凡人热衷于追逐富贵利禄,并不甘于自居卑贱,而在王权体制中,君王掌控生杀予夺的权柄,就可以剥夺士人生存的权利,也可以剥夺其思想自由的权利,士人不得不向强权妥协,胁肩谄笑,唯唯诺诺,而追求真相、真理的勇气,亦为之折半,甚至泯灭。《史记·伯夷列传》引述贾谊《服鸟赋》云:“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
 现实就是:众庶多于烈士,众庶均贪恋生命,伯夷、叔齐毕竟是极少数。于是,《荀子》《韩非子》等强化“王土”“王臣”等概念,就建构起直抵人之心灵和思想意识的大一统集权政治。
现实就是:众庶多于烈士,众庶均贪恋生命,伯夷、叔齐毕竟是极少数。于是,《荀子》《韩非子》等强化“王土”“王臣”等概念,就建构起直抵人之心灵和思想意识的大一统集权政治。
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云:“案《吕览》之言,最合民约,与《荀子·礼论》篇不同,《荀子·礼论》一篇(即“人生而有欲”数语),由争斗之人群,进而论完全之邦国,其形态、秩序,最合于《墨子·尚同》篇。但《荀子》之意,以立君所以制民,而《吕览》之意,以立君所以利民,此其不同之点耳。”
 此论甚确,刘氏透彻地看到了《荀子》“以立君所以制民”的本质,而其制民之“心”的“帝王术”特质,则尚有待深入揭示!
此论甚确,刘氏透彻地看到了《荀子》“以立君所以制民”的本质,而其制民之“心”的“帝王术”特质,则尚有待深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