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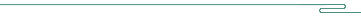
在《正蒙·太和篇》中,张载提出了著名的四句话:“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可以把这四句话称为“《太和》四句”。朱熹高度评价张载的“《太和》四句”,说“‘由太虚,有天之名’至‘有心之名’,横渠如此议论,极精密”
可以把这四句话称为“《太和》四句”。朱熹高度评价张载的“《太和》四句”,说“‘由太虚,有天之名’至‘有心之名’,横渠如此议论,极精密”
 。张载精心构撰的“《太和》四句”,具有对“天”“道”“性”“心”四大概念排列有序、界定清晰的特点,既是他对自己理学体系之形而上学部分的概括,也是其理学“纲领”。学者对何为张载理学纲领存在不同的理解。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牟宗三论及《正蒙·太和篇》第一章亦即“太和所谓道”这一章时指出:“此为《太和篇》之首段,大体是根据《易传》重新消化而成者。其所重新消化而成者,是以‘太和’为首出,以‘太和’规定道。‘太和’即至和。太和而能创生宇宙之秩序即谓为‘道’。”“此是《太和篇》之总纲领,亦是《正蒙》著于存在而思参造化之总纲领。”
。张载精心构撰的“《太和》四句”,具有对“天”“道”“性”“心”四大概念排列有序、界定清晰的特点,既是他对自己理学体系之形而上学部分的概括,也是其理学“纲领”。学者对何为张载理学纲领存在不同的理解。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牟宗三论及《正蒙·太和篇》第一章亦即“太和所谓道”这一章时指出:“此为《太和篇》之首段,大体是根据《易传》重新消化而成者。其所重新消化而成者,是以‘太和’为首出,以‘太和’规定道。‘太和’即至和。太和而能创生宇宙之秩序即谓为‘道’。”“此是《太和篇》之总纲领,亦是《正蒙》著于存在而思参造化之总纲领。”
 牟宗三认为,《太和篇》第一章不仅是该篇的“总纲领”,而且也是《正蒙》的“总纲领”。这意味着,他认为这一章是张载理学的总纲领。牟宗三所概括的张载理学“总纲领”有两个特点:一是认为,张载以“太和”规定道,把“道”这个单一概念归结为“总纲领”;二是认为,“总纲领”是以《易传》作为其经典依据的。牟宗三可能意识到,仅把体现客观性原则的“道”视作张载理学的总纲领,难以反映张载理学的完整内容,尤其难以说明“主客观之真实统一”
牟宗三认为,《太和篇》第一章不仅是该篇的“总纲领”,而且也是《正蒙》的“总纲领”。这意味着,他认为这一章是张载理学的总纲领。牟宗三所概括的张载理学“总纲领”有两个特点:一是认为,张载以“太和”规定道,把“道”这个单一概念归结为“总纲领”;二是认为,“总纲领”是以《易传》作为其经典依据的。牟宗三可能意识到,仅把体现客观性原则的“道”视作张载理学的总纲领,难以反映张载理学的完整内容,尤其难以说明“主客观之真实统一”
 。因而,他又引用张载《正蒙·诚明篇》“心能尽性,人能宏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宏人也”,认为这是“‘心能尽性’之总纲”
。因而,他又引用张载《正蒙·诚明篇》“心能尽性,人能宏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宏人也”,认为这是“‘心能尽性’之总纲”
 。这可以视作他对“太和之道”这一“总纲领”的补缀。
。这可以视作他对“太和之道”这一“总纲领”的补缀。
一种思想或学说的纲领,是指经过高度概括的框架表述,以概念组合或语句组合的形式,把特定思想体系的不同重要内容联结起来,并能够揭示该思想体系整体内容或局部内容的宗旨。此外,理论纲领或总纲领最好还要有经典资源作为依据。牟宗三所谓“总纲领”,仅以“道”这个单一概念为支撑,缺乏必要的框架结构形式;而“《太和》四句”则以“天”“道”“性”“心”四大概念为支撑,具备“纲领”的框架结构形式,因而其纲领特征相当突出。纲领性论述远比一般性论述重要,对二者不可等量齐观,应当格外倚重其纲领性论述。
多年前,笔者提出以“《太和》四句”作为张载的理学纲领
 ,但当时尚缺乏能够支持这一判断的经典依据。随着张载理学新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华书局版《张载集》外佚著《礼记说》辑本
,但当时尚缺乏能够支持这一判断的经典依据。随着张载理学新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华书局版《张载集》外佚著《礼记说》辑本
 ,是张载理学新文献之一。依据《礼记说·中庸第三十一》发现,张载“《太和》四句”原来是对《中庸》首章前三句的解说。
,是张载理学新文献之一。依据《礼记说·中庸第三十一》发现,张载“《太和》四句”原来是对《中庸》首章前三句的解说。
 《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句末的三个概念“性”“道”“教”,除了“教”不相应外,“性”“道”与张载“《太和》四句”的第二句和第三句对应,只是排列顺序不同。朱熹解读《中庸》前三句说:“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其本皆出乎‘天’。”
《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句末的三个概念“性”“道”“教”,除了“教”不相应外,“性”“道”与张载“《太和》四句”的第二句和第三句对应,只是排列顺序不同。朱熹解读《中庸》前三句说:“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其本皆出乎‘天’。”
 由于“性”“道”“教”这三个概念“以其本皆出乎‘天’”,因而,应当把《中庸》首章第一句第一个字“天”纳入前三句的概念系列,使之成为“天”“性”“道”“教”四个概念。这四个概念的前三个,与“《太和》四句”的概念系列“天”“道”“性”“心”前三个大致是对应的,同样也只是排列顺序不同。
由于“性”“道”“教”这三个概念“以其本皆出乎‘天’”,因而,应当把《中庸》首章第一句第一个字“天”纳入前三句的概念系列,使之成为“天”“性”“道”“教”四个概念。这四个概念的前三个,与“《太和》四句”的概念系列“天”“道”“性”“心”前三个大致是对应的,同样也只是排列顺序不同。
在理学家中,无论诠释儒家经典,还是解读前辈学说,朱熹都表现出很强的纲领意识。他在诠释“四书”“五经”时,便首先分述各书、各经之“纲领”
 。朱熹认为,《中庸》也有其纲领,其首章前三句就是“《中庸》纲领”
。朱熹认为,《中庸》也有其纲领,其首章前三句就是“《中庸》纲领”
 。张载经由对“《中庸》纲领”解说所形成的“《太和》四句”,本身也就具有了理学纲领的地位。可见,《中庸》正是张载理学纲领所依据的经典资源。张载理学新文献《礼记说》为张载理学纲领的确证,提供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思想资料,同时也为重新诠释“《太和》四句”的理学意义打开了空间。
。张载经由对“《中庸》纲领”解说所形成的“《太和》四句”,本身也就具有了理学纲领的地位。可见,《中庸》正是张载理学纲领所依据的经典资源。张载理学新文献《礼记说》为张载理学纲领的确证,提供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思想资料,同时也为重新诠释“《太和》四句”的理学意义打开了空间。
“《太和》四句”作为张载的理学纲领,其每一句解说中都渗透着对“《中庸》纲领”的传承和创新。张载的解说有两个特征:一是注重其整合,二是突显其宗旨。
第一,“《太和》四句”的整合诠释。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以整合为主,以分解为辅。张载的思维方式亦然。“《太和》四句”所界定的“天”“道”“性”“心”四个概念代表了天地间的四种存在,这四种存在之间具有互相感应和联结的关系。因此,不能把这四个概念切割开来,孤立地加以解释。
第一句“由太虚,有天之名”。无论是《中庸》首章前三句,还是张载“《太和》四句”,都将“天”置于概念序列的首位,作为最高概念。张载以道家“太虚”概念释“天”,是要批评秦汉以来儒者“知人而不知天”的“大蔽”
 ,从而改造儒家“天”观。句中的“由”字,是介词,有“因”“以”“用”等义,其引申义为依据、凭借。依据句意,笔者以“借用”释“由”字。张载借用道家的“太虚”概念以解说儒家之“天”,是因为他认为,秦汉以来儒者把原本形上的超越之“天”有形化、实然化、经验化了;
,从而改造儒家“天”观。句中的“由”字,是介词,有“因”“以”“用”等义,其引申义为依据、凭借。依据句意,笔者以“借用”释“由”字。张载借用道家的“太虚”概念以解说儒家之“天”,是因为他认为,秦汉以来儒者把原本形上的超越之“天”有形化、实然化、经验化了;
 而道家的“太虚”概念则具有无限性、超验性、非实然性等优点,可借此改造被汉儒实然化和经验化了的“苍苍之天”,从而使儒家之“天”重返超越和神圣的本体地位。
而道家的“太虚”概念则具有无限性、超验性、非实然性等优点,可借此改造被汉儒实然化和经验化了的“苍苍之天”,从而使儒家之“天”重返超越和神圣的本体地位。
第二句“由气化,有道之名”。古今不少学者都把这句话中的“道”归结为气或气化。这里的“由”字,与上一句一样,仍是借用的意思。张载对“道”的界定,借助了阴阳家和道家的气或气化。借助气化的主体是谁?当然是上一句的“天”。《中庸》第二十章曰:“诚者,天之道”,认为“道”是归属于“天”的。《中庸》还把“道”视作宇宙创生的力量。对于这两点,张载都是继承了的。朱熹解释此句说,“道”“虽杂气化,而实不离乎太虚”。
 可见,“道”既不可单独归结为“气”或“气化”,也不可单独归结为“天”或“太虚”,它是“太虚”与“气”的统一体。
可见,“道”既不可单独归结为“气”或“气化”,也不可单独归结为“天”或“太虚”,它是“太虚”与“气”的统一体。
 就张载的“天道”概念看,它具有一本(以太虚或天为本)、两层(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两个层次)、三合(天或太虚与阴阳气化三者整合)的特征。在儒学天道论历史上,张载第一次使“道”成为“天”或“太虚”与“气化”整合为一体的具有结构特征的概念。
就张载的“天道”概念看,它具有一本(以太虚或天为本)、两层(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两个层次)、三合(天或太虚与阴阳气化三者整合)的特征。在儒学天道论历史上,张载第一次使“道”成为“天”或“太虚”与“气化”整合为一体的具有结构特征的概念。
第三句“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此句中的“合”字,是整合的意思。张载说:“性其总,合两也。”
 这里的“合两”之“合”,同样也是整合的意思。这里所整合的是,本体之“天”或“虚”与现实之“气”。在张载那里,“道”与“性”二者是同构的,都是由“虚”与“气”构成的。这正是张载特别强调“性与天道合一”“性即天道”
这里的“合两”之“合”,同样也是整合的意思。这里所整合的是,本体之“天”或“虚”与现实之“气”。在张载那里,“道”与“性”二者是同构的,都是由“虚”与“气”构成的。这正是张载特别强调“性与天道合一”“性即天道”
 的主要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太虚即气”这一命题其实说的正是“《太和》四句”中“道”“性”这两个基本概念。
的主要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太虚即气”这一命题其实说的正是“《太和》四句”中“道”“性”这两个基本概念。
 “太虚即气”,与这里所说“合虚与气”,以及他处所说“太虚不能无气”
“太虚即气”,与这里所说“合虚与气”,以及他处所说“太虚不能无气”
 的意涵,都是一致的,都指太虚与气这两种不同的宇宙力量之间的联结与整合。尽管“道”与“性”是同构的,但二者在宇宙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则各有侧重:“道”,主要作为宇宙万物运行的动力,展现宇宙万物的变化过程及其秩序;而“性”,则主要作为宇宙万物生成的根源,赋予宇宙万物不同的秉性或本质。
的意涵,都是一致的,都指太虚与气这两种不同的宇宙力量之间的联结与整合。尽管“道”与“性”是同构的,但二者在宇宙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则各有侧重:“道”,主要作为宇宙万物运行的动力,展现宇宙万物的变化过程及其秩序;而“性”,则主要作为宇宙万物生成的根源,赋予宇宙万物不同的秉性或本质。
“太虚即气”的“即”字义,可以与张载话语系统中的“感”“合”等互证互释。“即”与“感”“合”,都是说“道”“性”内部存在虚、气相互感应、联结与整合的机制。关于“感”,是“同异、有无相感”
 的“感”,意为感应或感通,指特定主体对异质的他者发挥关联与整合作用的机制。关于“合”,亦即“合虚与气,有性之名”的“合”。按照张载论“合”的原则,指“合异”与“非有异则无合”
的“感”,意为感应或感通,指特定主体对异质的他者发挥关联与整合作用的机制。关于“合”,亦即“合虚与气,有性之名”的“合”。按照张载论“合”的原则,指“合异”与“非有异则无合”
 。这意味着,相“合”的二者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否则,“合虚与气”便不过是同语反复,毫无学理意义。在张载看来,“感即合也”
。这意味着,相“合”的二者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否则,“合虚与气”便不过是同语反复,毫无学理意义。在张载看来,“感即合也”
 。因而,“感”与“合”的意涵又是相通的。
。因而,“感”与“合”的意涵又是相通的。
第四句“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由于“《中庸》纲领”并未言及“心”,因而张载对“心”的界定便具有了观念创新的意义。这里的“合”字,仍是整合的意思。这里的“知觉”,主要指人的意识活动及其能力。但张载并非仅以知觉为心,而是认为知觉与性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心。应当说,张载对心的规定是相当独特的,也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了与后来朱熹的看法有所不同。朱熹认为:“横渠之言大率有未莹处。有心则自有知觉,又何合性与知觉之有!”
 张载所谓“心”,指主体以“性”为宇宙本体论根据的精神结构及其能力。他对“心”的这种规定,凸显了心的道德根据和方向,使心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同时也使学者对道德修养工夫的要求更加自觉和紧迫。
张载所谓“心”,指主体以“性”为宇宙本体论根据的精神结构及其能力。他对“心”的这种规定,凸显了心的道德根据和方向,使心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同时也使学者对道德修养工夫的要求更加自觉和紧迫。
总之,无论《中庸》纲领,还是张载理学纲领,都将“天”置于概念序列的首位,视作最高概念,而并未将“气”视作可与“天”“道”“性”相提并论的基本概念。因此,“气”仅仅是张载有关“天”“道”“性”“心”四大基本概念序列之外的辅助性概念,不宜将其拔高为张载天道论的首要概念。把“气”视作张载哲学体系中的本体概念或最高概念,无法从张载的理学纲领或其他理论学说中获得支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张载的“天”“道”“性”“心”四大概念中,除了“天”作为本体概念是无结构的,其他“道”“性”“心”三个概念都是有其内在结构的。其中,“道”与“性”都是由太虚与气整合而成的,
 因而是同构的。张载将“道”“性”“心”这三个概念结构化,
因而是同构的。张载将“道”“性”“心”这三个概念结构化,
 这是张载理学概念的突出特征,也是思想史上的理论创新。
这是张载理学概念的突出特征,也是思想史上的理论创新。
第二,“《太和》四句”的宗旨辨析。任何思想或学说都有其宗旨。对于张载理学宗旨的理解和解释,历来争议很大。流行的理解和解释是,把张载理学的宗旨归结为阴阳之“气”。《中庸》第二十章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以“继天立极”概括理学的“道统”,与《中庸》“不可以不知天”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以“继天立极”概括理学的“道统”,与《中庸》“不可以不知天”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
“阴阳”之名,起于西周晚期,属后世堪舆地形家之事。至战国时期,形成了“阴阳”的另一套说法,开始讲求天之气,而不再讲求地之形。
 张载的贡献是,以周、孔、思、孟的“天”观为基础,继承《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传统,并兼取阴阳家—道家的“气”论和“气化”论,将其纳入儒家的“天道”理论,从而把秦汉气化之“术”改造为“学”。
张载的贡献是,以周、孔、思、孟的“天”观为基础,继承《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传统,并兼取阴阳家—道家的“气”论和“气化”论,将其纳入儒家的“天道”理论,从而把秦汉气化之“术”改造为“学”。
 张载引进气论,加以消化,是他诠释《中庸》纲领的创新;但他绝没有因此就把“气”论作为自己理学的宗旨。在张载的话语系统中,“气”只是用以表述宇宙动能、自然元素、生物禀赋、生命活力等意涵的经验性词语,只是在“道”的构成要素及其表现形式的意义上才加以使用的;“气”并不具有价值意义,更无法作为宇宙本体。傅斯年曾指出,阴阳之教,五行之论,渊源于战国晚期的齐国,后来这一派在汉代达到极盛。
张载引进气论,加以消化,是他诠释《中庸》纲领的创新;但他绝没有因此就把“气”论作为自己理学的宗旨。在张载的话语系统中,“气”只是用以表述宇宙动能、自然元素、生物禀赋、生命活力等意涵的经验性词语,只是在“道”的构成要素及其表现形式的意义上才加以使用的;“气”并不具有价值意义,更无法作为宇宙本体。傅斯年曾指出,阴阳之教,五行之论,渊源于战国晚期的齐国,后来这一派在汉代达到极盛。
 余英时也曾指出,“‘气’这一概念并非汉代思想家的发明”,但“‘气’的观念在思想史上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则是在汉代”
余英时也曾指出,“‘气’这一概念并非汉代思想家的发明”,但“‘气’的观念在思想史上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则是在汉代”
 。清儒皮锡瑞认为,汉代儒学有“正传”,也有“别传”。他强调,孔子“删定六经,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
。清儒皮锡瑞认为,汉代儒学有“正传”,也有“别传”。他强调,孔子“删定六经,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
 。从历史脉络看,无论是先秦孔子儒学,还是宋代张载理学,都必不以阴阳五行或阴阳之气为宗旨;其间惟汉儒之学属于例外,并成为后世那些以气为宗旨的学说的理论源头。《中庸》纲领无一言及“气”,把诠释《中庸》纲领而形成的张载理学纲领归结为“气”,岂不扭转了从子思到张载以来儒学的思想方向?
。从历史脉络看,无论是先秦孔子儒学,还是宋代张载理学,都必不以阴阳五行或阴阳之气为宗旨;其间惟汉儒之学属于例外,并成为后世那些以气为宗旨的学说的理论源头。《中庸》纲领无一言及“气”,把诠释《中庸》纲领而形成的张载理学纲领归结为“气”,岂不扭转了从子思到张载以来儒学的思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