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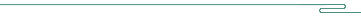
李士训《记异》所载《古文孝经》的发现,应当是经学史十分重要的事件,可惜未获得历代学人应有的重视。我们通过审察此一事件的真实与否,即可考见《记异》记事是否准确,亦可证其“初传与李太白”的记载是否可信。
《记异》说:“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与汉儒刘向、桓谭、班固等人所言《古文孝经》情形吻合。只不过,班氏、桓氏等人所言乃“孔壁古文”,其书已随孔传的失传而亡于梁末;隋世新出本又疑为刘炫伪造,“疑非古本”。二十二章的《古文孝经》之以古文字形行于世者,实有赖于大历初年的这次重要发现。
除李士训《记异》有载外,北宋古文字学家夏竦《古文四声韵序》也记载了这次发现。合两事观之,李士训所获石函绢素《古文孝经》乃出于灞上项羽妾墓之中,为秦汉之间旧物,非常可贵,所以当时就引起了李白、李阳冰等人的高度重视,转相传授和研习。
李阳冰从李白处接受了《古文孝经》,经过研习,“尽通其法”,一方面将其书“上皇太子”(当时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唐德宗);另一方面,又传与其子服之。贞元中,服之又传给韩愈等人。
王应麟《玉海》对此事也有所记:“李阳冰子服之,贞元中授韩愈以其家《科斗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后以归归登。其后以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再乞观之。张籍令贺拔恕写之(韩愈《科斗书后记》)。又渭上耕者亦得《古文孝经》。”
 可见在大历、贞元之间,《古文孝经》被李士训发现后,经历了初传李白,李白传李阳冰,阳冰上皇太子,阳冰又传其子服之,服之传韩愈,韩愈传归公(即归登),又传张籍、贺拔恕等人这一过程。这些都载在信史,记入方策,不应有丝毫造伪。只因其详情无人发覆,故对其所传《科斗孝经》与大历出土石函绢素《古文孝经》之间的因袭关系,每每讲不清楚,最为可惜。
可见在大历、贞元之间,《古文孝经》被李士训发现后,经历了初传李白,李白传李阳冰,阳冰上皇太子,阳冰又传其子服之,服之传韩愈,韩愈传归公(即归登),又传张籍、贺拔恕等人这一过程。这些都载在信史,记入方策,不应有丝毫造伪。只因其详情无人发覆,故对其所传《科斗孝经》与大历出土石函绢素《古文孝经》之间的因袭关系,每每讲不清楚,最为可惜。
如前所述,此本科斗《古文孝经》在五代、北宋都有传授,郭忠恕首次将其字形编入《汗简》,凡七例;句中正又据“旧传《古文孝经》”造《三体孝经》;李建中亦“尝得《古文孝经》,研玩临学,遂尽其势”
 。夏竦称赞说:“太学博士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编《汗简》,究古文之根本;文馆学士句中正刻《孝经》,字体精博;西台李建中总贯此学,颇为该洽。”
。夏竦称赞说:“太学博士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编《汗简》,究古文之根本;文馆学士句中正刻《孝经》,字体精博;西台李建中总贯此学,颇为该洽。”
 并据郭氏《汗简》和句氏《三字孝经》,将《古孝经》字形一一著录于《古文四声韵》达404例。此正与桓谭所谓古、今文“异者四百余字”的说法前后印证,若非出自真品不能如此巧合。
并据郭氏《汗简》和句氏《三字孝经》,将《古孝经》字形一一著录于《古文四声韵》达404例。此正与桓谭所谓古、今文“异者四百余字”的说法前后印证,若非出自真品不能如此巧合。
宋仁宗时,司马光从秘府发现科斗文《古文孝经》,并据之作《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复作《古文孝经说》
 ,还手书《古文孝经》,后人将之刻于大足北山石刻之中。
,还手书《古文孝经》,后人将之刻于大足北山石刻之中。
 其书旧时尚以为是汉代出于孔子壁中的《古文孝经》,但如前所述,其分章起讫、文字今古、经文内容以及与今文《孝经》异同之处,都与刘向、班固、陆德明、司马贞所言“孔壁古文”并不一致,应该在孔壁以外另寻渊源。经考证,该本疑即禁中秘府所藏的大历出土《古文孝经》,或许就是当年李阳冰“上皇太子”之本的异代流传。看来中唐以下直至北宋时期所传科斗《古文孝经》,有可能都渊源于大历初年的这次发现。
其书旧时尚以为是汉代出于孔子壁中的《古文孝经》,但如前所述,其分章起讫、文字今古、经文内容以及与今文《孝经》异同之处,都与刘向、班固、陆德明、司马贞所言“孔壁古文”并不一致,应该在孔壁以外另寻渊源。经考证,该本疑即禁中秘府所藏的大历出土《古文孝经》,或许就是当年李阳冰“上皇太子”之本的异代流传。看来中唐以下直至北宋时期所传科斗《古文孝经》,有可能都渊源于大历初年的这次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