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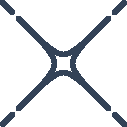
宋元理学基本范畴与命题的诗学表达问题,不管是其中心词“诗学表达”,还是充当限定语的“宋元理学基本范畴与命题”,都是较为抽象的词组或者短语。如果再对这些词组或者短语进行分解,则又可以析出若干概念或者范畴。显然,要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就必须对这些概念或者范畴有所把握,然后才能谈得上对课题本身进行研究。再就是,既然本课题涉及这些概念或者范畴,而概念或者范畴都是实践主体能动性的思维承载方式和主体藉以实现认知目的的工具,那么,这些概念或者范畴的组成物,是不是具有客观性,亦即是否具备历史的真实存在性及规律性等,都是我们从事课题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研究前提之后,才可以顺次而进入课题的研究环节。考虑到上述情况,显然,我们在确立研究课题时,就必须首先解决如下问题:
理学范畴与命题数以百计,为何本课题研究内容认定这些而不是那些作为“基本范畴与命题”?这一问题,可视作本课题研究的学理性前提或者研究基础。唯有对此问题有所探讨或者界定,才能筑牢本课题研究的基础。
我们知道,中西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先民围绕着“诗”与“哲学”关系问题,持续展开了至少四千年的论争。对此问题稍作叙述,有利于我们对于理学基本范畴与命题的诗学表达问题之历史渊源的认识。在西方文化史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最早对“范畴”作了系统研究,把它看作对客观事物的不同属性所作的分析归类而得出的基本概念,提出了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等十个范畴。他认为:“当若干事物虽然有一个共通的名称,但与这个名称相应的定义却不相同时,则这些事物乃是同名而异义的东西。”“反之,当若干事物有一个共通的名称,而相应于此名称的定义也相同的时候,则这些事物乃是同名同义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对“范畴”涵义的界定,为后来西方学者所遵从。中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奥卡姆则在《逻辑大全》中,认为“范畴”有两种意义:“在一种意义上,它被用来意谓根据一般性的大小排列的整个系列的词项。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个词被用来表示各个这样的系列中的第一个最一般的词项。”
亚里士多德对“范畴”涵义的界定,为后来西方学者所遵从。中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奥卡姆则在《逻辑大全》中,认为“范畴”有两种意义:“在一种意义上,它被用来意谓根据一般性的大小排列的整个系列的词项。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个词被用来表示各个这样的系列中的第一个最一般的词项。”
 显然,这里的“范畴”既包括“类属”之义,又包括此“类属”中的最一般的“类别”之义。康德则认为范畴不是来自经验而是知性先天原则或概念,他提出了一个范畴体系,包括十二个范畴,如“量的范畴”,包括“统一性”、“多样性”、“全体性”;“质的范畴”,包括“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系的范畴”,包括“依附性与存在性”、“因果性与相关性”、“交互性”;“样式的范畴”,包括“可能性——不可能性”、“存在性——非存在性”、“必然性——偶然性”。与康德有所不同,黑格尔则把“范畴”看作先于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客观实在”的绝对观念的发展过程的环节,亦即绝对观念的自我规定。康德、黑格尔对于“范畴”由来的看法虽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则是都把“范畴”视作“类属”。而在中国文化史上,现代中国学者常用的“范畴”一词,来自《尚书·洪范》。箕子在追溯“洪范”由来时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孔颖达疏:“‘畴’是辈类之名,故为类也。言其每事自相类者有九。”
显然,这里的“范畴”既包括“类属”之义,又包括此“类属”中的最一般的“类别”之义。康德则认为范畴不是来自经验而是知性先天原则或概念,他提出了一个范畴体系,包括十二个范畴,如“量的范畴”,包括“统一性”、“多样性”、“全体性”;“质的范畴”,包括“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系的范畴”,包括“依附性与存在性”、“因果性与相关性”、“交互性”;“样式的范畴”,包括“可能性——不可能性”、“存在性——非存在性”、“必然性——偶然性”。与康德有所不同,黑格尔则把“范畴”看作先于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客观实在”的绝对观念的发展过程的环节,亦即绝对观念的自我规定。康德、黑格尔对于“范畴”由来的看法虽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则是都把“范畴”视作“类属”。而在中国文化史上,现代中国学者常用的“范畴”一词,来自《尚书·洪范》。箕子在追溯“洪范”由来时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孔颖达疏:“‘畴’是辈类之名,故为类也。言其每事自相类者有九。”
 在孔颖达看来,“畴”为类别、类属之义。《辞原》把“范畴”解释为“类型”,当吸收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传统的因素。
在孔颖达看来,“畴”为类别、类属之义。《辞原》把“范畴”解释为“类型”,当吸收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传统的因素。
可以说,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到晚近的现象学美学代表人物波兰的英伽登(Roman Inganden)、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等,对此问题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中西方学者对于西方历史上存在的这一重大文化现象,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美国学者罗森的《诗与哲学之争》,从古希腊学者特别是从柏拉图出发,从多个侧面关注尼采以来现代思想所面临的危机,对“哲学”与“诗”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此乃“精神世界的永久战争”。马克·埃德孟森《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阿瑟·丹托《哲学对艺术的剥夺》等,都是通过对西方文明进程中的“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发展、变化的历史叙述来展开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十多年来,国内学者也对西方文明中的“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学术关注。亓元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诗与哲学之争”:怎么争?争什么?》借对《西方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一书的评价,对西方文明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奎志《“诗与哲学之争”的审美现代走向》则从“诗与哲学之争”的涵义演变、发展历程及审美现代走向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审视视角。从中国知网等检索亦可见,自进入21世纪至今,中国学者对于西方“诗与哲学之争”问题的研究,研究论文逐年增多,这些论文不管是在研究视域的宽广程度上,还是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当然,一些论文或因作者学术积淀等原因而有不少局限性,也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
无独有偶,如果把儒、道、释等视作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诗”与“哲学”关系问题,亦是左右中国古代诗学、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先秦儒家经典《尚书·尧典》提到“诗言志”,《论语》孔子强调《诗》之“兴观群怨”说,汉儒解《诗经》有“主文谲谏”说等,都是“哲学—诗”发生紧密联系的有力佐证。而《老子》、《庄子》用韵语来传达哲思意趣,当然亦是以诗歌形式来书写哲思意趣的文字写照。至于有汉四百年,从《郊祀十九首》、《房中歌》到《古诗十九首》等,以诗歌形式来书写哲思意趣,已经是颇为成熟的诗歌样式。魏晋之后,以诗歌形式来书写哲思情趣,已经成为历代诗人不言而喻的诗歌传统。而以玄言诗、步虚词、偈语诗、理学诗等为典型形态的哲理诗歌,更是中华文明中“诗”与“哲学”会通问题的重要呈现形式。文学史家把这些以诗歌形式来书写或者表达哲理的作品,称之为“哲理诗”。历代文论中,对中国古代的哲理诗的认识,要以民国人刘衍文的《雕虫诗话》最为系统和全面。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哲理诗发展及其代表人物有所总结。依其所言,宋元理学家之“哲理诗”为中国古代“哲理诗”之重要代表。他把中国历史上的“哲理诗”分为六种类型。其说云:“一曰概括旧有哲理之语以成韵语者”,认为“历代言哲理诗者必推程明道与朱晦庵,上更追仰邵康节,下乃及于王阳明、陈白沙与庄定山”。“二曰取用旧有哲理或故实以抒发成诗者。”“三曰宗尚旧有哲理而以新喻参证成诗者”,于此则举朱熹《感兴诗》和《观书有感》、程颢《偶成》、罗洪先《遣兴》等说明。“四曰赏诗者会心独远,以情志之抒为哲理之发者”,举陶渊明、杜甫、石曼卿三人诗作为例进行说明。其中,刘氏举石曼卿诗《题张氏园亭》:“亭馆连城敌谢家,四时园色斗明霞。富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邻隐士瓜。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纵游会得无留事,醉待参横落日斜。”在列举了程颢评价此诗“形容得浩然之气”之后,刘衍文进而评价:“自有诗人之诗以来,能得道学家如此称许者,可谓绝无仅有矣。然而此岂作诗之人本意所在哉。”“五曰诘难旧有哲理或故实而拓展成诗者。”“六曰作诗者参透世情物态道出之人生真谛者。”
 刘衍文对于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分类未必公允、客观,但也确实反映出中国古代哲理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史的历史进程来看,魏晋以后,历代士人对于“哲学—诗”关系的探讨也是不绝如缕的。仅就文道关系而言,自两汉以降,刘勰《文心雕龙》关于“文”之“道”的探讨,王通、韩愈、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人的“明道”、“贯道”文学观念,再到宋元理学家对于文、道关系的多重探讨,立足于“哲学—诗”关系而展开的文学批评论述,蔚然而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主线之一。上述说明:“哲学—诗”会通问题,亦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主线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中国古代诗学的独特面貌和文化精神。
刘衍文对于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分类未必公允、客观,但也确实反映出中国古代哲理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史的历史进程来看,魏晋以后,历代士人对于“哲学—诗”关系的探讨也是不绝如缕的。仅就文道关系而言,自两汉以降,刘勰《文心雕龙》关于“文”之“道”的探讨,王通、韩愈、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人的“明道”、“贯道”文学观念,再到宋元理学家对于文、道关系的多重探讨,立足于“哲学—诗”关系而展开的文学批评论述,蔚然而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主线之一。上述说明:“哲学—诗”会通问题,亦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主线之一,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中国古代诗学的独特面貌和文化精神。
从中国古代“哲学”—“诗学”的复杂关系来看,如果说,包括儒、道、释在内的“哲学”为中国古代诗学提供了内容、形式、表达方式和审美境界等诸支撑的话,那么,中国古代诗学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亦为中国古代“哲学”提供了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等包罗万象的“武库”。显然,要对中国古代诗学、哲学问题进行探讨,此两者的复杂关系是绕不过去的。可惜的是,较之学术界对西方文明中“诗与哲学之争”更为深入的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对中华文明中同样存在且地位亦不亚于西方文明的“诗与哲学”之关系的研究,显然是不足的。考察相关学术史可知,近百年来,伴随着现代意义上学科体系的建构以及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入,中西文明中均存在着的“诗”与“哲学”关系问题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出版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如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廖可斌《明代王学复古运动研究》、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张文利《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石明庆《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邓莹辉《宋元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陈忻《宋代文学与洛学研究》、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等有分量的研究专著,以及张鸣、祝尚书、左东岭、廖可斌、顾友泽、刘培、王利民、史伟、吴晟等学者的重要研究论文。这些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线索,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不少研究成果富有真知灼见。当然,毋庸讳言,限于时代因素及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所囿,其中某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学术缺憾。比如,一些学者在探讨宋元时期理学家的“诗”与“哲学”关系问题时,或习惯于泛泛而谈,以“往里凑”的方法来强作阐释;或热衷于对“诗”与“哲学”会通的外围问题,如作者门第师承、政治制度、地域文化传统等进行研究,而对“诗”与“哲学”会通问题得以发生的载体、关节点、产生条件及运行机制等缺少必要关注。特别是,很多学者在探讨哲理诗各种类型时,尚缺乏从“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其诗歌内容、主旨、审美风格及艺术境界等问题的生成条件、机制等。如此种种,导致了若干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科学性等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一些诗学研究学者对于宋明理学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明显不足,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理学义理问题。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因此,从理学“范畴”的诗学表达角度入手,来对宋元理学中的“诗”与“哲学”问题的会通性等问题进行研究,当然是可行的研究路径之一。显而易见,对“诗”与“哲学”会通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既是中西文明进行深度交流的客观需要,也是在当代世界文化融合背景下推进学术研究的迫切要求。
任何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必定是社会实践主体对一定范围内的历史存在,而实施的包括发生元点、结构形态、类别属性、价值、规律及其历史地位等多种层次的研究。显然,要推进“理学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这一学术研究课题,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何为范畴?理学范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理学基本范畴如何界定?理学基本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有无客观性的历史存在?显然,这些问题事关“理学—诗学”关系研究的基本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