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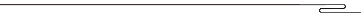
摘要: 将文化变量引入中非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中非关系的现状。此种视角并非否定权力在双方交往中的重要性,而是从文化与权力互动的视角来诠释中非关系。通过界定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权力和文化,分析其演进和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现代的权力研究呈现出将文化因素融入其中的趋势,而文化也从国际政治中的干预变量逐渐上升成为主要变量。具体到中非关系领域,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表现为文化对权力的建构,这种建构以中非双方的历史认同为基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为思想来源、以中非合作论坛为制度保障。可以说,现阶段中非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实质上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建构权力的实践。
关键词: 中非关系;文化;权力;建构
中国在非洲力量的扩大是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大陆上引人瞩目的发展动向之一。毋庸置疑,中国与非洲日益增加的交往已经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可以看到,中非之间的互动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更直达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但与此种现实不对称的是,文化因素的变量在中非关系研究中被长期边缘化,
 从学理上对此问题的分析就更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文化变量引入中非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解读与思考中非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但是,本文并非要否定中非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事实上,在整个西方世界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出现权力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出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其对国家力量的运用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外界的评价有褒有贬。因此,如何使用权力的问题是中国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但是,单纯侧重权力变量研究的现实主义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长,却没有寻求在世界上尤其是非洲大陆的主导地位,而始终坚持以平等的关系与非洲国家相处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只有战略性地分析权力与文化的互动,才能够解释单凭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或建构主义自身都不能充分解释的问题。
从学理上对此问题的分析就更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文化变量引入中非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解读与思考中非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但是,本文并非要否定中非关系中的权力因素。事实上,在整个西方世界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出现权力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出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其对国家力量的运用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外界的评价有褒有贬。因此,如何使用权力的问题是中国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但是,单纯侧重权力变量研究的现实主义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长,却没有寻求在世界上尤其是非洲大陆的主导地位,而始终坚持以平等的关系与非洲国家相处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只有战略性地分析权力与文化的互动,才能够解释单凭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或建构主义自身都不能充分解释的问题。
权力关系塑造了国际政治的本质,这一直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最为核心的论断之一。而与之相对的是,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被长期边缘化。但是,冷战的结束及后冷战时代文化和认同问题的凸显为国际政治的文化转向或者说回归提供了可能。
 “文明的冲突”
[1]
并非最近才有的现象,历史和当代的现实都表明了文化对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几乎没有国际关系学者会否认现代国际体系结构包含了许多文化成分。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分歧是:一是文化到底能够在多大的程度及在多大的意义上影响国家的行为;二是文化到底是合作的根源还是冲突的根源?基于此,本文首先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的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演进和发展的过程,指出现代的权力研究呈现出将文化因素融入其中的趋势;其次,在对文化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别从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阐述文化发挥影响的机制,并总结出文化和权力互动的模式。最后,从文化建构权力的视角重新审视中非关系中的合作与问题。
“文明的冲突”
[1]
并非最近才有的现象,历史和当代的现实都表明了文化对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几乎没有国际关系学者会否认现代国际体系结构包含了许多文化成分。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分歧是:一是文化到底能够在多大的程度及在多大的意义上影响国家的行为;二是文化到底是合作的根源还是冲突的根源?基于此,本文首先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的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演进和发展的过程,指出现代的权力研究呈现出将文化因素融入其中的趋势;其次,在对文化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别从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阐述文化发挥影响的机制,并总结出文化和权力互动的模式。最后,从文化建构权力的视角重新审视中非关系中的合作与问题。
权力是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但同时也是引发广泛争议的一个概念。与之相关并经常被换用的词汇包括实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等,这足以说明权力一词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和在运用中的复杂性。可以看到,在权力的角色和性质以及权力的目标和手段等问题上,不同的思想传统和理论流派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有时同一传统的学者也看法不一。比如,同为现实主义大师的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华尔兹对权力的理解就存在差异。在前者的著述中,权力既是国家追求的目的,也是国家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段。
 后者则认为,国家的权力只是国家生存的手段,不是国家政策的目的,国家获取权力只是为了国家的生存。
后者则认为,国家的权力只是国家生存的手段,不是国家政策的目的,国家获取权力只是为了国家的生存。
 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思想传统或学术流派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建构主义——权力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未被质疑。学者们无法达成共识的是权力的来源、构成以及运行机制。比如,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路径中以物质的方式定义权力,认为权力是由单纯的物质力量构成的;而与之相对的理念主义假设则是,权力主要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的。
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思想传统或学术流派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建构主义——权力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未被质疑。学者们无法达成共识的是权力的来源、构成以及运行机制。比如,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路径中以物质的方式定义权力,认为权力是由单纯的物质力量构成的;而与之相对的理念主义假设则是,权力主要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的。
 据此,理性主义认为权力的分配才是国际政治结构中的最重要变量,因此对权力及权力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之重点;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文化和观念的分配构成了国际政治的结构,其基本逻辑是,文化的变化引发国家身份的变化,国家身份的变化又导致国家利益的变化,国家利益的变化最终导致国家行为的改变。因此,文化才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有关建构主义对文化的讨论,将在下文深入阐述,这里主要考察国际关系中对权力的讨论和研究。
据此,理性主义认为权力的分配才是国际政治结构中的最重要变量,因此对权力及权力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之重点;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文化和观念的分配构成了国际政治的结构,其基本逻辑是,文化的变化引发国家身份的变化,国家身份的变化又导致国家利益的变化,国家利益的变化最终导致国家行为的改变。因此,文化才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有关建构主义对文化的讨论,将在下文深入阐述,这里主要考察国际关系中对权力的讨论和研究。
现代国际政治对于权力的分析和研究经历了一个“革命性”变化,即从“权力作为资源”(power-as-resources)到“权力作为关系”(relational power)的研究路径的转变。
[2]
当权力被视为资源,也就是摩根索所说的“国家权力的要素”时,权力包括了地理、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力、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等因素的综合,
 而这一路径在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著作中也得到了延续。
[3]
此种分析路径的潜在含义是,国家权力由许多不同要素组成,这些要素可以相加并得到一个总和,这个总和就代表了国家的真正实力。如此,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最为核心的自变量——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就是可以被计量的。但是,这种分析路径的问题在于其物质主义的方法,将权力等同于物质力量,从而过于简单机械地处理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未能看到非物质要素可能包含的分量和意义。因此,现实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具有足够国家权力要素的国家未必总能达到他想追求的目标。事实上,在国际政治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对一个国家的权力分析必须要包含对其他国家的目标和能力的分析。
而这一路径在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著作中也得到了延续。
[3]
此种分析路径的潜在含义是,国家权力由许多不同要素组成,这些要素可以相加并得到一个总和,这个总和就代表了国家的真正实力。如此,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最为核心的自变量——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就是可以被计量的。但是,这种分析路径的问题在于其物质主义的方法,将权力等同于物质力量,从而过于简单机械地处理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未能看到非物质要素可能包含的分量和意义。因此,现实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具有足够国家权力要素的国家未必总能达到他想追求的目标。事实上,在国际政治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对一个国家的权力分析必须要包含对其他国家的目标和能力的分析。
这就涉及了第二种研究路径,即将权力作为关系的路径。事实上,第一种路径在 20 世纪后半叶受到了第二种路径的挑战,这部分是由于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转向所致。 [4] 在这种分析路径中,权力首先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它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其次,它也是一种因果关系,即行为体A的行为引起或导致了行为体B的变化。最后,它也是一种不对称关系,即A与B处在不对称的位置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经对此有过经典定义:“A让(或者有能力让)B做B本来不会去做的事情。” [5] 以这种方式定义的权力在现实意义上更接近影响力的意思,即A能对B的决定和行为施加影响,无论此种影响是通过A对B的强制(威胁)、利诱还是吸引发挥作用。这种对权力的定义方式有着简单明晰的特点,同时也为更深入地研究权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其实,从第一种研究路径到第二种研究路径的转变并非是后者对前者的全盘否定。在将权力置于社会关系之中进行考察时,如果没有第一种路径中基于客观物质力量(资源)的计算,就很难真正说明行为体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权力要素越多,实现其对别国影响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权力要素只是实现其国际影响力的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首先,有的国家具备一定的权力要素,却缺乏足够的权力意图或者权力意志,也就无法在国际舞台上施加影响。其次,源于物质能力的权力只是影响力的一种来源,却远非最有效的来源。例如,著名现实主义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就曾经提出过威望的概念,指出诸如尊重和共同利益等许多因素构成了一个国家威望的基础,使之成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常备资源(日常货币)。 [6] 事实上,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得到信任、享有声望和具备权威,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诚然,在多数情况下,国家的威望是依靠其物质能力的支持,但不能否认的是,非物质能力亦是构成威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以上两种研究路径可以看出,将对权力的研究重点放在权力的实现手段和方式上似乎更具有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性的思想。作为最早提出“软权力”概念的学者,奈极大扩展了国际政治中权力理论的维度。
[7]
将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其实是将权力的来源分成了物质性力量和非物质性力量两种;将实现权力的方式分为强制、利诱和吸引 3 种,清楚表明了国家在不同的议题领域或者势力范围内应该采取的不同手段。中国学者陈志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软性软权力、软性硬权力、硬性硬权力和硬性软权力 4 种不同的权力模式,并正确地指出“作为权力运用的大局规划和策略,硬、软实力正朝着软使用方向发展是一种合乎潮流的方式”。
 上述学者的贡献在于,他们将原本处于国际政治研究边缘的非物质性力量——文化、制度、观念及规范等——带回到对权力这个国际政治的中心概念的研究之中。
上述学者的贡献在于,他们将原本处于国际政治研究边缘的非物质性力量——文化、制度、观念及规范等——带回到对权力这个国际政治的中心概念的研究之中。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经说过:“‘文化’这个术语因为它的多义性和模糊性,目前在社会人类学圈内名声不好。”
 几十年过去了,他所说的这种情况迄今为止也没有得到改善。至少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文化一词可以与意识形态、价值观、观念、规范和制度等术语联系在一起或者互换使用。甚至在一本专门研究国际政治的文化回归问题的著作中,居然也很难找到对文化清晰可见的定义。
几十年过去了,他所说的这种情况迄今为止也没有得到改善。至少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文化一词可以与意识形态、价值观、观念、规范和制度等术语联系在一起或者互换使用。甚至在一本专门研究国际政治的文化回归问题的著作中,居然也很难找到对文化清晰可见的定义。
 而最近一部以构建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为主旨的著作,则几乎通篇未对文化进行定义,更多的是在讨论欲望、精神和理智这三种动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而最近一部以构建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为主旨的著作,则几乎通篇未对文化进行定义,更多的是在讨论欲望、精神和理智这三种动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事实上,无论文化如何被定义,国际关系学者更加关心的:一是文化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政治?二是文化究竟是合作的根源还是冲突的根源?三是文化与权力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对立还是统一?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孰轻孰重?下面本文将从格尔茨对文化的定义着手,从体系和单位两个层次分别讨论文化的内涵及影响国际关系的机制,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事实上,无论文化如何被定义,国际关系学者更加关心的:一是文化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政治?二是文化究竟是合作的根源还是冲突的根源?三是文化与权力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对立还是统一?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孰轻孰重?下面本文将从格尔茨对文化的定义着手,从体系和单位两个层次分别讨论文化的内涵及影响国际关系的机制,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尽管格尔茨并非国际政治学者,但鉴于其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卓越地位,他对于文化的看法是值得引用和思考的。他指出:“文化尽管是观念化的产物,但它却不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中;尽管是非物质的,但它却不是一个超自然的实体。”
 也就是说,在格尔茨看来,文化不是简单的个人观念的集合,而是某种不可被还原至个人观念层面的共有知识;再者,文化虽然是非物质的,却是客观存在的和真实的。格尔茨随后解释道:“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系统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
也就是说,在格尔茨看来,文化不是简单的个人观念的集合,而是某种不可被还原至个人观念层面的共有知识;再者,文化虽然是非物质的,却是客观存在的和真实的。格尔茨随后解释道:“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系统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
 格尔茨的这个文化概念虽然简单,但却含义丰富,它至少说明:第一,文化具有历史性,因此往往是稳定的、持久的现象;第二,文化是一个意义结构,能赋予人认同,而认同则可以为人的生活提供相应的意义、秩序与可预测性;第三,文化是一个概念系统,因此既可以在体系层次上产生影响,也可以在互动层次和单位层次上发生影响。
格尔茨的这个文化概念虽然简单,但却含义丰富,它至少说明:第一,文化具有历史性,因此往往是稳定的、持久的现象;第二,文化是一个意义结构,能赋予人认同,而认同则可以为人的生活提供相应的意义、秩序与可预测性;第三,文化是一个概念系统,因此既可以在体系层次上产生影响,也可以在互动层次和单位层次上发生影响。
具体到国际政治领域,单位层次的文化属于温特所说的“自有知识”,对国家而言,这种知识往往来自国内因素或者意识形态因素。国家的自有知识可以成为国家判断国际形势和界定国家利益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是研究对外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体系层次的文化是“社会共有知识”,“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共有知识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互为敌人和互为朋友同样都是文化事实。文化有许多具体形式,包括规范、规则、制度、意识形态、组织、威胁体系等。”

从国际体系层次来考察文化,在社会学中是约翰·梅耶(John Meyer)和布莱恩·罗恩(Brian Rowan)所代表的斯坦福学派倡导的世界文化机制研究,
[8]
在国际政治中则是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所提出的国际体系文化研究。

迈耶和罗恩于 1977 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一文开创了组织社会学领域中的新制度主义学派。 [9] 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中心命题是强调合法性机制在组织结构内以及在组织与制度环境互动中的重要作用。比如,现代国家的存在和合法性就是西方文化扩张的结果,西方文化认可国家而非其他组织形式。事实证明,国家并非最有效的组织形式,特别是那些失败国家,但为什么还是要建立国家而非其他形式呢?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这就是世界文化机制的作用,即由外部文化合法性而非内部功能效率需求来决定官僚科层制度的存在及延续。制度主义者的结构是文化的,由西方理性和个人主义构成的文化创造了国家、市场、官僚组织以及资本主义自身。其实,社会制度主义者眼中的“世界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接近国际政治中的“国际规范”,对国家行为有约束作用。按照这种逻辑,文化是促进合作的重要因素。但是,现实远非如此美好。究其原因,世界文化机制学派所提倡的“文化”是西方文化而非其他文明或文化类型。他们的潜在假设是:西方文化就是普世文化。也正因为这样的假设,才会出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
国际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学派深受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影响,重视体系层次和互动层次的文化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建构和影响。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温特不认为文化一定有助于合作。在他看来,各国的国内文化可以没有相同之处,但国际体系的确存在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会影响到体系内成员的行为。国际体系文化大体可以分为 3 种: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以及康德文化。不同的体系文化会造就不同的国家行为。霍布斯文化的主体位置是“敌人”;洛克文化的主体位置是“对手”;康德文化的主体位置是“朋友”。
 换句话说,霍布斯文化体系主导下的国家之间的常态是冲突和战争;洛克文化体系主导下的国家关系是竞争和合作并存;康德文化体系主导下的国家关系是合作与和平。在此,温特特别强调角色身份的意义,在他看来,文化是有助于合作还是引发冲突取决于国家之间的身份和角色定位,即互为朋友还是互为敌人。
换句话说,霍布斯文化体系主导下的国家之间的常态是冲突和战争;洛克文化体系主导下的国家关系是竞争和合作并存;康德文化体系主导下的国家关系是合作与和平。在此,温特特别强调角色身份的意义,在他看来,文化是有助于合作还是引发冲突取决于国家之间的身份和角色定位,即互为朋友还是互为敌人。
从单位层次考察文化的作用主要是分析文化如何影响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和战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背景,因此用文化来解释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并不罕见。
 这种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将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第二类,将文化等同于观念和价值观;第三类,将文化等同于规范,其中文化又被分为政治文化、战略文化和组织文化 3 种类型。前两类大体是文化的因果作用研究,而第三类则涉及文化的建构作用研究。
这种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将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第二类,将文化等同于观念和价值观;第三类,将文化等同于规范,其中文化又被分为政治文化、战略文化和组织文化 3 种类型。前两类大体是文化的因果作用研究,而第三类则涉及文化的建构作用研究。
在第一类中,文化是可以与意识形态画等号的。比如,中外都有学者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是由意识形态而不是由某种狭隘构思的国家利益追求所驱动的。
[10]
美国学者迈克尔·H.亨特认为,文化不仅产生意识形态,而且可以支撑或抑制意识形态。在亨特的著述中,意识形态其实更像格尔茨所说的政治文化,因此他主张用文化分析的方法研究意识形态。
 中国学者王立新则将意识形态分为正式意识形态和非正式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后者可能比前者更加稳定和持久,因为后者根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之中,并因为潜藏在不自觉的意识中而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其影响可能也更大。
中国学者王立新则将意识形态分为正式意识形态和非正式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后者可能比前者更加稳定和持久,因为后者根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之中,并因为潜藏在不自觉的意识中而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其影响可能也更大。
 这些著作其实都说明了 3 个问题:第一,权力和利益背后总是有着文化的背景;第二,文化的作用是持久而深刻的;第三,文化的此种深层作用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这种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
这些著作其实都说明了 3 个问题:第一,权力和利益背后总是有着文化的背景;第二,文化的作用是持久而深刻的;第三,文化的此种深层作用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这种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
第二类研究将文化等同于观念和价值观。此类研究以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一书为代表。
 在这本书中,观念完全被定义为“个人持有的信念”。从哲学角度来看,只有个人才会持有观念和信念,这一点当然不错。但是,反过来却不能成立。如果认为所有信念都是个人信念,或者说都可以被还原为个人信念,这就是错误的了。戈尔茨坦和基欧汉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本书的问世表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开始重视观念和信念的作用。他们将观念这一非物质因素和理性主义的许多客观因素视为同样重要的变量,认为利益是客观因素,观念是主观因素,利益和观念都会影响行为体行为。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观念不是能够单独改变行为体核心利益的力量,而是协调政策的重要因素。还有,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主要是从因果作用的角度对待观念,这样做固然重要,但却不充分。观念怎样产生作用的问题不仅仅限于观念的因果作用方面。因此,对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而言,行为体之所以战略性地运用文化资源,仅仅是为了推进他们的自身利益,这和行为体利用其他资源是一样的。
在这本书中,观念完全被定义为“个人持有的信念”。从哲学角度来看,只有个人才会持有观念和信念,这一点当然不错。但是,反过来却不能成立。如果认为所有信念都是个人信念,或者说都可以被还原为个人信念,这就是错误的了。戈尔茨坦和基欧汉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本书的问世表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开始重视观念和信念的作用。他们将观念这一非物质因素和理性主义的许多客观因素视为同样重要的变量,认为利益是客观因素,观念是主观因素,利益和观念都会影响行为体行为。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观念不是能够单独改变行为体核心利益的力量,而是协调政策的重要因素。还有,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主要是从因果作用的角度对待观念,这样做固然重要,但却不充分。观念怎样产生作用的问题不仅仅限于观念的因果作用方面。因此,对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而言,行为体之所以战略性地运用文化资源,仅仅是为了推进他们的自身利益,这和行为体利用其他资源是一样的。
第三类研究是将文化等同于规范。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一书。在这本书中,国家的政治文化、战略文化和组织文化被用以解释国家偏好的根本原因。比如,江忆恩注意到中国战略文化与中国战略和外交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得出战略文化比其他变量更具有解释力的结论。
[11]
再比如,伊丽莎白·基尔代表了把军事学说作为内化优先选择方式的一种“文化主义”方法,这种思路与机构或功能解释是对立的。
 由此,卡赞斯坦认为,文化是指基于习惯或者法律之上的、民族国家权威或者认同的集体模式。文化既包括一套评价的标准(诸如规范和价值观),也包括一系列的认知标准(诸如规则和模式)。
由此,卡赞斯坦认为,文化是指基于习惯或者法律之上的、民族国家权威或者认同的集体模式。文化既包括一套评价的标准(诸如规范和价值观),也包括一系列的认知标准(诸如规则和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中的不同作者显然对文化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式呈现出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是因果方式;还有一种则认为是建构方式,即文化能够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从而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但这两者所指的经验现象是相同的,那就是驱动行为体付诸行动的共有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中的不同作者显然对文化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式呈现出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是因果方式;还有一种则认为是建构方式,即文化能够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从而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但这两者所指的经验现象是相同的,那就是驱动行为体付诸行动的共有信念。
综上所述,文化在单位层次上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规范等形态影响对外政策。不同文化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规范,也因此有着不同的对外政策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根本假设其实是关于异质性文化与冲突之间的关系。 [12] 按照亨廷顿的逻辑,许多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国内体制和价值观念被转化为对外政策,这些政策又与其他具有不同国内体制和价值观念国家的政策相冲突。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不可能学会在多样化情况下和平共处,也不是说相似的单位之间就没有冲突。但内部冲突可能是外部冲突的原因之一。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减少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增加他们利益的趋同,从而减少冲突的发生。
吉尔平曾经指出:“观念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寻求理解世界的理论必须……将观念和物质力量统合起来考虑。”
[13]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吉尔平的这段话可谓意味深长。物质主义理论使人们很难考察像文化这样的观念现象是怎样影响到像利益这样的物质现象的,因此,温特指出,要解释世界政治中的“少量重要大事”,最好首先考虑国家观念以及国家观念所建构的利益(国家文化),然后再考虑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这两位分属于不同学术流派的代表学者传达出的共同意思是,世界政治研究和外交政策研究都离不开对文化和权力的共同考察。重要的是,要表明文化形态是怎样与物质力量结合起来并赋予物质力量以意义的,物质力量又是怎样制约文化形态的。
这两位分属于不同学术流派的代表学者传达出的共同意思是,世界政治研究和外交政策研究都离不开对文化和权力的共同考察。重要的是,要表明文化形态是怎样与物质力量结合起来并赋予物质力量以意义的,物质力量又是怎样制约文化形态的。
传统意义上,文化与权力之所以有某种对立的含义,是源于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路径中以物质的方式定义权力。但是,建构主义路径为文化能够产生的权力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在建构主义者那里,权力就是由文化建构的。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连接在不同分析层面运作的过程,超越文化与权力的二分法。
基于前面对权力和文化内涵的学理性探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权力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类:第一,以国家行为和互动为基本出发点,分析权力和文化对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哪一个更大,或谁更关键。现实主义认为权力的作用大于文化,文化最多只能是权力作用的补充。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在权力成为背景因素的情况下,文化成为协调和制约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第二,文化是权力的工具。比如奈所提出的软权力概念即是将文化视为工具和手段。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中,文化和权力不是以平等的关系进行互动,文化始终处于权力的从属地位。第三,文化建构权力。这种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通过文化建构身份,身份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的途径得以实现。可以看出,文化变量在这三类研究中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逐渐由一个干预变量变为研究中的主要变量。无论是考察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政策,还是分析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又或是观察国际体系的变化和趋势,文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
总而言之,在国际政治的研究中,应该对权力和文化的互动进行战略性分析,避免将文化与权力要素简单化处理的思路。比如,不能认为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一定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或战争,也不能认为有着同质性文化的国家之间就一定没有冲突。另外,尽管有着强大物质权力的国家通常也有着向外传播和输出本国文化、制度和实践的冲动,有时甚至动用军事手段强制扩张,比如美国和苏联。但并非所有实力强大的国家都会如此,比如历史上的中国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没有向外输出自己文化活动的传教士般的热情。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内外学界对此项研究的热情也不断升温。目前,对中非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经验层面描述中非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二是从制度层面剖析中非关系,比如考察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轨迹。从总体上看,文化在这类研究中的作用或者被忽视或者被边缘化;同时,这些研究尚未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下对经验现象进行分析和解读,理论层面的研究相对滞后。
本文之前对文化影响国际关系的路径以及文化与权力互动模式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层地考察中非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在此,本文更多地采用建构主义的视角来考察当今的中非关系。换句话说,现阶段中非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实质上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建构权力的实践。此种视角并非否定权力在双方交往中的重要性,也并非反对应用其他变量来解释中非关系的发展,但希望能透过文化与权力互动的视角提供另外一种观察中非关系的框架。
事实上,尽管中国一直强调自身和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并以此作为双方共同的集体身份和价值理念,但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和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军事、经济和科技都较为落后的非洲,中国在双方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实质上的优势地位,并因此受到主要来自西方舆论的指责。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实并未影响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正如国内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所指出的,中国在对非政策中始终坚持的平等原则,是对西方国家奉行“强权即公理”原则的根本性颠覆,体现的是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传统。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实并未影响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正如国内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所指出的,中国在对非政策中始终坚持的平等原则,是对西方国家奉行“强权即公理”原则的根本性颠覆,体现的是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传统。
 也就是说,中国在非洲运用权力的方式并未受到中国实力日益上升的显著影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在非洲运用权力的方式并未受到中国实力日益上升的显著影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非在交往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积极的共有期望和记忆,或者说双方有着较深的历史认同和信任,此种认同即是前文所述的互为朋友的文化事实。这也正是大多数学者在论述中国对非洲政策时一般强调其历史连续性,而经常忽略其调适与变化的原因。
 并且,这种互为朋友的角色身份还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得以制度化,而制度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共有期望并形成新的规范和共识。在这样制度化的角色身份互动中,合作性质的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文化结构中,双方对于合作和收益的期望仍然是积极且稳定的。即便出现问题,也可望通过良好的沟通得到解决。应该看到,中非在历史交往中形成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非洲地区运用权力的方式,也决定了中非关系在现阶段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状态。正如有些学者所见,中非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厚的认同基础,而且双方相互认同的本质在 60 年的交往中不断扩大和强化,处于从历史认同到机制认同发展的过程之中。
并且,这种互为朋友的角色身份还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得以制度化,而制度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共有期望并形成新的规范和共识。在这样制度化的角色身份互动中,合作性质的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文化结构中,双方对于合作和收益的期望仍然是积极且稳定的。即便出现问题,也可望通过良好的沟通得到解决。应该看到,中非在历史交往中形成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非洲地区运用权力的方式,也决定了中非关系在现阶段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状态。正如有些学者所见,中非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厚的认同基础,而且双方相互认同的本质在 60 年的交往中不断扩大和强化,处于从历史认同到机制认同发展的过程之中。
 可以说,历史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现阶段对非政策的认知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中非合作论坛才能得以建立和发展,中非之间的关系方能形成制度认同。
可以说,历史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现阶段对非政策的认知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中非合作论坛才能得以建立和发展,中非之间的关系方能形成制度认同。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与埃及建交到 2006 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出台,中国的对非政策随着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在不断进行着调整和变化。从 1956 年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始,中国的非洲政策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是同步发展的,由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取向决定其外交方向。在此期间,中非关系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经济利益让道于政治外交需求。1971 年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对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中国则对非洲实行以单方面援助为主、双边贸易为辅的外交策略。
197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中国国家目标重新调整的开始。中非关系在此背景之下自然也经历了变化和调整,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逐渐开始变得与政治关系同等重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中国既需要自然资源又需要建立负责任的崛起中的大国形象,非洲成为中国最感兴趣的投资地点之一。换句话说,经济和贸易往来在此时的中非合作中的分量显著增加。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也从无偿改为有偿,从项目援建、人才培养和物资供给调整为共同发展、补偿贸易政策、推动国企进军非洲等。或者说,中国对非洲的外交方向已经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共赢。比如,从 1993 年开始,中国政府利用发展中国家已偿还的部分无息贷款资金设立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中小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在生产和经营领域开展合资合作。
 此种调整对非洲而言,意味着中国从不计较经济回报的“朋友”变成要从合作中受益的“伙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非之间平等而友好的历史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正如 2006 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所阐述的,中国要“继承和发扬中非友好的传统”,与非洲国家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此种调整对非洲而言,意味着中国从不计较经济回报的“朋友”变成要从合作中受益的“伙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非之间平等而友好的历史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正如 2006 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所阐述的,中国要“继承和发扬中非友好的传统”,与非洲国家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以上对中非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简短回顾充分表明,中非的历史交往在双方之间形成了深厚的历史记忆和认同,此种集体认同模式构成了双方互为朋友和伙伴的角色身份认知的文化基础。或者说,历史认同确立了中非之间友好关系的路径,中非此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会依赖这种路径。此外,这种路径还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得以制度化,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双方又形成新的规范和原则,强化之前的历史文化认同。基于此,双方即使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并不相同,或者说双方在事实上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之中,但由于上述的历史认同及由此而形成的互为朋友的文化事实,中国始终以平等的原则与非洲国家交往。
如前文所述,文化在单位层次通过价值观和规范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和对外行为。具体到中国这个国家,有国外学者注意到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对中国战略选择或曰战略偏好的持续性影响,比如在作战时倾向于进攻性地使用武力。
[14]
而另外一种广泛存在于政治文化之中的“以和为贵”的价值观以及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规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学者李安山正确地指出中国的文化有着“仁、恕、信、平等”的基因,希望研究者们更多地注意到这种基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
 另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大同”思想,将其置于当下的语境,就是世界要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国与国之间要实现和谐共处。
另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大同”思想,将其置于当下的语境,就是世界要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国与国之间要实现和谐共处。
 更有学者直接提出“道德力量中国”的说法,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善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强调道德责任的政治文化,即中国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运用知识、智慧、纪律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维护国际社会和谐。
更有学者直接提出“道德力量中国”的说法,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善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强调道德责任的政治文化,即中国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运用知识、智慧、纪律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维护国际社会和谐。

事实上,相较于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交往,中国政治文化中关于平等、宽容和仁慈的思想和价值观在与非洲的交往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方面是前文提到的正面的历史记忆;还有一方面是中国对于弱者的天然同情。以中国对非援助为例,尽管此种援助实践被西方普遍诟病,但在非洲当地却大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不愿对其他国家以施舍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而是以兄弟和朋友的名义互相帮助、施以援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也开始有学者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认识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仁”和“德”的重要影响。 [15] 除此之外,有西方研究者提出,中国与非洲的良好关系以及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并非只是中国经济实力上升的副产品或者只是中国对非洲原材料不断上涨的需求,而是中国在非洲长期经营的结果,这种经营包括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以及文化和技术交流。该研究人员特别提到中国在非洲的医疗队为非洲的公共产品所作出的贡献,并称其为“医疗外交”。 [16] 当然,中国的对非援助并非无懈可击,在援助方式和制度上的确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但相比西方而言,中国在对非援助的理念上是有中国“特色”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
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以及 10 年的实践不仅有效地推动了中非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国际影响。正如 2006 年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所指出的:“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中非进行集体对话与多边合作的有效机制,构筑了中非间长期稳定、平等互利新型伙伴关系的重要框架和平台。”
 在这份文件中,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则被凝练为“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这 16 个字。共同规范和原则共识的形成构成了中非合作机制的思想基础。
在这份文件中,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则被凝练为“真诚友好、平等互利、团结合作、共同发展”这 16 个字。共同规范和原则共识的形成构成了中非合作机制的思想基础。
事实上,任何制度的有效运行都需要制度参与者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并在参与者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集体认同。而同时,制度的有效运行又会创造新的集体利益和集体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参与者的利益,从而影响参与者权力的使用。制度中的大国利益固然重要,但这种个体利益必须与更大的集体利益保持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对大国权力的建构作用得以体现。首先,尽管中非合作论坛从制度架构上来说并非强制度类型 [17] ,但一旦中非双方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嵌入制度之中,通过制度的渠道进行沟通和平衡,那么中非双方的利益就更有保障,对实力稍强的中国也会形成一定约束。其次,论坛的弱制度性质有利于双方作出让步和妥协,对国家主权的干涉也相对较少,更容易处理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最后,平等原则是论坛的题中应有之义,中非合作论坛在制度上保证了双方的平等。
应该看到,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合作对双方的发展总体而言都有利。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新的矛盾也随之产生。有学者就指出中国在非洲面临着四大矛盾:中国国家利益与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利益的矛盾、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的矛盾、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与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利益的矛盾、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上述这些矛盾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外界对中国发出越来越多的指责和批评。例如,2007 年 2 月 19 日的《纽约时报》刊出社论《非洲恶治的庇护者》,在这篇社论中,中国在非洲实施“冷酷的人民币外交”,出于对石油的需求,与苏丹和津巴布韦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关系”。同时,中国在非洲的很多投资缺乏透明度,对当地人民和环境造成伤害。
上述这些矛盾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外界对中国发出越来越多的指责和批评。例如,2007 年 2 月 19 日的《纽约时报》刊出社论《非洲恶治的庇护者》,在这篇社论中,中国在非洲实施“冷酷的人民币外交”,出于对石油的需求,与苏丹和津巴布韦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关系”。同时,中国在非洲的很多投资缺乏透明度,对当地人民和环境造成伤害。
 而在不久前,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安哥拉记者在《世界事务》杂志上措辞严厉地批评中国在安哥拉的投资建设行为,并斥之为“新帝国主义”。
[18]
2013 年年初,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在给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时指出,非洲应该抛弃对中国的“浪漫幻想”,将其视为竞争者,认清中国“殖民主义的本质”。
而在不久前,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安哥拉记者在《世界事务》杂志上措辞严厉地批评中国在安哥拉的投资建设行为,并斥之为“新帝国主义”。
[18]
2013 年年初,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在给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时指出,非洲应该抛弃对中国的“浪漫幻想”,将其视为竞争者,认清中国“殖民主义的本质”。
 尽管这些论调未必经得起推敲和考证,
尽管这些论调未必经得起推敲和考证,
 但却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一定伤害,并促使中国反思自身在与非洲国家交往时所出现的问题。
[19]
但却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一定伤害,并促使中国反思自身在与非洲国家交往时所出现的问题。
[19]
正如巴里·布赞所指出的,随着交往密度的加大,文化互动和共同进化也会加速,但这一趋势并不必然导致文化同质或政治同质现象。
[20]
在中非关系中,中国一直强调和非洲有着共同的集体身份,在与非洲的交往中,中国也非常克制自身权力的运用。事实上,对自我进行约束是形成集体身份和友好关系的最根本基础,但集体身份从根本上说不是根植于合作行为(尽管合作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是根植于对他人和自己的文化差异所表现出来的尊重。近年来,中国决策层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因此非常乐于使用软权力战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21]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同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非洲大陆交往时,中国现有的软权力战略、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努力仍显不足。
 无论是对于非洲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形态的多样性还是文化内容的多维性,中国都需要时间和耐心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只有建立在充分了解和真正尊重彼此文化基础上的合作,才是更为厚重和持久的合作。
无论是对于非洲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形态的多样性还是文化内容的多维性,中国都需要时间和耐心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只有建立在充分了解和真正尊重彼此文化基础上的合作,才是更为厚重和持久的合作。
本文系统地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关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文化与权力关系的 3 种类型:一是文化是权力的补充;二是文化是权力的工具;三是文化建构权力。在这三种类型中,文化从干预变量上升为主要变量,充分说明文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无论是制定一国外交方略的现实需要,还是把握文化冲击下的国家间关系,文化与权力的互动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具体到中非关系的研究领域,本文认为,单纯侧重政治和经济的研究已经不足以描述和分析当前中非关系的状态。在考察中非关系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本文提出,中非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权力的实践。此种文化既包括历史认同,也包括政治价值观,同时还包含了制度。上述这些文化要素共同建构了中国在对非关系中使用权力的路径和方式,决定了中国在实力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也不会寻求对非洲的主导权,而是始终坚持对非洲平等而友好的传统。当然,中非关系现在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但双方要通过更好的文化沟通来解决,诉诸中非的历史记忆和共同价值观,真正实现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目标。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论文原载《西亚非洲》2014 年第1 期)
注释
[1]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Simon and Shuster,1996.
[2] David A.Baldwin, Paradoxes of Power ,New York:Blackwell,1989.
[3] 参见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Addison-Wesley,1979;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W.W.Norton,2001。
[4] 在这方面,西方学界比较认可的代表作是Harold D.Lasswell and Abraham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A Framework for Inqui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0。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要讨论权力概念几乎不能不提及福柯,特别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福柯不将权力看作一种真实的实体,而是看作一种关系。事实上,他思考权力的角度十分具有启发性,比如权力是物质的还是关系的,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参见Michael Foucault, Power/ Knowledge-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Brighton,Sussex:Harvester,1980.
[5] Robert A.Dahl,“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Behavioral Science ,1957,Vol.103,No.1,pp.201-215.
[6]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30-31.
[7]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Basic Books,1990;Joseph S.Nye, 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Joseph S.Nye,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
[8] John Meyer,John Boli and George M.Thomas,“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Vol.103,No.1,pp.144-181;John Boli and George M.Thomas,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9] John Meyer and Brian Rowan,“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Vol.83,No.2,pp.340-363.
[10] 参见Stephen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 eign Polic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 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11] 参见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战略》,载[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6—252 页;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12]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Simon and Shuster,1996.
[13]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20.
[1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15] 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6] Drew Thompson,“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From the ‘Beijing Consensus’to Health Diplomacy,” China Brief (Jamestown Foundation)October 2005,Vol.5,No.21,October 2005,http:// csis.org/ files/ media/ csis/ pubs/ 051013_china_soft_pwr.pdf,October 15,2013.
[17] 关于强制度和弱制度的区别以及弱制度的优势,参见Kenneth W.Abott and Duncan Snidal,“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0,Vol.54,No.3. pp.421—456。
[18] "Rafael Marques de Morais,“The New Imperialism:China in Angola,” World Affairs ,March /April 2011,pp.67-74.
[19] David M.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Might,Money and Mind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
[20] Barry Buzan,“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0,Vol.86,No.1,pp.22-23.
[21] Trefor Moss,“Soft Power?China Has Plenty,” the Diplomat ,June 4,2013,http:// thediplomat.com/ 2013 /06 /04 / soft-power-china-has-plenty/,October 24,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