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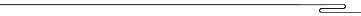
摘要: 伴随自身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外部形势的发展变化,当前中国对国际规范的政策立场已经由单向适应向适应和主动塑造两者并行转变,其中尤以主动塑造国际规范为未来的对外政策之重。如何理解这种政策变化背后的逻辑?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观察:中国自身发展经历带来的政策需求和基于这种需求而对国际规范产生的变革期待。从现实来看,中国虽然意识到了主动塑造国际规范的重要性,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尤其在具体操作和理念提出层面上面临巨大挑战。这决定了中国需要以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规范的变革进程之中。
关键词: 两种需求;问题与挑战;主要策略
伴随自身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外部形势的发展变化,当前中国对国际规范的政策立场已经由单向适应向适应和主动塑造两者并行转变——其中尤以主动塑造国际规范为未来的对外政策之重。如何理解这种政策变化背后的逻辑?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观察:中国自身发展经历所带来的政策需求和基于这种需求而对国际规范产生的变革期待。从现实来看,中国虽然意识到了主动塑造国际规范的重要性,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尤其在具体操作和理念提出层面上面临巨大挑战。这决定了中国需要以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规范的变革进程之中。
在自身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国际规范的互动具有了特别的发展内涵,因为从历史上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一个如此“异质”的体系内谋求实现和平崛起。鉴于自身崛起对国际体系转型产生的根本性影响,中国在与国际规范互动过程中将无法也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角色行事。相反,面对来自国际规范日益增强的刚性约束和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中国唯有将自身的理念注入国际规范的发展进程之中,才能实现对国际规范刚性约束的历史超越。展望未来,两种需求将对这一过程发挥着决定性影响。
回顾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促进中国迅速崛起的原因固然来自许多方面,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中国作出了融入国际体系的选择,并对其中的国际规范总体上采取了接受和遵守的政策,因而成为国际规范的重要受益者。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发展已经日益离不开世界,保持对国际规范的持续融入有利于中国继续享受其中的制度红利和进一步的发展壮大。这决定了未来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动力去采取大破大立的做法来对待国际规范。相反,在与国际规范的共处中寻求并拓展国家利益,仍是中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必然坚持的理性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美国权势的逐步衰落,全球治理及相应的国际机制已然成为全球竞争的重点。”
 鉴于国际机制与国际规范的密切联系,这种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国际规范的竞争。它已不仅仅关系到各国间的短期利益之争,从长远来看,还涉及未来国际秩序如何建立的大问题。
鉴于国际机制与国际规范的密切联系,这种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国际规范的竞争。它已不仅仅关系到各国间的短期利益之争,从长远来看,还涉及未来国际秩序如何建立的大问题。
 在这方面,中国的机制建设能力明显不足。因此,保持对既有国际规范的持续融入也是弥补中国在机制建设上的“短板”的一条捷径。对中国而言,深入了解国际规范的创制、演进和变革过程是未来取得国际话语权和机制创制权的必经环节。同时,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也有利于中国通过争取制度性权力进而实现和平崛起国家战略的目标。因为“将中国崛起寓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之中,有助于缓解面临的战略压力,节约了自身发展的成本,同时拓展了外交回旋余地,增加了与守成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这方面,中国的机制建设能力明显不足。因此,保持对既有国际规范的持续融入也是弥补中国在机制建设上的“短板”的一条捷径。对中国而言,深入了解国际规范的创制、演进和变革过程是未来取得国际话语权和机制创制权的必经环节。同时,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也有利于中国通过争取制度性权力进而实现和平崛起国家战略的目标。因为“将中国崛起寓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之中,有助于缓解面临的战略压力,节约了自身发展的成本,同时拓展了外交回旋余地,增加了与守成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
 。
。
简言之,作为现存国际规范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角色和在未来能够继续从其中获得红利的前景,决定了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塑造将会采取“改革者”而非“革命者”的姿态——规范中的合理之处将得到遵守和维护,而其不合理之处将会被修正或弥补。
“对国家而言只要处于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中就会出现约束行为的国际规范,并且会产生将规范组合而建构国际制度的需要。”
 在当前国际体系结构发生重大转型和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的大背景下,现存国际规范和新国际规范要想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必须与形势的发展密切契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期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在当前国际体系结构发生重大转型和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的大背景下,现存国际规范和新国际规范要想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必须与形势的发展密切契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期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现存国际规范变革进程应该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应兼顾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立场考虑融入国际社会和同国际接轨的。”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努力之所以收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能被动参与、接受国际规范的变革和修订,没能获得主动权。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自身的蓬勃发展客观上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强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动其作为一个整体积极参与国际规范的变革和修订进程,既是整合发展中国家内部关系,推动国际力量更加平衡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西方国家处心积虑推行全球治理“再规则化”的需要。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努力之所以收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是只能被动参与、接受国际规范的变革和修订,没能获得主动权。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自身的蓬勃发展客观上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强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动其作为一个整体积极参与国际规范的变革和修订进程,既是整合发展中国家内部关系,推动国际力量更加平衡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西方国家处心积虑推行全球治理“再规则化”的需要。
其次,新议题领域国际规范的生成应注入新的制度理念,不应照搬既有的国际规范生成模式,更不能只体现某些国家的单边意志。以网络、气候和反恐为代表的新议题领域的出现为新型国际规范的诞生开启了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说其开启了空间是因为,这些新议题领域——如网络问题,正对世界政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态,
 “信息网络对国际制度转制、改制和创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信息网络对国际制度转制、改制和创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这些新议题领域又大多缺乏完善的规范管理,充其量也不过“介于通过等级规则施加管理的综合制度与没有可识别的核心,且不存在相互联系的零散实践及制度之间”
另一方面,这些新议题领域又大多缺乏完善的规范管理,充其量也不过“介于通过等级规则施加管理的综合制度与没有可识别的核心,且不存在相互联系的零散实践及制度之间”
 。这种现状意味着,新议题领域既可能为新国际规范的发展提供空间,又不排除现存国际规范在其中得到大力推广的机会。就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正不遗余力地将各种体现自身利益的国际规范应用于上述领域,试图抢占创制国际规范的制高点,这对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新国际规范的生成构成了巨大挑战。对此,中国认为,新议题领域国际规范的确立应该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剔除其中的强权政治思维,避免其最终沦为个别国家野心的附庸。
。这种现状意味着,新议题领域既可能为新国际规范的发展提供空间,又不排除现存国际规范在其中得到大力推广的机会。就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正不遗余力地将各种体现自身利益的国际规范应用于上述领域,试图抢占创制国际规范的制高点,这对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新国际规范的生成构成了巨大挑战。对此,中国认为,新议题领域国际规范的确立应该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剔除其中的强权政治思维,避免其最终沦为个别国家野心的附庸。
再次,国际规范的延续和变革不应以牵制甚至遏阻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为目标。如前所述,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进程采取了遵循国际规范的做法,享受了巨大的制度红利,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突然转而采取“革命者”的姿态对待现存的国际规范体系。另一方面,面对世界权力结构的快速变革,现存的国际规范体系确实需要做出积极的调整来体现这一趋势——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必然要弱化西方在其中的地位和利益。从过去 10 多年间的表现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显得十分不适应,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近年来更是消极应对,
 表现出了一定的“规制中国”意图。
[1]
对此,中国认为,国际规范体系的变革应该体现世界潮流发展的大趋势,不应成为个别国家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表现出了一定的“规制中国”意图。
[1]
对此,中国认为,国际规范体系的变革应该体现世界潮流发展的大趋势,不应成为个别国家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就现实来看,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蓄意以破坏性方式来推翻现存的国际规范体系,反而采取了渐进式的改良做法来推动规范的体系变革。客观上讲,无论倡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的建立,还是推动国际社会在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的建章立制,中国付出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存国际规范体系的缺失和疏漏之处,是建设性地完善而不是损害现存的国际规范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规范体系的改革如果以牵制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的话,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将难以存续。
强调主动塑造国际规范无疑是中国外交政策理念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变化。某种程度上讲,它是中国从大国到强国,从地区大国到全球大国的必然取向,是为中国崛起进行的理论准备。
 但就现实情况来看,实现这一转变却是“知易行难”:例如,在具体事务上,当前中国缺少精通国际规范运作方面的“高、精、尖”人才储备,更不用说在经验和技能上存在着明显的短板。而在观念层面,如何淡化乃至消除国际规范演进过程中的强权主义色彩,最终将体现中国政治智慧的理念注入其中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总体而言,内外种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塑造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仅就当前形势来讲,中国在实现塑造国际规范目标过程中,面临着如下主要问题和挑战。
但就现实情况来看,实现这一转变却是“知易行难”:例如,在具体事务上,当前中国缺少精通国际规范运作方面的“高、精、尖”人才储备,更不用说在经验和技能上存在着明显的短板。而在观念层面,如何淡化乃至消除国际规范演进过程中的强权主义色彩,最终将体现中国政治智慧的理念注入其中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总体而言,内外种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塑造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仅就当前形势来讲,中国在实现塑造国际规范目标过程中,面临着如下主要问题和挑战。

历史上凡是成功塑造全球性国际规范的国家,无一不拥有鲜明的、具有极强感召力的治理理念。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国际规范的国家,18—19 世纪的英国在推行“自由贸易”理念方面可谓不遗余力。这一理念对英国借此在全球四处出击,建立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秩序至为关键。因为英国明白,“在一个贸易开放的世界中,英国在工业和金融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它占有对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决定性优势。”
 “自由贸易”理念源于英国国内资产阶级的需要,但它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统合,有利于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因而对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至于美国,则是通过国际规范确立本国霸主地位的典范。众所周知,早在“二战”前,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即已勾勒了美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大致轮廓。及至“二战”结束,美国通过一整套国际组织和规范体系来治理世界的框架已基本成形。从其内容来看,美国建立的这一套国际规范体系标榜以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自由航行等理念为中心,将美国的战略意图与对国际秩序各个领域的深层规划和设计相结合,其对战后世界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出了英国当年的成就。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自由贸易”理念源于英国国内资产阶级的需要,但它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统合,有利于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因而对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至于美国,则是通过国际规范确立本国霸主地位的典范。众所周知,早在“二战”前,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即已勾勒了美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大致轮廓。及至“二战”结束,美国通过一整套国际组织和规范体系来治理世界的框架已基本成形。从其内容来看,美国建立的这一套国际规范体系标榜以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自由航行等理念为中心,将美国的战略意图与对国际秩序各个领域的深层规划和设计相结合,其对战后世界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出了英国当年的成就。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与之相比,当前中国强调塑造国际规范的努力只是一个开端,还有待于进行大量艰苦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工作。一方面,中国需要清晰的国家定位,明确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和作用。与英、美相比,当今世界的复杂形势和中国自身现实决定了中国不会将谋求成为一个霸权式主导国家作为基本国家目标,这也决定了中国在推动现存国际规范变革和塑造新国际规范过程中不会实行“一家独大”式的安排。另一方面,结合国家定位和世界发展趋势,提出前瞻性的、具有极强感召力的理念口号,并且对具体领域进行精细的制度设计,增强规范的可操作性。
在这方面,中国取得的新进展是提出了“亲、诚、惠、容”理念和旨在落实这一理念并整合欧亚经济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客观地讲,“亲、诚、惠、容”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非比寻常的眼界、立意和抱负,逐渐推进并实现之,其对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推进国际规范变革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以笔者之见,“亲、诚、惠、容”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已提出了明晰的理念表达和宏大的愿景设计,下一步就需要对其进行细化和深化,不仅要让这一理念为国际社会所认知、所认同,而且紧密结合落实这一理念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通过翔实的制度设计,将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注入其中,为国际规范演进增添中国元素。
中国外交中事务主义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与过去 30 多年时间里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有关。鉴于自身长期孤立状态而带来的对众多国际规范的了解不多、熟悉程度不够等弊病,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不可避免要学习和接受为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和遵循的国际规范,而 20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做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口号客观上强化了这一倾向——事实上,也正是这一倾向使得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国际规范的模范遵守者。另一方面,与中国的开放模式及其带来的人们的思维惯性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际规范的接纳和遵循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其中尤以经济领域为最。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为兑现加入WTO而做出的众多承诺和充分利用由此带来的新机遇,中国在经济领域对国际规范的接纳更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过其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是——强调对国际规范的大力接纳很大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创设和塑造国际规范的一面,绝大部分精力被投入如何适应国际规范上,而对提出新议题、创设新议程等方面的关注明显不足。这一思维经过长时段的调适后极易保持原有的惯性,在面临需要做出重大改变时往往难以短时间内得到快速矫正。
问题是,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与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决定了中国需要适时做出调整,扭转目前过分强调事务主义的倾向,需要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思路和对策。具体来讲,中国需要认真总结近些年来为解决新问题而由外交官个人或国家做出的、具有积极启示意义的行为。前者表现为一些驻外人员围绕解决问题或突发事件而做出的创新性行为。
 这些行为虽然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但其对转换外交思路,实现“在既定方向和适度调整之间发现新的平衡点,即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基本路线为基础,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和‘有所作为’的力度”
这些行为虽然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但其对转换外交思路,实现“在既定方向和适度调整之间发现新的平衡点,即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基本路线为基础,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和‘有所作为’的力度”
 大有裨益。后者表现为中国近年来为维护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而在危机发生时做出的诸如打击索马里海盗、从利比亚撤侨等重要举动。就其认知根源来讲,这些举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如何看待现存的国际规范体系有关。
大有裨益。后者表现为中国近年来为维护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而在危机发生时做出的诸如打击索马里海盗、从利比亚撤侨等重要举动。就其认知根源来讲,这些举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如何看待现存的国际规范体系有关。
就基本选择来看,中国塑造国际规范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深度参与以实现对现存国际规范的逐步变革。二是谋划建立新组织或新机构来推行新的国际规范。前者表现为中国近些年来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份额和发言权逐渐扩大。后者表现为中国积极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性国际组织,通过参与解决地区性问题来确立新的国际规范。
两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大国权力竞争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存国际规范说到底体现了占优势地位一方的意志和利益,是强者做出的制度安排,因此规范的确立者对其发展演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要推动现存国际规范变革和确立新国际规范,在全球层面需要直视与美国的关系,而在地区层面,则需要恰当地处理与俄、印、日等中国周边地区大国的关系。前者恰好对应了中国如何谋求在现存的国际组织中实现变革的问题,而后者则是中国如何建立新国际组织来推行新规范的问题。
美国对现存国际规范变革的影响自不待言,作为规范的发起者和确立者,确保这些规范体现自身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这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寻求改革现存国际规范的努力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 [2] 而在地区层面,中国确立新国际规范的努力也不可避免会触动周边大国的神经。尽管从目前来看,中美已经尝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来缓解两国间的结构性权力困境,而在地区层面,中国已开始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缓和或促进与周边地区大国间的关系,但现存国际规范改革进程的迟滞不前和某些周边国家对新国际规范时时流露出的疑惧情绪表明,大国政治仍然是今后中国在塑造国际规范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
认知与立场方面的调整必然会带来策略上的变化。中国与现存国际规范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意味着中国要改变参与国际规范过程中的被动局面,建立新的双向互动模式——这一模式并不排斥对现存国际规范中合理成分的进一步学习和接受,它只是更强调中国对已有国际规范的改造和对新规范的确立。其带来的策略变化主要体现在:
随着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对国内问题的姿态和处理方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溢效应,其对国际规范的应对必然会受此影响,这决定了中国对国际规范的改革和塑造需要与对国内问题的成功治理经验相结合。
如前所述,谋求改革现存的国际规范是为了使其向更加公正、客观和合理的方向发展,而确立新的国际规范既是为了弥补已有国际规范的不足和缺失之处,同时也是为了从理念上实现对现存国际规范体系的改革。这样说是因为,当前国际规范体系的主导理念局限于霸权或强权政治两类,从近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两种理念主导下的国际规范难以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中国如果能够将本国历史上成功推行的“王道”思想注入对国际秩序的塑造之中,进而结合“一带一路”构想形成一个成熟的思路,那将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一个巨大贡献。现实当中的“亲、诚、惠、容”理念是这一思想在当代的实际运用,中国已经表现出了将解决国内治理问题与国际规范变革或塑造相结合的迹象,这在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事中初露端倪。客观上,这一组织的建立有利于解决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利于促进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规范变革的角度来看,就基础设施建设成立专门开发机构必然要求制定相应的国际规范,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从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方面都贯彻了全新的思维理念,是将中国的政治智慧与塑造国际规范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中国要摒弃之前采取的“先融入再塑造”式的做法,而代之以“边融入边塑造”的方式——在继续接纳现存国际规范中的合理成分的同时,强调改革现存国际规范和在新的议题领域确立新的国际规范两者并行。前者体现在如何对待已有的国际组织上,中国要继续推动具有改革意向的相关国家间的一致联合,强化改革共识,形成要求变革的合力。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为例,鉴于目前该组织的改革进程严重受制于美国方面的干扰而陷于裹足不前的僵局,中国需要持续强化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的联合,同时力争部分欧洲国家的支持,争取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持续让步。后者体现在高度重视新国际规范的确立上。还以IMF改革为例,由于该组织改革最终涉及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核心——国际金融的掌控问题,这决定了美国在修改组织运行的基本规范方面不会轻易地作出让步。中国突破目前僵局的一个选择就是以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契机,在这两个新国际组织运行的机制上,摒弃IMF运营过程中的弊病,做出针对性的制度设计,确立更具吸引力的、民主决策的规范设计,以此形成对国际规范确立形式的另一种路径选择。通过不断拓宽新国际规范的运营领域和空间,形成对现存国际规范改革僵局的间接压力。
之所以要采取“边融入边塑造”做法,是因为其背后体现了这样一个现实:已有的西方主导下的国际规范与新国际规范的产生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存。从规范发展的生命周期来看,已有国际规范最多呈现出的是一种衰退状态,还远远没有进入衰亡阶段。相反,鉴于规范变革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西方国家更倾向于采取怀柔做法,试图增加新兴国家在已有国际规范中的发言权来缓解变革压力。而从西方国家的视角来看,“当前的国际权势转移的确使西方感受到必须实现从规范和制度上‘引领’或‘开化’新兴国家,从而确保更为长期的国际体系主导权的必要。”
 这种“强化其规范性霸权以应对物质层面的国际权势转移”
这种“强化其规范性霸权以应对物质层面的国际权势转移”
 的行为客观上延缓了已有国际规范的衰退进程。
的行为客观上延缓了已有国际规范的衰退进程。
因此,中国将不得不面对规范的并存或兼容问题,即已有国际规范和新规范之间的竞争和合作问题。
 在这方面,中国应尽量促进规范间的良性竞争,减少或避免恶性竞争。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面对西方要求执行的规范压力时中国会牺牲规范确立的根本基础。举例来讲,面对西方国家质疑中国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国际组织后会损及对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等问题的国际努力的情形,中国完全可以在新成立的国际组织中纳入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措施,但一定要摒弃西方采取的那种将上述问题政治化或以这些问题为由头来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这就决定了中国对新国际规范的倡议和确立需要具备比西方国家更为宽广的视角和更为长远、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考虑。就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创制新国际规范努力的一个重要选择方向,就是从已有国际规范的薄弱或疏漏之处着手,这不仅有利于减轻改革现存国际规范的阻力,而且对增强中国的规范创制能力进而提升软实力有很大的助益。
在这方面,中国应尽量促进规范间的良性竞争,减少或避免恶性竞争。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面对西方要求执行的规范压力时中国会牺牲规范确立的根本基础。举例来讲,面对西方国家质疑中国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国际组织后会损及对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等问题的国际努力的情形,中国完全可以在新成立的国际组织中纳入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措施,但一定要摒弃西方采取的那种将上述问题政治化或以这些问题为由头来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这就决定了中国对新国际规范的倡议和确立需要具备比西方国家更为宽广的视角和更为长远、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考虑。就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创制新国际规范努力的一个重要选择方向,就是从已有国际规范的薄弱或疏漏之处着手,这不仅有利于减轻改革现存国际规范的阻力,而且对增强中国的规范创制能力进而提升软实力有很大的助益。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论文原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 年第3 期)
注释
[1] 由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等概念与国际规范密切关联,从西方学界、政界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探讨中不难发现其表达的基本观点。有学者较早前通过研究中国对不同领域国际机构和国际规则的参与情况,认为中国总体上比过去更遵守国际社会准则,但不能由此简单地判定中国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大国还是一个革命性的国家。参见Al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No.4,2003,pp.5-56。有学者则对此持消极态度,作出了相对负面的评价,参见C. Fred Bergsten etal. eds., China's Ris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D. C. 2008,pp. 209-229. Trine Flockhart and Li Xing,“Riding the Tiger:China's Rise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DIIS Policy Brief ,December 2010,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然面临危机,但仍然具有延续性,美国应通过强化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来回应中国崛起。参见David Shambaugh,“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U.S.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8,No.3,Summer 2005,pp.7-25;[美]约翰·伊肯伯里:《中国的崛起:权力、制度与西方秩序》,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7—163 页;[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有学者认为中国将会成立新国际体系,并将不同的规则运行逻辑注入其中,参见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82—286 页;同类著作参见:Eva Paus,Penelope B. Prime,and Jon Western eds., GlobalGiant:Is China Chang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Palgrave,2009;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asic,2010;随着近几年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和新一轮外交政策的推进,对此深感焦虑的西方政界频频以国际规则之名指责中国的外交行为,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多次强调要通过TPP谈判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权,防止这一权力旁落于中国之手,同时借南海问题指责中国“肘击犯规”。参见:《奥巴马:若美不敲定TPP,中国将受益》,http:// cwto. mofcom. gov. cn / article / d /201504 /20150400958354.shtml;《奥巴马指中国在南海“肘击犯规”》,《参考消息》2015 年 6 月 3 日。
[2]
美国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在大约 10 年前,围绕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学界对其进行了一轮密集的研讨。以陆伯彬(Robert S.Ross)、詹姆斯·凯利(James A.Kelly)、季北慈(Bates Gill)及迈克尔·斯温(Michael Swaine)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大致接受了美国主导的国际规范,在国际事务中总体上采取了比较负责任的做法。相关作品参见:Richard Baume,James A. Kelly,Kurt Campbell and Robert S. Ross,“Wither U.S.—China Relations?”
NBR(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Analysis
,Volume 16,Dec.2005;Bates Gill,Dan Blumenthal,Michael Swaine,Jessica Tuchman Mathews,“China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Monday June 11,2007; Thomas Christensen,“Will China Become a‘Responsible Stakeholder’?The Six Party Talks,Taiwan Arms Sales,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October 30,2005。但以卜大年(Dan Blumenthal)、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持消极看法。相关作品参见:Dan Blumenthal,“Is China at Present(or Will China Become)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Reframing China Policy:The Carnegie Debate,June 17,2007。
随着中国近几年来在国际事务中提出诸多新外交理念,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美国学界对此高度关注并出现了一些成果。参见:Aaron L.Friedberg,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America,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11;David Shambaugh,“In a fundamental shift,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w engaged in all-out competitio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une 11,2015;Douglas H.Paal,“Why Congress Must Pass the TPP,”The National Interest,June 18,2015;Alexander Sullivan,Patrick M.Cronin,“Preserving the Rules:Countering Coercion in Maritime Asia,”March 11,2015,http:// www.cnas.org/preserving-the-rules-countering-coercion-in-maritime-asia#.VYKmJNJmS6d>,等等。耐人寻味的是,个别非美国学界人士对此也持负面看法,参见Paola Subacchi,“The AIIB is a Threat to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April 8,2015,http:// www.chathamhouse.org/ expert/ comment/ 17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