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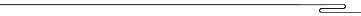
摘要: 在“两强众弱”的地区结构中,两大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其他中小国家采取双追随政策,构建起一种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将最有利于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将“分享”和“共同”作为核心原则,强调两大国应在相同领域分享权力并共同领导。地区秩序的构建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内部构建需要注意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大国与众小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区整体三个方面。两大国需要进行目标和利益的协调,采取共同行动,减少小国的偏向行为,并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地区机制的有效运行。而在外部构建的过程中,需要控制地区外部因素的影响,协调地区内各国对待外部因素的政策,促进相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根据两大国在地区内部既有地位的不同,地区秩序的构建过程可划分为平衡型构建和差异型构建两种类型。尽管两种类型都强调和遵循“共同”和“分享”的原则,但在差异型构建中,“分享”原则更为关键,特别需要关注主导国的分享意愿。崛起国在同主导国一起进行差异型构建地区秩序时,需要弥补自身短板、加强与中小国家发展关系、寻找共同利益并创设共同参与的有效的地区机制。
关键词: 双重领导;地区秩序;崛起国;秩序构建;地区机制
2015 年下半年,两件国际事件的发生似乎给中国周边外交提出了新的难题和挑战。第一个事件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2015 年 7 月,上海合作组织乌法峰会作出决定,启动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新成员的程序,正式开启了扩员进程。对地区合作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将扩大该组织的覆盖范围,增加合作规模,并通过新成员的加入为组织发展注入多元性和新活力。但印度作为具有相当体量的国家,将成为上合组织内除中国和俄罗斯以外的第三大国,其加入将改变组织内部原有的力量平衡。且印巴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有可能导致该组织效率降低,工作语言也将变得更加复杂。这些扩员进程中必将面对或可能产生的新问题,让人们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前景不免产生一些消极看法。 [1] 由此,尽管组织扩员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作出的决定,但其对中国外交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也显而易见。
第二个事件聚焦于中国东侧,其所带来的负面情绪更为浓厚。2015 年10 月,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秘鲁、智利、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 12 个国家宣布已成功结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达成基本协议。这个中国并未加入的新地区贸易协定设置了较高的贸易标准,将给中国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学界对此多有评述,
 并且相当多的观点强调了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可以说,TPP基本协议达成意味着中国将在亚太地区国际经济领域中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
并且相当多的观点强调了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可以说,TPP基本协议达成意味着中国将在亚太地区国际经济领域中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

尽管事态造成的影响依旧需要观察,但两者具有一个鲜明的共性,即它们将对相关地区的合作与发展构成影响并将作用于地区秩序的塑造进程。在亚欧大陆腹地,中俄两大国与中亚国家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开展合作,已经逐渐塑造出一种以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为核心的地区秩序。然而,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特别是大国印度的加入将使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从“两强众弱”变为“三强并立”,从而影响现有的地区秩序。而在大陆东侧的亚太地区,中国经过多年努力,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标志,显示了本国在地区经济合作领域中的突出作用,并在逐渐影响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甚至可谓形成了一种“二元格局”。
 但TPP协议的达成,显示了美国维护其地区主导地位的决心和努力,中美在东亚的“二元格局”似成昙花一现。这些新问题和挑战归结起来,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一山是否能容二虎”“一山怎么容二虎”和“一山中二虎能容多久”的问题,需要中国作出调整来应对,这是本文所讨论的现实问题。
但TPP协议的达成,显示了美国维护其地区主导地位的决心和努力,中美在东亚的“二元格局”似成昙花一现。这些新问题和挑战归结起来,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一山是否能容二虎”“一山怎么容二虎”和“一山中二虎能容多久”的问题,需要中国作出调整来应对,这是本文所讨论的现实问题。
从理论上讲,上述现实问题的核心是:当两个大国存在于同一地区时,一种“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是否可以被构建和塑造,其构建逻辑又是怎样的。对任何一个大国而言,单一主导型地区秩序最有诱惑力,也具有相对的最大收益。因为本国是所在地区的唯一大国,周边存在若干个中小国家,本国在地区体系内享有优势性的权力地位。此时,无论是怀柔还是强硬,在缺少实力相当的其他大国作为敌手的情况下,主导性大国能够比较容易地处理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也更易于维护安全和实现经济利益。而且,取得所处地区的主导权并免于地区纷争,是大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重要路径。 [2] 这也符合霸权稳定论的基本逻辑,是一些大国总在追求实力增长、试图成为霸权国甚至建立等级体系的重要原因。 [3]
然而,相当多的大国并不幸运,其所在地区通常会存在着与己实力相当的大国,例如早年的雅典和斯巴达以及历史上的法国与英国等,且毗邻国家对彼此在能力、优势和权力上的差异更加敏感,
 由此更容易导致安全困境和地区纷争。有时,大国崛起时面对着一个由主导国控制的地区等级体系,如何与这一体系及地区内维持秩序的主导国相处是需要崛起国妥善处理的重要问题,例如中国在冷战后所面对的是美国主导的东亚和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国家。
由此更容易导致安全困境和地区纷争。有时,大国崛起时面对着一个由主导国控制的地区等级体系,如何与这一体系及地区内维持秩序的主导国相处是需要崛起国妥善处理的重要问题,例如中国在冷战后所面对的是美国主导的东亚和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国家。
 回顾历史,权力竞争以及由权力转移引发的战争与冲突似乎始终是大国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的保留项目。因此,无论是原本存在两大国平衡性竞争的地区体系,还是崛起国面对着由一个大国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构建一种两个大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的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并维护该秩序的持续运行,都是实现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而这一地区秩序需要各国采取务实态度接受多元性的现实,以多样性和克制推动其生成,
回顾历史,权力竞争以及由权力转移引发的战争与冲突似乎始终是大国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的保留项目。因此,无论是原本存在两大国平衡性竞争的地区体系,还是崛起国面对着由一个大国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构建一种两个大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的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并维护该秩序的持续运行,都是实现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而这一地区秩序需要各国采取务实态度接受多元性的现实,以多样性和克制推动其生成,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崛起国来说,与主导国一起建立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是其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有利阶段和发展方向,有助于崛起国摆脱地区性纠葛,以更便捷地追求更高地位和更大影响力。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崛起国来说,与主导国一起建立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是其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有利阶段和发展方向,有助于崛起国摆脱地区性纠葛,以更便捷地追求更高地位和更大影响力。
 或许在实力对比没有发生更为明显和更为根本性的变化前,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也将是对崛起国最有利并具有中长期持续性的地区秩序形态。
或许在实力对比没有发生更为明显和更为根本性的变化前,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也将是对崛起国最有利并具有中长期持续性的地区秩序形态。
所以,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从理论上即是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方式和逻辑是怎样的?崛起国如何才能推动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形成?
当地区内存在两个大国和若干个中小国家时,学界通常使用两极、二元、共治等词汇界定和描绘这种“两强众弱”地区的地区秩序。
 两大国的明显优势和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地区出现极化,形成两极格局。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斗争为研究两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物质权力结构的崩溃和观念对抗的终止,将两极与冷战一并结束。
两大国的明显优势和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地区出现极化,形成两极格局。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斗争为研究两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物质权力结构的崩溃和观念对抗的终止,将两极与冷战一并结束。
 在失去了一极的后冷战时代,对两极的研究一度沉寂。然而,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态势的不断发展,学界对两极的研究又重新恢复了热情。
在失去了一极的后冷战时代,对两极的研究一度沉寂。然而,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态势的不断发展,学界对两极的研究又重新恢复了热情。
“两极”的表述更多描绘的是一种权力分配结构,不仅凸显了两大国的优势地位,也强调了其中存在的权力制衡。
[4]
与之相类似的是“二元”,学者们在讨论东亚地区秩序时更多使用“二元”这一词语,强调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种二元格局。
[5]
美国在维护地区安全秩序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中国在地区经济秩序方面产生了更大影响,东亚呈现出日渐增长的霸权与制衡并存的混合性特点。
[6]
这种所谓的东亚地区二元格局,实际上反映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地区经济秩序的分离。部分研究从公共产品的视角对东亚地区秩序进行了分析。
 整体上看,“二元”的界定指出了两大国在地区秩序构建过程中的领域差别和功能分异。杨原和曹玮使用“共治”的概念描绘了两极体系在“分治”对抗之外的另一种更为温和的权力互动模式,强调该体系不再以地域划分出两个分属不同大国的势力范围,两大国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差异化共治,从而凭借功能分异减少了大国之间的对抗性和地缘政治色彩。
整体上看,“二元”的界定指出了两大国在地区秩序构建过程中的领域差别和功能分异。杨原和曹玮使用“共治”的概念描绘了两极体系在“分治”对抗之外的另一种更为温和的权力互动模式,强调该体系不再以地域划分出两个分属不同大国的势力范围,两大国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差异化共治,从而凭借功能分异减少了大国之间的对抗性和地缘政治色彩。
 他们的观点实际上肯定了二元格局对实现地区共治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崛起国拥有“一技之长”将有助于其成功崛起并同霸权国竞争领导权。
他们的观点实际上肯定了二元格局对实现地区共治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崛起国拥有“一技之长”将有助于其成功崛起并同霸权国竞争领导权。

但正如刘丰所指出的,“二元格局论既夸大了美国对东亚安全的主导性,也夸大了中国对东亚经济的主导性”。
 从另一角度看,这一界定实际上不仅夸大了功能分异的程度,也放大了“效忠”或“从属性”的程度。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使用的“二元等级体系”概念
[7]
更鲜明地反映了上述问题。显然,中美在不同领域中的比较优势,并不能将所谓的“从属国”同另一个大国割裂开来,即便是在某个单一的功能领域中,也不能实现孤立主导国的目的。正如美国努力恢复其在亚太的经济地位所显示的,差异化共治在稳定性和持续性方面实际上存在不足,
从另一角度看,这一界定实际上不仅夸大了功能分异的程度,也放大了“效忠”或“从属性”的程度。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使用的“二元等级体系”概念
[7]
更鲜明地反映了上述问题。显然,中美在不同领域中的比较优势,并不能将所谓的“从属国”同另一个大国割裂开来,即便是在某个单一的功能领域中,也不能实现孤立主导国的目的。正如美国努力恢复其在亚太的经济地位所显示的,差异化共治在稳定性和持续性方面实际上存在不足,
 每个大国实际上都有强烈的欲望去弥补自身的短板,以追求对体系进行全面和单独的主导。而从地区的整体性和地区治理的角度出发,探索真正意义上或者完全意义上的“共治”方式
每个大国实际上都有强烈的欲望去弥补自身的短板,以追求对体系进行全面和单独的主导。而从地区的整体性和地区治理的角度出发,探索真正意义上或者完全意义上的“共治”方式
 以及弥合功能领域分异导致的地区分裂应成为地区秩序研究的新方向。
以及弥合功能领域分异导致的地区分裂应成为地区秩序研究的新方向。
刘丰从地区秩序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角度出发,试图弥合功能领域分异带来的认知偏差。他将经济和安全两个领域进行关联,并结合均势和霸权两种格局提出将国际体系划分为完全均势、部分均势、完全霸权和部分霸权4 种基本形态,而国际体系的转型是在 4 种模式之间的交替转换。
 刘丰提出的这一合成的结构现实主义模型尽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可以为体系转型方向和体系稳定性等问题提供解释,但这种类型化研究实际上更加适合对全球秩序或世界秩序的分析,在分析地区秩序时则存在明显的问题。因为作为理想类型的完全霸权秩序实际上在地区层面难以实现,仅仅具有地区支配性地位的霸权国很难排除地区外部因素特别是全球性霸权国对本地区的干扰。
刘丰提出的这一合成的结构现实主义模型尽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可以为体系转型方向和体系稳定性等问题提供解释,但这种类型化研究实际上更加适合对全球秩序或世界秩序的分析,在分析地区秩序时则存在明显的问题。因为作为理想类型的完全霸权秩序实际上在地区层面难以实现,仅仅具有地区支配性地位的霸权国很难排除地区外部因素特别是全球性霸权国对本地区的干扰。
 因此,在讨论地区秩序时,需要考虑到地区的“外部不完全性”所造成的地区体系本质上的开放性,
[8]
应该兼顾地区内外的多种复杂因素,而不适宜将一般意义上的体系概念简单地平移至地区问题的讨论中。
因此,在讨论地区秩序时,需要考虑到地区的“外部不完全性”所造成的地区体系本质上的开放性,
[8]
应该兼顾地区内外的多种复杂因素,而不适宜将一般意义上的体系概念简单地平移至地区问题的讨论中。
而“共治”一词仅仅描绘了两大国与众小国之间的一种关系状态类型。对整个地区的发展和地区秩序而言,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地区秩序整体的关系同样重要,甚至是更加重要,因为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秩序的形态与稳定性。两个大国之间及其与地区秩序的关系可以区分为如下 4 种状态类型或阶段。第一种是“共存”。位于同一地区的大国A与大国B,互相承认彼此的存在,不以消灭对方为目标,并认可本国与对方处于同一地区。这是两大国关系的初级阶段。
 第二种是“共处”。两大国彼此尊重对方的存在,愿意相处,发展双方之间的关系,不做出破坏地区秩序的行为。相较于“共存”对两大国事实上存在状态的客观描述,“共处”本身带有一定的积极含义,强调两大国之间具有善意,能够协调各自的立场、开展合作以保证各自实现部分国家利益。这些利益不仅可以涉及安全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还可以包括地位、威望等非物质性因素,同时也强调对地区秩序的维护。当然,上述所有方面的利益并不都能均衡性实现,但部分利益的实现已经意味着大国能够从地区秩序中获益。第三种是“共事”。“共事”意味着两大国之间开展了更紧密的合作,此时的合作并不局限在双边层面,而是更多聚焦于地区层次,两个大国愿意共同处理地区事务,承认对方在地区内的影响,愿意与对方在地区问题上开展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共治”实际上是“共事”的类型之一,治理是一种地区事务。大国A承认中小国家对大国B的效忠,认可大国B的地区地位,并愿意同大国B在地区问题上共同付出,一同维护现有的地区秩序;而反过来,大国B也承认并愿意同大国A开展合作。第四种是“共发展”。“共发展”是地区秩序的一种最理想状态,大国A和大国B在地区内和平相处,实现地区内各国的共同发展,大国对小国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并带动和促进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第二种是“共处”。两大国彼此尊重对方的存在,愿意相处,发展双方之间的关系,不做出破坏地区秩序的行为。相较于“共存”对两大国事实上存在状态的客观描述,“共处”本身带有一定的积极含义,强调两大国之间具有善意,能够协调各自的立场、开展合作以保证各自实现部分国家利益。这些利益不仅可以涉及安全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还可以包括地位、威望等非物质性因素,同时也强调对地区秩序的维护。当然,上述所有方面的利益并不都能均衡性实现,但部分利益的实现已经意味着大国能够从地区秩序中获益。第三种是“共事”。“共事”意味着两大国之间开展了更紧密的合作,此时的合作并不局限在双边层面,而是更多聚焦于地区层次,两个大国愿意共同处理地区事务,承认对方在地区内的影响,愿意与对方在地区问题上开展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共治”实际上是“共事”的类型之一,治理是一种地区事务。大国A承认中小国家对大国B的效忠,认可大国B的地区地位,并愿意同大国B在地区问题上共同付出,一同维护现有的地区秩序;而反过来,大国B也承认并愿意同大国A开展合作。第四种是“共发展”。“共发展”是地区秩序的一种最理想状态,大国A和大国B在地区内和平相处,实现地区内各国的共同发展,大国对小国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并带动和促进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如果能够实现“共存”和“共处”,并达到“共事”的阶段,就可以将这一地区的秩序界定为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领导”一词不仅表明大国在地区中的作用,如对国际关系进行组织、塑造和引导,
 也表述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状态。赫德利·布尔(Hedlly Bull)认为“领导(primacy)”意味着大国没有经常性地蔑视国际行为规范,也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而是获得小国的自主承认,认可“该大国可以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作用”,是同“支配(dominance)”和“霸权(hegemony)”相区别的大国行使地区主导权的形式。
也表述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状态。赫德利·布尔(Hedlly Bull)认为“领导(primacy)”意味着大国没有经常性地蔑视国际行为规范,也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而是获得小国的自主承认,认可“该大国可以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作用”,是同“支配(dominance)”和“霸权(hegemony)”相区别的大国行使地区主导权的形式。
 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将国际领导类型分为王权、霸权和强权三类,
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将国际领导类型分为王权、霸权和强权三类,
 其“王权”的概念同布尔的“领导”概念存在相近的含义。本文接受上述观点对“领导”概念的基本认识,作为一个地区的领导,大国既有优势性的实力地位,能够提供公共产品,也得到了小国的普遍认可,享有权威,并能够带领小国共同发展。
其“王权”的概念同布尔的“领导”概念存在相近的含义。本文接受上述观点对“领导”概念的基本认识,作为一个地区的领导,大国既有优势性的实力地位,能够提供公共产品,也得到了小国的普遍认可,享有权威,并能够带领小国共同发展。
此前在讨论东亚地区的二元格局时,也有学者使用“双领导”的提法。
 但“二元格局”尽管可以防止因划分势力范围而出现的地理性分裂,但却容易导致地区出现功能性分裂,使大国的“领导”作用并不能真正发挥,所以,本文所界定的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在“双”的基础上更强调“重”的概念。在此种地区秩序内,“分享”和“共同”是两大核心原则。两个大国发挥领导作用,意味着两大国具有共同的领导身份,彼此承认对方的地位并愿意分享权威。两大国各自在地区中的作用不存在明显的分野和差异(包括领域性或功能性的分野和差异),而是具有“共同性”或者说“重合性”。“重合”意味着两大国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追求着相近的地区目标、愿意合作共事,也意味着地区内小国不需要分别“效忠”。换句话说,即两大国不需要对小国展开争夺,
但“二元格局”尽管可以防止因划分势力范围而出现的地理性分裂,但却容易导致地区出现功能性分裂,使大国的“领导”作用并不能真正发挥,所以,本文所界定的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在“双”的基础上更强调“重”的概念。在此种地区秩序内,“分享”和“共同”是两大核心原则。两个大国发挥领导作用,意味着两大国具有共同的领导身份,彼此承认对方的地位并愿意分享权威。两大国各自在地区中的作用不存在明显的分野和差异(包括领域性或功能性的分野和差异),而是具有“共同性”或者说“重合性”。“重合”意味着两大国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追求着相近的地区目标、愿意合作共事,也意味着地区内小国不需要分别“效忠”。换句话说,即两大国不需要对小国展开争夺,
 这是一个共赢、共担和共同行动的整体,不仅包含着共治所具有的意义,
这是一个共赢、共担和共同行动的整体,不仅包含着共治所具有的意义,
 同时也是在弥合二元格局可能造成的鸿沟。因此,本文对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讨论,建立在维护地区秩序整体性的基础上,强调应从整体角度思考地区秩序的构建逻辑。
同时也是在弥合二元格局可能造成的鸿沟。因此,本文对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讨论,建立在维护地区秩序整体性的基础上,强调应从整体角度思考地区秩序的构建逻辑。
考虑到地区秩序构建初期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起始状态,可以将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过程区分为“平衡型构建”和“差异型构建”两种类型。平衡型构建也可叫作“对称性构建”, [9] 意味着实力接近的两个大国在地区地位和身份方面具有较为平衡的状态,在构建地区秩序时可以共同发挥作用。差异型构建也可叫作“非对称性构建”,意味着两大国最初在地区地位方面存在比较意义上的差距,一国具有主导国地位;另一国是崛起国,崛起国对构建双重领导的意愿更为迫切,主动性和积极性更为强烈。在遵循“共同”原则方面,两种类型不存在差别;但在遵循“分享”原则方面,差异型构建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主导国的意愿,主导国是主动还是被迫分享权威,将对地区秩序构建的过程与结果造成影响。这是两种不同构建类型之间的最主要差别,是以往研究较为忽略的部分,也将是本文可以作出微薄贡献的重要方面。从现实来看,中国作为崛起国如何使主导国认可和接受中国的地区领导身份,并愿意与中国分享权威和共同发挥领导作用,是重要的现实问题。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主要分为 3 个部分。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逻辑,分析双重领导的建立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具备哪些基础和条件。特别是那些正在崛起的大国,为了在既存的地区体系中获得被认可的领导地位,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这是该部分重点讨论的问题。之后,本文将结合 4 个具体案例,
 即西欧地区的法国与德国(1950—1973 年),东亚地区的中国与日本(1997—2010 年),中亚地区的中国与俄罗斯(1996—2015 年),东亚地区的中国与美国(2010—2015 年)。在每一个案例中,本文将分析不同地区在构建秩序的过程中存在的优势条件和障碍问题,验证理论部分提出的主要观点。最后将结合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两部分的内容,对地区秩序的发展前景、理论研究的方向和可采取的对策作出分析。
即西欧地区的法国与德国(1950—1973 年),东亚地区的中国与日本(1997—2010 年),中亚地区的中国与俄罗斯(1996—2015 年),东亚地区的中国与美国(2010—2015 年)。在每一个案例中,本文将分析不同地区在构建秩序的过程中存在的优势条件和障碍问题,验证理论部分提出的主要观点。最后将结合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两部分的内容,对地区秩序的发展前景、理论研究的方向和可采取的对策作出分析。
在构建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时,该地区需要具备如下基础条件。第一,存在两个大国和若干个中小国家。“两强众弱”的权力结构是构建双重领导的基础,因为“合作应以少数大国为中心,而由大量的小国追随其后”。
 第二,每个大国均具有成为地区领导国的实力。这不仅意味着两大国都具有实力优势,同时也意味着两大国都对其他小国具有吸引力,小国愿意追随,尽管这种吸引力并不一定涉及所有方面。第三,两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较小或具有减小的趋势。实力接近和相对平衡是实现双重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不仅是促使两大国彼此接受对方领导地位的基础,也是两大国能够对小国产生相同吸引力的根本。即便是在差异型构建时,两大国也不存在明显的实力差距,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地区地位和大国同小国的既有关系方面,主导国只是在旧有联系和影响力上具有初期优势。
第二,每个大国均具有成为地区领导国的实力。这不仅意味着两大国都具有实力优势,同时也意味着两大国都对其他小国具有吸引力,小国愿意追随,尽管这种吸引力并不一定涉及所有方面。第三,两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较小或具有减小的趋势。实力接近和相对平衡是实现双重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不仅是促使两大国彼此接受对方领导地位的基础,也是两大国能够对小国产生相同吸引力的根本。即便是在差异型构建时,两大国也不存在明显的实力差距,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地区地位和大国同小国的既有关系方面,主导国只是在旧有联系和影响力上具有初期优势。
地区秩序的构建首先要解决内部问题,制定内部运行规则。因此,地区秩序的内部构建逻辑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国的妥协、协调和合作对地区秩序建构至为关键”,
 两大国是否愿意承认对方在地区内的实力地位,是否愿意分享权威,并彼此进行协调与合作,是秩序构建的基础。第二是两大国与众小国之间的关系。小国是否愿意接受两个大国的领导,或者说两大国的共同领导是否是小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领导”的存在是秩序构建的重要条件。第三是地区整体。是否存在一种地区机制或地区架构能够稳定大国之间以及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状态,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开展互动的过程中推动合作,并不断塑造双重领导秩序。
两大国是否愿意承认对方在地区内的实力地位,是否愿意分享权威,并彼此进行协调与合作,是秩序构建的基础。第二是两大国与众小国之间的关系。小国是否愿意接受两个大国的领导,或者说两大国的共同领导是否是小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领导”的存在是秩序构建的重要条件。第三是地区整体。是否存在一种地区机制或地区架构能够稳定大国之间以及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状态,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开展互动的过程中推动合作,并不断塑造双重领导秩序。
1.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与利益协调
既然地理条件已经使两个大国存在于同一地区,那么在共存基础上如何共处和共事,成为构建地区秩序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探索双重领导之路,需要更进一步分解大国的对外目标和国家利益。在国家间关系上,大国A与大国B之间没有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有意愿开展合作,双边关系稳定发展,有助于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这是双边层次目标。保持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发展,维护本国的地区地位,并能够从地区安排中持续受益,是大国最主要的地区性目标或地区性利益。大国的全球性目标则是提升本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扩大全球影响,使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有助于实现和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这三个层次的目标具有关联性,彼此之间也相互影响。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最重要和最核心的目标是全球性目标,而全球性目标的实现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地区性目标和双边层次目标的实现,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全球性目标,地区性目标和双边层次目标可以做出适当的调整甚至牺牲。而双边层次目标具有基础性作用,其实现有助于汇聚并促成地区性目标和全球性目标的达成。但在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各大国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在不同时期也会具有差异性看法。有的大国为了地区性目标,可以在双边层次上作出相应让步;而有的大国宁愿放弃地区性目标,也需要保证双边层次上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大国A与大国B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上均具有共同利益和一致目标,可以进行合作与协调,这将最有利于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退而求其次,如果在双边层次上存在问题,地区和全球层次上的目标具有共同性或接近性,也不会对构建地区秩序造成过大影响。但如果全球性目标分歧巨大,而为实现全球性目标进行的协调又不能促使两大国放弃在双边和地区层次上的利益,那么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将很难建立。
特别是在差异型构建时,崛起国实际上是在同主导国分享权威,这种分享的实质是对主导国权威的削弱。因此,就更加需要处理好同主导国的关系。崛起国需要细致分解本国和主导国在不同层次上的利益和目标,寻找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如果不能达到最理想的 3 个层次目标均一致的状态,则要对不同目标进行排序,考察是否可以通过减低某个层次的目标需求以增加或换取双方在其他层次目标上的一致性,从而促使主导国接受崛起国,并加强彼此的利益协调。
2.两大国与众小国之间的关系
当小国愿意同时接受两个大国的领导,并同大国一起参与地区机制建设时,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得以构建。小国的一条重要生存之道是依靠大国。当地区内只有一个大国时,小国并没有太多选择,但如果存在两个大国,小国可以选择追随其一,也可以同时与两大国发展密切联系,或采取“抱团取暖”的集体行动。在构建双重领导时,大国需要让小国意识到追随其一和集体抱团的收益都小于同时追随两大国的收益。
首先,两大国目标和利益的协调或一致,特别是地区目标的一致,可以限制小国进行“非此即彼”选择的空间,有助于增强小国的“双追随”意愿。在两大国实力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如果两大国在小国最关注的地区发展目标上仍然趋同,那么小国将看不到差异的存在,无法进行比较,也就不可能进行单一性追随。其次,两大国自身具有的优势地位可以吸引小国即便已经抱团也愿意集体性追随大国,且在同一领域中两大国各具特点和优势,有助于增强小国的“缺一不可”认识。最后,任何一个大国不存在敌对小国,因为敌对者将具有强烈的择一偏好或采取挑拨行为,阻碍双重领导秩序的建立。
这三个方面对差异型构建和平衡型构建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差异型构建时,崛起国应在与主导国相同的领域中,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和比较优势,塑造“不可或缺性”,提升本国的地区贡献。同时,崛起国应规范自身行为,防止在地区内树敌。正反两方面的共同努力,将吸引更多小国接受本国的领导,从而增强同主导国分享权威的可能性。
3.塑造地区整体性的地区机制
地区秩序构建的核心表达是地区制度的确立。
 通过制度化进程所形成的地区机制,既是构建秩序的必要条件,也是维持秩序运行的基础。地区机制应将地区国家纳入其中,反映地区内部的权力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缓解安全困境,推动和平与促进繁荣。双重领导意味着两大国应该在同一领域中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塑造和构建秩序的地区机制即便无法是全面性的,也应至少聚焦于某一具体领域,这是秩序构建过程得以启动的关键。在这个领域中,该机制不仅应是合作与协商的平台,能够保证每个国家的意见充分和平等地表达,不损害任何国家的话语权,同时又应具有执行能力,能够发挥实效,不能沦为清谈场所。
通过制度化进程所形成的地区机制,既是构建秩序的必要条件,也是维持秩序运行的基础。地区机制应将地区国家纳入其中,反映地区内部的权力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缓解安全困境,推动和平与促进繁荣。双重领导意味着两大国应该在同一领域中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塑造和构建秩序的地区机制即便无法是全面性的,也应至少聚焦于某一具体领域,这是秩序构建过程得以启动的关键。在这个领域中,该机制不仅应是合作与协商的平台,能够保证每个国家的意见充分和平等地表达,不损害任何国家的话语权,同时又应具有执行能力,能够发挥实效,不能沦为清谈场所。
从理论上看,平衡型构建地区秩序时,两大国可以采取共同建立机制的方式,吸纳中小国家参与,利用地区机制共享收益、共担责任,并自我约束,防止出现破坏机制的行为。而在差异型构建过程中,两大国可以采取共同建立新机制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主导国开放原有地区机制以吸纳崛起国参与,或崛起国创设新地区机制邀请主导国和其他小国参与的方式。无论机制采取哪种方式建立,在其设计和运行过程中都需要考虑到“两强众弱”的权力结构和两大国对领导地位的分享。如果某一领域的地区机制有效实现了两大国共同领导的地区合作,那么当积累了经验的各国愿意在其他领域建立类似机制或扩大现有机制的合作领域时,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就进入了良性推进阶段,也是领域拓展的阶段。而秩序构建的理想结果是两大国领导其他小国通过某一地区机制进行多领域的全面合作,次优结果是在不同领域各有一种地区机制实现两大国的双重领导。
地区作为次体系,无法完全排除外部行为体对地区内部事务施加影响,因此,地区秩序在外部构建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外部影响。有时,外部因素施加的是一种负面影响。例如,当体系中的大国认为某个地区形成一种双重领导秩序将更加排斥本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和影响时,体系大国就会采取措施干扰秩序的构建,或者挑拨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或者帮助其中一个大国吸引更多小国采取偏向性的追随行为,或者支持小国采取独立行动。这是地区秩序构建的不利因素。影响程度的大小、影响方式的选择等取决于外部行为体相对于地区内两个大国的实力地位、其所掌握的优势资源以及对地区重要性和地区局势的认知等。
但也必须承认,外部影响有时也是秩序构建的有利条件,这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两个大国或地区内的所有国家拥有共同的外部敌人。此时,共同御敌的需要将弥合两大国之间的矛盾分歧,将二者的全球性目标和地区性目标加以协调,为两大国构建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提供基础。特别是当外部敌人是整个地区的敌人时,中小国家也将更加积极主动地追随两个大国的领导,地区凝聚力的增强将有助于秩序构建。第二,外部行为体是一种支持性力量,赞同该地区建立双重领导型秩序,愿意为秩序构建提供帮助和支持。此时,外部支持的存在将有助于增进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促进利益协调,并推动小国采取双追随立场。
整体上看,地区秩序构建的外部逻辑是协调地区内各个国家对待外部因素的政策,促进相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当外部因素是消极影响时,地区内国家如果在防止外部介入上存在共同认知,那么任何一个大国或中小国家将没有邀请外部大国介入地区事务的意愿和行动,从而有助于实现共同行动减少外部干扰。而当外部因素能够发挥积极影响时,地区内国家如果同样存在共同认知,将有利于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利用这一积极影响。总之,当地区内各国对待外部因素的政策不断趋同时,能够增强各国立场的接近性,从而增加对地区的认同感, [10] 并将有助于地区秩序的构建。特别是在差异型构建的过程中,崛起国可以利用外部因素塑造主导国和中小国家的认知,增强自身的领导作用,促进权威的分享和秩序的构建。综上所述,在地区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外部逻辑因外部影响性质的不确定性而并非不可或缺。但如果据此忽略外部因素和外部行为体的影响,也是不正确的。
2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认识。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的重塑和地区秩序建构的勃兴成为国际秩序建构的突出特征。
 本部分选择 4 个案例讨论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逻辑,其中 3 个案例都发生在冷战结束以后,显示了地区秩序构建问题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活跃程度。必须指出的是,在每一个案例中,不是所有国家都在有意识地追求一种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但各国的互动和地区秩序的不断发展都为构建此种地区秩序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本部分选择 4 个案例讨论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逻辑,其中 3 个案例都发生在冷战结束以后,显示了地区秩序构建问题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活跃程度。必须指出的是,在每一个案例中,不是所有国家都在有意识地追求一种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但各国的互动和地区秩序的不断发展都为构建此种地区秩序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的西欧百废待兴,但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各国而言,恢复经济必须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探索防止新大战发生的方式,实现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成为各国的主要目标。在冷战铁幕将欧洲分裂为两大阵营后,西欧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塑造新的地区秩序成为西欧探索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新课题。
1950 年,舒曼计划出台,西欧各国开始以煤钢联营的方式,将可用于发动战争的煤炭、钢铁等工业置于同一机构的管理下,一方面可消除战争隐患,防止某个大国重整军备;另一个方面也以集体的力量开展共同行动,促进资源的合理调配,推动经济复兴。1951 年 4 月,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署欧洲煤钢联营条约,随后于 1952 年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西欧一体化进程就此启动。1957 年,上述六国签署《罗马条约》,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 年,六国又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 3 个共同体合并。1967 年 7 月,欧洲共同体正式诞生。回顾这一过程可以发现,从 1950 年舒曼计划推出至 1973 年英国加入欧共体的 20 余年间,西欧实际上探索并构建了一个由法国和德国作为双重领导的地区秩序。其构建具备一些有利条件。
第一,遭受战争重创的法国和德国,作为地区内部的大国,实力接近,有意愿进行合作,并在多个层次具有共同利益。自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法德两国经历了一连串恩怨纠葛,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两国依然固守寻求成为唯一的地区主导国的思维,那么“二战”后的持久和平几乎难以想象。这是时任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支持和推动煤钢联营的重要原因,法国与德国必须学会在一个地区共存和共处。战败后的德国被极大削弱,连国家也被一分为二,此时,“加入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不仅获得了一种平等的地位,而且还有了影响局势的机会”。
 因此,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既有利于恢复主权,也有利于减轻其他国家对德国复兴的担忧和畏惧。只有重新找到本国在地区内的位置,与其他地区大国和平相处,德国才能重新获得恢复和发展。同样遭受战争重创的法国,也不得不接受时代变化的现实,“与其争当世界大国,还不如在欧洲共同体内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后者也更易做到”,
因此,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既有利于恢复主权,也有利于减轻其他国家对德国复兴的担忧和畏惧。只有重新找到本国在地区内的位置,与其他地区大国和平相处,德国才能重新获得恢复和发展。同样遭受战争重创的法国,也不得不接受时代变化的现实,“与其争当世界大国,还不如在欧洲共同体内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后者也更易做到”,
 且欧洲是恢复法国昔日伟大辉煌的途径。
且欧洲是恢复法国昔日伟大辉煌的途径。
 因此,作为传统大国,地区和平与恢复发展为法德两国的首要任务。两国在地区性目标和双边层次目标上找到了共同点,寻求共事与合作。而且法德两国均不在地区内具备主导性优势地位,所以西欧地区秩序的构建属于平衡型构建的类型。
因此,作为传统大国,地区和平与恢复发展为法德两国的首要任务。两国在地区性目标和双边层次目标上找到了共同点,寻求共事与合作。而且法德两国均不在地区内具备主导性优势地位,所以西欧地区秩序的构建属于平衡型构建的类型。
第二,地区外部因素提供了压力和动力,有利于地区秩序的塑造。冷战实际上为西欧新地区秩序的塑造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方面,苏联成为西欧各国的共同敌人,对共产主义的担忧成为一种压力,促使法德两国及其他中小国家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威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提供了足够的动力,支持西欧的联合进程,马歇尔计划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对西欧的联合起到了积极的实际效果。正如北约首任秘书长罗德·伊斯梅(Lord Ismay)所说,北约的目的是防御俄国、抑制德国和拽住美国(keep the Russians out,the Germans down,and the Americans in),
 既解决了西欧内部的安全问题,也减轻了西欧面对的外部安全威胁。这些压力和动力从正反两个方向增加了法德两国在地区和全球目标上的一致性,即全球性目标是借由地区发展获得本国国力的恢复和提升,抵抗共产主义苏联的威胁;地区性目标是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发展,防止战争再次爆发。苏联作为共同敌人,美国作为外部支持,都帮助塑造了地区秩序。
既解决了西欧内部的安全问题,也减轻了西欧面对的外部安全威胁。这些压力和动力从正反两个方向增加了法德两国在地区和全球目标上的一致性,即全球性目标是借由地区发展获得本国国力的恢复和提升,抵抗共产主义苏联的威胁;地区性目标是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发展,防止战争再次爆发。苏联作为共同敌人,美国作为外部支持,都帮助塑造了地区秩序。
第三,小国支持法德的共同领导,参与到地区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中。从煤钢共同体到欧共体的发展过程中,地区机制在各个领域得以建立,每个领域的机制都是由六国共同参与、集体推动的,小国支持地区大国,并采取共同行动。尽管因建设怎样的欧洲存在分歧而引发了“空椅子危机”,但各国并没有试图脱离地区机制,而是协调协商,共同推动地区机制向前发展,最终将不同领域的地区机制加以整合,形成推动地区整体合作的欧洲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西欧各国的经济也得到恢复和增长。
由此,西欧借由欧共体的发展而逐步构建起法德两国作为双重领导的地区秩序,当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一地区秩序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但也必须承认西欧各国并未放弃对共同安全和防务的探索。英国在 1961 年和 1967 年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被拒,除了英国未达到相关标准、曾经与一体化对抗等其自身因素外,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欧共体各国拒绝英国加入有保持地区秩序稳定的需要。戴高乐就曾明确指出,英国是美国的“特洛伊木马”,让英国参加进来,将会彻底改变共同体的性质。
 也正如戴高乐所言,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于 1973 年加入欧共体,尽管地区机制的覆盖范围得以扩大,但英国的加入改变了地区的权力结构。此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仍然是德法两国作为发动机或轴心,
也正如戴高乐所言,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于 1973 年加入欧共体,尽管地区机制的覆盖范围得以扩大,但英国的加入改变了地区的权力结构。此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仍然是德法两国作为发动机或轴心,
 但就欧共体和此后欧盟的发展而言,双重领导已经不复存在,地区秩序因为权力结构的改变开始重新塑造。
但就欧共体和此后欧盟的发展而言,双重领导已经不复存在,地区秩序因为权力结构的改变开始重新塑造。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东亚地区的内外形势为中国与日本构建一种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提供了契机。 [11]
首先,冷战结束使中日两国开始重新认识本国与东亚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在日本方面,泡沫经济破灭带来了负面影响,不仅给日本经济和国家实力造成实际打击,也削弱了日本在东亚经济“雁阵模式”中作为头雁的领先地位。日本与美国关系的漂移阶段很快结束,重新回到美日同盟的轨道上,这意味着日本没能成为可在全球层次上与美国一较高下的竞争者,日本仍然是一个经济强国,但它也依然没能跃出东亚。在中国方面,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尽管仍然存在各种问题,但成功实现的软着陆不仅帮助中国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更使中国有能力在金融危机中给东亚国家提供实际支持。这些表现不仅为中国赢得了地区内相关国家的肯定和信任,也提升了中国同东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意愿和能力。此前,中国并不是从地区(region)角度出发处理与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而更多是在双边层次上; [12] 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东亚地区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并开始从地区的视角审视同东亚各国的合作。由此,中国与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具经济实力的两个大国,既拥有领导东亚的经济实力,也具有促进地区合作、塑造地区秩序的意愿。综合对比各方面情况,中日两国符合平衡型构建的类型,具备启动构建地区秩序进程的条件。
其次,经济领域成为地区秩序构建的主要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在地区安全领域都不具有相应的能力和影响力,两国都是在地区经济领域具有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地区内其他中小国家对两国的主要期待也都集中在经济领域,希望同时与中国和日本开展经济合作。由此,要在东亚构建由中日两国作为双重领导的地区秩序将最有可能在经济领域实现。而现实的发展也增强了此种可能。1997 年 12 月,在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尚未消散之时,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各国表达了加强经济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意愿,并探讨了合作开展的思路和路径。此后逐渐形成惯例,每年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并配套召开部长级会议。这逐渐发展成为覆盖东亚国家的重要地区机制。这一机制从启动之初就聚焦于经济领域,也试图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起到了塑造地区秩序的作用。
最后,外部行为体对构建地区秩序的影响相对可控和有利。尽管美日同盟在 1995 年实现了再定义,但中美关系也在 1997 年实现了稳定发展,中美两国宣布致力于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在1997 年东亚国家有意加强地区合作之时,美国作为“外部行为体”对两个地区内大国(中国和日本)并不持有明显的偏向性立场。从地区秩序构建的外部逻辑来看,尽管没有明确的支持性力量,但也不存在明显的干扰性因素。
然而,后续的发展并不符合启动阶段时的美好预期。中日之间的竞争、地区机制的日渐繁杂和外部干扰的出现形成合力,导致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偏离了原先的轨道。
第一,中日之间在双边层面上矛盾不断,缺乏利益共同点。在地区发展思路和国家间关系上,中日之间缺乏信息沟通和利益协调,导致双方的互信不断降低。中日之间固有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一直未能找到解决办法,中国不断批评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日本则指责中国阻碍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民间时而高涨的敌视情绪,都加剧了中日在双边层次上的矛盾。2006 年,日本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概念,意在推行价值观外交,团结所谓的民主国家,实际上是在谋求更大的地区影响力,也成为中日较量的直接体现。这些都导致“10+3”机制框架下的自贸区谈判进展缓慢,而具有双边特点的“10+1”谈判对中日两国都显现出更大的吸引力,并成为中日在地区内部竞争的主要方面。
第二,开放的地区主义导致地区机制的繁杂性不断增加。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主义逐渐升温,各国意识到加强合作的重要意义。但东亚自身的多样性,导致地区内部出现了涉及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多种地区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10+1”、“10+3”、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
 除主要讨论安全问题的东盟地区论坛外,其他繁多而复杂的地区机制都旨在推动经济领域的地区合作。然而,过多机制的存在使机制的繁杂性明显增加,导致各国精力分散,缺乏凝聚力和行动力,很多机制效用下降,谈判旷日持久,无法取得一致,部分机制甚至变成了清谈场所。
除主要讨论安全问题的东盟地区论坛外,其他繁多而复杂的地区机制都旨在推动经济领域的地区合作。然而,过多机制的存在使机制的繁杂性明显增加,导致各国精力分散,缺乏凝聚力和行动力,很多机制效用下降,谈判旷日持久,无法取得一致,部分机制甚至变成了清谈场所。
至 201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实质性变化。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宣布建成,意味着中国在中日竞争中取得优势。不断加强的外部干扰也在此时取得突破性进展。2010 年,东亚峰会宣布接纳美国和俄罗斯参与其中,从而彻底改变了地区机制的权力结构,也冲淡了原有的“10+3”机制的作用。这些情况都表明,中日两国已经错失了构建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最有利时机。
苏联解体使 15 个国家获得独立,也使中亚成为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一个地区。中俄作为中亚国家最大和最重要的两个邻国,与中亚国家构成了一个包含 2 个大国与 5 个中小国家的地区。如何塑造地区秩序成为中亚的核心问题。
独立之初,失掉了超级大国地位的俄罗斯在极力摆脱周边地区的“小兄弟”和“穷兄弟”,试图轻装上阵拥抱西方和整个世界。然而,西方并没有按俄罗斯预想的那样热情地接受新生的俄罗斯,反而推动俄罗斯在下坡路上继续前行,这种窘境迫使俄罗斯不得不放弃倒向西方的对外政策,重新重视起周边地区。1994 年 5 月,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俄罗斯战略》的报告,认为俄罗斯应当维护这些周边国家的政治独立,通过创造政治、军事和其他条件,促进经济交往和融合,以确保和支持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利益。报告也明确指出,运用这一方式的哲学思想就是“用领导地位代替直接控制(лидерство вместо прямого контроля)”。
 中亚国家在完成独立进程后也发现,它们在对外关系中仍然需要“从俄罗斯讨生计”。
中亚国家在完成独立进程后也发现,它们在对外关系中仍然需要“从俄罗斯讨生计”。
 由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开始在地区层次上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中国则在双边层面解决了建交、履约等问题后,开始主动探索在地区层面同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发展合作的思路。1996 年和 1997 年,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两份文件的签署正式开启了中亚地区的安全合作进程,并由此逐步建立起上海五国机制。
由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开始在地区层次上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中国则在双边层面解决了建交、履约等问题后,开始主动探索在地区层面同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发展合作的思路。1996 年和 1997 年,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两份文件的签署正式开启了中亚地区的安全合作进程,并由此逐步建立起上海五国机制。
尽管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是在新独立国家的基础上开展地区合作,但必须承认几十年统一国家的历史使俄罗斯对中亚各国具有重要影响,它们开启的一体化进程被称作“维系式的”,
[13]
它们组成的地区带有松散的等级体系的特点,俄罗斯在其中享有地区主导地位。因此,中国所面对的中亚是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中国是崛起国,不仅要不断介入中亚,
 也需要参与构建中亚的地区秩序。但对中国来说,在中亚构建由中俄两国作为双重领导的地区秩序是更有利的选择,且这一构建过程属于差异型构建的类型。
也需要参与构建中亚的地区秩序。但对中国来说,在中亚构建由中俄两国作为双重领导的地区秩序是更有利的选择,且这一构建过程属于差异型构建的类型。
首先,中俄两大国目标的接近和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成为构建地区秩序的重要基础。1996 年,在高层频繁互访之后,中俄两国明显提升了双边关系水平,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全球层面,两国都主张建立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主要目标都是提升本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在地区层面,两国都希望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同地区国家开展合作。2001 年,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从新世纪起,不断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双边关系的良好使作为主导国的俄罗斯愿意接受中国参与中亚地区事务,并且中国也没有采取破坏性的方式继续对俄罗斯施压,而是推动实现双赢和共赢的结果。
 正是这种不严重损害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传统地位的思路,使中俄两国得以共同推动中亚地区建立上海五国机制。无论是边境稳定还是打击三股势力,中亚国家不仅需要俄罗斯,也少不了中国。从客观上看,实现各国的边境安全需要中国的参与,地理因素塑造了中国的不可或缺性。
正是这种不严重损害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传统地位的思路,使中俄两国得以共同推动中亚地区建立上海五国机制。无论是边境稳定还是打击三股势力,中亚国家不仅需要俄罗斯,也少不了中国。从客观上看,实现各国的边境安全需要中国的参与,地理因素塑造了中国的不可或缺性。
其次,地区机制建设选择了单一领域切入,并逐步实现制度化和组织化。上海五国机制以及 2001 年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都聚焦于安全领域开展合作,这是俄罗斯的优势领域,俄罗斯所具有的信心使其减少了对中国参与和介入的反对。地区机制的建设和不断发展也塑造和维护着中俄在地区内的领导地位。
最后,在外部因素上,尽管不能完全阻止美国对中亚施加影响,但美国并不具备改变地区现有架构的能力和决心,中俄两国在防止外部介入问题上存在共同认知。由此,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中俄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在同一功能领域(安全领域)中的共同领导。
然而,中亚地区的双重领导秩序从单一的安全领域向经济等其他领域的拓展过程却并不十分顺畅。各国虽然多次认可了开展多边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并在边贸、能源等具体领域开展了相关合作,但建立自由贸易区等经济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展开,更多的合作聚焦于双边层面。这反映出各国在形势认知和利益评估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巨大优势使其有意借助于上合组织的平台开展深层次的经济合作,加深本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但不仅俄罗斯对中国拓展经济影响的负面结果存在担心,中亚各国也担忧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国。俄罗斯于 2011年开始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在其众多的利益诉求之中,以集体方式应对中国的经济介入并同中国在新框架下开展经济合作尽管不是主要目标,但也是重要的附带目标之一。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积极参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除了合作基础良好外,也存在抱团取暖和防止本国成为中国经济附庸的考虑。这些都是中国作为崛起国在差异型构建地区秩序时需要不断面对和解决的新问题。
2015 年,陷入多重困境的俄罗斯终于有意愿推动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同中国开展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与中国推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对接建设。这不仅给中国提供了深度介入中亚地区的契机,也为合作领域的拓展即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提供了动力,包含中俄两大国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显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俄罗斯推动多年的上合组织扩员也在 2015 年 7 月实现突破。印度的加入将改变上合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也意味着初具雏形的中亚地区双重领导型秩序的构建过程遭受重大影响。
作为后冷战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将地区层面视作维持其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构建超地区项目模糊地区和全球层面之间的差别,使美国成为相关地区的实际成员而不是一个外来的介入力量,
[14]
从而实现对地区秩序的塑造和掌控。然而,该战略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面临着调整的迫切需要。一方面,中国挺过了 2008 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以“金砖国家”的耀眼身份成为令全世界瞩目的新兴经济体,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则备受金融危机打击,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着有利于中国的转变,并在 2010 年实现标志性变化,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经济提升相伴随的是中国在全球层面谋求发挥更大影响的决心和行动,二十国集团(G20)会议、金砖国家集团等机制和组织都成为中国扩大影响的舞台,这在美国看来是一种愈加明显的对其地位发起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 2010 年中国与日本在东亚的地区较量“尘埃落定”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出现质变的趋势。中国已成为周边 11 个国家以及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7 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
 这些新情况都促使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战略东移,更深刻、更直接地介入东亚地区事务中。由此,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秩序上的互动可作为讨论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构建的又一个案例。
这些新情况都促使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战略东移,更深刻、更直接地介入东亚地区事务中。由此,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秩序上的互动可作为讨论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构建的又一个案例。
从类型上看,以中美两国为核心建立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属于差异型构建,美国具有主导国地位,在东亚拥有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传统盟友或追随者,中国则是崛起国,中美尽管依然存在差距,但差距已呈现缩小趋势。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显示出在经济领域中的比较优势,吸引以东盟国家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中小国家加快经济合作步伐,进一步密切经济联系,这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得以率先建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采取的主要战略措施集中在军事领域,包括强化美韩、美日同盟,与中国展开军事竞争等。这些表现使学界认为东亚地区呈现出“二元格局”,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出现了功能分异,地区中小国家作出了“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选择。
然而,从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出之始,美国的目标就不是集中于单一领域,它试图帮助亚洲建立一个有助于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安全和经济体系,以维护其全球性领导地位。
[15]
美国采取多种实质措施,通过区域性组织、新的对话以及高层外交增加对亚洲事务的参与。
 2010 年,美国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国反映出其扩大地区参与的努力。一方面,美国不断强化在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制定了在 2020 年前将 60%的美国海军作战舰艇部署到亚太地区的目标;
[16]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经济领域加大投入以进行所谓的“收复失地”。2008 年,美国作出了加入TPP谈判的决定,显示了其改变区域经济政策的动向。在美国看来,通过推进TPP,不仅可以避免自身被排除在地区合作进程之外,借此获取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权,而且可以在经济合作进程中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孤立,至少可以从制度和规则等层面消解中国在地区经济领域的影响力。
2010 年,美国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国反映出其扩大地区参与的努力。一方面,美国不断强化在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制定了在 2020 年前将 60%的美国海军作战舰艇部署到亚太地区的目标;
[16]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经济领域加大投入以进行所谓的“收复失地”。2008 年,美国作出了加入TPP谈判的决定,显示了其改变区域经济政策的动向。在美国看来,通过推进TPP,不仅可以避免自身被排除在地区合作进程之外,借此获取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权,而且可以在经济合作进程中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孤立,至少可以从制度和规则等层面消解中国在地区经济领域的影响力。
 至 2015 年,TPP协定的初步达成,不仅显示出美国强化地区经济合作、塑造其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决心,也成为中美二元格局“昙花一现”的某种标志。
至 2015 年,TPP协定的初步达成,不仅显示出美国强化地区经济合作、塑造其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决心,也成为中美二元格局“昙花一现”的某种标志。
对照本文的概念,中美在东亚形成的所谓“二元格局”并非真正的双重领导,中美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而将地区秩序建立在分享原则和包容性领导的基础上,则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管控中美竞争。 [17] 但中国作为崛起国,在真正实现同美国分享地区领导权方面,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首先,美国是以一个超级大国的身份充当东亚地区主导国的,这不仅意味着中美在事实上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实力差距(尽管有所缩小),更意味着不存在一个能够迫使中美两国接受对方的地区外部力量,而在其他 3 个案例中,无论作用是否积极,地区外的强势行为体(实际上就是美国)都是存在的。其次,中美两国在国家利益的不同层次目标上存在分歧,协调难度较大。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认为“中国寻求多极世界、单极东亚的格局,而美国寻求单极世界、多极东亚的格局”。
 尽管这一观点未必完全符合实际,但中美之间的目标差异显而易见,这使得双方很难像在中亚地区的中俄两国一样开展战略协作。在美国看来,中国不仅在东亚地区挑战了其地位,更在全球层面是有力的竞争者。最后,这一时期的东亚缺乏推动中美开展紧密合作的有效地区机制或合作框架。2010 年,东亚峰会(EAS)接纳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也就同时宣告了这一机制将难以实施有效行动。类似的地区机制或跨地区机制,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都存在效用有限的问题。而无论是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还是美国试图做强的TPP,都心照不宣地排除了对方的参与,这两者都是在经济领域开展合作的机制平台,体现出中美两国在地区事务的单一领域中存在着明显竞争。而中美两国在整个地区秩序上发挥协作,进行功能重合性的双重领导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这一观点未必完全符合实际,但中美之间的目标差异显而易见,这使得双方很难像在中亚地区的中俄两国一样开展战略协作。在美国看来,中国不仅在东亚地区挑战了其地位,更在全球层面是有力的竞争者。最后,这一时期的东亚缺乏推动中美开展紧密合作的有效地区机制或合作框架。2010 年,东亚峰会(EAS)接纳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也就同时宣告了这一机制将难以实施有效行动。类似的地区机制或跨地区机制,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都存在效用有限的问题。而无论是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还是美国试图做强的TPP,都心照不宣地排除了对方的参与,这两者都是在经济领域开展合作的机制平台,体现出中美两国在地区事务的单一领域中存在着明显竞争。而中美两国在整个地区秩序上发挥协作,进行功能重合性的双重领导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本文所涉及的 4 个案例进行整体性评估,可以发现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并非易事。德国和中国的实力增长都增加了法国和俄罗斯引入第三大国的意愿,尽管它们已经在经济或安全的单一领域构建出双重领导,但终究未能阻止地区机制成员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地区权力结构的改变。中日两大国对外目标的难以协调和国家利益的激烈竞争使地区机制未能发挥实际效用,加之缺乏外力影响,双重领导未能得以建立。而中国作为崛起国,在一个由超级大国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试图构建双重领导,其障碍和难度更为巨大。结合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障碍作出总结,并提出可能的破除路径。
第一,实力的不均衡发展。国家实力的差别化发展,是国际关系难以改变的现实。德国实力的快速增长是促使法国转变对英国加入欧共体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经济的强大实力,也是促使俄罗斯极力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导致安全领域的双重领导型秩序在向经济领域拓展的构建过程中因地区权力结构改变而遇阻。因此,减小实力不均衡发展的负面影响有助于维系双重领导秩序的持续构建,对于两大国中实力发展更为迅速的国家来说,将自身国力提升的收益与周边国家特别是地区内另一大国分享,有助于保持双方的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国要自缚手脚,因为提升本国国力始终是获得和维持领导地位的根本,特别是在差异型构建的过程中,崛起国要同主导国分享领导地位,也必须依靠自身实力的增强才能获得对话和分享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仅仅是在经济领域有所成就,中美之间依然明显存在着实力差距,这也是双重领导难以构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平衡型构建的过程中,发展较快的大国应注意分享收益;而在差异型构建的过程中,在分享收益的同时,崛起国不仅应具备“一技之长”,吸引中小国家,也需要在保证长板更长的同时,努力补足短板,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地区领导者之一。
第二,领导国特别是主导国的分享意愿。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得以建立的最关键因素是两个大国愿意分享领导地位和权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并促进发展。法德和解与中俄关系的持续推进都是地区秩序构建的推动力,甚至是源动力。中国提出同美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也是有助于塑造双重领导秩序的有益尝试。但即便其中一个国家或者说崛起国愿意分享,让另一个大国特别是主导国同样愿意分享权威也是非常困难的。结合本文各案例提供的经验教训,可以从以下方面破解这个关键障碍。首先,寻找利益共同点,在目标排序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换和协调。法德在防止新战争上具有共识,中俄在边境稳定和应对美国压力上具有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即便在很多目标上存在冲突,也依然可以找到利益共同点。例如,在反恐、贫困、大规模疾病、环境等全球问题上中美依然具有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在实力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崛起国在双边和全球层次上同主导国的更多合作,将有助于促进两国在地区层次上的协调。其次,发展同中小国家的关系,迫使另一领导国特别是主导国接受。在差异型构建过程中,主导国分享权力更具被动性,因此崛起国可以采取“围魏救赵”式的迂回战略,通过与中小国家密切合作和联系,促使主导国承认和接受崛起国的领导地位,此时崛起国成为一个被中小国家邀请的领导。其中,崛起国可以注意发掘和塑造本国的“不可或缺性”,增加中小国家的合作意愿。例如,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边境稳定问题上具有不可或缺性,因此主导国俄罗斯必须和中国一起同中亚国家开展合作。
第三,地区机制的缺失或失效。在德法、中俄和中日的案例中,地区机制都是存在的,但由于加入新成员或者机制本身存在问题而在塑造双重领导秩序时失效。中美之间则缺乏一个符合“两强众弱”权力结构的有效机制。因此,采取由小领域切入、逐渐扩展的方式,在某个领域,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议题领域,建立一个由两大国及其他中小国家共同参与的机制对秩序的构建也是有益的;地区机制的制度化水平也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思路,以保证其有效运行。对崛起国而言,寻找或制造某项议题,并同主导国共同倡建一个合作机制,将有助于利益协调和秩序构建。
除上述三方面外,崛起国还可以通过寻找“共同敌人”的方式来破解秩序构建的障碍。尽管外部因素并不是决定性力量,特别是在超级大国作为主导国的地区,外部因素可能并不存在,但崛起国可以通过树立共同敌人的方式来设定议题,以此促成与主导国的合作和建立地区机制。例如,恐怖主义或流行性疾病可以作为地区共同敌人,尽管议题较小,但却可以成为利益协调和合作启动的契机。
本文结合实例,探讨了双重领导型地区秩序的构建逻辑,其基本框架在于理清地区内外各种因素在构建地区秩序时的作用,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区整体 3 个方面是地区秩序内部构建时的主要因素,而地区外部因素对地区内部的影响也需要加以引导和控制。这些因素之间存在联动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因素和特点尝试破除秩序构建过程中的障碍。
回到现实问题上,我们对相关地区的发展前景可以作出评估。作为2016 年年内的重要事件之一,英国退欧将开启欧洲地区秩序新的一页,欧盟是否会重新回到“双重领导”秩序,其秩序构建将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值得持续关注。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尽管增加了地区互动的复杂性,但却并不意味着此前所有的互动与合作将被中断或抛弃,既往的合作依然可以帮助中国稳固在地区安全领域中的领导性作用。对于具有经济优势的中国而言,有效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契机和自身优势,仍将有利于塑造和巩固本国在地区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而在东亚地区,尽管TPP可能已经无法生效,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秩序构建过程中的短板依然未能补起,长板则存在下滑趋势。继续增强国力,稳定目前向好的与地区中小国家关系发展的趋势,寻找共同利益和议题将中美纳入同一个有效的地区机制中,都将有助于塑造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论文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1 期)
注释
[1] 有关上合组织扩员前景的分析,可参见许涛、王明昌:《“上海进程”持续二十年的地缘政治意义》,《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 4 期;Антон Фань(Фань Суэсун), Расширение состава ШОСшансы и вызовы,7.27 ,2015,http:// eurasian-defence.ru /?q =node /34066,访问时间:2015 年 9 月 10日;Игорь Денисов и Иван Сафранчук, Четыре проблемы ШОС в свете вопроса о расширен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9.2,2016,http:// infoshos.ru / ru /?idn = 15909,访问时间:2016 年 9 月 20 日。相当多的学者尽管强调了扩员的积极意义,但也明确指出了扩员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
[2] 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s ‘Peaceful Rise’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1.3,2010,p.28.
[3] 关于霸权稳定论可参见经典著述: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Charles P.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No.3,1981,pp.242-254。有关等级制的研究,参见David A.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4] 摩根在讨论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类型时,就将“两极”直接归入了权力制衡类型。参见Patrick M.Morgan,“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and Regional Orders,”in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eds., 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pp.33-34。
[5] 有关二元格局的讨论,可参见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 年第 5 期;周方银:《东亚二元格局与地区秩序的未来》,《国际经济评论》2013 年第6 期;蔡鹏鸿:《亚太两强竞争性合作格局趋势与中国外交》,《国际观察》2013 年第 1 期;G.John Ikenberry,“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American,China,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20,No.20,2015,pp.1-35。
[6] G.John Ikenberry,“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American,China,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20,No.20,2015,p.7.
[7] [美]约翰·伊肯伯里:《地区秩序变革的四大核心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1 年第 1 期;G.John Ikenberry,“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American,China,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20,No.20,2015,pp.1-35.
[8]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Affairs,”in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eds., 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9.
[9] 本文讨论的对称性和非对称性主要聚焦于两大国在地区内的不同地位,如果地位或身份相当则是对称性的,如果其中一个是主导国而另一个谋求分享权威,则是非对称的。所有的讨论建立在两大国实力差距已经接近或在不断缩小的基础上。这与汉瑞德讨论的两极体系的对称和非对称的类型划分并不一致,汉瑞德主要关注的是两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是否对称,更偏重于物质性因素,本文的对称性更多关注的是非物质性的地区地位比较。参见Wolfram F. Hanriede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Bipolar or Multibloc?”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9,No.3,1965,pp.303-304。
[10] L.J.Cantori and S.L. Spiega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Eaglewood Cliffs:Prentice-Hill,1970,pp.6-7.
[11] 有相当多的研究和观察认为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特别是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但这并不妨碍大国在地区内谋求领导地位,且实际上正是本部分所谈到的中日构建双重领导秩序的失败和作为地区两大国的中日之间的竞争,使东盟的领导作用得以实施和显现。有关东盟领导作用的研究,参见Richard Stubbs,“ASEAN'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n Region-Building:Strength in Weakness,” The Pacific Review ,Vol.27,No.4,2014,pp.523-541。
[12] Rosemary Foot,“Pacific Asia: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alogue,”in Lou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39.
[13] Alexander Libman and Evgeny Vinokurov, 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2.
[14] Barry Buzan,“The Asia Pacific:What Sort of Region in What Sort of World?”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Routledge,1998,pp.68-87;[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 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06—108 页。
[15] Hillary R.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Issue 189,2011,pp.56-63.
[16] 2014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QDR) ,March 4,2014,http:// www.defense.gov / Portals/ 1 /Documents/ pubs/ 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访问时间:2016年 10月2日。
[17] Alexander L.Vuving, What Regional Order for the Asia-Pacific?China's Rise,Primacy Competition,and Inclusive Leadership ,http:// apcss.org/ wp-content/ uploads/ 2012 /09 / Chapter17.pdf,访问时间:2016 年 12 月 1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