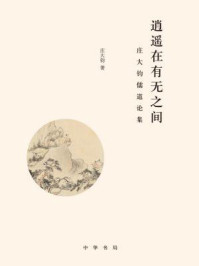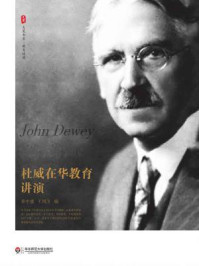韓愈在散文上的主要貢獻,是倡導“古文”,從理論到實踐,全面地實現了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根本革新,造成了文學散文發展的又一個高峯。
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認爲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東坡後集》卷一五)。這主要是指他以古文取代了東漢以來逐漸興盛起來的駢文。桐城派的創始人方苞認爲,所謂“古文”乃是“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肆也”(《古文約選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曾國藩則明確指出,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覆許仙屏》,《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一四)。這都從對流行的駢文摧陷廓清之功上肯定了他在轉變文體與文壇風氣上的貢獻。
關於韓愈的文體“復古”,涉及問題很多。這裏祇討論一點,即韓愈倡導與創作“古文”得以成功,不僅由於他善於繼承與發揚上古秦漢散文優秀傳統,並多方面學習古代各體文章的表現方法,也是他廣泛汲取東漢以來散文發展、包括駢體文發展所取得的藝術成就的結果。
造成“古文運動”的興盛,本不是韓愈一個人的功勞。古文取代空洞浮豔、雕繡藻繪的駢文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文體與文學發展的歷史潮流。舊史説:
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
清人趙懷玉也指出:
退之起衰,卓越八代,泰山北斗,學者仰之。不知昌黎固出於安定(梁肅)之門,安定實受洛陽(獨孤及)之業。公則懸然天得,蔚爲文宗。大江千里,已濫觴於巴岷;黄河九曲,肇發源於星宿。(《獨孤憲公毘陵集序》,《毘陵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這都説明,大曆、貞元年間,倡導“古學”已形成風氣。而如追溯淵源,提倡文體復古早已始於北朝;至隋代南北文風融合,改革文體、文風的要求更漸趨强烈,代表者有李諤、王通等人。入唐以後,批判六朝浮靡文風、提倡革正文體已是文壇一般主張。經陳子昂到開、天年間的李華、蕭穎士、元結等人的努力,到中唐時期“古文”已漸成聲勢。韓、柳等人不過是順應歷史潮流取得傑出成就的佼佼者而已。
但應當承認,韓愈及其文壇盟友柳宗元在倡導與創作古文方面確實取得了遠遠度越前人與同時流輩的成就,而做到這一點又有多方面的原因。其重要一點在於他們總結了散文發展的歷史經驗,不是形式主義地擬古(如北朝蘇綽仿《周書》作《大誥》,王通仿儒典作《元經》),更不是單純追求實用而反藻飾(如隋文帝楊堅反對文表華豔、要求“實録”),也不如李華等人片面强調文必宗經;而是更辯證地理解並遵循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對前人積累的藝術經驗去粗取精、融液搜澤,將其有價值的成果納入自己的創作實踐,從而實現了“復”中有“變”的創新與發展。而從文學發展歷史看,正是自魏晉以後進入了“文學自覺”的時代;文學創作中藝術表現上的許多進步,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韓愈等人否定駢文,是實現了辯證的“揚棄”,即捨棄了它的僵化的形式,而繼承了它所取得的藝術成就。葉適説:“若夫言語之縟爲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而益趨於文也。”(《櫟齋藏書記》,《水心文集》卷一一)就説出了這個道理。
阮元論駢文,謂“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揅經室三集》卷二)。他作爲新“文筆論”的代表,爲駢文争正統,看法往往流於偏頗,但其見解又是有合理内容的。駢文文體發展中把中國散文中固有的排比對偶、聲韻詞藻、使典用事等表現方法絶對化、程式化了。但這種“别於經傳子史,通於詩賦韻言”(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卷三《雜説下》)的對偶用韻之文,確乎發展了中國散文的技巧,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成就。因此後人謂“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一)。唐代作家大都嚴於指斥六朝文風,但唐代文學的偉大成就却又是在六朝文學發展的基礎上取得的。韓愈的“古文”成就也是如此。後來不少人指出了這一點,如袁中道説:
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内都無才人。但以辭多意寡,雷同已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爲功多。(《解脱集序》,《珂雪齋文集》卷一)
劉開説:
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與阮芸臺宫保論文書》,《劉孟塗文集》卷四)
劉熙載説: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藝概》卷一《文概》)
蔣湘南説:
淺儒但震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七經樓文鈔》卷四)
如此等等。韓愈的創作正可印證這些看法。
從行文體制上看。韓愈的“古文”已完全不同於先秦盛漢質樸無華的散行文體,在句式、聲韻、詞藻等方面都融入了駢體的技巧。他主張文章要“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宫商相宣,金石諧和”(《送權秀才書》),要求“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這都涉及駢體結句和聲韻等技法。他的有些文章如《進學解》、《送窮文》等,基本上用整句韻語;如《原毁》,則全篇以長排組成。他更把儷詞偶語融入行文,取其嚴整流暢,音調諧合;他還靈活使用意對語不對,語對意不對,散行中兼用四、六偶句等方法,把駢儷消化在散體的語氣文情之中。這樣,他調動了駢體修辭的各種功能,增强了文章的表現力。包世臣曾指出:
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至爲微妙。(《文譜》,《藝舟雙楫·論文》卷一)
韓愈在發揮駢、偶兼行的功能上就是如此深入化境的。
從文章體裁看。吴汝綸曾指出:先秦以來有集録之書,自著之言,前者出於《詩》、《書》,後者出於《易》、《春秋》,“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録之體”(《天演論序》,《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三)。而這種單篇集録的創作體制正是形成於魏、晉以來“四部分,文集立”之後。也正由於創作單篇集録的文章,才發展了不同於秦漢著述形式的各種散文文體。包世臣又指出:
周、秦文體未備,是矣,魏、晉以後漸備,至唐、宋乃全。(《復李邁堂書》,《藝舟雙楫·論文》卷三)
實際上,韓愈所運用與發展的散文體裁,基本是直承六朝的。劉開則指出:
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備;文之體制,至八代而乃全。(《與阮芸臺宫保論文書》,《劉孟塗文集》卷四)
因此,没有六朝各體散文的創造,就不會有韓愈各體散文的成就。例如韓文中藝術成就很高的碑傳、記序、書信等體裁,都先後興盛、完善於六朝。而在韓愈創作中,比起另一類論説、表狀等文章,這些文體的作品顯示出更强的藝術創造特性,更能突現出他的散文藝術的高度水平。
從表現方法看。韓愈散文的藝術獨創性表現得非常突出,重要一點是更强烈地發展了文學主觀創造的特性,在這方面大大超越了先秦盛漢的傳統。如袁宏道就曾指出:
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虚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别,有叙事;爲文者有辨説,有論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虚,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雪濤閣集序》,劉大杰編校《袁中郎全集·序文》)
這裏涉及詩的問題不論;關於文的用“虚”而“不能實”,正是發揮作家主觀創造力的表現。朱宗洛在分析《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時説:
如題是《送温處士》,便當贊美温生。然必實講温生之賢若何,便是呆筆。作者已有送石生文,便從彼聯絡下來,想出“空”、“羣”二字,全用吞吐之筆,令讀者於言外得温生之賢,而烏公能得士意,亦於筆端帶出。此所謂避實擊虚法也。(《古文一隅》卷中)
如這裏的“避實擊虚”,不只是黏題不黏題的構思問題,更重要的是發揮作者想像、聯想、虚構的能力,以實現藝術概括與創造的問題。韓愈善於架空虚説,别開生面,“文體均稱,翻出異樣,采繪照耀耳目”,“用意筆墨皆烟雲”(惲敬《答來卿》,《大雲山房言事》卷二);批評他的人又説他的文章多“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朱熹《讀唐志》,《朱文公全集》卷七〇)。“諂諛”當然不足取,但“戲豫”追求趣味,“無實”有虚構成分,用之得當,乃是有藝術價值的寫作手法。在韓愈寫作中,這些都顯示出他有意識地從事藝術創新的努力。而在這方面,他也是發展了六朝的傳統的。六朝文的浮靡不實也是一種用“虚”,只是表現的内容多淺薄或頽唐而已。
清人王鐵夫指出:
古文之術,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於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爲大家。自非馳騖於東京、六朝沈博絶麗之塗則無以極其才……韓、柳皆嘗從事於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掃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夐絶千餘年。(轉引淩揚藻《蠡勺編》卷三八《王鐵夫論韓柳》)
這個看法是符合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