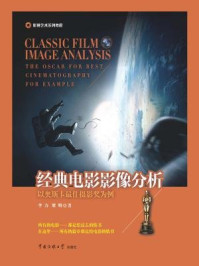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党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入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1886—1934)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尼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10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布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监禁。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
为了使“大清洗”显得合法,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1881—1936)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1885—1939)、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10年或8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应付国内外舆论而刻意制造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于1936年9月被更加严酷的叶若夫(1895—1940)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1899—1953)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处决。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迫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英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