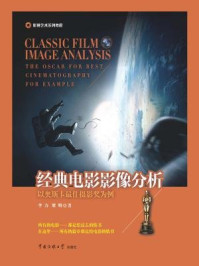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中大声疾呼: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这是专制君主统治下的人们的真实写照。对于生活在专制暴政下失去自由的启蒙思想家来说,自由弥足珍贵,他们热烈地渴望自由、追求自由;他们要打破枷锁,挣脱镣铐,恢复和实现自由。
启蒙泰斗伏尔泰一生受尽专制统治的迫害,青年时因开罪于贵族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其著作受到专制政府的查禁,他自己甚至不能踏上祖国的土地,晚年被迫住在法瑞边界地区的菲尔奈,被尊称为“菲尔奈教长”。一生的悲惨经历使他对法国毫无自由深为痛心,并渴望获得自由。他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专门列有“论自由”一条,认为自由就是你个人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利。他还曾对“自由”作过这样的解释,认为除了法律之外,不依赖任何东西,就意味着自由。其含义为,自由是一种源于自己独立意志的一种行为,一种权利,一种天赋权利,它不容压制和剥夺,自由的界限并不是专制君主的意志或别的什么,只是法律的规定,这种法律是符合于自然权利的立法,而非封建专制的任何法规。换言之,自由并非是随心所欲,它是在不违背法律前提下的自由,如果你的意志和行为违背了法律,也就侵害了别人的自由,也使自己成为不自由。他说:“成为自由,那就是只受法律支配。”

伏尔泰在英国生活了三年,亲眼目睹了英国人民所享有的高度自由,“所有的公民不能同样地有势力,却能同样地自由”。他在《哲学通信》一书中向法国人介绍了英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内容:人身和财产的自由;用笔向国家提意见的自由;只能在一个由自由人所组成的陪审委员会面前才可受刑事审问的自由;不管什么案件,只能按照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来裁判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他指出:这些自由是人民所享有的天赋权利,不容剥夺,它是超之于国家之上的人的特权。如当你睡觉在第二天醒来时,你的财产还和昨天一样,没有丝毫变动;你不会在半夜三更从你妻子的怀抱里或从你孩子的拥抱中被人家拖出去押入城堡,或流放沙漠;当你若有所思,你有权发表你的一切想法;当你被人控告,或写了闯祸的文章,只能依照法律来裁判等等。
作为思想家,伏尔泰更重视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他认为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人们的天赋自然权利,“我们天然地据有使用我们的笔的权利,就像我们有说话的权利一样”,“发表自己思想的自由是公民的自然权利。公民能够使用自己的笔就像使用自己的声音一样:禁止写作比禁止说话更不应该;用笔犯法而受处罚就像因说话而受处罚一样”。一个社会只有允许自由地发表言论才会带来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伏尔泰强烈地谴责下令烧毁卢梭著作的日内瓦当局,认为焚书行为是令人憎恶的,那种以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将导致亡国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事实证明,“倘若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表意见,社会会是平静的,不会产生混乱”,相反,如果暴君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则是社会的灾难、人类的灾难。
从伏尔泰所列举的自由的这些内容来看,不仅全都是法国人民所没有的,也是他自己所遭受的毫无自由经历的真实表达。通过对比,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没有自由的痛苦和自由的可贵。“在自由的国家有一百金币比在专制的国家拥有一千金币更有价值。”伏尔泰向法国人民大声疾呼:“人民呵,醒来!挣断自己的枷锁,自由在向你呼唤!”
与伏尔泰不同,孟德斯鸠生为贵族,作为个体,他享有很多“特权”式的自由,但他却看到了整个法国在专制统治下毫无自由可言的状况。所以,在他的内心,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自由的追求。
孟德斯鸠很明确地把自由分为两类:一种为“哲学上的自由”,一种为“政治上的自由”。他说:“哲学上的自由,是要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如果应从所有的体系来说的)自己相信是在行使自己的意志。政治的自由是要有安全,或者至少自己相信有安全。”这两种自由完全不同,第一种自由相对应于自己的意志,第二种自由则与社会相互联结,形成互动。政治自由不像哲学上的自由,不是在自己的意志中完成和实现,而是在社会中完成和实现。有人以为在民主国家里,仿佛是人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此,孟德斯鸠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政治自由的含义,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实际上,“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
。
自由的界限是既存的社会法律,而自由的真正存在与否则与政体密切相关。人们通常总是认为民主政治有自由,而君主国无自由。他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是把人民的权利与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他认为民主政治的国家在性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国家,“政治自由只在宽和的政府里存在”,并且,它“只在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存在”。由此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认定“政治自由是通过三权的某种分野而建立的”。否则的话,将会出现暴政,人民将失去自由。他说:“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他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这种政府即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政府。
自由并非是被动的,在一个好的政体下会自动出现,自由应是主动的积极的。要享有和保全自由的话,必须让每一个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实现思想和言论自由,“说或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说或写的东西”,决不能以言定罪。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他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一个人推理推得好或不好,常常是无关紧要的事,只要他推理就够了,自由就表现在这里,自由就是使人不受这些推理的影响的保证。”只有专制国家才会以言定罪,以思想定罪。如果这样做,“不但不再有自由可言,就连自由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自由是人们在法律界限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人们自由地思想、言谈和行动,就如同呼吸空气一样的自然和必不可少,没有自由,人们便无法生存。自由是世间最为珍贵的东西,它远胜于物质的利益和财富。如果拿自由与物质利益相比较,自由更为重要。所以孟德斯鸠说:“人民为了保卫这个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的财富、安乐和利益,宁愿担负最重的赋税,这种重税就是最专制的君主也不敢让他的臣民去负担的。”
 的确,在这样一种热爱自由、保卫自由而甘愿牺牲一切的民族那里,难道不能实现他们真实的自由吗?
的确,在这样一种热爱自由、保卫自由而甘愿牺牲一切的民族那里,难道不能实现他们真实的自由吗?
孟德斯鸠是用“三权分立”来捍卫人们的政治自由,而卢梭则认为靠三权分立,只能是短暂的政治自由而不能长久。他认为只有在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状态下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自由。卢梭把自由分为自然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两种,认为自然的自由是人民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即“人生而自由”。但人无法永远生存于自然状态,他必然要进入社会状态,在社会状态下,原先的天然的自由要丧失,而代之以社会的自由。卢梭说:“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的东西的所有权。”
 自然的自由受制于个人的力量,社会的自由受公意所约束。卢梭还认为,在社会自由之中,还有一项自由的内容,即道德的自由。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自由,它存在于社会自由之中,又超然升华于其上,在具有社会性的同时,又更多地带有人的主体良知的道德性。卢梭说:“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这里意味着必须要脱离自然状态下人的本能和原始性的欲望,自觉地服从在社会契约订立后社会共同体的法律,使自己的行动与法律相互协调一致。因而卢梭并不像伏尔泰、孟德斯鸠那样仅从自由是法律前提下的自由来考虑,而是更进一步从人的道德良知的主体性和人与法律关系的视角来考虑,在服从法律的前提下,人的自由并不在于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在于可以做他不想做的事,实际上也是做他不能做的事情。记住并理解了卢梭关于公民“美德”的阐释,就不难理解“道德的自由”,正像卢梭所说,没有道德,何来自由。
自然的自由受制于个人的力量,社会的自由受公意所约束。卢梭还认为,在社会自由之中,还有一项自由的内容,即道德的自由。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自由,它存在于社会自由之中,又超然升华于其上,在具有社会性的同时,又更多地带有人的主体良知的道德性。卢梭说:“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这里意味着必须要脱离自然状态下人的本能和原始性的欲望,自觉地服从在社会契约订立后社会共同体的法律,使自己的行动与法律相互协调一致。因而卢梭并不像伏尔泰、孟德斯鸠那样仅从自由是法律前提下的自由来考虑,而是更进一步从人的道德良知的主体性和人与法律关系的视角来考虑,在服从法律的前提下,人的自由并不在于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在于可以做他不想做的事,实际上也是做他不能做的事情。记住并理解了卢梭关于公民“美德”的阐释,就不难理解“道德的自由”,正像卢梭所说,没有道德,何来自由。
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像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也强烈要求人的政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他在百科全书中列有“出版自由”条目,认为出版自由利大于弊,它应该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法律。除此之外,狄德罗还主张每个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实现财富的自由流通。他多次指出贸易自由将会给国家带来繁荣,“如果仔细思考一下,人们会发现最接近高度民主的政府是最适合经商人们的政府,因为他们的繁荣取决于最大的贸易自由”。相反,如果没有贸易自由,货物和财富不能自由流通就会变成同饥荒一样可怕的灾难。由此可知,狄德罗的贸易自由代表着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表达了他们发财致富的愿望。
当启蒙思想家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他们也在要求平等。如果没有人格和地位的平等,又何来自由?卢梭就曾说过,立法的最终目的应是自由和平等,没有平等,自由便不能存在。两者应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统一体。
对于平等,伏尔泰认为凡是具有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地位的差别、压迫和奴役。他说:中国的皇帝、蒙古的大汗、土耳其的苏丹都不能对地位最低微的人说:我禁止你消化、上厕所和思维。在这个意义上,平等意味着独立和不受奴役,是一种天然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赋予他具有一种与别人平等的地位。人类不仅仅在事实上是平等的,在社会状态下,在法律的规定上也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即是任何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法律使人平等,使人成为拥有同样权利和同样政治地位的公民。这样,任何依附和奴役都是违背平等的,并且任何凭借外在的力量进行奴役和制造不平等都是违背自然的。
当然,人的平等并非意味着一切平等,意味着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无差别。伏尔泰就曾举例说,红衣主教和他的厨师是一种职业上的差别、分工的不同,他们在法律上、政治上拥有相同的权利。如果人们硬要抹杀社会分工的差别,实现一切平等,这不仅不可能实现平等反而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伏尔泰说,人人在心里都有权自信与别人完全平等,可是红衣主教的厨师并不因此就可以命令他的主人给他做饭。因此人们必须对平等有一种正确的认识,不应走向极端。平等是最自然的,如果走向极端,也就变成最荒诞不经的了。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深刻揭示了人类如何从自然状态下的平等走向不平等,然后再实现平等的长期历程。他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私有制的出现。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处于平等状态,后来随着生产活动的展开,产生了贫富分化,由此导致私有制的出现,这是不平等的起源。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富人们为了确保自己的财产,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借口下,与穷人共同缔结约定成立国家,富人们成为统治者,于是出现了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这时人类的不平等进入了第二阶段。在国家建立之后,统治者成了奴役人民的专制君主,或曰暴君,因此,专制暴君的暴政统治是人类不平等的第三个阶段。当不平等进入第三个阶段时,这是不平等的顶点和终点,在这里,它和平等的起点相遇,可以说是新的平等的起点,预示着新的平等的到来和实现,其途径就是人民使用暴力推翻暴政,迎来自身的新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