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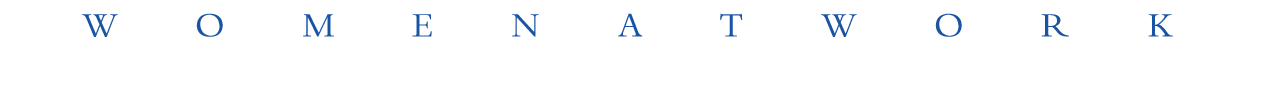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毕肖普女士和两位友人动身去北黑文(缅因州佩诺布斯科特湾的一个岛)度夏前三天,我在波士顿的刘易斯·沃夫公寓采访了她。她的会客室在刘易斯·沃夫公寓的四楼,波士顿港的景色一览无遗;我到了之后,她立刻带我去阳台,指着远处的波士顿地标如老北教堂,说“老铁壳”
 就泊在附近。
就泊在附近。
她的客厅宽敞迷人,锃亮的宽条木地板,横梁顶,两面老砖墙,还有一面墙全部摆满了书。除了一些舒适的现代家具之外,还有紫云木摇椅和其他从巴西运来的古董家具,两幅洛伦·麦克维尔的画,一个基韦斯特岛带回的巨大马螺,还有一座富兰克林火炉,柴火都装在一个驴背篓里,也是巴西来的。屋里最显眼的是一尊巨大的雕塑,无名野兽张着大嘴,头上有角,蓝眼睛,高高悬在墙上。
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便是她的书房,很乱。文学杂志、书、报纸堆得到处都是。墙上有玛丽安·摩尔
 、罗伯特·洛厄尔和其他朋友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巴西的末代皇帝,她特别爱给巴西朋友看。“大部分人不知道他是谁,”她说,“这是在他退位之后,在去世前不久拍的——看上去很悲伤。”她的书桌紧挨着唯一的窗户的一角,也能看到港口的景色。
、罗伯特·洛厄尔和其他朋友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巴西的末代皇帝,她特别爱给巴西朋友看。“大部分人不知道他是谁,”她说,“这是在他退位之后,在去世前不久拍的——看上去很悲伤。”她的书桌紧挨着唯一的窗户的一角,也能看到港口的景色。
六十七岁的毕肖普女士很出挑,向后梳的白色短发衬托着叫人过目不忘的高贵脸庞。她穿着黑色圆领衫,灰色西裤,戴金表和耳环,棕色日式平底凉鞋令她看起来要比一米六三的实际身高矮一些。虽然她看上去健康、兴致也不错,但抱怨最近得了花粉病,她拒绝拍照,并挖苦道:“摄影师、卖保险的、葬礼司仪是最糟糕的人生。”
七八个月后,她读了我给《瓦萨季刊》写的一篇人物特写(基于这次访谈),担心自己会显得像个“轻浮之徒”,于是给我写信:“我曾经挺欣赏弗雷德·阿斯泰尔的一个访谈,他拒绝讨论‘跳舞’、伴侣或者‘事业’,坚定地只谈‘高尔夫’——所以我希望读者能够明白,即便我像一条极浅的小溪那样碎碎念,也时不时会思索一下艺术问题的。”
虽然毕肖普女士有机会修改《瓦萨季刊》的文章中收入的部分访谈内容,但以如下形式呈现的访谈她尚未过目。
——伊丽莎白·斯派尔斯

《巴黎评论》: 你的客厅堪称新与旧的完美结合,这些家具背后有什么故事吗?特别是那尊雕塑,它相当壮观啊。
毕肖普: 我以前在巴西住的房子特别现代。等到我终于得搬家时,我就把最喜欢的家具都带回来了。所以现在是混搭风格。我很喜欢现代的东西,但住在那儿时又买了太多老东西,无法割舍。雕塑是在圣弗朗西斯科河买的,有些更漂亮,这尊算是非常丑的了。
《巴黎评论》: 它是用来驱挡邪灵吗?
毕肖普: 大概是。这些雕像曾经被放在一截两三百英里长的河段旁边,这些雕像大概有五十年的历史吧。圣弗朗西斯科河虽然不能跟亚马孙河比,但也是巴西第二大河。这尊雕塑是原始艺术,我甚至认为自己知道是谁造了它。有个黑人雕了二三十件作品,这尊就是他的风格。有一尊叫红马的紫云木雕特别有名。它和这尊一样美丽,马嘴张开,可惜出于某种原因那些雕像统统消失了。一九六七年我去那河上待了一星期,一尊雕塑也没看见。我乘的是一艘一八八〇年造的艉明轮船,小到你没法相信。我们慢慢开啊开了好多天……有趣的旅行。
《巴黎评论》: 你花那么多时间旅行是为了寻找一个完美的地方吗?
毕肖普: 我不觉得。我好像也没有一直在旅行。一切都很自然,虽然我并不富裕,但继承了一小笔遗产——我八个月大时父亲就去世了,我从学校毕业后就靠这笔钱出门。我旅行时很节约。靠这笔钱我去巴西住了几年,但现在已经没法再靠它度日了。第一本收录我作品的文集中的作者小传这样写:“噢,她去过摩洛哥、西班牙等地。”这话被重复了很多年,尽管我再也没有重温过那些地方。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像如今的学生这样到处跑。我的学生们好像每年复活节假期都会去尼泊尔之类的地方,跟他们比我真是哪儿也没去过。
《巴黎评论》: 好吧,我总觉得你很有冒险精神。
毕肖普: 我想去亚马孙河上游看看,也许我会去。可以从秘鲁出发顺流而下——
《巴黎评论》: 你在旅途中会写作吗?
毕肖普: 有时写,要看情况。我通常会记笔记,但也不一定。我记类似日记的东西。我最喜爱的两次旅行,一次是亚马孙,一次是三四年前去加拉巴哥群岛……我还很想再去意大利,因为根本看不够。还有西西里。威尼斯太棒了。佛罗伦萨比较辛苦,我觉得。上一次去意大利还是一九六四年,和一个巴西朋友一起。我们租了一辆车,用五六个星期玩了意大利北部。我们没去罗马。我必须再去一次。有太多东西还没看到。我喜欢绘画的程度可能要超过诗歌。我也有些年头没去巴黎了,物价太贵了!
《巴黎评论》: 之前你提到要去北黑文一段时间。这是“工作假期”吗?
毕肖普: 今年夏天我想大干一场,因为真的很久没有做任何事了,我要在见上帝前完成几样事情:两三首诗和两三个长故事。这个地方是我在《哈佛深红报》的广告栏里偶然发现的,有时候我觉得不应该老是去这里,也许我应该多看看艺术品、大教堂,等等。但我太喜欢北黑文了,总忍不住要去。从屋里就能看到水,一大片水和土地。小岛都很美。有些岛径直在眼前,先看到花岗岩,然后是阴郁的冷杉丛。北黑文不是这样,但也非常美。岛上人烟稀少,在那里有房产的很多业主都富得吓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这岛可能就像许多缅因州的小岛那样被抛弃了,村子实在太小了。不过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有工作,他们是捕龙虾的渔民,也当看守员……那里的电力不算发达。两年前的夏天是一小时有电,一小时没电。我有两台电动打字机,根本没法连续工作。杂货店里有一幅漫画,画中一个男人在五金店里说:“我要一根十八英里长的延长线!”(岛上跟大陆相距十八英里。)去年他们终于跟大陆连上了,安装了电缆。但偶尔还是会停电。
《巴黎评论》: 所以你在打字机上写作?
毕肖普: 我可以在打字机上写散文,写诗不行。因为没人能看懂我的字迹,所以我用打字机写信。我终于训练自己能在打字机上写散文,然后再大幅修改。但写诗我得用笔。写到一半时,有时我会打几行出来看看怎么样。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完全用打字机写作。罗伯特·洛厄尔就是直接发表——他从来没学会写作。他发表所有东西。
《巴黎评论》: 你从来没有像一些同龄作家那样多产。是不是很多诗只有开头,能完成的很少?
毕肖普: 是啊,唉,的确如此。很多东西我写了开头以后就放弃了。过去几年里因为教课我没写什么。现在我空下来了,又拿了古根海姆奖的奖金,希望能够多写点。
《巴黎评论》: 你写《麋鹿》(1972)花了多久?
毕肖普: 很有趣。很多很多年前我就动笔了——起码二十年前,我有一大堆笔记,前两三节和最后一节。
《巴黎评论》: 这首诗太梦幻了。它进行的方式就像巴士前进。
毕肖普: 的确。巴士之旅是在我去巴西之前,我去看一个阿姨。实际上我乘错了车。目的地是对的,但我上错了快线车。它绕了路,正如我在诗里写的,只有“七个亲戚”不是真的,他们不是真的亲戚,而是几个继子继女。我想写完这首诗是因为喜欢,但中间部分一直写不出来,就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那部分。然后我住在麻省剑桥时,有人邀请我去哈佛给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写首诗。我挺高兴的,想起来还有一首没写完的诗,是关于鲸鱼的,也是很久很久以前写的。我怕我是永远不会发表这诗了,因为现在鲸鱼成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发表这诗好像显得我特别要求与时俱进似的。
《巴黎评论》: 那首诗现在写完了吗?
毕肖普:
我感觉写完应该不难,我打算把它带去缅因州。我得给它加个日期,不然没人会相信这诗早就开始写了。不过当时我没找到鲸鱼诗(那大概是一九七三或一九七四年),于是我把《麋鹿》挖了出来,心想也许我可以先完成这首。优秀生庆典那天(我在大学里可从来没当过优等生),我们都坐在桑德斯剧院的讲台上。请我写诗的人隔着校长探身过来小声问:“你的诗叫什么?”我说:“麋鹿,M-o-o-s-e
 。”然后他起身介绍我,说:“毕肖普女士现在会朗诵一首诗,题为Moos
。”然后他起身介绍我,说:“毕肖普女士现在会朗诵一首诗,题为Moos
 。”我一时语塞,而且我的帽子也太大了。后来报纸上说“毕肖普女士朗诵了一首诗《麋鹿》,她的学士帽上的流苏在她脸上前后晃荡,好像挡风玻璃上的雨刷”!
。”我一时语塞,而且我的帽子也太大了。后来报纸上说“毕肖普女士朗诵了一首诗《麋鹿》,她的学士帽上的流苏在她脸上前后晃荡,好像挡风玻璃上的雨刷”!
在我之后是合唱团表演,他们唱得可糟了,我这么觉得,大家也这么觉得。一个没能来现场的哈佛朋友认识几个合唱团里的男生,他后来问了其中一位:“演出怎么样?”“噢,马马虎虎,唱得不算好。”这是实话——接着他说:“一位女士朗诵了一首诗。”我朋友问:“读得怎么样?”他说:“就诗论诗,相当不错!”
《巴黎评论》: 你有没有碰到过天赐之诗?就是那种好像自动流淌出来一样?
毕肖普:
是,偶尔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一直想写一首维拉内拉诗
 ,但总写不出来。每次开个头,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写完。直到有一天,真没法相信,就像写信一样写了一首。
,但总写不出来。每次开个头,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写完。直到有一天,真没法相信,就像写信一样写了一首。
 有一个押e-n-t的韵我想不出,这时候正好诗人朋友弗兰克·比达尔来看我,我说:“弗兰克,给我一个押韵字。”他随口说了一个,我就放进去了。不过我俩都想不起来是哪个字了。可惜这种好事很难碰到。也许有些诗人一直那样写,我不知道。
有一个押e-n-t的韵我想不出,这时候正好诗人朋友弗兰克·比达尔来看我,我说:“弗兰克,给我一个押韵字。”他随口说了一个,我就放进去了。不过我俩都想不起来是哪个字了。可惜这种好事很难碰到。也许有些诗人一直那样写,我不知道。
《巴黎评论》: 你是不是经常给玛丽安·摩尔提供押韵字?
毕肖普: 是啊,她翻译拉封丹那会儿。我一回纽约(那会儿我大部分时间在巴西)她就会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一个押韵字。她说她很迷恋押韵和用韵结构。有时候很难分辨她是不是在开你的玩笑,她那凯尔特血统让她对这些东西神叨叨的。
《巴黎评论》: 评论家经常说你晚近的诗歌不那么形式化,更“开放了”。他们说《地理三》中有更多的“你”,情绪范围更宽阔。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毕肖普: 评论家说他们要说的。无论是我多么想写的东西,我从来没写过会让自己毕生仰慕的东西。也许没有人能写。评论家总爱作惊人语!
《巴黎评论》: 我正在读安妮·史蒂文森关于你的评论专著。她说在你的诗里自然是中立的。
毕肖普: 是,我记得中立这个词。只不过不太明白她要表达什么意思。
《巴黎评论》: 我觉得她的意思是,如果自然是中立的,就不存在任何引导性的精神或力量。
毕肖普: 有个名人,我想不起来是谁了,反正特别有名,有人问他如果他可以问斯芬克斯一个问题并得到答案,他会问什么?他说:“自然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但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喜欢乡下,特别是海岸,如果我能开车,可能就会住在乡下。很不幸,我买过至少两辆车,但从来没学会开。在巴西我有一辆名爵,很喜欢。我们住在山顶上,要开一个小时才能找到地方练习,再说也没有人能经常挤出一个下午来教我开车。所以我没考过驾照。不过话说回来,我肯定不会在里约开车的。反正你不会开车,就没法住在乡下。
《巴黎评论》: 你这儿有你叔叔的画吗?你在《诗》(1972)里写过的“一张老款美元大小”的画?
毕肖普:
当然,你想看看吗?太小了没法挂墙上。他是我的外叔祖
 ,我从来没见过他。
,我从来没见过他。
《巴黎评论》: 这画里的牛真的只用了一两笔!
毕肖普: 我夸张了一些些,诗里的一处细节画里并没有,我现在记不起来是哪处了。我的外叔祖在他十四五岁时还画了一幅画,我在一首较早的诗《糟糕的大画》(1946)里写过。有两幅画曾经挂在蒙特利尔的一个姨妈家的前厅,我可想要了,去过一次想买下来,但是她不肯卖给我。她相当抠门。几年前她去世了,那幅大画现在不知道归谁了。
《巴黎评论》:
刚才你带我看书房时,我注意到客厅里挂着一个小橱窗,是约瑟夫·柯内尔
 的作品吗?
的作品吗?
毕肖普: 是我的小型作品之一,讲的是巴西的婴儿死,那个作品叫Anjinhos,意思是“小天使”——巴西人这么叫早夭的婴儿或儿童。
《巴黎评论》: 那些个物件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毕肖普: 一个圣诞节我在里约东边的海滩上发现了小孩的凉鞋,最后决定用它创作。安抚奶嘴本来是大红色的橡胶,巴西人在药店里整瓶整罐卖这种奶嘴。我决定它不该是红色的,就用墨汁把它染成了黑色。我在染色的时候,一个巴西朋友的侄子来看我,非常聪明的年轻人。他带了两个美国摇滚乐手一起来,我们聊啊聊啊聊,但整个过程里我都没有想到要解释一下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走后我才想到,天哪,他们肯定以为我是个女巫或者什么!
《巴黎评论》: 那些装着米的小碗和煮锅呢?
毕肖普: 噢,就是小孩的玩具。当然米和黑豆是巴西人的日常粮食。
柯内尔非常棒。我第一次看到“美第奇自动售货机”是在大学里,噢太爱了。想想如果那时候就能买到那些东西呢。他是个怪人,暗恋唱歌剧的和跳芭蕾的。两年前我在纽约看他的展览时差点晕过去,因为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他也喜欢的而且他将它用在了展览里。那是一个英国科学家为孩子写的讲肥皂泡的小书——《肥皂泡:它们的色彩和塑造它们的力量》,C.V.鲍伊斯爵士一八八九年写的。
柯内尔的妹妹在读过我翻译的奥克塔维奥·帕斯
 为柯内尔写的诗后开始给我写信。(她不懂西班牙语。)她寄给我一本德—法语法书,明显是柯内尔想用来创作最后却没有实现的。许多书页被折成星的形状,周围有红色墨水……他住在一个叫仙境公园的地方。那地址可真够奇怪的。
为柯内尔写的诗后开始给我写信。(她不懂西班牙语。)她寄给我一本德—法语法书,明显是柯内尔想用来创作最后却没有实现的。许多书页被折成星的形状,周围有红色墨水……他住在一个叫仙境公园的地方。那地址可真够奇怪的。
《巴黎评论》: 之前你一直是少数几个不靠教书或朗诵活动为生的美国诗人中的一个,是什么让你决定开始做这两件事?
毕肖普: 我从来不想教书。最后决定教书是因为我想离开巴西,需要钱。从一九七〇年起就有人开始给我寄诗,他们只要知道你在哪儿就会给你寄。以前在巴西我也会收到一些,但不算多。寄信很容易丢。我根本不信写诗能教会,但这就是他们希望你做的。每周读那么多诗,你会失去判断力。
至于朗诵,一九四七年我的处女作出版后两个月,我在威尔斯利学院搞了一次朗读。之前几天我都在生病。噢,太荒唐了。一九四九年我在华盛顿又朗读了一次,结果又生病了,没人能听见我在读什么。之后二十六年我都没有公开朗读过。现在我好像克服了害羞,又可以朗读了。大概教书有帮助,我注意到老师都不害羞,他们相当好强。最后总会变成那样的。
《巴黎评论》: 你读书的时候上过写作课吗?
毕肖普: 我在瓦萨读书的时候上过十六到十八世纪的文学课程,然后是小说课。这类课你得读很多东西。我完全不相信写作是可以教授的。我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创意写作课,只有晚上有诗歌写作课,但不算学分。有几个朋友去上过,我没有。
“创意”这个词能把我逼疯。我不想把它看成治疗。几年前我住院,有人给了我一本肯尼斯·科赫
 的《玫瑰啊,你的红色哪里来?》。的确有时候孩子能写出美妙的东西,画美妙的画,但我觉得他们不该被鼓励。就我的所见所闻,英语系学生选修文学课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同时想上写作课的人却越来越多。哈佛每年有两到三门写作课。我的课一般只有十到十二个位置,却能收到四十份申请,有时五十份。越来越多。我不明白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补偿平时考虑实际问题太多,还是别的什么。
的《玫瑰啊,你的红色哪里来?》。的确有时候孩子能写出美妙的东西,画美妙的画,但我觉得他们不该被鼓励。就我的所见所闻,英语系学生选修文学课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同时想上写作课的人却越来越多。哈佛每年有两到三门写作课。我的课一般只有十到十二个位置,却能收到四十份申请,有时五十份。越来越多。我不明白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补偿平时考虑实际问题太多,还是别的什么。
《巴黎评论》: 我想他们肯定希望能说自己会捏陶器或是写诗这些有创意的事情。
毕肖普: 三月份我刚参加北卡罗来纳州和阿肯色州的朗读会回来,我发誓要是我再看到手工艺品肯定会发疯!我觉得我们应该直接回到机器,人一辈子能用几根皮带呀。抱歉啊,说不定你也做手工。
《巴黎评论》: 有很多陌生人给你寄诗吗?
毕肖普: 是啊,很难办。有时候我会回信。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粉丝信,写得很好。从笔迹看是小孩子的,他叫吉米·斯帕克斯,六年级。他说班级正在编一本诗歌小册子,他很喜欢我的诗(他提到了三首),因为它们是押韵的,而且写的是自然。他的信如此可爱,我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我想他应该是想让我寄给他一首手写的诗或是照片什么的(学校都这样要求),但他没有提类似的要求,肯定是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巴黎评论》: 他喜欢哪三首呀?有《鹬》(1962)吗?
毕肖普: 有,还有关于镜子和月亮的《失眠》(1951),玛丽安·摩尔说是一首廉价的爱情诗。
《巴黎评论》: 结尾是“……你爱我吗?”那首?
毕肖普:
是,我一点都不喜欢那结尾,差点就没用。但去年艾利奥特·卡特为它和我的另外五首诗
 谱了曲,它作为歌词听上去好多了。玛丽安·摩尔可讨厌它了。
谱了曲,它作为歌词听上去好多了。玛丽安·摩尔可讨厌它了。
《巴黎评论》: 她大概不喜欢最后那句。
毕肖普: 她向来不爱谈论情感。
《巴黎评论》: 回到教书,你在哈佛教课的时候会布置作业吗?比如,让学生写一首维拉内拉诗?
毕肖普: 每周我都给全班发一整张要交的作业清单;但每隔两三周会安排一次自由作业,他们想交什么都可以。有些班级的学生太能写了,我得宣布暂停交作业才行。我会说:“拜托,你们两周不许写诗!”
《巴黎评论》: 你觉得可以说初学者写规定格式的诗比写自由体好吗?
毕肖普: 不好说。我教过一次六节诗,让学生随机选词,很快我就后悔了,因为它居然在哈佛风靡一时。后来想选我课的人老是写六节诗,他们好像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诗体——其实并不是。
《巴黎评论》: 我以前写过一首六节诗,讲一个整天看肥皂剧的女人。
毕肖普: 你上大学的时候看肥皂剧吗?
《巴黎评论》: 不看。
毕肖普: 好像在哈佛还挺流行的。两三年前我教一门散文课,发现学生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看肥皂剧。于是我也看了两三集,想知道到底有什么好看。可无聊了。还插播广告!一个学生写了一个短篇,讲一个老头请了一个老太来家里吃饭(她其实是个鬼魂),他在做准备工作时,把盘子擦得亮到可以照见自己的脸。这学生写得还不错,我在课堂上朗读了一部分,然后说:“不过,这里不可能,你不可能在盘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全班同学一齐说:“易洁!”我说:“什么?你们在说什么?”原来有个易洁洗洁精的广告就是主妇拿着盘子可以照见脸——你知道那个广告吗?即便如此,还是不可能!我觉得这很烦人。电视里放的就是真的,没人注意到不真实的地方。这就好比以前人认为亚里士多德说的都是对的,几百年都没人指出来,女人的牙齿不比男人少。
我住在巴西的时候,有个朋友给了我一台黑白小电视机。我们几乎立刻就送给了女佣,因为我们只看政治演讲或是那些革命大事。但她可喜欢了。她和电视机一起睡觉!电视对她那么重要,因为她不识字。那年放了一个肥皂剧叫《生命的权利》,播出时间是晚八点到九点,简直改变了整个里约社会的时间表。平时晚饭时间是八点,所以你要么提早吃饭,这样女佣可以看《生命的权利》,或是等那剧结束以后再吃饭。我们最后把晚饭改到了十点,就为了让乔安娜可以看那玩意儿。最后我决定我也要看。它成了时髦,人人都在谈。可是太可怕了!他们从墨西哥买了版权,配上葡萄牙语。整个剧极为粗糙,怎么狗血怎么来——棺材里的尸体、奇迹、修女,甚至还有乱伦。
我有个朋友住在贝洛哈里桑塔,每天晚上他妈妈、家里的厨娘和一个孙辈一起看肥皂剧,他们称之为“中篇小说”。厨娘会激动地对着屏幕说:“不!不!某某夫人,别这样做!你知道他是个坏人!”他们太过激动的时候还会哭。我还认识两个老姐妹,她们有一台电视。她们会一边织毛线一边看一边哭,其中一个会站起来说对着电视机说:“对不起,我要去卫生间了!”
《巴黎评论》: 一九五六年你得普利策奖的时候就住在巴西对吧?
毕肖普: 是的,当时挺搞笑的。我们住在山顶上,真的很高。当时家里只有我和厨娘玛丽亚,朋友去集市了。电话响了。是美国使馆的新闻官,他用英语问我是谁,当然听到有人说英语是很稀罕的。他说:“您知道您得了普利策奖吗?”噢我以为是开玩笑。我说:“噢,得了吧。”他说:“您没听见我说的吗?”电话线路不太好,他在那头尖叫。我说:“噢,不可能吧。”但他说不是开玩笑。我没法让玛丽亚对这消息感到振奋,但我觉得必须和谁分享一下,于是急急跑下山,跑到半英里远的邻居家,结果没人。我觉得应该庆祝一下,喝杯红酒什么的。但我能在邻居家找到的就是些美国饼干,糟糕的巧克力饼干——好像是奥利奥,于是我吃了两块饼干。这就是我怎么庆祝得普利策奖的。
第二天下午的报纸上有一张照片——巴西人对这些事可认真了。再过了一天我的巴西朋友又去集市了,那个集市有个大棚罩着,小摊位上什么吃的都有,我们一直去一个摊位买蔬菜。摊主问我朋友:“昨天的报纸上是不是有伊丽莎白女士的照片?”她回答:“是的,她得了奖。”摊主说:“太奇妙了!上周某某夫人参加自行车比赛也赢了呢!我的顾客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很棒?!
《巴黎评论》: 我还想问问你的短篇,特别是《在村子里》(1953),我很喜欢。你的短篇和诗歌有没有关联,除了共同的主题之外?比如说,“攻击方式”?
毕肖普: 它们联系紧密。我怀疑我写的有些短篇实际上是散文诗,而不算很好的故事。我写了四篇关于新斯科舍的短篇。一篇去年发表在《南方评论》上。还有一篇比较长的正在写,希望今年夏天可以完成……《在村子里》很有趣。我已经做了不少笔记,有时我会犯很严重的哮喘,医生给了我很多可的松,这会让你睡不着觉。药效上来的时候感觉很好,但之后就很糟糕。我没法睡觉,只能整晚醒着忍受酷热。那个短篇大概有可的松的功劳,还有我半夜喝的金汤力。两晚上就写完了。
《巴黎评论》: 难以置信!那可是很长很长的短篇了。
毕肖普: 很特别,我希望可以再来一遍,但我再也没有碰过可的松,我尽可能避免用它。
《巴黎评论》: 我一直对不同的诗人如何写他们的童年很感兴趣。
毕肖普: 每个人都会写,我想这无法避免。小时候的你观察力敏锐极了,你会注意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没有办法把它们串起来。我对幼年的记忆要比后来的记忆(比如一九五〇年发生的事)清晰多了。但我不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把写童年搞成一种崇拜,我一直试图避免这样。但必须说,我发现自己的确写过一些。四十年代我断断续续看过精神分析师,她对作家和黑人尤其感兴趣。她说我能记得两岁时发生的事实在很惊人。这的确很少见,但作家好像经常能记得。
《巴黎评论》: 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毕肖普: 我想应该是学走路。我妈妈不在,外婆试着鼓励我走路。那是在加拿大,她在窗边放了许多植物,那时候女人都这样。我记得模糊的植物,还有外婆伸出手臂。我肯定走得东倒西歪。在我看来这就是记忆,一切都很朦胧。很多年后我跟外婆说了,她说:“是的,你是在你妈出门的时候学会了走路。”小孩学走路是在一岁时,不是吗?
我记得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妈带我去乘天鹅船。那时候我大概三岁。那是在我们回加拿大之前。妈妈穿着一身黑,那时候只有寡妇才这么穿。她有一盒混合坚果和葡萄干。天鹅在我们周围游来游去(我想现在已经没有天鹅了)。一只天鹅游过来,她喂了它,它咬了她的手指。也许她只是告诉了我这些,但我相信是真的,因为她一边给我看黑色羊皮手套一边说:“看。”手指处是裂了。我兴奋得差点死了!罗伯特·洛厄尔把这些天鹅船写进了两三首诗里,收在《威利爵爷的城堡》里。
《巴黎评论》: 你在童年经历过种种困难,但你的许多写童年的短篇和诗歌都极为抒情,同时也很有失落感和悲剧感。
毕肖普: 父亲去世后,在我四五岁时,我妈妈疯了。亲戚们大概都觉得我很可怜,所以他们尽力帮忙。我觉得他们的确帮了很多。我和外祖父母住在新斯科舍,后来跟麻省的伍斯特市的亲戚住过一小段时间,生了很重的病。那时我大概六七岁。再后来我跟母亲的姐姐住在波士顿。夏天我总是去新斯科舍过。十二三岁时我已经有足够的自理能力,可以去韦尔弗利特参加夏令营了,一直到十五六岁去上学。大姨对我特别尽心,人好得不得了。她结婚了但没有小孩。我和家里亲戚的关系——感觉我一直是客人,至少我自己觉得是。
《巴黎评论》: 你的青春期平静些了吗?
毕肖普: 我以前非常浪漫。我曾经从科德角打弯处的瑙塞特灯塔(现在大概没有了)一直走到尖部的普罗温斯敦,要走上整整一天一夜。我时不时去游泳,但那时的海滩很荒芜,后滨滩上什么也没有,没有房子。
《巴黎评论》: 那时候你多大年纪?
毕肖普: 十七八岁。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回去过——因为我无法忍受去想它现在的样子……我再也没有回过楠塔基特岛——自从——唉,真不想说。大四那年我和当时的男友去那里过圣诞,没人知道我们去了那儿。一次美妙又浪漫的旅行。我们在圣诞节后去那里待了大概一周。当时很冷但也很美,我们在荒野里一走就可以走很久。我们住的小旅馆很舒适,以为房东太太会把我们赶出来(当时像我们这么年轻的情侣同住还不太常见)。我们喝了一瓶雪利酒,或是别的什么无害饮料。新年前夜大概十点钟有人敲门。是房东太太用餐盘端来了一瓶格罗格烈酒!她进来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她认识管博物馆的人,还特意为我们开了门。那里有几家不错的博物馆。
《巴黎评论》: 我听说你在瓦萨上学时有一次在宿舍外的树上待了一晚上,是真的吗?
毕肖普: 是啊,我和一个朋友,不过名字不记得了。我们真的很疯,爬树也真的爽。我以前爬树很厉害。噢,我们大概凌晨三点才下来。这事是怎么传开的?我可不知道!后来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实际上因为她请了两个西点军校的男生来过周末,她尽找些最傻的男生[她还用手在空气里画披肩和制服——采访者注]!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快发疯了。那时我大概就开始不理她了……我住在宿舍顶层的转角大房间,因为注册得有点晚,于是被分到了一个不太理想的室友——怪女孩康丝坦斯。我还记得她那半边房间里有各种苏格兰狗的装饰——枕头、印刷品、雕刻、照片,我这半边空荡荡的。不过我大概也不算是好室友,因为当时我有个理论,一个人应该把所有梦境都记下来,这样才能写诗。所以我有一个记录梦的笔记本,觉得如果你睡前吃很多难吃的奶酪,就会做有趣的梦。我去瓦萨的时候带了这么大一个罐子(而且有盖子!)的洛克福羊奶酪,放在书架底部……那个年纪大概人人都有怪癖吧。听说奥登在牛津读书时枕头底下有一把左轮手枪。
《巴黎评论》: 你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作家吗?
毕肖普: 没有,一切都发生在不知不觉中。我从来没想过去巴西,也从来没想过任何现在会做的事。我生命中的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巴黎评论》: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毕肖普: 是有人事事计划,但我恐怕真的不是这样。
《巴黎评论》: 但你一直对写作有兴趣吧?
毕肖普: 我从小就写,但我进瓦萨时本来打算当作曲家。我在胡桃山学过音乐,有个特别好的老师。我学了一年对位法,还会弹钢琴。在瓦萨,每个月都要公开演出,我很怕,怕得要命。我就演了一次,然后就放弃弹琴了,因为实在受不了。现在我已经没事了,但也没法继续弹琴了。第二年我就转去英语系了。
我们班同学都很文艺。玛丽·麦卡锡比我早入学一年,埃莉诺·克拉克跟我同班,穆里尔·鲁凯泽大一时也在班上。我们创办了一份刊物,你可能听说过,《精神抖擞》 [1] 。我大概三年级,我们有六七个人——玛丽、埃莉诺和她姐姐、我朋友玛格丽特·米勒、弗拉尼·布劳和其他人。那时候有禁酒令,我们会去市中心的非法经营的酒吧,用茶杯喝酒。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恶行了,糟透了!我们大多数都给《瓦萨评论》投过稿,全被拒了。当时的杂志还很老派。我们很生气,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写得挺好。于是我们想,干脆自己办份杂志。我们觉得匿名是个好主意,就都匿名了。等出到第三期时,《瓦萨评论》找上门来,我们的几个编辑成了它的编辑,然后它就开始发表我们的东西了。办杂志的时候我们过得挺开心。
《巴黎评论》: 我在别的一个访谈中读到过你毕业后被康奈尔的医学院录取,准备去那儿深造。
毕肖普: 我好像拿了所有的申请表,那是在我从瓦萨毕业一年后。但后来我发现得学德语,之前我已经放弃过一次德语了,实在太难了。而且我还得再学一年化学。当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玛丽安劝我别去,我就没去。我去了欧洲。
《巴黎评论》: 大萧条对三十年代的大学生有影响吗?
毕肖普: 所有人都疯了一样找工作。所有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除了我。我一直挺另类的,就去研究T.S.艾略特和英国国教。但当时的精神氛围很激进。有意思的是,比我大一级的一个最激进的女孩跟《时代周刊》的一个头头结婚多年,他的名字我忘了。他很有名,是最保守的那种人,他写的社论都很吓人。我现在还记得她站在图书馆外面,拿着一个铃鼓为这样那样的事业募捐。
《巴黎评论》: 你想过当作曲家、医生、作家——这些兴趣的比例如何?
毕肖普: 噢,我对它们都很感兴趣。我其实最想当的是画家。我从来没有坐下来对自己说,我要当一个诗人。从来没有。至今我对人们认为我是诗人还不太习惯……我大四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我记得收到的第一张支票是三十五美元,那一刻可激动了。发稿费的好像叫《杂志》,加州出版的。他们发表了一首诗,一个短篇——噢,我希望那些诗从未发表!它们太差了!但我把支票给室友看了。我还上了校报《杂录新闻》,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上的,总之很神秘。他们经常坐在报纸的编辑室里讨论怎么才能发表,诸如此类,我只能忍住不说话,觉得很尴尬。我现在仍是这样。没什么比当诗人更尴尬的了,真的。
《巴黎评论》: 特别是第一次见人时得向别人解释你的工作。
毕肖普: 就上周,我和一个朋友去拜访一个我在魁北克认识的女士。她七十四还是七十五岁了。她没对我但对我的朋友爱丽丝说:“我本来想请隔壁大宅的邻居来吃晚饭,她人很好,但她肯定会问伊丽莎白是干什么的,如果伊丽莎白说她写诗为生,那可怜的女人肯定整晚上没有一句话!”这真很糟,我觉得不管你自己觉得多谦卑或是多渺小,你心里一定有一块自大的核心,能让你去写诗。我从未感受过它,但它一定在那儿。
《巴黎评论》: 在你给我的信里,听上去对采访者比较审慎。你怕在采访中被误解吗?比如说,你拒绝出现在全女性的诗选中会被误读为一种对女权运动的反对?
毕肖普: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最近我接受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记者的采访,我跟那姑娘谈了几分钟后,发现她想把我塑造成一个“老古董”,作为埃丽卡·容、艾德丽安·里奇(我挺喜欢她)和其他激烈的女权主义者的对立面。这完全不是真的。最后我问她到底读过我的诗没有,好像她只读过一首。我不懂她怎么能来采访,如果她对我一无所知的话,而且我这么对她说了。她还算好,在《芝加哥论坛报》对其他几位的长篇报道之外单独发了一篇文章。我说我不相信诗歌能成为宣传工具,那很少成功过。她写在报上就成了“毕肖普女士不相信诗歌能够传达诗人的个人哲学”。这让我听上去像个彻底的蠢人!她从哪儿听来的,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为什么对采访很紧张。
《巴黎评论》: 通常来说你会同意选集编纂者的选择吗?你最喜欢哪些诗?有没有你觉得应该收入诗选但没有被选的诗?
毕肖普: 除了《鱼》(1946)什么都好!我暂停了那首诗的重版。编诗选的人总是互相重复,几年前我终于觉得烦透了,说任何人不许重印《鱼》,除非他们重印其他三首诗。
《巴黎评论》:
还有一两个问题。你在事业早期去过雅斗
 好几次。你觉得艺术家聚集地的氛围对写作有帮助吗?
好几次。你觉得艺术家聚集地的氛围对写作有帮助吗?
毕肖普:
我去过雅斗两次,一次是夏天,住了两周,还有一次是我去巴西之前的冬天,住了好几个月。埃姆斯夫人
 很出风头。我不太喜欢夏天去因为不断有人来来去去,冬天就很不一样。当时只有我们六个人,很巧我们都互相喜欢,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在那期间我好像写了一首诗。也是在那儿,我第一次喜欢上赛马。夏天你可以走到惠特尼庄园去看赛道,现在应该还可以看。我和一个朋友以前大清早走去那儿,坐在赛道边,喝咖啡吃蓝莓麦芬,看他们训练马儿。我可喜欢看了。八月份我们还去看周岁马买卖,都很美。集市在一个大帐篷里,马夫用黄铜簸箕和黄铜手柄的刷子,跟着小马驹扫它们的粑粑。这是我对雅斗最美好的记忆了。
很出风头。我不太喜欢夏天去因为不断有人来来去去,冬天就很不一样。当时只有我们六个人,很巧我们都互相喜欢,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在那期间我好像写了一首诗。也是在那儿,我第一次喜欢上赛马。夏天你可以走到惠特尼庄园去看赛道,现在应该还可以看。我和一个朋友以前大清早走去那儿,坐在赛道边,喝咖啡吃蓝莓麦芬,看他们训练马儿。我可喜欢看了。八月份我们还去看周岁马买卖,都很美。集市在一个大帐篷里,马夫用黄铜簸箕和黄铜手柄的刷子,跟着小马驹扫它们的粑粑。这是我对雅斗最美好的记忆了。
《巴黎评论》: 你去雅斗那段时间也在国会图书馆当诗歌咨询馆员,对吗?在华盛顿的那一年要比在雅斗更富有成效吗?
毕肖普: 我有点受罪,因为我这辈子都很害羞。可能几年之后我会稍微好一些,但当时真的不喜欢。我恨华盛顿特区。到处都是政府大楼,看着像莫斯科一样。图书馆有个人很好的秘书叫菲利丝·阿姆斯特朗,帮我渡过了难关。她承担了大部分工作。我写点什么,她会说“噢噢还不够正式”,然后就帮我改成官样文章。我们还赌马,菲利丝总是投每日二重彩。我俩会坐在办公室里看《赛马新闻报》,诗人们来咨询时,我和菲利丝肯定在谈赌注!
干过那份工作的“幸存者”(许多已经过世了)最近被邀请去朗读,很不巧去了十三个人。
《巴黎评论》: 我一个朋友想去听,结果她说堵得水泄不通。
毕肖普: 人山人海!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不可能有比这更无趣糟糕的活动了啊。我们每个人不能超过十分钟,我按时读完了。但碰到詹姆斯·迪基这样的人可不能叫他停。斯塔福德很好,我从来没见过他本人。他读了一首很短的诗,真正让我热泪盈眶,他读得太好了。
我不很喜欢读诗会,我更喜欢读书会。我知道我可能错了,但只有很少几次诗歌朗诵会让我还能忍受。当然你还太年轻,没有见识过那阵迪伦·托马斯狂热……
如果是洛厄尔或者玛丽安·摩尔的朗读会,那简直就像我亲生的孩子一样。我会太动感情。我去过几次玛丽安的朗读会,最后实在没法再去了,因为我坐在那里就不停地掉眼泪。真挺尴尬的。你总在担心他们会出岔子。
洛厄尔认为读诗会最重要的是诗人在朗诵一首诗之后的点评。我第一次听他读诗是很多年前在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的一个狭小灰暗的礼堂里。他和艾伦·泰特、露易丝·博根一起。洛厄尔比其他人小很多,当时只出版过两本诗集。他读了一首长得无边无际的诗(题目我忘了)
 ,关于一个加拿大修女在新布伦瑞克省的事。我也忘了那诗的主旨是什么,但真的很长很长,写得很美,特别是开头。他开始读,读得很糟糕。他在那儿哼哼唧唧,所有人都努力想听清楚。他读到三分之二处时,突然有人大喊“起火了”。还好火不算大,五分钟就被扑灭了,大家又回到座位上。可怜的洛厄尔说:“我最好还是重新开始吧。”于是他又从头开始读!不过他晚年读得好多了。
,关于一个加拿大修女在新布伦瑞克省的事。我也忘了那诗的主旨是什么,但真的很长很长,写得很美,特别是开头。他开始读,读得很糟糕。他在那儿哼哼唧唧,所有人都努力想听清楚。他读到三分之二处时,突然有人大喊“起火了”。还好火不算大,五分钟就被扑灭了,大家又回到座位上。可怜的洛厄尔说:“我最好还是重新开始吧。”于是他又从头开始读!不过他晚年读得好多了。
《巴黎评论》: 诗歌中心最近发布的他的录音棒极了,不可能更好了。而且很风趣。
毕肖普: 我还没有勇气去听。
(原载于《巴黎评论》第八十期,一九八一年夏季号)
[1] 此处提到刊物名是 Con Spiri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