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萨克·迪内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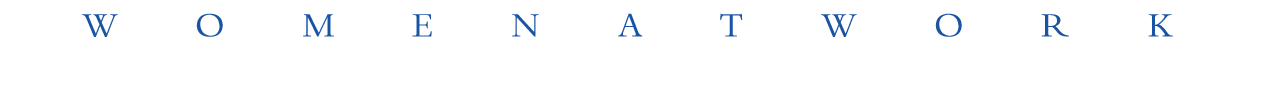
前些年,当嘉宝计划在大荧幕版本的《走出非洲》中出演伊萨克·迪内森本人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有点像本色出演,因为演员和原著作家一样,都是北欧的某种神秘造物。伊萨克·迪内森,原名卡伦·克里斯汀·布里克森—芬奈克,是如假包换的丹麦男爵夫人,她的父亲是威廉·迪内森,也是十九世纪经典作品《狩猎书简》一书的作者。布里克森男爵夫人在不同国家用不同的名字发表作品:通常是伊萨克·迪内森,有时候也会用塔尼娅·布里克森或卡伦·布里克森。老朋友们称呼她为塔纳、塔娅或塔尼娅。曾经还有一本令人愉悦的小说,有段时期她一直不承认那是自己写的,虽然所有读者一看就能猜出皮埃尔·安德切尔不过是男爵夫人的又一个化名。文学圈一直流传着各种传闻:她其实是个男作家;他其实是个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其实是个兄妹合用的名字;“伊萨克·迪内森”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去过美国,她其实是个巴黎人;他住在埃尔西诺
 ;她大部分时间待在伦敦;她是个修女;他非常好客,经常招待年轻作家;她很少露面,基本隐居起来了;她用法文写作;不,英文;不,丹麦文;她实际上……这样的传言从未终止。
;她大部分时间待在伦敦;她是个修女;他非常好客,经常招待年轻作家;她很少露面,基本隐居起来了;她用法文写作;不,英文;不,丹麦文;她实际上……这样的传言从未终止。
一九三四年,哈斯与史密斯出版公司(后被兰登书屋收购)推出了《七个哥特式故事》,哈斯先生读过一遍就决定出版它。这本书一夜成名,成为很多作家和画家的心头挚爱,这本新书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经典来对待的。
在现代文学正典之外——就像一只黄鹂在一笼子蜕毛的红雀外面——伊萨克·迪内森为她的读者提供了聆听故事时永无止境的满足感:“后来怎么样了?……好,那么……”她身上那种说故事的本能,或者说民谣诗人的本能,和她那种细腻而清晰的个人风格相得益彰,以至于海明威在接受诺贝尔奖颁奖时抗议道,这一荣誉早应归于迪内森。
——尤金·沃尔特,一九五六年

罗马,初夏,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对话发生在一个人行道边的餐厅内,在纳沃纳广场,这个长条形的广场经历过洪水,也曾上演过激烈的模拟海战。暮色沉沉,天空是一片鸢尾花般的蓝紫色;伫立在贝里尼雕塑中间的方尖碑看起来苍白且轻盈。在咖啡馆的桌边,坐着布里克森男爵夫人、她的秘书兼旅行伴侣克拉拉·斯文森,还有采访者。男爵夫人就像从她自己的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苗条,直接,风趣。她穿着一身黑,黑色的长手套,一顶黑色的巴黎款式的帽子,帽子的顶端到底部颜色渐深,在她漂亮的眼睛上投下阴影,眼底深深浅浅地闪着光。她的脸瘦长而醒目,嘴角和眼边漾着浅浅的笑意,表情瞬息万变。她的声音悦耳轻柔,却有一种力量和音色让人立即感受到,这位夫人既有着深刻见解,又不乏绮丽魅力。她的同伴斯文森小姐,是位面带稚气却有着迷人笑容的年轻人。
伊萨克·迪内森: 采访?哦天哪……好吧,我希望……别是一长列的问题或者残酷的逼供吧,我希望……前不久刚做过一次采访……太可怕了……
斯文森小姐: 是,有个男人要拍部纪录片……那次有点像在做教义问答……
迪内森: 要不我们就一起随便聊聊,然后你写下喜欢的部分?
《巴黎评论》: 好啊,你可以划掉一些,再补充点什么。
迪内森: 好的,我不应该答应太多的采访。我已经病了一年多,一直住在疗养院里。我真觉得我会死。死亡在我的计划之中,我做好了准备,我等着它。
斯文森小姐: 哥本哈根的医生告诉我:“塔尼娅·布里克森很聪明,但她做得最聪明的事就是挺过了两次手术。”
迪内森: 我甚至计划了最后一次电台谈话……我在丹麦时做过很多次电台谈话,关于各种主题……他们很乐于邀请我担任电台嘉宾……我策划过一次关于死是如何容易的谈话……这不是一种病态的想法,我的意思是,这个观点其实能令人感到安慰和振奋……死是一种绝妙的、可爱的经历。但我病得太厉害了,没能完成这个对话。在疗养院里待这么久、病得这么严重,我甚至几乎感觉不到这条命还属于自己。我就像一只徘徊萦绕于此的海鸥。我觉得世界是如此奇妙、快乐,一息不停,而我已不是它的一部分了。我来罗马就是为了试着再次进入世界。啊,快看那天空!
《巴黎评论》: 你对罗马熟悉吗?上次来是什么时候?
迪内森:
好多年前了,那次是来觐见教宗。我第一次来罗马是一九一二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和我表姐,还有我最好的朋友,她嫁给了丹麦驻罗马的大使。那时我们每天在博尔盖塞别墅
 里骑车,路上马车来往,车上坐着当时那些快活的美女,时而停下来聊天。太舒服了!看看现在,汽车和摩托车,刺耳的喧嚣,人们行色匆匆。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想要的,速度才是最重要的。而当我骑着我的马——我是个小女孩时一直有匹马——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丢失了一些珍贵的事物。我们那时的孩子活得很不一样,即使住大房子,你也没什么玩具。现代的机械玩具,自带动力,我们那时基本不存在。我们只有很简单的玩具,而且得自己琢磨怎么玩。我对提线木偶的喜爱就来源于此,我还试着自己动手写剧本。你当然也可以直接买一只木马,但我们更喜欢自己去树林里找来枝条,用绳子捆绑连接起来,用想象力把它变成布西法拉斯
里骑车,路上马车来往,车上坐着当时那些快活的美女,时而停下来聊天。太舒服了!看看现在,汽车和摩托车,刺耳的喧嚣,人们行色匆匆。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想要的,速度才是最重要的。而当我骑着我的马——我是个小女孩时一直有匹马——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丢失了一些珍贵的事物。我们那时的孩子活得很不一样,即使住大房子,你也没什么玩具。现代的机械玩具,自带动力,我们那时基本不存在。我们只有很简单的玩具,而且得自己琢磨怎么玩。我对提线木偶的喜爱就来源于此,我还试着自己动手写剧本。你当然也可以直接买一只木马,但我们更喜欢自己去树林里找来枝条,用绳子捆绑连接起来,用想象力把它变成布西法拉斯
 和珀伽索斯
和珀伽索斯
 。现在的小孩,从出生开始就满足于做个袖手旁观的人,而我们习惯做创造者。现在的年轻人不再熟悉材料,也很少使用,所有的东西都是机械的、城市化的,孩子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不亲近燃烧的火、鲜活的流水和土壤。年轻人想和过去一刀两断,他们憎恨过去,甚至不想听到过去的事。也能理解一部分原因。刚刚过去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段长长的战争史,他们没兴趣。这也许是一些事情的终结,一种文明的终结。
。现在的小孩,从出生开始就满足于做个袖手旁观的人,而我们习惯做创造者。现在的年轻人不再熟悉材料,也很少使用,所有的东西都是机械的、城市化的,孩子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不亲近燃烧的火、鲜活的流水和土壤。年轻人想和过去一刀两断,他们憎恨过去,甚至不想听到过去的事。也能理解一部分原因。刚刚过去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段长长的战争史,他们没兴趣。这也许是一些事情的终结,一种文明的终结。
《巴黎评论》: 但是厌恶会导向爱:他们也许转个圈还是会回到传统。我会觉得漠不关心更可怕。
迪内森: 也许吧。而我会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现在我爱上了爵士乐。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音乐领域里唯一的新事物。我不会说我喜爱它胜过古典音乐,但我的确迷醉其中。
《巴黎评论》: 你的很多作品看起来都属于上个世纪(十九世纪),比如《天使复仇者》(1944)。
迪内森: (大笑)那本小说是我庶出的孩子!德国占领丹麦时期,我无聊乏味得快疯了,想要自娱自乐,此外我也缺钱,所以我去见我在哥本哈根的出版商,对他说,你愿意预付一本小说的费用并且给我安排一个速记员吗?他们说好,速记员也来了,于是我开始口述。刚开始时,对于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完全没头绪。每天,我即兴地加上一点。那可怜的速记员一定觉得莫名其妙。
斯文森小姐: 对,她对商业信函更熟悉,当她从速记本上誊抄出故事时,她会用数字来标记,比如“2个惊吓的女孩”“他的1号爱情”。
迪内森: 我会这么来开始写一天,“×××先生走进房间”,速记员就会大叫,“哦亲爱的,他不行!昨天他在十七章里就死了。”啊不,我还是宁愿《天使复仇者》是我的秘密。
《巴黎评论》: 我喜欢,我记得有一些很棒的评论和书评。很多人都猜出来那是你写的吧?
迪内森: 有一些。
《巴黎评论》: 《冬天的故事》(1942)呢?它是在战时出版的,你是怎么把它弄到美国去的?
迪内森:
我去了斯德哥尔摩——这可不像说起来这么容易——而且更难的是,我还得随身带着手稿。我去了美国大使馆,问他们是否每天都有班机回美国,是否能把我的手稿带过去,但他们说他们只运送政治和外交文件,于是我又去了英国使馆,他们问我能否提供英国方面的介绍信,我可以(我在内阁有很多朋友,包括安东尼·艾登
 ),所以他们就发电报去确认这事,然后他们答复说可以,于是我的书稿就踏上了美国之旅。
),所以他们就发电报去确认这事,然后他们答复说可以,于是我的书稿就踏上了美国之旅。
《巴黎评论》: 美国大使馆太丢人了,他们肯定可以做到的。
迪内森:
哦,别太苛责他们。我欠美国公众太多了。随书稿我还给我的美国出版商附了一封信,说一切都靠他们了,因为当时我没法联系他们,关于《冬天的故事》的书稿他们是如何收到的,我也一无所知,直到战后,我突然收到数十封来自美国士兵和世界各地水手的可爱的信件:那本书被设计成部队特供版本
 ——小开本的书正好可以放入士兵的口袋。我十分感动。他们给了我两本,我把其中一本给了丹麦国王,他很高兴,毕竟在那个黑暗年代,他沉寂的王国还是对外发出了一些声音。
——小开本的书正好可以放入士兵的口袋。我十分感动。他们给了我两本,我把其中一本给了丹麦国王,他很高兴,毕竟在那个黑暗年代,他沉寂的王国还是对外发出了一些声音。
《巴黎评论》: 你刚才提到了美国公众?
迪内森: 是的,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对我毫不迟疑的接纳。从一九一四年开始我就待在非洲,当一九三一年我返回丹麦时,我花光了结婚时所有的积蓄,因为咖啡种植没赚到钱;我请大哥资助我用两年的时间来准备写《七个哥特式故事》,我告诉他,两年后我就能靠自己了。书稿完成后,我去了英国,某一天午餐时,出版商亨廷顿先生也在,我说:“我有本书稿,想请您看看。”他问:“是什么?”我说:“一本短篇小说集。”他挥手喊道:“不!”我近乎哀求:“您不先看看吗?”他说:“一个无名作者的短篇小说集?绝不可能!”后来,我把它送去美国,立刻就被罗伯特·哈斯先生接受并出版了,美国读者接纳并喜爱这本书,他们总是值得信赖的。不,谢谢,我不用咖啡了,我得来支烟。
《巴黎评论》: 出版商总是很愚蠢,作者的哀叹几乎是一种惯例了。
迪内森: 有趣的是,书在美国出版后,亨廷顿先生给罗伯特·哈斯先生写信一番褒奖,并希望能拿到作者的地址,说他一定要在英国出版这本书。哈斯先生和我之前从未见过彼此。于是,亨廷顿先生见到了作为“布里克森男爵夫人”的我,而哈斯先生却素未谋面。亨廷顿先生从未和作为“伊萨克·迪内森”的我联络过。后来,他的确在英国出版了我的这本书。
《巴黎评论》: 太有趣了,就像你书中的故事。
迪内森:
坐在这开阔的地方太舒服了,但我想我们得走了。我们可以周日接着聊吗?我会去朱莉亚别墅
 看伊特鲁里亚文物
看伊特鲁里亚文物
 ,也许到时可以再聊会儿。哦快看月亮!
,也许到时可以再聊会儿。哦快看月亮!
《巴黎评论》: 太好了!我来叫出租车。
有雨,暖暖的周日中午。因为天气原因,朱莉亚别墅的伊特鲁里亚文物展人不多。布里克森男爵夫人身着红棕色的羊毛套装,锥形的褐色草帽再次为她漂亮的眼睛打上阴影。当她在新近安放的伊特鲁里亚雕塑、陶器和珠宝中间漫步时,她看起来和那些画廊观众一样疏离,轻盈地穿越其间。她走得很慢,身子挺直,时不时停下来,流连忘返于那些打动她的细节。
迪内森: 他们怎么弄到这种蓝色的,你能猜得出来吗,青金石研磨成粉?看看那只猪!在北欧,猪在我们的神话中非常重要。它是太阳的宠仆。我猜想,在黑暗和寒冷的季节,它那胖胖的、可爱的外形能让我们觉得温暖。特别聪明的动物……我喜欢所有的动物。我在丹麦有一条大狗,一条德国牧羊犬;太庞大了。我会带它去散步。如果我活得比它久,我想我会再养一只小型犬——哈巴犬。但现在是不是不太容易弄到一只哈巴犬,它们太时髦了。快看那个石棺上的狮子。伊特鲁里亚人怎么会了解狮子的?这是我在非洲最喜欢的动物。
《巴黎评论》: 你一定知道非洲最好的部分,是什么让你决定去那儿的?
迪内森: 我还是个小女孩时,从来没有过去非洲的想法,我也无法想象一个非洲农场会让我待得十分舒服。这也证明了上帝比我们拥有更伟大的想象力。当我和表弟布洛·布里克森订婚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叔叔去非洲参加大型狩猎,回来后对那片土地赞不绝口。西奥多·罗斯福当时也去过那里打猎;东非也出现在新闻中,所以布洛和我决定去那里试试运气,两边的亲戚资助我们购买农场,在肯尼亚的高地,离内罗毕不远。到那里的第一天,我就爱上了那块土地,我感觉自在又快活,置身那些我不熟悉的花朵、树木、动物中间,还有恩贡山上不断变幻的云朵,和我之前见过的都不一样。东非那时真的是天堂,借用印第安人的说法,“快乐狩猎之地”。年轻时我特别着迷于打猎,但在非洲的那些年,我对非洲各地的部落更感兴趣,尤其是索马里族和马塞族。他们都是漂亮、高贵、无畏且聪慧的人。经营咖啡种植园并不容易。一万英亩的农田、刺槐,以及干旱……当我意识到我们所在的这块台地实在太高、不适合种植咖啡时,一切都已经迟了。我相信,那里的生活很像十八世纪的苏格兰:赚钱很难,但生活在很多方面又很富足,美妙的风景,几十只马和狗,还有众多的仆役。
《巴黎评论》: 我想,你是在那里开始认真写作的?
迪内森:
不,我在去非洲之前就已经开始写作了,但我从没想过当一名作家。二十多岁时,我在丹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评论鼓舞了我,但我也没继续写——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本能地害怕被困住。同样地,当我年轻时,我也在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学过绘画;一九一〇年我去巴黎跟随西蒙和梅纳尔学习,但(她咯咯笑)……但我基本没在学习。巴黎对人的影响实在太强大了;事实上,我觉得出去四处看看画展、看看巴黎更重要。在非洲我又画了一些,大部分是本地人的肖像,但每次当我开始画画,就有人走过来说有头牛死了之类的事情,我不得不去田地里瞧瞧。后来,当我内心里知道我不得不卖了农场返回丹麦,我这才又开始写作。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开始写故事。哥特故事集中有两篇就是在那里写的。但在更早,我学会了讲故事。因为,你看,我有很棒的听众。白人无法再听游吟故事,他们一直在瞎忙、烦躁不安。但本地人还愿意听这些。我一开口说“有个人,他有一只两个头的大象……”,他们马上就想听到更多,“哦?是吗,但夫人,他是怎么找到它的?他怎么喂它呢?”诸如此类的。他们喜欢这样的虚构。在那儿,我说话时押着韵,这让他们听得很开心;你知道,他们没有押韵的概念,从没发明出这个。我会这么说话,Wakamba na kula mamba,字面意思是“坎巴人
 吃蛇”,如果直接用大白话说可能会激怒他们,但押着韵说出来,他们就听得特别开心。后来他们会说:“夫人,求求你,像雨一样地说话。”我懂了,他们喜欢我的这种说话方式,因为“雨”在非洲十分珍贵。
吃蛇”,如果直接用大白话说可能会激怒他们,但押着韵说出来,他们就听得特别开心。后来他们会说:“夫人,求求你,像雨一样地说话。”我懂了,他们喜欢我的这种说话方式,因为“雨”在非洲十分珍贵。
哦,斯文森小姐过来了,她是天主教徒,所以今天出去聆训一位特别的枢机主教的讲道。我们得去买些明信片,希望有那种狮子图案的。
斯文森小姐: 早上好。
迪内森: 克拉拉,你得去看看那些可爱的狮子;然后我们去买些明信片,再去午餐。
(明信片买到了,出租车也叫到了,雨伞撑开,我们一行人跑上出租车,穿过博尔盖塞别墅花园离去。)
瓦拉迪耶俱乐部是一家非常时髦的花园餐厅,就在人民广场的上方,俯瞰美丽的罗马城。在积满水的阳台上,我们瞄了一眼雨中灰蒙蒙的城市,随后进入一个锦缎装饰的房间,房间里有仔细用灯罩护住的枝形吊灯,还有颜色明亮的地毯及油画。
迪内森: 我坐这儿,这样就能看到一切。(点了支烟)
《巴黎评论》: 环境不错啊,是吧?
迪内森: 是,很不错,我承认。一九一二年我来过这儿。当年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我现时现地都能清晰地辨识出来。(停顿片刻)哦,我快疯了!
《巴黎评论》: (怔住了)怎么了?
迪内森: 看看那幅画歪得!(她指着房间那头一幅熏黑的肖像画)
《巴黎评论》: 我去把它摆正。(朝那幅画走过去)
迪内森: 再往右边一点。
《巴黎评论》: 这样?
迪内森: 好多了。
(肖像画下面的桌子,两位坐着的、表情冷峻的绅士有些困惑。)
斯文森小姐: 就和在家时一样!车流穿行中,我也要去把画挂正。
迪内森: 我住在北海边上,就在哥本哈根和埃尔西诺之间。
《巴黎评论》: 也许也在设拉子和亚特兰蒂斯之间。
迪内森: ……也在《暴风雨》中的岛屿和我身处的无论何处之间。
(服务员来点菜;提供午餐服务。)
迪内森: 我得抽支烟。你不介意我们在这里多待会儿吧?一旦在喜欢的环境中安顿好了,我就不想再动。人们总是叫我快点,来吧,干这干那。有一次我们坐船绕过好望角,我看到一只信天翁,身边人不断在说“你待在甲板上干吗?快进来”,又说“午餐时间到了”。“该死的午餐!”我说,“午餐哪天都有,但我再也看不到一只信天翁。”
它展翼时多漂亮啊!
《巴黎评论》: 再谈谈你的父亲?
迪内森:
和我祖父一样,他加入过法国军队。普法战争之后,他去了美国,在你们国家辽阔的中部和平原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他为自己建了一座棚屋,用他年轻时在丹麦度过欢愉时光的一处地名命名它——“弗吕登伦”
 (意为“快乐的坟墓”)。他狩猎,同时也是一名皮货商。大部分毛皮他都卖给了印第安人,再用获益买礼物送给他们。在他身边渐渐形成了一些小团体,我相信,现在弗吕登伦已经是威斯康辛州某个地区的名称。返回丹麦后,他开始写书。所以你看,作为他的女儿,我去非洲和当地人一起生活,然后回到丹麦写下这些,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儿。顺带着,他还写过一本战争经历的书,书名叫《公社之下的巴黎》。
(意为“快乐的坟墓”)。他狩猎,同时也是一名皮货商。大部分毛皮他都卖给了印第安人,再用获益买礼物送给他们。在他身边渐渐形成了一些小团体,我相信,现在弗吕登伦已经是威斯康辛州某个地区的名称。返回丹麦后,他开始写书。所以你看,作为他的女儿,我去非洲和当地人一起生活,然后回到丹麦写下这些,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儿。顺带着,他还写过一本战争经历的书,书名叫《公社之下的巴黎》。
《巴黎评论》: 你用英文写作感觉如何?
迪内森: 很自然,就是这样。我曾经接受过家庭女教师的一部分英文教育,后来又在英国的学校里短暂地待过。也因此,很多别人觉得正常不过的新词汇我都缺乏起码的了解。但这些家庭女教师都野心勃勃:她们确实在教授语言,其中一位就让我把《湖上夫人》翻译成丹麦文。在非洲,事实上我只能见到英国人,所以我讲了二十多年的英语和斯瓦希里语。我读英文诗和英文小说,尤其是那些年长的作家的作品,但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赫胥黎的《铬黄》时,就像咬了一口不认识却异常新鲜的水果。
《巴黎评论》: 你的大部分故事都设置在上个世纪,对吧?你从没写过现代的故事。
迪内森: 我写过,如果你认为我们祖父母那一代,一个刚刚远去的年代,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分的话。我们吸纳了(过去)太多,自己却意识不到。另外,我写了很多人物,他们和故事是一体的。你看,开始我会以故事的风格开场。然后我找到人物,他们会接管整个故事。他们设计故事,我只需批准他们的主动性。而在现代生活和现代小说中,讲究的是环境和氛围,最首要的是人物的内心活动——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觉得在生活和在艺术中,本世纪的人们之间有点隔阂。孤独现在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但我会酝酿人物,看他们彼此相互作用、发生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对我来说很重要,你看,友情对我来说很珍贵,而我也受崇高的友情庇护。时间在我的故事中是富于弹性的,我可以从十八世纪开场,然后故事迅即来到“一战”期间。这些年代都已经被人梳理过,十分清晰。此外很多我们从其故事主题和出版时间判断为当代的小说——想想狄更斯、福克纳、托尔斯泰还有屠格涅夫——这些故事的背景都设定在更早的年代,或者讲述的是前一代人的故事。当下总是动荡不定的,没人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它……在我成为小说家之前,我是一名画家……一个绘画者,从不希望描画的对象就在鼻子底下,他会站远些,眯着眼来打量、研究一处风景。
《巴黎评论》: 你写过诗吗?
迪内森: 还是小女孩时写过。
《巴黎评论》: 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
迪内森: 草莓。
《巴黎评论》: 你喜欢猴子吗?
迪内森: 我喜欢艺术作品中的猴子:在画中,在小说里,在瓷器上面,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总是显得有些悲伤。它们让我紧张。我更喜欢狮子和瞪羚。
现在,我们在塞尔莫内城堡中央塔的胸墙上,城堡栖息在一座小山坡上,四周环绕着村镇,这里离北边的罗马大概有一小时半的车程。我们穿过一座护城河吊桥,攀上一列摇摇晃晃的阶梯,看到了残存的十四世纪的壁画。要塞塔内的墙上满是信手乱涂的字样和图画,是拿破仑的士兵被囚于此时留下的痕迹。涂鸦一直保存到现在,却笔触新鲜,恍若刚刚写成。我们走了出去,手搭在眼睛上遮挡阳光。下方,被金色和绿色覆盖的庞廷平原一直延伸到大海边,沐浴在午后明媚的阳光中。城堡下方数英里外,能看到豆田和桃园里正在农作的渺小人群。
《巴黎评论》: 我很好奇,美国和英国的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评论人士,都没有人指出你作品中的喜剧元素。希望我们能聊聊你的故事中的喜剧精神。
迪内森:
啊,你提到这个我太开心了!人们总会问我,故事中的这个或那个意味什么——“这个象征什么?那个代表什么?”我总是很难让他们相信,故事所表达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说的。如果对作品的阐释超出了作品本身,那就太可怕了。我的确经常试图呈现某种喜剧效果,我热爱笑话,我喜欢幽默感。“伊萨克”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笑声”。我时常想,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了不起的幽默作家。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笑声”。我时常想,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了不起的幽默作家。
《巴黎评论》: 英语里面有哪些幽默作家打动过你?
迪内森: 嗯,比方说马克·吐温。但所有我赞赏的作家通常都有某种喜剧精神的心绪。对写小说的作家来说,这是必须的。
《巴黎评论》: 哪些小说作家比较吸引你,或者,哪些人你会觉得亲切?
迪内森:
E.T.A.霍夫曼
 、汉斯·安徒生、巴贝尔·多尔维利、穆特·福开
、汉斯·安徒生、巴贝尔·多尔维利、穆特·福开
 、沙米索
、沙米索
 、海明威、莫泊桑、司汤达、契诃夫、康拉德、伏尔泰……
、海明威、莫泊桑、司汤达、契诃夫、康拉德、伏尔泰……
斯文森小姐: 别忘了梅尔维尔!《贝尼托·塞雷诺》之后,当她(迪内森)不再说我是桑丘·潘萨,她就用那本小说中的人物巴伯来称呼我。
《巴黎评论》: 天,你全读了啊!
迪内森: 我真的得有三千岁了,而且和苏格拉底吃过饭!
《巴黎评论》: 哈?
迪内森:
(大笑并点了一支烟)因为从来没人告诉我,必须读什么,以及什么不能读,我读了一切能拿到的东西。我很小时就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直到现在我还觉得,人生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则什么都不是。顺带说一下,我的一个新故事就是关于一群演员排演《暴风雨》的。我喜欢一些现在已经没人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比如沃尔特·司各特。我很喜欢梅尔维尔,还有《奥德赛》,北欧萨迦
 ——你读过北欧萨迦吗?我也很喜欢拉辛的作品。
——你读过北欧萨迦吗?我也很喜欢拉辛的作品。
《巴黎评论》:
我记得《冬天的故事》中的一篇,其中有你对北欧神话的看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顺便问一下,你怎么选择故事的形式?
。我觉得很有意思。顺便问一下,你怎么选择故事的形式?
迪内森: 它自然而然就来了。家中的文学朋友跟我说,我的作品的核心不在于理念,而是故事的行文本身。有些你是可以讲述出来的,有些不行,就像你可以讲述《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但你无法讲述《安娜·卡列尼娜》。
《巴黎评论》: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你的故事,比如《诺德尼的洪水》(1934),这样的故事是怎么成形的?看起来一切有序且必然,然而经过深究我们会吃惊于这种故事中又嵌入故事的设计。
迪内森: (畅快地大笑起来)读,再读,你就会发现它是怎么写成的。
作为结语,我想摘录布里克森男爵夫人作品《阿尔博多卡尼》
 中的几段,这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故事,直到作家一九六二年辞世时也未完成。摘录节选自《空白页》,一九五七年以《最后的故事》为题出版。一个靠讲故事为生的老妇人说道:
中的几段,这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故事,直到作家一九六二年辞世时也未完成。摘录节选自《空白页》,一九五七年以《最后的故事》为题出版。一个靠讲故事为生的老妇人说道:
“在我祖母那里,”她说道,“我经受了严格的教育。‘要忠诚于故事,’那个老魔女告诉我,‘完全地、坚定地忠诚于故事。’‘为什么我要这么做,祖母?’我问她。‘我难道是用理性和经验把你滋养长大的吗?’她叫嚷道,‘你注定要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为什么你要变成一个讲故事的人,我来告诉你原因!听着:如果一个讲故事的人忠诚于故事,完完全全、坚定不移地对故事保持忠诚,那么,到最后,沉默就会说话。而如果故事被背叛,沉默就只是空洞而已。我们这些忠实之徒,当我们说出最后一个词,就能听到沉默的声音。不管你这个流着鼻涕的小姑娘听不听得懂,就是这样。’”
“‘那么谁,’她继续说道,‘谁能比我们更好地讲出一个故事?沉默。在哪里能读到一个比印在最珍贵的书中最好的纸上的故事还要深刻的故事?只有空白页。当一支忠实的、勇敢的笔,在它灵感迸发到最高点的瞬间,以最珍稀的墨水写下它的故事——那么,在哪儿还能读到一个比这故事更深刻、更甜美、更快乐和更残暴的故事?在一张白纸上。’”
(原载于《巴黎评论》第十四期,一九五六年秋季号)